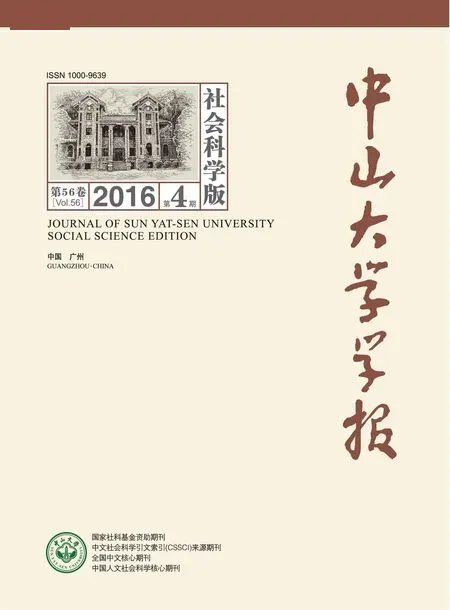晚清岭南文化传承的自觉与乡土认知的新变*
——以《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为论述中心
翁 筱 曼
晚清岭南文化传承的自觉与乡土认知的新变*
——以《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为论述中心
翁 筱 曼
摘要:《南海百咏》在晚清岭南得到广泛传播和极高关注,相关的追和、续和作品层出不穷,与乡土地理志编修的风潮互相呼应。通过这种艺文作品与地理注释结合的诗歌地理志形式,历史的人与事能因“地”(古迹名胜)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保存;而相应地,“地”也因人和事而彰显,成为历史情感与乡邦记忆的承载,并深化人对地域、对国家的情感。通过对《南海百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体内涵的阐释,返观《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及相应学术现象,这股社会学术风潮反映出晚清岭南地域文化传承的自觉,进而折射出内忧外患、社会结构变动中的晚清中国,在家国观念的重新建构过程中,“乡土”认知与内涵的丰富。
关键词:文化传承; 《南海百咏》; 乡土; 家国; 自觉
建筑、山水,因其相对的稳定与恒久性,成为人与地域之间最有代表性的审美中介。历代文士透过建筑和山水这些审美中介所抒发的情感以及相关的史地性记载,以文字的方式,将历史信息与记忆封存在建筑与山水之中,营构出一处富含诗意而笺证历史的空间。这种文字记载,通过隔代的追和与续写,不断丰富与推进历史记忆,从而凝聚为地域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同为审美感应的文字记载,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传统内涵,可以窥见时代风潮与地域的文化风貌,亦是地方认同的深化与演变的过程。异代的同题阐释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学术推进与转变的认识。
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是一部以南宋时南海山水建筑为咏叹对象的诗歌地理志,此书作于南宋,镂刻行世于元,直至晚清,在岭南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续和追和之作频现,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有其时代的必然与偶然性,折射出晚清岭南文化传承意识的自觉与地域观念的凸显。我们通过对《南海百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体内涵的阐释,返观其晚清流播及相关学术现象,并结合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内容以及追和续和的情况,兼及彼时岭南学界的地理志编修风潮,更延伸至民国时“新学”对地方教育的大力鼓吹,对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家国”观念重构以及乡土认知新变进行探讨。
一、《南海百咏》简介
《南海百咏》的作者方信孺生于兴化军莆田地区(今福建)的方氏大族,理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曾祖及祖皆有名于时。父崧卿,登隆兴癸未进士第,任广西转运判官时卒。因此,方信孺荫补番禺尉,时年方二十初,从此踏上仕宦生涯,《南海百咏》应作于番禺尉任上。“南海”当指南宋时期广东南路广州,南宋绍兴后,广州置八县,即南海、番禺、增城、清远、怀集、东莞、新会、香山*《宋史·地理六·广南东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后来,嘉定元年(1208)方信孺任通判肇庆府,三年(1211)又知韶州,皆在广东境内,与南海大地结下不解之缘。
(一)《南海百咏》及其版本
方信孺好游山水,对南海山水兴致盎然,曾入罗浮一月不归。他不畏辛苦寻访古迹,征之史籍,并以古迹为题吟诗,每题之下皆有小注,对此古迹的由来及与之相关的典故、民间传说、诗文记载作进一步的描述,其注解甚为详实。明清以来涉及广东名胜古迹的著作多参考此书,如明代黄佐编修《广东通志》时便多处引用此书内容。略举例如下,借此一窥其百咏风貌:
南濠
在共乐楼下,限以闸门,与潮上下,盖古西澳也。景德中高绅所辟,维舟于是者,无风波恐。民常歌之,其后开塞不常。
经营犹记旧歌谣,来往舟人趁海潮。风物眼前何所似,扬州二十四红桥。*③方信孺:《南海百咏》,光绪壬午刊本,第6,14页。
小注将南濠的地理位置、繁华的景象、开辟之历史用寥寥数语便交代清楚,而诗歌的渲染与情感的抒发则与注释互相发明,让南濠不复存在的年代,后人仍然能够由此诗此注打开时光的大门,回到那段似扬州红桥那般景致的南濠时光。
又如《花田》此条:
花田
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弥望,皆种素馨花,一名那悉茗。南征录云,刘氏时,美人死,葬骨于此,至今花香异于他处。
千年玉骨掩尘沙,空有余妍胜此花。何似原头美人草,樽前犹作舞腰斜。③
花与美人是永恒的传说,方信孺既尽叙花田之美,又引《南征录》之南汉刘氏之美人葬骨传说,让花与美人一同谱写花田的历史。
此书较常见的版本是学海堂光绪壬午年刊刻的本子,书前有此书最初刊刻时叶孝锡作的序,书后有两位收藏者校勘后所作的跋文,记述了该书的流传以及对作者生平事迹和此书内容的考述,为我们了解此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分别引用如下:
南海百咏,大德间镂版行世,后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抄本,承伪踵谬,不无鲁鱼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订正之。今春苕贾钱仲先携一册至,点画精楷,装潢郑重,卷端有印章曰绛云楼钱氏,乃知为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观三日而校勘之功毕,因命学徒重为缮写,珍诸箧笥,视向之承伪踵谬者相去远矣。镫下对酒,辗卷欣然,因速浮大白而为之跋。时康熙己亥岁长至前三日,艾亭金卓识于城东书塾之碧云红树轩。*金卓:《南海百咏·跋》,方信孺:《南海百咏》。
信孺字孚若, 兴化军人, 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尉……是集乃其尉番禺时咏古之作, 每题各疏缘始, 时有考证, 如辨任嚣城非子城, 卢循故居非刘王廪, 石门非韩千秋覆军处, 皆足以正《岭表录异》、《番禺杂志》诸书之失, 不仅以韵藻称也……是集刻于元大德间,黄泰泉广东通志多引之,而吴任臣作《十国春秋》、厉樊榭作《宋诗纪事》皆不及见,则明季以来流传已少,故《四库》未著录,余从江郑堂先生假得钞本,爰为校正并稽其事迹,书于卷末云,道光元年五月嘉应吴兰修跋。*吴兰修:《南海百咏·跋》,方信孺:《南海百咏》。
由此可知,该书自元大德年间刊刻之后,流播十分有限,且没有重刻,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且错讹在传抄中增多。叶灵凤在《北窗读书录》中就提到他曾托友人辗转觅得本书,记述了基本的版本情况,认为明末时本书便流传甚少。《琳琅秘室丛书》第三集目录中写道“阮相国于嘉庆中始得其书,进呈内府,故四库书目未曾著录也”*胡珽辑,董金鉴续校:《琳琅秘室丛书》,光绪十四年本,见《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叶灵凤的判断。收藏者金卓以钱谦益绛云楼藏善本校对过的抄本后来应该归江藩所有,直至江藩随阮元来到广州时,吴兰修方有机会假得钞本,校勘后将之收入《岭南丛书》,于道光辛巳年行梓于世,而后光绪壬午年学海堂又重新刊刻,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扩大了此书的流传*《南海百咏》2010年刘瑞点校本的前言对《南海百咏》的版本有详细而精到的梳理,认为该书现存的《宛委别藏》本和《琳琅秘室丛书》本以及丛编本、国图本等等,皆出自甘泉江氏影钞原本,而元大德年间的刊本则是各本的共同祖本。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前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二)《南海百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体内涵
地名百咏,以百篇之结构涵盖一地风土的大型组诗,在宋代已经颇具规模,除了《南海百咏》,其他如曾极的《金陵百咏》、许尚的《华亭百咏》、张尧同的《嘉禾百咏》、阮阅的《郴江百咏》,都可说是开一地先河的作品。
针对南宋地名百咏组诗兴起的文学现象,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其滥觞、演变与时代、学术等因素密切相关。
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土壤,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宋代是一个重儒尚文的时代,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以及《册府元龟》的编纂,既是立国之初典章制度与图书典籍重新整理之举,亦由上而下带动起一种崇尚文化、倾心学问、以资鉴戒的社会风气。在蓬勃发展的教育和图书出版的有力推动下,宋代士人形成了追本探源的学术精神,尚理、尚史、尚博以“资鉴”的意识深入人心。其次,屈辱的亡国历史,山河的沦陷,民族危机的如影随形,极大地刺激了南宋士人,原先习以为常的一切,瞬间不再,因此产生了一种惧怕人事变迁而力求详细记录,以文字将当下所见所闻所感所知所及定格的焦虑心态*参见刘芳瑜:《地志与记忆:南宋地方百咏组诗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第79—80页。。
从文学学术发展的角度来定位地名百咏这一兼具诗文与地志功能的文体,有学者认为《南海百咏》因应了“文学地志化”的潮流。“文学地志化”的概念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家们将地志编撰中的结构、视角、功能、注释模式等原则和方法,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的创作实践中,这为南宋以后地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因此,宋代地名百咏呈现出以下特色:(一)较鲜明的纪实色彩。创作者翻阅大量典籍,实地采风,确保作品有较强的纪实性。(二)较深入的微观视角。与宏大的正史叙事不同,地名百咏是从某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角度切入来进行创作。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历史社会信息的细节补充。(三)开拓诗歌的题材和创作模式。百咏彼此间关联性较强,具有较好的结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所强调的,不只是简单的作品排列和叠加,还有更多层次,更广视野的整体观照和把握。换句话说,在风土作品所包含的地方知识信息的结构建架方面,宋代地名百咏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参见叶烨:《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南海百咏》的产生,体现一个核心观念及相关的导向,这个核心观念是“地方”。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修齐治平”的最终指向是天下,“国”是凌驾于“家”的。因此,以往不是没有“家”,也不是没有“地方”, 只是此“地方”非彼“地方”,以往的“地方”都是相对于中央的政治区域意义上的“地方”,其内涵是行政区划或者方位名词。美国汉学家包弼德曾提出“地方”的兴起,认为南宋以降,“地方”的观念变成士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包弼德著,吴松弟译:《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0—451页 。在两宋以前,“没有太多的乡土指向,而到了宋代,人们对地方的理解已经有了边界意识,对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也有了更深刻的区别和认知”*叶烨:《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正如前文谈到的,社会外因进一步加深了“地方”的认知,当时代裂变,国土沦丧,“南宋士人对于个人生存空间与国家疆域的剧烈改易,在检视新居地的同时,促使自我反观原有生存空间与改换后生存空间之间的差异,必定是极为切身之课题;不同立场、身份之人在重新定位自我与空间关系的过程中,在空间上对‘家’与‘国’之认同势必也有所调整,而呈现出认同多元且复杂的特性”*刘芳瑜:《地志与记忆:南宋地方百咏组诗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第70页。。由“国”到“家”,他们将目光转向了身边的家乡、宦游的任所、行旅的山水,在吟咏的同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与情感空间的定格。因此,当方信孺来到南海,也不辞辛劳踏遍山水古迹,着力创作打上时代以及他本人印记的南海胜览。正是在认识了不同的“地方”,在宋尤其南宋以来士人更为频繁的旅行、互动交流中,在家乡与他乡的比照中,在自我与他者的相反相成、相互建构中,认识了他者,更认识了自我,家国观念完成了新的阐释。
“地方”观念的浮现与深化,还推动了对一方风土记忆有意识建构的进程。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看法不同于“空间”、“场所”、“区位”等概念,其意指“人有主观与情感依附的空间”。 巴舍拉的《空间诗学》,将家视为人类接触的最早世界或最初宇宙的最初空间,所以“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方”,人们在此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家往往塑造了往后我们对外在各种空间的认识,因而人对于熟悉的、养育的地方产生认同,即“地方认同”*参见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年,第15、42—43页;刘芳瑜:《地志与记忆:南宋地方百咏组诗之研究》,第69页。。方信孺并非南海人,在广东为官期间,其对当地山水的吟咏遨游,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对岭南的“地方认同”*关于“地域意识”,可参见拙文《古代诗学视境下的“地域意识”——以岭南地域诗学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而是“文学地志化”潮流以及地方文人书写权强化的驱动。虽然如此,其客观上却开启了有意识地对岭南风土人情进行构筑的地域文化传承行为,对后世的岭南文化建构产生了影响。此前对地方风土人情记载与描述的文字并非少数,包括许多贬谪而寓居岭南的诗人,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诗篇,然而,有意识去进行地方风土人情建构的,却应是在“地方”观念出现之后。寓粤诗人的风土诗篇“以景写心”的程度更深,而方信孺的百咏,以景写景,有意识地去记录与景物有关的资料,为南宋时期的岭南风物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此交相呼应的南宋地方志编修热潮。南宋朝廷吸取历史教训,要求各州撰修州府图经以备战时所用,激励了“近时州郡皆修图志”*周辉:《清波杂志》卷4《修图经详略》,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3页。的热情,“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纪录焉”*黄岩孙:《保佑仙溪志·跋》,收录于《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33页。。这些方志在编修时大多由地方州县学教授和郡人执笔,方志除了介绍地方基本自然情况与历史外,还大量摘引笔记杂录和诗赋题咏,甚至设专门加以收录,体现了更为浓厚的地方色彩,可谓当时编纂地方志的一种新旨趣*参见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具有宣传地方特色且实施教化的功能。因此,方志编纂对于地方士人的“地方认同”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
前文述及《南海百咏》版本情况时已经对该书在晚清的流播做了介绍,笔者以为除了版本带来的传播信息,他者的接受亦是重要的流播体现。《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离不开当时岭南的学术阵地学海堂及围绕着学海堂所形成的文人群体的有力促动。这种促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学海堂以此书作为课士的题目,可以说是把《南海百咏》当成了学海堂的教材;其二,有关此书的追和续和,以学海堂学长樊封的《南海百咏续编》最为突出。
学海堂办学初期即定下了课士的基调与原则,历届学长皆谨守之。在课卷结集出版的《学海堂集》一至四集中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学海堂一集的典范性尤为凸显。《分和方孚若南海百咏》一题即出现在学海堂一集之中,题目之下有小注曰:“按孚若百咏皆有小序,引证详敷,今备录之。原作七绝,兹和以七古。”*阮元编:《学海堂集》卷1,道光五年刊本。可见彼时此书尚不易得觑,故备录编者认为学术价值高的小序。此题具有浓郁的岭南历史意蕴,将宋人眼中的南海古迹一一道来,兼以地理注释考证和典故、民俗的记录,后之人读之,无不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带着历史的幽情去触摸这片土地曾经的记忆,从而使阅者、和者心中对乡土的深情,得到释放且产生共鸣。后来学海堂又先后以《续和南海百咏》,《分和宋方孚若南海百咏》为题课士子,分别限以五古和七律,同题而限以不同诗体,既是诗歌创作的锻炼,又是乡情教育的绝佳范本,体现了学海堂在课士时深化地域文化感应的意图。
学海堂以此课士,持续时间长,传播的范围广,士子于课卷之外又别有追和、续和之作,散见于各种个人诗集文集之中。不仅如此,学海堂人在追和、续和之外,还进一步表达对《南海百咏》的认可,学长樊封的《南海百咏续编》便是另一种形式的隔代追和。该书体例与《南海百咏》相仿,依然是对古迹的地理和历史陈述,诗歌吟咏,再加以注解;分为4卷,共有8类,卷1名迹、遗抅,卷2佛寺、道观,卷3神庙、祠宇,卷4冢墓、水泉。在该书的序中,樊封谈道:“考据者嗜古而略今,咏歌者守近而忽远。躬际明良,目摩简素,虽小撰著,须益于时……读先子之遗书,耳邦人之习谚,幽光可颂,畸行堪悲。恒惧其久而就湮,更虞其讹以传讲。会戴醇士学使山堂课士,以‘南海百咏续编’命题,一时俊髦咸效孚若。凡属陈迹,争事网罗。因仿厥制,稍为变增,晰以子目八门,都为小诗两卷,广辑近闻,附诸细注。诗虽咏古,注实传今……邦国掌故,安可诬也。志乘蒐罗,或有取焉。道光丙午朴学山房主人录。”*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叙录(全文底本无,据扬大本补),第145页。可见本书的创作目的在于传承地方文化。
《续编》目前笔者所知所见有三种版本,清道光二十九年刊本,光绪十九年学海堂刊本,清末王宗彝抄本。书前有道光刊刻时张维屏和黄培芳的序,两位岭南文坛名宿都给予了此书极高的评价。引张序如下:
维桑与梓,聿垂恭敬之文;某水某邱,用识钓游之地,而况事关家国、义系纲常、迹合幽明、典兼文献者乎?此吾友樊子昆吾续方孚若《南海百咏》所以为必传之作也。昆吾铁岭世家,穗城老宿,诗探五际,学贯九流,以其暇日乃著斯编。考地志之自为注解,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地志之自为诗歌,见于迺贤之河朔访古。是编参其体例,加以变通,句定七言,条分八类,诗必有注,注必求详。思古贤而凭吊,如闻楚些之歌……披览兼旬,率题俪语,道光己酉腊月番禺张维屏。*张维屏:《南海百咏续编·序》,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第144页。
作为彼时羊城举足轻重的学人领袖,张维屏对此书“事关家国、义系纲常、迹合幽明、典兼文献”的认定以及“必传之作”的极高赞许,即便有学人间相互推举之嫌,樊封作此续编的功力与价值亦足见一斑。兹举《续编》中的《黄木湾》和《萝岗洞》为例:
黄木湾:在郡东波罗江口即韩昌黎南海神庙碑所称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所矣。
黄木湾头寄画桡,高荷大芋接团焦。怪他蠏舍春风紧,莺粟花开分外娇。
阿芙蓉即莺粟蕊浆和砒石而成者也,夷人特以流毒中原,其祸至烈。圣天子仁育万类,欲挽浇风起而禁之,诚转移之大机。而奸商狃于肥己多方挠乱。大司马莆田林公竭尽忠诚,卒之鲜济兹,则斩山为屋,架树成村,百弊丛生。阿芙蓉之毒不止,遍布东南已也。*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第167页。
萝岗洞:在郡东八十里,危峰四拱,一径通人,中亘数十余里,咸膏腴佳壤,烟村星错,皆莳梅种荔为业,洞内有萝峰寺、玉岩书院,堪停巾车,冬梅盛开,晶玉廿里,真同香雪海,粤人多往游焉。
石发林霙滑马蹄,东原小猎玉岩西。风流四镇归何晚,鞍上梅花月里鼙。
平王镇粤,每届隆冬必躬领将卒围猎于郊坰,虽非从禽,然借以驰驱习劳,亦国俗也。时藩下有四总兵,卢可用、班际盛、田云龙、张国禄,最握权要,分班列队,呆鞬乘骑以侍王猎,日暮必会于看城,烹鲜行酒,赏梅为乐。今洞内犹有尖屯卡伦故址,而尚王之放鹰台,里老犹能指其处也。*②③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第169,212,248页。
上引内容既有历史之记载,又有当下之描画,更通过今昔对比联系,进一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如黄木湾一条,谈及阿芙蓉也即鸦片,樊封痛陈鸦片之流毒,也极赞林则徐禁烟之举,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广州士人对鸦片的态度,而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环境下,“经世致用”的文风以及士子对国家大事、社会情势的关注。
对诗歌的注释,实际上是对与名胜古迹相关的历史典故和传说的进一步阐释,用更为直观和生动的历史故事来还原历史的记忆,使阅者如临其境。上文描述萝岗洞的文字简洁而动人,不只是一般的介绍性文字,而带有散文般行云流水的优美。不仅如此,作者还在介绍中放进其他同时代的文友甚至自己的一些活动,使文字更加亲切、真实,另一方面也因之保存了不少士人交游的资料。如卷2《安期仙祠》和卷4《君臣冢》:
安期仙祠:诗人张南山、黄香石、林月亭、段纫秋七人,于观左别筑南雅堂,广植名花奇卉,胜结吟坛,补禊消寒,殆无虚日,伊墨卿太守为南雅堂记,镂石于壁。②
如果说方信孺所记录的是宋时南海负有盛名的古迹名胜,樊封的《续编》选录的古迹名胜也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学海堂课题中不少拟作课题,所歌咏的主题多是当时有名的游览胜地,有不少与樊封《续编》中所选录的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发明。如二集《黄木湾观海拟孟襄阳望洞庭湖》、《越台怀古拟高常侍古大梁行》、《游六榕寺拟韩退之山石》、《拱北楼铜壶歌》、《罗冈洞探梅》*“萝岗”与“罗岗”常通用,此处以原文为准。,四集的《绝武君臣冢》等等。因此,我们认为樊封的《续编》以及其他士人的同题作品是对《南海百咏》的隔代追和与延续,也是《南海百咏》流播的重要体现。
三、《南海百咏》的选择与被选择
返观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某一部作品的流播以至成为经典,在选择与被选择中都充满了必然与偶然的各种因素。也许可以不是《南海百咏》,而是其他某一部同一类型的诗文地理志来扮演其角色,但《南海百咏》的后世流播恰正反映了这本书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时间轴上与地域文化传承、与晚清学术风尚的契合。
(一)《南海百咏》的纵向呈现:地域文化传承
由宋及清,沧海桑田,方信孺与樊封,二人以隔代的同题呼应,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变动着的南海大地景致,在时空的穿越中,流淌着文化的默契。这种默契,根源于地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而其呈现方式,则体现为诗文与山水古迹所营构的绵延不绝的地域文化空间,即是境与诗文的交织,境与人文的交织。
方信孺之友叶孝锡在《南海百咏》序中写道:“境以诗名,在在皆诗也……方君来尉番山,剜苔剔藓,访秦汉以来数百年莽苍之迹,可考者百而缀以诗,可见胸中磊落,使其乘飞廉,凭丰隆,翱翔乎氛埃之上。”此序不仅阐明了方信孺创作此书时实地勘考之艰辛,亦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境”与“诗”的相依并存之关系,山水古迹之成为一地名胜或某地象征,诗文是重要的推动力,而相应的地域文化空间,则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方信孺与樊封隔代呼应的媒介。
世易时移,方孚若与樊封,二人的视角,二书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呢?南海大地的人文空间在二人的笔下又有着怎么样的改变?
方信孺所记载的古迹,大多与南越、南汉相关,尤其是短祚的南汉王朝,虽然历时才五十余年,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帝王也是花招迭出,留下了很多悲惨的、骄奢的、香艳的、奇异的故事。也许药洲已找不到炼药的丹炉,只剩下不会说话的石头;也许刘王花坞早已没有夹岸而生的鲜花,土里只残存当年妃子、宫女嬉戏跌落的发簪,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传闻,始终缠绕着这一空间,从而转化为南海百咏中永不磨灭的文字。对于清末的樊封而言,南越、南汉是极为遥远的时空了,即使是明末的南明小王朝,清初平王镇粤,也渐渐在世人的记忆中淡去。樊封所选取的古迹,有一些是宋以前的古迹而方信孺没有记载,而后因为新的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新的意蕴,譬如旧迹新筑;其他宋以后形成的名胜古迹,或因人而名,或因事而显,有很大部分内容与南明和清初那段时期紧密相关。如靖王府、平王马圈、靖王马圈、备调军装库、铁局、怀远役等等,还有一些是甚受时人喜爱的名胜景点,所述内容下延至道光年间,则又具有了近代史的史料意义。
从注解之详敷来看,樊封比方信孺更为精审,力求完整地、清晰地呈现该地的过去与当下。他在书的序言中也提到“盖前编之咏,藉证耳闻;斯录之收,多凭目验”*方信孺、张诩、樊封撰,刘瑞点校:《南海百咏 南海杂咏 南海百咏续编》,叙录(全文底本无,据扬大本补),第145页。,强调其真实性更胜方信孺之《南海百咏》。方信孺的注解多引用《岭表录异》、《南征录》等书,有些古迹注解略显简单,但是在当时关于南汉的历史记载甚为简略的情况下,方氏能对古迹作比较精确的注释,相关历史典故和传说也较为详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见作者经过了深入的调查和寻访,作出极大的努力。由上文所举《黄木湾》和《萝岗洞》,可见樊封则更为注重名胜古迹的现时状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内容和环境。总的来说,樊封更注重当世价值,自觉地纪当代史,而方信孺则较侧重纪古代史。有学者指出,随着“文学地志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文学作品中对中小地区社群的地理、文化面貌的描绘越来越多,以致有时候文学只剩下一个躯壳,实际内容已是对地域历史、地理信息的介绍和建构”*叶烨:《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第101页。。这固然是极端化的比方,但正说明了从方信孺到樊封,正是一个文学发展循序渐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方信孺和樊封都将他们所看到、听到、问到的内容呈现于文字之中,或翔实记载,或动情歌咏;都关注古迹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追古思今。他们将南海大地的历史时空连接了起来,营造出更富有内涵和时空感的诗意空间。如果说《续编》与《南海百咏》之间带有历史的层积性,樊封从纵向的历史链条上承接方信孺记录南海古迹的使命,那么,元代吴莱的《南海古迹记》、明代张诩的《南海杂咏》、明代南海郭棐的《岭海名胜记》,如此种种与南海名胜古迹相关的著作,都是这一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文我们分析过,《南海百咏》因应着“文学地志化”学术潮流以及南宋时地方文化书写的有意识建构,这种建构也深层地体现了古代文人的“立言”心态。樊封对《南海百咏》的追和,除了当世意识的加深,通过地域文化构筑使自己成为地域文化链条的一个节点,更体现出这种建构以及文化传承的自觉。张维屏说樊封之续《南海百咏》“为必传之作也”,虽然意在指出樊封之续编文质彬彬,于史有补,重要性自不待言,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樊封与书同传的深层期望。诸位学人或为专书或仿而作诗以和,固然是寻前贤之源而前行,而今日之举,亦可成为他日后辈学人之源,自己亦可随之留名后世。重要的是,学术链条因之而延伸,集体记忆、地域文化也能够波澜不惊地传递下去。
(二)《南海百咏》的横向呼应:晚清学术风尚
纵向的历史链条延伸为我们搭建起时光的经度,如果从横向的社会风尚契合来进一步剖析,则纬度的营构可以使这一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
嘉道时,诗歌地理志或乡土地理性质的著作编撰呈现出相对集中而且备受学人重视的态势。
首先,围绕着《南海百咏》,除了刊刻重梓,以及樊封的《续编》、学海堂学子同题课卷的追和续和,在《广州城坊志》中还提到“陈昙《补南海百咏诗》自注引李士桢《街史》云:‘亚荷塘在东门内,宋周茂叔为提刑时种莲处,后人转为雅荷塘,又讹为阿婆塘……’”*黄佛颐编纂:《广州城坊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陈昙是当时备受赞誉的诗人,也是学海堂肄业生,这条记载既说明陈昙熟悉且认可《南海百咏》,不然不会有“补”之举,而且其诗自注也带有《南海百咏》古迹介绍的意味*方濬颐:《二知轩文钞》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此外,莅粤为官,与粤士人交往甚密的方浚颐,仿南海百咏而作五言诗,其小注云:“乙丑冬日仿吾宗孚若先生作南海百咏五言诗,取其考证以成韵语,体虽不袭,义实相沿,非敢谓于诗境之外另开一境也。亦聊见前贤门户,后人尚有寻源而至者尔。”或以此为题,或续和、补和,这样的诗人诗作在元大德此书刊刻之后当为数不少。根据现在所见资料,至少可以肯定,到了嘉道年间,《南海百咏》受到的重视是比较明显的。
其次,异曲同工的相关著作卷帙颇繁,蔚为大观。如与学海堂人交往密切的邓淳,他所编纂的《岭南丛述》内容十分丰富。列目40,釐卷60,共有24册之多,内容遍及岁时、舆地、群山、诸石、水道、礼制、文学、武备、服饰、宫室等方面。
略往前追溯,乾隆时陈兰芝编辑刊刻的《岭南风雅》也较有代表性。此书分3卷,每卷分上下,是为广东地方艺文总集。初集之前编列各种文体及其阐释,其后是岭海名胜古迹。在目录部分,古迹名胜下会有小注,或注明彼处之名由来,或注明彼处之特色,或注明所处方位,如刘王花坞,羊城西郭;华林,西来寺达摩初到此;秫波钓台,黎贞辞辟后筑,白沙有诗;坡公宅,惠阳春梦婆处;百花冢,才女张乔坟;荔支湾,南汉主燕歌地;马侍郎宅,香山宋端宗驻跸处;泷峡,文公为阳山令时信宿于此;越华楼,陆贾所居……该书意在保存历代广东艺文,然而视之为对粤中古迹名胜、鸟兽草木等资料之保存,亦不可谓不可。因为书中辑录的诗歌文赋,出注甚多,譬如第5册,卷2《石门贪泉有怀吴刺史》小注便将晋吴隐之清操一事及其后续的传闻一并记入;彩云轩,小注“在罗浮麻姑峰,麻姑常降此,至则彩云缭绕……”有借诗而存人存事存地,详述岭南风土人文、历史人物的意味。
陈兰芝以“吾粤古迹名胜,鸟兽草木”作为选编地方艺文的主干,附以地理方位、历史人物事件、风情民俗的注释,可见,吟咏古迹名胜的诗作可以成为向世人介绍吾粤风情的窗口,可以保留地理情况和历史资料,可以成为方志编修的借鉴和参考,更可以成为乡人深入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文本。这一点,与《南海百咏》、《南海百咏续编》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是相同的。而“古迹名胜”,通过这种艺文作品与地理注释结合的形式,使历史的人与事不仅仅是史书或地方志上略显单薄和严肃的文字,还能因“地”(古迹名胜)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保存;而相应地,“地”也因为人和事而彰显,成为后人游历和思咏的所在,成为超越时空的历史情感与记忆的承载。并进而深化人对地域的情感:乡人游之增其自豪与归属感,外乡人游之增其认同与体验,从而凭借“古迹名胜”的审美感应,产生地域的共鸣。
(三)《南海百咏》的异代阐释
《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可以说是该书的晚清阐释,或者说是晚清的学术及社会因素在该书流播上的折射。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晚清中国面临的挑战,“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卷2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25页。,丝毫不比南宋朝廷简单,不再是民族的相争,外国列强的枪炮彻底粉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地方士人在忧心国事之时,充满了文化流失乃至灭亡的焦虑,因此,汲汲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自觉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清末新政期间,政府大力推行乡土教育,地方的读书人编纂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作为初等教育的教材,用以培养青少年的乡土感情,或透过介绍地方物产来传播爱乡爱国的观念。如1909年出版的《潮州乡土教科书》,格致一科选取了诸多日常生活中惯常可见的事物,譬如“芥,气味辛烈,俗称为大菜,经霜而味益美,民家以盐蓄之曰咸菜,潮人以为常食之品焉”*林宴琼:《学宪审定潮州乡土教科书》第21课《芥》,汕头中华新报馆,宣统二年(1910)。。而《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则以游记体的形式,带着受教对象去游历他们所熟悉的、习见的,但也许并未深入了解的当地的建筑景观、风土人情。该书的编写独辟蹊径,“嘉应居广东之东,吾人爱慕乡土,不可不先事游历,今与诸生约,遍游一州,自城内始,后及于三十六堡”*萧启冈、杨家鼐编:《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宣统二年(1910)。。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当然颇有些“新学”的意味,但是在记录并传播乡土特色、培养乡土感情的方面与古代的各类地方志书并无二致。
由爱乡土而爱国家,对“乡土”的认知和对地域文化的热爱,正是对凝聚这一切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深爱。此时的“国”已不是天子的国,既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义上的“国”,体现了近代国家意识的萌发和过渡性的特征。文化的认知构成了“家国”观念重构的核心,而地方文化的认知与建构的自觉,奠定了这种重构的基础。
嘉道而下及至民初,围绕着《南海百咏》一书而延展开去的乡土地理志编撰之风,对地方风物尤其是古迹名胜的重视,固然与当时学术界的地理学背景、与国家受到内外挑战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然而更重要的是这股风潮之下所蕴含的人与地域之间审美感应的互动,在地域辨识和自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人与地的审美感应,面对古迹名胜本身,抑或面对与兹相关的《南海百咏》式文本,浑然而成的感情与体悟空间,既是个人的,自得的,灵动的,又在开启集体记忆的同时,延续和推进集体记忆,扩展为共同的集体记忆空间。因此,无论是方信孺,还是樊封,抑或学海堂中应答课题、补和续和“百咏”或其他古迹的士子,他们营构充满地域特色的诗意空间时是自我的,而后这一空间又成为共享的,成为其他人营构空间的起点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迹名胜有可能会有物理形态的转移,而精神形态的诗意空间,却能够在文化群体和历代士人的推动下,拥有更加活跃和茁壮的生命力。循学术链条而上,这股风潮与汉代杨孚作《南裔异物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精神,是地域宝贵的人文积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方信孺和樊封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这从某种意义上阐明了地域文化传承既是地域性的,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晚清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层次的变动,新的社会阶层萌发成熟壮大,旧有体制观念遭遇质疑颠覆重构,“家”与“国”的概念处于重新确立的过程中。 因此,“乡土”的认知方式与丰富内涵都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地域文化传承自觉意识亦逐渐鲜明。
在晚清的社会大背景下,以《南海百咏》的晚清流播所代表的文学文化现象,既沿袭了地域文化传承的传统内核,又呈现出具有现代意义的自觉意识,折射出晚清中国传统文明深层变革的未来走向。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收稿日期:2016—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研究”(12CZW058)
作者简介:翁筱曼,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006)。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