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上海
●张家康/文
陈独秀在上海
●张家康/文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始自上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表述,陈独秀在上海创建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由此发起各地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召开中共“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之前,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缘何由北京来上海,创立起如此开天辟地的功勋。

陈独秀
《新青年》和北大不相干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文科改革很不得守旧派人物的待见,《新青年》又是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在民国7年(1918)12月,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更直接、更快捷的方式,介入实际的时事政治,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更是予以坚决的鞭笞和批判。
这种无畏的战斗姿态,激怒了顽固的守旧派,林纾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漫骂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甚至表露出借重皖系军阀干将徐树铮压迫新派人物,以置之死地的心迹。
紧随其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通信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返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此,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舆论。于是,民国8年(1919)3月4日和6日,上海《申报》先后发表陈独秀被北大 “驱逐”和“辞退”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
胡适最先出来辟谣说:“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陈独秀紧接其后,在《每周评论》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而又不便正常辩论,只得让张厚载“闭着眼睛说梦话”,以中伤异己。他们没有别的本领,只能“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
北大校长蔡元培有意为陈独秀转圜,不愿陈独秀此时离开北大,他公开声明:“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作为惩诫,还将张厚载开除学籍。
与此同时,京、沪、浙、川四省市的14家报纸,发表了27篇文章,斥责林纾等守旧派,声援陈独秀等新派人物。舆论明显倾向陈独秀一边,封建官吏坐不住了,由后台走到前台。民国8年(1919)4 月1日的《申报》是这样报道的,参议员张元奇来到教育部,敦促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
陈独秀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在北大所受蔡元培的器重和呵护,一直感激不尽,而直面如磐的压力,他不愿蔡元培卷入其中,故郑重声明,《新青年》“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试图减轻北大和蔡元培的压力,然而却丝毫不起作用,北大内的顽固派与校外的舆论积极呼应,以内外结合的方式,非欲把陈独秀逐出北大不可。

蔡元培(左)和陈独秀(右)合影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北大放逐不羁之才
陈独秀在北大两年,文科改革已是成绩斐然,校长蔡元培极为满意。陈独秀自己也十分自信改革的成果,对于是否留在北大,其实心中早已有了主张,他对学生陈钟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的思想又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这飞跃的推动力来自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政治嬗变,由相信康梁到鼓吹民主和科学,这过程中的所有努力,换来的却都是理想的幻灭,就在他焦躁的越发看不到希望时,十月革命成功的范例,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把十月革命与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称作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且预言:“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作为一个言行统一的政治家,他已有投身这一“大的变动”的激情,至于是否留在北大,对于他确已是无关紧要。
驱陈风波一点也没有平息的迹象,而不胫而走的谣言却越传越广,产生出“三人成虎”的效应。在如此强势的舆论导向下,蔡元培也退却了,表示北大在下学期,文理科将不设学长,改由教务长“统辖教务”。厚道的蔡元培想以此,让陈独秀体面地离开学长的职务。
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因为,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在维护北大形象,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再无所为了。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私德太坏”,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动摇了。4月8日,校方提前发布消息,马寅初为教务长,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此夜之会,胡适因故没有出席,他对陈独秀的离去北大,一直心存疑惑。16年后,他阅读了汤尔和的日记后,对“以小报所记,道路所传”的“无稽之谈”极为不满,在10天的时间里,3次致信汤尔和,明确表示不相信那些谣言,认为那是“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他为蔡元培与汤尔和“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而惊诧不已。
多少年来,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离去北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乃至晚年,胡适仍然坚持己见,他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就在陈独秀到上海的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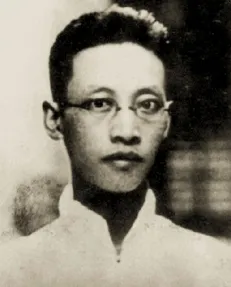
李汉俊

李达
陈独秀在上海结交新朋友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 “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民国元年(1912)赴日本留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并深受其影响,选择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自己所钟爱的数学。他还结识了戴季陶、沈玄庐,3人思想激进,志趣相投。民国7年(1918)秋,李汉俊回到上海。次年6月,戴季陶、沈玄庐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成为主要撰稿人。据统计,从《星期评论》创刊到民国9年(1920)6月终刊,《星期评论》所发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李汉俊的文章就有38篇之多。
民国9年(1920),李汉俊撰写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同年8月,陈望道翻译完《共产党宣言》,交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正式出版。次年,李达翻译 《唯物史论》,也多方请教李汉俊,李达在附言中说 “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帮助”。
中共早期党员对李汉俊评价很高,张国焘称李汉俊是“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董必武则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包惠僧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茅盾则感叹“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
可以这么说,陈独秀、李汉俊是上海这批搞政治的朋友的灵魂和核心。民国9年(1920)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回国。民国8年(1919)6月,他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年底,他回到义乌的乡村家中,闭门翻译《共产党宣言》。鲁迅曾这样称赞陈望道:“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新青年》因陈独秀而迁回上海后,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越益彰显,为此,遭到胡适等自由主义的北大同仁的质疑,并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口角之争。年底,陈独秀去广州任教育委员长,将《新青年》交由陈望道编辑,《新青年》更是积极译介大量的革命论著,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变化和成就。
民国9年 (1920)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
俞秀松(1899—1939),浙江诸暨人。民国5年(1916)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与施存统、宣中华、夏衍等创办《浙江新潮》。民国9年(1920)1月,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3月,经李大钊推荐,来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的工作。他和那一时代的许多青年革命者一样,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施存统(1899—1970),浙江金华人。民国6年(1917)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浙江新潮》的创办者之一,因发表《非孝》,批判旧伦理,而受开除学籍的处分。民国9年(1920),与俞秀松等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3月,施存统与俞秀松回到上海,栖身之所就是《星期评论》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民国6年(1917),东渡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在日本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给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民国9年 (1920)8月,回国来到上海,先找到留日时的好友李汉俊,然后又去拜见陈独秀,并在陈独秀家住了下来。他们的经常性的谈话很融洽、很投机,在组织政党、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沈雁冰,即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民国5年(1916),北大预科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与陈独秀相识,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老同盟会会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民国9年(1920)5月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中共一大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陈独秀的这些 “搞政治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李汉俊、李达分别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多早已认识,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又都是通过《星期评论》等交流思想。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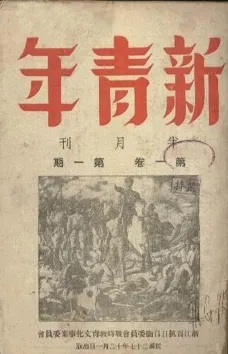
第一次亮出中共旗帜
陈独秀回到上海,先住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法租界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这里成为这批朋友常常光顾的场所,他们的组党活动多在这里筹划。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陈独秀最早注意到宣传和鼓动工人。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创办《劳动界》和《伙友》两份工人刊物,并且亲自撰写文章,为工人立言、说话,号召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正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民国9年(1920)11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随后,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会也相继成立。
陈独秀还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旧中国,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罗亦农遗孀李文宜曾在《忆罗亦农同志》中写道,罗亦农17岁时,因常读《新青年》,竟“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
这些青年来到上海,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他们学成后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
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完成帮助中国建党工作的报告里说:“我们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显然,“革命局”是个领导机构,报告并没有明确党的实际名称。民国9年(1920)9月11日,陈独秀在《对于时局之我见》中,几次将“社会党”与“吾党”交替使用。俞秀松于民国9年 (1920)6月的日记中,也把上海党称为“社会共产党”。
根据张申府的回忆,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就党的名称,征求过他与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 “就叫共产党”。民国9年(1920)11月7日,党的刊物《共产党》月刊出版发行,共产党一词这才明确于世。陈独秀作发刊 《短言》,明确表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也是11月,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公布的党的全名称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