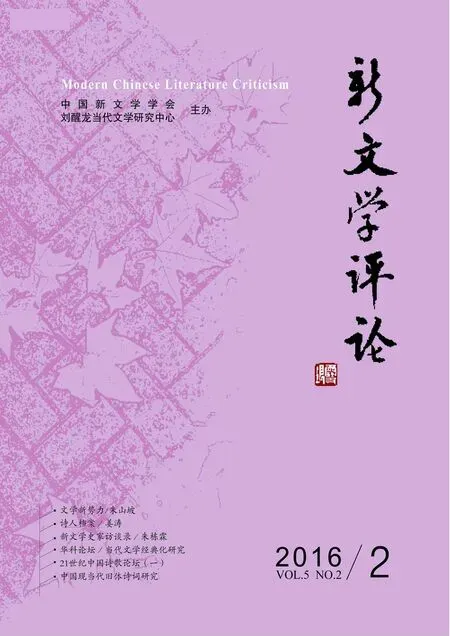郊区的自习室与窗外的鸟
———论姜涛的诗
◆ 王辰龙
郊区的自习室与窗外的鸟
———论姜涛的诗
◆ 王辰龙
一、由“怀旧”说起
过去之于当下,种种意义,不言则不明,遗忘的惯性,加速晦暗的蔓延。春风之下,万物生长,有关荒芜的体验与记忆,随之恍惚,都在意无意间。“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①张承志的反问,实是蔑视怀旧病,之所以是病,在于发热发狂,黑白颠倒,旧日中实际的衰败,经“青春无悔”“劫后侥幸”的笔墨,也升华为新生活到来前必然的阵痛,而是非曲直,久久搁置。各路前辈们,先是纷纷回忆八十年代②,继而争取七十年代的产权③,有得有失,生活史的细节,心史的曲幽,个体记忆丰富起来,也难免有后知后觉被虚构成早慧的痛楚。这状况及其历史性的缺憾,已是常识,但似乎不是后来者必须遵守的公约。更年轻的一代,已开始为1990年代提供各种文类的记忆,或许是由于这国度多年“灾变”在他们的童年期终将暂时减速,抑或是日常的连续性开始得到可贵的保证,因此,仅就文学书写,更年轻的一代,熟练操持“个体历史化”的方法论,对庞大事物保持审慎距离的,又在过于精致的时刻,显出千篇一律的疲态,开始为某些可复制的美学风尚所困。这亦是平安旧战场上的老问题,注定只有少数杰出者能够从中跌跌撞撞地突围,试图幸存,成为见证者。曾经拥有,只是基本前提,年过而立,继之不惑,重要的,是以哪一种意志进行书写,并能真正扩宽“怀旧”的意义边界。毕竟,在我们的时代,各个意义上的“过去”,太过重要,又太缺失,很多令人忧虑的喧哗,正源自暧昧地谈论“过去”。1990年代之于治文学者,重要性所在,是已到必须“走异路,逃异地”④的时段,对此,诗人钟鸣因痛切而又精辟地总结:“我个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像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似非常晦暗的,犹如骨鲠在喉。”⑤
新近,与记忆中的90年代相关的个人努力,有勇者之悲壮,是说康赫的长篇小说《人类学》。小说家重建千余页的记忆遗址,末了,主人公麦弓决意离开他为圆明园与北京大学(在小说中被刻意地以错位法则命名为“燕大”,正如著名诗人北岛也被称为“悲岛”)合抱的住处:“麦弓跨上自行车,从耳房飞快冲到温城佬家门口,灵巧地左拐,到了江西老表门前,紧接着一个右拐冲到了门槛前,身体稍稍后仰,提起前轮,越过门槛前的水泥疙瘩,立刻俯下身去,让脑袋顺利掠过门楣,腾起屁股,双脚踏紧脚蹬用力一蹬……看看最快速度骑到清河要多久,呜——顺坡而下西下坡,往圆明园方向飞奔而去。”⑥麦弓主动的加速度,在消费主义的逻辑看来,已然落伍,它试图更快些,却没有散步优雅,没有慢跑健康,而它又是迟缓的,显然比跑车与高铁慢。从这个意义来讲,当康赫用百万字将麦弓与北京城一起从上世纪90年代打捞出来,完成记录的同时,也以背向时间的方式与哀悼者的姿势,作告别与纪念。圆明园艺术家聚居地所表征的美学理想主义,以及“燕大”所指代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对二者,康赫亲身体验,保持警惕,并借人物进行象征式的疏离,而本文将要论述的诗人姜涛,缠绕他写作史的最初时空,便是康赫小说中的环境与气氛,从清华到北大,姜涛或许不止一次,曾与麦弓得以成型的各个肉身打过照面。亦如小说家笔下也有很多青年诗人的传说,秘而不宣,等待亲历者阅读时的会心一笑与五味杂陈。
做完如上交代,论诗之初选定《毕业歌》⑦,便是必要的。“毕业”的特殊,在于它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书写这时刻,是在评断即将过去的日子,由此,诗人将“怀旧”作为一种问题来看待:“怀旧即是走到原来的位置,脚跟并拢/在微风中感受增大的要为像麦浪起伏在时光中……”诗行间,逡巡于各种毕业期场景的目光,不含踌躇的感伤,置身其中又刻意疏远、游离的状态,透露出对意义的焦虑。已过去的,终归谈不上多么完善,甚至令人丧气。例如,对论文答辩这一学院生活的重要结点,诗人展示的,却是表情充沛、动作丰富的滑稽剧:“历史需要噱头,正如革命需要流线型发式/旁听的女同窗粉颈低垂,若有所思/她邻座的稻草人却已哈欠连天……当众人轻拍掌心以示首肯/唯有那只鼓吹过新思潮的笔/还在衣襟上汹涌向前、欲罢不能……”组成这幕知识生活场景的人们,似乎从未真正述说与倾听,他们各自独白,而他们的独白,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也像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知识殿堂的檀木结构,似已被空虚的、无聊的白蚁群所腐蚀,徒剩金玉其外,大学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重要公共空间的崇高性,因被质疑而可疑。即将到来的,根据已有参照,同样不尽如人意:“后来有人如愿以偿作了医生/在菊花怒放的季节用一张处方换来了艳情/有人违法乱纪,因殴伤饭店经理蒋门神/至今还在‘小西关’的高墙下服刑/有人已远走高飞,用两支波音翅膀和更多件衬衫/告别了雀斑、酒瓶、脏兮兮的单身宿舍/和北国腰肢柔韧的炊烟/回首往事,旧日的伙伴大都音讯杳然/一蹶不振的故乡拿不出新的花样……”时间的消逝之手,剥着生活的洋葱,核心秘密在被迫的泪流间,终究为“零”。象牙塔外,“广阔世界”也难以保证做出选择后生活能有多丰富,如《机关报》一诗,借工作空间的展开,暗示了知识者的可能出路,无非是创造性被抑制的平庸日常,全诗反讽语气中,有叹息在回旋:创造性则意味改变,在缺少流动性的社会机制中,改变则意味破坏。告别时刻的“怀旧”,因没有“去历史化”,便也去除了暖色的、温存的光晕,可能的晦暗,已有的缺憾,诗人对这二者的意识,促使“怀旧”成为当年歧路人试图理解生活的契机,他出于不解而惶惑,出于初解而忧愤。
写于1997年的《毕业歌》,是生活史的一次记录,它已预示出诗人日后写作中常见的手法,如以戏剧化的结构能力准确地提取场景,如游走于对外部世界的尖锐反讽与对个人生活的往复掂量,这些暂且不表,本文想强调的,是诗中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不能独善其身的位置:试图用语言对“变化”进行定位、定性,使之凝固为可把握的“不变”,或于“变化”中寻求某些“不变”的常量,却又无法保证自身不被裹挟其中。这一种主体位置的实感,可用逝者马雁在《北京城》中的诗句概括:“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⑧由此而来的挫败感,盖住了诗人有“怀旧”因素的作品,如《鸟经》:“记下的心事,有时也留在了床上/这都是往事了,不提了——/多希望你能飞过墙来再看看我/现在的我,看看我的新居和新娘/但什么星移斗转,人海沧桑的/其实,什么都没变/一山一石,我还是住在过去的沙盘里……”秦晓宇曾对这诗有妙论:“像李商隐写给女道士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般暧昧且深情。情爱的聚散也引发了他对时光的怅惘……他写《鸟经》,也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吧……”⑨类似的书写,往往感发于“风景异幻,人事难料”(姜涛《流金岁月》一诗中的句子),世事的无常,使诗句与诗句之间的时间感加速,也就是说,某一句触及的“变化”,迅速地被下文中实际的“不变”所截击;反过来,关乎世道人心的“变化”,又为很多基本面的“不变”所反扑。《固执己见》有一句:“新开发的山谷总会旧了、埋没了/新交的女友也会包容起三餐,变丑……”“变化”,是由新意转向陈旧,它的结果是“不变”,意识到这看似逻辑游戏下的悲凉事实,诗人便也在“怀旧”的同时免疫了“怀旧病”。“怀旧病”患者总是感伤地偏执于某些因常识、惯性与盲视而意义胶着的事物,而诗人的选择是观察事物之意义在进入具体情境时的跌宕起伏。心境投射出曲折的句法,结构上便呈现为连接词(如“而”或“但”)对诗意的推进,如“本来,计划妥当/在分叉的经济中,抽出一根枯枝/抽打这个下午暴露的臀部//但你说,要向生活的强者看齐”(《家庭计划》);如“F16低低飞过了浅海,亮出肋下/瘦长的导弹。我本以为/它会在某朵云的胸衣上,停留片刻/拖延一下本地的奇观/但相机吞下的还是旧店铺/和一排叉烧林”(《花莲》);如“阳光正好,树叶正红/一行人故地重游,提包里掖好/马蹄和换洗的内衣裤/而北风也前来凑趣,一五一十//供认参与了十年前的残忍。/但变化还是带来惊讶:操场挖成了/深坑,游泳馆也翘起水泥臀尖”(《缺根弦儿》);等等。

二、郊区的自习室



被提炼出的“传统”,转入写作实践,得自阅读的母题便常作为诗意的动机,不同社会的语境,往事与今生的对话,丰满着文本,扩展诗的容量,显然是想在历史认识论的层级上有所作为。如《伤逝》,鲁迅小说中“老师—丈夫”离弃“学生—妻子”的故事,经改写,成了当代男女的情爱传奇,结局是我们时代的子君出轨,不回到旧日子,不让涓生留遗恨,她乘坐的出租车所奔向的,是下一段关系。得到重描的,仍是家庭空间中目录般的琐碎,当代男女声称反传统,却似乎不脱启蒙期的旧窠臼,但也不尽然:鲁迅那里,冲突两端,一是启蒙新观念,一是帝国旧秩序;姜涛诗中,个体的自由,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当代常识,令人捉摸不定的是自由的真义,主动选择的意志与搁置永恒性问题的盲目,两者的界限,暧昧不明。相通之处,是知识者意愿中的日常,都与外部合围时显出脆弱。诗的结尾,似乎有别种意味:“同居不是坟墓,朝闻夕死的也好,/两人痛苦了一宿,黎明/相互安慰着分开/在出租车里,还用短信疯狂表白/但心里都在暗自庆幸/世界拆开了它的迷津/小说的封套中,影子却还说着回声……”戏剧性的场景中,真情假意混沌一片,末句的“小说”、“影子”与“回声”似乎在提问题:关系的失败,是否正由于全然遵从了现代知识体系制造的某些价值观?启蒙与革命,一体两面,都是现代中国早年的问题产品,而至今未过保质期。《伤逝》还展示出作为“传统”的早期新文学能激发出的书写可能,旧题新咏的意图,使当下与过去,经由语言隧道彼此沟通,也彼此映照。有互文意愿的诗,也是知识性的“怀旧”,它检讨着历史与传统,于是便逸出个体生活的范围,也就是说,室内的幽闭,有化解的可能,而处境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再衡量,狭隘也会少些。隐喻性的“自习室”为旁观者所用,这是文学姿态,也是历史意识。很多旧日的青年才俊,早已成消费自身、模仿自身的文学名流,而坚持在“自习室”中阅读、写作,便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自新能力,这朴素的格言,于写作者而言,暗合功夫在诗外,可谓性命攸关。

“郊区”的幽闭,是室内的“幽闭”,如《即景》中主体于“草木葱茏,天色氤氲”的时刻,“站在阳台上”,却受限于空间的边界,无法理解即景的含义:“我不理解气味,不理解主妇嘴里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东北话,不理解肌肉里那些纤维状的山麓/其实我不理解的还有很多/它们层叠着、晦涩着、在春光里充斥着/正等待一个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姜涛诗中,室内的主体,常是“写作者”,《诗生活》对此有洒脱的声称:“我几乎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上写诗。”“写作者”形象的自我塑造,构建出主体置身的知识性空间(按上文的命名,即“自习室”):它内在于“郊区”生活,又以私人性为前提,因而如坚固的秘密,是边缘地带的边缘;由此界定出的疏离意识,不是走向自我的封闭,知识生活的延展可能与创造力,辅以诗意的想象,便可成为突破“郊区”之幽闭的契机。简言之,“自习室”意识与“郊区”意识,在诗作中得以重合,前者扩展后者的限度,后者又使前者始终对称于我们时代的日常,不至于因脱轨而沦为空想。两种位置感相互激发,写作于认识论向度之外,生发出自救性。以《郊区作风》为例,既有书斋之外的生活景观(“穿体面点儿,就能像个中介了/每个早上,打开洞穴,骑电动车冲出去/人生,需要广大绿色的人脉/那随便放狗咬人的、随处开荒种菜的/人其实不坏,就想花点闲钱撒野”),又有书斋之内的主体状态(“深夜不睡:写写打油诗维权/即使不能如愿,北边窗户下/那些开往包头的火车还是甜蜜的”)。其中,“需要广大绿色的人脉”是有深究的,“绿色”隐含的万物生长,恰切地表述着为金钱逻辑所推动的蓬勃表象,“自然化”的想象方式也为《送别之诗》所用:“捷达、奥迪、帕萨特/一连串野兽的名字,替换了/猪獾、臭鼬或果子狸”;“其实,你只想做一枚抽烟的植物/好无偿接受雨露”。闯入“郊区”的文明利器,被想象为自然界的野兽,它们表征的生活便显得野蛮,与之相对的身体,表述着由人为世界逃向“自然”的心愿。此处的诗意空间,“自然”被赋予救赎性,而类似的祈愿,也见于《另一个一生》:“我开始离开人群,走向郊外//向一片树林心理咨询/树木分不出性别,都长出粗大的喉结/和落叶的乳房/它们的准则是原地不动/和每一件经过的事物接吻/又不担心将它们轮番忘记……”值得考虑的是,在城市生活的背景中,在写作者试图对室内之幽闭进行化解时,“自然”如何进入姜涛的诗歌。
三、窗外的鸟

广义的“自然”及其当下的处境,也是姜涛诗歌触及的重要问题。诗人通常选取“窗口”作为视点,因而“自然”并非以“景区化”的山水之貌现身,诗人或从“自然”收割想象力,或是从它的广阔无私中择下某物,尤以后者为主。“窗口”为界,当室内因幽闭陷入困境,窗外的鸟,或将衔来“自然”的丰富意义,而首要的,便是救赎的契机,对应着时势迁变间个人必须忍受的局促。例如,在《即景》中,瘟疫袭城,受困经验引发对处境的不解,而观察窗外的草木,有慰藉惶惑之效:“他和我一样,站在六层的高度、危情的高度/重新将各种各样植物的族谱默念。”再比如,在《厢白营》中,“自习室”空间激发的感性力量(“难道你不曾为一本书中的注脚所打动,它拆开乡村和典故/标志出一处昏睡的琴房”),引出逝者的形象(“小煤渣路上一个亡灵曾青衣小帽诗意地踱步”),它仿佛在预示主体的终将失败,哀悼亡灵也仿佛在提前祭奠自身(“当哀歌或朗诵接近了尾声,/不要再哀悼什么了”),于是身姿踌躇(“但与生活相比我总是慢了半步”)。在整体性的困境表述中,“自然”成为能够给予启示的形而上存在,“鸟”的行动启示着写作本身(“窗外一只小鸟击打树干仿佛一台打字机打下了一份早春的遗嘱”),而在“雨”中,主体恍若劫后余生(“一场春雨能否将这苦闷化解,你抬起头/镜中的脸颊已与一个亡灵相仿”),最终,主体在与“自然”进行情景交融式的沟通时,也暂时地与对立面和解,但所谓和解,不是指成功学意义上的锐意进取,而是指开始理解事境之于人的晦涩:
“最后,让我们道一声晚安。”幕落时总会有一个死者从池里
重又站起,局促不安地等待着大地上稀稀落落的掌声
并且继续用一只夜莺的口吻安慰自己:“怀疑啊怀疑
我命运中的一块水晶”。当一次次的阅读被深夜的造访打断
当飞过书橱的燕子反复溺死在同一个梦中
而我也伏案熟睡了吗?——
怀念一对乳房像怀念果园门外一双秀美的门环
“无人叩响这个时刻,无人跨越门槛”
白银与黑铁的交谈已铸成了一条舌头
‘厢白营,厢白营,小麦带来诡计,爱情带来不忠
出门是一个生人,归来已是一个亡灵’。”

“自然”的救赎向度,在意义叠加的空间中,有了伦理学上的困顿:主体渴求“自然”纾解室内的幽闭,却又因他者的身份而不必承受“自然”内部的黑暗。这困顿,被追忆为组诗选《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的开端:“六年前,我就来过这儿/带着新鲜的肺和脸/左顾右盼,看个不停/结果,车子撞在半山腰/民族司机被警察带走/我听见身下江水的咆哮/在山水,还有人高声断喝/——有何贵干?/那时,我无家累,无房产/认真读书,也没超过四年/怎么可能有答案?/结果,他们逼我不停喝酒/说一两个内地笑话/我缺氧,口拙,讲不清/像块石头从雪岭滚下/滚到了车里/又滚回了北京……”如何测量六年来变与不变之间的夹角,这构成整组诗的动机。城市空间的逻辑,仍是“命运和钞票纠缠”,而“国事不平坦”与私人生活的死水状,加重着室内的幽闭,故地重游成为必须。在标题为“青草坡”的一节,“自然”空间的救赎性仍然可期,接下来以“小历史”为标题的一节中,“白皙的种族”的生存史被讲述为“自然”进入现代性空间的过程,在现代性话语的规训下,“自然”开始了对都市空间的模仿,并似乎恰如其分地将自身的意义变为秘闻,“自然”主动地消声,虽尚未匿迹。在现代性话语的持续介入下,“自然”空间中的人,相比于都市人,特征所在,不涉及主体的内在性,而是外表与贫穷:“院子却收拾得干净(所有院子一个样)/花木齐整,主客对话也简约/像是事先经过了排练,小孩子的邋遢/和他们的作文最醒目/错字不多,但都按了规定言情/在结尾写到受灾的四川……”“自然”的语言选择接受现代性的统战,是为一种出路:“陌生人说来自北京,学生中的少数/曾计划去那里大发展/政治老师赞同这个想法/以自己为例,激励大家学汉语……”现代性话语,终因朴素经济学的推动,在“自然”中确立了权威。
“自然”被现代性改造,必有伤痕,通过书写这“自然”的困境,诗性语言的质地,终也通过感同身受,由判断力转向悲悯心。组诗选最后,诗人听来的宣言(“我只关心人类,海子说的不对”),何尝不是一种必要的、带有纠正意味的心声与新声?简言之,“人类之诗”(《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组诗选)》中的一个标题)的可能,抑或人性胜利的可能,已露出迹象,在新纪元有别于过往的、另一种形式的“灾变”处境中,如何生发微薄的可能性,如何赋予“诗可以群”当下的含义,或许正是姜涛与同时代人的着力点之一。
注释:
①张承志:《鱼游小巷》,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关于顶力的理论计算的基础上,通过顶管顶进过程的受力分析,顶力计算过程分为覆盖在顶管上的载荷计算、顶管管壁摩阻力的计算、构建合适的顶力计算模型3大步骤。
②有关八十年代的出版物,较为知名的,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除由肉身入思怀的随笔方法,学界也开始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将其制作成知识性的档案。如洪子诚等的《重返八十年代》(程光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③北岛与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续集》分别于2008年、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⑤钟鸣:《新版弁言:枯鱼过河》,《畜界,人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⑥康赫:《人类学》,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5页。
⑦姜涛:《鸟经》,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25页。本文征引的姜涛诗歌,除个别外,全部出自《鸟经》,不另出注。
⑧马雁:《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⑨秦晓宇:《七零诗话》,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26页。
⑩吴向廷:《〈鸟经〉中的拯救与自救》,见臧棣、萧开愚、张曙光主编:《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