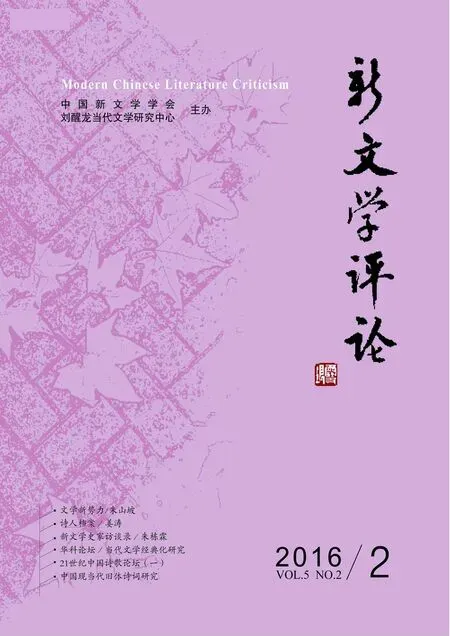刘醒龙:重回公共领域的小说审美
———兼论文学的“公民写作”
◆ 李俊国 王玮璐
刘醒龙:重回公共领域的小说审美
———兼论文学的“公民写作”
◆ 李俊国 王玮璐
近些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在思考与寻找中国文学叙述方式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显现与被重视,背后隐含的是对于“五四”以来近百年的白话文写作实践的一种反思与探索。
80年代中后期,中国作家开始在文学的维度与世界对话,自觉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现代派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在现代主义兴盛背景下催生而成。王蒙、徐迟等作家对于现代主义创作的早期探索,寻根文学所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伤痕文学开创的“重述忠诚与信念”的风气①,仍然是从政治实践中寻求文学生存模本。而90年代以后先锋派的形成,则意味着文学“向内转”,不再是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力量。随之形成的文学多元分立的情势,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文学叙述方式从大一统走向破碎。而“王朔现象”和新写实文学则是对于原本历史的一种祛魅,一种从内部消解历史正统性的革命,他们更专注于日常与细节,让中国文学叙述方式转向了更多差异性、更为多样化的探索。
在经过了80年代对于体验的描绘,90年代对于语言的实践和90年代后期对于事相本身的写作以后,汉语小说走过了一条歪歪斜斜的探索之路,提出了一个包含更多可能性的议题。达到了成熟期的一批作家,累积了更为厚实的文学体验,具有了更为自觉的文学思考,甚至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的老练成熟的统一。无论莫言以玩闹、戏谑处理历史的方式,还是铁凝所坚持的大历史中超性别视角的小叙事,或者阎连科将后现代思维引入传统乡土叙事之中,抑或张炜将自我经验与汉语艺术推向形而上范畴,他们的这些创作,都在为汉语文学写作寻找中国式文学叙述的路径。
而刘醒龙所提出的“公民写作”,也由于其对中国文学叙述的探索,而具有了研究价值。作为写实小说的一部分,刘醒龙的作品脱离了启蒙主义的影响,不去计较精英与底层的分岭,而是以自然而宽广的方式呈现中国现实;作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刘醒龙的作品倾向于将历史事件作为标记存在于历史的时间坐标之间,而真正构成文本本身的则是小说构建出来的生活细节和伦理风习,形成了一种创造复杂丰富的文本空间的叙述方式。这种“公民写作”同样显示了汉语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
一、公民写作:中国问题与刘醒龙的创作姿态
在中国当代文坛之中,刘醒龙是少数沿着自己确立起来的文学风格稳步推进的创作者。
刘醒龙自己同样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应该分为三个阶段②:“大别山”之谜的浪漫想象和幻想,“现实主义冲击波”时期的写实与披露,《圣天门口》及之后的作品所形成的“公民写作”意识,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他对于小说和世界的不同态度、不同视角和不同感悟。
他在2005年提出的“公民写作”的叙述原则,是他对于他个人体验与创作路径的一种思考与超越。刘醒龙自己将其定义为以“公民意识”作用于文学的审美写作。“公民与平民并不完全一样。公民的言行必须有责任。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却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责任感很重要。”③与卢梭的定义一样,刘醒龙所认为的“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公民在独立之中一方面要执行自己获取财富、表达政治诉求的公民权,一方面也要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因此“公民意识”要求在摆脱国家政治权力支配的同时,对日常世俗的也要有限性的超越,对中国现实的也要普遍性的关怀。
这种“公民写作”的思路从一开始就在刘醒龙的创作中萌芽。早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刘醒龙建立起来了对于文学回归公共性的尝试;《分享艰难》作为一个标志性作品,以平视的眼光展现了小人物的微弱希望,在时代大背景下力挽狂澜的努力显得卑微而悲壮;而《圣天门口》以后,刘醒龙将历史作为根本上遭受质疑的对象,而舍弃了批判与颂扬的眼光,实现了文本对于人物平等无差的怜悯与关怀;《蟠虺》则意味着刘醒龙将现代性思考引入到了文本之中,建立起来的在其小说中以审美的眼光叙述汉语文学的可能性。
这种“公民写作”的特质之一,是刘醒龙始终坚持的“大”的写作。他的小说所选择的题材往往是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尖锐面貌和独特景观,以其特有的沉重而深厚的写作方式形成了一种“大文体”。从《凤凰琴》和《天行者》关注于小山村或者乡镇生活里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乡村教师,到《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留心描述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乡镇国营企业,到《分享艰难》中写出“官本位”思想下的乡镇中国和中国基层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结构,到《蟠虺》中深邃刻画了中国政治官场怪相和知识分子的衰败与坚守。《圣天门口》更是通过持久的人性救赎与巨大的传统伦理来重新解构和重构整个中国历史。刘醒龙的目光是远大的,他在写作之中,有意识地要对变革、贫困、动乱进行探索,对于人类命运有着真诚而诗意的关怀。《圣天门口》就是一部在史诗格局中探寻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小说,其对于历史进行了新的还原和建构。刘醒龙用互文结构将整个天门口的故事与说书人的《黑暗传》扭结在了一起。《黑暗传》是以韵文形式出现的民间丧歌,诉说了汉民族的创世史诗,通过说唱人在天门口镇居民文化生活的主要节目出现的,有时是作为小说的“楔子”突然插入故事之中。在《圣天门口》的整个历史叙述中,《黑暗传》中从商汤灭夏的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杀戮与征战,一直到东汉末年混战,这一段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黑暗的时期,正与天门口的从共产党土地革命开始,到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和轮流管辖之下的局势相对应。文本形成了一种互相扭结互相发展的双螺旋结构,使得历史的联想性与现实的冰冷性之间形成了一种背景烘托式的艺术张力,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某种必然性。刘醒龙总有为现代中国立书做传的雄心。因而他的小说,往往是在与细节中的中国人相结盟、并在具体的中国生活中有所担负。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活在真实的中国经验里,因而能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发言。这样一种写作态度,让刘醒龙始终与商业写作保持距离,他更倾向于“灵魂和血肉”④的创作,这种创作是严肃的,也是痛苦的。他用稳重、迟缓、吃力的目光注视这片土地上的中国经验,让他笔下的小说交织组成了一个深邃、复杂、多维的现代中国的复刻。
倡导“公民写作”的刘醒龙,同时坚持着一种对于基本道德原则的关注与弘扬,并赋予小说以精神维度的意义。在刘醒龙小说世界里,无论是问苍天责大地、为民请命、借景怀古甚至于科研考据,作家无不怀着大爱大德,以小说叙事通达崇高和庄严。《凤凰琴》里的几位乡村教师在极度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虽然心思各异,不得不为自己的私利与出路做打算,但同时他们又都有着高度自觉的人生信念,能让他们默默无闻地守在这个岗位,坚持这种天地间的启蒙之伟业。《燕子红》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主题就是对于劳动与仁慈两大基本道德的诠释和建立。刘醒龙通过笔下的几个劳模人物陈老小、高天白,通过上山担石头的陈百勤,来试图用劳动与仁慈对堕落的时代以教化,用以挽救早已崩溃的民间道德体系。刘醒龙试图为文学的精神承担重构起自己的宏大叙述。处在一个社会激荡的时代,为中国现实的驳杂所倾心、为寻找通透现实症结的出路所折磨,因而,他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写作的责任,通过写作来进行精神探索。刘醒龙的小说能够在中国经验背后发现其丑陋,但是也能从丑陋背后发现善良和希望。他描绘了这个时代的衰败、萎缩、可怖,但同时他的文本之中总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圣天门口》归根结底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和历史现实,与以仁慈、宽恕、博爱为根本内涵的基本道德原则的历史哲学张力及其矛盾冲突。在充满了杀戮与争斗的历史进程之中,梅外婆和雪柠始终是历史博弈的局外人,她们目睹并亲身感受着“革命”给广袤的中国大地所造成的巨大改变。然而,她们的内心却怀揣着具有圣性意识的“大爱”,并以圣性大爱参与历史的博弈。刘醒龙始终对于美好的事物有希望与爱,对于丑陋的世界有伤感与恨。正如他自己始终认为的,“要将最丑恶的东西挖掘出来,用我们的理想来烛照”⑤。因此,刘醒龙的小说总有一种扬清去浊的正气,他试图超越丑恶与绝望的写作困扰,在现实与历史的写实界面,敞开了更为辽远的目光。《蟠虺》可谓之二十一世纪的官场怪现象,小说所剖露出来的强权与腐败,怵目惊心,但是,繁复的小说故事之中始终有曾本之这样执着的铁肩担道义者,像一股清流汩汩地在文本中流淌,让这个颓败的文学叙事能于无所希望中获得救赎。有此在的承担,同时也有对将在的展望,更深邃地、更完整地直面中国经验的多重视域。
“公民写作”的精神承担,使得刘醒龙总是试图去寻找大叙事下的大美。因此,刘醒龙小说文本都具有某种文学传奇化的倾向。他惯于从庸常的人生中化出精巧的故事,这些精巧的故事的每一个组成符号背后都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含义,是刘醒龙小说文本的结构特征。《圣天门口》中的柳子墨和雪柠上山寻找燕子红,找到的却是中国腹地华北地区暴雨和洪水气象之源,那里撕裂的深谷大树上都留着雷电烧焦洪水肆虐的痕迹。柳子墨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天堂”。“天堂”的象征意义十分明确,指上帝承诺给人们的天国,即终极的理想之地。但这个理想之地却是永远也到达不了的所在,没有人能上得去,上去了的也没有人能待得住,结果是天门口所有的纷争、厮杀都是发生在天堂门口的故事,死者死矣,生者生矣,最终都无法进入天堂。天堂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就像梅外婆信守的人道理想,既救不了一国,也救不了一方,结果只有劝告雪柠,以一己之力来救某一个人,做某一个人的福音。结果到了最后,连某一个人的福音都是假的,“福音之福不是幸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睁大眼睛做出来的黄粱美梦”⑥。《蟠虺》之中,曾侯乙尊盘也是类似于终极的一个象征,它是国之重器。这样的君子之器居然能被偷盗、被授受、被伪造,怵目惊心。故事的最终结局里,身份特殊的男人闯进了设在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老省长和熊达世的国师之路不过是黄粱一梦,郑雄带着曾侯乙尊盘坐快艇行至龙王庙,“一只大手从江底伸出来,生生从他怀里夺过木箱子,轰隆一声坠入江中”⑦。安静喃喃道:“天意,一切都是天意。”因为曾侯乙尊盘是唯一的,出现了曾侯乙尊盘真器,世间就不会允许曾侯甲尊盘也现在人间。该天谴的一定会遭天谴,该天赐的一定会有天赐。因此,刘醒龙的笔下总是不乏“怪力乱神”的抽象性元素。《燕子红》中只有勤于劳动的人的机床上才会有湛蓝的铁屑,这蓝色的铁屑已经化为一种劳动与仁慈的精神象征。《蟠虺》里冤死的人坟上会冒白雾、天命所归的曾侯乙尊盘沥血生紫烟。刘醒龙始终保持着对死亡、对自然、对神秘事物的敬畏。他将异象、预兆、宿命等巫术思维引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增强了小说创作的神秘、奇诡、浪漫、传奇、抒情的色彩。这些抽象的因素赋予了文本以超验性,让小说形成了一种诗性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一个隐喻的语言场域。小说故事是一个个现世寓言,充满了象征、隐喻等史诗性质的特点。
《圣天门口》本身就是一个与《圣经》U型结构相对应的大史诗。在故事的一开始,雪家娶亲的堂皇雅致体现了天门口这样一个小镇,在乱世之中的平静安详。然后,如同毒蛇切西亚一样,傅朗西如何引诱人们去摘取堕落的伊甸园果实,让天门口第一次陷入暴动的屠杀狂欢之中。在一次次杀戮中形成的种种伤痕即景与暴力奇观,将人与人之间的血腥报复与咀嚼吞咽的必然性悲剧供述在历史文本中,剖明了各色人性的嗜血性成分。故事的结尾,“文革”武斗中的天门口终于迎来了一缕久违的清风。“风吹到身上,谁就觉得轻松了一大截。”⑧宗教仪式的周期历法形成一个“类比”,《圣天门口》本身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其中不管是受难还是复活,都是对永恒生活的翻译与模仿。冬天刮起风来了,这股风会很冷,很厉害,很多人可能就会凋谢。但这依然是属于上帝的风。风暴过去后,更加纯洁、更加美好、更加强大的土地将屹立在阳光之下。而复活则意味着春天的来临,万象更新,生机盎然,只有在这时才能庆祝生命的复活。《圣天门口》之中的人物脆弱无比,生命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毁灭,但是人总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精神的超越与救赎。
一次次试图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使刘醒龙小说形成一个个复杂丰富的文本空间,用以探讨更为广阔、幽深的精神领域。他的小说是植根于中国经验的,但中国经验已经成了某种精神的关照,不再是写实仿真的经验描述,而是被刘醒龙个人重新理解了的现实。刘醒龙一直在自己的小说中经营这样一种实验,即用仁慈与大爱来对抗丑陋国民性与人心残酷性的小说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人类生存的苦难与绝望、人生意义的追寻与救赎,一次次的碰撞与博弈。这些小说就是以个体生命与世俗生活的细节映耀普遍人生的寓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作家在寻求思想的独立性的过程中,不断地抽去了社会职责中的政治内涵,文学拘于诗学的狭小言说。刘醒龙的“公民写作”则尝试将文学重新拉回公共领域。正如阿伦特认为文学不是孤独的作家的创作活动,也不是单个读者的阅读行为,而是由包括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参与的主体间的互动—呈现空间⑨。刘醒龙的公民写作也更关注文本带给读者的意义效果。80年代文学“向内转”开始的一系列文学潮流,从伤痕文学、朦胧诗、先锋派到后现代主义实验,中国文学逐步形成了“去政治化”的路径。刘醒龙的公民写作是对于“去政治化”的有意反叛。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独立于文字试验和私我书写的时代潮流之外。他不再把政治和文学对立起来,而是希望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建构一个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小说中国。
这种叙述方式建立了这样一种写作规范:故事一定是承载意义的。刘醒龙将一种意义的探索引入文本之中,用广泛隐喻性的方式去写人性内在的精神维度。这样的公民写作不仅仅为小说提供了精神本体,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审美。
二、圣性图景:精神建构与刘醒龙的创作伦理
“公民写作”在刘醒龙小说中所坚持的写作姿态,而“圣性图景”,则是作家不断地构建的小说的精神本体。将圣性图景熔铸于公民写作,形成刘醒龙在不断探索自己的创作途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创作伦理。
刘醒龙的“圣性图景”,大致经历了“自然神圣性”、“道德清洁性”和“人格圣性化”这三个阶段。在早期的“大别山之谜”时期,作为一个自发写作者,《黑蝴蝶·黑蝴蝶》是对于身体经验的感悟和联想与想象的记录。《大别山之谜》系列充满了漂浮在虚空的抽象冥思,处在自我的审美氛围之中。如同沈从文写湘西之美一样,刘醒龙也从大别山之中发掘出来了一种野性而自然的美,这种美往往同淳朴与善良联系在了一起。从90年代开始,刘醒龙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主流力量蜚声文坛,他创作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乡村教师题材的《凤凰琴》、《天行者》,还是村镇官场生态题材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燕子红》中,小说都致力于站在平民视角,写出底层人物心态和生存状态,兼具写实与抒情的品性,创造了一种新乡土小说范式。在这一系列的作品里,刘醒龙坚持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写作方式,小说人物始终有着抗击丑恶、召唤崇高的人生姿态和道德立场。《圣天门口》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描绘,抛弃了既定的历史价值观,而始终以仁爱思想作为整部小说的伦理基石,在血腥暴力的苦难史中建立起来了神性意义上的精神慰藉。刘醒龙在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步步建立起来了追求神圣化和道德化的精神诉求。






《蟠虺》则意味着刘醒龙将目光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蟠虺》是一部城市审美的小说,因此文本之中“圣性”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在这部小说里,不再是弱者在乞求怜悯,也不是学童在有待启蒙,而是一个个公民在发声。在这里,每一个人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真正的公民需要行使自己的权利,更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现代性的“圣性”要求人活在现世,与世俗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是一种济世救民的传统知识分子气节。这种气节要求他们做世间脊梁,坚挺腰撑傲然风骨,思哲高尚雄美万方;以诗情气节岁月境界为人生之重,对国家民众要有责任与担当。在官场气象污浊,满朝阴诡之士的大背景下,刘醒龙赞赏的“不识时务者”,是国之君子青铜重器。他用一个“真与假”的曾侯乙尊盘来隐喻着灵魂的真实与虚伪的冲突、道德的光辉与绝境的搏斗。《蟠虺》的圣性意识,已经不再仅仅以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作为思想的支撑点,也不再是漂浮于虚空的“仁爱”与“善良”,而是对世俗生活的承担。在这里,日常生活的合理化行动并不取决于任何超现实的神灵,而在于人自身的创造、追求和体验,在于他们对于世俗生活的个人感受与承担。这种承担是现代性的,早已经区别了“都市恶、农村美”的单向度思维的道德观。

同时,《蟠虺》中的圣性精神,比既往作品更具有同情心。刘醒龙不再用启蒙主义的眼光注视他笔下的人物,他不再继续高高在上的教训与感化,不再用精神的训诫或者情感的施舍,而是用一种理解的方式去面对世俗。《蟠虺》不再是巨大的审判场,不再是对人的衡量与拷问继而判决。刘醒龙也不再是法官与陪审团,决定黑白泾渭之分。他能够从暴虐与恶行之中看出可怜与荒诞,从摇摆不定之中看出苦苦寻求生存空间的艰难与智慧。面对充满了悖论和混乱的中国经验,《蟠虺》的“圣性精神”已经与世俗生活裹挟在一起的一种俗世道德体系。一生隐忍的圣人曾本之,华姐的痴情决绝,老三口的侠肝义胆,郑雄为了仕途殚精竭虑,他的辛苦奔波,以及可悲的牺牲,让人心生怜悯。《蟠虺》之中再没有什么底层人民,也没有什么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是活生生的呼吸着的,具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感觉。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有生命、有权利、有尊严、有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有在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并充分地去活着。而刘醒龙不再用训诫的眼光俯视着他们,而是那样宽厚地走入他们当中。因此《蟠虺》的世界是悲哀的,也是欢喜的,因为在刘醒龙这里,他让读者和自己一道饶恕了那些犯恶的人。
现代性的社会生活,允许平常的人性、软弱的人性、妥协的人性,允许人在苦难前的喘息,在现实前的苦熬与匍匐。而一个人在整体性的厄运和磨难面前仍然要去生活,在人世的恐怖与残酷前所能做到的坚守,他卑微的倔强与尊严,在时代抉择中瞬间爆发出来的灵魂光耀,因其生命力而变得壮美又震撼。这种从简化走向宽广的复杂人性,才是真正精神维度的“圣性”,那是磨难背后的希望,痛苦背后的坚定,是一个成熟、健康、有力的灵魂在行走。
三、审美叙事:意象碎片与刘醒龙的诗性叙事
审美叙事,保证了刘醒龙的“公民写作”避免了文学趋向历史学、社会学、问题学的偏枯,形成了一种“审美眼光”介入文本的艺术自觉。
在其“现实主义冲击波”时期的小说创作,仍然保有着自发式写作者的问题的发现、生活的体验与精神的启示的书写方式,包括在《燕子红》中对国企改革问题、乡镇企业发展困境问题的发掘与反思,《天行者》中对于乡村教师群体问题的同情与怜悯,《村支书》中对于官僚作风问题、社会不正之风问题的揭露与批判,骨子里并没有脱离“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即便如此,在他早期的小说之中,仍然流淌着诗性的叙事笔致。


在碎片审美参与文学叙事过程中,刘醒龙放大了人物的生命感觉。在前期的《凤凰琴》、《燕子红》中甚少给人物以情感、心理上的描摹,更多的是将人物符号化,用以恪守成规地完成文本交予他的任务。而后期小说,刘醒龙给予了文本中每一个人活生生的感受、思考与领悟,捕捉到了他们每一个瞬间的殊异状态,赋予人物以生命气息。马鹞子不过是一个打着国民党自卫队旗号嗜杀成性的屠夫,常守义不过是个用杀害杭家老二和镇长的方式嫁祸两家挑起暴动的投机分子。然而雪家败亡时马鹞子摸着雪柠的头发安慰她时的那一笑也是温柔动情的。麦芒飘进雪柠眼睛里时连常守义也能为她跪下身子轻轻吹一口,雪柠认为即便是这两个人,她也能看见他们的福音。《圣天门口》里没有一个是脸谱化的好人或者是坏人,那里面呈现了人的行为的伟大、静谧与动人,也供述了其恍惚、乖戾和荒诞,那里面有人性的柔情善良和宏大悲壮,也有其血腥报复与咀嚼吞咽。那里面的人有着对美好未来的遥想和奔波,有着对自我罪孽的狂怒和羞耻,有着对酷烈世界的惶恐和愤怒。《圣天门口》历经三代的数百人物,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个人命运,构成了一道庞杂而汹涌的精神洪流。在《蟠虺》里,作为正面形象的郝文章为了探究曾侯乙尊盘的秘密自愿入狱,是多么伟大的自我牺牲;可他离开情人与亲子近十年,又是何等决绝无情。曾本之在东湖边上情绪深陷绝境时,看着那冬雪之中一清二白的东湖,“紧闭双眼,任凭泪水一颗颗滚落在雪地里”。在那一瞬间的感受传递给了每一个人,每一次得而复失的遗憾后面接踵而至的是从未有过的惶惑,这一台活生生的戏从来也弄不清该当悲剧看还是当喜剧看。小说里的人物都展现了他对当下的存在感、对过去的记忆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刘醒龙能让读者能切实感应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内涵,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作者在捏造雕琢的努力,而且是那些人物自己要呼吸要行动要呐喊的生命力。刘醒龙让读者能切实感应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内涵,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作者在捏造雕琢的努力,而且是那些人物自己要呼吸要行动要呐喊的生命力。即使是最情感匮乏生命麻木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到触动心灵的效果。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整部小说是一个巨大的拼图,当最后一颗板块归位之时,读者能感受到笔下的人物的生命感觉的绽放,以及刘醒龙那继往开来的气度。

四、中国故事:当下意识与刘醒龙小说的复合型文本
90年代以后,文学逐渐从社会公共领域撤离。“先锋小说”的文体实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过于热衷,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造成了零散片断拼贴后的虚空;九十年代末期的文学“断裂”运动、“日常叙事”的提倡,使文学流于日常琐碎的记录与唠叨,小说叙事被简化成为对平面经验的直白转述。在过于破碎的文学背景下,中国文学叙述必须努力弥补新时期以来“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的巨大断裂,搭建一条桥梁用来联结对立的两岸。从这个意义来说,刘醒龙的“公民写作”,对于中国文学叙事而言,其意义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叙事的可能性。
刘醒龙提倡回归叙事,用广泛隐喻性的方式去写人性内在的精神维度。他以一个故事为载体,精心构建了错综复杂、驰心旁骛的结构,不厌其烦地执着于人物内心的探幽析微。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很容易从短篇的乡土小说中读出“反腐”文学和权力异化的符码,后期发展出道德至上的倾向。文学还在意识形态共同体尚未破碎的格局中运行,很自信地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角度去解读。而从《分享艰难》开始,刘醒龙的创作出现了许多旁溢的元素,来源、边际和目标都日益模糊,这一种破碎的趋势就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真实的撕裂。《圣天门口》和《蟠虺》,都摆脱了批判文学的单一声调,不再只是简单的讽刺与揭露、批判与追寻、赞美与愤怒。《圣天门口》具有非暴力意识,然而书中崇尚暴力和原始冲动的杭家却并非是完全的反面人物。杭九枫是一个暴戾与勇智并存的复杂人物,刘醒龙用宽恕和欣赏的笔调描绘这个人充盈的生命状态,对他高涨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予以称赞。如同贾平凹在写《秦腔》时所保留的那种“说不清”的态度,他对陕北的那一片土地爱得如此真诚,担负起终极思索的重担,在写作的迷茫与矛盾之中做痛苦而真实的呈现,而非对现实横加指责或者是溢美于表。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以宽容、谅解的目光望着中国,恐惧软弱与委曲求全交织在文本之中,这种目光使得他成了恰当的历史见证人和修复记忆的那一个。这样的作品是多义的,因为作者没有拿几个名词和概念蛮横地命名那个时代,而是把那个充满细节而全局混乱的暧昧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与他同时处在这渴望被命名的焦虑里。文本之中的情感如此隐晦意义如此庞杂,读者必须凭借一个巨大的感悟来阅读来参与,深入到精神深处,去体验人性的一次次不经意的颤动,去感受记录人内心无处述说的恐惧。这种文学叙事不再只是单纯的揭示社会现实的丑恶、描绘底层人物的苦难,而是一种沉入生命深处的体验与感觉。

刘醒龙的“公民写作”是他对于现代性大潮的写作反思。这正是因为后现代理论让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思想的独立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去社会职责中的政治内涵,旧的叙述结构被解构得更加破碎,对有着严重冲突的各种合理性具有包容性的普遍认同。要建构起真正的文学现代性,必须要求解构之后的重构,破碎之后的重建。在文学日益边缘化以后,中国文学的写作面临着的巨大困惑,如何面对文学摆脱意识形态控制之诉求与挥之不去的现实批判感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刘醒龙的小说创作给中国叙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公民写作”要求现实承担,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浸淫在中国的土壤里发酵生长,氤氲在中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空气里,脱离中国经验去谈论中国文学是不合理的。在刘醒龙笔下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历史,是交织着战争、灾荒和政治动乱的历史:个人命运与时代动荡的纠结,人性伦理与民族政治的缠绕,战乱饥荒、天灾人祸……因而活在这种真实的中国经验里的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对当下的中国生活有所承担。同时,“公民写作”又要求文学用智慧的方式去介入世界。他在紧贴地面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要有诗性的解脱和浪漫的超越。如同艾伟用超现实主义的狂欢式赛跑来表现人类欲望的智慧、愚蠢和激情,用水面上巨大而漂浮的尸体之花来建构和反讽历史的荒谬,隐喻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民族性的精神分析是无限深入的。方方的基于现世的荒原感的“刀锋写作”,那不可言诉而又无处不在的忧人情怀让她的小说能直逼现实,一方面为现世而焦灼,一方面却又有着对常人所迸发的超凡脱俗的灵魂的关注。中国叙事不可避免地要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建构起来一个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中国,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确认自我的必经之路。用智慧的方式打击了现实所立足其上的合理化的世界本身。这种精神转向,不仅仅是执着于对现实问题的暴露,也不只是历史的焦虑和矛盾,更要求精神的超越。现实如此黑暗又如此脆弱,人理应有着追求希望的冲动与走向光明的勇气。
刘醒龙在现世之中探索衰微的文化品格,寻找失落的人性情感,参与民族灵魂的重铸,他的“公民写作”是“贴着地面”的,然而又不至于沉沦于地面匍匐爬行,而是为中国叙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注释:
①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③刘醒龙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家谈》,《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
④刘醒龙:《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⑤杨建龙、陈海英、蒋进国:《官场病态与理想坚守——刘醒龙长篇小说〈政治课〉三人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⑥刘醒龙:《圣天门口》(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8页。
⑦刘醒龙:《蟠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69页。⑧刘醒龙:《圣天门口》(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6页。
⑨汉娜·阿伦特著,汪晖等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页。
⑩刘醒龙:《燕子红》,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