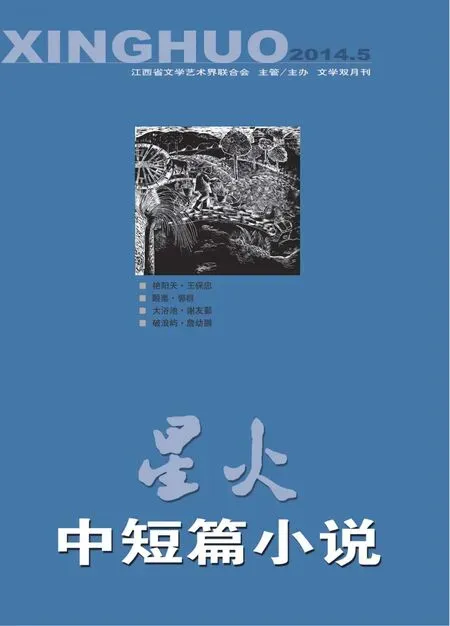如果不写作,你会在哪里?
——方格子访谈录
○海 飞 方格子
如果不写作,你会在哪里?
——方格子访谈录
○海 飞 方格子
海飞,小说家,编剧。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500多万字,大量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多种选刊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著有小说集《麻雀》《青烟》《像老子一样生活》等多部;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没有方向的河流》等多部;长篇小说《花雕》《向延安》《回家》等多部;影视作品《麻雀》《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隋唐英雄》《花红花火》等多部。
1、前些年,读你的小说,总给人以向内的阅读体验,不知不觉进入小说营造的氛围。你的叙述讲究情绪,情感,以及自觉的感悟。近些年,你的创作更多把笔墨往外拓展,延伸。是因为你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信心了?还是他人惯常以为的,进入了瓶颈期?
2010年,我去了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是我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光。除了上课,余下来的时间,就是写作。同学几度提醒,你不能这样闷头写,你得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一再引导我读书,大量阅读,长时间的思考。
有太多需要表达的东西,除了写出来,我无暇其他。我想说的是,那一年以及之前的十多年的创作,缘于个人对世界的体悟,那些经验来自内心。比如,一个炸弹在我面前爆炸,我也无法将现场记录,形成文字——我对当下生活缺乏描摹实录。没有直抵人心的体验,我无法写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建立起来的个人时代,每一个小说,都是自我的诛心之作。
这样的写作持续十多年,我满心欢喜,写完一个,内心便豁朗一些。仿若有数不清的线缠绕成数不清的结,盘亘在心。每完成一次创作,便是解结的过程。内心的愉悦无与伦比,虽然师友善意地指出,我的作品不够大气,开阔性有待加强,也都不能影响到那时自娱自乐式的写作。
直到有一天,写完中篇《赞美诗》,这个小说几乎是我整个写作的分界线。那是一个家族小说,没错,当我开始浅层次地涉及家族故事时,才醒悟过来,属于我的那个秘密的矿藏已经被我开采,见了底。
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的,有些狰狞。我已经把小说写死,那种深藏在内心怎么也藏不住的东西,已经完结。或者说,我已经不能再拿那点浅薄的经验积累支撑起让自己满意的叙述了。
2、谈谈非虚构吧。从《留守女人》,到最近出版的《一百年的暗与光》,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你个人创作的突破。写作者都知道,从采访,到创作一部厚重的作品,历经漫长的过程并非易事。这样的创作,对你个人有什么特殊意义?
从第一部非虚构《留守女人》开始,我不再钟情于虚构一份情感虚拟一份情绪,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忍再回头重读虚构出来的故事。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虚构的力量如此单薄,弱小。那种我之前追求的轻盈的气息,在一节节火车硬座车厢混杂的汗味中,在那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面前,显得遥远而羞愧。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并非厚此薄彼,只是,生活这把匕首太过锋利,太过刻薄,容不得我不敬畏。
坦白说,当初决定外出走访留守家庭时,是抱着私心的。小说之泉已然枯竭,我想探求另一种生活真相,到远方获取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来充实我的小说创作。我一头扎进现实之中,在一所全是留守儿童的学校,在一个哭泣的年长的村支书面前,我的笔除了客观的记录之外,不能再有多余的讲述。
我深知,这也并非是生活的全部。回到江畔,喝茶,嗑瓜子,依然与人谈未来,这是另外一种生活。只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有个开书店的女友,说她的书店,偶尔会来打工者,满身的汗渍浓重的汗味,她迅速告诉人家书价是嫌弃他们希望他们早点离开。读了《留守女人》的某些篇章之后,“我会想到,他们的老婆孩子在老家,等他们。”
我没有崇高到要用一本书来教化他人,我只是忠实地记录。在我生活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那样生活,那样终老。我只想为她们写一本书。也为我自己留一本书。
3、出了三部非虚构,回头再来写小说,从叙述的语境,到文本的节奏,都会有所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小说创作的视野相对扩展,但也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你小说中独特的叙述气息,也就是小说的品质。你是否觉得有能力调适这两者的关系。
事实上,这是我近几年遭遇的一个创作困境。历年走访,记录,积累,从生活的层面来看,的确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一度厌弃小说,却又心心念念,饱受相思之苦。不可否认,我已走出之前絮絮叨叨式的写作,向往广度深度的叙述,然而,那些看似丰富的经历,当我试图把它们用小说的方式呈现时,气息、内容、甚至情绪的掌控,依然是纪实的痕迹。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纪实式的小说是否能成为我一段时间的小说训练。摘下一个苹果,是把苹果做成樱桃,还是吃了苹果,融入血液后,重新栽种出一棵樱桃树来。这是我近些年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4、《纸上的眼睛》,与你之前的小说有较大的区别,你摒弃了精致的叙事风格,初读有些粗犷,语言上几乎很难找出你之前的影子。你说过,这是一个纪实风格较为明显的小说,的确也能从整篇看出实录的痕迹。写作这个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那年秋天,我在皖北乡村,在一所小学走访留守儿童。那些记忆,如影随形,伴随我这些年。有个男同学上课迟到,老师问原因,孩子羞愧地说:“俺奶病了,俺要带俺奶看病。”他父母外出十一年未曾回家一次,生死不明。另一个男同学的姐姐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死,那时他跟姐姐还有爷爷奶奶留守在家。在一户农家,一个女孩羞怯地看着我,因为家里负担太重,她没读完小学,家里就不让上学了。她见了我就流泪,抽泣着直不起腰。
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总是抬头看天空,觉得他们遭受的这些,应该有一双眼睛在看,又看得见。而皖北乡村的天空,却常常因为田野焚烧玉米秆而烟雾蒙蒙。
最近一次跟老师通话得知,那些我曾经惦记的孩子,都有了不同的去处。有个男同学到杭州来打工了,老师没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我那年去的时候,他正好上六年级,“俺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就到杭州去打工,俺爸在杭州。”他的父亲到杭州打工时忽然病逝,未能回到家乡。我听老师淡然地说着这一切,忍不住,鼻子酸楚起来。写这个小说,是因为我如此地想念着他们。
5、我们曾经谈到过,你之前的创作,源于最初的情感表达,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对文学天然的热切,与他世界几乎没有关联,你也自称是没有担当意识的作家。那么,回到非虚构写作,以及你近些年的“转型小说”的创作,是一个给自己以责任感的宣言吗?要知道,没有人需要你写作,某个角度说,也没人要求你承担什么。
有一年,我跟一位写作的女友谈到我们的过去、未来,写作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我说,写到不能再写时,就停止。女友脱口而出:可我们还得活着啊。那是忽然之间的事,我想到,我们写作完全出自对时间的抵抗,衰老的抵抗,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渴求,就像我的写作从来都只关注内心。我坦言自己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作家,无论小说,还是非虚构,我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因为担当,而是出于最初的表达。当然,还是有什么改变了,因为,我会比较在意规避无病呻吟式的写作,开始从自我封闭式的关注,拓展到他者的命运认同。
6、大约在十年前,我开始接触到你的小说,文字中铺阵了大量的平静却涌动着的内心。十年,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相信这十年让你的小说也在变化着。生活与小说之间,若即若离又唇齿相依,这是许多小说家的常态。你认为这些变化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的创作?
独处时会问自己,所有这些年,这十年的经历,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年轻的时候写作,会比较随意地在作品里处置一个生命,他们的命运由我的笔掌控,缺乏适度的对生命的尊重。
随着年岁增长,就内心来说,似乎又回到原初。但有时也忽然发现,无论是写作,还是对世界的认知,成长显得迟缓而疲惫。
要一个中年女人坦言生活没有亏待自己,是不容易的,即便她从生活获取很多。归结到创作,似乎更为挑剔,甚至语言上有轻度的洁癖,不忍看某些过于残忍的场景。生活也一样,素食,常常喜欢独处,我是如此由衷地热爱独处的时光,那是我的另一个王国,没有四季,不分晨昏。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其实对于写作还是有很大的损伤,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很自暴自弃地说,大时代里,总依然是有小人物的欢喜的。
7、读你以前的小说,让我觉得你一直停留与沉湎在小我中。也就是说,与大部分女性作家的思维,行文,小说的指向等都十分接近,甚至气味。当然,并没有谁来规定,从小我到大我,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思考。
如果说有“风格”这一说,我愿意把这样一种气味一种指向的小说,归结到南方女性创作的“自我风格”,毫不客气地说,这有比较明显的自恋痕迹。如果作家没有自我警觉的话。但是,一定有问题会让这样的写作趋同,自我趋同,同为女性作家写作风格的趋同,这可真冒险。因为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你写了十年二十年小说,读者只以为看过她们一个小说。话说回来,爱情,婚姻,这是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题材,就看作家如何掌握。
这其实也是悖论,我们渴望形成独有的创作风格,又担心重复。不断探求,一次次毁灭重组,只为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或许,写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魅力,就在于此。
8、如果不写作,你会在哪里?
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一次关于“如果”的冒险。很多时候,我总是心怀感恩,感激文学收留了我。让我走在苍白的小路上,依然觉得生活是五彩的。
很多次,被某一次的写作击碎信念,我会很自然地想,如果不写作,是否会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快乐。但是,真正想象自己远离文学时,不可否认,我心有余悸。然后,在又一次开始写作之旅时享受劫后余生的幸福感。由此,即便我的文字,只为记录一只蚂蚁的一生而存在,弱小而卑微,我依然愿意保持对小说的虔诚与敬畏,以及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