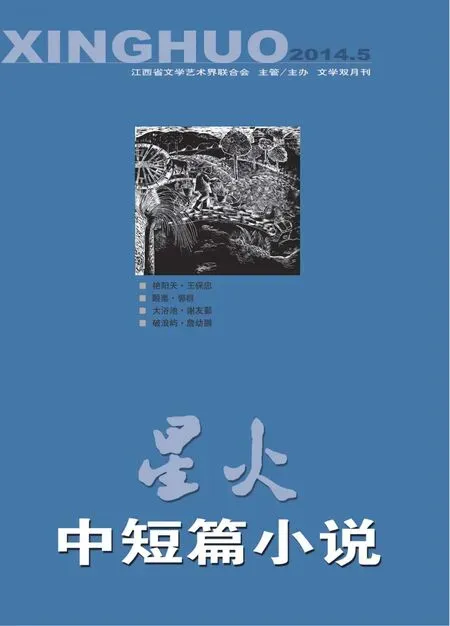苦难造就了张贤亮
○张守仁
苦难造就了张贤亮
○张守仁

著名作家张贤亮
一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因患肺癌不幸去世。闻此噩耗,我当即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怀念张贤亮》一文,以表痛惜之情。
1980年初春,张贤亮在《朔方》登出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不久,从银川到北京。我和章仲锷约他在东四三条宿舍见面聊天。酒酣耳热之际,贤亮给我们讲了他当右派后苦难的经历以及他那死里逃生的故事。
1960年“劳改”时,他曾经逃跑,想去新疆谋生。因害怕被追捕,走的是荒山野岭、人烟稀少之路。由于饥饿,他贱卖了自己戴的浪琴表,换了五碗炒面。他慌不择路地奔跑,口渴得要命,又不敢进村要水喝,恐被民兵逮住,只能忍耐。
饥馑遍地,走投无路,他只得又返回劳改农场。有一天,他犯了重病,昏迷不醒。他有一个医生朋友(也是右派)在农场干活,同时给人看病。当时,这位医生被叫到另一农场给人治病去了。农场里的人错认为张贤亮已死去,便把他抬到了太平间。贤亮在太平间里躺了一天,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身边都是死尸。他怀疑自己做了噩梦,挣扎着坐起身子,见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置身在太平间尸体中间。他勉强挪动身子,在死人胳膊、大腿中间爬动。他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太平间门口。他有气无力地拉拉门,但太平间坚固的铁门纹丝不动。不久,他又昏迷过去了。他的医生朋友从附近农场回来,听说贤亮死了,他不相信,根据平时对贤亮体质的了解,判断他绝不会死去。医生赶到太平间,打开门,把他从死人堆中救了出来。
那晚贤亮对我和仲锷说:“我既然从太平间里爬了出来,就一定能坚强地活下去。对我来说,命是捡来的。从那之后,什么困难、艰辛、贫穷、受辱,都不在话下了。我经得起各种各样的摔打,承受得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二
之后,贤亮把中篇小说《土牢情话》《绿化树》交给《十月》发表。我个人认为:1984年第2期《十月》发表的《绿化树》,是他一生所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贤亮在《绿化树》中,动用了他特殊的生活体验,描绘了落难知识分子章永璘(其实是他自己的身影)的饥饿心理。而马缨花这个年轻农村妇女的心灵美,她那清秀、纯朴的脸,她对念书人的敬重,以及苦难生活磨炼出来的坚韧耐劳、麻利能干、乐观开朗,一一跃然纸上。在以稗子、野草、树皮充饥的年代,主人公章永璘饥肠辘辘地来到马缨花家里。她竟送给他一个白面馍馍。他慢慢地咀嚼,忽然在馒头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马缨花对章永璘的怜爱之情凝结成鲜明的指纹,雕塑般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眼睛潮湿了,骤然陷入温暖的湖泊,耳边轰然响起爱之交响乐。一颗清亮的泪水滴落在馒头的指纹里,水乳交融,把两颗苦难的心,紧紧粘合在一起。马缨花在她那陋屋里多次让章永璘吃到她舍不得吃的食物,喝到土豆白菜汤。一个多月之后,他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当他穿上了她为他缝制的御寒棉裤之后,更是心怀感恩。他捧住了她的右手。她的手刚在碱水里浸过,手掌通红。他仔细观察曾在白面馍馍上留下指纹的手,并把她的手贴在他嘴唇上轻吻着。他轻吻着她的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尖,柔情地说:“亲爱的,我爱你。”马缨花的手始终顺从地让章永璘把握着。另一只手不停地、深情地抚摸着他的肩膀。她的手指怯生生地、迟迟疑疑地、微微地颤抖、迎合,既惊愕又娇羞。马缨花问章永璘:“你叫我啥?”“叫你‘亲爱的’。”“不,不好听。”“那叫你什么呢?”“你要叫我‘肉肉’!”“那你叫我什么呢?”“我叫你‘狗狗’!”章永璘情不自禁展开双臂把马缨花搂进怀里。她轻轻呻吟了一声,红着脸说:“你别干这个……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
啊,无与伦比的细节,至深至情至亲的对话,怎能不令我这个编稿者击节赞赏、感动莫名?!
三
1985年4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颁奖会。各地获奖作家、获奖编辑齐聚金陵领奖。
3月31日,我和河北获奖作家铁凝、陈冲在北京火车站一起乘车南下,在火车上遇见《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陈冲获奖小说《小厂来了个大学生》的责编刘翠林。又在软席卧铺车厢里见到了唐达成、唐因、束沛德、袁鹰、蒋和森等评委。第二天即4月1日清晨抵达南京,由军旅作家胡石言接站,把我们送到中山路江苏省委招待所。这儿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交际处,马歇尔、司徒雷登在院子里住过。
南京比北京的节气要早半个月。这儿春光明媚,空气清新。河边垂柳依依,飘着柔软的枝条。桃花开放。迎春花在春风里轻轻摇曳。紫黑的枝条上,玉兰花已挣开毛绒绒的花蕾,绽放出洁白的花瓣。就在这春色满园的草坪旁,我遇见张贤亮、冯骥才、理由三条大汉乘飞机来这儿报到。张贤亮身着西装,潇洒倜傥,一派绅士风度。南京是他的故乡,自从1951年离宁之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故里。他告诉我:他1936年12月8日出生在南京,家在湖北路一幢花园洋房里。那洋房占地七亩多,几乎占了公共汽车小半站路。花园中有一幢幢小楼,楼下有地下室。院中有棵大樟树,粗合数抱。一条小河穿园而过。河上有桥。河边有片梅林,故取名梅溪别墅。这别墅是他任国民党驻尼泊尔大使的祖父的私邸。抗战爆发之后,他们全家迁至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旧居。敌占期间,他的家变成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回宁后,他记得在他那幢楼的地下室里,还见到日本人留下的许多刑具。他至今还保留着一帧他母亲陈静宜抱着他在别墅里照的幼儿照。他对故居很怀念,说这次要到湖北路转转,看看童年的家。
我认识江苏大型文学杂志《钟山》的主编刘坪,请他下午弄辆车满足贤亮探望老家的心愿。
次日上午,颁奖会由升任作协副主席的陆文夫主持,王蒙作评奖报告。王蒙说:这次评奖,中篇小说比较丰盛。读者欢迎的是拥抱时代、贴近生活、能够说出人们心里话、艺术上有特色的作品,特别提到了张贤亮的《绿化树》。还说即使《绿化树》这样的获奖佳作,人们对它仍可能有争议。有争议是好事,越争越清楚,越争越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
王蒙作报告之后,获奖作家、编辑纷纷上台领奖、领纪念品。
然后与会者齐聚到会场前台阶上合影。恰巧张贤亮站在我身边,我问他昨天下午探望旧居有何感想。他说:“到了湖北路一看,面目全非。过去的花园洋房没有了,只有一家工厂。当时的建筑荡然无存,只有一株皂角树还留在原地。树干上钉着一块牌子:‘请勿存车’。我小时候觉得那株皂角树有两三抱粗,现在变得只剩一抱粗了。唉,童年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旁边的冯骥才听了说:“这很悲哀,但悲哀也是一种感情财富。世上多少经典作家撕心裂肺地描写了人间的悲情啊!”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张贤亮和她母亲、妹妹一起来到北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贤亮就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没考上大学,从北京迁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因在当年第7期《延河》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判为“右派分子”,失去自由长达22年之久。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贤亮获得平反,重新执笔创作。《四十三次快车》《吉普赛人》《霜重色愈浓》等稿子寄到《宁夏文艺》(《朔方》前身),因其文笔老到,立意高远而在重要位置刊发。宁夏文联领导爱才若渴,立即把他从南梁农场调到编辑部任职。这样,他和年轻的女编辑冯剑华成了同事。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们恋爱结婚。张贤亮每天骑着用28元钱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让冯剑华坐在后座上,离开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夫妻俩双双到编辑部上班。他们过着和谐美满的生活,从此佳作井喷般写出来,从《灵与肉》《龙种》《肖尔布拉克》到《绿化树》《河的子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并有多部作品拍成电影……一时文名鹊起,到处传说着“宁夏出了个张贤亮”的佳话。
上世纪80年代初,广西电影厂要拍摄根据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改编成的电影,请宁夏文联干部寻找一个适合拍摄影片的地点。张贤亮就把离他劳改农场不远、他常去赶集、那里古城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镇北堡推荐给他们。张艺谋在那儿拍完了《一个和八个》,又拍出了在国际上获大奖的《红高粱》。从此镇北堡和电影结上了缘:谢晋的《牧马人》、滕文骥的《黄河谣》、陈凯歌的《边走边唱》、冯小宁的《红河谷》、黄建新的《关中刀客》等数十部影视剧都在那里拍摄。从那里走出了巩俐、姜文、葛优等一批电影明星。镇北堡成了“东方好莱坞”,其首功应归属于懂得荒凉美价值的张贤亮。
五
1993年3月,张贤亮用稿费投资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
镇北堡位于银川市区西北,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它原是明朝为防备蒙古族入侵而修筑的一座要塞,地处要冲,具有军事价值。1740年,宁夏地震,镇北堡城墙及城内建筑物全部坍塌。清政府在原址旁修起一座新堡。新旧城堡被统称为镇北堡。辛亥革命后,清军作鸟兽散,城堡成为当地农牧民的居住点,后渐渐形成一个小集市。张贤亮在附近农场干活时,到镇北堡赶集,给北京的母亲寄过信,买过盐和黄萝卜。贤亮在复出后写的散文中,曾描绘过镇北堡:“那时,镇北堡方圆百里有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不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贤亮觉得它巍然挺立在一片荒原上,背后是蜿蜓的贺兰山,头顶衬托着碧空白云,这种雄伟蛮野的气势,视觉上特具画面感。
贤亮不仅利用影城“出售”荒凉,还给荒凉注入全新的元素,使它具有文化和艺术的内涵,从而产生高附加值。摄制组到他的影城拍电影,他从不收费,但要求剧组拍完影视后留下美工师搭建的场景,并将真实材料使其坚固化,供游客们观赏。这样,《红高粱》里的“酒作坊”、《黄河谣》里的“铁匠营”、《五魁》里的“土匪楼”、《新龙门客栈》里的“客栈”,都改建成供游客观赏的景点。张贤亮还用较低价格从山西、陕西、北京、山东等地收购来明清时代的老家具、老门窗、老雕版、老戏台、老纺织工具,充实、丰富展览内容。经过多年经营,西部影城还建立了“老银川一条街”。这样,影城就变成了“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式的主题公园。游客到影城还能听到各种叫卖声,能看到拉洋片、皮影戏、旧式婚姻……如此布置、重建古城废墟,使之成为宁夏最吸引人的景区,已被国家旅游局定为5A级景区。游客众多,收入颇丰,每年向国家年纳税一千多万。
贤亮从此成为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富人。他每年拿出150万至180万元救助宁夏贫困病人,被评为著名慈善家。过去边喝稀粥边读《资本论》的穷汉,如今变成了西装革履、驾驶“宝马”的富翁;昔日劳改苦役之地,现已成为创业、创收乐园。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时事物变化之快,出乎人们的想象。
慧眼和创新,乃天下财富之源。
六
贤亮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中说:“一个男人总是随时随地面临两种东西的进攻: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这是他的经验之说。他的前半生受到了政治进攻,因文致祸,经历了整整二十二年的炼狱之苦。在他后半生,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由于他英俊儒雅、才华横溢,不断受到姑娘、少妇们的青睐、纠缠和进攻。贤亮多情善感,也有人性的弱点,被女性久攻之下,不免陷入情网。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麻烦和不睦。
贤亮去世后,他夫人冯剑华写了一篇深情的悼文《世间再不见贤亮》,因其真诚和宽容而使我感动。同时她对前往银川吊唁的《南方周末》记者朱大可说:“他给我的幸福我接受,给我的痛苦我也接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冯剑华用文学语言委婉指出:“他并不是在一个个女人身上寻找母亲,而是在一个个女人身上寻找他父亲喜欢的女人……”冯剑华对张贤亮在外面“彩旗飘飘”有所微词和不满。
但贤亮有负责任的一面。一位年轻女郎E在笔会上认识他之后,见他风度翩翩,产生了爱慕之心,提出要和他结合。他严肃地说:“我已成家,有了儿子。我不想让心爱的儿子受到伤害,让他遭受、重复父亲遗留给我的命运。”
在《十月》上发表过中篇小说的西部B女士,跟我熟悉之后,向我详细诉说过她对贤亮的恋情以及贤亮对她兄长般的呵护和珍惜。从银川移居北京亚运村的Y女士,写了一部她和贤亮之间情感历程的长篇记述文学,转辗托人请我审读,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看完打电话给她,力劝她不要发表,说:“这段情事是你主动进攻,当时你俩都有自己的家庭,这类婚外情发表之后,对你和贤亮都没有什么好处,徒给小报刊增添一些无聊的话题。”Y女士问我:“我能否改一改,把爱情改成友情来写,然后出书。”我说:“不能。书稿中种种细节和对话,其显示的基调、场景和氛围,处处流露的是情爱的迹象,而非友谊的表示。”Y女士接受了我的劝告。
有次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相见时旁边无人,我问他关于他和美女G在上海、香港的种种传闻。他对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在上海相识、又在香港相遇的过程。贤亮很坦诚,这是他的可爱之处。
世无完人。全面地、公正地说,张贤亮和张艺谋一样,都是国之重才。贤亮是一棵文学大树,是一株高耸在贺兰山下的“绿化树”。这棵大树上长出了几个树瘤,出现三五根枯枝,或有一些发黄的败叶,无损于它的光彩和巍峨,仍因他的特殊贡献而受到人们应有的推崇、爱惜和肯定。
试问,古今中外有完美无瑕的人吗?
七
我和贤亮已有三十多年交往。我们在北京东四章仲锷家中,在《十月》石景山笔会上,在华侨大厦送他去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访问的饯别会上,以及在几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有过多次恳谈。贤亮既是改革开放后标志性的大作家,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又是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他思想前瞻,视野开阔,谈吐幽默,是个难得的文友。他曾约我去银川一游,由于彼此杂事繁忙,一直未能成行。如今阴阳永隔,看来我只能到他已去的那个世界晤面了。呜呼!
贤哉斯人,亮哉斯文;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