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柔寡断的夏济安
郑培凯
一
夏志清过世之后,夫人王洞整理他与兄长夏济安的往来书信,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年共六百多封。整理数据并输入计算机,工作量极大,费时费力,很难在几年内完成编辑工作,于是求助于王德威。王德威介绍了苏州大学的季进,带了一批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年轻人,打字编注,很快就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印出了第一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的一百二十一封书信。
近来在书店看到此书,买了一本仔细阅读,读得兴味盎然。其中最有趣的,当然是兄弟两人谈女人,特别是夏济安仔仔细细描述他对恋爱与婚姻的看法,以及追求女人过程中的自恋自责与心理挫折过程,让人联想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写斯万的处境。夏济安这种赤裸裸展示内心欲望的需求,并以极其冷静的理性分析来叙述感情受挫的过程,读起来像是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个案,令人唏嘘。这也可以见证亲人之间私密信件作为史料的重要,透露了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毫无掩饰,吐露平常羞于启齿的感情真相。
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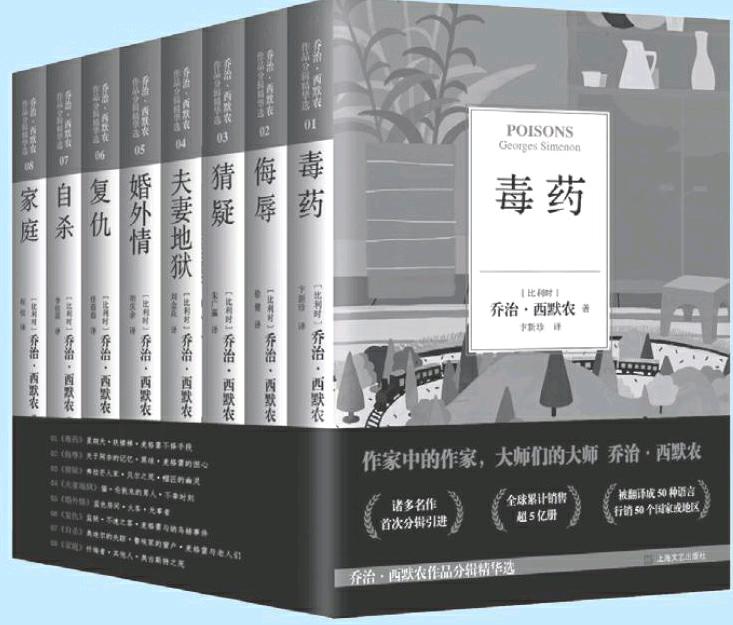
我不认识夏济安先生,但似乎又很认得他,还不只是在中学时读过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他在台湾倡导现代主义有一种模糊的景仰之情。我会不顾父亲反对,执意去读外文系,以人文研究与文学创作为终身职志,绝对与他的倡导有关,因此,他还是我进入文化领域的引路人。我考上台大外文系那年,他早已离开台湾,就在那一年逝世于美国加州;但是,他似乎一直环绕在我生活的周边,若即若离的,像原始部族中的巫师长老,在遥远的山岗上,每到夜晚乌云密布的时候,就点起一盏灯,扑簌迷离的,好像在召唤年轻的心灵,看,文字有魔法,信者得永生。在台大读书的时候,经常从一些师友口中听到各种对他的赞誉与惋惜,赞誉他对文学的艺术敏感与睿识,惋惜他流落美国,为五斗米折腰,做一些历史的研究,却又不幸英年早逝。我到美国留学,读到他的《黑暗的闸门》,觉得他批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人的激情与冒进,有更深层的人性思考,对躁动在革命潮流中的纯洁心灵,往往要面对血污的人生处境,最后陷入悲剧下场,显示了深沉的哀悼。
在美国认识了许多直接受教于夏济安的学长,如丛苏、庄信正、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等,听到更多夏先生命途多舛的故事;特别是他多愁善感,纠缠于感情世界的纷扰,分不清究竟是自己自作多情,还是意中人心有灵犀,经常作茧自缚,春蚕到死丝方尽。学生说起老师在美国的伤心事,总是有点顾忌,说得云山雾罩的,好像童话故事里勇敢忠诚的武士,遇到了圣洁的月光少女,为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少女的月光原来并非圣洁,而且阴晴圆缺不定。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唉,我们这位浪漫又腼腆的老师,命运弄人啊。我每次听学长感叹,就不禁想到,夏先生是生错了时代的贾宝玉,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情欲浪潮中,还没经过警幻仙姑的指点,就在情天欲海里没了顶。
读《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发现夏济安从来就有贾宝玉情结,而且是糅合了传统的贾宝玉与带点现代性的哈姆雷特,有着无尽的浪漫情怀,却又不断犹豫自责,徘徊在情欲与道德理性之间,整天在那里to be or not to be, to do or not to do。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他心细如发,绝对温柔体贴,是可以娓娓谈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的顶级知性上海男人。做朋友很好,假如他是同性恋就更好,还可以谈谈涂什么颜色的指甲油,戴什么样的发夹来配紫色的盘花扣,到哪一家咖啡馆去喝英国下午茶。可惜他不是,他是个对女人有兴趣的现代贾宝玉,他会动情,他有色欲,他更想结婚。
实在是麻烦得很。他在北京大学教英文,爱上小女孩董华奇,觉得自己找到了梦中情人,想跟她结婚,至少订定婚约。可是,董华奇比他小二十岁,年龄差距大是个问题,不过,更大的问题是,董小姐才十三岁,所以,他犹豫加惭愧,实在难以启齿,无计可施,只好通过写信,吐露给身在美国的弟弟夏志清。夏济安的行为,放到现在,就不是贾宝玉那么浪漫了,绝对是执法机关要抓起来的恋童癖。
他后来又遇到了一个年龄比较相当的女大学生刘璐,开始积极追求,好像颇有进展。可是,他满心还是想着董华奇,给夏志清的信中说:“我假如同别人结婚,她一定非常痛苦,我认为她很有点像林黛玉,刘璐则像薛宝钗(并非故作多情,我真有此感)。两个人我得了任何一个,我都是很幸福的。只要有董华奇,刘璐的事成功不成功,我并不怎样关心。”看来贾宝玉终究是爱林黛玉的,不过,娶了薛宝钗也幸福。可叹的是,夏济安不久就因战事逼近北平,先逃回上海,后来再逃到香港,再也没回去。也不知道,他心中的林妹妹下场如何。
三
夏济安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乘船从上海到香港。他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香港地方很好,满街汽车,无三轮车,黄包车也难得见,很整洁,有山有海,气候虽已入夏,但并不闷气,很适宜居住,你来了一定喜欢。我现在稍微不满的是住的地方太挤一点,假如一人有独用一间,那是很舒服了。”他觉得香港的东西跟上海比起来,要便宜得多。美国货,或许比美国都便宜,到处充斥着上等西装料子与讲究的衬衫。女人的旗袍料,美金才一元就可买一件。上馆子吃饭,也比上海便宜,冷饮店很多,又便宜。诸如此类的细节,把香港描绘成了当年的“购物天堂”,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逃难,还是到香港“自由行”来的。
他到香港,住在湾仔的六国饭店,似乎十分阔气,其实手头并不宽裕,住处是他投靠的老板安排的。他特别跟夏志清解释,“六国饭店并不贵族化”,设备跟上海的大中华、东方相仿,环境是不错,而且面海,正对着维多利亚港,空气倒是很好。“六国的好处是service好,茶房都懂国语与沪语,吸收很多逃难人。六国饭店似乎比上海我讲的那些饭店干净,常常大扫除,墙壁常常粉刷,电梯新近加了一层油漆。床上没有臭虫,奇怪的是香港这样一个半热带地方,竟然没有蚊子,晚上睡不用帐子。”他还发现,六国饭店住了很多舞女,有些还是以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交际花。他告诉弟弟,这些舞女流落到香港,情况就比较艰难:“舞女的开支大,据说对于客人很迁就,以谋开源,sex是开放的,不必在上海还有一点架子及种种delicacies,pretences。”他虽然偶尔接触,但保持一定距离:“你知道我对于这种妖姬,并无兴趣,我感到兴趣的是带点天真的女人。来港以后,毫无adventure,近来用钱省,更不敢有非分之想。”
好在他善于交际,有份闲散的工作,又有朋友安排,做些杂事补贴生活,曾到钱穆开办的“亚洲学院”(新亚书院的前身)教过英文,担任家庭英语教师,经常去舞厅,看跑马,虽然有点无聊,倒并不寂寞。夏济安多少有点海派纨绔习气,但个性腼腆,在北平任教北大的时候,就正式学过跳舞,却一直放不开来,跳不好。在香港陪朋友上舞厅,也经常是看人跳,自己抹不开脸面,不敢下场。倒是喜欢赌马,他说:“跑马赌钱我认为很有兴趣,经济情况如好,每次跑马我都想去花掉几十块钱去试试运气。”他认为跑马可以让群众发泄欲望,稳定社会秩序:“上海于胜利之后把跑马禁掉,实是大不智。香港假如没有跑马,一般人的生活一定要更无聊,更烦躁,做更大的坏事,而且这两个钱亦在别的坏事上面花掉。”他还说,台湾管制很严,不准跑马,不开反共群众大会,“民众只有恐惧而无发泄,这种统治一定失败”。看跑马还看出这样深刻的群众社会学心得,也算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夏济安生活过的香港,过了六十多年,香港还是地狭人挤,照样跑马,好像没变多少。
四
夏济安本来在北京大学教英文,刚升任讲师,就碰上国共内战的转捩时刻。夏济安先回到上海家中,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逃难来香港,成了当时从上海涌入香港自称“白华”群中的一员。他在香港的一段时期,跟着上海朋友学做生意,发现广东人与上海人经商赚钱的方式不同,在于社会环境的模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甚至生活追求也不同。有趣的是,他从老同学宋奇(后改名宋淇,笔名林以亮)在香港的发展,看到了“白华”转化成香港人的契机,更看到了士大夫文化精英转型成为资本主义精英的历程。
夏济安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写信给弟弟夏志清,说自己不适合做生意,因为“我的教养使我与经商格格不合”。他认为自己是封建社会的精英,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治生产,而敢于用钱,讲义气,守礼教,保守怀古,反对革新”。而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的同学宋奇,“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elite,趣味风格与我不同,因此我不会同他们很intimate。我认为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义气重要,信用都须put into black or white ……他们过着紧张的生活,不能够悠闲地享受他们的财富,拼命地赚钱,很疲劳地消费他们的钱。他们的计算精明,分毫不差,而且乐于计算,财产乃可积少成多”。他对香港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得相当深入,而最直接的认识就是来自宋奇。夏济安是出色当行的文学评论家,对社会人生有其特殊的敏感触角,又有细致缜密的分析能力,能够在生活细节中发现本质性的生命状态,通过直感掌握社会的脉动。他发现上海人与广东人的经商模式,简直是南辕北辙:“上海人常说,你问广东人买货,你先要付钱给他,他再给你货;你要卖货给他,他却要收到你的货,验对了再给你钱。上海人很少把支票退票向有司告发,据说广东人是不客气的。在香港,大本钱做大生意,小本钱做小生意,很难投机取巧,做生意失败,患难时亦不容易有人来帮忙。”
夏济安在香港初遇宋奇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与宋奇是老友,熟悉彼此处世行事的方式,曾介绍给自己做苏联生意的老板,一起合作,销售苏联肥田粉到远东各地。宋奇方面则介绍浙江兴业银行来担保,成了这笔生意的合伙人,利润对半分,并答应付给夏济安佣金。在国共内战的混乱时期,趁着各地物资流通困难,掌握商机赚钱,大家得利,本也无可厚非,至少让牵线人夏济安得意万分,给弟弟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这是他经济生活的大转机,以后或可衣食无忧了。没想到宋奇经过精密的调查与思考后,觉得其中牵涉金融汇兑的复杂性,风险很大,不是百分百的稳赚生意,于是退出不干了,也就打消了夏济安赚钱的美梦。
夏济安在香港经商不成,生活乏善可陈,基本上就是混日子,前途茫茫,就希望能得到奖学金资助,到美国去进修。夏志清帮他安排了Oberlin的入学许可,需要一笔二千四百元美金的外汇存款证明,才能申请赴美签证。他找宋奇帮忙,宋奇没能帮,想来让夏济安觉得实在不够朋友,在写给弟弟志清的信里(1949年8月5日)说:“亏得张君秋答应划一张一万五千元港币,用我的名义在中国银行开一户头,才得解决。”这也反映了夏济安与宋奇对待金钱与友谊的不同态度,而张君秋愿意拔刀相助,显然是传统义气的展现,从戏台走入了真实人生。
在夏济安眼里,宋奇在香港活得很滋润,长袖善舞,花样很多。他在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志清的信里,显然带点调侃的意味:“宋奇新开了一家小型旅馆‘星都招待所(Sanders Mansion),他的公司本来叫城大行。英文名称S.D. Sanders & Co.,他自居vice-president。这个S.D. Sanders大约是president,但并无其人,是他发明来骗人的。有一天假如真出来一个S.D. Sanders去看宋奇,倒是很合乎宋奇趣味的一部喜剧题材。”
夏济安最终离开了香港,但暂时没去成美国,退而求其次,借助他在北大教书的经历,到重新整顿的台湾大学去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