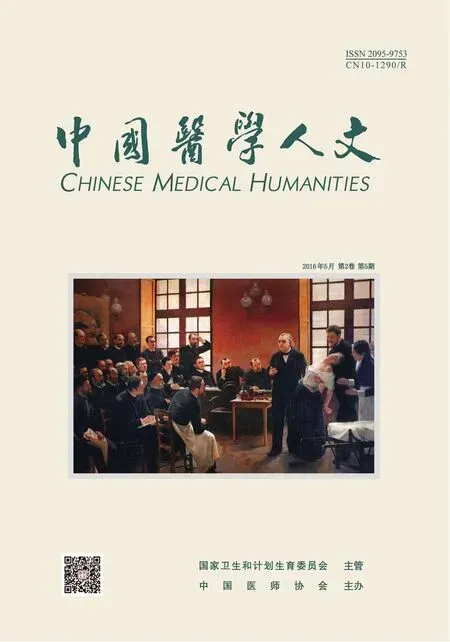一次病 赢得几多情
文/洪云钢
一次病 赢得几多情
文/洪云钢
“金钱草、海金沙、车前子、鸡内金……”美丽草药的名字,亲切动听,时而滑出记忆,列队而来。我暗自庆幸,自己有生以来的一场大病,得到了医者的真诚关照与悉心呵护。
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诊为尿路结石,在家乡的地区医院。当泌尿科医生听说我在医疗条件差的山区工作时,十分同情,建议“在城里确诊,回厂里治疗。”“两步走”战略确实是为我着想。那时B超、CT很遥远,连名词都没听说。采用拍平片、做“造影”的笨办法。拍片简单,做造影人就遭罪了,医生用特大号好像注射畜生时的特大针管,往体内注进满满一管显影剂。我被绑在垫了黑色橡皮的床上,腰部位塞进圆形的硬物压迫,难受万端大汗淋漓几乎脱虚。我把保存了30年的病历找出来复习,平片报告:16K纸复写,满满一页,共计309个字,一气呵成,无增删修改。肾图报告:坐标图上红蓝铅笔逐点勾勒出来的曲线。术语专业,一丝不苟,令我动容。
漫长的疗程,开始奔西医,继而中西结合,最后死心塌地投靠了中医。而家乡邻居陈大爷,地区医院资深药剂师,给我送来金钱草,黑色的干枯的叶茎,蓬蓬松松一大竹篮,关照道:“熬水当茶喝,使劲喝,喝完我再搞。”
草药的名字俏丽动听,可它们的汁水却苦涩逼人。近百副中药下肚,顽石仍在尿道虎踞龙盘。偶尔暴动,大痛,痛得床上打滚、剧烈呕吐、胆汁喷涌。病急乱投医,辗转打听到地区治疗结石的名医,中医院副院长史先生。慕名前往,老先生年过七旬,衣衫素净,儒雅亲和。静静为我把脉,慢慢旋开带帽的老式钢笔,用老派的字在病历上书写。接过处方,一看竟与年轻的厂医如出一辙,唉。希望中有些失望,徒有虚名?效果不言而喻,过了一周,我又来到他的面前。趁着年轻助手替他抄写处方的当儿,老先生和声细语,殷殷切切:在哪单位工作?家住哪里?父母多大?孩子好小?然后看看周围,悄悄地“晚上到我家来,给你偏方‘气气’。”先生南方人,把“吃”念成了“气”。不得不谨慎,当年谁敢私下行医?
如约赶到先生家,昏黄的灯下老人正在“气”饭,放下碗,从里屋拿出一小包东西,挺神秘。“多少钱?”我忙问,老人摆摆手:“不要钱!”我还是掏出了10元钱。见状,老人手一缩,欲将我的期盼收回。“一天一次,用加饭酒送服,记住!不能用茶水。”“加饭酒,绍兴黄酒。”怕我不懂,先生特地解释。我暗暗惊叹,尽管不是鲁迅痛恨的药引“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何处买到加饭酒?逛大街走小巷,终于在一家烟酒商店的柜台底层,如获至宝般地发现了“绍兴黄酒”。一看产地:黑龙江省某某县。妈呀,“南辕北辙”。
一小撮灰白的粉剂抖进口里,舌头“嗞”地产生灼热反应,仰头一小盅黄酒,将石灰般硌牙的劳什子冲进喉咙,黄酒草木灰浓烈的古怪糊味,经久不息,“绕口三日”。吞下12包“石灰”12盅黄酒,石头依然偏于一隅。向老先生汇报详情,目的暗示名医加大力度,或是提供更高级的秘方。史先生十分淡定,依然如故地开出了“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让我再去他家拿偏方,再一个疗程。拿第一次偏方时,我像“抱了十世单传的婴儿”,这一次时就犹疑了,到底吃不吃呢?患者到底是“小学生”,对医生的话总是言听计从。第二个疗程刚进入第三天,奇迹发生!随着剧烈的疼痛和血尿,“当”的清脆的金属声,一粒固状物击中了洁白的痰盂。霎时间,我清晰地看见了黄豆瓣似的赭色石子。兴奋得蹦了起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第二天拍了平片,结论“未见明显致密结石影”。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买了一斤鸡蛋糕、一斤羊角酥,去谢老先生。还是昏黄的灯下,老先生正“气”晚饭。见我手里的东西不高兴,我脸红,连忙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老先生叹了叹气,“怎么都是这样呢?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病治好了,你没忘记告诉我一声,不就是最好的回报么?别的都是多余的!”
那时节的医患关系很真诚,沟通、理解,唇齿相依,相互体恤,泌尿科医生、厂医、药剂师陈大爷、史先生以及我,都是赢家。时光,一块脏兮兮的橡皮擦,史老先生的眉目已被擦得模糊不清了,但他那悦耳、充满仁爱的“给你偏方‘气气’”的吴侬软语,却时常萦绕耳畔,温暖。

ICU护士精心呵护患者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