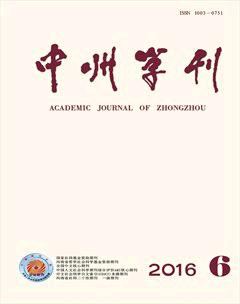心、性、气、形:十字打开的孟子工夫论
王正
摘要:孟子将自孔子提出的工夫修养予以了细致化、体系化,同时他还注重将心性和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孟子一方面以“求放心”来确立道德的主体性,进而以“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工夫来将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境界予以养成;另一方面以“不动心”而“集义”的方法养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象,从而实现道德从心性到行为的转化即“践形”。孟子这种在心、性、气、形上同时展开的工夫论,恰如陆九渊所形容的,“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关键词:心性;践形;工夫;孟子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6-0100-07
根据《中庸》以及相关出土文献的记载,子思的工夫论在慎独、节情等方面都很有创获,为儒家工夫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一方面子思的工夫论尚有不甚细致之处,另外其系统性还不是很强,因此仍有待于后学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思孟学派的另一位大儒孟子,正是在大体延续子思思路的基础上,将工夫论的精细化、系统化大大推进。而正如陆九渊所说,“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①,孟子的工夫论建基于性善的论证,进而在心性修养和践形修身两方面共同发展,从而既存心、养性、事天,又养“浩然之气”而成“大丈夫”之气象。
一、心的工夫
在孟子看来,工夫论的第一步,或者说最初的出发点,在于立志。立志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志向不立,就没有做工夫的动力;二是因为志向不明,就没有做工夫的方向。因此,一个进行儒家工夫修养的人,首先就要立志。孟子曾以“类”观念来论证立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②身体上有疾患,不像他人那样正常,人们就会厌恶自己的不足,进而苦苦寻求方法以求自己变得正常起来,而当人们的心理有问题、心术不正的时候,却常常不能厌恶自己这方面的不足以寻求改变。这表明,人们在认识上混淆了自己归属的类别,即未能把心灵上的不正常归于不正常,进而无法认识到什么是正常。因此,孟子特别强调人禽之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③人和禽兽的差别不在于生理上的差别,而在于人性上的差异,也就是人是有道德自觉的,而禽兽是没有道德自觉的。在这里,孟子通过“类”的论证,逻辑地将道德注入到了人性之中,从而真正对旧有的天生人成的人性论进行了突破,使得性善在人性中得以扎根。
由此,人立志立的不是别的志,而是使自己符合自己“类”的要求,并将自己的本性予以实现和完成。所以,作为工夫之基础和出发点的立志,就是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做的事。孟子进一步通过类比论证道:“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④人们在学习射箭的时候,都知道目标在于射中靶心,也知道必须要立志不达到那个标准誓不罢休。因此,作为与禽兽不同的一类存在——人来讲,也应立志必须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不将人做好就誓不罢休。所以,立志是每个人工夫论修养的基础、出发点。“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⑤作为士,所应当从事的事情就是确立高尚的志向,而这志向就是仁义,就是要使自己的心以仁为居所、以义为道路,这样就可以由士而达到大人,也即成德。因此,立志于仁义最为重要,也最为基础。而立志之后的工夫,就在于对心做工夫,使它能居应居之所、行应行之路,这就是接下来的工夫——“求放心”。
孟子将道德仁义通过类观念逻辑地注入人性之中后,作为道德情感的仁和道德律令的义就都是内在的了,两者应当是人心之所居和所行。但是,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⑥,所以人在相当程度上还有与动物相似的地方,如饮食、欲望等。因此,我们的心实际上是会在人类和禽兽类之间游走的,即仁义之心常常会放纵为禽兽之心,而在这个时候,人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人,而堕落为禽兽了。所以,立志立的是要使自己始终成为人,因此首先要做的工夫,就是使自己的心不能放纵为禽兽之心,而必须始终保持它是一颗人类之心。这一步的工夫,就是——“求放心”。
孟子指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⑦人们对外在财物利益的丢失常常十分警醒和计较,这是人的生物性所致;但正因为人还是人,所以应当对自己仁义道德的丢失也需要十分警醒和计较,否则人便失去了其类的归属。因此,在孟子看来,一切的学问工夫,可以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求放心”——将自己放纵而流失、堕落到禽兽层面的心追回来,使之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仁义道德,进而以仁为知情意的居所,以义为行为的标准。由此,就可以使人成为人,进而进行此后更精微高深的工夫修养。
孟子对失却本心和求放心之间的差异有深刻的理解,他曾以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⑧孟子在这里讲的是义利之辨,而义利之辨的实质其实是人禽之辨,能由仁义行的便是人,便是高于禽兽者;不能由仁义行的便是禽兽,便是低于人者。每个人的心中本来都是有仁义道德本性的,这叫作人的本心,但是人心却会因为生物、生理上的欲望而丧失掉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这就叫失去了本心。
通过求放心的工夫论,使得人可以保持其仁义道德的本心,所以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⑨“赤子之心”即是“本心”,有更高工夫修养的大人也必须以不失却本心为基础,即以求放心为最重要的基础工夫。在求得本心之后,我们就回复到了人本身,符合了人的类规定,这样进一步的工夫就可以展开了。“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⑩所谓自得就是获得其自身本具的仁义道德之心,使自己放纵走作的心重新回到本然之仁义道德中来,如此就能安居仁义,也就能凭借此先天之心而进一步修养并有所获得了。可见,求放心是工夫论的根源之处,因为放心不追求回来,就无从立本,而“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人没有求放心的工夫,本心就不立,本心不立的人,则必将无所成就。
二、心性工夫
求放心之后,我们已经使自己放纵堕落于禽兽之心的心恢复成了以仁义道德为居所和道路的本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本心发挥作用,让它来指导我们进行认识和活动。而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讲的都是本心的工夫。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工夫,但如果细致分析,则有先后之别,即尽心、知性、知天在存心、养性、事天之前。
尽心,就是让心发挥作用,那么心的作用是什么呢?孟子将人的官能分成两部分,一是大体,一是小体,而这两者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则决定了一个人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大人、小人之分,是本心和放心的差别。小人,就是本心无法发生作用,而只能听凭耳目感官的作用,于是就会被外物所遮蔽和诱惑,这样就会陷溺于财货利禄之中而无法自拔了。大人,则是本心能发挥作用,其作用就是思,通过本心的积极作用,就能有所得、有所立,如此外物就不能再蒙蔽和诱惑我,于是便能超越世俗的功利,而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本心的作用就是思、尽心,也就是发挥心的思的功能。
对于思的工夫,孟子十分重视,并提出了“思诚”的观念。这是继承子思“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思想,而进一步完善的工夫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子思讲的是“诚之者人之道”,而孟子却讲“思诚者,人之道”。应当说,孟子的讲法是对子思的一个修正。因为按子思的讲法,“诚之”的工作是由诚来完成的,而诚本身是个表示状态的词,虽也可活用为动词,但由它来讲具体的工夫,总显得主体不明了、过程不清楚。因此孟子改用“思诚”,以求将工夫论的主体和过程讲得更加清楚明白。而孟子的“思诚”实际上仍是就诚意来讲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正如刘述先先生指出的,孟子认为“人与人的分别不在禀赋上,乃在官能运用的选择上”。思是人心的功能,内在的仁义礼智这些善端,需要人心通过思来得之。如果心之思不起作用的话,人就会听从耳目这些血气官能的作用,被外物遮蔽而行不善。所以,道德实践工夫的关键在于思,在于通过思来在人心的诸多意念中进行选择,并由此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
通过尽心,发挥了心的思的功能后,人就能真正透辟地了解人性了,这就是知性。对于人性,此前的求放心其实已经有所获得,但尚未有坚实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非得经过尽心的过程才能达到。关于人的本性,孟子之前的思想界有很多种讲法:“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但孟子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就天生人成的旧观念而言,是不知类的真解,因此要想真正认识人性,就必须发挥心的思的作用,由此才能拨开层层迷雾,认识到真正的人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之所以会行不善,不是人本心本性的缘故,因为人的本心具有仁义礼智的四端,也就是人的本性是仁义礼智,是道德的、善的。可见,人性善先天地内具于人心中,因而人的本心也是善的。由此,孟子得以由人道而进至于天道。
孟子的天道观,大体是对子思的继承,他也赞同“诚者,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既是自然之天,更是义理之天,而且这两种意义互相证成、互相支持。天,生生不息,既体现了诚之道,同时又将诚道贯注入人道之中,所以人才要做“思诚”的工夫,以求合于天道。可见,天是人的根源,天道之诚也正是人性之善的根源。另外,孟子的天论也承认命运之天的意义,这是自孔子以来儒家就一直肯定的一个观念。这个意义上的天,代表了一种外在客观对人主观的限制。“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而了解到人性之本善和其先天的来源在于天,以及天对人的限制后,就是知天了。
由上,我们可以说,尽心、知性、知天,是偏重于认识论层面的工夫,是通过发挥心之思的功能,透彻地了解人性之善和义理、命运之天,从而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能力和限制所在,以及天道的内涵和法则。有如此之认识后,人又当如何具体地去行动呢?接下来要使这些认识对实际的道德生活起作用,这就是“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所谓存心,就是将通过求放心而追回的具有思的功能的本心加以操存,从而使它时时刻刻能够发挥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孟子一方面认识到身心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因而重视身的修养对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更认为存心的工夫对身有决定作用,因此他指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以身体上的大小关系来比喻身心关系上的主次问题,一方面,每个人对其身、心都是兼爱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另一方面,正如手指和肩背有大小之别,身、心之间也是有大小之别的,人不会为了手指而舍弃肩背,这表明肩背重于手指,同样,在身心关系上也是如此,心要重于身,心为主,身为次。因此,存心的工夫在孟子这里十分重要。
存心的工夫,决定了一个人是君子还是普通人。孟子认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所谓“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固然是内在的,这里的礼也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因为孟子之心是四端之心,包含仁义礼智之四端。所以存心,就是存仁义礼智之四端,而存心之法,孟子在这里提到了一种,就是自反。当别人对我不仁、无礼之时,应当反省自己的问题,看自己的心是否有不仁、无礼之处。如果发现自己没有不仁、无礼之处,那么要进一步自反,看自己的内心还有没有不诚之处。可见,自反就是通过反省的办法,保证自己的心时时刻刻按照四端之心的本心来作用。当然,自反只是存心的一个消极的办法,存心还有一个积极的办法。
存心与养性实际上是一体之两面,因为道德仁义之性实际上就是人的本心,因此养性即是养本心。所以当孟子论述养性的时候,实际上即是养心,即,使心中的本心更多地呈露而不被欲望之心所削减,这就是“养夜气”的工夫:“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注意到,一般来讲,人们在早晨初起之时,因为尚没有经受社会上种种事情的影响,因而本心尚未受到侵害;而当白天到社会上经历各种功名利禄的生活后,到晚上的时候,本心很容易就被减削殆尽了。因而孟子指出要重视夜里和清晨的时光,通过这一段独处的时间,使自己较少受欲望和功名利禄影响的本心能够呈露出来,进而体验它、认取它、把握它,从而保养自己的本心,使之不至于因白天的影响而消磨罄尽。通过长期养夜气的工夫,就可以使本心得到滋养,从而得到生长,于是逐渐在白天也能发挥作用,进而渐渐地在一整天、一整月、一整年、一生中都发挥作用。可见,存心养性是一项工夫,因此孟子也有养心的说法:“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寡欲正是为了不使欲望来砍伐伤害本心,由此本心才能得到滋养和生长,因此存心、养性的积极工夫正在于培植本心而克减欲望。对于孟子寡欲的工夫论,李源澄先生曾指出,孟子在工夫论上,一方面对于大众“不仅不绝情,而主于达情”,但同时“于私人修养,则主寡欲”,“盖寡欲正所以同欲,多欲者必不能与人同欲,两者实相反相成也”。的确,寡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使得本心得存、善性得养后,人之成德就可以有所期待,也就可以进一步由人道而跻于天道了。前面已经讲到,孟子的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就义理之天讲,存本心、养善性,即所以事天。而就命运之天讲,则是认识到客观命运的严峻性和限定性,从而谨慎地过正道的生活,而不求侥幸。孟子认为人一生中的遭遇:“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客观意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命运的无可奈何,但是明知可能有困难和危险的发生却还要去做,这就不是客观意外,而是主观松懈了。因而在尽心、知性、知天后按着所知去做,而不是肆意妄为,这样就能在命运的客观限定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本心、本性,这就叫作正命,也就是事命运之天了。
三、气的工夫
心性的修养,只是孟子工夫论中的一个面向,因为在孟子看来,心灵和身体之间虽然有主有次,但都是一个人修养成德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心灵和身体连贯为一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心性的工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和外在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光进行心性工夫,而身体和外在的行为没有进行修养,也会有问题。因此,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修养工夫,成德的工夫就不算真正完成,心性工夫也就达不到极致。所以,孟子的工夫论还有践形修身的一面,而这既与此前的心性工夫相连,因而也有心性工夫的内容;另外也通向实际的道德实践、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因而也有具体实践的内容。所以,这一步的工夫,也是很丰富的。
在孟子身体方面的工夫论中,最重要的就是养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的养成,又离不开不动心的工夫。因此,两者应当放在一起讨论。
所谓“不动心”,是和勇德联系在一起的。“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勇有两种,一是因着血气之刚强而一往无前之勇,一是发挥心之思的作用而有所权衡的道德理性之勇。孟子赞同后者之勇,因为这个勇不是以气驭心,而是以心驭气,所以是真正的勇。而“不动心”,正是以心驭气。
不动心的达到,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孟子四十而不动心,而和他争辩的告子还先他不动心。但两者的不动心却不同。“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告子达到不动心的方法有两个,即专心求言语的不可反驳和专心求心志的不可动摇,而说到底是追求言语上的不可动摇,即其理论的不可动摇。而孟子认为,这种工夫实际上是分裂的,而且是混乱的,因为告子无法处理言语和心志的关系问题,当言语不得时,却不去求心,反而只在言语上争辩,这只会陷于表面而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孟子之所以这样认为,与他的言语观有很大关系。我们曾指出,孟子认为“知言”是自己的一大特长:“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生当战国诸子百家风起云涌之时,这时候,言辞的重要意义为各家所认识,而分辨各家各派的理论言辞更是诸子重要的能力,孟子的“距杨墨”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孟子认为片面的、过分的、不当的、不清楚的言辞,并不仅是言语表面的问题,而是说话人自身的心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人自身的心的认识是片面的、过分的、不当的、不清楚的,他的理论言语才会如此。而听信这样的言语,再以这样的理论去治理国家,只会坏事。可以说,言为心声是孟子的言语观,这和他“以意逆志”的诠释观、读书法正相通。也正因如此,孟子对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达到不动心的方法,坚决反对。
另外,告子达到不动心的方法说到底是在理论言语上一味地坚定,这实际上是上面所讲的勇的第一个层次,而不是守约的办法。而孟子自己的不动心的工夫论,则是守约,即只持守于心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在身体之血气和心灵之意志的关系上,孟子显然认为心主导身,因此需要以心志来指导身体之血气,而不能是相反的次序,这是达到不动心需要注意的第一点。但同时,也要“持其志,无暴其气”。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孟子也认识到身体血气对心灵意志的反作用:“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专一的意志固然会主导血气,但外在的身体血气如果也专一起来,就会反过来主导意志。如果仅仅是因为运动或意外的影响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因着欲望的过度,那么就会令我们丧失本心,危害就大了。因此,不动心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不要使自己的身体血气泛滥不受限制。
通过坚定意志、以意志主导身体和限制血气、收敛身体欲望,我们就可以达到不动心。这个不动的心,不是仁义道德的本心,而是活动层面的功能的心,当它在活动时,不受天生人成的生理、生物、欲望之心的影响,因而不会堕落于禽兽层面,我们就能始终保持人类层面的本心。由此再进行修养,就可以在外在气象上养成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浩然之气,并不是外在之气的集合,而是内在仁义道德之心经过不断的滋养和发用而积累进而呈现于外的一种气象。通过“求放心”和“不动心”,我们的本心得以居仁宅、由义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我们得以通透地了解自己的心性之善本性和与天道之连续;再通过存心、养性、事天,我们的心性得以时时刻刻依照善来活动,进而符合天之规定性。由此,我们的心就会始终合乎义的标准,而走在仁道之正路上,这样,我们的身体就会呈现出不受欲望影响、不受外物诱惑的刚直不阿的气象,这就是浩然之气。需要指出的是,孟子在这里特别提到在养浩然之气时,要注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一方面,要把养浩然之气的工夫视为一件大事认真去做,时时刻刻去追求;但另一方面,又不可过于用力,否则会拔苗助长。前一方面的意思好理解,孟子为什么要提到后一点呢?这是因为养浩然之气的工夫是一个由心而身的自然而然逐渐积累的过程,如果过于着重结果而要求速度的话,就会偏重于外在气象而忽视内心的工夫,这样就会适得其反,丧失了根本。
浩然之气的养成,标志着人的道德修养工夫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即由心性扩展到了身体,由内在而形于外。正如劳思光先生指出的:“孟子之本旨乃成德之学,以德性我为主宰,故必以志帅气,且必以心正言。”“以志帅气,其最后境界为生命情意之理性化,至此境界之工夫过程即孟子所谓‘养气。”“生命情意若皆能理性化,则经理性化后之生命力量,即浩浩然广大无际。”的确,浩然之气的养成正是在于生命的义理化,而道德行为的最终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工夫,以使得我们的身体能最终真正地践行仁义道德。
四、形的工夫
通过以上的各种工夫,人的气象达到了浩然之气,人的道德实践得以展开,这就使得人的心灵和身体之功用都得到了发挥,这就叫践形。“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身体、相貌等等,都是天赋予人的,因此它们从根本上来讲是要成就人,而不是陷溺人的。因此,人最终是要实现身心合一于道德,即完全实现自身性善的本质于现实中。徐复观先生将孟子工夫论的核心归于“践形”,而认为践形的工夫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从充实道德的主体性来说,这即是孟子以集义养气的工夫,使生理之气,变为理性的浩然之气。从道德的实践来说,践形,即是道德之心,通过官能的天性,官能的能力,以向客观世界中实现。”
从最终落脚点的角度来说,孟子的内在修养工夫论最终指向的是“践形”说。而孟子的工夫论,特别重视身心的调适与合一:“身体,在古代儒家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论述中,区分为三个层次:心——气——形。儒家主张以‘心来统帅形体,是道德心自然渗透到人的躯体,而使人格美呈现于外,可以被感知。而且,儒家也强调把自然意义的‘气或‘血气,转化为德行意义的‘浩然之气。”而践形所达成的圣贤人格,实际上就是身体与心灵的完美重建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和谐调适。圣贤不仅是一种人格,更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是孟子工夫论中修养境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一般都将万物看作是自己外面的、与自己相对为二的,而孟子却不这样认为。其原因有二:首先在于孟子所说的万物,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是指它们的本性,是它们的本性与我的本性为一,所以我能具备万理。其次就在于孟子的万物,更多的是结合着道德实践来讲的,在道德实践中的万物所呈现的,就不是客观的了,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应然法则。比如在我们对父母的道德实践中,所呈现的理就是孝,这个孝当然不是客观的,而是我们的善本性中所具有的。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所以,我们的修养工夫中,万物就不是外在的了。因而修身践形的工夫,一是反身而诚,我们不要一味地去追求外在的道理,而应该时时回过头来关注自己,发现我们的良知良能,并按着它去做事。这样我们就能体察到自己的本性,感悟到万物的道理,乃至领会到天地的究竟,于是我们会豁然开朗,而其中的喜悦自然无法形容,也就是乐莫大焉了。二是强恕而行。我们不要想太多应该怎样对待人和物,而只要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对自己的爱推广成了对他人的爱,这样也就是仁了。因此要追求仁道、实现仁道,不需要太多智巧的考虑,只要用恕道去做,就是最简洁的道路了。说到底,孟子的践形工夫论,仍是要回到自己内心上做。因为在孟子这里,心是身的主宰,践形说到底只是使心的主宰发挥作用,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时时刻刻符合本性、本心,这样就会通过浩然之气的养成,而具有大丈夫的人格气象。所谓大丈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一种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人格,是完全按照道德和礼制去做事情的人所达到的气象,是恪守心中的道德自律和社会礼仪规范的人的标志。而这种人是不会为任何其他的东西所动摇和屈服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道的代表、正气的所在。孟子这个大丈夫的定义,下得酣畅淋漓,让人心境明畅而振奋,因而在历史上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践行,成为中华民族正气不衰的脊梁写照。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对此人格境界的一个很好的展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总之,“践形”是孟子工夫论的最终指向,是以身体这个载体将本心本性的道德之善在现实生活中予以完全完善的完成。因此可以说,孟子的工夫论是要恢复人本心本性的道德纯然性,进而以此实现人的个人道德,然后再将此个人道德推扩到社会政治的重建中去,以最终实现社会政治的正义。这也正是自孔子以来儒者对仁道的共同追求,并规范了日后儒家工夫论的基本形态。
注释
①陆九渊:《象山语录》,《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②④⑦⑧《孟子·告子上》。本文所引孟子文本均出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③《孟子·离娄下》。⑤《孟子·尽心上》。⑥⑨⑩《孟子·离娄下》。《孟子·尽心下》。《孟子·离娄上》。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梁惠王下》。李源澄:《儒道两家之论身心情欲》,《李源澄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黄俊杰:《“身体隐喻”与古代儒家的修养工夫》,《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责任编辑:涵含
Mind, Human Nature, Qi and Body: Research on Mencius′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Wang Zheng
Abstract:Based on Confucius′ theory, Mencius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et relation between body and mind.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Mencius established moral subjectivity by the way of getting back the lost mind, then brought up moral consciousness, moral judgment and moral state by the way of fully developing the kindness of the mind,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understand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preserving one′s kindly mind, supporting one′s human nature, and serving Heaven. On the other hand, he brought up a great man with the vast vital energy by the way of imperturbation of the mind. And once one person has transformed his moral consciousness to body action, he has been a great man. Mencius′s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just as what Lu Jiuyuan said, "Mencius′ theory opened everyone′s inner and outer world without any secret."
Key words:mind and human nature; body action; self-cultivation; Menc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