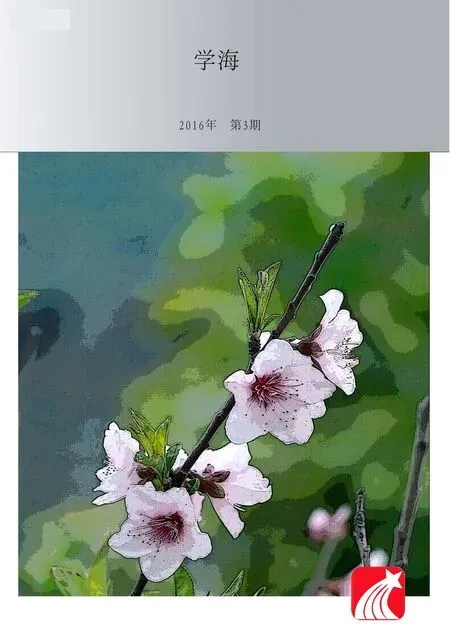资源、机制与制度: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与启示*
蒋 绚
资源、机制与制度: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与启示*
蒋绚
内容提要创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国从技术赶超到创新强国,有着独特的创新历程与治理特征。本文聚焦政府职能,梳理美国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考察政策执行下的创新资源形成、运行机制演变与宏观制度影响。美国创新资源由单一到丰富、由政企提供到多元提供,运行机制经历企业为主学研为辅、产学引领市场培育、企业主导多元参与、市场与社会环境广泛发展的历程,体现了政府以市场为核心,引导资源配置与建构运行机制的职能。国家干预型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为美国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政策与法律基础以及自由独特的资本市场。这些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形成重要启示。
关键词创新驱动创新体系美国政府制度
问题的提出
《国富论》出版以来,学界与政策界便开始探讨增长与财富驱动因素。古典经济学者认为专业分工与制度是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与基础设施投入是重要因素。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创新被视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融合体,是打破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随后,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质,并非简单提高资本有效积累的过程,而是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条件下转化技术能力为产品创新的过程。①鲍莫尔甚至认为18世纪后的经济增长最终归因于创新。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议题再次兴起,创新而非价格被视为竞争主要手段。《200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制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提升、市场完善均有助于持续增长,然其效益均逐步递减,唯创新可使经济水平持续扩展性提高。
近年,中国出口型增长所依靠的低廉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丧失。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宣告了中国“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终结,中国经济将持续以低于以往的速度增长,原本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下掩盖的低效率问题日益突出。效率方面,我国技术水平一直较低,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是未来提高经济水平的重要方式。同时,国际竞争、技术变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也加速瓦解我国要素驱动与技术模仿战略。因此,创新驱动是中国当下迫切问题。中国政府于2006年作出有关自主创新的决定,十八大期间强调“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2014年又提出“万众创新”倡议,使得创新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关注。在力图增强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中国对创新水平领先国家的学习借鉴非常必要。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同时也是创新名列前茅的国家。彭博社调查揭示,2015年市场价值最高的全球十大科技企业中,美国占有九家。美国独立后的百年里,其科学创新曾滞后于欧洲,而在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创新领先国家,发起了电子通信、生物与太空技术革命,并在电气、汽车、化学、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位于世界出口前列,成为世界经济技术强国。这些既源于多年科技与产业创新的积累,也源于一贯的创新引领世界理念。美国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其创新道路与模式有何特点?特别是,政府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与企业和市场形成何种互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使得我们对创新驱动发展过程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对探索中国创新发展政策有重要启迪。
美国创新驱动发展是各国创新领域的重要参照,因而吸引了学界一定的关注。学者们对其创新体系建立进行过宏观描述、初步探讨以及国际比较,②对创新主体的行为,譬如大学对创新的产生、转化与扩散的作用③、国家实验室的发展模式④、政府管理功能⑤等分别进行过研究;评述过特定科研政策;⑥分析了创新投入与执行乃至产出绩效;⑦对创新所需资本市场、专利、法律、技术转化条件、市场功能等分别进行过探讨。⑧美国创新研究较为丰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阶段性科技政策,尚未对美国创新体系、政策或发展路径变化进行完整探讨,割裂了政策发展连续性,忽略了创新道路中蕴含的很多研究意义,还可能造成政策深层逻辑的片面解读。现有研究对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因与机制也缺乏深入挖掘,使国家创新政策难以与相应制度背景形成对话,为经验借鉴形成潜在阻碍甚至误导。因此,有必要在一定理论框架里,深入研究美国创新驱动发展,探讨其创新政策发展的演进逻辑、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以及特定制度背景对创新政策与运行机制的决定影响。
研究回顾与框架
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学者对创新概念进行了充分诠释,大体强调创新是市场行为,需通过技术革新开辟市场,刺激经济发展。⑨之后至1990年代,创新研究多聚焦政府与市场关系。新古典学派提出政府对创新市场的间接干预和引导;新熊彼特学派强调企业主体的市场结构;制度学派认为创新与制度相互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学派认为,国家建立的体系规则会影响利用创新资源的互动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


创新政策的选择历程
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政策的强大推动作用,对创新结果形成重要影响。熊彼特认为科技创新亦是经济过程,科技系统与产业系统通常共同演变。同时,技术变革是累积的过程,过程特征显示创新体系风貌。因此,十分必要简要梳理政府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及其与世界情形和国家发展的适应性,考察其演变的现象、原因与结果。美国创新发展起步早,创新道路漫长而富有变化。本文结合美国创新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背景变化与技术和产业需求变化,将政策选择演变历程分为四大阶段:赶超模仿创新阶段、战备集中创新阶段、新经济企业创新阶段与高科技广泛创新阶段。
1.赶超下的模仿创新(19世纪中-1940年代)
19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对英、德实施经济与技术赶超,政策关注科技发展,期待通过引进、改进英国的机械技术,实现本土制造业大发展。
为吸收英国技术,美国的高等教育首先改革,采纳了德国高校的“教研统一”原则,在理论教学外,强调知识的实用和服务精神。1862年,《莫雷尔法》等系列法案颁布,联邦政府向各州赠地,以建立大学,并发展农工机械教育与研究。当时,大学科研成果属于公有,大学成果专利化与商业化必须通过科研公司进行。为革新技术,联邦政府也成立国家实验室从事研发。随着技术的进步,美国工业逐渐发展,资本与生产因规模效应而愈发集中,从而形成大型企业。大企业效仿国家实验室的集体研究形式,建立内部实验室进行研发。1890年,《谢尔曼法》出台,防止企业垄断导致创新无法外溢。国际上,政府大幅下调进口关税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为科技移民提供便利与激励。

2.战备下的集中创新(1940年代-1990年代)
二战与冷战的筹备,使美国大力发展国防技术,以信息、航空航天和新材料等技术发展为目标,聚焦航空、电子通讯、计算机产业领域。
二战前夕,联邦政府大增科研经费,成立国防委员会(后更名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以扶持大学和军用企业建立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防研究项目,集中国防技术研发。二战尾声,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出台,敦促政府促进创新,特别大力资助公共基础研究,同时继续限制公共研究专利权,并强化执行反垄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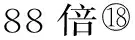
该阶段,美国在原子能与电子技术方面跃居世界首位。“曼哈顿计划”造出世界第一批原子弹;计算机、软件和半导体工业也空前发展。多个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园区”出现,如MIT校企合作下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北卡政府支持下北卡大学和杜克大学共建的“三角研究园”。
3.新经济下的企业创新(1990年代-2008年)
19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经济竞争激烈,美国经济体系向民用过渡,科技政策以新能源、生物、网络等技术为核心,产业聚焦相关知识密集型新经济。
政府针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竞争性资助,1990年到1997年对信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超20%。同时,政府为创新企业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对研发永久减税,简化企业审批手续,向企业开放电信资源;放宽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加强监督与知识产权保护,消除技术转让障碍。《技术优先法》出台,加强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授权。《小企业技术转移法》扶持小企业技术转移,资助小企业与大学、国家实验室合作,也促使企业间合作,保障重大、新兴技术研发。

4.高科技发展的广泛创新(2009年至今)
近年来,全球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开始创新驱动发展。美国近年制造业创新相对落后,同时研发成本上涨,边际收益下降,削弱了国家创新优势。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危及研发经费与创新风投。2009年的《美国创新法》及其2011年与2015年修订法案出台,将创新目标聚焦新能源、生物、先进制造、空间、纳米、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领域。创新政策强调要素投入与广泛包容创新。
要素与设施投入方面:政府将研发投入升至GDP的3%,特别加大基础研究与信息通信技术研究的投入;人才要素上,改进理工类教育,扩张社区学院,并为高中设计世界一流网络课程,同时简化技术人才签证;设施要素上,改善创新运输系统,保证宽带与网络开放、安全与中立。
广泛创新方面:政府执行反垄断法,确保创新市场准入,为小企业提供贷款,并培育创新孵化;实施研发税收永久减免,支持创客、众筹和全民参与,培训创业者,鼓励学生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开放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在信贷、储蓄和支付市场保护创新需求者与供给者;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和国家实验室创新网络;推动政府透明与参与,增强政府数据公开与利用。

创新体系演变分析
创新政策对创新体系的主体关系形成影响,从而塑造着资源与运行机制的形成和演变,创新主体识别、发展与利用资源,协调主体行为互动,形成运行结构与机制,实现创新目标。宏观制度环境作为主体互动的范围与约束,为创新资源与运行机制提供了支撑与限定。
(一)创新的资源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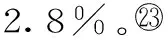
人力资源即科技型人才培养方面,是美国创新政策的重点。从赶超时期起,联邦政府便开始资助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通过对自然科学与工程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从国外引进科技专家。21世纪后,人才培育更加广泛,高中与社区学院也加入到未来创新人才孵育之中。
知识资源即基础知识发展方面,美国起步较晚。在赶超时期,美国应用技术与基础知识依靠欧洲。二战后,独立创新需求紧迫,政府开始强调基础研究带来的知识积累,交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执行。21世纪后,基础研究重要性被再次重申,大学依然是主要的基础知识发展基地。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投资从1952年的1.2亿升到2012年的310亿。
美国创新资源是政府有意识发展与利用的。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资金资源逐渐丰富,由政府少量为研究机构和高校提供,以及企业仿效政府进行自我提供,发展到政府大量为产学研提供,再到政府激励下以企业为主的产学研及资本市场的多元提供,乃至全民参与提供。人才与知识资本发展均在政府引导下,以及创新资金向联邦实验室与高校的配置下,由教育机构与研究机构提供。创新资金、人才与知识资源的形成奠定了创新活动的有形与无形资本基础。
(二)创新的运行机制演变
创新的运行机制演变涉及在新技术生成过程中,主体构成与运作结构的变化。

赶超阶段,技术是外生变量,由本土变革内化。政府资助的国家实验室与大学是新技术生产的途径。技术商业转化上,大学成果专利化不被认可,只能通过科研公司商业转化,导致公共研发数量少、规模小,研发属于少部分人的行为。美国崇尚市场经济,政府不介入企业,创新主要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手段,大企业仿效国家实验室进行内部研发,反垄断法也促进了更多企业与其实验室的形成,使大企业成为创新生产另一途径。此阶段,政府是创新驱动者,企业是创新生产与转化主体,国家实验室与大学辅助创新生产。
二战期间,政府资助大学和军用企业与联邦实验室共同研发。企业是重要技术生成力量,大学作用也十分突出,兼管重要国家实验室,并建立战略领域衍生公司。冷战期间,政府大力资助大学教研,但大学专利化持续受阻,使大学技术生产与市场脱离,1970年代末,企业仅资助大学研发的3%。1980年后,公共研究机构的公共研发专利受立法保护,大学技术转让支持性机构成立。反托拉斯法的放宽,也促进了企业间及产学研合作。大学科研规模增大,研究型大学成为科研中心。该阶段,在政府安排下,以大学与企业为核心,集中协调技术生产,形成产学协同技术转化的结构。
1990年代,民用知识经济发展,政府直接干预减少,更加鼓励市场机制。政府通过向企业提供竞争性资助,对研发减税、对企业放宽审批和放松规制,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技术生产与商业转化提供更好市场环境。联邦实验室研发也因政府立法保护而实现技术商业化,国家实验室纷纷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并加强产学研合作。1990年代末,企业资助占大学研究支出比增长到7.4%。该阶段,在政府扶持下,形成企业为核心、产学研协作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21世纪,全球竞争使政府意识到,社会力量对高科技创新特别重要。政府通过加强创新基础设施投入、人才培育和吸引、小企业与创业者的扶持与去规制、资本市场完善、知识产权保障、开放性与参与性政府建设、全民投资与参与等方式,为企业作为创新生产与商业转化的核心而塑造良好竞争环境和宽容的社会环境。该阶段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社会广泛参与的市场竞争结构。
美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整体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针对各阶段情况对市场机制进行务实灵活的调整。政府在创新伊始,扶持学研研发,间接促成企业仿效研发;二战间,对产学研短暂直接干预后,以产学为核心,逐渐放松规制;新经济下,政策激励与法律保障企业创新,并激励产学研合作;近年,继续发展为对创新友好型社会环境的积极培育。政府除战争时期外,基本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以企业为核心,角色从增长主义视角的支持物质与人力的形成,发展到新古典主义视角的对市场竞争的维持。创新驱动机制也经历了从市场与政府并驾齐驱,到以市场为核心、政府提供必要服务的动态重构过程。
(三)创新的制度影响
诚如诺斯所言,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政府为相应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适宜结构,涉及制度的重要意义。在创新领域,从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的制定,到政策下形成的创新资源积累与创新运行机制,都与所在制度密切相关。熊彼特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路径依赖为特征的经济过程,是国家特定动态结果,在国家特定制度下产生。伦德沃尔进一步指出,国家特征导致不同创新路径与特征,制度引发主体互动不同,导致不同创新结果。帕托与帕维特也认为,创新由制度环境中嵌于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技术构成,制度影响创新运行成本,制度激励结构与能力决定一国创新速度与方向。因此,在创新体系分析中,还须探讨创新的制度影响。
创新驱动发展中,美国政府通过法律与政策,将可集中动员的创新资源投入大学、科研机构甚至企业,除非常时期外,坚持市场竞争原则,引导与激励企业在竞争下创新,被“芝加哥学派”视为国家干涉型经济自由主义制度。
1.制度对创新政策与法律的影响
美国创新驱动发展以政治联邦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权力受限,创新驱动发展主要由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运行,政府起推动作用。
美国作为三权分立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不同程度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和管理。国会作为立法部门,负责科技计划预算审批,决定税收、知识产权和监管等事务,促进研发法规制定,同时也对科研项目质询、评估与认证,并出台法律法规。司法系统拥有科技法律条文的最终解释权。行政系统参与度最高,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商务部、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署、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均可提出立法建议、制定与执行政策、预算与规划科技、组织科技项目如纳米技术国家计划等。
国家干预型经济自由主义下,法律环境支撑了美国新技术的生成与转化,保证了创新资源集中,同时为企业维护了市场竞争环境。虽没有专门科技法,但相关法规确保了科研竞争力和科学家研发自由。譬如《莫雷尔法》、《海奇法案》在赶超时期支持了应用科学在高校的发展;《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降低进口关税,使工业面对国际竞争;《杜拜法案》、《技术优先法》为公共研究机构的政府资助项目提供知识产权,为公共研究成果商业转化扫除障碍;《谢尔曼法》的反垄断目标、《小企业技术转移法》对小企业研发的协助与激励,均帮助建立竞争性市场环境。法律框架下,联邦政府是创新推动者,政府资金用于公共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进入市场前的应用研究,政府建立国家实验室,扶持大学教研,引发公共科研机构对人力与知识资源的发展和对新技术的创造。对于企业,政府除战争时期对军用企业进行资助外,不直接干预企业,只进行激励与引导,并放松规制,创造国际与国内竞争环境。政府同时鼓励各机构技术转化,协助产学研合作,开放基础设施,开放政府,激励全社会的创新参与。因此,美国的制度减少了创新过程中的阻碍,降低投资风险、刺激合作和改善信息流动,使各主体创造力得以良好释放。
2.制度对融资环境的影响
前文所述,资金是创新驱动发展最重要资源之一,因而融资环境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技术与产业创新以快速根本性创新见长,其计算机、通讯、医药、生物等技术与产业发达是对该优势的极佳反映,与累进式创新相比,根本性创新具高风险高投资特性。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下,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除政府的科技创新资助与银行主导的信贷系统,发达的风险投资机制为创新企业,特别是它们的根本性创新提供了重要融资渠道,对高科技产业扩张十分有利。
根本性创新的短期高风险融资通常是风投行为,美国大资本市场通过纳斯达克市场,资助有前景的科技企业。这些融资通常是短期的,当投资高回报可能存在,风投资本家会对技术企业投资,而当企业没有实现发展目标时,资金就会停止。美国的风投在高科技类的计算机、生物、医药、通讯等产业投资比高达90%以上,并集中于创新企业的初创和成长两个融资需求旺盛阶段。

美国国家干预型经济自由主义制度背景大体解释了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实现。美国通过立法,规定与限定了创新主体的行事范围,政府在保证市场竞争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资源配置与协助创新活动的市场网络形成。同时,企业产权机构金融化,使创新企业雇主可设计管理者与雇员的绩效激励,协调风投的风险与收益,促进创新资金资源的快速形成。
结论与启示
在美国两百年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上,经历了赶超时期模仿创新、战备集中创新、新经济下企业创新,以及如今高科技下广泛创新的过程。政策执行下,创新发展所需资金、人才与知识资源相继形成并逐渐丰富,提供主体由政府与企业为主到社会多元提供;创新运行机制经历了企业为主体的学研辅助创新、到战时政府直接干预后以产学为核心的市场培育、到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创新、对创新友好型市场与社会环境的培育的历程。该过程在美国国家干涉型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下,由政府有意识的资助与引导形成,联邦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以及独特的风投融资机制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


政策层面,中国急需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中国在政府主导下,在已具备一定经济、技术积累后,土地换技术、市场换技术仍是地方政府依赖的快捷发展模式,自主创新落后。因此,应努力促使社会各界以企业为核心构建创新体系,建立完善的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从而建立良好竞争环境,加强官产学研合作,消除技术商业化壁垒,建立利益共享网络,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我国目前科研投入占GDP的2%,与创新国家相比尚有差距,政府需保证科研投入,用以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保证风险大、回收长、外溢强的项目或国家战略项目的运行,同时加强各层教育系统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对企业研发平等提供财政、税收、信贷优惠,实施部分国企私有化,避免政府对研究经费再分配。后危机时代,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应更为严格,搭建银企平台,建立评估体系,保障政策激励的公平公正。
①Kim L. and Nelson R. Technology,Learning and Innovation: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Frances Pinter,1987.
③王志强、卓泽林、姜亚洲:《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主体地位的制度演进——基于创新过程的分析》,《教育研究》2015年第8期。
④卞松保、柳卸林:《国家实验室的模式、分类和比较——基于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创新发展实践研究》,《管理学报》2011年第4期。
⑤李洁:《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政策、管理与政府功能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6期。
⑥Hemphill T A. 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do they imped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ercialisation?TechnologyAnalysis&StrategicManagement, 2014, 26(7):717-731.
⑦Mowery D C, Rosenberg N, Mowery D C, et al. Paths of Innovation -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EconomicHistoryReview, 1998, 147(4):538-540.
⑧Hicks D, Breitzman T, Olivastro D, et al.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 US — a portrait based on patent analysis,ResearchPolicy, 2001, 30(4):681-703.
⑨Mansfield E. Patents and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ManagementScience, 1986,(32):173-181.
⑩Bonaccorsi A. and Piccalug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R&DManagement, 1994,(24):229-247.

















〔责任编辑:曹小春〕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广东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项目号:GD15CGL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绚,博士,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xuanjud@hotmail.com。广东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