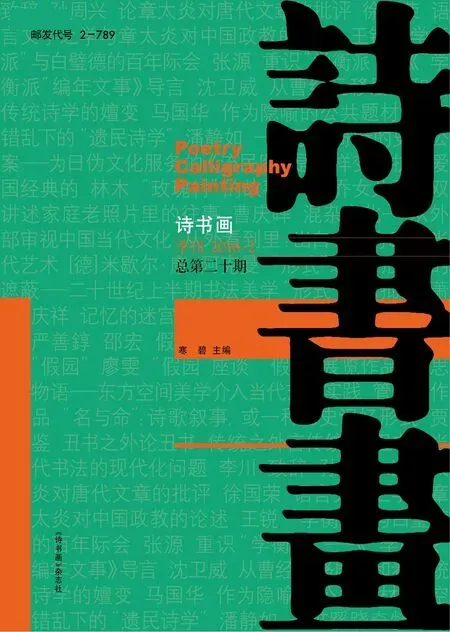作为隐喻的公共题材:时空错乱下的“遗民诗学”
潘静如
作为隐喻的公共题材:时空错乱下的“遗民诗学”
潘静如
辛亥以后,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经历“国变”的一批士人选择以清遗民自居。学术界通常还会把他们加以分类,分为政治遗民、文化遗民两类。这极大地丰富了清遗民的“义蕴”,但是在笔者看来,此间犹有“剩义”。清遗民酬唱的“公共题材”实际上蕴涵着极其隐微的“遗民诗学”,是政治遗民、文化遗民这两种范畴所不能概括的。从“遗民”到“弃民”的转变,是处在古代与现代交汇处的清遗民的特殊经历,亦即其所以不同于宋、明遗民之处。清遗民的存在与这些题材之间其实有着相当深刻的联系。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强调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题材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而是说在中国步入现代的前夜或关口这个特殊阶段,这些题材与清遗民具有某种共生的关系,或者说,这些题材与清遗民是在同一种社会范型下互为存在的。我在这里使用“公共”二字并不在哈贝马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加以使用,这是需要强调的。让我们把议题首先从两组《移居》诗开始。
一、从沈曾植到曹经沅:两组《移居》诗
民国元年(1912)七月,“遗老”沈曾植(1850~1922)移居到上海麦根路十一号,写了四首《移居》诗:
残生只合入山迁,那更移居向海壖。百尺楼高弹指见,五车书在启行先。张南周北多相识,远眺明居也自怜。不用指南重审度,景公夕室是西偏。
岑楼高建赤城标,霞思云情慰寂寥。举手径疑回若木,有怀直与欨神霄。天空一相圆于水,月海千家静不潮。如此山居元不恶,一峰更比一峰超。
乱后河山病后身,老悬海澨拜鹃魂。移家图画安洪灶,禁足光阴在翟门。剑首唐虞无起灭,卮言凡楚有亡存。崆峒仙杖经年望,一唾终消万劫痕。
随处容身一露车,隐囊纱帽竟何如?安排白伞仍持诵,不用黄神助解除。三白瓜来冰振齿,五明扇动电缠枢。披襟别有真人想,云白山青万世庐。①沈曾植《移居》,《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73~474页。版本下同。“残生只合入山迁,那更移居向海壖”“、乱后河山病后身,老悬海澨拜鹃魂”等联的确可以说是介入了自己的遗民身份。不过,这组诗在基调上是相对超然的,所谓“剑首唐虞无起灭,卮言凡楚有亡存”,毋宁说展现的是一种“逸民”心态。但是,情况很快出现了变化。
樊增祥(1846~1931)的和诗“义熙末运无安土,只有柴桑得地偏”、“德祐亡犹遗谢枋(按:用谢枋得事,德祐二年,元兵攻占临安,详《宋史·谢枋得传》),宣仁在已罢王存(按:用北宋王存事,详《宋史·王存传》,指宣统二年沈曾植开罪贝子戴振而乞归事)”;陈三立(1853~1937)的和诗“枯槁卜居能颂橘(按:用屈原事,详《卜居》《橘颂》),苍茫挥涕与添潮”、“寻源《世本》余新语(按:疑用共伯和干王位,摄行天子事,史称“共和”,详《世本》,又见《竹书纪年》,盖指袁世凯任总统事),移梦华胥署老樵(按:兼用黄帝梦游华胥国、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事,详《列子·黄帝》)”;梁鼎芬(1859~1919)的和诗“晚岁浮萍似高密(按:用东汉献帝初平,建安间郑玄避居徐州,潜心著述事,详《后汉书·郑玄传》),单身结草见阿先(按:用东汉末隐士焦先事,详《三国志·管宁传》裴注引《魏略》)”、“开元盛日寻常过,德祐师儒一二存”;杨钟羲(1865~1940)的和诗“家有辋川荒鹿柴,人疑皋羽过蛟门(按:用宋遗民谢翱于文天祥殉难后过蛟门感夫子浮槎之叹事,详谢翱《鲁国图诗并序》、任士林《谢处士传》,分见《晞发集》卷六、卷九)”、“三度卜居终未定,说经待傍郑公庐(按:用郑玄事)”;吴庆坻(1848~1924)的和诗“自著田冠逃世法,且餐橡饭受天怜”、“出世姓名人尚讶,归禅文字障难除”;吴士鉴(1868~1934)的和诗“芳时鹈鴃如相诉,晚岁夔蛇各自怜”、“琴剑西征伤往事,衣冠南渡尽高门”;沈瑜庆(1858~1918)的和诗“野史亭边几来往,凉宵清梦有啼痕”、“等身著述无年月,容膝门庭但扫除”①以上诸诗见《沈曾植集校注》附,第475~484页。,都把诗歌聚焦向了乱世遗民避居自隐这一主题。职是之故,沈曾植接下来的两组《移居》叠韵诗,也给人感觉少了第一组诗的那种超然。
推寻这背后的机制或缘由,清亡后第一年的“移居”本易触发各种联想,比如隐士逸民的隐居,或历代遗民的避乱结庐,唱和诸人用的典故,关涉的都是陶潜、郑玄、焦先、谢翱、王维、元好问等一流人物,不是隐士/逸民,就是遗民。这些“故实”本身不是“纪实”,而是指向或呈现着一个意象、一个历史场景或画面,也就是说,作者在使用它时包含着想象或记忆,形诸歌咏则是一种历史的投射。正像科林伍德强调的,对过去或历史而言,由想象扮演的那部分很可能不是装饰性的(ornamental),而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②转引自Lukacs, Joh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The Remembered past, Trans Publishers, 1994, p.20.。不止是想象,这些故实又与记忆密不可分。尽管大部分研究者都强调记忆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制,而是复杂的暧昧的文本,但记忆究竟只能是个人的,还是应当扩展到或定义为公共的、社会的、文化的,却聚讼纷如③Radstone, Susannah. Memory: Histories,Theories, Debate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s, 2010.此书导言叙说甚详。。举个例子,《晋书》卷六十《索靖列传》云“: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这里头就含有了乱离兴废的苍凉感,特别是“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的“会”字虽然是在展现索靖的“先识远量”,但赋予了历史或人事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蕴含着一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美学,因而成为了后世诗家钟爱的故实。清遗民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其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常常并不是外在于逝去的历史,毋宁说,他们本身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典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不管朦胧或具体,自觉或不自觉,作者与读者的历史意识必然根植在其中。而且,在历时性的角度上,上海在地理位置上还属于两晋南北朝时所谓“江表”一带,容易触发吴士鉴和诗所谓“衣冠南渡尽高门”、沈瑜庆和诗所谓“名士过江怨播迁”的想象,表现为一种“异代同时”或“异代同情”,他们借助“名士过江”或“衣冠南渡”这一公共的文化记忆来强化自己的亡国体验和遗民体验④侨居上海租界的清遗民还由此生发出一种“海上流人”的体验,并通过“海上流人”来强化彼此的身份认同,参见潘静如《从中心到边缘:民初“海上流人”的结社或雅集新论》,《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1期。。“移居”也就包含了多种意蕴。
一九二九年,住在北京的曹经沅的移居同样引起了数百人的唱和,但这一次唱和流露出来的意味却与沈曾植那一次移居颇有不同。先看看《借槐庐诗集》附录一《〈移居〉诗及〈移居图〉卷酬和、题咏选录》的编者按:
先生在北京日,僦居宣武城南之南横街,其间壁为翁同龢故居,而隔巷之米市胡同,则为潘祖荫滂喜斋所在,皆京师名宅也。己巳(一九二九)秋,先生移居城东隆福寺侧,有《留别南园》及《移居城东》两律(俱见《集》中),以“东”“翁”为韵。海内外诗人酬和者数百家,复得著名画家张大千、溥心畲、黄孝纾等,绘成《移居图》卷五、六帧,题咏殆遍。今图卷散佚,仅就诸家诗集与《国闻周报·采风录》残帙中,选录若干首,以见一斑。⑤曹经沅《借槐庐诗集》,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53页。版本下同。

沈曾植
现在图卷散佚,无从得见。不过,当时同人酬和、题咏的盛况,还可以仿佛一二。曹经沅原诗云:
春明景物盛城东,此地为家最酌中。晓担人知花市近(自注:地近隆福寺),夜谈客喜冷斋同(谓散释、哲维、邠斋诸子)。未妨随处成三宿,政爱哦诗出屡空。一室扫除吾事了,且浇畦菜灌园翁。(《移居城东,蹇庐枉诗,次韵》)
横街地近耤坛东,岁岁槐阴满院中(旧居左右邻有老槐两株,夏日扶疏,可以忘暑,汪君巩庵为作《借槐庐图》)。隔巷书声滂喜接(米市胡同潘文勤滂喜斋,今为坡邻僦居),连墙诗老放庵同(谓移梳丈)。南洼雅集何能忘,北海清尊总不空。付与梦华成掌录,比邻八载话瓶翁(南园间壁为松禅老人旧居)。(《叠韵留别城南旧居》)①《借槐庐诗集》,第99页。
针对当前高校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同时考虑课程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信息交流的复杂过程,存在动态性、多因素性、模糊性等特征,论文提出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证研究。
曹经沅的《移居》诗之所以引起同人的酬和、绘图、题咏,除了因曹经沅创办《国闻周报》而建立起的名声和威望外,我们觉得,宣南南横街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人文要素特别是有关同光的记忆和想象是一个重要因素。于他们而言,曾经歌于斯、游于斯的翁同龢、潘祖荫乃至无数的晚清名士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因此,与沈曾植的那次移居不同,在清亡将近二十年以后,此次同人的唱和诗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亡国之痛,有的主要是人世沧桑后对人文掌故的追寻和对翛然自适的遗民生活的“满足”—这种满足当然也含着聊以自慰的意思。袁励准(1876~1935)的“犹恋旧邻难买得,觥觥名辈有潘翁”、陈宝琛的“铜狄摩挲还醉此,梦余如对霸城翁”、樊增祥的“昔铸铜人曾眼见,猗嗟吾与霸城翁”、杨钟羲的“平津阁下来三度(己酉、己丑、庚寅三次借居鄂立亭阁读所,章佳文勤、文成、文毅后人也),明照坊南感五同(乙未至己亥,与刘正卿同年同居明照坊、同榜、同官、同分校、同在国史馆会典馆)”、张尔田(1874~1945)的“从今世事无烦问,赖有吾庐著此翁”、王乃徵(1861~1933)的“千年故物巢痕扫,九陌春光梦影空”、赵熙(1867~1948)的“不分京华作边塞,且将皇古泝咸同”、卓孝复(1855~1930)的“京华卅载头如雪,剩得旁人唤作翁”、王式通(1864~1931)的“庄襟老带踪何定,岐宅崔堂主半空(东城华屋,多易新主)”、林志钧(1878~1961)的“远书为报陈无己,能念宣南一秃翁”、江庸(1878~1960)的“惟此旧京堪共隐,江湖何处著渔翁”、叶恭绰的“剩饲丹砂偕鲍靓,移家图写葛仙翁”、夏敬观的“庙市借春妨意尽,宫[宣]南温梦欲谁同”、李宣龚的“倘作盖公堂畔饮,不辞歌舞对衰翁”、李宣倜的“世风骚雅成尘土,犹对贞元几老翁”、夏仁虎(1874~1963)的“疏柳荒陂响活东,幽居不碍在城中”、由云龙(1876~1961)的“遨头屡向禁城东,佳椠曾收古寺中(曾于隆福寺中得明椠《诸葛忠武陶渊明合集》,即钱辅宜所称博收数十年而不得者)”、谢无量(1884~1964)的“抱膝定知多好咏,小车排日会诗翁”、黄侃的“惟应画本添名胜,谁作他年耐得翁”、陈曾寿的“故国已惊朝士尽,胜情还与昔贤同”、陈夔龙(1857~1948)的“闻见四朝搜日下,輶轩四国采风同”、袁思亮(1879~1939)的“借枝犹近上林东,劫后觚棱在眼中”、何振岱(1867~1952)的“治圃故应吾辈事,消寒欲与疏霜菘”、乔曾劬(1892~1948)的“此心安处知何在,试叩南迁玉局翁”②以上引诗见《借槐庐诗集》附录一,第253~264页。,大体都寄寓着这种情怀。
两种不同时空的“移居”,从民国元年(1912)到民国十八年(1929),从上海到北京,从沈曾植到曹经沅,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遗民心态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清遗民士大夫的亡国之痛似乎在逐渐变得淡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结庐人境、颐养天年的情怀,一种依恋往昔生活、珍爱旧时文物的心态,居于他们的表达的中心地位的,不再是清亡的刺痛,而是体现了传统秩序的生活方式、熙隆的文治、对于往昔生命的眷怀以及置身世变之外的逸民心态。这还有大量的旁证,比如在曹经沅《借槐庐诗集》中一再出现的“蟠胸诗史话同光”、“即论盛事殿同光”、“想见同光是盛时”、“蟠胸历历同光史”①《借槐庐诗集》,第27、27、65、122页。就都透露出这种消息。与之类似的,比如郭曾炘的“记与高轩留款洽,同光朝事颇罗胸”、“京尘留滞年复年,同光已是羲皇前”②郭曾炘《匏庐诗存》,《清代诗文集彙编》7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3、105页。,甚或邵瑞彭的“人物同光委劫灰,先朝玉殿亦蒿莱”,寿玺的“乾嘉人物渺难俦,盛业同光委胜流”③邵瑞彭《师郑先生举瓶社以四月二十七日为翁文恭公作九十生辰招同人集江亭赋此奉呈》、寿玺《同题》,孙雄编《瓶社诗录》卷一,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26、134页。,念念不忘的都是恍如隔世的同光朝人文掌故。同光/光宣朝当然是清朝的一部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追忆同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忠清。最简略地说,“同光/光宣”承载的是一个有关文物、人物、衣冠的文治符号,特别是近代以来价值秩序、文化范型和自我理想的失落更刺激和强化了他们有关同光的记忆和想象,从而当曹经沅从“南横街”移居至隆福寺的时候,他们情难自已,感慨万端。换句话说,“南横街”既是空间,又维系着时间。曹经沅从这里“移居”他处,恰似带走了—同时也唤醒了—那里的记忆。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与其说他们遗于“清”,不如说他们遗于“同光”—不仅作为“历史事实”的同光,也作为“文治符号”的同光。
不管是沈曾植的“移居”,还是曹经沅的“移居”,都成了唱和者得以言说的“津逮”。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九年,从沈曾植到曹经沅,同是“移居”,其意味乃迥然不同。题材之作为题材,藉由吟咏者不同的处境与心态而获得新的意义。在这里,“移居”乃是作为一种“隐喻”而存在。按照西方的经典理论,所谓隐喻(Metaphors),乃是不同的高级体验域(superordinate experiential domains)中两个概念之间的映射,将源域(source domain)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④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隐喻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涉及语义理解的认知机制。因此,隐喻从本质上讲不是语言表达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思维层面的问题⑤“隐喻”最基本的一种形式是“名词隐喻现象”,它有助于我们去了解“隐喻”,参看李强《基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的名词隐喻现象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移居的本意是从一个住宅迁移到另一个住宅。沈曾植的“移居”,唱和者冥会的乃是“亡国”或“覆巢之下”的“迁徙”;而曹经沅的“移居”,唱和者冥会的并非空间上的迁徙,乃是时间上的潜移—从“同光”至“现在”,曹经沅的“迁徙”,仿佛顺带着还带走了属于他们的时光,所谓“梦余如对霸城翁”。
二、作为隐喻的“公共题材”
不光“移居”题材,像宋遗民郑思肖画兰卷子、元朱玉的《灵武劝进图》一类的直接的遗民题材,或杨钟羲《雪桥诗话图》、孙雄《感逝诗卷》一类的有关“国朝”特别是同光掌故的题材,除非清遗民们要刻意避开,否则他们很容易会流露出遗民意识,至少是遗民意味;其次,像天桥酒楼、夕照寺、重九、东坡生日这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点或日子的题材,是历史的、人文的综合存在物,也容易触发典型的文人幽情,进而因人而异地介入自己的遗民身份。这正是题材作为隐喻的体现之一。然而,这体现的还是某一具体题材的指涉或诱导功能。我们将进一步把清遗民唱和的公共题材视为一种类型,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隐喻功能的整体,来考察清遗民是怎样一种存在。
追溯起来,宋代以后,古典诗歌的题材变得异常丰富,一只苍蝇、一个虱子、一阵喷嚏、一条蛆虫,再怎么“俗”的东西或事物,都会引起诗人的兴味,写在诗歌里头,而且不光是提到而已,还有比较细致的描写⑥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不少学者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立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士大夫文化的世俗化,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元、明、清的诗人在整体上似乎消退了这种热情—明公安派、清性灵派的诗虽然号称求俗,但题材的选取、语句的使用是有选择的(也许因为对苍蝇、喷嚏、蛆虫的描写功能分流到散曲、小说里的缘故),往往要俗出神韵和味道来,不过恰恰因为如此,我觉得明、清的这种文学现象与“市民”兴起之间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因为这意味着一批士大夫有一种反省的态度和反抗精英主流话语的精神。这种态度和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我们比较倾向于把宋代诗歌这一类题材的扩展放在文艺演变的内在理路来看,亦是一种求变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尝试①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了一些,不过,都不算深入。详见杨坤道《宋代诗歌的陌生化美学特征》,《文学欣赏》2007年5期;崔现芳《因难出奇:“陌生化”与“白战体”》,《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从而可以解释它为何并不具备长久的延续性。近代以来,社会的变化十分剧烈,旅居上海的很多文人士大夫率先体验到“现代性”,从而其诗文小说、行为、思想和认识确实流露出与传统士大夫相当不同的成分;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少属于传统社会的绝对精英的范畴。之所以要做这一番梳理,是因为大部分清遗民诗文的题材和审美是拒绝“现代”的;哪怕像张荫桓(1837~1900)、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这样“博以寰球之游历”②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卷首,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描摹异域风光的名大家,使用的语言、意象和追求或隐藏的美学仍然是古典的。近现代旧体诗人的诗集有大量的描写现代事物的诗歌,但是在笔者阅历所及的清遗民诗集中,看不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题材的选取表面上是美学或趣味的问题,但确实隐含了清遗民的角色认同、精英意识、文化洁癖和他们自身由礼俗社会塑造出来的诗意的存在—确切地说,是残存;他们的那种寓托于生活和自身的诗意,在现代已经被摧毁,现代的诗意常常是要向这个世界重新寻找和创造。
隐喻这个词也许被用得太滥了,但是,就像上面分析的,题材的选取确实是一种隐喻;从这里出发,可以解读出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包括对清遗民现象的更加细致的认识。从大量的别集、唱和集、诗社文存和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共题材。现在只就阅历所及列一些遗民唱和的常用题材,并把这些题材分为三大类:
1.胜地类 香山 玉泉山 陶然亭/江亭 万柳堂天桥酒楼 斜街 南横街(宣武城南) 查楼菊部 龙树寺 戒潭寺 慈仁寺 碧云寺 崇效寺 夕照寺 什刹海畿辅先哲祠 琉璃厂 水西庄 乾隆柳墅行宫 哈同花园豁蒙楼 莫愁湖 鸡鸣寺 乌龙潭 私人庭院(比如花近楼/樊园/鉴园/藏园/稊园/栩楼/苍虬阁/水香簃)……
2.节日类 立春 花朝/二月十二日 清明 修禊日/上巳/三月三日 端午 七夕 中元 中秋 重九 冬至 腊八 消寒 浴佛日/四月八日 东坡生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渔洋生日/八月二十八日 同人生日 ……
这些题材常常是有交集的。通过这个极其简略的陈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充当清遗民酬唱的公共题材都是生活的,或者说都属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范畴(areas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life),因而在这些礼俗的、韵事的、诗意的、历史感的、文化气息的题材之中—特别是考虑到他们与宋、明遗民置身在不一样的时代和场域之中,亦即他们处在中国步入现代的前夜或关口,被社会映衬为另一种存在,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愿意或天然地、自然而然地会融入自我的遗民身份和遗民体验。很显然,这里的“遗民”一词的意义不完全在宋遗民、明遗民那样的概念上发生。
上文的两组《移居》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当清亡二十馀年后,清遗民已经逐渐不再汲汲于爱新觉罗氏政权的得失。那么,为什么他们与五四新民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仍不可消泯,特别是从当时大量的舆论包括五四新民的各类文章来看?正是在这里,清遗民之间赖以唱和的公共题材作为一种隐喻、一种区隔了“遗民”与“新民”的隐喻出现了。
三、时空错乱下的“遗民”与“新民”
按照前面的论述,充当清遗民酬唱的公共题材都是生活的,或者说都属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范畴,因而他们的题材是礼俗的、韵事的、“诗意的”(也许应该避免使用这个词)、历史感的、文化气息的。我要格外提醒的是,这些题材即是生活,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但进入十九、二十世纪特别是一九二〇年代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胜出和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实际改变,所谓“现代性”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舶来词,而是侵入到了中国的都市生活中。也正是在一九二〇年代,以胡适的《尝试集》为起点,现代新诗开始了它的征服历程。同样称为“诗”,但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是大部分人都承认的。要比较二者的差异,可以从语法、词汇、结构、意象等各方面展开,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本文要做的是,借助于新、旧两种诗体,从“题材”出发来说明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得清遗民与五四新民成了完全两类人。在忠清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促成这二者的分裂甚至对峙?

《尝试集》
上个世纪中叶台湾曾兴起“现代新诗”是“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的讨论,提出“现代诗是成人的诗,传统诗是小儿的诗”①纪弦《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现代诗》第35期。。现代新诗对古典诗歌的替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一环。它背后隐藏着现代人的认知模式、美学趣味的转变,而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传统的士大夫公共生活本身就是题材,但在新诗人或理性的“新民”那里,这一切变得迂腐、陈旧而了无新意,他将寻求别样的生活,—事实上,他的确置身在别样的生活中。从认知模式到美学趣味,每一范畴都体现着这样的背离。于是,题材就作为一种隐喻而出现,在新、旧诗人之间划出界限,在“新民”“遗民”之间划出界限。我在这里用“遗民”或“新民”一词,显然不是从忠不忠清、亲不亲近儒家文化的角度立言,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区分也是有迹可循的。就认知模式来说,二者的分际很像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拈出的“天理”与“公理”两个框架,但由于在后世的使用中,“天理”一词带有强烈的儒家文化气息,我不愿把讨论局限在这里。我不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与儒家文化相勾连。根本上,这些“遗民”乃是遗于古老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英译community),正如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托尼斯(Tonnies)及其后的沿用者所观察到的,在工业时代或者说“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英译society)确立以前,“礼俗社会”是遍布于全球各地的。过去通过英译而译成“共同体”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一词语的核心意义②与之相对的,Gesellschaft/society就被译为“社会”。根据维基百科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词条,托尼斯的著作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曾被译作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logy (1940)。按:这是以托尼斯原书的副标题为书名,大约翻译者觉察到正标题的不易翻译,所以这样处理了事,又曾被译作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1955),直到1957年才被译作Community and Society,并被最广泛的接受下来。此外,中国学者蒋永康梳理了“Gemeinschaft”一词在德国文献中或者说德国相关学者眼中的意义,但奇怪的是,他恰恰把韦伯给漏了,详见蔡永康《德国文献中的“Gemeinschaft”》,《社会》1984年4期。。依托尼斯之见,礼俗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角色、价值、信仰都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上,而法理社会则属于间接的社会关系,非个人的角色、正式的或公开的价值与信仰都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上③To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Happer & Row,1963.这一版本的前言简单列述了有关两种社会范型的学术史和代表人物,从柏拉图一直到1960年代的索罗金自己,可以参看。。马克斯·韦伯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对此作了扬弃,他认为Gemeinschaft是根植于个人的直观感受,亦即情感的或传统的直接感受,而Gesellschaft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根植于互相协定的理性契约,商业合同就是最好的例子。一言以蔽之,“礼俗社会”是一种以“自然意志”为主导的“理想型”(Ideal type)社会。儒家文化是礼俗社会的产物,当然保留了这诸多特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在英译本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前言中提到的,以社会伦常而论,托尼斯给Gemeinschaft归纳的母亲与孩子,父亲与孩子们,兄弟姐妹们,朋友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们这五重关系,特别接近孔子所赞扬的父子、兄弟(长幼)、夫妻、君臣、朋友这“五伦”(five fundamental social relationship)①Pitirim A.Sorokin. “Foreword,” Community and Society, p.7.按:其实索罗金所说不确,这五伦不是孔子提出的,乃是孟子提出的,见《孟子·滕文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局限于此。我们认为,当我们介入到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分野的时候,托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礼俗社会是以“自然意志”为主导的理想社会的这种分析,给了我们跳出儒家文化框架之外的启示和灵感。
伟大的天才评论家本雅明曾论断道,相比于古典艺术,现代艺术正在失去它的“光晕”,—这是复制时代的一种症候。事实上,现代与古典之间的区别是全方位的,这种区别也将渗透到艺术世界以及创造了艺术世界的主体—人—之中。据哲学家看来,在传统社会,“德性”寓于“业行”之中;步入现代以后,“业行”转为“职业”,德性与之相分离,不再浑然一体②参见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对于中国的古典诗人、现代诗人而言,这个观察同样切用。我说古典诗人是一种“业行”,现代诗人是一种“职业”,并不是说现代诗人靠写诗来挣钱吃饭,而是说就写诗场域、写诗过程和写诗目的而言,现代诗人一落笔,就在承担其作为诗人的责任,展开对“意义”的追求或创造,—这一“意义”超出于自然之外、也超出于生活之外,它是“现代诗”的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称“现代诗人”是一种职业,一种追求或创造“意义”的职业。这使现代新诗可以触及到古典诗歌所无从到达的幽深邃渺之境,从而也可以更深刻地观照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然而它终究不是生活本身。因此,传统所谓“诗意的”一词,在现代新诗这里完全失去了效用,现代的所谓“诗意”可以在任何媒介、任何事物中获得,但这种“诗意”不是自明的。为此,我想打一个比方。在传统社会(甚至今天偏远的山区或乡村),“草地”是个一望无际、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上面打滚甚至撒尿,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存在。但在现代社会(我指的都市)的公园或小区中,我们人造了一块块草地,通常唤作“草坪”,通常还树立各种“禁止践踏草坪”的警示牌③“禁止践踏草坪”的“警示牌”,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它与现代艺术的同构性,这一点,曾与冯庆兄交流过。譬如,(后)现代艺术家可能随手洒下二十五个米粒,告诉你“这就是艺术品”,你不能否认,否则你就已经侵犯了我的艺术,彼此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其实,现代艺术的这种“宣言”或“警示”,正同于草坪上的“警示牌”。草坪与作为自然存在的草地之于我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草坪”也许是为了生态或环境的绿化,抑或是为了城市风景的点缀,总之有它自己额外的目的;在这里,“草坪”的定位就变得非常可疑,或者说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好像的确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外在于我们的生活的。“草地”与“草坪”的这种分野,在我看来正是古典诗/人与现代诗/人的分野。
作为隐喻的公共题材,恰好在这里找到了安放之地。在古典诗人那里,看花、登高、宴饮既是诗歌的题材,也是士大夫的公共生活,诗只是这一生活的“羡余”,诗内、诗外,是比较好的交织融合在一起的。现代诗人就不同了,他愿意通过一个街道邮筒、一个工业烟囱、一辆公共汽车来写现代人的孤独、寂寞或犹疑,但看邮筒、看烟囱、看汽车却并不是他的生活,尽管他完全可以强迫自己一整天地盯着邮筒、烟囱或汽车看。就登高、看花、宴饮这些题材的诗歌来说,依然有很多篇什攫取我们的心魂,使我们获得愉悦。之所以如此,可能由于这乃是礼俗社会中我们与自然或生活相融洽的原始记忆,它不需要过分地追求意义(追求意义是理性的内在要求),它只需提供一种直观感受,一个我们在场的代入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潜在的“遗民”。这正是我们—全世界—不断地反思甚至反对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在现代社会,我们感到不适。“反现代化”是“遗民”的一场“复国之梦”。
结论
准上所论,在“遗民”与“新民”之间忠不忠清就不是唯一的甚至主要的区分要素。我们相信正是上述事实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持久的隔阂与疏离。换言之,这一意义上的“遗民”,是作为礼俗社会的孑遗而存在,这使他们与易代之际的政治遗民相区分开来,也与通常所谓文化遗民有别。当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步入现代的前夜或关口,慌乱之中,这些“遗民”以“清遗民/政治遗民”或“文化遗民”的面目问世,他们“骗”过了自己,也“骗”过了世人。但作为隐喻,登高、看花、宴饮这些传统士大夫生活的公共题材,依然在提醒我们另一种认知模式、另一种美学趣味和另一种生活。这是他们与五四新人格格不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根本原因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