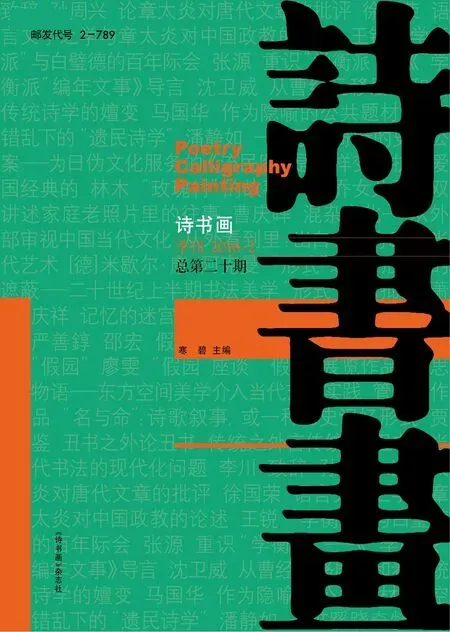“学衡派”与白璧德的百年际会
张 源
“学衡派”与白璧德的百年际会
张 源
一、引言:“学衡派”的“帽子”问题
《学衡》杂志及随之得名的“学衡派”从诞生之日起,便没有受到严肃的对待。不论是自鲁迅《估〈学衡〉》①原载《晨报副镌》,1922年2月9日,署名风声。之后的各种批判文章,还是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②该文作于1922年3月3日,原载1923年2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之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论),多以“掊击新文化”的“反对党”目之,而草草一笔带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学衡》及“学衡派”的名誉再创历史新低,如在王瑶极具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③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当中,“学衡派”人士成了“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进入“新时期”之后,《学衡》的声誉每况愈下,直至一九八九年仍被目为“恣意诋毁新文化运动”的“守旧复古势力”④鲍晶《“学衡”派》,《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第189页。。不过,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保守主义”思潮在全球的“复兴”,人们开始对“文化保守主义”焕发出极大的同情,相应地,对《学衡》的热情亦随之高涨,不少研究者开始站在“学衡派”的立场批驳当时的“激进派”,从而陷入了与先前的论战模式相同的逻辑理路,不免同样沦为意气之争⑤90年代末,学者李怡曾针对“先前的近于粗暴的批评”及90年代以来对“学衡派”“近乎理想化的提升”,就其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作了极为出色的“重新检讨”。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翻案”文章,事实上,这种以“翻案”、“摘帽”为特点的文章在历史进入新千年后亦屡见不鲜,如二○○二年出现了《八十年沉冤案要翻》⑥这是一篇颇有影响的网文的题目,作者为李汝伦,文末注明日期为“2002 年9月26日”。这种戏剧性的题目,为“学衡派”激情抗辩。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们对《学衡》的学理探究逐渐增多,但同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流批判话语仍旧势头强劲,并活跃在各种批评文章及现代文学史中。仅以“现代文学史”为例:自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中一般都会为“学衡派”开辟一个专章,而这些专章往往一律题为“对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事实上,这一“学衡派”“专享”的题目本身已经“经典化”,作为一种“套话”代代相传而沿用至今,直至进入“新千年”之后,我们仍可看到这一整套的批判话语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学史中,相信今天应该已经出现了更“新”的版本。
也就是说,直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对《学衡》及“学衡派”的讨论仍有不理性的成分在。一方面,今天“新文化派”的精神后裔们不假思索地简单继承了当年的主流批评话语,在坚持“五十年不变”的同时,在愤怒声讨当年的所谓的“保守派”的同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功转型,实际上已经成为今天的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保守派”。另一方面,那些大量的为“学衡派”激情申辩的“翻案”文章,其运思理路主要不外有两条:一,为“学衡派”辩护,说明其并非“保守的”,从而其潜台词似乎是说“保守”确实是不好的,这实际上便与“新文化派”的价值取向趋同;二,或者进而为“保守”辩解,说明“保守”本身其实并不坏,那么“学衡派”的“保守”也就是好的,从而当年的“激进”自然就是不好的,结果便一笔抹杀了当年社会思潮转向“激进”背后之巨大的合理性。这些辩护各有其道理,但认真想来,当我们说“学衡派”是“保守的”外加“反动的”,或者反之,是“前瞻的”、甚且“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帽子”戴得“莫须有”,固然令人不平,可如果旧帽子摘得潦草,转而又匆匆戴上了另一顶新帽子(当然这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帽子),这是否也令人生疑?—如果“帽子”的“戴”与“摘”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那么其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就可能会遭到忽略。
二、现代中国与美国:“自由”、“激进”与“保守”
一般说来,与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对应,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亦具有“保守”、“自由”、“激进”等若干面相。最能彰显其“转型期”时代特点的是,这些思潮中都各有某些思想成分可以找到其远在西方的“祖庭”,并且当那些源自西方的思想元素进入中国与中国本土元素相结合、产生出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之后,这些新的形态复与其西方“原型”构成了一组组相映成趣的“镜像”。如胡适等“自由派”,即“新文化派”的“右翼”,继承了其美国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新文化派”的“左翼”,即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派”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尚有“新文化派”的“反对党”,如“学衡派”等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移入了其美国导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激进”、“保守”的三重变奏,实系通过汲引不同的西方思想元素,针对中国形态提出的同一个题目—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给出的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在今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以上“激进”、“自由”、“保守”的三分法,仅是为我们论述方便而给出的一种用以宏观审视世界(包括中国)现代思想格局的大致构架,不能当作某种固定不移的最终表述。
比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来源地之一的美国,本身并不存在“真正”的、或云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①美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如美国独立战争前夕(乃至战争期间)出现了一批数目可观的少数派,这些经济、社会乃至心理等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站在英国一方与殖民地同胞对立,这些“殖民地时期的保守主义者”(colonial conservative)被当时愤怒的殖民地人民斥为“托利党”(Tories,此即支持英国王室的“保王党”Royalists),但这所谓的“托利精神”(the Tory mind)在独立战争之后便彻底失去了市场。See Leonard Woods Labaree, Conservatism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Ithaca, New York: Great Seal Books, 1959, pp.143-170.。不但“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激进主义”也从未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唯一的思想传统,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本土自始至终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美国思想史家钱满素曾如是描述“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欧洲相比,美国从未存在过普遍的封建和教会的迫害,故而既缺少真正的反动传统,也缺少真正的革命传统,欧式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与美国无缘”,“而这种没有敌人的美国自由主义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乃至有时被称为‘保守主义’”②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该书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整部美国历史亦是一部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发展史,如“内战”原是“自由主义清理门户”,而“新政”无非是“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而“新左派”的出现则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继续左倾”等等,种种精彩论述不一而足。至于美国何以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工党,社会主义亦从未进入过美国思想的主流,根据钱满素的分析,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面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第137页。。如果一定要讨论所谓的美国的“保守主义”,首先要明确它并不具有一整套固定不变的政治原则与意识形态,而仅仅涉及一个不固定人群的态度、情感与倾向,它仅代表了人们维持现状的愿望与“保守”既定习惯、秩序与价值的心态,而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要“保守”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与价值,从而美国式“保守主义”的核心实为自由主义。因此,当人们试图区分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时候,便会注意到在美国这两种“主义”的“核心理念”发生了奇特的错位现象:“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乃是“自由”,它“保守”的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而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则是“平等”,它代表了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根本信仰③Claes G. Ryn, “Dimensions of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s’”, Humanitas, vol.XIII, No. 2, 2000, pp.6-7.。
在美国成就了“大一统”的自由主义,一开始便在内部具有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倾向,这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的内在保险机制。以社会生活中最具典型性的政治生活为例,美国的政党通过长期的演变最终发展为稳固的两党制,自由主义亦由此分身为二:一方是通常被视作较为“保守”的美国共和党,此即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右派”,另一方则是较为“激进”的民主党,此即自由主义的“左派”,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轮流执政无非代表了自由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二者貌似彼此对立,但其实质却并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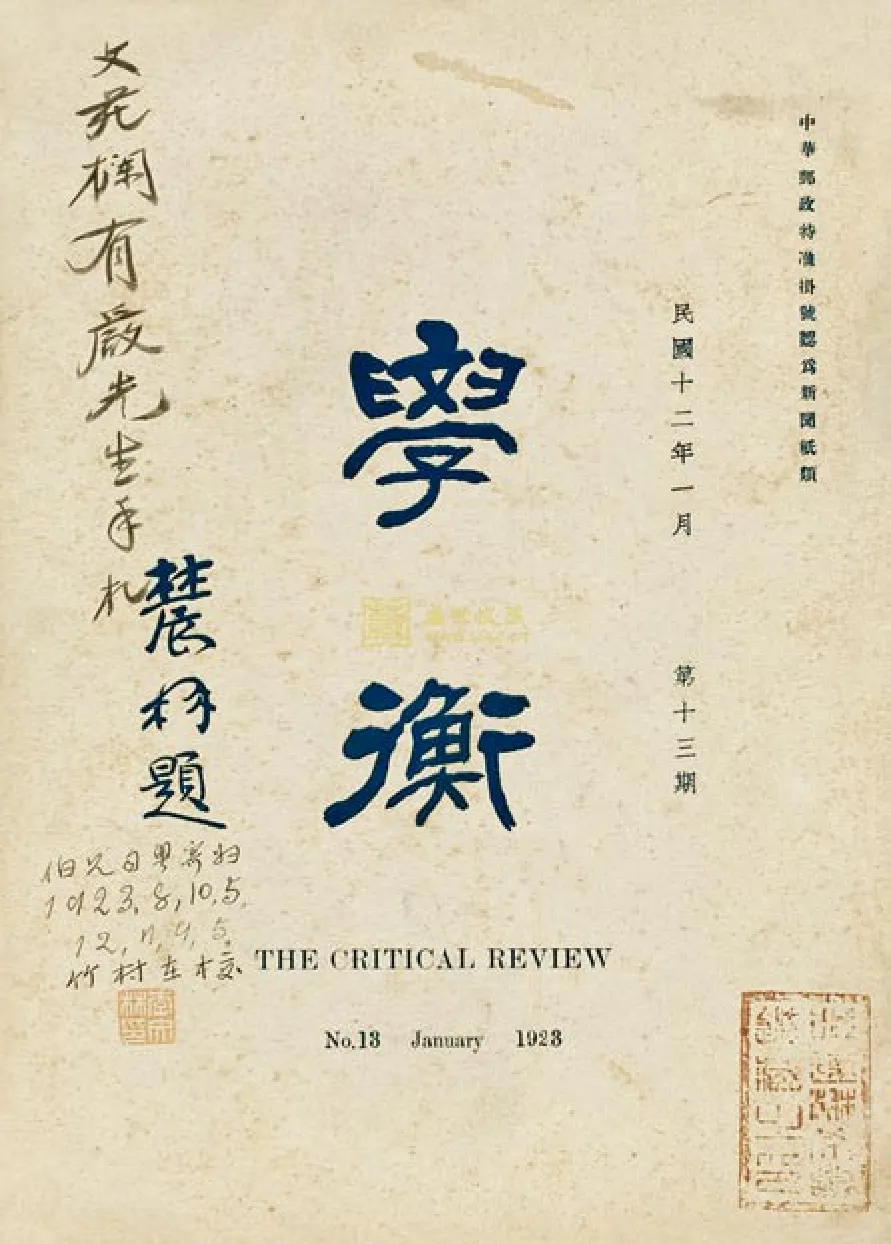
《学衡》杂志
其实,早在美国建国之初,这一原则便已基本确立。如欧文·白璧德所见,美国从一开始便具有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一方是以华盛顿为人格代表的承载了“传统标准”的“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另一方则是以杰斐迅-杰克迅为人格代表的具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正如个人具有克制其“普通自我”的“更高自我”,国家也应具有某些代表“更高自我”的机构,对其“普通自我”,即“众意”(the popular will)形成约束,此即“宪政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政府观的对立之处,—显然白璧德对这两种民主制度有非常明确的倾向性。白璧德进一步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政府观起源于不同的自由观(views of liberty),并最终着落于不同的人性观,而美国式的民主试验必将在华盛顿式的自由(Washingtonian liberty)与杰斐迅式的自由(Jeffersonian liberty)二者之间不可抑制的冲突与斗争中找到答案;如果把握住了这两种自由观之冲突的全部意义,便掌握了开启美国历史的钥匙①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4, pp.246-248.。—这段引文取自白璧德的政治学名著《民主与领袖》,这部集中讨论“民主制”的著作在行文过半之后,出人意料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章节“真假自由主义者”(True and False Liberals),其实当我们看到,白璧德这部讨论“现时代民主制应该是怎样的”的著作,实际上是在阐述“现时代民主制下真正的自由何以可能”,便会明白这一转折实为该书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白璧德“人文主义”②西方研究者为避免混淆,通常以humanism指称广义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以首字母大写的Humanism一词来特指白璧德之“人文主义”。See Malcolm Cowley, “Humanizing Society”, The Critique of Humanism, edited by C. Hartley Grattan, New York, Brewer and Marrow Inc., 1930, p.63. 或直接将其命名为“白璧德那种人文主义”(the Babbitt brand of Humanism), R. P. Blackmur, “Humanism and Symbolic Imagination”, The Lion and the Honeycomb,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56, p.148. 或虽小写而仍冠之以白璧德之名,即“白璧德之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Babbitt),Dom Oliver Grosselin,O.S.B.,The Intuitive Voluntarism of Irving Babbitt-An Anti-Supernaturalistic, Anti-Intellectualistic Philosophy, ST. Vincent Archabbey, Latrobe, PA., 1951, p.6. 相应地,本文以不加引号的人文主义指代广义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以加引号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指称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思想。:自由的,抑或保守的?
自由一词在白璧德这里具有双重含义(熟悉白氏思想的读者对此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其一为柏克式的自由,它意味着对更高之权威(authority)的“服从”(subordination),这乃是“真正的自由”(genuine liberty)的基础;另一则为卢梭式的自由,它的核心不复为自由,而是平等(equality),它属于无视等级与权威的世界,同时为卢梭式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与集体主义乌托邦(his anarchistic and his collectivistic Utopia)所共享③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108.。
白璧德在这两种自由之间作何取舍,一望可知。他郑重指出,这真假两种自由主义(a true and a false liberalism)之间的斗争在共和国(指美国)建立之初便已展开,那种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的“新自由”(new liberty)不同于“真正的自由”,后者乃是道德努力(ethical effort)的奖赏,如果人们将自由视为“自然”(nature)的慷慨馈赠,“真正的自由”便会消失无踪④Ibid, p.220, p.295, p.312.。他引用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的话说:力图结合自由与平等,只会导致恐怖主义,并由此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崛起决非偶然事件,—拿破仑其实是法国大革命之真正的继承者与执行人⑤Ibid, p.127. 我们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来看,白璧德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判断有其深刻的洞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亦无非承袭了一种“古典”的政治观点:僭主政治(tyranny)是从民主政治产生出来的,平民领袖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由一个保护者变成十足的僭主独裁者(tyrant),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八卷,第339页,第346页。这与我们接下来将提到的柏克的意见属于同一传统。。

白璧德
在白璧德这里,柏克式的自由(亦即英国式自由)与卢梭式的自由(亦即法国式自由)构成了一组真假、优劣有别的二元对立项。白璧德所说的这两种自由,借用甘阳的分类话语来说,正是“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时代)“欧洲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亦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对待民主制的态度成为两个时代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水岭,需知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评判民主制的,而法国自由主义统系下的托克维尔则是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来批判检讨民主的,因此后者对民主的批判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有着本质差别①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第39期。。
从白璧德对“众意”的不信任,及其对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以“平等”为核心特质的“新自由”(即他眼中的“假自由”)的憎恶,以及他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表达出的对“自然的贵族”的尊崇②白璧德著名的“自然贵族”说,其实完全本诸柏克,甚至其“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术语“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亦由柏克始创。,对“等级”(hierarchy)社会的青睐以及对“菁英”统治的热衷③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202.看来,他所主张的自由似乎明显具有某种“反民主”的特质,从而确实是“保守主义”的。
不过,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虽然白璧德在自己的著述中曾一再以肯定的语气引述柏克,这并不意味着他便完全认同后者的政治制度选择。
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后,英法两国政治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英国式的“旧的机构”(old establishments)不是“依据任何理论而建立的,毋宁说理论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而法国人则打算根据“一种坏的形而上学”“制订一部宪法”,并据之全力摧毁那个古老的国家(指法国)在宗教、政体、法律以及风俗上的一切遗迹④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1959, pp.212-213, pp.225-226. 相关译文参考了中译本: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本下同。。即英国是先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作为依据,后有其“顺其自然的幸福结果”,即英国宪法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之一贯政策的,而法国则是先预设了一种未经历史检验的形而上学观念,并强行命令现实符合这一观念,从而使活生生的传统本身成为了这一人为观念的殉葬品。因此,在柏克眼中,世间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便是英国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他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曾多次饱含深情地阐述君主立宪制的好处,并在反复对比英法两国政体的“优劣”之后,进而向“邻居”法国人推荐英国宪法的“样板”(the example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国政权,根据柏克的判断,则“装作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affects to be a pure democracy),但却“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寡头政治”,“因此完美的民主制”,柏克断言道:“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the most shameless thing in the world)⑤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113, p.152,p.306.。
正是在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白璧德与柏克有着本质的不同。英国人柏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年之后,自豪地向“邻居”法国人推荐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四十年后,法国人托克维尔经过慎重的考察与对比之后,却转而选择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近九十年之后,美国人白璧德面对英国与法国两种参照物,复进而选择了与英国式自由相联系的“宪政民主”。不过,历史绝非在原地画了一个圆圈,“回到英国”只是表面现象。白璧德从未在根本上反对民主制,他反对的从来都是“不加限制的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直接民主”,或“平等主义的民主”(equalitarian democracy),即与法国大革命政体相联系的民主制,但绝非民主制本身。其实,只要当我们注意到《民主与领袖》一书所讨论的主题并非“要不要民主”,而是要“怎样的”民主(即在“宪政民主”或“直接民主”两个选项中作一取舍),便可看到白璧德与柏克的根本区别了。需知美国是以“平等”(equal)、“自由”诸观念立国的共和国,一向缺乏欧洲国家那样的建立在世袭或阶级基础上的官方统治集团,几乎完全没有军事等级或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构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思想传统,可谓深入人心;直至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1865~1917),美国早几代的国民生活特征—异乎寻常的流动性和多面性—仍始终保留着,这使阶级和阶级观点难以固定,同时整个时期里强有力的民主化影响—教育—也一直在起着重要的作用⑥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21页。。事实上,“民主”已成为白璧德不得不面对的“传统”,他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却不会主张将之连根拔除。一如柏克对君主立宪制的偏爱与英国的贵族传统密不可分,白璧德倾向于“宪政民主”亦与美国的民主传统紧密相关。当柏克说:“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白璧德却说:“宪政民主”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①Irving Babbitt, 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2, p.206.,—这两种判断真是相映成趣。正是出于这个背景,白璧德才会在自己的政治学著作中指出:在当前环境下(即美国自建国以来形成的“民主”大环境)成功捍卫真正的自由主义(true liberalism),仅以柏克的方法(Burke’s method)是不够的②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116.。
事实上,在对待民主制的问题上,白璧德没有站在柏克一方,而是与托克维尔站在了一起。众所周知,托克维尔在亲身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③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第8页。版本下同。;在他这里,“要不要民主”已经不复成其为问题,问题转而成为是要“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即如何“对民主加以引导”④同上,第2页,第8~9页。,—这其实已预告了此后白璧德的“两种民主”之分。虽然白璧德在其“人文主义”系列著作中仅提及托克维尔两次,但这两次均系引述托氏对民主制的判断,且文中对托氏的判断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肯定与赞赏⑤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8, p.105, p.110.,这一情况颇能说明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白璧德与托克维尔一样,深知现代/民主潮流不可逆转,却仍对民主制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这自然会导致人们的误解。面对广泛的置疑,在《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五年之后,托克维尔在该书下卷(1840)中申辩道:“正是因为我不反对民主,我才会认真地谈论关于民主制的问题。”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514页。而白璧德亦深知时人对他的误解,曾如是自明心迹:“人文主义者的目标不是否认他的时代,而是完成他的时代”⑦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pp.258-259.,“批评家的任务便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搏斗,并赋予这个时代在他看来所需要的东西”⑧见George A.Panichas, Claes G.Ryn eds., Irving Babbitt in Our Tim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86)一书扉页之编者引言。。—白璧德不复像柏克那样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对之展开批判,而是像托克维尔那样站在民主一方对之加以审视与检讨,从而他的批判不是沿着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脉络展开,而是由此进入了托克维尔式的自由主义的统系。
四、“学衡派”白璧德思想译介-阐释形态对于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发生学意义
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继先秦、魏晋之后第三个重要的转型期。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外来/西方文化不仅承载着为本土文化提供镜像/他者/参照物的职能,并且直接参与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文化身份的建设:从最初的“中体西用”假说,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西/古今之辩,发展到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中西文化之“体用不二”的现实,西方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渗透与转化的过程,如今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关于“失语”问题的讨论,始于“文论失语”(1996年)而迅速扩散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而发展为关于“文化失语”的论争,至今未衰,—这一现象很可说明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是,自“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话语汇入本土话语近一个世纪之后,如何确认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便得到了深切的关注,如“东西文化之论争”、“学衡派的反攻”,“科玄之争”与“甲寅派的反动”等等题目均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不过,如果说当时的论争出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自觉的忧患意识,本世纪之交爆发的这场关于“失语”的讨论本身,则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忧虑不可逆转地实现之后而自发产生的症状之一。在此我们不拟对“失语”问题本身加以评论,仅由此提请大家注意“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于延续至本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这乃是本文论述的基本进路之一。。
“新文化运动”后期,美国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通过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徐震堮、张荫麟、梁实秋等中国学人的译介与阐释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与其他西方观念和思潮一道参与了中国新文化身份的建设,并且通过此后中国本土不断的“重估”工作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形态,从而在中国持续至今的文化身份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人们对之产生了多种理解与阐释,这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共四种形态:
1.第一期:“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两种形态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学说于二十世纪一○年代在美国本土初为人知,至二○年代这一学说的影响逐渐扩大进入鼎盛阶段,并开始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其间吴宓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中国创办了《学衡》杂志(1922 年1月~1933年7月),并围绕该杂志形成了中国二十世纪独树一帜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学衡派”,由此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正式通过“学衡派”的译介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阐释形态。
《学衡》译者作为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批”阐释者,由于他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立场与近似的学力背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取用有着大体一致的倾向,因此均采取了共同的语言转换模式,即均以浅近文言作为目的语的基本形态。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在人们看来,《学衡》译者对“语言载体”的选择成为左右这一思想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须知《学衡》一向是以其“文言”取向见谤于“新文化派”、乃至“新文化派”在新时期之精神后裔的①逮至2003年,仍有人对《学衡》的“文言”取向深恶痛绝。如朱寿桐《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颇具代表性,文章认为:《学衡》的“文言主张”使之“始终处在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对立面”,“此一旗帜一展,各派旧式文人、守旧势力即以陈词滥调竞相邀集,从而使得《学衡》客观上成了(至少在新文学家看来)群魔乱舞的诗坛,藏污纳垢的文场”,“在锐不可当的新文学潮流面前……呈现着僵死的灰暗,散发着陈腐的霉味”等等。仅寥寥数语,我们已可看出该文充满了与所谓“学术论文”殊不相称的激情,这一现象颇为有趣。我们固然不必伴随着今日“保守主义”在全球的“复兴”,对此前倍受批判的《学衡》转而顶礼膜拜,但亦不必坚持将之留在十八层地狱。看来,虽然是“新文化派”,经过一个历史时段,也会有其“遗老遗少”。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一种激进主义,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顺利蜕变为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此自当会心。。
《学衡》的“拟古”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读者对白璧德学说的主动接受;不过,稍后便出现了以白话宣传“人文主义”学说的又一健将梁实秋。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留学美国②按梁氏赴美之前,曾于1923年3月到东南大学参访,据吴宓记载,“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这可是白璧德最心爱的话题之一),结果“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并且在返回清华后在《清华周刊》中对东南大学的学风以及吴宓溢美一番,吴宓就此发议论说:“此亦与清华1924冬之聘宓往,有关。”《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42~243页。版本下同。显然梁氏对吴宓授课印象非常之好,这可能与他赴美之后在哈佛选修白璧德讲授的课程有直接的关系。,在白璧德的影响下,他一改对浪漫主义的热衷,转而成为中国当时宣扬古典主义的巨擘,并且从此一以贯之,再未发生动摇③梁氏曾自述:“读了他(白璧德)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载《雅舍菁华》,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梁氏撰写了大量白话文体的文学批评作品,从第一部文学批评集的第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④该文于1926年2月作于纽约,载梁氏第一部文学批评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开始,便几乎是在“复述”、或大胆“挪用”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文学观(这与白璧德美国学生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这种宣传手法比“学衡派”更加隐蔽、效果也更为理想。吴宓最早注意到了梁实秋文学观的转变⑤见吴宓1926年3月29日日记:“梁实秋(治华)在《晨报副刊》所作评论新文学一文,似颇受白璧德师之影响”,《吴宓日记》III,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63页。,三年之后双方合作出版了《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书。令人兴味的是,吴宓对梁氏这一时期用“白话文”所作的宣传工作并不排斥,相反还似乎颇为赞赏⑥见吴宓所记“对于宣扬白璧德师之学说,尤其在新文学家群中,用白话文作宣传,梁君之功实甚大也”,《吴宓自编年谱》,第243页。。
梁实秋对白璧德学说的“挪用”构成了其在中国的又一阐释形态(1926~主要止于1934)。它与第一个阐释形态的生成时段部分迭合,但二者选择了不同的语言载体(一者文言、一者白话)与宣传策略(一者直接译介并以之为批判武器,一者大胆挪用并据之开展批评实践)。从而,在中国文言/白话并存的这个时期,白璧德学说也产生了文言/白话两种并存的阐释形态。不过,梁实秋的“白话”宣传策略同样未能改变白璧德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由此看来,人所共识的《学衡》在选取“语言载体”方面的“失策”,或许并非这一学说遭到冷遇的决定性因素。
二十年代末期,“新人文主义运动”(New Humanist Movement)在美国本土进入了巅峰状态,“人文主义”学说随之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与传播。但是伴随着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衰退,这一运动很快便急转直下,并在三十年代跌入低谷,“人文主义”学说亦随之销声匿迹。同时,中国的《学衡》杂志于一九三三年白璧德去世当年宣告停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第三一三期后不再由吴宓担任主编,从而失去了又一个宣传白璧德思想的阵地。从此,“学衡派”对白璧德学说的推介工作限于停顿(此后仅有吴宓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不时引述或阐发白璧德的学说),而梁实秋的相关推介工作亦主要止于一九三四年⑦除1923年自费刊印的《冬夜草儿评论》之外,梁氏共出版了五部文学评论集。这五部文集均在不同程度上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翻版:《浪漫的与古典的》(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文学的纪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文艺批评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偏见集》(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以及30年后在台湾出版的《文学因缘》(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最后一部文集收录了梁氏滞留台湾期间所写的文字,与此前文集内容其意相同,因此我们说他的推介工作“主要止于1934年”。。
2.第二期:“新时期”以来的两种形态
“学衡派”与梁实秋对白璧德学说的宣传与推介均大致止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此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学说连同其宣传者在国内长期遭到了非学理意义上的批判,从此正面宣传的声音湮没无闻达数十年之久。一九四九年梁实秋选择在台湾定居,而“学衡派”中坚则留在了大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被梁氏带入台湾之后,其阐释与传播工作便分别在大陆与台湾以“花开两朵”的模式继续展开,并随之形成了两种新的阐释形态。
台湾较早重提白璧德的名字及其学说。梁实秋赴台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梁氏的门生侯健对白璧德学说做了大量的宣传与阐发工作。这一时期除了对白璧德学说本身的译介、研究以及据之展开的阐释实践外,还新增了“影响”研究的项目:第一期的阐释形态经过数十年的积淀与消化过程,开始对新一轮的阐释发挥强大的效用。八十年代以后,大陆零星出现了一些相关译介作品,进入新千年以后,相关译介纷纷涌现,并在短短数年之中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双方的情况多有不同。先来看台湾:梁实秋最先将白璧德学说直接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中来,而侯健此后亦继承了梁氏的这种阐释方式,从而这一学说“由初抵中土时的社会与文化论述,逐渐被削弱而沦为批评论述,及至局促台湾一隅时,则演变为学院中的学术论述”①李有成《白璧德与中国》,《中外文学》,第12卷第3期,1991年,第64页。本文作者作为台湾学者,描述的乃是白璧德“人文主义”从“新文化运动”后期进入中国直至“局促台湾一隅”的“旅行”历程(从“学衡派”到梁实秋再到侯健)。此时大陆新时期阐释工作刚刚开始,尚未进入作者的视域。不过,在大陆目前的诸多研究中,我们也往往会看到这一学说被视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白璧德也常常被称作“著名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大师”等等,这种“误会”实与梁实秋当年的文学批评实践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直接后果之一。。问题是,一种学说之所以会“沦为”狭隘的“学术论述”,与其生存环境密不可分。面对台湾(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日趋“冷漠”的接受环境,这一“文学批评”理论不得不渐次退守于学院一隅,这与其在美国本土三十年代的际遇分外相似。当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便脱离了其产生的背景、及其所要对质的命题,由此逐渐失去生命力。正如当“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借助“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广为传播之时,恰是这一学说遭到曲解、创造力枯竭的时刻。不过,当“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运动“销声匿迹”之后,“人文主义”思想此后却在新的历史时刻再度焕发出了生机。—此为后话,回到主题,我们看到,这一学说“偏安”台湾之后,可能恰恰是由于台湾与大陆“意识形态环境”的隔绝,导致其脱离了大陆复杂而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与环境,才会由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
大陆新时期之阐释形态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尽管梁实秋的阐释工作在大陆同样发挥着影响,有时我们也会把这一学说看作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在大陆围绕这一学说展开的相关论述,无论是正面阐发,还是负面批判,几乎无一不以中国广阔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为参照,特别是其“意识形态环境”无论是恶劣得无以复加、还是忽尔否极泰来,都不曾有过一天的“冷漠”。当这一学说在台湾最终演变成为“学院中的学术论述”,它在大陆所引发的相关探讨却总会沿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展开,这正与“学衡派”当年引入白璧德学说的意图符合若契。
不过,大陆阐释工作的问题在于,白璧德学说的译介工作在一九三四年之后便基本陷于停顿,而其已有的阐释形态则遭到批判与唾弃,新时期繁荣起来的译介工作事实上又出现在诸多所谓“研究”之后,在极为不利的“意识形态环境”的长期挤压之下,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只能处于“缺席受审”的境地。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们对白璧德学说的讨论往往仅限于追究其“负面”的影响,但却并不触及这一学说本身,这正是特殊时代语境带来的特殊问题。
阐释必须面对阐释对象始能展开,但是,目前诸多白璧德思想“阐释者”直接处理、或曰能够直接处理的对象却只是“学衡派”或梁实秋的阐释文本,而非白璧德著述本身。由于缺乏对白氏思想之自身形态的探究,使得诸多相关“影响/接受”研究呈现出严重的先天不足: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所讨论、阐释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往往只是经过“学衡派”或梁实秋阐释的“白璧德人文主义”而已。从吴宓一九二一年一月将humanist(人文主义者)译为“儒者”开始,“学衡派”人士在《学衡》中屡称白璧德为“西儒”以及“美儒”②如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1922年1月第1期《学衡》)“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於未知运思之人,其祸立见”一句中的“美儒某氏”即白璧德。吴宓《我之人生观》(1923年4月第16期《学衡》)“西儒谓通观前史,精约之世Age of Concentration与博放之世Age of Expansion 常交互递代而来”中的“西儒”显系白璧德。柳诒徵更是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1924年9月第33期《学衡》)中明确称白璧德为“美儒”:“宣城梅子迪生,首张美儒白璧德氏之说,以明其真,吴子和之。”,并在各篇译介白璧德思想的文章中大量羼入中国传统思想的元素,直至今日仍有研究者称白璧德为“白老夫子”③朱寿桐《白璧德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宿命角色》,《外国文学评论》,第122页。,白璧德之“儒者”形象在整个阐释链条中贯穿始终。事实上,正是通过《学衡》译文,白璧德本人及其思想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至今仍有不少研究以《学衡》译文为本概括出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实质”,再由此来论证“学衡派”人士的基本观点与这一学说有着“契合之处”。
例如,有论者指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儒教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文化之间有许多类似之处”,并举例说明道:“白璧德在一九二一年为美国东部之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也已经提到东西方文化在文化与道德传统上的相似性,并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①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6月,第37期,第68页。按:作者引文有误(将“人文主义者”写作“人道主义者”),此系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孙尚扬、郭兰芳编,第47页。胡氏译文原文为“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对应“人文主义者”之原文为“humanists”。事实上,白璧德是不会把孔子与“人道主义者”相提并论的。王晴佳这篇论文有其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上述误会仅为玉瑕之处。拈出该文为例,可以看出,当前很多研究者把“阐释形态”当作阐释对象本身的情况仍相当普遍,并对此缺乏自觉。云云。—需知经过“学衡派”阐释的白璧德,已不再是“美国的”白璧德,而成了中国的、特别是《学衡》中的白璧德,继而惟有这个“白璧德”,才能说出“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之类的话来。论者显然把“学衡派”对白璧德学说的“阐释”当作了这一学说本身,由此这一翻译/阐释便对此后的再阐释悄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学衡派”译文经常会非常自然地嵌套在后世研究者的文本当中,行使原文文本才能行使的职能,享受原文文本都未享受的尊荣,传递着自己创造的形象,并左右着后世研究者的想象。上述那种在不经意间展开的循环论证,实际上已经不复是严格意义上的“影响”研究,而是本身充当了相关“影响”的一个例证,昭示着白璧德学说已经进入了“飞散”(Diaspora)的状态。
我们知道,一种文化/思想在进入异质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会在“期待视野”的制约下经历某种“文化过滤”的过程;在置换文化语境的同时,其原有意义必然会发生转化并导致新意义的生成,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某种“扭曲”与“变形”。—这里描述的正是一个翻译/阐释的过程。

吴宓

胡先骕

梅光迪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或曰西方文化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渗透与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彼时大量的译介工作完成的。征之于历史,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往往会对思想史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中国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与魏晋时期发生的文化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便可谓不言而喻,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此后中国思想史的进程。翻译行为发生在每一种文化/思想进入异国文化语境的瞬间,它是最有效的“文化过滤”的手段,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出译者/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要想把握住一种西方文化/思想一变而为“中国的”那个瞬间,就必须从这种文化/思想的首次译介入手。
“学衡派”人士是最早译介白璧德“人文主义”的群体,他们的译介工作构成了这一学说在中国的整个接受史的起点,可以说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初始效果”(Primary Effect)②此系借用叙事学“阅读动力学”术语,原指最初的阅读具有的“Primary Effect”对于此后的阅读感受有着最为强烈的影响力。See Shlomith Ri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 London: Routledge,2002, pp.119-120 。,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甚至是决定了白璧德学说此后在中国的再接受过程。“学衡派”抓住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本义”(即狭义的“贵族性”的“人文主义”),并以之为武器向当时国内“大行其道”的“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思潮展开了批判①“人道主义”概念在白璧德这里,几乎是一个可以容纳一切“人文主义”对立物的“总名”,不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科学主义”,“情感主义”,或“物质主义”等等,都可以很方便地统统纳入其中加以批判;“学衡派”弟子显然继承了老师的这一批判话语。。《学衡》所严厉批判的,正是《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积极加以宣传和推介的;同时《学衡》与《新青年》等杂志的“文言”与“白话”之争,复被认为是“贵族的”/“人文主义的”文字/文学与“平民的”/“人道主义的”文字/文学之争,从而文字/文学不但成了思想斗争的载体,本身还成了斗争的内容与手段。是以不论从目的、内容还是手段而言,立足于狭义的“人文主义”的《学衡》与代表了“人道主义”的《新青年》恰构成了一组白璧德“二元论”式的对立。正如汪晖所见,同是“humanism”,在五四时期却存在着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和以《学衡》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两种“几乎对立的命题”②汪晖《人文话语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陈清侨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另李怡曾总结过五四时期的中国歧义丛生的“人文主义”概念,认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他们对“人文主义”的不同理解与定义,《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1998),《解析吴宓》,李继凯、刘瑞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6~148页。。
“学衡派”人士从一开始就自我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学衡》杂志的创办,最初本是为了建立与胡适等人展开论争的阵地,他们引入白璧德的学说,是为了与胡适宣扬的杜威“实用主义”形成制衡,并对抗“新文化派”推崇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与社会思潮。“学衡派”推介、传播白璧德学说,是出于明确的“为我所用”的目的,而非单纯地为宣扬白璧德学说而宣扬之。

徐震堮

梁实秋

张荫麟
美国在逐渐步入“现代”的前夕,曾面临着与中国此时颇为相似的境遇:各种“现代”思潮纷至沓来,代表“旧文化”的“文雅传统”遭到了全面的批判而土崩瓦解。面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美国本土显然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正如著名文学史家卡辛所云,欧洲的作家们经过马克思、罗斯金、阿诺德等人的不懈批判,对资本主义秩序及其伦理总算有所戒备,而美国现实主义以及此后的现代主义先驱们,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却毫无防范、不免一败涂地③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rose Literature,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2, p.19.。正是在这一时期,白璧德开始集中称述阿诺德等“现代批判者”的主张,并将他们的思想作为自己社会/文化批判学说的一个重要资源,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及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可以说,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是美国本土在外来现代思潮冲击之下,借助“外力”“应运而生”的现代批判学说。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各种现代思潮亦奔涌而入,思想与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然而其时却一无传统的有力制衡,二无相应的批判机制,与美国当年的境遇分外相似,于是白璧德的学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适时”地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域。—先是白璧德大量称引阿诺德等人的学说,此后稍晚,复有吴宓等人远涉重洋,将他们“偶然”发现的美国“圣人”白璧德的学说带回中国,并以之为有力的理论武器,向国内诸现代思想的代言人提出了质疑与辩难。也就是说,“学衡派”自觉担任了“人文主义”学说在中国的阐释者,并由此充当了现代思潮的制衡力量①关于此节,可以在《吴宓日记》中找到大量的佐证材料,这些材料已多为研究者所熟知。亦可参见K.T.Mei(梅光迪)对《学衡》事业的回顾文章“Humanism and Modern China”中的相关论述,The Bookman, June 1931, p.365.。同时,“学衡派”亦就此“分享”了老师白璧德作为“时代批判者”的命运:《学衡》从诞生之日起,便命途多舛,《学衡》所推介的白璧德学说在中国亦随之“得罪”而前路多艰。
如果说“新青年”们代表了“进步”的趋势,“学衡派”与之公开对抗,便代表了“保守”“反动”的势力,从而“学衡派”就是“昧于时势”的,人们的这种逻辑,如刘禾所说,将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落入提倡新文化者的“修辞陷阱”,因为正是这些新文化提倡者首先给《学衡》加派上了一个社会进步之绊脚石的恶名②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 -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56页。。然而,“新青年”的精神后裔们,仍对这套话语恋恋不舍,直至二十一世纪仍斥责“学衡派”为了“复古”的目的不惜走向极端,他们介绍西学,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不过是将其作为装饰“国粹”的花环等等③许祖华《五四文学思想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
如果与主流思潮“针锋相对”就是“昧于时势”,那么白璧德本人自然也不免“昧于时势”之讥。白璧德认为,如果现代崇尚物质进步的趋势不加限制,人类文化终将面临毁灭,这乃是白璧德长怀的“千岁之忧”。在他看来,“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人欲横流的恶果,如果不以“道德律令”(the moral law)对之行使“否决权力”(the veto power),这种自然主义的谬误终将毁灭人类文明(wreck civilization)④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9, pp.367-368.。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美国人引用白璧德这段充满了忧患之思的文字,不过,引文稍微作了一点修改,掐头去尾略去了白璧德这段文字的具体语境—对于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痛反思,从而使得白璧德对战争威胁下的人类文化前景的深切忧虑看来言过其实,愚蠢可笑。该论者复以戏谑的语气评论说:“白璧德以一个早期清教徒阴郁的宗教热诚,提醒我们现在的生活早已是人间地狱(hell on earth)”,“他自认为找到了解救之方,于是毕其一生致力于那种‘人间的救赎’(secular salvation)”。⑤Keith F.McKean,“Irving Babbitt”,The Moral Measure of Literatur, Denver: Alan Swallow,1961, p.49.然而,事实证明白璧德并非杞人忧天,一战的阴影还未消除殆尽,更为残酷的二战便接踵而至。可是这位六十年代的评论者竟无视于此,拿这个严肃的话题开了一个轻薄的玩笑。看来,事实再一次证明,后人的有利视野并不能保障其“后见之明”,批评前人对“意识形态环境”缺乏意识的同时,阐释者自己往往容易失去自觉,并丧失对所研究之时代的“意识形态环境”的真切把握。“学衡派”在事实上已经将白璧德学说引入中国,并产生了一定的接受效果,不论这效果本身如何,后世阐释者只能将之作为一段效果历史接受下来,而不宜指责推介者明知某理论“不合时宜”却仍旧逆流行事。那个时代的“逆流而动”者可能并非对主流“意识形态环境”缺乏自觉,倒是后人常常会顺应今天的“意识形态”去思考那个时代的问题,结果反为自己的视野所蔽,—当代的研究者们对此可不慎诸?直面白璧德思想本身并重新审视“学衡派”的译介/阐释文本,对已有的阐释传统进行合理的开掘与再阐释,或可使这一思想及其中国阐释在当下重新发挥效应。这将有助于白璧德思想本身与中国现代思想史重新产生直接的关系,从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那一段故事对于延续至今的文化转型或将呈现出新的意义。
五、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以《学衡》吴宓译文为例
《学衡》全部七篇白璧德译文,吴宓独揽了其中四篇。这四篇译文均为原文目前所知唯一的中译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所有七篇译文之按语以及大部分注解与点评亦出自吴宓之手,也就是说,全部《学衡》白璧德思想译文的整体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吴宓来统筹、定调的。作为《学衡》主编和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最主要的译者,吴宓对白璧德及其学说在中国之形象的塑造与流播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在吴宓翻译的《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载1924年8月第32期《学衡》)一文中,“高上意志”(the higher will)一词—作为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首次出现在了《学衡》杂志,并第一次为国人所知①“the higher will”这一概念在白璧德《民主与领袖》一书中首次出现。《学衡》是当时在中国宣传白璧德思想的唯一阵地。吴宓在写给业师白璧德的信中,曾提到:“除了《学衡》的专栏,我从没见过任何关于您的思想的讨论、您的姓名的出现。”见“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通信”,《跨文化对话》,2002 年10月第10期,第160页。因此《学衡》中出现的“高上意志”概念系首次为国人所知。。在白璧德这里,“意志”分为“高上”与“卑下”两种类型,其中“高上意志”决定人的“内在生活”(inner life),对于人的“一般自我”(the ordinary self)表现为一种“约束的意志”(a will to refrain),乃是一种“使人之为人”并“最终使人具有神性”的特质②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p. 6-7.,相对于理性以及情感而言,它无疑居于首要的位置。吴宓在文中“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the opposition between a lower and a higher will)一句下面作了两行夹批:“吾国先儒常言‘以理治欲’。所谓理者,并非理性或理智,而实为高上之意志,所谓欲者即卑下之意志也。”吴宓以极具本土特色的表述(“以理治欲”)来比附“高上意志”对于“卑下意志”的对峙与制约(此即“内在制约”)之义涵,使得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从一开始便获得了某种强烈的“归化”意味。
有趣的是,到了新时期,在本土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以理治欲”这种理解却一脉相承,在新时期研究者的论著中延续了下来。如有研究者曾论及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的接受影响关系,认为白璧德一再强调的“新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依赖自己的理性”或所谓的“更高的意志”来对个人的冲动和欲望加以“内在的制约”,而梁实秋与白璧德一样,也强调“以理性节制情欲”,是以“梁实秋文艺思想的真正核心,应该说是理性与理性制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以理制欲的人性论”③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艺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5~168页。版本下同。。
我们注意到,虽然新时期研究者与吴宓均将“高上意志”对于“卑下意志”的对峙与制约(此即“内在制约”的过程)解释为“以理制欲”,但二者所指的“理”并不是一个概念。如前所述,吴宓重点强调了“理”“并非理性或理智”,而新时期研究者将“以理制欲”等同于“以理性节制情欲”,从而“理”在这里指的显然就是“理性”,是以与吴宓的观点正相矛盾。
或许吴宓当初已预见到“以理制欲”这一批注可能会造成某些误解,所以在该篇译文的长篇按语中特别说明了“理者,并非理性或理智”的道理:
白璧德先生以为政治之根本,在于道德。……欲求永久之实效,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是已。……宗教昔尝为道德之根据,然宗教已见弃于今人,故白璧德提倡人文主义以代之。……令各人反而验之于己,求之于内心。更证之以历史,辅之以科学,使人于善恶之辨、理欲之争、义利之际,及其远大之祸福因果,自有真知灼见,深信不疑,然后躬行实践,坚毅不易。……白璧德先生确认道德为意志之事,非理智所能解决。……想象可补理智之不足,而助意志之成功。此又白璧德先生异乎西方道德学家之处也。其与东方耶孔异者,在虽主行而并不废知。其与西方道德学家异者,在用想象以成其知,而不视理智为万能。就其知行并重一层言之,似与佛法为最近。……故夫以想象窥知道德之真,而以意志实行道德,人咸能自治其一身,则国家社会以及世界,均可随之而治。此白璧德所拟救世救人之办法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吴宓在这段按语中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政治的根本在于个人道德的培养,由此“则国家社会以及世界,均可随之而治”,可以说仍旧未离“修齐治平”之基本思路。第二,道德的培养“为意志之事,非理智所能解决”,理智尚须依赖“想象”的力量以补其不足,由此“窥知道德之真,而以意志实行道德”。
正是出于对白璧德学说的这种认识,吴宓在译文注解中着重强调了自己所说的“以理制欲”之“理”并非“理性或理智”。应该说,吴宓对于白璧德的这种解读是符合原义的:白璧德曾指出,“理性”(reason)对于“冲动”(impulse)或“欲望”(desire)具有某种制约作用④Irving Babbitt, 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Introduction”, pp. xiv-xv.;但他进一步强调说,适度的法则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则,希腊作为人文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文明却由于“理性”高度发达、以至于走向怀疑主义而遭受到了巨大的痛苦⑤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pp. 23-25.。也就是说,“理性”如果走向极致,亦会破坏人文主义者应当保持的“平衡”。总之,“人文主义”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认为“理性”如果走向极端、发展成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则是根本无法制约“欲望”的⑥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p. 173-174.,甚至过分的“理智”(intellect)还会堕落成为一种“欲望”—知识之欲(libido sciendi),从而“理智”和“欲望”一样,同样必须受到“意志”的制约①白璧德认为,人有三大欲望,即知识欲、情感欲与权力欲(the lust of knowledge,of sensation, and of power),并引用帕斯卡尔(Pascal)的判断,指出高上意志将对自然人(the natural man)的这些欲望发挥制约的作用,见Irving Babbitt, 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 p.195.白璧德还曾说过:伟大的宗教导师们坚持认为人应当屈从于某种高上意志之下,最重要的是,人的理智需要承认某种这样的制约,因为不加管束的理智(intellectual unrestraint,此即libido sciendi知识之欲)很可能将会带来最大的危险,见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182.。
由此看来,将“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阐释为“以理性克制欲望”似乎并非一种稳妥的解释。不仅如此,上述新时期研究著作还指出:“天理人欲论与白璧德的善恶二元论,在程度上或有差别,各自的思想背景也不同,但其理论实质是十分接近的。它们都力图把特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凝聚转化为某种普遍必然的‘理性’或‘天理’,用以扼杀人的感性存在和自然欲求,并通过这种理性对人欲的压抑,来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文章还提到林语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二者的相似”,并引用林氏的话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通常所谓Humanism,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不同,他的Humanism是一方与宗教相对,一方与自然主义相对,颇似宋朝的理性哲学”②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艺理论》,第170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按:林语堂原文为“性理哲学”③《新的文评》,林语堂编译,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序言”,第2页。)云云。
从上文对林语堂评述的误引来看,作者似乎在不经意间表露了自己对于“以理制欲”说的认识,即“以理制欲”便是“以理性克制欲望”。关于宋明理学话语系统中的“以理制欲”是否可用“以理性克制欲望”来解释、沟通,我们暂且不论;关键在于,由此“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渐由“以理性克制欲望”演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人欲论”,这种论说方式不免令人生疑。
我们之前曾讨论过白璧德对“理性”的态度:信奉“中道”的“人文主义”不会主张“扼杀人的感性存在和自然欲求”,亦不会主张“理性对人欲的压抑”,同时就其“内在制约”的主旨来看,恐怕还会特别反对“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因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完善”与个人的“内在生活”(inner life),与社会维度相比,它更看重个体之维度④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Introduction”, p.8.:它认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首先不是存在与社会,而是存在与个人”⑤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251.,“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对于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作用于世界的力量,而是他作用于自己的力量”⑥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p.56.,个人就是要依靠这种“作用于自己的力量”、而非外在的律法与约束而达于“内在制约”的。从而,追求“适度”的“人文主义”并非宣扬“以理性克制欲望”,其精神实质与“存天理,灭人欲”亦无瓜葛。
“人文主义”何以一来二去竟与千里之外的“以理制欲”论钩扯在一处,并且直至新时期都与之都难脱干系?要知道,“以理制欲”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具有负面意义,和它划上等号只会导致“人文主义”与之一损俱损,那么,吴宓为何还要在“高上意志”一词出现的文句中加以“以理治欲”之批注?看来,问题首先是从吴宓那里、而非新时期研究者那里开始的。
吴宓是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作为白璧德的得意门生,他通读过本师所有的文章,堪称深悉“人文主义”的精义,因此他对“人文主义”学说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或许不过是忠实秉承了白璧德思想的原义。那么,在白璧德本人看来,“内在制约”说是否与“以理制欲”说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呢?
一般说来,在一八八九年之前,西方对中国理学的研究未见明显成效,此后逐渐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者,不过直至朱熹研究的真正先驱卜道成(Percy Bruce)发表了两部有关朱熹及其前辈的著作(1922~1923)之后,西方对理学较为严肃的研究才正式开始⑦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耿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西方对中国程朱理学的发现”,第183~233页。。不过,“吾国古籍之译成西文者靡不读”、“凡各国人所著书,涉及吾国者,亦莫不寓目”的白璧德似乎对性理之学很早就有一定的认识与研究。早在一九二一年为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年会所作的讲演中,白璧德就曾提到,“有一位作者曾在《哲学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中指出,当圣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即《学衡》中的‘圣亚规那’,或‘亚昆那’)沿着经院哲学的路数在其《神学大全》(the Sum of Theology)中统合了亚里士多德与耶稣之说,与之大致同时之中国的朱熹(Chu Hsi),亦在其伟大的集注中以一种经院式的做法将佛学与儒学元素结合了起来”⑧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 17, 1921, p. 86. 按:文中提到的“有一位作者”不知所指何人,疑系白璧德自指。,并在此后出版的Democracyand Leadership一书中再次将朱熹与圣阿奎那并举:“我们注意到,当圣阿奎那试图在其《神学大全》中结合亚里士多德与耶稣之智慧,朱熹大致在同时亦在其伟大的集注中将佛学与儒学的元素混和了起来,二者形成了有趣的类比。”①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p.163-164. 不过,白璧德并不是西方唯一使用这一类比的人。1929年5月第69期《学衡》中《古代中国伦理学上权力与自由之冲突》一文的作者美国人德效骞(Homer H. Dubs)博士亦曾将朱熹称为“儒教之圣亚规那”,不知这一类比是否西方理学研究的“套话”之一,值得留意。—看来白璧德对朱熹所作的工作相当熟悉且极为欣赏。
不过,白璧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孔子的次数远较朱子为多,对孔子的推崇亦远较朱子为甚:在白璧德眼中,朱子是融合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而孔子则“是人类精神史上四大杰出人物之一”②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p.163.,甚至“由于孔子清楚地认识到了适度的法则(the law of measure)本身服从于谦卑的法则(the law of humility),他要优于诸多西方的人文主义者”③Irving Babbitt,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p. 90.。
事实上,白璧德本人曾根据孔子的学说来沟通“高上意志与卑下意志之对峙”:“亚里士多德是‘认识’方面的宗师(a master of them that know),而孔子则与之不同,是‘意志’方面的宗师(a master of them that will)。孔子试图用‘礼’、或云‘内在控制的原理’(the decorum or principle of inner control)来制止膨胀的欲望,在此,‘礼’显然是一种意志品质。孔子并非蒙昧主义者,但是在他看来,理智是附属于意志且为其服务的”④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 165.。白璧德这段极为关键的表述出现在《民主与领袖》一书第五章,有趣的是,该章曾被译出刊载于《学衡》,而译者就是吴宓。
在吴宓曾翻译过的《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载1925年2月第38期《学衡》)一文中,我们找到了这段文字:“诚以亚里士多德者学问知识之泰斗,而孔子则道德意志之完人也。……孔子尝欲以礼(即内心管束之原理)制止放纵之情欲。其所谓礼,显系意志之一端也。孔子固非神秘派之轻视理智者,然由孔子观之,理智仅附属于意志而供其驱使。二者之关系,如是而已。”译文与原文无甚出入,吴宓忠实地译出了白璧德这段关于“内在制约”的解释。
其实,早在“中西人文教育”一文中,白璧德便将孔子之“礼”(li)对译为“law of inner control”了⑤白璧德曾注明这个译法系借自翟林奈之《论语》英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p. 89.。这说明在他看来,孔子之“礼”与“内在制约”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白璧德眼中,儒家学说与自己的“内在制约”说相通之处恰恰在于“以‘礼’治欲”。《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译文中说得明白:“孔子尝欲以礼(即内心管束之原理)制止放纵之情欲,其所谓礼,显系意志之一端也。”“制止放纵之情欲”的“礼”在此显然便是“高上意志”。不过,这并不妨碍该篇译文的译者吴宓将“高上意志”行使的“内在制约”自行发挥为“以理制欲”。
其实,一般论者都倾向于用儒学而非理学来阐释/沟通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见出白璧德“内在制约”说通于儒家“克己复礼”之旨的研究者亦不在少数,如台湾沈松侨曾明确提出:“‘内在克制’(inner check)……就是儒家所谓的‘克己’之道。”白璧德那种“尊崇传统的态度,相当于儒家所谓的‘复礼’”等等⑥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 年,第128~131页。。那么吴宓为何要舍弃更为“相通”的儒学“克己复礼”之旨,转而去强调白璧德思想与理学之“以理制欲”说的关系?
看来,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处理眼前的问题,可能会收效甚微。或许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彼时整个的时代氛围与学者的心态入手,方可找到吴宓对“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作如此解读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涌入中国的各种现代思潮观念之中,我们特别要强调“科学”的观念在当时中国价值体系转换及意识形态冲突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获得了无上的尊严与战无不胜的神奇力量,诸多传统的攻击者,都通过与“赛先生”联手而获得批判、取代传统价值体系的权力与势能,并由此向承载着旧价值的旧秩序发起了致命的攻击。有论者认为:中国对“科学”的热衷贯穿了二十世纪整个前半叶,这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倾向”可称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由于儒学为思想和文化提供参考框架的功能衰退,……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科学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由此“在中国文化与意识的连续性问题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此即一九二三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或科玄之争),亦即“传统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之间的一场战斗”;正是在这场战斗中,唯科学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①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12~13、109、140诸页。。
“科学”成为中国当时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一切旧的价值体系都在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一败涂地,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传统世界观”—“玄学”。
关于“玄学”,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哲学”一词后加括弧说明“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并根据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对人类社会三个时代的划分,认为“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次多数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还有就是“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而“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②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云云,从而“玄学”成了人类进步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自然便是这场论战矛头直指的对象。
“玄学”如果指的就是“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或“所谓形而上的哲学”,那么在中国当得起这一名号的,自然便是宋明理学了③关于“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可参见钱穆对朱子思想的论述:朱子思想主要有两部分,一为理气论,略当于今人所谓之宇宙论及形上学,一为心性论,乃由宇宙论形上学落实到人生哲学上,并且“朱子此项理气一体之宇宙观,在理学思想上讲,实是一项创见,前所未有。”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2~37页。。吕思勉在《理学纲要》中论及“晦庵之学”时说:
人类之思想,可分为神学、玄学、科学三时期。神学时期,恒设想宇宙亦为一人所创造。……玄学时期,则举认识之物分析之,或以为一种原质所成,或以为多种原质所成。……玄学之说明宇宙,至此而止,不能更有所进也。宋学家以气为万物之原质,与古人同。而又名气之所以然者为理。此为当时之时代思想,朱子自亦不能外此。④吕思勉《理学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4页。版本下同。按:《理学纲要》是吕思勉于1926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成文距离“科玄之争”(1923)大约三年时间。
吕思勉在此理所当然地把“宋学家”即“理学家”归入了“玄学”一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正是陈独秀在“科玄之争”中的分类话语。尽管吕思勉本人不乏为“理学”辩护之意⑤如吕思勉曾云:“宋儒所谓理者,……其说自成一系统;其精粹处,确有不可磨灭者,则固不容诬也。”《理学纲要》,第197页。,但从他自觉运用上述分类话语的情况看来,我们可知“科玄之争”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之剧,同时亦可窥见那些已经深入人心的话语将如何长期陷“理学”于不利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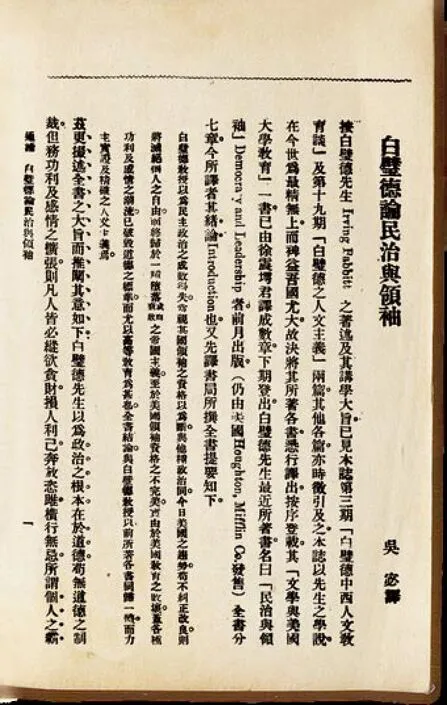
《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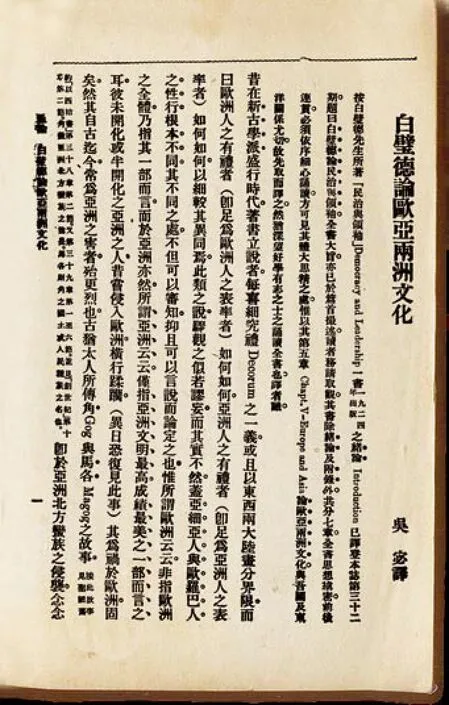
《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
吴宓在学成归国以前,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内的这种氛围,自觉未归之时国内大局已定,时势已无可挽回①见吴宓1919年11月12日日记“: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殊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等等,《吴宓日记》II,第91页。。由于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关系,吴宓很早便蒙发了回国与“势焰熏天”“炙手可热”的“胡适、陈独秀之伦”鏖战一番的想法,他主动站到了当时席卷国内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传统文化之卫护者的角色②如吴宓在1920年3月28日日记:“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着重号为吴宓所加)”,《吴宓日记》II,第144页。。同时,就吴宓的个人气禀而言,他又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诗人的气质,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洞见”到了回国后将面临的种种“苦恼磨折”和黑暗的前途,心中无比的郁激与愤懑,并且在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之下多次想到自杀,甚至还有一次自杀未遂③见《吴宓日记》II,1919年4月19日、12月29日日记,第127页,154~155页。。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吴宓突然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中旬接到梅光迪的“快函”,急召他回国“发展理想事业”,吴宓仅“略一沉思”,便即同意到东南大学就聘,并于同年六月中开始办理回国手续④《吴宓自编年谱》,第214~215页。,真可谓迫不及待、归心似箭。
但吴宓归国后面临的形势,正如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所预见到的,“新文化派”已经一统天下,“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辉煌胜利的尾声,任何“新文化”的反对者在这时都已无力回天。吴宓归国创办《学衡》(1922. 1)仅一年之后,一九二三年便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之大论战。以丁文江为代表的唯科学主义者们坚持科学与人生观不可或分,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分别;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哲学属于内在世界的“我”所要解决的问题,“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⑤引文分别见张君劢《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33~35页;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41~43页。一方坚持科学进步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方则强调关乎人之内心生活的人生哲学问题断非科学所能为力,—可以想见,这场论战在吴宓眼中,套用白璧德的经典话语来说,实质上代表了“物律”与“人律”之间的斗争,而前者可以说在此对后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学衡派”人士当时并未加入战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学衡》对此完全没有反应。缪凤林在一九二四年二月第二十六期《学衡》《阐性(从孟荀之唯识)》一文中,曾以“唯识论”对质“西洋哲学科学所有之因果论”,其中谈到:
曩有争辨玄学与科学者。主科学之士,咸主因果,谓心理现象之起,必有其因。此诠因果二字,诚属无误。惟其所以说明之者,仍不外一“刺击与反应”S-R之公式。……乃彼犹欣然自得曰,此西洋博士之实验也,差足尽人世问学之能事。
由此似乎可以看出,这篇在“学理层面”就“西洋哲学科学所有之因果论”提出批评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科玄之争”之背景提出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答案的。
与对手相比,唯科学主义者们的论争姿态则要激烈得多了:当梁启超认为人生大部分问题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然而有一小部分(或许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甚至他的这种较为平和的提法也被陈独秀毫不留情地斥为“骑墙态度”⑥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5页。,—我们从中赫然可以见出“科学”、或任何一种口号和话语意识形态化之后所具有的专制力量。以梁启超在学界辈分位之尊,影响之大,温和地提出相对执中的意见尚且会立刻遭到批判,其他人噤若寒蝉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时,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大力渲染“科学”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并提出自己所理解的“科学的人生观”其实就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第22页。。这样一来,“自然主义”这一白璧德终生的大敌,在这场论战中借重“科学”之力迅速“得势”,从而“物律”就此彻底战胜了“人律”。
吴宓对此自然不会全无感触。他在一九二四年《民治》这篇译文中,将“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比附为“以理治欲”,现在看来,这寥寥数字的批注中蕴含了多少言外之意!要知道,白璧德学说分明与先秦儒学“甚通”,在当时对“玄学鬼”的一片谩骂声中,在上述二者之间相互阐发或许是更为明智的做法,而吴宓却一定要使用理学家的话语来激发人们对白璧德“人文主义”和宋明理学之间的联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简直无异于“顶风作案”,这种行为之“反动”、之“复古”,—或用新时期以来更为常见的批评话语来说—之“保守”,自是可想而知。在时人眼中,至少从《学衡》宣扬白璧德学说的宗旨来看,此时将白璧德学说解释为已在国内恶名昭著的“以理制欲”论,可以说是完全缺乏宣传策略的。并且在“科玄之争”胜负已判、尘埃落定之时,再做无关痛痒的发言,发出一些微弱的反抗之声,自然可以说是“慢了半拍”,这不但于事无补,还徒显得是在争戴一顶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玄学鬼”的帽子。事实上,吴宓与时势对抗的苦心为大多当年与其一同留学的好友所不解,例如当年意气勃发、宣称“定必与若辈(指胡适与陈独秀)鏖战一番”的张鑫海,回国后转而成了与胡适过从甚密的朋友,认为吴宓办《学衡》是“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①见吴宓1925年5月25日日记,《吴宓日记》III,第28页。,甚至当《学衡》面临停办,吴宓为之奔走至陈寅恪处,陈寅恪也直言不讳地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面对一生经营之事业终将被毁的厄运,吴宓是夜不能成寐、“怅念身世,感愤百端”②吴宓在192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说:“接中华书局来函,言《学衡》60期以后不续办云云。不胜惊骇失望。……寅恪并谓《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云云。”《吴宓日记》III,第251页。。
然而,吴宓的“以理制欲”这一注脚绝非下笔即是的随意攀扯。吴宓可以说很早就对宋明理学深具同情,而他对理学最初的同情与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导师与挚友的影响:首先,白璧德盛赞中国儒家文化,且对朱子有着极高的评价,这必然会对吴宓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好友陈寅恪亦曾多与倾谈对中国儒家哲学、佛学的见解,特别是对融合二者之义理的程朱理学体会极深,吴宓曾在日记中不惜笔墨全篇详录陈寅恪的谈话云: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着重号为吴宓所加)③见吴宓1919年12月14日日记,《吴宓日记》II,第102~104页。
虽然吴宓对理学的理解不仅限于耳学陈氏,但从这些大段的引文可见,陈寅恪的见解应该给他带来了不小的触动④吴宓目陈寅恪为人中之“龙”,多次在日记中不遗馀力地盛赞这位朋友,如“陈君(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以及“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故超逸出群,非偶然也。”(着重号为吴宓所加)等等,《吴宓日记》II,1919 年3月26日、4月25日所记,第20页,第28页。吴宓经常在日记中大段记录与陈寅恪的谈话,可见陈寅恪对吴宓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小的影响。。从这些线索可以知道,吴宓自然会认为当时国内对理学的批评有失公正。他的这种心态在《学衡》创办早期已有显露,如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即“科玄之争”爆发之前)第四期《学衡》《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已经在为宋明理学的“以理制欲”说进行辩护了:
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他还说道:
凡人之立身行事,及其存心,约可分为三级。……中者为人界(Humanistic level),立乎此者,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以为凡人之天性皆有相同之处,以此自别于禽兽。道德仁义,礼乐政刑,皆本此而立者也。人之内心,理欲相争,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于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吾国孔孟之教,西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下之说,皆属此类。……下者为物界(Naturalistic level),立乎此者,不信有天理人情之说,只见物象,以为世界乃一机械而已。……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有欲而动,率性而行,无所谓仁义道德等等……吾国受此潮流,亦将染其流毒。(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六期《学衡》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一文,可以视作吴宓首次明确地就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虽然他采取的是远离论争中心的一种非论辩式的态度:
主张人性二元者,以为人之心性(Soul)常分二部,其上者曰理(又曰天理)Reason⑤注意吴宓在此注出“理”即是“reason”(1923年4月),而在1年多以后,他在《民治》(1924年8月)一文中复特别强调了“理”“并非理性或理智”,看来吴宓对于白璧德学说的认识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下者曰欲(又曰人欲)Impulses or Desire,二者常相争持,无时或息。欲为积极的,理为消极的;欲常思行事,而理则制止之,阻抑之。故欲[按:此应为“理”之误]又称为InnerCheck或Will to Refrain。……彼欲见可求可恋之物近前,则立时奔腾激跃,欲往取之。而理则暂止之,迅为判断,如谓其物而合于正也,则任欲之所为而纵之。如谓其物之不合于正也,则止欲使不得往。此时,欲必不甘服,而理欲必苦战一场。理胜则欲屈服,屡屡如是,则人为善之习惯成矣。若理败,则欲自行其所适,久久而更无忌惮,理愈微弱,驯至消灭,而人为恶之习惯成矣。……理所以制欲者也,或疑所谓理者,太过消极,不知理非不许欲之行事,乃具辨择之功,于所可欲者则许之,于所不可欲者,则禁之而已。……人能以理制欲,即谓之能克己,而有坚强之意志。不能以理制欲,则意志毫无,终身随波逐流,堕落迷惘而已。故曰,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谓几希者,即心性中之理也,即以理制欲之“可能性”也。克己复礼……盖即上节所言以理制欲之工夫也。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能常以理制欲,则能勤于省察而见事明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以理制欲”在吴宓这篇论述自身“人生观”的文章里,成了一个贯穿始终、频繁出现的关键话头。甚至在吴宓《民治》译文中出现“以理制欲”之注解的同一个段落里,吴宓不失时机地再次为“今夫人之放纵意志(即物性意志)与抑制意志(即人性意志)常相争战”一句加注曰:“前者即吾国先儒之所谓理,后者即其所谓欲”,—对“以理制欲”说的强调已经是无以复加,真可谓用心良苦。
此后在吴宓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的译文《诗之趋势》中,仍可见到这样的说法:“须认明人性中实有互相冲突之二成分,其一为放纵之欲、其二为制止之理。其一为被动而成形者、其二能选择而使形成者。其一乃尘秕、其二则圣神也。”吴宓并且再其后加以按语解释云:“按其一为人性中卑下之部分、 其二为人性中高上之部分。东西古今凡创立宗教及提倡人文道德者、皆洞见此二者之分别、而主张以其二宰制其一,各家之说、名不同而实则无异也。”
而原文的表述大致是这样的:“应认识到人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对立,即‘欲望的力量’(the power of appetite)与‘控制的力量’(the power of control)之间的对立,一者主动塑造,而另一者被动成形,二者仙凡有别。”①Irving Babbitt,“Review of The Cycle of Modern Poetry”,Forum, vol. 82,1929, p.xx.—吴宓对原文的“扭曲”一望可知。
吴宓为何要逆流而动、大力支持在当时已经被众人弃如敝屣的“以理制欲”之说?事实上,吴宓对“以理制欲”这一宋明理学关键话头的反复申辩与陈说,已决非单纯为对抗“新文化运动”而展开的论辩,而实际上是与其救国救世之热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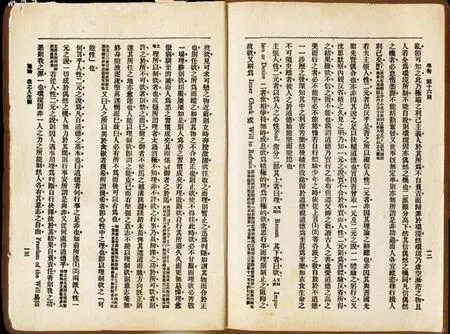
吴宓《我之人生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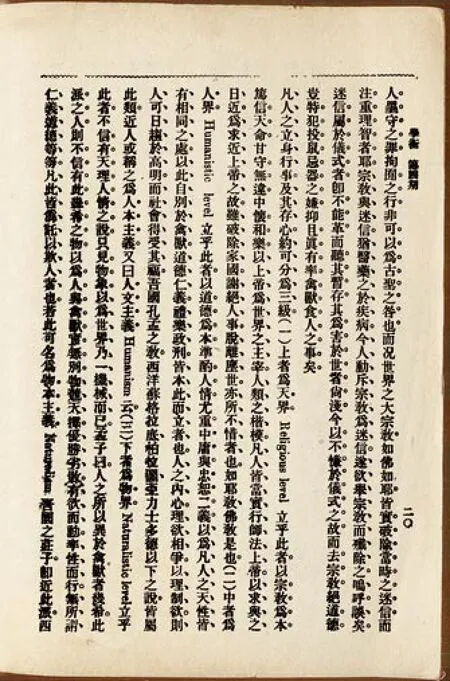
吴宓《评新文化运动》
忧国忧世,可以说是五四学人的特有心态①单就吴宓而言,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述了自己的忧国之苦,亦曾数次谈及诸同学友好感伤国事的情形,如他在1919年7月24日日记中写道:“今日中国之危乱荼苦,尽人所为痛哭而长太息者也”,日记间有几行小字曰:“每日读报,中国之新闻,无一不足摧心堕魄。明思,性气雄厚活泼之人也。然明思告我云,‘今某之幸不致疯狂者,亦几微之间耳’。可见忧国之苦,无术解脱也。”《吴宓日记》II,第39~40页。又见其1920年2月2日日记:“……宓最易发心病之原因,(一)与知友谈中国时局种种。(二)阅中西报纸,载中国新闻。(三)读书而有类中国情形,比较而生感伤者,……(四)计划吾所当行之事,如何以尽一身之力,而图前途之挽救。(五)悬想中国将来之复亡,此日之荼苦。……每至不能解决之时,终觉得寻死为最快乐。”《吴宓日记》II,第127页。并在同年4月19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念及国内形势“忧心如焚”,“同心知友,偶见面谈及,亦只楚囚对泣,惨然无欢”的情状。《吴宓日记》II,第154~155页。,引入西学,往往是为了“为我所用”。有论者认为:“学衡派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表现与其说是一种内容上的接受,毋宁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②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第73页。吴宓等人全身心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奉之为圭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一学说能够有力地支援国内日渐失势的旧有传统价值体系。在吴宓等人看来,那些学习工程、实业的留学生不过是学了一些末技,环境稍有改变,便“不复能用”,唯有“天理人事之学”是历久不变的,“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行而上之学)为根基”③见吴宓1919年12月14日所记陈寅恪述谈之大旨,《吴宓日记》II,第101页。。因此,“科玄之争”中对于“玄学”的批判,在吴宓眼中,可能无异于在动摇“救国经世”之本。
这样看来,与其说吴宓是在力图宣扬“人文主义”而不得其法、是以不免“昧于时事”之讥,毋宁说吴宓是在极力声援国内大受批判的宋明理学而孤军奋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支持国内大遭批判的“形而上之学”,吴宓祭出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将之作为一种权威学说,转来佐证理学的合理性,指出“以理制欲”正通于“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这一“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这可以说是“六经注我”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吴宓一方面是在用“以理制欲”为白璧德师的“高上之意志与卑下意志之对峙”概念加注,另一方面更是在发挥白璧德学说的核心概念来为“以理制欲”说作注!这样一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附带结果便是,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文本进入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后,其间不免充斥了诸如“礼教”、“复古”,以及“以理制欲”等诸多敏感字眼,其“保守”的面相遂由是奠定。
由此可见,我们须从译者吴宓所处之时代背景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入手来对译文加以理解,才会看出他的译文在“为我”与“为他”两种意图之间那种微妙的游走往还,以及其中反映出的五四学人立足于“我”的那种特有心态,由此后世研究者才可避免对那一时期学人之“有意的扭曲”产生“无心的误读”,并且不再任由这些误解在此后的研究中延续下去。
事实上,前文提到过的相关“误解”并非孤例。肇始自吴宓的“以理制欲”这一阐释流传之广,或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新时期的研究者们广泛继承了这一说法,如有人泛泛而论“宋代新儒家理欲的划分以及对理的强调和新人文主义‘人性二元’的观点与对理性的推崇是相通的”④旷新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有人则径将“新人文主义”概括为“‘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实践道德论”⑤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47页。。由此看来,如果不加辨析地接受吴宓的译文,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质便是“以理制欲”的—这一看法便很可能会成为定论。八十年前吴宓的一番苦心,当时固然几乎无人理解,而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却多是吴宓“忠实的叛逆”,顺理成章地将“人文主义”之“内在制约”的概念坐实为“以理制欲”,从而误解了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本义,也误解了吴宓在文中批注“以理制欲”的真实用意。不论是《学衡》后期“人文主义”思想之更有力的阐释者梁实秋,还是同时期《学衡》的反对者林语堂,他们根据不同的需要或作出“理性克制欲望”的阐释,或“别有用心”地沿着吴宓的思路继续发挥、给出“颇似宋朝性理哲学”之论断,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看来都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层面上说话的,针对的是何对象,涉及的又是何问题。而新时期的研究者却有时会表现出缺乏一种相应的历史感,对全部的阐释性内容不加分辨地“照单全收”,从而造成了对“人文主义”所谓“误读”的误读,—这难道不足以令我们深思吗?
六、结语:“学衡派”与白璧德的相遇与错过
我们此前曾提到过,白璧德对“柏克式的自由”情有独钟,而“柏克式的自由”意味着对“更高之权威”的“服从”,这乃是“真正的自由”的基础。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权威”概念的内涵在此其实已经悄然遭到了置换:白璧德所说的“权威”,与柏克所说的由“古老的政府体制”及“祖先的遗产”所代表的 “权威”⑥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35.不同(白璧德称之为“outer authority”,外在的权威),白璧德的“权威”虽然“高于”、但同时无外乎“自身”,其标准得之于个人的“内在生活”(inner life)①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9.,并由“高上意志”从内部向个人发出“绝对命令”。
柏克当然并非无视于“个人”的维度,他曾说过:“所有自然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人是一些个人,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他还说过:“凡是个人能独立去做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他都有权去做。”②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页,第68页。不过,当柏克说“人是一些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用“自然的个人”来对治“原则上的人”,并由此来批驳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念,即所谓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克才会特别指出“所有自然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同时,虽然柏克认为“凡是个人能独立去做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他都有权去做”,但在这有限的让步之后,接下来话锋立转,“社会”要求个人的“意志应该加以控制”,“情感应该加以驯服”,而这只有通过他们“自身之外的力量”(a power out of themselves)才能做到③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p.71-72.,归根结底,“个人”仍需服从“外在的权威”。相比之下,柏克的“个人”显然并非“个人主义的”个人,而是“小心翼翼地”遵从“先例、权威和典范”、“满怀感激地”继承“古老的政府体制”及“祖先的遗产”的个人,这与白璧德之拒不承认任何“之前的、之外的、之上的权威”的“个人”有着显著的区别。
白璧德与柏克思想的“亲缘性”是如此的显著,人们往往会由此忽略二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实际上,他们的根本歧异还不止于“民主”问题,或者说,“民主”问题只是他们所面对的“现代”这个大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个人”问题。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一个突出的性质,便是其中贯穿了一条深深的“个人主义”的脉络。白璧德着重指出,个人主义的精神与现代精神密不可分,成为“现代的”(modern)不仅意味着成为“实证的”(positive)、“批判的”(critical),还意味着要成为“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④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p.xii.,同时他的“人文主义”亦“不但是实证的、批判的”,而且是“个人主义的”⑤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8.,从而其“人文主义”无疑是“现代的”。
白璧德认为,批判精神(the critical spirit)、即个人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individualism)的出现导致了欧洲旧式统一性(older European unity)的丧失;成为“现代的”意味着个人日益成为“实证的”、“批判的”,并拒绝接受来自任何“之前的、之外的、之上的权威”(an authority “anterior, exterior, and superior”)给予的东西⑥Ibid, p.142.。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白璧德亦非无视于个人的“社会”维度,这里有一个颇为典型的例证:密尔此后在On Liberty(1859)一书中提出了与柏克的观点(即“凡是个人能独立去做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他都有权去做”)看似一脉相承的命题⑦J.S.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4.,但二者关键性的区别是,密尔的提法显然遗漏了柏克相关论述“话锋一转”之后的层面。有趣的是,白璧德对密尔的做法并不“领情”,此后他曾专门针对密尔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密尔未能见出人性中关注他人与自身利益的成分实难判分,此外还有一个道理居然是,密尔未能见出“甚至从社会角度来说”,“人性中关注个人利益的成分”亦“更为重要”⑧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201.,从而将好不容易开辟出一片“私密空间”的个人又重新拉回到了社会领域中来。—白璧德这种“神龙摆尾”般的招式在其论著中比比皆是,一切成熟复杂的思想原本都会尽力弥缝自身的漏洞。
白璧德进而指出,柏克是“反个人主义的”(antiindividualistic),他的“个人”过多地倚重于权威性的因袭习惯(prescription),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传统的宿命论式的默认(fatalistic acquiescence),并由此放弃了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形而作出的合理调整。长此以往,个人可能会无法保持“自主”(autonomy),失去独立的意志,并最终成为“具有无上权力的国家”(the all-powerful State)的一件工具,此即柏克思想的偏颇之处⑨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p.100-101.。
相应地,白璧德认为自己乃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a thouroughgoing individualist),而“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是“现代”的特有产物;他之所以反对某些“现代人”(the moderns),乃是因为他们“不够现代”,他们仅根据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与浪漫幻想与此前的传统决裂,其实称不上是“现代人”,只是“现代主义者”(modernist)而已,然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便是彻底的、完全的现代人,《民主与领袖》一书便是写给那些投身于现代实验(the modern experiment)的同道的⑩Ibid, pp.143-145, p. 317. 比较吴宓对“the moderns”(即“今人”)的批判态度,则完全是站在传统的角度立言的。。因此,不能再遵循“旧式的偏见与不理性的习惯”,这正是“柏克的方法”弱点所在,而应通过“实证”与“批判”的方式、即与“现代精神”相一致的方式,以重新获得并保持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遗失了的关键因素①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157.,—这便是白璧德此前未曾明言的柏克“之外”的方法。
在当前情形下(白璧德总是不忘强调“环境”与“时代”的“当下”性,即其“现代”性),具有“实证”、“批判”诸精神的“现代人”,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者”(sound individualist)应从“内在生活”中获得真理,而与过去彻底决裂(breaking completely with the past),—且慢,当我们听到这句话居然出自白璧德之口,可能会怀疑引文有误,然而,白璧德接下来继续意犹未尽地说道:内在生活需要标准(standards),标准在过去来自于传统,而如今的个人主义者要想获得标准,就必须依靠批判的精神,与传统对生命的统一规划(the traditional unifications of life)彻底决裂②Ibid, pp.8-9.。也就是说,白璧德不但站在了民主一方,并且最为关键的是,他决定性地站在了现代一方。此时如果由柏克来评判白璧德,后者不但不能说是“保守的”,反而甚至应该是“激进的”了。(顺便一提,吴宓对白璧德这句话的译文是:“内心生活……必遵从一定之标准。在昔之时,此标准可得之于古昔传来之礼教,……然在今日,奉行个人主义者,既将古昔礼教所定为人之标准完全破坏,欲另得新标准,须由自造,而惟赖乎批评之精神。”③见1924年8月第32期《学衡》吴宓译文《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译文对原文的“改造”显而易见,而这种“改造”最直接的效果便是,白璧德鲜明的“现代”立场变得模糊起来,而由此重新踏上了“保守”的旧轨。)与柏克存在着一百三十馀年时代落差的白璧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现代”,并在这个“大问题”上就此与之分道扬镳了。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一直在讨论白璧德与柏克之“异同”,并着力将柏克设定为白璧德之“保守的”参照物,好像通过举出二者之间的“根本歧异”,便可证明白璧德与“保守”并无干系了。为了消弭这种可能的误解,不妨在此做几点说明:首先我们不会任由自己掉头回到此前诸多“翻案”文章的论述逻辑中去,这种简单的逻辑是根本无法覆盖、解释复杂的现实情况的。
其次,本节论述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辨析白璧德与柏克之“异同”,我们举二人的“异同”为例,是希望传达如下一个观点:对于在思想史中发挥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只能将之“放回”各自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加以评判。白璧德与柏克虽然同具“保守”之名,但这“保守”二字在不同地域、不同情景下将具有不同的内涵,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一个本身尚需因时因地进行辨析的名目而将相关人等“一网打尽”。
比如,就柏克时代之英国的整体氛围而论,恐怕很难以“保守”一词概括柏克的整体立场。不要忘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柏克始终都是英国辉格党的主要发言人(1765~1790),大革命爆发之后,柏克始与托利党政见趋同,政治姿态日益“右”转。虽然柏克的基本思想始终一贯,并不以法国大革命为“转折点”,但其影响巨大而备受争议的《法国革命论》(1790)一书,毕竟是他晚年渐趋保守之后的著作。
相应地,尽管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柏克的思想相比,乃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者说,是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大陆自由主义的某些成分、进而在美国土壤中自行“开出”的一脉的自由主义学说体系,但就其所处的国家与时代而言,在美国“自由”、“民主”的整体大环境下,—这显然不能与素来具有保守气质的英国、特别是柏克时期之英国相提并论,自由主义的“右翼”观点便自然充当起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钟情于“英国式自由”的白璧德自然便成了美国“保守”倾向的代表。不但诸多“自由主义批评者”称之为“保守主义”的典型,还有不少“保守主义思想者”将之奉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先驱:如“共和党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H. Nash)认为白璧德等人开创了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④除了白璧德,还有穆尔、艾略特等与“新人文主义运动”相关的人士均被称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老一代先驱”。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Since 1945, New York: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1976, p.58.;另有著名当代“保守主义思想家”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在其梳理“保守主义”源流的名著《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一书中开辟了一个专门讨论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章节,通篇以毫无保留的肯定语调大量引述了白璧德的观点,甚至以无可置疑的赞美语气说道:“亚里士多德、柏克与约翰·亚当斯是他[白璧德]的导师,……在他身上,美国保守主义臻于成熟。”⑤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0, p.477.—白璧德在此成了继承亚里士多德-柏克“道统”的美国“保守主义”集大成者,“保守”的称号看来已无从推卸。
不过,不但素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①See 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chap. VI: True and False Liberals.自命的白璧德本人不会认可“保守”的称号,与他同时代及稍晚的穆尔与艾略特等人也不会同意这一判断。我们此前曾提到过,白璧德的学说不但为同时代的“现代主义者”所诟病,且同样招致了“传统主义者”的不满,特别是其中还包括了与白璧德立场趋同的某些“人文主义者”。如穆尔与艾略特等人与白璧德产生分歧,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够“自由”,而正是因为他不够“保守”。大家已熟知的他们在看待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只是其根本分歧的一个主要方面。再举一例,保守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便是“所有权”问题,柏克维护“公民所有权”不遗馀力,并对法国革命政府残酷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深恶痛绝②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pp.127-131,pp.186-188.;有论者曾指出:柏克在论及自由时,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但是一旦涉及财产,他就只谈权利不谈义务”了③陆建德《柏克论自由》,《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在这一点上,白璧德的挚友穆尔才是柏克的真正后继者:穆尔顷力维护财产权,竟然老实不客气地公然表示,“对于文明人来说,财产权(the rights of property)比生存权(the right to life)更为重要”④Paul More, Aristocracy and Justice, Shelburne Essays, Ninth Series, New York, 1967, p.136.。—这句话成为全部“人文主义文献”中征引最广的一句“名言”,更成了论敌们说明“人文主义者”群体“保守”、“反动”的有力证据;因为白璧德与穆尔的密切关系,人们经常将此当作白穆二人共同的立场,甚至一位同情“人文主义”的研究者也由此叹曰:他们(白璧德与穆尔)在维护财产权的问题上,完全没有了“人文主义的适度与克制”,从而使得很多人“掉头而去”⑤J. David Hoeveler, Jr., The New Humanism: A Critique of Modern America,1900-194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7,p.132.。然而,“人文主义者”群体及其观点并非铁板一块,穆尔的这一表态当然不能代表白璧德本人的观点。上述研究者没有看到,白璧德一方面严厉批判卢梭对私有财产的攻击,但另一方面则特别批评了“今日保守主义者”(the conservative nowadays)往往“为了财产本身而保护财产”,而不是像柏克那样,保护财产是为了达成“个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从而他们将财产看作了目的本身,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⑥Irving Babbitt,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p.75, p.272.。白璧德言下固然是在“泛指”“今日保守主义者”,但具体所指为谁,穆尔应该心中雪亮。—以此而论,白、穆二人之分判然矣。
至于艾略特,对于白璧德竟尔斥拒“之前的、之外的或更高的权威”的个人主义立场始终意不能平,甚至在白璧德去世后仍不能释怀⑦如艾略特在白璧德去世次年出版的书中提到了“已故的欧文·白璧德”,说他“似乎在力求通过一种赫拉克里士式的、然而又纯然是理智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努力来弥补活生生之传统的丧失”云云。T. S. Eliot, After Strange Gods-A Primer of Modern Heres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34, pp.39-40.。—英国当代保守主义理论家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指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保守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的价值并非绝对,而是从属于另一更高层次的价值,即既定政府的权威;同时政府这一核心“权势机构”的主导理念便是“基督教社会的理念”,斯克拉顿进而以艾略特为例指出,后者便在这个意义上对英国国教秉持了一种“高度自觉的态度”,因此不能把艾略特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笃信宗教者”⑧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页,第151~152页。。确实,白璧德与艾略特的这一分歧不仅代表了二人在宗教态度上的歧异,更表现为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在广泛的政治、文化、宗教诸社会生活领域中整体价值观的差异。当白璧德站在美国本土思考“那些英国人”不仅将“宗教”、还将“实际上的教会机构”视为“他们的国家”及“宪法之根本”的时候,艾略特则干脆加入了英国国籍,并率尔自称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王党”(此即英国托利党)与“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教徒”⑨T. S. Eliot, For Lancelot Andrewes—Essays on Style and Order, London: Faber & Gwyer, 1928, “Preface”, p.ix.,以鲜明的姿态与(美国)自由主义宣告了决裂。
从白璧德两面受敌的情况来看,当时国内比他远为“保守”者大有人在。可见,即便是在“民主”、“平等”的美国,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转型期”,白璧德也并不能充任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也就是说,白璧德的思想并非“保守主义”的,“学衡派”引入中国的原是最正宗不过的美国自由主义“右翼”思想。只不过,当这一思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曾经无比传统、守旧的国度却已经以最大胆的姿态拥抱了自己的“现代转型”,从而在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美国这一自由主义“右翼”思想及其传播者就此顶风而上,与中国本土传统保守力量一道,充当了“保守主义”的典型。
美国自由主义的“右翼”进入中国,成了“保守主义”;胡适等人引入中国的“自由主义”,则其实不过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左翼”。此前我们曾提到过,美国进入进步时代(1904~1917)之后,针对前一时代(即镀金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全社会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此即进步运动);在这个旨在“纠前代之偏”的年代,维持现有“秩序”的意识日趋让位于“改革”的冲动,整个社会思潮开始呈现出某些“激进”的品格。杜威主持的以“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为核心理念的“进步教育”便是“进步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教育理念曾吸引了当时诸多知识分子,其中艾略特校长在哈佛大学展开的一系列改革便构成了“进步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艾略特校长的改革为标志,“democratic education”的理念开始入侵大学,与此前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恰构成了一对“反题”。白璧德作为“liberal education”的坚决捍卫者,针对杜威推广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批评①与之相应,中国一方面有《新青年》杂志正面宣传“平民教育”,另一方面则有《学衡》杂志对“平民教育”提出异议。:二人的对立当然不仅表现为教育理念上的冲突,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对立,即新老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自由主义的“右派”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指责“左派”已经走向了激进主义,如前面提到过的对白璧德称服不已的柯克便曾激愤地指出杜威的思想体系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杜威)根据卢梭的观点发展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鼓吹一种平等主义的集体主义”,并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求获得“大众”(the masses)的满意,总之,“自一七八九年之后,每一种激进主义都在杜威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②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p.476.。不过,与法国、俄国的激进主义相比,杜威的“激进主义”在中国却最多只能落得一个“自由主义”的名号而已。
啰嗦至此,我们已可看出,“保守”、“自由”、“激进”等等名堂原本只是相对而言。比如英国“自由党”的前身叫做“辉格”,美国“共和党”的前身之一也叫做“辉格”,同是“辉格”,然而由于水土不同,在英国是“左派”,在美国则只能当“右派”了。由于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市场,处于美国自由主义的“右翼”的白璧德有时便被当作了“保守主义”的代表;同样,由于美国也不存在真正的激进主义,处于美国自由主义“左翼”的杜威有时便被看成了“激进主义”的典型。同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激进的”中国,“激进的”杜威这回转而担当起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国内至多给他一个“进步主义自由主义者”progressive liberal的名号),而白璧德式的自由主义则只能退而居于“保守主义”的序列当中了。
现在回到《学衡》,我们知道,《学衡》所刊文章,包括译文在内,素因其“文言”载体而遭到世人的诟病。然而,一篇译文被接受的程度固然与其语言载体有些关系,但归根结底文章的内容仍将构成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译文以大力宣扬“民治”与“平民教育”为务,那么,即便是以“文言”出之,想来也不会招致那样猛烈的反对了。问题是,白璧德这些文章本身便极具“反平等主义”的特质,此后这种精英立场更通过胡先骕的译文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此外,在吴宓笔下复衍生出刺人眼目的“以理制欲”等提法来,从而白璧德学说的“保守”性质立刻凸现出来,此时再加上原文内容与译文载体配合得丝丝入扣,《学衡》这批译文愈发犯了“可恶罪”。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中国这一特殊的时代,吴宓等人引入的白璧德式的自由主义只能是“保守”的。—时代永远是判断一种思潮的风向标,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学衡派”“怎样”译介,而是在于他们译介了“什么”,进而甚至在于他们“译介”了。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选择译介了白璧德的学说,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学说在中国的“命运”。与选择“文言”载体这种“可恶罪”相比,他们的“译介”行为本身,才是《学衡》这批译文的“原罪”。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某种做法有违时代思潮主流,便斥之为“不智”;当整个时代的力量积聚于此,这股洪流将奔决何方,自有其“不得不然”者在,已非人力所能为之。如果,—我们只能作些无谓的假设,时间仅提前十年,白璧德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前进入中国,那么它将不复是“保守”的,而将是“激进”的了,则更无论杜威、法、俄矣。那么,后世研究者又或许将试着为“学衡派”摘去“激进”的帽子了罢。无论是怎样的“帽子”,无论这“帽子”摘掉与否,“学衡派”因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到底遭受了不幸。到底有无最终的“正义”,或者这最终的“正义”对于已灰飞烟灭的当事人而言是否还具有意义,后人已无法可想,我们的研究亦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