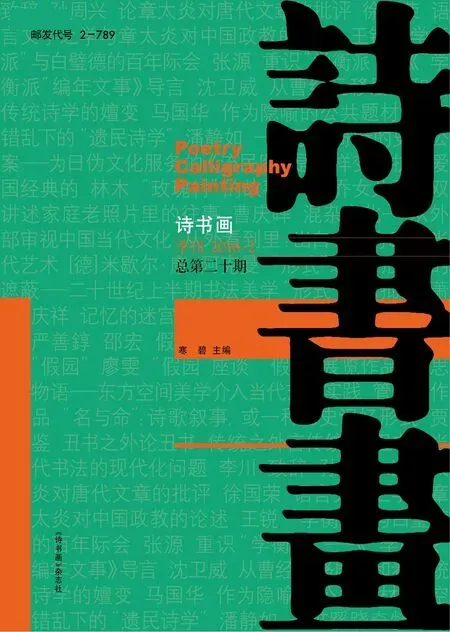论章太炎对唐代文章的批评
徐国荣
论章太炎对唐代文章的批评
徐国荣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文学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唐诗可谓达到诗之顶峰。这几乎是古今学人的共识。但章太炎却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在很多文章与讲演中对唐代文学在总体上评价不高,甚至有卑视之倾向。且不论被他视为“始造意为巫蛊媟嬻之言”①章太炎《与人论文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版本下同。的唐人小说,即使被他视作文学正宗的诗文方面,在他看来,唐代亦并无多少突出成就。虽然唐代诗人辈出,大家众多,诗歌成就亦为后人交口赞誉,而章太炎认为,唐诗并无情性,即使公认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亦有可议之处;而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文章虽然对后世散文影响甚大,但除了刘知几、杜佑以及陆贽等人的政史论文颇得章氏称许外,其他则少有获赞者。尽管他在民国之前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和民族主义情绪,对唐代整个社会习俗颇多不满,在评价唐人(如王勃)时或过甚其辞,晚年观点渐趋平实,但终其一生,他对唐代文学的整体评价都并不高,批评远远多于赞扬,甚至可以说,他有较强的卑唐观念。这在古代文学学术史上是个较为独特而值得注意的现象。
作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其所持论虽不无偏颇,但却不是无的放矢,也不可能仅以空言相詈,而自有其独特的理由。这些理由,既有其个人的原因,也有其时代文化氛围之故。他一生著述丰富,在文学观念上持较为宽泛的“杂文学”观,虽无意于专门的唐代文学论述,但对唐代文章(几乎包括诗赋和小说之外的所有文章,即广义的散文)论述较多,也最能体现其对整个唐代文学的态度。因而,检视章太炎对唐代文章的批评,了解他作出这些判断的依据与原因,发覆其中微意,将其置于学术史的层面来考量,可以较为准确地对章太炎及其学术作出知人论世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也是唐代文学学术史不应或缺的一部分。
一、唐文意度:无学问根柢而饰以华辞
清民时期,虽然受西方影响的“纯文学”观念正为更多学人接受,但章太炎始终秉持“杂文学”观,将一切文字记载(甚至“无句读文”)皆归入“文”之范畴,反对将学说文辞分立。就狭义的无韵之文而言,他对清代以来的骈散之争持较为宏通的态度,也并不仅仅关注抒情类的散文,更重视那些议礼论政以及论述经史典章的学术文章。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说:“近代论文,若阮文达则以《文选》为主,于经史子三部,皆格之文章之外;若李申耆则主耦丽;若姚惜抱则主散行。而海外文家,复有以文辞与学说对立者。先生皆无所取,以为‘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不主耦丽,亦不主散行,不分学说与文辞,其规摩至闳远,足以摧破一切狭见之言。衡论古今,则推汉世之韵文记事,而持论则独尊魏晋。若唐若宋,则以为文学之衰。”②《章太炎生平和学术》,章念驰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1页。他将唐宋视为“文学之衰”,自是他的一家之言,未必能为人认同。但若就古代文学的发展来看,他重视说理文,特别是那些议礼论政以及经史述学的论著,将其当作古代散文的重要方面,这在先唐时期甚至包括唐代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章太炎重视说理文,还有其当时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他生活的当时,无论是要“排满”革命,还是“爱国保种”,都需要以文章进行宣传,与其他各种不同声音的论辩当然更需要雄辩的说理之文。而说理之文不但要析理精微,论证时须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辨性,还要有充分的论据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由解放的思想。在他看来,“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③《革命的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0页。他自己精通小学,学识渊博,所作文字古雅,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以此标准来看待古代文章,最令他心仪的自然是先秦诸子之文,其次则是魏晋玄理之文。这也是章太炎经过不断探索而得到的结论。一九〇二年,他叙述自己的创作历程说:“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第9页。说明自己开始作文时,刻意学的乃是貌似古雅的秦汉古文,但结果得到的只是“唐文意度”。所谓“唐文意度”,其实指的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风貌。这与东汉末年仲长统等人“综核名理”的政论文大异其趣。一九三一年,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与此所说基本一致,而且更进一步阐述了自己行文风格的变化及其原因,同时也展示了自己所依赖的学术资源,其云: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汪中)、申耆(李兆洛),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寔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乎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余又寻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舆(陆贽)。然平彻闲雅之体,始自东汉,讫魏、晋、南朝皆然,非敬舆始为之也。……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②《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陈平原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7~648页。版本下同。
韩愈古文喜欢造词,“惟陈言之务去”,对后世文章影响甚大。章太炎承认自己开始亦颇慕而效之,但后来受到谭献的影响,宗法清代的汪中、李兆洛。汪、李皆重六朝文章,尤其是骈文。他们的文章虽美,却不能与三国两晋文辞相比。何以然也?因为他们只能运其辞作六朝式的“常文”,亦即王湘绮式的淳雅典丽之作。故章太炎推崇当时文人中王氏之“能尽雅”,不过以此而已。更进一步的“议理论政”及“玄理”之文,不仅要“平彻闲雅”,还要“仪容穆若,气自卷舒”,这种高标准的文章,清世及当时均未能见,只能求之于古,于此又看出汪、李之不足,更不用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王、苏等人了。兼之章氏当时“宗师法相”,耽于思辨之乐与精深义理的阐释,更加觉得“师心遣论”之可贵,加上自己的写作实践,悟到以古雅典丽之辞阐发高深义理之不易,故古今文人中,惟“王阮嵇裴”之属为不可及也。唐人文章,他比较推崇的是陆贽的奏议文,而陆文在唐代当时却并不被看重,因为“大凡文品与当时国势不符者,文虽工而人不之重。燕许庙堂之文,当时重之,而陆宣公论事明白之作,见重于后世者,当时反不推崇。萧颖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结始为谲怪,独孤及、梁肃变其本而加之厉。至昌黎始能言词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语,必屏弃不取,而别铸新词。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孙樵,无不皆然。风气既成,宜乎宣公奏议之不见崇矣。”③章太炎《文学略说》,《国学讲演录》,吴永坤讲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按:本文所引《国学讲演录》一文皆出于此。陆贽之文明白晓畅,不重华辞,而唐人崇尚的是气势壮大、别铸新词的壮美之风,追求文采斐然,故陆文“不合时宜”。但若将陆贽之文与三国两晋文辞相比,则又高下立判。
正是由于重视说理之文,章太炎特别青睐古代“论”体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炳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顾盛推魏、晋之论,谓汉与唐、宋咸不足学;独魏、晋为足学而最难学;述《论式》。”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论式》为其《国故论衡》中卷之一篇,通论古代论体文的发展。他于古代散文中本重说理文,而论体文又是古代说理文中的精粹,作者既可展示文士驰骋文采的优势,又可表现学者的学术底蕴,所以说:“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观其流势,洋洋纚纚,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惟刘秩、沈既济、杜佑,差无盈辞。持理者,独刘、柳论天为胜,其馀并广居自恣之言也。”⑤《论式》,《国故论衡》中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78页。按:本文所引《论式》一文皆出于此。“出入风议,臧否人群”,也就是放言高论,品藻人物,此类之言随意性较大,善于夸饰的“文士”自是擅长。但如果要“持理议礼”的话,则需要以学问为底蕴,讲究严谨的逻辑,先秦名家之文是其典型。而整个唐代能够合此者不过寥寥数家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缀文者在彼不在此”。也就是说,唐文过于重视华彩之辞,文章写得洋洋纚纚,似乎潇洒自若,实则内容干枯,“即实不过数语”,大段文字其实表达的不过几句话而已,内在早已“自偾”(自我覆败),自己都难以说服自己,更无法令他人信服了。根本原因在于此类文章“非擅其学莫能至”,唐人学术既疏,自然不能于此争胜了。
他所提到的唐代刘、沈、杜几家,稍见称许,其实只是由于他们的“史才”所致,此“史才”体现于其史论中,稍能说理,故太炎称之“差无盈辞”。至于唐代散文,当然还是以韩、柳最有代表性。这也是章太炎所认同的。他说:“唐人散体,非始于韩柳。韩柳之前,有独孤及、梁肃、萧颖士、元结辈,其文渐趋于散,唯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渐厚耳。譬之山岭脉络,来至独孤、萧、梁,至韩柳乃结成高峰也。”(《国学讲演录》,P252)在一九一〇年所作的《与人论文书》中虽然也批评了韩、柳之文,但还是认为:“今夫韩、吕、刘、柳所为,自以为古文辞,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①《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68页。到底还是承认韩吕刘柳之文在唐文中的地位。但即便是韩柳,其文章仍然短于说理,因为“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说理。韩柳为文,虽云根柢经、子,实则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韩较柳,柳犹可以说理,韩尤非其伦矣。……然则古人之文,各类齐备,后世所学,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国学讲演录》,P242)韩、柳为唐宋八家之首,也是后世“古文”的典范,他们学的乃是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秦汉高文”,其范文已不以说理取胜,本身也无“根柢经子”的学术底蕴,因而他们的文章既无唐初的“轻清之气”,更无法像魏晋文那样气象雅淡。这在其一九二二年的国学讲演中表述得更加清楚:
唐初文也没有可取,但轻清之气尚存,若杨炯辈是以骈兼散的。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苏许公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信)也不同于陆(机),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的滥觞。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的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的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湜、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诘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渐变为后代的“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②《国学概论》第四章《文学之派别》,曹聚仁记录,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91~92页。

《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

《国故论衡·试论》(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他认为韩、柳等中唐以后的文章已无法与初唐相比,而初唐文源于六朝却不足以承其美。他认可美不胜收的晋人文章:“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笮蹇吃之病,斯信美也。”①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虞云国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6页。本文所引《菿汉三言》一文皆出于此。“观晋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②《菿汉闲话》,《太炎文录续编》卷一,《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陆机之文是他心目中古代散文(当然也包括论体文)的典范,得到他自始至终的推崇,所以将李商隐的四六文与之相比称为“天壤之分”,在其他很多地方也一再表示艳羡。
可以说,他对唐文的批评也与其心目中的“魏晋情结”相关,在哲学、文学以及学术与社会风俗等方面他皆给予魏晋以高评。而论体文则尤以魏晋文章为典范,因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论式》)魏晋文在很多方面皆承继汉代—主要是东汉(即章氏所谓“东京文学”),“独持论仿佛晚周”,在说理论辩方面则可以与晚周诸子相媲美。虽然时过境迁,两者“气体”(气调体制)有异,风格与语言皆已不同,但魏晋文之说理似乎臻于美轮美奂之境。“守己有度”,就是阐述自己思想时候有理有据,不给论敌有机可乘,可以充分而恰当地阐明自己的见解。“伐人有序”,即批评别人或与他人辩论时,有自己的逻辑次序,析理绵密,进退自如,有张有弛。“和理在中”,即“和理”包含在内在的心中而通过文章表现出来。“和理”,是借用《庄子》中的原文。章太炎非常重视先秦诸子文章,特别重视诸子文章所体现出的“义理”,尤其推崇《庄子》一书,在《五朝学》中,他又说:“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这里的本意是说玄学名士并不是像后世那样被评价很低,在道德品行方面也是值得推崇的。其原因就在于“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这句话正是出自《庄子·缮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③《庄子集释》,郭庆藩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8页。庄文本意是说,恬静是人的本性,知也是人本来所有,但要任其自为,不要伤害了恬静之性,两者不是相妨,而是相养,这样的话,“和理”也就出自本性了。但章太炎此处所说的“和理在中”的“和理”,当然不是指人的道德,而是指文章中所包含的内在的逻辑思维的思路,一种一以贯之的理性认识,即内在之理。有了这些在内后,然后“孚尹旁达”,外在地表现出来。“孚尹旁达”出于《礼记·聘义》:“孚尹旁达,信也。”郑玄释曰:“孚读为浮,尹读如竹箭之筠。浮筠谓玉采色也。采色旁达,不有隐翳,似信也。”①《礼记正义》卷六十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79页。这本是古人一种比德于玉的说法。也就是说,“孚尹旁达”就像人的诚信这种品德一样。用在这里,表示魏晋文章的特色,其意是:文章有文采,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并不隐晦,因而显明。换句话说,因为玉有温润之性,又有美丽的外在之形,给人赏心悦目之感,但它美好的品性可以透过美丽的形式表现出来,却是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的张扬。这种文质彬彬的文章,以学问为根柢,追求内在义理的精微阐发,不刻意追求外在形式之美而华丽自在,只有魏晋文章、尤其是魏晋玄理之文能够体现。一旦文学新变,作者有意识地追求华辞,文章也就不再“平彻闲雅”了。章太炎将这个文学变化的时限定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之后,自其子简文帝始,文学真正开始“声色大开”,“平典之风,于兹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论式》)这段话在其之前的《与人论文书》中也曾说过。所谓“平典”,即平正典雅,亦即其所云“平彻闲雅”—平实深彻而造就的典雅。盛唐的“燕许大手笔”已然不逮,中唐时最有代表性的韩、柳等人仅仅“劣能自振”,成就上已自身难保,更不用说晚唐与两宋了。于是,他得出结论:“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论式》)汉文质朴,但持论明白准确,唐宋论文则只能“利其齿牙”,以浮滑之辞炫人耳目而已。只有魏晋论文既能谨守法度,又免于浮滑无实之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必先豫之以学”,须以学问为根柢。论者常引这段话以说明章太炎的文学观,而深会其意则是章氏弟子许寿裳。许氏在一九四五年为其师作传时引而申论曰:“‘必先豫之以学’这句话,最为切要。世人但知道魏、晋崇玄学,尚清谈,而不知道玄学常和礼乐的本原、律令的精义,彼此相扶。玄学者其言虽系抽象,其艺则切于实际,所以是难能可贵。”②许寿裳《章太炎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而批评者虽然承认章氏的学问精湛,却认为不能以此要求他人,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③《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62页。本篇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但行文恐作于1922年。胡适之论有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非得失可另当别论,其实他们俩所说的“必先豫之以学”不是同一个问题。胡适所云是对今人文章创作的问题,许寿裳所说乃是章太炎对古代论体文写作的学术底蕴的要求。于此,我们梳理出章太炎看待唐代文章的逻辑思路是:唐代学术中衰,文士学问疏薄,以此为基础和底蕴的文章不能辨名析理,无法做到舒卷自如,失去了“平彻闲雅”的气度,只能依靠文饰之辞而作浮夸之游谈,从而形成汗漫之文。最有代表性的韩、柳、刘、吕之伦亦复如是。根据“修辞立诚”的原则要求,这是非常恶劣的文风。那么,章太炎何以判断唐人学术之疏呢?这便涉及他对中国学术的认识。
二、唐人学术之疏:六艺之学的中衰
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章太炎虽然并不排斥当时的外来之学,还对进化论之类西学颇感兴趣,但他心目中的“学”自然还是指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他认为,中国学术源于先秦六艺,“汉人所谓六艺,与《周礼·保氏》不同。汉儒以六经为六艺,《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P2)魏晋玄学虽似老庄形名之论,实则是对传统六艺之学的继承,而且恪守名家辨名析理之分。“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忤,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争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原注:唐初犹守六代风,……中唐以降,斯风绝矣。)”(《五朝学》)玄学名士之清谈在六朝时已有批评者,后世的“清谈误国”几为价值判断之定谳,章太炎非常崇尚的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条中亦持此论。但章太炎却为之彻底翻案,认为玄学是六艺之学的继承,前人对玄学没有“务综终始”,没有仔细推究,只有“大雅”者能够“推见至隐”,掘其微旨,发现了玄学乃是涵盖六艺传统中经政技形诸端的深层意义。就玄学之“理”而言,为六经之“大艺”,故“不与艺术文行忤”;就其学之“用”或“术”来说,为“小艺”,故“与礼律相扶”,玄学名士多技艺。玄学名士的辨名析理与“六艺方技”“要之以名,格之以分”完全相符,故其文章析理明晰,逻辑谨严,无须华辞而风华自在,这种内在的修养也使得玄学名士的气质平易不躁竞,故而“和理出其性”。而唐人文章之所以不及之,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及唐,名理荡荡,夸奢复起,形于文辞。”(《五朝学》)唐人不崇玄学,不讲“名理”,无学问为根柢,自然无法做到晋人文章的优游自在,只能以“夸奢”之辞炫人耳目。在《检论·通程》中,章太炎又说:“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①《检论·通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页。版本下同。他认为唐初诸儒尚有六艺方技之一端,故文章中犹存“轻清之气”,中唐时学术更衰,文章亦随之而变,不能以形名之学守之,只能济以华辞了。在《检论·案唐》中,他论证道:“唐初《五经正义》,本诸六代,言虽烦碎,宁拙不巧,足以观典型。其后说经,务为穿凿。啖助、赵匡于《春秋》,施士匄于《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于《礼》,蔡广成于《易》,强蒙于《论语》,皆自名其学,苟异先儒,而于诸子名理甚疏。韩、李之徒,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者。”②《检论·案唐》,《章太炎全集》三,第451页。按:本文所引《案唐》一文皆出于此。从唐代传统学术之衰微说起,颇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路,最后将韩愈、李翱等人的“文章华采”与“未有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联系起来,两者看似并列关系,若结合章氏其他文章及其论唐的一贯思路来看,其实是因果关系。即韩、李之徒之所以“文章华采”,正是由于他们的学术之衰,不能“深达理要,得与微言”。
章氏高足黄侃深受其影响,在《汉唐玄学论》中步趋其说曰:“唐世学术中衰,而玄言尤为稀简。三教并立,实则皆无异观。浮屠之伦,舍昌明自教,掊击他宗外,殆无馀暇。其于和会众说,自立门庭,有所未能。假令舍弃梵言,彰立殊义,弥不敢已。今论唐氏玄学,于此悉从删焉。……王通《中说》,盖有善言,而多夸饰,即其谠论,犹是老生常谈。流波及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温之伦,文章华采郅优,而持论不可检核以形名之学。”③《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卷》,吴方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8~389页。他认为唐代学术中衰,不识名理微言,故哲学上亦无创见,影响及于文章,最有代表性的韩、柳、刘、吕之伦不能如魏晋文章那样谨守形名之义以论理,只能以“华采”自炫,其结果便形成了章太炎常常批评的所谓“汗漫之文”。汗漫者,调和而无主见,貌似折衷,实则皮相,毫无主见,不过人云亦云,左右逢源,四处讨好。此辈之学,既无定见,其为人亦可知矣。故章太炎说:“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意,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④《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5页。故太炎深恶“汗漫”之学,而喜好晚周诸子与魏晋子学。至于唐人,在他看来,学术既疏,又不能辨名析理,自是不能作独立自由之论,因而在文章与行为上只能哗世取宠而已。
无论是传统的六艺之学,还是后来分类的经史之学,古人最为重视的是礼学。刘师培曾撰文《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证曰:“礼训为履,又训为体,故治国之要,莫善于礼。三代以前,政学合一,学即所用,用即所学。而典礼又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故一代之制作,悉该入典礼之中,非徒善为容仪而已。试观成周之时,六艺为周公旧典,政治学术悉为六艺所该,而周礼实为六艺之通名。”⑤《左盦外集》卷十,《刘申叔遗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1543页。后世政学分途,而典章制度、法规律令、礼仪规范乃至学术文化其实都是典礼的一部分。当时学人中持此见者不少。章太炎作为清代学术的“押阵大将”(胡适语),对刘氏此论莫逆于心,故论及古代学术文化时十分重视当时的礼学。而礼学又与社会风俗密切相关,章太炎一贯坚守“学”“人”一致的论证思路,而为人为学又关涉到一个时代的政俗风气,所以强调学术与社会风气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他与刘师培相互影响且相互欣赏的原因。两人定交于一九〇三年,刘氏虽年少于章氏十五岁左右,但学术精湛,深为太炎所重。他们俩桴鼓相应,对于六朝学术的观点大致相同,刘氏虽少,实则许多文章阐发在前,章太炎反而受其影响。如刘氏《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作于一九〇七年,刊于《政艺通报》,文章引征史实,立足于“自立自强”之论,认为六朝名士受益于玄学思潮的熏陶,因崇尚自然而不重名利,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上“宅心高远”,追求超功利之美,而在学术思想上则“学贵自得”,注重个性和独立思考。这与章太炎一九一〇年《五朝学》中替玄学及玄学名士辨诬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对于玄学名士的讲究名节以及为后世“不可及者数事”的五个方面,同样为章太炎所接受,章氏一九〇八年所作的《五朝法律索隐》说:“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①《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章太炎全集》四,第79页。从法律的角度论五朝风俗之美,与刘论异曲同工。他们皆是从社会风俗、学人气节入手,论述学术与文学风尚,因而得到唐代风习之衰的结论。只不过,他们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文论之所及,章氏卑唐,刘氏则稍弘通。风习之衰则是礼教衰微的结果,而文辞的厚薄又是从习俗风尚中来。故章太炎《菿汉微言》曰:“观世盛衰者,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唐世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始自燕、许,终有韩、吕、刘、柳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壮驵,则与两京相依。”(《菿汉三言》,P55)他虽然承认唐代属于盛世,唐文属于“壮美”之畴,但由于礼教之衰微,盛世之中实多巧诈。故其《检论·本兵》曰:“礼教益息,文辩益盛,而怀杀之心衰。其政又一于共主,民有老死不见兵革者。唐虽置府兵,其民固弗任,故有征役悲痛之诗;又设重法,诸临军征讨,而巧诈以避征役,若有校试,以能为不能。”②《章太炎全集》三,第442~443页。既然唐代“真挚之诚逊于两汉,高尚之风又逊于六朝”,世风及于学风,学风自然影响文风,在学术之疏与习俗之衰的前提下,章、刘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文不能说理而只能济以华辞,无法与析理精微而又卷舒自如的魏晋六朝文相比拟。

《太炎文录初编·五朝学》(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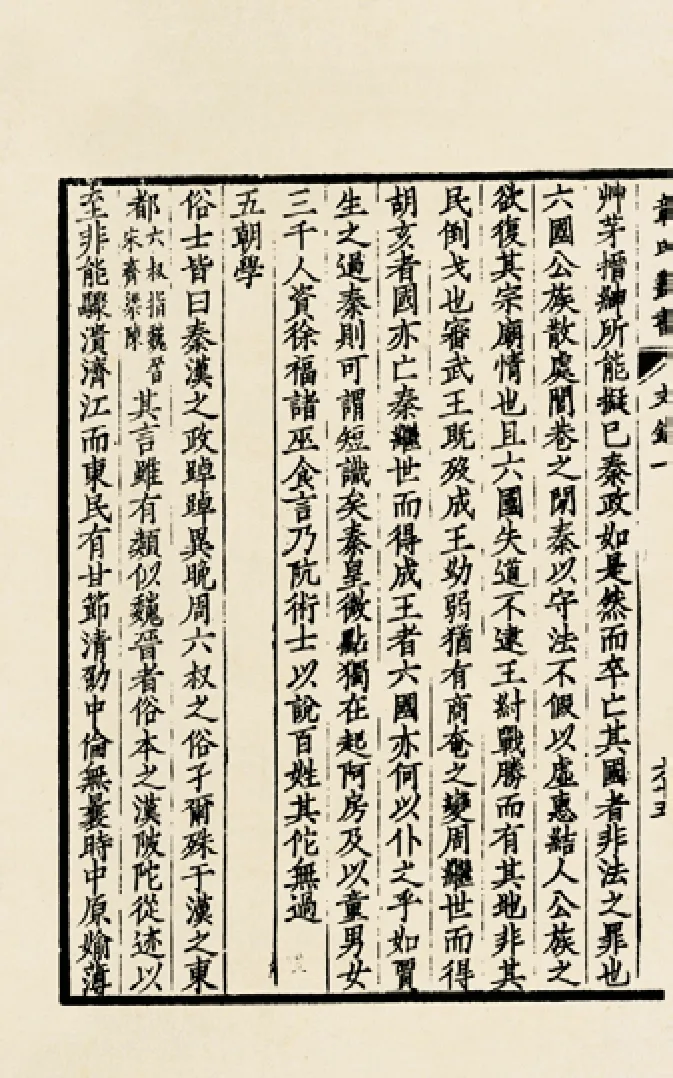

《太炎文录初编·五朝法律索隐》(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以中国古代学术思潮而论,传统的六艺之学和讲究哲理的玄论,唐代自是式微,但隋唐佛学却向为人所称,而章太炎却说:“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没有。数学、礼学,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③《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内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页。而中唐正是以韩愈文章为代表的时期。韩愈不但是中唐文章的代表,也是唐代文章与诗歌以及学术文化的代表者与转型者,对后世文学文化的影响甚大。章太炎虽也一再承认韩的才气与影响,却往往凭借直觉对韩愈进行批评。且无论对韩愈文章与学术,甚至对其为人之气节德行有过怀疑。《菿汉昌言》曰:“韩退之笃于故旧,见人有技,休休乎若己有之,视前世诸文士诚贤。然其戚于贫贱,耽于饮博,去居易俟命能节制者盖远,而便栩栩欲拟孟子,亦不自度甚矣。”(《菿汉三言》,P57)这是从个人志节品行上予以非议。至于从文章风格和“文以载道”的角度来批评韩愈,后来他的学生周作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与其不无关系。
中唐如是,即使是初唐,在章太炎看来,传统的六艺方技之学也已处于若断若续之际。其实,无论是从哲学、佛教以及文章的论理角度而言,唐代与魏晋六朝在社会文化环境上已颇有差异,尤其在影响文士甚大的取士制度上,一持门阀,一以科举,士人的出身不同,取径相异,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章的风格及其各自特长。汤用彤先生曾较而论之曰:“盖魏晋六朝,天下纷崩,学士文人,竞尚清谈,多趋遁世,崇尚释教,不为士人所鄙,而其与僧徒游者,虽不无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谈名理相过从。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大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盖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学士如王维、白居易、梁肃等真正奉佛且深切体佛者,为数盖少。”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页。魏晋六朝名士与名僧相互交游,喜谈名理,当世以此相高,故士人对佛理钻之甚深,发之于文,能析理精微;唐代士人乃以“文词诗章为要事”,不能专心于释氏名理,又以治世为要务,即便如韩愈《原性》之类论理文,不过气盛言宜,实则论理甚浅。这便可解释唐代文士何以对佛理不能精审以及文章在辨名析理上不能与魏晋争胜的原因了。而章太炎的呵唐,正是自其卑唐观出发,还常举出实例以证明唐人的学术之疏,特别是对唐代开国者多有苛求。《菿汉微言》曰:“魏玄成谏诤剴切,至学术则非其所知。所集《群书治要》,有古书十馀种,为今世所无有,故其书因以见重。若在当时,盖不足道。观其截削文句,多令蹇吃难通,至于编次经典,卦取一爻,象存半语,割裂诬谬,令人失意。其《类礼》五十篇,盖亦此之流也。孙炎之书已废,而魏书代之,元行冲为作疏,张说尼焉有以也。唐初名相,虽被服儒雅,实无根柢,观房玄龄所注《管子》,妄陋如此。兹二公者,固非汉初张苍、陆贾之伦学有归趣者比也。”(《菿汉三言》,P69)从表面上看,这种结论是学术性的论证,也有理有据,可成一家之言。但这种学理上的论证实则带着较强的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章太炎的学术文章强调以“求是”为“致用”,在为其现实关怀目的的学术论证中,仍以史实为据,因而这种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立论即使到了民国以后仍然可以自圆其说。他对唐代文章的诸多观点,终其一生,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唐代在时间上已远离清末,为何章太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会影响到他对唐代文章的立论呢?究其实,乃因李唐之习多沿于鲜卑,染于胡俗,类于清人之夷狄,又有闺门失礼与兄弟阋墙之事,在气节与德行方面皆有所亏。在章氏“学”“人”一致的学术思想中,传统的夷夏之辨正好是可以利用与发挥的宣传工具,卑唐实即是呵清。
三、唐人习俗之衰:夷夏之辨的推衍
李唐兴于西北,胡汉杂陈,相互通姻,此为史实。陈寅恪尝论唐代政治制度及其习俗之渊源曰:“《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②《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页。所谓“闺门失礼”,不过指武则天及杨贵妃与唐帝室之复杂关系,朱子将其归于“唐源流出于夷狄”,但后世应者寥寥。陈寅恪从“中国文化本位论”出发,论此主要是从客观立场出发,甚至带有褒扬之意,故陈氏对唐代文学文化及韩愈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颇为推崇。其《论韩愈》一文固然如是,即便是章太炎颇为轻蔑的唐代小说,陈寅恪亦著《韩愈与唐代小说》予以表彰,并许其对唐代文章的贡献,对韩愈《毛颖传》之类“似小说”的文章给予正面评价。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章太炎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不止一次批评韩愈此类文章,并曾将“唐人小说”作为贬词来评价林纾的古文。章、陈其实皆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同一问题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可见章氏之说乃由其卑唐观的习惯思维所致。也因此而可明了,他何以把唐室的“闺门失礼”当作德行有亏和风俗之衰的证据,且对唐太宗及其开国大臣多有呵斥。
唐太宗号为一代明君,文治武功历来为世所称。但章太炎对于他的诛兄杀弟而登帝位,颇有微词,在《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说到“:唐太宗之事,新、旧《唐书》之外,有温大雅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在。温书称建成为大郎,太宗为二郎。据所载二人功业相等,不若新、旧《唐书》归功于太宗一人也。”(P161)他认为两唐书之类正史的所据资料都曾经过了唐太宗的过目检视,所以只留下了对其有利的记载,“史载太宗命房玄龄监修国史,帝索观实录,房玄龄以与许敬宗等同作之高祖、太宗实录呈览,太宗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隐讳,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观此,则唐初二朝实录,经太宗索观之后,不啻太宗自定之史实矣。开国之事,尚有温大雅《起居注》可以考信,其后则无异可考,温公(司马光)亦何能再为考校哉!”(同上,P163)章太炎一向推崇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但他认为由于很多资料已被唐太宗作了选择性的处理,所以司马光也无法考校唐太宗兄弟争位时的血腥细节了。其实,对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太宗兄弟争位之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说过:“俱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七《史部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章氏之评不知是否从此而来,但却因此而责太宗之“不义”以及房玄龄、杜如晦等佐命大臣之气节有亏。《菿汉昌言》曰:“汉楚王英谋逆,明帝徙英丹杨,未尝罪其妻子。唯楚狱连及者广,袁安则以死自任,为理出之。唐太宗杀太子、齐王,亦可已矣,而又诛其十子,房、杜于此无一言。岂非明帝之举以义,故不患楚嗣之报复;太宗之举以不义,故深患二嗣之报复乎?玄龄欲子孙师汉袁氏,未思己之得比袁安否也?”(《菿汉三言》,P142)当然,在他心目中,由于“唐室闺门失礼,其时诗人亦多荡佚”(《菿汉三言》,P146)虽然他也承认“唐士”如刘知几、杜佑、陆贽等人的质信与文章,表彰过元德秀、颜真卿等人的德行,但总体而言,正是由于满清王朝的出于外族,使得章太炎论学时常常将民族主义思想与情绪融入其中。这一点,学界论之已多。同时,作为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章太炎在论述唐代文学文化时将唐人染于胡俗的史实放大了,从而影响了他对学术问题的客观判断。《菿汉微言》有曰:“唐承周隋之绪,戕杀萧铣,泯毒汉宗,斯胡戎之嗣子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南史》书北主则曰崩,《北史》书南主则曰殂。王通《中说》殆亦唐人所拟,其言‘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弃亲昵而媚豺狼,悖逆至此,讫于宋初,鸮音未改,《御览·帝王部》揭举魏周,而江左则入僭伪焉。唐时独有一皇甫湜能正南朝江陵既陷,始归周统,可谓鸡鸣知旦者矣。”(《菿汉三言》,P57)称唐室为“胡戎之嗣子”,自是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主观情绪,亦因此而不满唐修史书中对南北正统地位的记载以及称呼的错位。上引文中对王通及其《中说》的强烈批评,终其一生皆未改变,在言辞激烈的《讨满洲檄》中亦云:“奸人王通复以《元经》张虏,乃云‘黎民怀戎,三才不舍。’由是言之,非虏之能盗我中华,顾华人之耽于媚虏也。”②《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90页。目王通为“奸人”,因王通以《元经》为“索虏”争正统,也就为唐之登帝位提供了历史与理论的依据。而他对唐太宗及其佐命功臣如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批评亦正与王通其人其书密切相关。
王通,号称隋末大儒,但《隋书》无传,《旧唐书·王勃传》载曰:“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③《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4~5005页。此人虽不及唐,但传说唐代诸多名臣皆为其门人,又俨然以孔子自比。不过,他的事迹及《中说》、《元经》的著作权一直颇有争议。《元经》今存十卷,前九卷旧题王通撰,末一卷题其门人薛收续,但宋人已疑其伪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然,并谓其无所取。但伪托者为谁,伪托的动机何在,则见仁见智。章太炎认为伪撰《中说》及《元经》的始作俑者皆为王通之孙王勃。《全唐文》卷一三五今存杜淹《文中子世家》,谓文中子“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云云,王勃《续书序》、杨炯《王勃集序》、皮日休《文中子碑》皆有类似之言,而章太炎认为《文中子世家》之类文章其实也是王勃伪造的,虽然他也认同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文学才华,但在事关诚实与作伪这样的名节与德行上,他认定王勃是有亏的。且不论《中说》中的前后抵牾,《元经》仿《春秋》体例,以史书形式颂“戎狄之德”,也就为唐之正统地位作了理论与史料上的证明。如此为“索虏”张目,清廷恰恰又是章氏认作“乌桓遗裔”的“索虏”之一,这自然是他无法容忍的。作为一个理论家与宣传家,他需要且必须在学术上予以批驳。可以说,他对王通的所谓“拟经”,自始至终都表示厌恶。当他读到王阳明《传习录》上表彰文中子的“拟经”以“明道”时,他加以批语曰:“诸语纯是乱道。”①《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325页。按:章太炎所读《王文成公全书》,现藏暨南大学图书馆,该语即题其上。而集中加以批驳的体现在其《检论》卷四《案唐》一文中。由于文中子其人事迹不详,章太炎认为其著作均为王勃伪造,故此文以对王勃的批判为主要线索,集中地对唐代学风与文章乃至整个风习作了比较彻底的负面评价。
《案唐》开头先称赞了隋唐以科举取士的进步意义,但马上话风一转:“及乎风俗淫泆,耻尚失所,学者狃为夸肆,而忘礼让,言谈高于贾、晁,比其制行,不逮楼护、陈遵。章炳麟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也。”(P450)他认为唐代“风俗淫泆”,学者好为夸诞而不实诚,而王勃是始作俑者,并且给整个唐代风习及文章均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王勃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章氏曰:“由今验之,《中说》与《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谰诬也。夫其淫为文辞,过自高贤,而又没于势利,妄援隋唐群贵,以自光宠。”(《案唐》P451)他认为王勃伪造的动机出于“势利”,欲借重其祖王通的身价,攀援“隋唐群贵”。由于王勃为“初唐四杰”之首,其夸肆而不诚实的学风与行为给唐代学风和文章之士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故论曰:
终唐之世,文士如韩愈、吕温、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皇甫湜之伦,皆勃之徒也。其辞章觭耦不与焉,犹言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复之。不悟魏晋老庄形名之学,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沐浴礼化,进退不越,政事堕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固不以玄言废也。加其说经守师,不敢专恣,下逮梁陈,义疏烦猥,而皆笃守旧常,无叛法故。何者?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苟诬也。扬搉其人,色厉而内荏,内冒没而外言仁义,夫非勃《中说》之流欤?且夫《中说》所称“记注兴而史道诬”,其言鉴燧也。而勃更僣其言,矫称诬辞,增其先德。唐世学士慕之,以为后世可绐,公取宠赂,盛为碑铭;穷极虚誉,以诬来史。此又勃之化也。魏、晋虽衰,中间如裴松之禁断立碑,法制所延,江表莫敢私违其式。此何可得于唐世耶?……勃之言文,取陆机而已。……夫不务质诚,而徒彰其气泽,虽《尧典》、《商颂》,犹为浮华也。勃之言,虽中取陆机,己又离于陆机逾远。要其憙自矜大,转益恢郭,不效法苏绰不止。(《案唐》P451~452)

《检论·案唐》(广陵古籍刊印社本)
他论学衡文,恪守“修辞立诚”之古训,既然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韩、吕、柳、刘之伦“皆勃之徒”,在道德品行上已有不实诚之亏缺,自然也就不必论其“辞章觭耦”了。与魏晋的学术相比,魏晋的“不敢专恣”而“笃守旧常”自是实诚而不浮华,且“覃思自得”,而唐代的“夸肆而忘礼让”当然是浮华了。从文章到学术风气,乃至社会风习,其不诚之心皆由“王勃之化”。其中所谓“盛为碑铭,穷极虚誉”云云,虽未点名,实是暗讥韩愈等人。“绐”者,欺骗也。“以为后世可绐”,即指唐人碑铭之欺世不诚。这与魏晋的“禁断立碑”相比,非仅关乎文章,更是人之德行与社会风习问题。而王勃之文,虽曰学习陆机,但由于先存“不务质诚”之心,气貌上已然不逮。更何况,陆机是章太炎最为看重的魏晋文的典范作家,王勃若此之行,其人其文,较之于陆,判若云泥。文章最后,“章炳麟曰:若夫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隋唐之间,其惟《颜氏家训》也。”引用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之言,始终强调人之道德文章的一致性,甚至因颜之推《颜氏家训》而褒美其唐代后裔颜师古与颜真卿。又联系其当代情形,暗讥康有为等人,将“不质诚”之风称为“此复返循王勃《中说》之涂”。论者或评述此文曰:“结尾又论述从文章上看,韩、柳古文运动与王勃的骈俪似乎是不同的,但是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实际也是一致的。也都证明了太炎述学文章结构是严谨的,而逻辑性也是很强的。”①任访秋《章太炎文学简论》,《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04页。实际上,这有“为尊者讳”之嫌。我们认为,章太炎论学文章确有较强的逻辑性,但此文以批判王勃为主线,虽然前后呼应,结论却过于武断。王勃虽才华横溢,但卒时不足三十,其影响至多只是处在六朝与唐代文学之间的一个承接点,对后来的唐代文章与学风的影响并无如此之大,更谈不上对整个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况且,王通其人其书,是否为王勃伪撰,实际上是有争议的。章太炎断为王勃伪撰,实际上也是揣测之辞,并没有坚强的事实佐证。退一步说,即使《中说》、《元经》等皆为王勃伪造,就其动机而言,固然是不实诚的,但其影响也绝无如此巨大。所以,《案唐》一文虽前后呼应,但往往以假设为立论前提,不能说“逻辑性也是很强的”。如果说,此文名为“案唐”,毋宁说是“案清”,其最后一段将其当下的现实关怀与王勃联系在一起,说:“然夫文质相变,有时而更。当清之世,学苦其质,不苦其文矣!末流矫以驰说,操行更污,乃更以后圣涣号。此复返循王勃《中说》之涂。”可见其着眼点乃在于对“当清之世”学风的批判。其实,清人末流的“操行更污”已与王勃《中说》毫不相关了,章太炎只是抓住“不质诚”一点将两者联系起来,与其说是学术论证,不如说是对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推洐了。这一点,其实周予同先生早就明白地说过:“清朝末年章炳麟‘继承’了顾炎武的‘经世’内容,发挥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同一学派,而‘继承’关系却自不相同。”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原载《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今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页。换句话说,章太炎以“求是”为“致用”,当时过境迁,“致用”目的已达或已过时,“求是”的内容仍以学术的方式存在,却未必过时。况且,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从文化角度来说的,并非完全着眼于种族。尽管他因痛恨清室而将满族归之于“野蛮民族”之列,实则是针对满清的统治者而言。一九○七年,他在《答铁铮》中就说过:“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③《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371页。也正是从“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的文化角度出发,其所论学往往立足于史实,即使在情绪上带有主观意愿,角度上有所偏颇,却可以自成一家之言。这也是《案唐》一文及其卑唐观念下的相关文章可自圆其说以及为人所尚的背景与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章太炎对唐代文章、尤其是中唐以后的文章基本上持以批评的态度,既有其文学观念上的原因,也受其现实关怀目的的影响。就前者而言,他重视论理文,有着较强的“魏晋情结”,并以此而卑视唐文;同时,他持“杂文学”观,本身又学问精湛,故重视文章的学术底蕴。而唐代学术,在他看来乃属浅疏,故唐文无学术根柢而只能饰以华辞。就后者来说,他论学衡文时需关怀现实,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满清的出于外族,而将唐室染于胡俗的史实放大了。他又强调道德与文章的一致性,关注社会风习的变迁对于文章的熏染,由有争议的王通其人其书说起,判断王勃伪托之“不质诚”对唐代学风及社会风习的不良影响,实则是对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推洐。因此,唐代文学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章太炎以学术论证的方式给予较强的批评,我们以其论述较多的唐代文章为例,说明其观点或可自圆其说,在学术史上自有其意义,而对于具体问题时可具体分析,了解其立论的历史语境。这样,方可理解他对唐代文章的批评态度,也可对其学术观点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约稿 谷卿 责编 周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