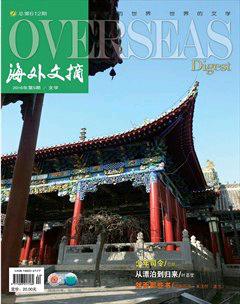高树多悲风
孟伟哉去世了。
孟伟哉去世一年了。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瞻望孟伟哉生前身后事,我想起曹植的如此诗句,想起与他交往的过去种种。
那么,值此肃穆缅怀的时刻,我且斗胆拾笔,钩沉往昔,衍生成文,权作恭奠这位文学前辈的祭酒,也期望据此让人们感知一个和传说中略微有别的孟伟哉。
我是从其画作认识其人的。
2002年秋,中国作协为迎接中共十六大召开,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作家诗书画选》,一直关注作家文人书画的我得知消息,托人专门从中国作协购回一本作品集,就是从这本差不多囊括当代作家书画的集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孟伟哉的画作。一幅题为《金秋一曲》的荷花,一幅画的是“千里快哉风”的雄鹰,笔墨浑厚,高张一股苍朴之气,由此我便萌生了收藏其书画的念想。两年后,我去北京再次拜望贺敬之先生,顺便向他要了孟伟哉电话,当晚即与他联系,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踏入他位于方庄芳古园一幢普通居民楼十二层的家。第一感觉就是房间几无亮色,逼仄的客厅里,两张过时的桌子摆放着一些生活用具和书籍,一个陈旧的双人沙发用来招待客人,连地面也是未加修饰的水泥地,简陋得近于寒酸。不敢想象,这就是那个先后担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新闻出版总署专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曾在文坛举足轻重且发表数百万字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孟伟哉的“府邸”。更令人叹惋的是,年过七十的他,孤身一人生活,连个保姆也没有,洗衣做饭全靠自己。可以说,他是我在京走访过的作家中,晚景较差的一个。从他的话语中,也可看出其心境的不适。在闻听我自报家门来自安徽工人日报社后,他马上说开了那位从安徽走出的文坛名人和他的一段恩怨,言谈中不乏愤懑之词。当说到是贺敬之告之我其电话号码时,他又直言不讳地忆起两人过去在工作中产生的误会,不过,这种误会随着他应邀参加不久前举行的贺敬之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得到消弭。“这是因为海外法轮功网站造谣说孟伟哉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闹了一场风波。我则于2014年12月9日委托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授权新华网刊发声明,以正视听。你想,我于1953年4月在朝鲜战场火线入党,我的父亲孟守义是一位革命烈士,我6岁时,身为山西抗日救国决死队排长的父亲惨遭敌人杀害,是共产党培训我参军入伍、上大学,走上革命道路,至今我身上还有美军投下的弹片,我怎能叛党!但是敌对势力十分阴险,在新华网刊出声明后,又发帖说新华网声明是伪造的。这时恰好贺敬之从艺六十年研讨会召开,有关部门希望我去亮个相,也算是辟谣吧,这样我就参加了研讨会,在会上,我回忆起当年在部队文工队时,演过大春的一段往事。”老人说到这里,似有所思,沙哑的嗓子更显低沉:“为什么法轮功会造谣说我退党,这反而也可能说明我目前处境不佳、或者说比较困顿,拿我挑事人们容易轻信吧!我现在生活也确实不尽如人意,一个儿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的工资连个保姆也不敢请……”
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初次见面就不设防地吐露心扉,这固然因为其生活比较落寞,但依我看,主要还是性格使然。
一个开口见胆、不隐一点心曲的老人。
这让我陡生敬慕之情。在得悉他的老部队即是与我当年服役的部队一路之隔的180师时,不由又多了几分亲切。拿着他赠送的小说散文集《逃兵·表姐·蹦蹦跳》离开京城后,我很快写了一篇5000字的散文《孟伟哉的两支笔》:“孟伟哉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昨天的战争》,一支笔绘现代的画儿……”“如枪之笔砥砺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确实非同凡响。宏大的场景,宽广的视角,深入的吟述,凝重的笔触,刚烈的质地,炽热的情怀,构成这部反映抗美援朝作品的全景诗品格。”对他的另一支笔,则作如下描述:“这支笔,柔软且轻盈,飘逸且新奇。徐徐地、冉冉地,左勾右染、上濡下泅。清清墨荷,晶晶冰花,透溢着现代气息,和传统和《昨天的战争》拉开距离———名曰《我的画》……”文章在《志苑》杂志发表后,收到较好反响。而在台湾《世界论坛报》的刊载,让他不可思议。“台湾的报纸能登这样的文章?”他念叨着,不解,又感到欣喜。自此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我每每去京,都要抽空前去看他。我们相谈甚欢。他为我忆说文场掌故,我向他介绍画坛新闻,并常在一起共进午餐。承蒙他不弃,多次赐我墨宝,或是清旷简逸的荷花,或是涩重沉郁的牦牛,让我收获颇丰。一天下午,我又赶过去与他促膝长谈,到了晚上,他邀我一起参加一场聚会。在芳古园附近一家酒店,见识了他的几位好友: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文艺评论家丁振海,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马威,原华艺出版社副社长王文祥,台海出版社社长安然。年近八旬的原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待大家坐定,送给每人一幅一尺见方的篆体福字,给大家一份新春小礼。经过交谈,我知道除谢云先生外,他们都是来往密切的南开大学校友,如此自是无话不谈。不知不觉,话题由我在《世界论坛报》刊发的那篇文章谈到台湾,此时,孟伟哉郑重其事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台湾人均‘国民收入有30万台币,合人民币6万多,没有革命的基础。”丁振海接腔应道:“像老孟这样知名的原教旨布尔什维克……”戏谑的口气引来大家哈哈一笑。晚宴结束合影后,大家一一道别,孟老坚持要送我到公交站台,记得走过一段拐弯黑暗处时,他怕我有闪失,经常头晕犯病的他竟然用手拉着我的胳膊走了一段路,如今回想起来,心头不免发热。
接下来,还有不少事情堪可言说。
譬如2006年6月,我和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丁颍合作创办美术刊物《华人画事》,样刊出版后,我给他送去,请他帮忙组稿,他没有迟疑,立即给著名画家赵土英、刘晨阳打去电话……
譬如2009年7月,他在798桥艺术中心举办画展,将《华人画事》列为支援单位,我专程去京参加了开幕式,之后在《华人画事》杂志上对画展做了宣传报道。譬如2010年2月,《华人画事》推介画家精品展在北京琉璃厂举行,他不仅作为嘉宾和高莽、鲁光先生为开幕式剪彩,还主动打电话给央视书画频道,请他们派记者前来采访。
譬如2012年3月,由他担任会长的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召开会员代表会议,他推荐我为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在会上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华人画事》杂志。
譬如我的又一本报告文学集《人字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请他为该书作序,他欣然应允。在序言中,他带着感情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群就是个歌者,作为报社记者、作为青年作家、作为刊物总编,他在不倦地为我们多彩的艺术和美好的生活做着歌唱……”
对年轻后生的鼓励溢于笔瑞,但把我比喻为歌者,着实让我汗颜。他才是一位真正的歌者呀!
只是,他这个歌者在这个苍黄翻复、时变俗易的社会有些不相适宜。耿直,固执,愤世嫉俗,书生意气,坚守自己的本真,不随世风而舞,不随潮流而歌,依然咏唱着过去的乐曲,让他落入“荷戟独彷徨”境地。不然,以他的名望和丹青功夫,稍微炒作包装一下,似会像一些爆红的所谓名家一样,大行其道,赚得盆满钵盈,闹个“文人画大师”称誉也未可知。
然而观实就是如此“嶙峋”,他孟伟哉只有远离繁华,在孤独中带着战争中落下的伤残,兀自老去。
“那是一个完整的场景———冰雪茫茫,一大群牦牛在觅食寒风中裸露的枯草,而在一个凸起的巨大岩石上,在岩石上厚厚的雪层里,却有一头牦牛,好像这一群牦牛的将军和统帅,高扬着头,镇静雄立,凝望远山,又好像在顾盼他的群落……”
其《无耳,翘尾———我的牦牛》一文描绘的此景,是他自己处境的写照乎?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4年秋,刚从医院出院的他,在我带去的一本册页上,用他那峭拔的行楷书写了两首毛主席诗词。言及筹备几年的十卷本《孟伟哉文集》即将出版,我提出届时购买十套送人,以聊表心意,他高兴地答应了。从北京返回安徽后,我念及此事两次打电话给他,均被告之还未印好。“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除”,2015年春节倏忽而至,大年初二,我按惯例给他拜年,家中电话无人接听,打手机也未通,就很纳闷,是回故乡洪洞?还是出去旅游了?直至在3月4日的《文艺报》上看到孟伟哉于2015年2月28日去世的讣告,我的心,忽地一沉。
惊诧、悲伤,几个月前还为我挥毫落墨,怎么就突然去了呢?
谈好的由他在那十套文集上为朋友一一签名的设想,变成梦幻一场,这是我哀痛之余的遗憾、懊丧。
这种情愫没有随着时间的嬗变而递减,而是渐渐在我心中凝成一个结。
应该提笔再为他写点文字,将心中他的形象大致勾勒下来。这是怎样的形象呢?
似乎是一头牦牛。对,是他在青海工作时痴爱并常放笔讴歌的牦牛:坚韧、执着、赤诚,从遥远的雪山走来,在温暖的田野上形单影只,彳亍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