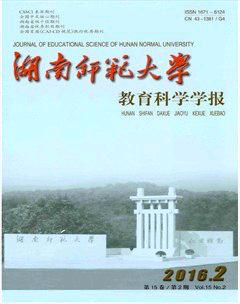教育工程师的现实存在方式
摘 要:教育工程师目前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称谓,但行教育工程师之实的人员是客观存在的,这说明教育工程师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在未来,当被称为教育工程师的专门人员出现以后,不过是集中行使了被分散的职能。现实地看,的确存在着各种人员,他们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进行着有意义的连接工作,共同的特征是把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转化。我们所说的“教育工程师的现实存在方式”主要指具有一定特征的现场教育者、创造并实践自己理论的教育学家和在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教育应用开发的专门、专业人员。
关键词:教育工程师;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工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2-0005-06
“教育工程师”这一称谓在W.W.Charters1945年的著述中已经出现了,至今整整70年,但他之后人们对于教育工程师就少有理论的关注,以致对教育工程师进行理论的把握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最初使用“教育工程师”概念的时候,就有朋友怀疑地发问:教育工程师在哪里?谁是教育工程师呢?要知道这样的问题是最让人头疼的。假如人们普遍对新的思维充满怀疑而非欢迎的态度,可以说人文社会领域的任何创新都不如用一句轻轻的发问更有力度。人文社会中虽然充满着先有观念后有事实的现象,但人们似乎更容易适应和接受先有事实后有观念的逻辑。当然,就源头来说,观念总是在事实之后的,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种综合性的观念完全可以是在已有单个观念的基础上结构而成,从而新的综合观念与事实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这种新的综合观念如果要与事实形成直接的联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根据新的综合观念制造出新的事实。由此来看,人们对于“教育工程师”概念的怀疑,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感觉世界中找不到教育工程师,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教育工程师”之名与实还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连接,因而也就没有“教育工程师”这一概念。
为了消除人们的怀疑,笔者想说明自己关于“教育工程师”概念形成的情形,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于教育学学科构成的思考,提出“教育工程师”之名。笔者把教育学学科分为哲(教育哲学)、理(教育科学)、工(教育工学)和艺(教育技艺)四个层次,与每一个层次相对应的创造主体分别是教育哲学家、教育科学家、教育工程师、教育艺术家,“教育工程师”即在其中。在这一阶段,“教育工程师”只是一个无实之名。
第二阶段,基于教育工学功能的思考,对“教育工程师”进行功能性界定。2007年对“教育工程师”有如下论述:
基于教育工学的基本原理,教育工程师首先要对教育基本理论进行操作性解读,以帮助实践工作者顺利接受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理论提供的概念、原理和理念。其次要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应用性的开发。这种应用性的开发,包括教育模式的设计、教育方法的构思以及教育技术的发明,归结起来,主要是进行教育操作思路及辅助性技术的构想和设计。再次要对自己所做的应用开发进行操作建议。这种操作建议一般分为两个层次,即操作原则和操作规则。操作原则具有思想性的建议,意在保证实践应用不远离蕴含在具体教育模式、方法之中的精神性的内涵;操作规则具有技术性的建议,意在保证教育实践者对教育模式、方法的应用是正确的和恰当的。最后要对教育实践中的优秀经验进行初步加工和处理,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提供“理论原型” [1 ]。
第三阶段,笔者发现对“教育工程师”功能性界定的内容在教育实践领域已经存在,只是既有的存在要么是非系统的,要么是在旧观念统摄之下的。比如,对教育理论的操作性解读在一些高水平的教育培训中可能存在;在教育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应用性开发,在每一所学校都可能存在;对某种应用开发进行操作建议,既可能存在于学校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于专业人员对学校教师的指导中。然而,能够完整承担以上各项任务情形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应该说,与“教育工程师”之名相关的既有事实,使得这个名远离了虚妄,这就为我们建立“教育工程师”之名与未来完美之实的连接奠定了认识和实践基础。
第四阶段,在已有教育工学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把教育工程师界定为:借助教育理论改善教育实践的人。这样的界定表面看来过于简单,但并不粗放。这是因为此界定在教育领域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同时也保持了传统对工程师的基本认识。如国外词典中把工程师解释为“工程师是运用科学知识识别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或说“每一件工程产品都需要设计、制作,工程师就是从事这一工作的” [2 ],与我们对“教育工程师”的界定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根据我们的界定,教育工程师在现实中可以有两种存在方式:其一是在教育现场的教育者自身。由于他们完全可以实际上也已经运用教育知识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而且为了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和人格素质对教育活动进行设计并实施自己的设计,他们实际上就成为教育工程师。就此来看,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既具有修辞色彩,也具有实际意义。其二是不在教育现场的又心系教育现场、试图运用教育理论改善教育实践的人。这样的人既可以是创造教育理论的教育学家,也可以是处在教育学家和现场教育者之间的专业人员。
依据上述概念,教育工程师现实存在方式即是具有一定特征的现场教育者、创造并实践自己理论的教育学家和在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教育应用开发的专门、专业人员。
一、作为教育工程师的现场教育者
教育的现场可以是社会生活的一切场所,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有来自家庭的,有来自社会公共生活的,当然也有来自学校的。由于社会分工,教育虽然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场所,但当人们提起教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学校。社会分工带来了教育的职业化,教育职业的发展又把教育带向专业化,以致存在于学校之外的教育不仅越来越具有非正式属性,而且也越来越失去了权威。学校功能的趋强使得家庭的教育功能趋于孱弱,也使得社会公共生活与学校里的学生很难相遇,系统、深刻而持久的教育只能发生在学校这一教育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什么人比学校教育者在教育的事情上更有责任和更有策略。责任是社会分工对他们的要求,策略是他们为了很好地履行职业责任对教育活动进行谋划的结果。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教育对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成人来说只是偶尔为之的,对学校教育者来说却是唯一的事情,他们是教育的职业甚至专业人员。既然是职业的和专业的人员,学校教育者和其他任何职业和专业的人员一样,要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进行谋划,这就为他们运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埋下了伏笔。endprint
不过,运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可能发生的。在没有教育理论的历史阶段,学校教育者的行为依据基本上是社会文化系统的期望和教育行业的传统,他们会有种种明确的教育目的和目标,但不会在教育的策略上花费过多的心思。为了实现目的和目标,他们更多的情况下是顺从自己的心性自然、恪守行业的传统规范。即使教育理论历史性地出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实践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行业的传统和个人的心性。笔者以为教育理论被教育者自觉地运用,主要是教育者自己追求教育完美和教育生活民主化的结果。教育理论的创造者通常就是教育者,强烈的实践取向决定了他们的创造动机基本上是为了教育的完美。教育理论创造者之中的许多人往往会用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当实践卓有成效时,也会有其他的教育者慕名追随。所以,如果没有追求教育完美的动机,恐怕就不会有以指导实践为目的的教育理论创造。然而,教育生活的民主化应是学校教育者运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更大的推动力。原因是在民主的教育生活中教育者的角色权威难以持续,服务于学生学习的职业定位要求教育者不能仅仅顺着自己的心性和传统规范运行教育活动,而是要以学生为本、基于学生,从而,讲究教育的策略既不可能敷衍,也不可能仅仅体现自己对教育完美的追求,而是为了学生的利益必须考虑的事情。
学校的教师一定想不到自己会承担教育工程师的角色,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缺少或不习惯具有工程的意识,但事实是在完美追求或教育民主化的背景下,他们的确需要顺应性地接受有关教育精细化的要求。尤其是在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当代中国,学校教师怎么可能无视和回避设计、模式等充满着工程色彩的概念?当一个教师为了他的教学、训育进行构思、设计时,他就是一位教育设计工程师,继而,当一个教师依循自己的设计进行他的教学、训育时,他就是一位制造工程师。在此需要赘言,不能把工程简单等同于机械、呆板的技术性事件,工程虽然原发于物质制造的领域,但工程的思维是可以迁移到非物质制造领域的。再者,技术作为工具性存在可以服务于任何活动,心理上无原则地拒绝技术恰恰是远离理性的。
随着学校教师在观念和操作上习惯了工程性的思维,他们的职业工作内涵会更加丰富和深刻。到那时,教师就是存在于教育现场的教育工程师,而不是在自己的职业劳动中偶有教育工程师的片段行为。笔者猜想更多的人更愿意赋予教育活动以诗意的和人文的内涵,实际上教师具有了工程思维并不会破坏教育的诗意与人文,相反的,工程思维的务实特性和效率理想会让教育的诗意与人文不只是一种虚无缥渺的意念。实际上,即便是饱含诗意的诗歌,其创作的过程也是既依于诗人纯粹、浪漫的心灵,也不排斥一定程度的技法,否则文学写作的训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显而易见,我们期望学校教师成为运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工程师,如果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期望他们成为拥有教育精神和情怀的教育工程师。做这样的补充是因为在教育精神和情怀不充分的前提下,工程的表象容易把教师塑造成精致的教育技术主义者。须知,即便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物质工程领域,人们对工程师的形象也有了新的建构。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工程师,“论个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在西方工程师之下,……但是工程师作为一个群体整体性道德理性几乎不存在” [2 ],进而对工程师的文化形象和社会角色也有了新的认知,主张工程师应该发展出像医生和律师那样的专业文化来,并认为“描述工程师的词语将越来越多地包括利他、善行、同情、博爱、仁慈等” [2 ]。不难发现,传统的工程领域正在接受人文的洗礼,那么我们的教育以及教育者是否应该接受工程思维的启示,以完成人文与技术的辩证呢?
二、实践自己教育理论的教育学家
今天的教育学家完全可能也完全可以脱离教育的现场,但总有一部分教育学家不仅进行着教育理论的创造,而且会以教育工程师的姿态把自己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实现。至于过去的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教育学家,他们大多是自己理论最忠实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在推行自己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一定范围的教育实践因接受了理论的指导而改善,最初投入实践的理论也因实践的检验而更为完善。
夸美纽斯(1592-1670)这位17世纪的捷克教育学家,他写了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在其中表达了他的泛智论思想,即把一切知识传授给一切人。他说:“我们希望有一种智慧的学校,即泛智学校,也就是泛智工场。在那里,人人可以受教育,在那里可以学当前和将来生活上所需的一切学科,并且学得十分完善。” [3 ]他不仅提出了泛智论的理论,而且亲自制定了实施的计划,其著作《泛智学校》就是以泛智论为依据为他在匈牙利建立的实验学校所拟定的实施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完全的实施,但已经足以证明夸美纽斯属于实践自己教育理论的教育学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只是有这样一次行动,同样在匈牙利期间,他还撰写了儿童启蒙教材《世界图解》,贯彻了自己主张的直观教学原则。
裴斯泰洛齐(1746-1827)这位孤儿慈父、瑞士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同样既是一位理论家和思想家,又是一位亲身实践自己教育理论、思想的行动者。作为一位强调情感和爱的教育价值的教育家,他不只是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情感教育、爱的教育的思想,还用生命活动身体力行了爱的教育实践。1774年,他自己仍处于穷困状态,仍然在新村成立了贫民学校,收留一些流浪儿和小乞丐;1798年,他谢绝高官厚禄,毅然接受了政府的委托,负责斯坦兹城的孤儿院,苦行僧似地对战争留下的80名孤儿实施了难以复制的爱的教育。裴斯泰洛齐还是“教育心理学化”理论的提出者,同时也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性探索。他所进行的“要素教学法”实验就是解决教育心理学化的一项重要探索。他用自己的实践践行了自己的理论,也用自己的实践检验了自己的理论。在谈到自己在斯坦兹的教育实践时,裴斯泰洛齐说:“我感到我的试验已经证明民众教育可以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 [4 ]
约翰·杜威(1859-1952)是时间上离我们较近的一位教育大家。他是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也是在教育中推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杜威的教育著述颇丰,其核心思想常常被归结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从做中学。而他于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实验学校则是他的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这所学校最初叫“大学初等学校”,1902年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杜威学校”。有研究者专门关注了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实践,并认为杜威实验学校的第一特点就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5 ],而这个理论基础正是杜威自己的教育理论。endprint
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位教育学家进行叙述,旨在说明“实践自己教育理论的教育学家”这一事实的存在,在笔者看来,这种看似轻易的叙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其意义主要在于又一次提醒我们教育理论的创造者虽不必须实践自己的理论,但如果他们在理论思维之外还具有工程思维的兴趣和能力,便能够在教育理论创造之外制造出自己理论最可靠的实践版本。在评论叶澜教授领导的新基础教育研究时,笔者讲过,教育学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创造来改造实践者的观念系统和实践活动,进而经由学校生存方式的改善,最终和实践者共同创造出能够培养出新人的新学校,进而认为“借助实际的体验与思考教育理论,同时,与实践者一道创造新的教育” [6 ]是教育学者实现自身核心价值的最佳路径。概而言之,实际上是表达了自己对教育学家兼做教育家的期望。
这种期望可能会过于理想,毕竟,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相异,擅长于理论的教育学家只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已经可贵,分工的趋势更利于个人工作的专门化,在今天莫说要求,即使是期望都是一种过分。可是,和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杜威这样的教育学家做同样的事情也的确不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处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育学家的确很少也很难有机会亲自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那我们就退一步,是否可以建议教育学家们逐渐形成对与理论思维具有同等价值的工程思维的兴趣?教育的生命感注定了任何类型的教育学家都无法轻视实践的价值,都不会公开否定为教育实践服务的立场。如果教育学家面对教育实践不想做一个好龙的叶公,那么,虚心学习工程思维,为自己所创造的教育理论的价值实现做一做工程师的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还是要明确一点,即教育学家也可以只专注于理论和思想的创造,越来越专门和专业化的教育学研究,使研究人员在学科内部还得各司其职,让他们既做理论家又做工程师的确是一种奢谈。也许正因此,教育工程师才有了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即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者。
三、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者
这是一种工作不在教育现场却时常造访教育现场的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构想出可以投入操作的教育技法、方法、模式等;二是传播、推广自己的成果。如果离开教育系统,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并不陌生,在传统工程领域表现为工程人员基于科学理论进行应用开发、发明创造,然后申报专利继而推销成果,然而,在教育领域,这样的专门人员好像是不存在的。教育领域同样需要这样的应用开发者,应是教育的技法、方法、模式等应用开发成果没有经济的价值,所以才难以激活人们在这一领域投入情感和智慧的兴趣。而且悲观地估计,这种现象还将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希望,原因是教育技术学有技术开发向工程开发的转向,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成为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的典范。当代教育技术学已经把教学设计视为研究的核心,有从功能上把教学设计视为教育、学习等理论和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连接学科和实践学科,基于这一立场,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专家已经在教学设计领域完成了理论的建构并创造了有效的操作性成果。事实上,在教育实践领域,教学设计、教学质量监控这样的观念和行为正逐渐走向普遍,各种个性化的学习模式、教学模式以及在某种理念支撑下的课程开发广受欢迎。相信随着教育实践自身发展需求品位的提升,出现为一线教育、教学服务的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必将成为教育活动运行系统的基本元素。
目前让人疑虑的是教育技术学影响下的教育应用开发,从范围上看,基本上局限于教学,对于教学之外的其他教育活动缺乏关注,从结果上看,客观上强化了学校教师的技术理性,同时也就淡化了教育事业不能没有的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首先,系统、持续的教育与教学具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使得人们在思考和研究教育时几乎自动地走向教学。此种现象不仅仅在教育技术学领域表现出来,连同前文提及的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在走向实践和进入实践之后都没有避免变为“教学心理学化”。我们的认识是:如果把工程视为一种立场和思维方式,一切服务于教育目的的活动都可以被“设计”和“控制”。尽管教育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具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但“规范”和“精确(准)”在教育活动的一定时间和空间也是必需的。长期以来,我们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价值的辩证,这不只是获得思维圆融的需要,也是实践智慧的基础。其次,不能轻视教育活动中技术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现实。技术作为工具是任何活动的必需,但技术作为工具总归是手段性质的,忘却了目的,一切本有深刻意义的活动都可能沦落为没有诗意的简单或精致的劳作。应该没有人承认自己在教育活动中忘却了目的,而实际的情形往往是他们把目标误认为目的。须知目标和目的一方面具有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教育活动的具体时空中又可以相互分离。就两者关系而言,在时间的维度,目的是终极性的,目标是阶段性的,在空间的维度,目的是整体性的,目标是部分性的。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人的活动总处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内,以致当人们把目标误认作目的时并无觉察,最终,忘却终极和整体的目的就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
回到现实,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群在性质上很接近我们所说的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者,这个人群就是存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管辖范围的各级教研室里的教研员。我国的教研室产生于1950年代,应国家基础教育规模扩大带来的高质量师资短缺而生。教研室的工作主体是基础教育各个学科的教研员,理论上讲他们是来自学校教学一线的优秀分子,他们的职责是对一定范围内的学校教师进行教材处理、课堂教学等方面的指导,追求的是具体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质量提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教研员的业务工作属于“就事论事”,与教育工程师的职能少有关联。1980年代中期后,受学校教育应试取向的影响,教研室在很多地方适应性地成为“考研室”,教研员莫说与教育工程师关联,连同他们原始的功能也基本丧失。积极的转变得益于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因教育理念与传统差异明显,在行政推动改革的机制运行中,教研室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的业务机构顺应性地承担了课程改革的指导和推进职能,教研员的形象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endprint
教研员形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他们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指导学校教师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造自己的教学,由于新课程改革是以课程改革为切入点的整体教育改革,使得教研员的指导范围客观上超越了教学的范围走向教育整体。这一次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既深且远,不仅带来了学校教育顺应时代的积极变化,也催生了专门、专业的教育应用开发者。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现在的教研员就是教育工程师的一种,但基于教育理论的应用开发不再是天方夜谭。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传统的教研室正悄悄地转型为教科研中心,也就是说教研室在传统的教学研究之外开始触及科学研究。而由教研室里的教研员进行的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扎根于教育实践应用开发研究。教研员不是以追求教育真知为目的的教育学家,也不是以追求教育实际效益为目的的一线学校教育者,那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显然是处在纯粹教育理论与纯粹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人物。既然是中介,职能上必然是引导、促进和实施双方的互通互动。他们有条件总结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纯粹的教育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经验性资源,更有责任把纯粹的教育理论转化到教育实践之中,这里的转化正是我们的教育工学所关注的、将属于教育工程师所承担的教育应用开发工作。笔者曾基于教育工学的原理,阐释了教育工程师的基本职能:(1)对教育理论进行操作性解读;(2)在教育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应用性开发;(3)对自己所做的应用开发进行操作建议;(4)对教育实践中优秀经验进行初步加工和处理,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提供“理论原型” [7 ]。现在看来,我们的理论设想和实践领域的变化不期而遇。
参考文献:
[1]刘庆昌.教育工学初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5):1-6.
[2]李曼丽.工程师与工程教育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0,90,87.
[3]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42.
[4]裴斯泰洛奇.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2.
[5]朱治军.在实践中孜孜探索——芝加哥大学时期杜威教育实践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49.
[6]刘庆昌.感悟“新基础教育”研究[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3):63-65.
[7]刘庆昌.教育工学与教学研究新的使命[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5):95-101.
Abstract:At present,educational engineer is not a professional title. However,staffs who take responsibility as an educational engineer objectively exist. It shows that educational engineer has a reliable realistic foundation. In the future,when staffs that are called educational engineers appear,they just do dispersed functions in a centralized way. Realistically,there are indeed some people who work on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common feature is they transform educational theory into educational practice. What we called“the real existence mode of the educational engineer”mainly refers to spot educators with a certain feature,educationalists who create and practice their theories,and those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 staffs who conduct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Key words:educational engineer;educational theory;educational practice;educational engineer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