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学术
丛文俊
艺术与学术
丛文俊
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史学的关注。
我讲的是书法史研究如何更好地去关注艺术,也就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史学关注,并且更好地去解读文献。我们在强调学术的同时,不能离书法太远,如果做的工作始终在外面打外围,对我们的研究和书法的学科建设即缺少相应的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未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是很可惜的。
大家知道,书法史无所不包,面非常宽,哪一个方面的研究都可能牵涉很多问题。比如书法作品。我们现在所说的作品很泛化的,似乎把古代遗迹都包括进来,这些年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作品,就相当复杂了。它不仅涉及到作品的分类、作品的功用、作品的形式,还涉及到延伸的很多问题,包括理论问题。比如说古代很随便的一通尺牍、一个便条为什么我们会称之为作品?很多文字遗迹本来不是为了成为作品而存在的。它们只是实用过程中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留下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称之为作品呢?现在,我所讲的作品其实是采用一种通俗的说法。说到作品,还要学会去关注作品后面的人。书法家来自古代文化群体的主导力量,他们是知识阶层,他们所有关注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了解。比如他们的知识结构,即使我们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全面,也应该努力去理解、去接近他们,能够解读他们留下的文章或者诗词、著作、题跋这些东西。如果对这些不能很好地解读,书家研究也是很有困难的。换句话说,古代书法家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应该去关注,甚至有些在文献中记载比较少的,也应该试图去关注。比如在古代城市文化当中,可以衍生出很多和书法有关的内容。一个都市的文明,市民思想和文化、生活乐趣、习俗都可能对书法家的思想、审美、创作产生很好的影响,而我们平常不太去关注这种东西。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对皇帝讲道:“京师翼翼,四方取则。”意思是说首都的各种风向都会影响到天下。同时他也讲到帝王的“一人之风,天下之化”。皇帝的好尚,他的一些政策也都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书法,甚至更为深远。像这些情况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书法研究当中现在还缺少一些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还有一些缺环。
如果要读古代书法文献,首先要有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的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断代、今注今译等。很多伪篇要进行考证,有些像图谱类的东西往往有缺失,我们就要根据后代的一些线索力图去弥补,以便揭示它们最初的面目。比如《笔阵图》,应该属于图谱类的东西,后来怎样给它增加文字的内容,使之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这类文献的时候,不仅要能够辨伪,还要找出它最初的文本面目,这样才有利于今天的使用。在文献学之外,我们知道古代传到今天的书论大概有二十几种文体。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相应的文章做法、相应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有与之相应的解读能力。比如像《述书赋》,当代人写文章很少引用《述书赋》。因为它是赋体,赋体首先在于文学,书法只不过是它的写作材料。但是毕竟里面包含很多思想,是文辞内容很难懂,大家都敬而远之。类似情况还有很多,也就是说在文体方面,它会引出很多文学问题,而这些文学问题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书法的解读。还有,书法作品都有一个文字问题,书法文献也有一个文字学的问题。关于文字学,不是简单、传统的“小学”,还包括现代学科的古文字学。古文字学最初还是从古器物学中分出来的,从金石学里分出来的。这里包含又很广泛。仅作品形式,像我们所熟悉的金石拓本——黑老虎,它也是专门的学问。传世品这些墨迹的研究像傅申先生昨天报告所讲的,也是很专门的学问,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很多学科的学问。如果再进一步讲阅读文献,还涉及到语言修辞问题,都很具体,有些内容下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作为书法史研究,它需要的学科知识的储备是非常多的。它涉及到文、史、哲很多领域,但对于高等书法教育来说又缺憾太多。如果要把研究做好,我的体会就是自己去补课。补课也是很需要技巧的事情,不能全面补,全面补人就老了。可以急用先学,也可以有选择地学,在老师指导下有所借鉴。下面主要讲解读书法文献和复原历史的体会。

陆机《平复帖》
一、关注风格
书法史研究要关注风格。在书法史研究中,免不了要对书家和作品进行评述。很多评述都是把古人的评述引用过来,引用过来以后或者加以解释,或者不加以解释,或者借题发挥扯出很远。这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要解决什么?如果只引用前人的评述,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学术。如果扯出很远,往往要借助西方的东西,这不是不可以借助,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还是个问题。学术的立足点在哪,还是应该思考的。比如张芝,关于他的作品风格我们真是一无所知,比较权威的记载也只是卫恒《四体书势》讲到他“下笔必为楷则”。那么,楷则在草书中又是什么?他的草书集杜度、崔瑗之大成。杜度和崔瑗在《四体书势》上都有记述,杜度的书法是“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瑗是“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说明杜度用笔沉劲而稍瘦,崔瑗效之得其笔势而结体或有疏失。但这样我们对杜、崔二人的风格了解还是很有限的。这里需要一个材料作为佐证,就是崔瑗撰写的《草势》。崔瑗在《草势》中讲道“几微要妙,临时从宜”,也就是说草书有随机性,写完之后是“一画不可移”。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显然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章草是不一样的。因为章草缺少随机性、字字独立,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杜度、崔瑗的草书会不会是章草的模样?我想应该不是。如果草书有随机性,那么它一定是很快速的书写,特别是“杀字甚安”,是沉着痛快的一种用笔,章草是做不到的。张芝风格则应该是一个变化。这种变化赵壹在《非草书》中也讲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张芝每作字都说“匆匆不暇草书”,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写草书,这个草书即“难而迟”,也就是说草书到张芝写慢了。慢了的草书应该是什么样?张怀瓘在《书断》里有一句话很有价值,“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也就是说章草之名跟张芝有关。张字是应该作为“楷则”来存在的,章草具有楷则,也就是和传世的松江本的《急就章》很接近。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杜度、崔瑗的草书基本上还没有脱离实用,到了张芝发生了转折。草书发展开了一个叉。之后索靖延续张芝的路,卫瓘兼采张芝法,都有脱离实用的倾向,剩下的一个线索就是东吴的皇象。皇象的书法是“沉着痛快”,想来也是实用的。这种实用的草书是什么状态我们不知道。但是看陆机《平复帖》应该相去不远。或者说,《阁帖》里所见的皇象《文武帖》不可靠,至少是不准确的。那么对陆机的书法,王僧虔《论书》曾经评价:“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多是褒扬,少是批评就是微词。没有办法判断优劣、高下,也就是东吴书法和中原流行的卫瓘、索靖书法是不一样的。《平复帖》大家都知道,像章草又不是章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纵向取势。所以我认为它还是草书的自然延续。它书写是快速的,是从实用的角度发展,也可以说东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续杜度、崔瑗的草法,这一点正是今草的一个渊源。换句话说,今草是不可能从章草中解放出来的。因为章草每一个收笔都是横势或向上的。作为一种经典,它的样式已经凝固了。对于凝固的样式,大家都是学习,亦步亦趋,没有听说任何书家去破坏章草而成名,所以章草不能代表古今草书演进的一个环节,它只是开了一个叉。今草则是延续了杜度、崔瑗以实用为主的草书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张芝的“楷则”,可以借助《急就章》去觅它的风格。相关的文献像王献之劝他父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其实,这个话不可靠。因为这个话是后人认为今草是从章草演变来的,所以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劝他父亲改体,“不若藳行之间”,另创别法。这个显然是后人杜撰的。首先认为章草和今草一脉相承,才劝他改体。其实那时王羲之早已成名,今草也早已成熟,用不着改体,不存在这个问题。其次,所谓“藳行之间”还是讲王献之的“破体”。由此可见,关注一个书家,必须要关注他的风格,书法研究总是要涉及到风格,不然怎么能成为艺术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引几句话,就等于说明书家风格了。例如王羲之说:“然张精熟,池水尽墨。”说张芝书法“精熟”,只能是一个点,精熟是什么样子?精熟的种类非常多,智永的字也精熟,显然是不一样的。
精熟是一个中性词,任何书体都可以用精熟来形容,它不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风格问题,风格判断需要有很多东西来支撑它。后代的东西容易了解,离我们时间近、评述多、记载也多。早期的东西很难溯其源,三千年书法史差不多有一半是没有开头,只能看到作品,而作品的解读也就是后人,特别是清朝以来的一些书家、学者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对不对还难说。再比如王羲之的作品风格。大家知道,王羲之的名气太大了,评价他的人也多。按理说王书风格不难评议。但是如果我们用学术的眼光去审视的话,仍然存在问题。何延之的《兰亭记》讲到王羲之兰亭草稿“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在有的辞书里面释“遒”为有力,并且引用其他人评价褚遂良的书法时使用了“遒媚”这个词。现代学者还有人写了《论遒媚》一文,但是“遒媚”是什么?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大家可以想想,从修辞的角度看,如果“遒”是代表有力,那么后面“劲健”的“劲”做什么用?不是重复了吗?我想何延之即使不是文学家,他的修辞不至于如此拙劣,所以这个“遒”不是讲有力。“遒”可能有这一方面的义项,但是在这里绝对不是有力。它是讲点画线条的质量感。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王羲之的点画结实。往前推,可以用王僧虔《论书》里的话对换。王僧虔《论书》在评价“二王”书法时讲道:“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骨势”应该是“遒”的核心所在,“媚趣”是在于形式。“媚”一般说是讲视觉上的感受,但视觉感受又不是纯粹的样式。所以古人经常用态度或意态这样的词和它换言。也就是说,“遒媚”讲点画的质量和它的视觉形式,后面的两个词做补充和说明,“健”是点画的质量,“劲”是笔力,都很具体。在这里,王羲之风格从比较早的可能看到王羲之作品原迹者的评价上,去寻绎王羲之作品的风格,应该是可靠的。宋以后的人再评价王羲之就不可靠了。因为都是摹本、刻帖,谁说王羲之风格如何,都是看个大概,只能得一个粗略的印象而已。所以要讨论王羲之作品的风格,还要从唐以前的文献来看。回过来看,评说王羲之的作品用“遒媚”来概括比较合适,宋高宗在《翰墨志》再次引用和强调这个问题,后来黄道周更把“遒媚”说成书法的最高境界,都可以说明“遒媚”这个词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按照前面的理解,“遒”在于点画的质量,“媚”在于能够看见、能够感知的形式,也就是“骨势”和“媚趣”,可以互换。引申开来,以其最初评价的是《兰亭》,而今天能看到的《兰亭》有两类,一类是神龙本《兰亭》、其他摹写本《兰亭》,它们能否有“遒媚”的美感?如果说摹写本不准确,那么刻本会怎样?也就是定武系统的。临本不可靠,不能算。在刻本当中,究竟哪个更好?如果进一步扩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王书”,无论是刻帖还是唐摹本,究竟哪个有“遒媚”的美感呢?或者说哪件作品能典型地显现“遒媚”的风格?这个问题其实很需要琢磨。如果不负责任,稍微用点力气,或者在电脑上把关于王羲之的评价全拿来,之后排排队,分分类,描述或转述一下就完成任务了。但这种完成任务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书法研究能不能较真?

皇象《急就章》(局部)
下面咱们再说一下欧阳询。欧阳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书家,历史上的评价也非常多。古人的评价问题在哪?他们经常说欧阳询如何,不分书体也不分作品。对欧阳询最早做评语的是张怀瓘,《书断》评其书“劲险”,后人或认为欧阳询的字最险,遂用“险绝”来描述。“险”究竟是从哪看出来的?很多人评价草书的时候也用“险”字。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难题,草书曲线多,字形歪歪扭扭的很难说哪里“险”,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就等于承认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它。咱们这一代还是应该做点什么。欧阳询的“劲”好判断,“险”不好判断。在欧阳询的楷书中,有很多作品向右上方倾斜,右角高左角低,他的字不稳,这是一个“险”的可能。还有他的字棱角分明,甚至很多转折处带圭角,就是尖角,可能是“险”的来源。张怀瓘还有一个辅助性的评价说欧阳询的书法“森森焉若武库矛戟”,就是说像兵器库里矛戟的锋利,冷森得可畏,和他的棱角是对应的。但是,有棱角的字不见得“险”,比如褚遂良的字有棱角,薛稷、薛曜的字也有棱角,唐楷越写越瘦,到张怀瓘的时候,棱角成为社会性的弊端了。不是棱角都“险”。还有一个特点,欧阳询的楷书两个竖画向内微曲,张力向内,往里挤。颜真卿向外,向外拓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险”究竟是从哪来的?是怎么产生的?这就要讲下一个问题——复原想象。
二、复原想象
古人所有的书法批评用语,在今天的书法美学和书法研究当中经常把它称为概念和范畴,或者叫美学范畴,或者叫理论范畴。这个不是不可以,这得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词比如这个“险”字,不是为概念而存在,更不是为范畴而存在。它的本意就是一种意象,这种意象的表达有多重因素在内。一个是文学描写,它的评论也要考虑到文体问题。第二就是雅言修辞。士大夫写书面语言一般都用雅言,很少用方言和白话。书法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借助意象来表达审美所得。这种意象表达的原理是什么?原理就是古人习惯于审美当中由此及彼。他想说这个事但是他不直接描述,或者是无法做到直接描述,这就是古人思维和表达的一个特点。要说欧阳询的字有棱角,就应该直接说有棱角,为什么要换一种说法呢?古人习惯打比方,以此及彼,进行联想喻说,以所知喻其所不知。为了说明问题,为了传神、概括,至少要提示一个联想的方向。这种意象即使具有不确定性,也都是有参照系的。比如“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险”是有一定理解的,和我们今天不一样。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很好的社会体验,到黄山看天都峰你会觉得它“险”,自古华山一条路也是非常“险”。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直观的东西,再看欧阳询的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险”的概念。按照古人的生活阅历和体验,它的获取是约定俗成的。游泰山的人没有说泰山险的,因为泰山只是大。大的东西是不能险的,险的东西往往是高、挺拔。为什么“危险”要经常组成一个词呢?危就是高,“危”字是从古“岸”字上面站一个人,站在崖岸旁边当然就危险了。这种险是有参照系的,所以看到欧阳询的字就能想到险。有人用“四壁削成”来形容,一个山的四壁都是用刀剑削成的,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险”确确实实是指欧阳询的字形。既然是能够看得到的东西。那么他就具有了风格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研究欧阳询的时候,首先要为他的风格找一个切入点。古人的评述很多,但是不见得都是风格。像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欧阳询书法如“虎饿而愈健”,饥饿的猛虎突然见到食物,会立即疯狂地扑过去。用它来形容欧阳询的字是得到瘦劲了,但是得不到险。
如果说所有的古代风格描写的词语都是意象,应该说差不太多,但不完全,因为有些风格描述是隐性的,比如黄庭坚经常使用“古法”的概念。他的古法有两层意思:一个专指晋人古法,一个就是泛说的——晋唐古法,有的时候只包括唐。宋人不仅黄庭坚,大家都喜欢这么谈。他们不直接说风格,而是借用古法来说,如说某某书甚得古法。昨天,看傅申的图版里有苏舜钦的字,苏字用笔更多强调力量,得唐人东西多而得晋人东西少,他的笔在纸上用功夫的时间多,抬起来凌空取势的时候极少,所以得唐人的东西多。还有一个黄庭坚批评的周越,说他“劲而病韵”,周越的字从唐人出来,其古法就狭义地指唐人的东西了。对唐人的东西进行批评的时候,苏东坡的两条书论比较典型。一个是他在评价晋唐书法的时候说:“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萧散简远”主要是凌空取势,下笔在空中就是一个有效的运笔,打纸而入,所以能“萧散简远”,同时也是笔方势圆
的一个特点。唐人不是,唐楷、大草都可以在纸上平拖,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的笔法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二是苏东坡在批评苏舜钦、苏舜元兄弟书法时说:“俱太峻,非有余,乃不足也。”二苏所学的古法像古人或者达到古人的水准,不是有余而是不足,不足的前提就是没有晋人的“萧散简远”,点画之外可以品味、想象的东西不多。虽然没用什么概念来描述风格,但是它已经存在了。有些东西还需要我们进行想象,黄庭坚评价王羲之书法“如左氏”,王献之书法“如庄周”,左氏是左丘明,《左传》的作者,庄周是《庄子》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就得从这两本书当中去找。这也是隐性的对风格的描述。但是不管怎样,传统书法批评最多使用的还是审美意象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普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贯穿两千年书论始终,当代人缺少这种想象,但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这种生活、缺少这种文化和思维训练了。王勃《滕王阁诗》中说“珠帘暮卷西山雨”,是有珠帘的,李清照写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也是有帘子的。今天的窗帘是卷不了雨,也卷不了风的,方向变了。有很多东西就没了,就像我们登一座高楼,有可能以后去台北旅游登101楼,也不会写出来王勃《滕王阁序》那种“披绣闼,俯雕甍”的美感,它们只是高而已。换句话说诗意没了,想象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人太现实,现实以后就没有了诗意,没有诗意不要紧,偏偏还要搞艺术,这就有问题了。要搞艺术缺乏想象是不行的。西方美学、艺术理论有很多概念对书法风格的评价来说很难用上,或者说远远不够。古代的东西如果我们缺乏对它的研究,就会变成了僵化的标准件,使用起来难免犯错误,表现出一种很苍白的学术能力。

米芾《丞徒帖》
今天写文章,或者研究古人,或者评价当代的作品,真是要有想象的。这种想象力好像演员的一种训练,一种职业化的本能。一个演员首先要进入角色,不能演什么戏都是他自己。书法研究的想象就是要针对作品,它不仅仅有助于研究还有助于创作。也就是说,想象能帮助我们进入角色。在想象和选择表达词语之间,有很多是属于经验性的,和长期的学习体验有直接关系。评价一个人的作品,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评价,最关注的首先还是风格问题。要做出好的风格判断,是需要经验积累的。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跟白谦慎在电话里聊过,就是语言规范经验的问题。我们看一个人的书法往往得到很多,而描述时可能就两个字,古人有时节省就用一个字,有时两字不够用就四个字。可能感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名家作品,它的美感一定是很丰富的。可是当你选择评说用语的时候,就有了经验的问题。选择用语首先是表达方式,用比喻的方法,还是比较的方法,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批评。一般来说描述风格还是从经验出发的为多。其次,是形象的联想,用形象比喻,这二者是最为普遍的。选择什么来比喻?打比喻得让人懂。米芾在《海岳名言》里也曾批评前人的用语说:“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他看不上这种话,而他形容某些人的字“笔笔如蒸饼”。宋代的蒸饼是馒头,形容笔画像馒头那样圆,也是一种比喻。蒸饼是静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动的。其实,比喻好的非常管用,有时真的不知所云,比如像袁昂《古今书评》他讲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谢家子弟即使不成才,不端正者,也比一般人家的子弟有气质。李嗣真《书后品》评王羲之书法“终无败累笔”“万字不同”,也是说写坏的字也是好的。这里就有一种偏向,不涉及到书家风格,等于说王羲之书法最好。但是,我们说最好就没有美感,人家说就很玄妙,就能吸引人。袁昂评殷钧书法“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乏精味”。高丽使人穿民族化的服装,要能想象出他们的气质风度,就能够传神地得出殷钧的书法风格。这里就有一个用语直接,还是隐曲,或者不当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很难对它们进行解读。不管古人说什么,我们应该把它弄懂,这里面有很多非常传神的批评,是用经验的词语或者其他意象所不能取代的,是一份很好的文化遗产。从袁昂以后一直到康有为,历代书论传承不衰,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像宋人重学术,可是他们还对这种批评方法念念不忘,还要模仿。米芾就不用说了,黄庭坚、苏东坡也都采用。“比拟失伦”,就是打比方不当。像《古今书评》评价张芝草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汉武帝喜欢长生,追求长生不老之后,泛舟海上,凭虚欲仙,这跟张芝的草书有什么关系?我写《袁昂〈古今书评〉解析》的时候下了很多工夫,多方求证,最后还不是很有底,很难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联想有助于美感,幻想则有碍美感,太离奇不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验是非常多的。不同的是,古人的经验都能借助于文学来表达,并从心灵深处影响创作。古人从小就有很好的诗文训练,长于想象发挥,遣词造句能力极强。有个很有名的故事,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写完之后觉得“推”不好,用“敲”好不好?反复地推敲,在路上结果撞见了韩愈,韩愈认为还是“敲”好。月明人静的时候,一个和尚回来晚了,进不去寺庙,就得敲门。轻轻推门则有点胆怯心虚,敲门则理直气壮。尤其是夜深人静,一敲传出很远,又很清脆,诗意更浓,于是“敲”就成为诗眼。黄庭坚曾经讲:“字中有笔,如禅家字中有眼。”“字中有笔”有些人不懂,苏东坡却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很难看到,今天人写字好用生宣,墨什么都很淡,着纸即涨开,结果笔是方是圆、是枯是润、是转是折,什么都看不出来。吉林省博物馆藏苏东坡《二赋》,它的纸像蜡笺一样,笔痕都留在纸上了,能清楚地看出来哪是侧锋,哪是中锋,哪是藏锋,入笔出锋宛然目前,确确实实是“字中有笔”。就“字中有笔”的层面进行评论,得不得古法,或者得不得笔意,它都有依据的,都可以根据经验进行判断。当它进行书面语言的表达的时候,它就会选择恰当的联想和描述。如果都像今天作品的状态,很多人喜欢用水把墨涨开,涨出立体感,我就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没法再说话了。王铎写字有涨墨不是故意的。他写字快,有人帮他拉纸或者拉绢,即晕出涨墨。今人或觉得还是涨出笔画之外效果更好,于是想办法用宿墨或者用水,到作效果。古今书法经验有很多悬隔,这种经验的悬隔是很可怕的。比如从北宋以后到清代为止,篆书、隶书的审美和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相当低下。陈槱在《负暄野录》里说宋代开始用烧毫、束毫的方法来写篆书,以保持精细匀一的玉箸笔法和线条。他引用黄庭坚的话说:“篆摹当随其斜、肥瘦与槎牙处,皆镌乃妙。”得把它们如实刻出来才行,但是工匠往往把它们修刻得一般粗,像玉箸似的。如果按照黄庭坚的话去写,人家说你不懂篆书,所以书家不得已而循时俗,按照工匠刻出的效果去写,于是烧毫、束毫,或者退笔作篆的各种方法就都出来了。从宋代到清代,烧毫、束毫作篆是非常普遍的。邓石如出现以后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但是有一些写铁线的还在用这种方法。今人用小笔,写完一个线条再去蘸点墨写下一个线条,写一个字蘸多次笔,古人那种体验就没有了。古人用烧毫、束毫写字,名家用普通笔写字的经验也没了。经验没有了,审美就要退化。从宋代到清篆、隶理论水平相当低下,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碑学的理论水平,有很多东西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像吾丘衍这样的名家也能搞错,把三国魏碑当成汉碑。我们看赵孟、文徵明的隶书真是挺丑的。其实,邓石如隶书也不好,一看就知道从三国的碑里面出来的。他也不是写汉碑。清人对汉碑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在审美表达和批评的时候,语言经常是无能为力的。说了很多中性词,和不说也差不多。后来,杨守敬评建安时期《樊敏碑》时说它石质粗糙,“锋芒多杀”,“而一种古穆之气,终不可磨灭”。什么是“古穆之气”?说它“锋芒多杀”,锋芒没有了就不知道风格原貌是什么了,“古穆之气”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变肥的残缺字形出来的,是拓本现象所提供的,还是作者原来写出来的呢?审美完全偏差了,此碑已远远不是原貌,即使是碑的原貌,也未必是书写者的原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评价作品风格的时候凭的是拓本现象还是未损时碑的原貌?刻工对碑有多少影响?不清楚,就拓本现象去评价作者和作品,是有很大问题的,也是书法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再如文吏字,文吏字就是馆阁体、台阁体类型,段成式《酉阳杂俎》称之为“官楷”,也就是宋人讲的科举字,姜夔在《续书谱》中讲到的“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即此。当《郭虚己墓志》出土以后,一看就知道颜真卿是从官楷里出来的,是缺乏个性的官样,后来才有个性。历史上对颜真卿评价最高的是从欧阳修《集古录》开始的,是因人及书,人品即书品,再加上苏东坡的推波助澜,颜真卿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王羲之大统的一个分支。其实大家都能看出来他和王羲之无关。古人非常重操守。人品不佳,字再好也不行,今天对书法史的研究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检讨,用后代尊崇颜真卿的一些评论来给他在唐代书法定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唐代写墓志碑文最长的大概就是颜真卿。颜真卿的文集不忍卒读,他不厌其烦,家世及亲属的家世一遍一遍地说。以光大门庭为己任,也有虚荣心,如果要为颜真卿复原的话,就没有必要用后人的崇敬去充填起来。颜真卿是一个重要书家,历史上已经成为事实。历史地位如此,没有必要把他推倒。但在描述唐代书法的时候,不能说天下人都学颜真卿,对唐代那段要有节制,这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古人有很多虚的,他们对书法的理解也有错误的方面,我们不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对前人有的毛病,我们在书法史研究中要一个字一个词去仔细地推敲,找出合理和不合理的东西,我们的学术才有价值,才能够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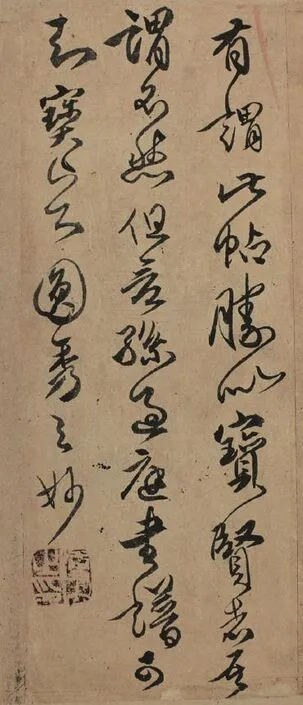
傅山《读鬼谷子公孙龙子等杂记册》(部分)
下面再讲一下词语的简单分类。作为书面语言表达,可以把它们叫做词语,从古代书法审美的状态来看,它实际上是从想象到意象的方式。从古代书论反映的基本状态来说,一般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风格用语,有的比较隐晦一些,需要费一点思考。词语也有一些交叉的使用,如果经验性的词语表达不足以尽其意,那么还要选择其他的形式进行补充描述。补充描述当中既有技法,又有美感,还有风格,需要我们去体味选择。我把词语大概分成三类:一是风格的对应词语。二是中性词。中性词如“神”,包括“神采”“风神”“精神”等,任何人的作品都可能存在,没有风格指向。“韵”也是这样,像梁讲的“晋尚韵”,对于晋人来说,他是否尚韵是另外一回事。宋人以韵评书,也经常使用“俗韵”,就是俗态。俗也有韵,所以韵应该是个中性词。还有像“气”,也有多种用法。当暗含人品或书品的时候,气有清浊品格之义;如果指作品也就是流贯于字里行间的、按照笔顺进行的书写过程中的生机,这个气比较简单;如果在哲理的层面进行描述就是阴阳二气,同时它又是一种规律,存在于所有书写的过程和所有的细节当中。气比较复杂,但无论多复杂,都不存在风格指向的问题。有大家熟悉的“骨”“肉”等等,都是如此。只有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风格,像“颜筋柳骨”。中性词在书法批评里也有很多,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不要把它们误以为是一种风格的描述,而更多的只是美感或者量说美感的一个标准,或某一层面的倾向、意味。第三类就是判断词,古人很喜欢做价值判断。虞龢《论书表》讲道:钟、张与“二王”互今古,“二王”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古今”的标准由此产生,进而有“质文”或“质妍”之分。宋苏、黄、米书法重视个性,即把唐或时人的字称之为“俗”,那么他们的东西就是“雅”,“雅俗”就出来了。“雅俗”其实是中性词,也是变动不居的概念,始终像阴阳一样相对依存的。价值判断既有得失,也有品质高低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书法史如何推进的。我们对词语的判断要多下一些功夫,并且进行较多的统计和排比。搞清楚都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的字会雅,什么人的会俗,这样才能对雅俗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什么时候雅俗可以互相易位,就像我们对美丑易位的把握一样。本来字往好了写是好,可是当审美心理发生逆反的时候,写丑了是美,写美了就是丑。米芾认为欧阳询、柳公权的楷书不好,为丑怪恶札之祖,把颜真卿楷书视为“俗品“,即认为“行字可教”,都是立场分明的。冯班在《钝吟书要》说米芾、苏东坡喜欢做快口语。快口语就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其实不然,唐楷确实有它的弊端在内。批判唐楷有道理,就像批判铁线篆一样。很多东西到一定程度以后确实有物极必反这样的规律。这时很多概念都会随之发生易位,需要我们灵活掌握。
三、复原历史
复原历史想说两个小题目。一个是我们尽量努力去进入古人的生活场景。我是讲文化主体,就是留给我们书论,留给我们经典作品的书家。我们尽可能进入古人的生活场景,去体验或者想象他们会怎么想、追求什么东西。要有针对性。当代很多人都喜欢讲书法与文化,书法也是一种文化,如何从文化的角度看书法等。但是,文化得有一个底线,即什么样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和书法发生关联。换句话说,文化是怎样转化为书法动力的,转化为书学思想、书法风格等。不能说有了文化就有了书法,那太抽象了,也不能简单地比附。比如到苏州就说明代苏州文化和书法,把明代苏州文化编出几条之后,就把文徵明、王宠、祝枝山拿出来说一说就完了。结果文化是文化,书法是书法,谁和谁都没有关系,文化并没有落实到书法上。今天的文化概念其实是挺成问题的。一讲文化就“儒”“释”“道”,一定落不下佛家。其实佛学和所谓的禅学在书论当中极其罕见。要是从字眼上去找说某某人喜欢以禅论书,于是他的书法就有禅意,这就有点杯弓蛇影。像宋代的士大夫就喜欢禅悦之风,喜欢与和尚打交道,参禅讲论、机锋或偈语,都是一种时尚,不能说他就信佛,也不能说他的字里面就有了禅意。像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抄的是佛家语录,一定有禅意,好像很多人都信。黄庭坚自己还经常用禅来说书法。但他还有一件非常有名的作品,时间和《诸上座帖》接近,就是李白的《忆旧游诗》,能从那里看到禅意吗?如果从那里看出禅意就会生出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包括文辞内容是否会影响作品风格?如果肯定那么写李白的诗应该浪漫啊。有的人写文章就说它的书法风格和李白的诗仙精神是如何统一的。有时候越看越像,觉得拐弯抹角都有禅意。这实际就是把自己带进幻觉,自己还不知道,以为很有道理,很科学。文化和书法一定要切实找到可以证明的衔接点。大家知道,叙论唐代书法,很多人都会说“盛唐气象”,那么,“盛唐气象”是怎样融合到作品里面的?得找一个渠道要能证明某一种风格和某一件作品的象征意义。比如像张旭的《断千文》有盛唐气象,颜真卿楷书也有“盛唐气象”。但颜真卿书法在唐代不太出名,也没有多大影响,怎么能有“盛唐气象”呢?“盛唐气象”真要落实到书法上就很难说了。唐代人是怎么生活的呢?按照考古复原图,唐长安城是一个长方形,中间都是小格子,即里坊制度。里坊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宵禁,白天做什么都行,晚上每一个里坊都要关门的,谁也不能犯禁,所以唐人没有夜生活。和它相比,东京的汴梁就大有变化,变化的根本始于经济活动,就是漕运。漕运就是从运河入汴河,从《清明上河图》所画的水西门一直往里去。运河、汴河可以说是宋朝首都的经济命脉,什么好东西都是从那运进去的,于是城市第一次出现斜街,里坊制度也就随之废除了。又有了夜生活,夜生活使宋代的市民思想整个文化明显地不同于唐代。讲到书法史,都说宋朝有“尚意书风”。
宋代有很多风气与唐人不一样。风气转换以后自然影响到很多方面。宋人的“尚意书风”提倡个性,他们为什么反对唐人?唐人讲法度,法度太严,是一种束缚,宋人有很多前人没有的体会。我曾经专门买了一些书,例如有从考古复原的角度研究东京汴梁的,读进去就会进入到当时宋人的生活场景,想象出一些东西。有关于临安的《武林旧事》,讲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看,还有《东京梦华录》等。看完后我觉得那时的宋人确实活得有声有色。此前魏晋风度是对一个时代的推进,但其中有矫枉过正的成分。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论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我觉得他看魏晋很有意思。如果能从社会学或者文化学很多方面去探索晋人的生活,你对晋人的书法就不会概念化。在通常情况下,我最长两年读一次《世说新语》,每次读完都能有新体会。宋代的也是,过几年时间宋代的就要读一批。以免忘了。宋代的各种各样的笔记、小说中哪些细节对我们了解宋人有好处,而这些又是如何启发宋人的精神生活,为他们重新构筑起一个精神世界,这样他们才可能在书法上有所谓的“尚意书风”,有个性解放,有各种各样的代表新思维的书论出现。宋代不仅是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书论也是一个重大转折,提供的信息非常多,如果我们能进入北宋的市民生活中,即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答案,从而推动当代书法学术研究。复原历史要写出一些活生生的人。现在写书家往往概念化,都是籍贯、历官、著述、交游,之后就是书学思想、作品,描述之后书家研究结果。有些书家记载详细的还可以再加一份年表或者年谱,之后换个研究对象还这么做,就好像古代书家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最近几年我经常跟学生推荐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用十年的时间研究一个书家,研究如此深入,并且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可以透过一个书家看很多问题,看整个书法世界。书家不是孤立的,他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很多东西是有代表性的。所以书家要研究好,一定要进入那个社会、进入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当中,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明代书法史离不开苏州,如果把吴门书法和吴门书家取消,明代书法史就没法写。其实,吴门书法是一群在野的读书人做主体,不当官的人居然能挺起书法半边天,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还有相当多人支持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能存在,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事情就不偶然。目前对书家的研究相当多,但是从整个明代吴门的经济入手,探讨其城市思想、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吴门书法找根源,至少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大的空间。清代的扬州也有这种情况。郑板桥当过县令,在八怪里他很自豪,有仕历,和别人不一样,其实都是怪,都在民间。他还觉得是专业干部。这种感觉确实能帮助我们思考。郑板桥的字也不是很好卖,他也得找出路变法。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郑板桥集》里面他自己不记载。还是在别人的笔记当中看到他的真实想法。他说世人好奇,非得写得怪怪的才买。这才让我们知道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初衷是为了卖给没文化的盐商,他开始下海的时候也不那么顺。我们讲扬州八怪,能不能也进入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当中?
最后讲一下怎样阅读史料和书论。当然有很多方法。在这里我专门讲一个话语情境。苏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第一次提出了君子小人之书和“苟非其人,虽工不贵”的审美标准。苏东坡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大家知道,苏东坡在元丰二年秋天被下了大狱,即著名的“乌台诗案”。被人陷害,九死一生,被发配到黄州。元丰三年春天到了黄州,元丰四年见到唐林夫所收藏隋唐六家书迹,于是借题发挥,“君子小人”的概念就在不正常心态下产生了。后来黄庭坚心思缜密,替他圆场,推广出一个雅人和俗人之书,再用“书卷气”来解释,使这个理论稍微圆满了。还有一个就是傅山的“四宁四毋”说,本来是傅山《作字示儿孙》一篇当中的几句话。他叙述过自己当年学过赵孟,后来觉得写赵字有点后悔了,像与匪人交游。傅山在清代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他为了维护面子,必须得告诫子孙:“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傅山接下来说:“此是做人一著。”也就是说,他的“四宁四毋”是告诫子孙写字也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做人的,不可不谨慎。宁肯把字写坏,也要写出个性、写出风骨。千万别写软媚了让人骂。他前后的言语都很多,大家都不引,专门引这四句,使它脱离了原有的话语情境,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书法真理。这实际上不是傅山的本意,如拿它当口号,说傅山就这么讲的,就有一定的假象。很多人都是这么转引的,根本不注明出处。这就是做学问不规范,无论是研究书法史,还是研究书论,甚至涉及到创作,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