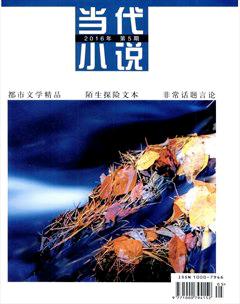雷同的退缩与无用
武润泽
“你以为这还是一个拼天赋的时代吗?……最后就是谁在浊流中活得更久一点。”这是周嘉宁在新作《抒情消亡简史》中借人物之口对这个时代的戳刺。浊流初显,生活方式、评价体系、审美标准等等渐趋雷同,无趣与无奈成为生活的常态,但比之生活表象的粘稠与焦灼,作家作品中表现出的一代人的退缩与无用更令人惊心。
少数民族作家包倬的新作《我还是我吗?》(《民族文学》2016年第2期)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拘一格的叙事手法和情节设置使作品的可读性和人物的可塑性得以凸显。作品以近似玄幻的手法讲述了“我”的身体缩小得如一岁五个月的儿子同般大小后的所见所闻。身体的缩小这一情节设置迸发了多重的隐喻空间。首先,“我”获得了全新的认知视角和存在身份,由此很多潜藏于生活表层下的暗流开始暴露。妻子毫不遮掩地将自己与上司偷情的丑事告诉“我”;妻子为了羞辱我,“把我的鼻子贴在乳房上,狠狠按着”,大声命令我“像个男人一样”;甚至“把我的手按在了她的下面,并且想往里塞”,“那种屈辱相当于把我扔进了粪缸”。作者以“我”缩小后的性无能为激发点,将无用男人的形象加以丰富。而身体缩小更喻指着无用男性在家庭、工作、社会等多方面挤压下的退缩与坠落,可退缩却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的爆发。退缩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奋进又显得无能为力,这正是弱势人群在这个时代之下的维谷之困。这是一个习惯退缩与求和的时代。当“我”的妻子与人争吵时,我的第一句话却是“算了吧……”在我被打后,出警的警察察看完伤情,也说“伤得不重,算了”。无论是平民还是代表权力的警察,所有人都保持着求和的姿态,都开始被时代同化。包倬这时又巧妙地设置了另外一个情节,那就是“我”的儿子命命的好斗成性。“我无法理解他仿佛与生俱来的暴力”,当他哭的时候“任何人接近他,他都要出手”。此时,退缩与好斗,求和与搏击,老一代与新一代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时代精神和姿态发生更迭,作者内蕴在文字中的希望之光得以倾泻。
隐蕴着两代人对抗的还有张怡微的新作《又一年》(《芙蓉》2016年第1期)。劲吾和自己的大伯“两人一直杠着,十几年没有分出真正的胜负”,“劲吾从小就不喜欢他,因为大伯从小就爱贬低他,奚落他。他做什么,大伯都说没前途”。随着16万块钱在两个家庭之间的搅拨,亲情发生了微妙的离析。大伯是一个悲情存在,他心中压抑的不甘是一代人的遗憾。大伯“想去上海,努力了一生,甚至找了一个上海女人再婚”,“但最终,他也没有拿到上海户口,生意小失败,灰溜溜回家乡”。入城的期望纠缠不断,使大伯的人生轨迹随之位移。被城市的排斥在情理之中,却又残忍生硬。劲吾继续着入城的使命,他渴望成为“大力水手”,甚至将女友称为“菠菜”,面对城市时内心滋生出的无力感只能期冀于近乎幻想的称谓里。而女友的分手短信——“我不是你的菠菜。神经病也是骂你。你老想着我给你力量,你什么时候当过我的力量”则彻底将幻想湮灭。层层阻障,让劲吾“觉得世界真是荒诞不已,躲到哪个角落都不能稀释浓郁的、跟鸡精块儿似的不合时宜”。于是,去台湾读书的情节更像是一种退缩和败逃。文末,“劲吾可喜欢坐飞机了”的直露表述,更隐喻着劲吾时刻保持着逃离的姿态,但,终点又在何处呢?
当上层的阴霾过于深重,我们只得选择“朝低空飞翔”。寒郁新作《朝低空飞翔》(《钟山》2016年第1期)的篇名即带有了某种抑止的味道。小说叙写了发生在一个夜晚的爱情悲剧,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女主人公青芝坠楼自杀。坠楼的情节首先是对“朝低空飞翔”最为极端的表现。寒郁的叙述思路极为清晰,女主人公被压迫至“至此心死”的过程在小说中可以提炼出一条完整且合理的线索。马明对青芝从珍视到漠视,进而开始无视青芝对家庭的付出,进而在争吵中开始怀疑青芝的忠贞,进而封堵了青芝对于未来的希望,最后主任在得知青芝怀孕后的疑问语气,将青芝生的欲念彻底击碎。作者在浅吟低语中将整个故事构建完整。寒郁以男主人公马明在争吵中的语气和心境,指摘了拥挤的时代和粘稠的生活中男性的艰难处境。争吵中马明多次想化解危机,却又一再佯装强势,表面的不服软,正在于希冀保有自己本已在外界丧失殆尽的尊严与地位。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它是梦工厂,也是梦想的屠宰场”,但“老子是真喜欢这地方啊!”对于城市的硬性融入,被挤压掉的不仅是尊严,还有生活的志趣与爱情的情趣。文中有一段类似于独白的精彩文段:“现实处境就是这样,都有一份梦想,却不够坚强;不甘于现状,却没有可以飞翔的方向。回到现实里,只能是做着一份鸡肋般的工作,一颗心蒙了尘、沾了灰,粗糙了,麻木了。连爱的人,都懒得费点心思去爱了。”朝低空飞翔,以飞翔的姿态反讽现实的退缩,坦然地接受渐变“迟钝,坚硬,冰冷,越来越没有耐心”的躯壳。
迷茫与退缩是这个时代雷同的特征,思考却没有答案,总不安分的向往着他处,却又无从达到。“永恒不变的单调正在折磨这个时代,谁都无法逃避”,我们都在经历“相似的痛苦,相似的折磨”。在这样的时代,抒情变成了略带戏谑意味的奢侈品。这便是周嘉宁《抒情消亡简史》(《长江文艺》2016年2月)中所凸显的。小说中出现的三个人物,分属三个年龄梯次,代际的演进与更迭表现得更加切实。年已五十的杨是个文艺男,喜欢斯汀和治疗乐队,惨淡经营着酒吧和画廊,却“靠贩卖廉价的艺术周边产品赚到不少钱”,“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盲目的热情和目空一切的顽固”;80后的A是名画家,怀念着曾经的热望岁月,怀念标榜自己是情境主义者的日子;而90后的年轻女孩活泼开朗,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无情”,又“和大部分同龄人的生活不太一样”。时代的雷同在小说的细节中得到了恰当的映射。A对年轻女孩样貌的评价是“如今杂志上常见的时髦长相”,而在评价瘦女孩的样貌时再一次是“是杂志里常见的另外一种时髦长相”。美与外在表象都成为了量产的复制品,因为我们都“太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丧失自己的判断标准”。A嗔怪杨:“你总是太容易被这些事情感染。”而杨反呛:“你总是太容易置身事外。”对待外界的态度,在游离中又掺杂迫不及待的贴合,我们“一边反对谬误,一边又不断地参与到谬误中去”。这或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渐趋雷同与无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