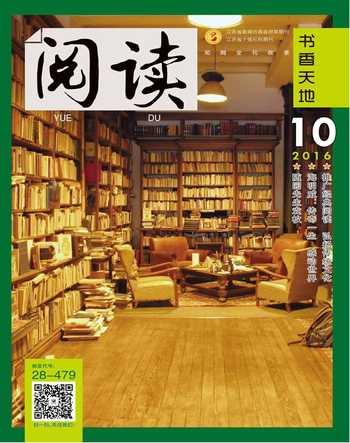无缘社会:那些与一切关系“断舍离”的日本人
邓郁
一年之中,日本全国共有32000人在孤独中悄无声息地死去。高龄、无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日本人: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故乡,也没人和他们联系;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遗体,甚至无法知道事主姓甚名谁。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
2010年,日本川崎市的一套单元楼。
一名90岁的独居女子死后过了将近一个月,遗体才被人发现。
家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厨房的烤面包机里还留着没烤好的面包,浴室的浴缸里放满了水,所有迹象都说明她是猝死的。
据说这是个有事业心的自立型女性,一直未婚。女子亲笔所书的纸笺上面写着“四时独吟红蜻蜓”的字迹,像是有感于自身境遇而写下的字句。
听上去透着诗意的词句,揭示的却是无比冷酷的现实。根据日本NHK的随后调查,一年之中,日本全国共有32000人在孤独中悄无声息地死去。
高龄、无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日本人: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故乡,也没人和他们联系;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遗体,甚至无法知道事主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最终被总结为寥寥几行的骨灰认领布告。
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
2009年到2010年,NHK走访了那些主动或是被动与亲缘、地缘和职场缘悉数“断舍离”的人。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对“无缘社会”的恐惧已经从耄耋老者蔓延到了年轻人,甚至十多岁的少年身上。
节目播出后,在日本国内激起巨大反响,由节目组创造的“无缘社会”一词也旋即入选日本当年度十大热词。由制作团队撰写的采访笔记《无缘社会》中文版也已面世。随着更多幕后故事的呈现,邻邦的严峻现实也更加清晰和富有警醒意味地裸露在我们眼前。
拒领遗体,“情比纸薄”?
“靠在浴室的马桶上,脸朝天,就是这个样子……”
2009年4月,55岁的常川善治因脑溢血在富山市的公寓内孤独地去世。尸体的第一发现人向来访的NHK记者摆出背靠马桶,面朝天花板的姿势。
常川原是在有钱人家长大,家里靠开超市过得相当富裕。但随着巨型超市的兴起,家道中落,常川与两个兄弟离散四方。他先后在客车公司、纸张批发公司、纺织公司、殡仪公司辗转奔波,直到最后的出租车公司。
从出租车公司辞职后,常川在打短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下,只能靠救济金生活。因为没人认领,常川的遗体最后被送到新泻的一所大学医院供实习生解剖。
循着线索的记者前往石川县常川善治前妻家,刚一开口“常川君过世了……”,前妻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啊?真的?”接着记者告诉她常川遗体的情况,前妻依然话中带刺:“啊——没有人去认领?哎呀!幸好没有来找我。”
常川的舅舅高山说,自己多年来跟他没什么来往。常川和高山是不同的姓,“如果出点钱什么的,我还能照办;可是连骨灰也让我领走,那可就难办了……现在他恐怕已经是没人管的孤魂野鬼了吧。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住在富山县的常川的哥哥,说起来则更加“寥落”:“我跟弟弟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我现在也有老婆孩子,自己家的生活已经很够呛了,所以才会请求把弟弟埋葬到医院的无名死者墓地去。”
说到这里,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要用“人情冷漠”来定义日本的亲情关系。且慢!外交学院的娄雨婷指出,家意识淡薄正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不像中国那样根据族谱追溯同宗同源,日本家庭一般只供奉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即使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字迹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也不会再刻写,三代以上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遗忘。
“情义最难接受”,是日本一句俗话,这其中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对涉及情义的语言已经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所带来的“义务”。
“命若垃圾”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根据世卫组织2013年的统计,日本女性平均寿命达到86岁,男性为79岁。
近年来,既不搞灵前守夜,也没有家中的告别仪式,只经过遗体火化就算追悼过死者的“直送火葬”在日本悄悄兴起。
据分析,“高龄化”“长寿化”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大原因。活得越长,熟人中先离世的也越多。以前存在过的邻里交往和血亲关系,因为隔代原因而中断,以致举行丧礼,这些人也不会来参加。硬把人召集到一起举行葬礼,无论对逝者家人还是周围的人,都不啻为一种“麻烦”。这种观念正在日本社会普及。
此外,“无缘死”现象还催生了一个新行业——“特殊清扫业”。他们受托于区县政府,专门代替家属整理遗物。
在东京都设有办事处的一家特殊清扫公司向NHK介绍,他们一年能收到300多个清扫委托。死者去世的住处被称为“工地”。
虽然他们的工作要尽可能保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和心态,可是碰上那种声称“十多年没有来往,无法认领”的甥侄亲属,清扫人员心里也会“愤愤不平”。“以前那种骨肉情,越来越淡薄,不起作用了。”
在东京都品川的某套公寓,一对老夫妇死后,独自住在这里的儿子因欠下债务失踪了,房子成了拍卖对象,连老夫妇的骨灰都被遗弃在房间里。
特殊清扫人员把骨灰盒轻轻放进了纸板箱,他们要把它快递到寺庙。然而,在“寄件品名”栏里,写的却是“陶器一個”。看到这四个字,NHK的记者板仓弘政难掩心中的不平。
“这些骨灰以后会怎么样?”板仓问道。
“就跟垃圾差不多吧。”清扫公司的员工回答。
被亲戚和外人视若草芥的遗物,却得到了毫无关联的方外之所的悉心对待。
在富山县的高冈大法寺,僧人戴着白色口罩和手套,将东京这对老夫妇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祭坛上,为他们诵经祈福,一脸恭敬和肃穆。
这里寄存了100多盒从东京、神奈川、千叶等地送来的无人认领的骨灰。寺院住持将一格一格盛放骨灰的地方称为“公寓坟墓”。
像短尾嗣一样潜伏在社会最底层
“我几乎没有亲戚来往,也没有深交的朋友,只要不结婚的话,‘无缘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35岁的筒井隆次一边从电视里收看《无缘社会》,一边发出推特。像他这样,在电脑公司工作,因为劳累患上抑郁症或其他疾病,之后无法继续工作的状况,在日本年轻人当中比比皆是。
日本学者、《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一书作者近藤大介回忆,在他的青年时代,没有的只是地位,年轻的精力和能量是无窮无尽的。当时身处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人们都天真地相信“世界是我的所有物”,每天过着嬉笑怒骂的多彩生活,正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然而如今东京的街道,只有安静、干净和“成熟”。就连夜里结伴去过夜生活的年轻人,也减少了许多。
据估算,四五年前,日本1500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中,六成已被退休的老年人持有。2011年,日本老年人消费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占全国个人消费额的44%。从7-Eleven到百货商场,商家都将销售重点放在了白发苍苍的婆婆、爷爷们身上。
与此相比,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每个月只能拿到20万~25万日元的工资(税前)。而且20多年来,几无变化。
这与日本“消失的20年”有很大关系。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银行体系遭到打击,而政府没有及时采取紧缩政策。至今,日本都一蹶不振。
曾旅居日本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南指出,十年前,每个退休的老人都有四个上班族来供养,而如今只有两个人来供养,这势必加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情况。如果日本的上班族不能承担此重担,日本将无法支付老年人退休金和兑现医保承诺。为防止财政破产,日本政府选择的缓解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延长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鼓励老年人趁着身体还硬朗,继续工作,多赚钱。但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有可能带来恶性循环: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更少。
在东京的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可以看到《高龄者雇用安定法》的宣传海报。对此,你若知晓全日本的麦当劳雇佣了40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这一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52岁的NHK研究员山田贤一说,他80岁的老母亲虽然早就备足存款,做好了去养老院的准备,但她现在还在家中教授他人珠算课程,毫无懈怠之意。
在每天早上吃的油条分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日本年轻人的就业野心,早已沦落到如何维持“岌岌可危的地位”和“少得可怜的存款”这么简单。
被称为“草食系”的他们非常安静、认真,工作完成得很好,但是他们身上没有惊喜,没有任何可期待的附加价值。
当近藤带着年轻同事去法国餐厅用餐,他们的脸上不会有喜悦之色,而是一副“真是浪费啊”的表情。而当近藤将他们带去只有200日元一杯的扎啤可点的廉价居酒屋,他们终于表现出了“如鱼得水的愉悦欣喜”。
根据学者的观察,“如今日本社会活跃的都是年过五旬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则像短尾嗣一样潜伏在社会的最底层。”
这是时代流转的节奏,还是社会停滞甚至倒退的悲哀?
“最小不幸”与“结缘社会”
有人说,NHK的纪录片,也打开了老龄化日本社会潘多拉的魔盒。骗领父母亲养老金的案件,得以曝光。而因为常年劳累和看护导致的失业,最终弑父弑母的事件,近年也呈增长趋势。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提出“建设最小不幸社会”,在应对老龄化和诸多社会问题上,日本已经不再去追求光辉目标了,而是更加的务实:建托儿所或者养老院,让血缘关系淡薄的家庭能够少一点负担;向农村发放更多的补助金,让无助的地方社会有点活力;通过减税等措施,让企业尽可能雇佣一些劳动力为国家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成了日本政治中让“不幸”减少到“最小”的唯一指向。
2000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看护保险制度”。到了八九十岁也要和家人一起生活,这样的想法已被证明只是幻想。现实情况是,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支撑老年人生活的人群,会是朋友、旧识,以及能够信赖的福利护理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护理保险制度是老龄人群能够度过丰富老年生活的“救世主”。
在政府的措施之外,NPO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和歌山县的白滨海岸,大海湛蓝,风景迷人。那里却也是日本自杀的高发地之一。
NPO白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海边巡逻,劝阻那些意图结束生命的人们。小镇的教堂留下了十多位被救助者。他们白天一起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活计,晚上则留宿教堂,在那里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联接,以实现“牵绊再造”。
河上勉正是其中一位。到达白滨站的半年里,他天天早晨从教堂附近的豆腐店的桶里舀走豆腐渣,装进自带的大圆钵里。“有了这个,就能做400块饼干啦。”河上在化开的黄油里和进面粉和豆腐渣,使足浑身的劲用力揉,额头上渗出汗珠。
在来白滨之前,他却是和家庭与社会双双“失联”的落魄者。因为一心扑在制造公司的销售工作上,过度劳累导致病倒,既丢了工作,又跟妻子离了婚。这样的结果,让河上曾经有过轻生之念。
“豆腐渣本身上不了台面,这和我们这些被社会淘汰下来的失联人正好相像。如果能把豆腐渣变成大家都喜欢吃的饼干……”说到这里,河上勉忽然停住,接着坚定地说道:
“豆腐渣,要是你也被人扔掉了的话,我会让你再活过来的!”
以这样的信念,河上在几个月之后,已经能够去劝慰和勉励后来加入的失意者了。
从东京与和歌山再反观中国,情况似乎和1990年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高度依赖出口,内需市场难以扩大,代际间和城乡间的“失联”也日趋明显。
“再过10年、20年,中国也会一样。独生子女和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会日益严重。中国需要对‘无缘社会这个问题早些作出准备,要注意啊!”NHK研究员山田说。
(摘编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