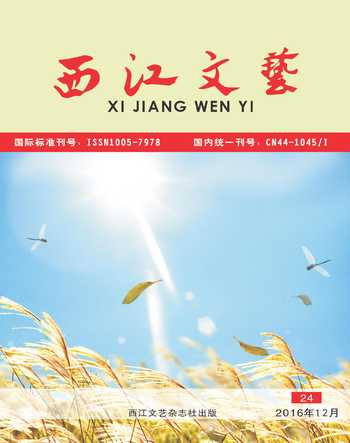“河流场域”中的民族浮沉
马文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书写鄂温克族群在百年变迁中逐步走向倾颓的文学史诗。小说采用了独特传神的叙事策略,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河流场域”,洞见“我”所在的“乌力楞”独特的原始文化品格和族人质朴本真的道德哲学,是一部兼备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上乘之作。
【关键词】:河流场;《额尔古纳河右岸》;族群;叙事策略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他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逐渐延展到文学领域,形成了独有的文学场域理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河流场域”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中以河流为定位和依存的社会网络空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建构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河流场域”。
小说采用了精湛的叙事策略,以第一人称叙述构建了“河流场域”这一独特的叙事空间,洞见“我”所在的“乌力楞”独特的原始文化品格和族人质朴本真的道德哲学,“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一、精巧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书写我国东北地区鄂温克族生活图景和百年变迁的文学史诗。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往往需要采用全知全能视角,以期“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迟子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见微知著,以“小视野”影射“大历史”,让年逾九旬的这一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描摹其所在的“乌力楞”原始狩猎生活的古老文化模态和日常风俗画面,从而向世人诉说鄂温克族的生死传奇和兴衰浮沉。
迟子建作为一位汉族作家,“汉写民”很容易带有“他者”烙印,而第一人称叙事天然带有增强故事真实感的功用,她在小说中巧用匠心,采用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合二为一的叙述视角,将读者的视线聚焦到显性叙述者“我”的身上。“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小说通篇都以“我”所见所闻所感为叙事中心,站在“我”所在的民族的立场洞彻本民族的百年沧桑。在某种程度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看做是对鄂温克族历史最有发言权的“我”的“独语体”自传。“我”在空旷的营地将自己从出生到九十岁期间的生活阅历和民族的兴衰往事徐徐道来,使得“说”和“看”之间形成平等的姿态,于无形中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文化隔膜给作品带来的不利因素。
毋庸置疑,限知视角可以让读者葆有充分的想象空间,提升文本的审美张力,但是迟子建并没有满足于私语化的“讲述”,她极力凸显叙述者“我”与被叙述者“我”之间的区别与分化,即叙述者和被叙述者虽然具有同一性,但却是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的不同的“我”: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回忆的“我”,一个是作为叙述主角的经验的“我”。例如,在《清晨》这一部分,迟子建灵巧运用儿童视角,以童年的“我”的视角关照“我”身处的“乌力楞”(部落),体察族人们赖以生存的“河流场域”。“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殊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就在这样的风声中,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久,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这个“我”不是从现时的距离回溯往事的回忆的“我”,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彼情彼景的天真烂漫的经验的“我”。纯粹干净的的儿童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第一部分《清晨》处在清澈浪漫的氛围中,展现出回忆的“我”与经验的“我”之间的叙事张力。
《额尔古纳河右岸》带有明显的“族群史”乃至“民族史”意味,但是遲子建独辟蹊径,将女性第一人称“私语化”叙事与再现相对封闭的“河流场域”中民族浮沉往事有机结合,形成了柔美浪漫与悲壮悠远有机统一的审美趣味。总的来说,迟子建以“小历史”展望“大历史”是一次勇敢的“冒险”,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古朴本真的道德叙事
所谓道德叙事,就是存在于道德实践中的叙事现象,是叙事手段和道德伦理的有机结合。《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温暖又不失节制的笔触描绘了鄂温克族顺应天命的独特生活图景,映刻出鄂温克族人古朴本真的生命哲学。迟子建全身心地融入到这一独特的“河流场域”之中,以“亲历”的方式用熨帖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描述出族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于无形中体悟到生命的厚重与无奈。“额尔古纳河右岸”是鄂温克族赖以生存的相对封闭的场域,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河流场”拥有独特的道德伦理。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余华的《活着》拥有某些相似之处,源源不断的死亡,麻木又沉重。但是,与《活着》不同的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生死观透露出深远的“宿命论”色彩,同时也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的道德命题。妮浩萨满每救治一条生命就会失去一个孩子,哪怕是未出生的胎儿。马粪包是个口无遮拦的酒鬼,对女儿柳莎粗暴,对酋长瓦罗加也不恭敬,他在吃熊肉時无视氏族的禁忌,结果“报应”般地被熊骨卡住了喉咙。只有作为萨满的妮浩可以救气若游丝的马粪包,但是,救马粪包意味着要以她心爱的女儿交库托坎“一命换一命”,然而妮浩仍旧披挂上了比大山还要沉重的神衣。最终,马粪包得救了,妮浩的女儿被马蜂蜇伤,毒发身亡了。马粪包是氏族“臭名昭著”的“败类”,妮浩依然要救他,哪怕失去自己可爱的女儿。“一命换一命”是一个尖锐的道德命题,妮浩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次道德选择,这也昭示着,这个独特“河流场”拥有其独特的生命伦理和道德理念,即无论谁的生命遭遇威胁,都要一视同仁,义无反顾地救助,这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在有形无形地逐渐将鄂温克族的原生态文明吞并融合,“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一独特“河流场”受到不可修复的侵袭和损害。玛克辛姆在妮浩萨满走后的第三年开始出现一些预示着即将成为萨满的怪异举动,但是族人却竭尽全力让他“与那股神秘而苍凉的气息隔绝”,使得他又逐渐正常了起来。萨满文化是鄂温克族的信仰,阻止萨满的形成预示着鄂温克族群伦理的没落。“木林因砍伐过度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山风却越来越大”,“激流乡现在已是一座空城”,整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其他的族人们都选择下山定居,住进“白墙红顶的房子”,将驯鹿圈养到用铁丝网拦起的鹿圈里,至此,族群伦理已然彻底失效。
三、神秘野性的原始文化书写
“野性”原指“野蛮”之意,用以诟病原始部落族群落后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变迁,文明开化,“野性”逐渐衍变“成为一种自然原始和社会性的力量,其目标直指现代性及其思维、生活方式”,旨在展现出最质朴的人性和最原始的生命形态。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简约生动的笔触书写了鄂温克族充满神秘和野性气息的原始文化图景,为这个行将就木的民族文化形态刻碑立传。她贴切地展示了鄂温克族真实、原始的世俗生活长卷——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繁衍生息着一个以“乌力楞”为群居单元的鄂温克族,他们住在用松木搭建的“希楞柱”里,以狩猎为生,信奉“玛鲁”神,靠萨满“跳神”来驱除病魔,呈现出超然旷达的生存姿态。
迟子建是一位植根于東北边陲自然野性的作家,《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弥散着“万物有灵”这一神秘悠远的远古浪漫气息。“万物有灵观”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的学说,他将灵魂客观化、对象化,并延伸到其他事物身上,认为世间万物如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和人类一样拥有灵魂和意志。鄂温克族崇拜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赋予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和奇诡变换的自然景象以主观意志,山有“山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动物也皆有灵性,族人们恪守信仰,虔诚奉行本民族的自然崇拜意识。例如,“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不但要给他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来磕头,企求山神保佑。如果猎获了野兽,还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这神像之上。”另外,鄂温克人对“火”有着天然的崇拜,“不能往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小说中还提到了族人们对于动物尤其是熊的崇拜,所以在吃熊肉时有诸多禁忌,“马粪包”就因为吃熊肉时出言不逊而遭到“报应”,险些毙命。
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并在独立的“河流场域”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萨满文化。萨满被视为“宗教的使者”,他将神的意志传达给族人,也将族人的祈愿诉诸于神灵。在小说中,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书写萨满文化的重要线索,他们尽职尽责,依靠“神力”为族人超度亡灵,治病救灾,祈愿丰收等。小说中极尽笔力塑造了妮浩萨满这一极具悲剧意义和崇高品格的形象,尽管她早就预感到救活何宝林的儿子就要牺牲自己的孩子果格力,但是她依然义无反顾地救治病患。此后,她又相继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救活了“马粪包”和偷驯鹿的少年,最后甚至为了祈雨救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小我”的“大爱”精神是萨满文化的鲜明写照。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话语语境下,迟子建独辟蹊径,将写作眼光放置到鄂温克民族的纵深地带,多角度、多層次、多侧面地观察和表现了鄂温克族人原始、野性的繁杂日常,并进行了执着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成为鄂温克族的民族标识。与此同时,小说中浸润着鄂温克民族的悠久的远古气息和虔诚的萨满文化,交织成神秘野性的原始文化风味,从而赋予这片独特的“河流场域”以浓厚的原始文化底蕴。
总之,迟子建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展示了鄂温克族百年变迁的历史进程,也蕴含了对于原始民族文化倾颓的悲悯和感怀。我国当代民间文艺家冯骥才曾断言:“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传承人的传衍。……如果其中一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失;如果它们大批地中断,就会大片地消亡。”迟子建本人在谈及《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也曾提到:“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因此,小说在竭力关照鄂温克民族的百年浮沉历史的同时,也隐含着对于这一原始文明失落的叹息,和对人类文明进程与民族倾颓之间的冲突的拷问与思考。另外,小说也通过建构独特的“河流场域”传达出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反观文明,反思存在,为当下浮躁的“现代人”找到精神回归的道路,使其看到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弊病和症结之所在,以期在后续的发展中得以缓和与平衡。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译者.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张惠林著.人性关怀与审美观照 当代文学论札[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
[4]杨义著.杨义文存 第1卷 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