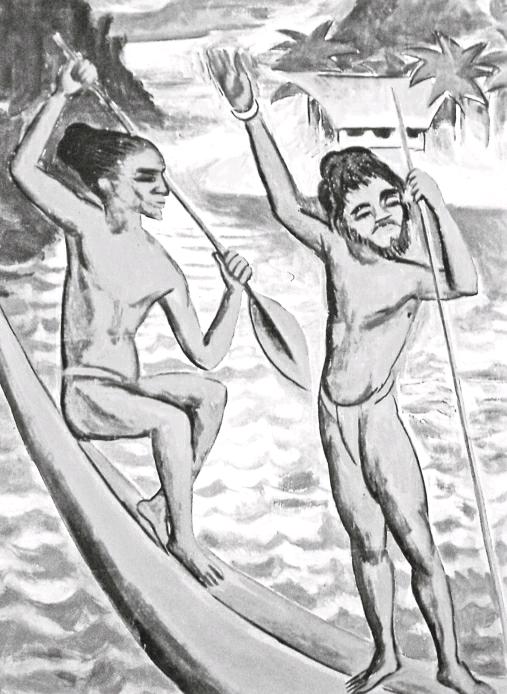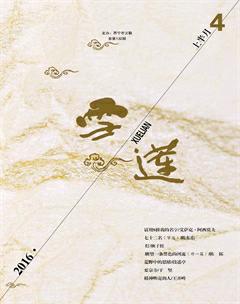文学和记忆
伊凡·克里玛
我经常被问及正在写什么,但是至今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
1
过去常常把写下的东西都认为是文学。李维、塔西佗,同样还有西塞罗和维吉尔,都简单地被认作文学创造者。我们将圣经称作“书中之书”,于其中我们发现和神话故事并列的有仪式规定、历史记事、箴言集锦、法律条文及爱情诗。许多古代和中世纪关于法律、医药、地理、数学等学科的书都是用韵文写成的。在它们当中,幻想的成分超过事实本身,今天我们更宁愿将其当作文学来读而不是考虑它们在科学上的优点。只有在现在,我们才开始考虑一门技术性的、最特殊的写作,将其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我们怎样把每天淹没读者的洪水般的垃圾进行分类?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精确界线在哪里?当然,有着许多种分界线和定义,其中大多涉及作品形式上或美学上的特点。从形式上定义文学的尝试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定义中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也许能将科学著作从艺术著作中划分出来,但是忽略了内容因素,而通过内容,将真正的艺术从仅仅是娱乐中划分出来的一系列品质才显露出来。更有甚者,结构主义对作品于社会的冲击毫无兴趣。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引起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关注,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愿意尽可能精确地定义我所以从事的活动的原因和意义。
两百年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询问了同样的问题,他试图区分科学和艺术(艺术是在自由状态下的创造)以及艺术和手工艺(在一种杰出的区分中,他将艺术定义为从中受益的)。康德当然意识到一部作品美学品质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创作者本人的作用赋予了密切的注意,或者,用他的术语来说,如果没有天才,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将不可能产生。我并不想分析康德关于创造者现象或他的活动的定义,但是,他发现若不考虑到创造者本人的素质,他的思想及动机,便不能真正理解一部艺术(并且因此是文学)的本质,这是非常关键的。
2
这使我返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上来:我为什么写作?尽管这个问题很少被问及,但其答案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这里,仅举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谈促使他写作的因素为例:
“在我们内部,有着层层叠叠的黑暗——喧闹的声响,多毛的、饥渴的野兽。那么,没有什么东西死去吗?难道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死去?那些原生的饥渴和忧伤,在人类黎明到来之前的那些夜晚和月光,将继续存活;那些饥渴和苦恼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我曾经惊恐地听见我所承载的可怕的负担在我的内脏中开始吼叫。我将永远不能得救吗?……说到底,我是最小的和最受钟爱的孙子,除了我以外,他们(我的祖先)没有指望和庇护。所有他们遗留下来的复仇、享受和受苦,只有通过我们才能继续。如果我消亡了,他们也将跟着我消亡……”
这个充满感情的自白以同样充满感情的作家使命的展望而结束:
“我知道我的真实面貌和我灵魂的责任:尽可能富有耐心、充满爱意及运用我所能掌握的技巧,将这个面貌描绘出来。去‘描绘它?那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将这一切大白于世。因此卡伦从我这里什么也拿不走。这就是我最大的野心:什么也不让死亡带走——除了一点骨头什么也拿不走。”(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向希腊人报告》,第26页,布鲁诺·卡西勒出版社,牛津,1965年)
当我最初读到这一段时,我惊讶于卡赞扎基斯如此接近于我对为什么要写作和在写作中我期待什么的答案。我记得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我的感受如何:在一个集中营里我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几乎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的同代人和我的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人——都死去时,我却幸存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赋予了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他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种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感情促使我去写作,而我当然没有想要去遏制写作、创造故事和寻找最好的方式向别人转述我想说的东西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3
变成别人的声音这种令我振奋的感情,以不同的形式在其他时机再现于我的生活之中。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这种感情为大多数写作的作家所拥有,在不自由的条件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只活了不长时间。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引用米兰·昆德拉在 《笑忘录》里的一段话说:“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另外有人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在同一本书中昆德拉发明了一个短语并启发了我:“遗忘的总统。”一个在“遗忘的总统”引导下的民族将走向死亡。而适用于一个民族的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成员。
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死亡不再是每一件事情结局的情感,是基本的生存情感之一。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回到卡赞扎基斯充满情感的自白,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创造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这种确信必然成为创造者当下的头脑状态: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忽略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创造这种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沉思创造的意义、价值和真实性的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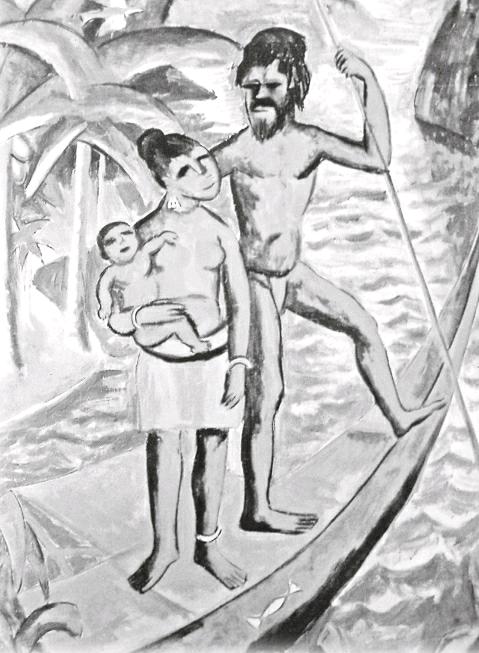
战争结束之后,我却并没有从一个幸存者的角度写出关于战争和集中营的经验,实际上关于那些事情我几乎没有动笔。记忆并不仅仅通过对某一种特定经验的如实报道来体现,而毋宁说它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产生于对过去曾经降临又离开的每一件事情延续性的意识,是对于如果我们不想在真空中消失便不能遗忘的那些东西的责任。我们正在经验文明加速度的感觉,包围在我们身边丰富的信息及其喧嚣同时带来危险,我们将要在它的空洞中走向结局,我们将断绝和根的联系,陷入无尽时间和虚无。同样的危险威胁着文学和所有的艺术。在现代历史的某个时刻,对许多人来说,似乎记忆和传统仅仅是一个必须加以抛弃的负担。在我们这个世纪降临于人类的灾难由这样一种艺术提供帮助,它推崇原创性、变化、无责任感、先锋派,它嘲笑所有以往的传统和蔑视在画廊和剧院的观众听众,它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愉悦冲击渎者,而不是对那些拷问人的问题提出解答。出现在这期间的极权主义制度将先锋派文学视为颓废而加以抵制,这无关紧要,然而基本上它也像先锋派一样轻视传统和传统价值以及真正的人类记忆,接着便试图强加给文学一种假冒的记忆和虚假的价值。
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本新书问世。它们中的大多数将是使得我们失去听觉的那种欺骗的一部分。这种书甚至变成遗忘的工具。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也笼罩于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一部文学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