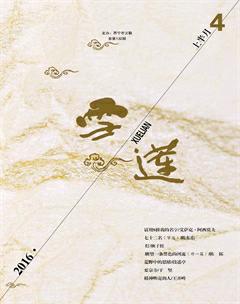七十二名(节选)
陈东东
词
词是飞翔的石头,黑暗嗓音里闪烁的天体。它的运行带来方向,它的吸引力以及拒斥构成了距离,而它那听从内心呼唤的自转则创造时光。每个词独立、完满,却又是种子、元素、春天和马赛克,是无限宇宙里有限的命运。正当冬日白昼,正当我躺在朝南的斜坡,我的目力穿透光芒,能看到语言夜景里不同的物质:感叹如流星划过,数字的慧星呼啸,一个形容仿佛月亮,清辉洒向动之行星……名:太阳。名近于永恒,燃烧又普照,以引擎的方式提供血流和热力给语言。在名之下,有了期待、成长和老去,有了回忆、悔悟和死难,有了四季、轮回、重临和不复返,有了旧梦,新雪,有了生活和妄想拥抱虚无的生命……
海
海被我置于当前。海不是背景,而是我诗的心脏。活着的心脏优先于灵魂。我同意一个说法:“海没有阴影。”海这个字眼也不被阴影遮覆。海总是在我的上方,倾斜、透澈、明亮、静穆。我所知对海最好的比喻,是瓦莱里写下的“平静的房顶”。海一样的房顶在中国的深宅大院里时常能见到:由一爿爿精细的青瓦编成的广大缓坡,檐上有想象的动物——麒麟、人面兽和鼓眼的蟾蜍,檐下有金属铃铛,还会有象牙鸟笼。处身或回忆、梦想那些远离大海的旧建筑,我一再听到过潮音的节奏,如同沉冥中蓝色的心跳。然而,海是父性的。海匆忙繁盛,一切荣耀归其所有。海比天气更多变化,比大地有着更多物产。海是父性的。海容纳一切名,甚至太阳,太阳也升自海的天灵盖。海是父性的。被海的环状闹市区围拢,逆死亡旋转的海盆体育场里巨人们骑着剃刀鲸争先。在绝对的中心,光辉的塔楼如一枚鱼骨,使世界的咽喉充血,几乎刺穿了嘶声一片。那光辉的塔楼里一双神圣的手正打开,放送真理的白腰雨燕。对于诗,海的名声如此——不是诗的躯体包藏海之心,而是海这颗心脏涌流着诗。
湖
如同一面能剔除阴郁和浑浊的宝镜,湖映给诗篇分明的四季,星辰良夜,晴朗的日子,人鸟俱寂的降雪之晨,越来越明亮的黄昏的雨……湖提供给诗人这样的修辞:平静、安逸、澄澈、开阔、闲适、舒缓、清和、散淡……它也提供了这样的物产:菱藕、荷花、芦苇、青萍、螃蟹、鱼虾、珠蚌、鸥鹭……以及这样的景观和倒影:碧绿的山色、火红的落日、隔岸的杨柳、水中的云霓、月下孤舟、雾里亭台、正午的光芒间争航的楼船……莲女和渔夫、渡叟和钓翁、志士、隐者、琴师、高手、墨客、僧侣、看风景的和饮花酒的……这些老式人物则出没于湖上,增添对旧时代的怀恋之情——这就是名之湖,书面的湖,泛黄纸张之间的湖,汉字围拢的绝对的湖。它或许是我颓废的内生活,脱离开时间的静止的美,想象力朝向遗忘的坍塌。
书
我妄想过关于书的百科全书,即在一种书里包容下所有既有的书、将有的书、可能的书和梦幻的书。它构成真正的彼岸世界。它来自这个世界的思想之子宫、语言之子宫、野心之子宫和恐惧之子宫。它的一半是迷乱的镜像:无限繁殖自身的虚构,歪曲地反映母亲的形象。它的另一半,是开口说话的永恒的坟场,是它母亲的最后居留地。词是秩序,词也是路径,词就是彼岸世界的完整肉体。词是,那关于书的百科全书的三位一体。奇异的是,这彼岸世界可以被无数次复制、毁坏、放大、缩小、节选、加注、精装、简装、携带、丢失、赠送、转让、抵押和遗忘。它可能在印刷术、统计学、目录编排、系统索引、电脑程序和激光数码之中诞生,但它也可能出自一个抄写员之手,出自一个要把世界的纸张全部用尽,以实践童年妄想的老诗人之手。
纸
纸的命运仿佛写印者。它来自一些琐屑的物质:桑皮、碎网、废麻和破布;但它也来自林涛和竹影,来自几种火焰、沸水和大机器,来自鸟鸣、风动、日照和结霜成花的拂晓。它也来自它自身,当它被再生,一个写印者知道,那墨迹未干的文字里,哪些是他的前辈先贤老调被新唱。纸张递送出去,写印者经历危险的旅行。纸张保存下来,写印者循环于同一个大梦。一线月光掠过纸张,写印者醒来,在另外的时空里以空白重新书写另一生。更多的纸张会遗失、丢弃、撕碎、焚毁。纸张太多,不值得珍惜。集体反复的众口一辞或许的确是必要的浪费。纸币改变纸的命运、写印者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命运。纸币的命运是银行祭起的神之命运。为了说明这种不同寻常的非人命运,写印者在规定的特异纸张上烙下过被奉为圣明的奇怪人像。这人像显露于纸的表皮,它更深刻地隐现于纸的内部纹理,偷换纸和写印者的骨头、血液和心。
梦
太多的想象力分给它一副呼吸器官。它从疲乏中独立出来,它刚有了系统的蓝色血脉,又攫取一颗狮子的心。它却以一个人形出现在窗口,以鹰的姿态缓慢地起飞,穿透玻璃,掠过庭院里孤寂的树冠,进入另一间睡眠的卧室。它几乎点破钟敲数下时色情的幻想——以一根钢针的锐利,刺探又一个自水底上升的菲红气泡。在诗篇里,甚至在生活中,它已经不再是一次释放,它对于我肯定是一种必然,是命运之车的钢轨,是写作之河的闸门。但它更进一步,它是一种自由,一条进入我体内的生命,一个掌握时间的火车司机,一个调节嗓音的扳道岔工人,一个迫令诗歌长出了翅膀和一对鹰眼的绝对的王者。它持续到死,它贯穿每一个滴血的字眼,它彩虹的骨架,结构每一本狂妄之书。它置换我的呼吸和心跳,它以只能被名之为梦的方式,刺杀因它而深陷进睡眠的做梦的我。
火
火是人类欲望的起点,火也是人类欲望的终极。它破除人的原始禁忌:星球背向太阳的黑暗,睡梦步入恐惧的黑暗,记忆抵达遗忘的黑暗和生命化作死亡的黑暗。人的白昼由火打开,生活在它的光焰之上迅速蔓延,成为存在的伟大主题。从七千年常明的神圣的火中,人类提炼出元素中最为本质的元素——反自然的精神也终于以火的方式流动于血脉,张扬自我中心的人之命运。反自然精神照耀人类的进化和进步,文明和发明,并一再点燃人之为人的热烈的欲火。语言之欲火,狩猎之欲火,劫掠之欲火和创造之欲火,以及祭祀、求告、收获、节庆、征服、毁灭、思乡、远离、建设、玄想、宗教、艺术、竞技、智慧、算计和无限占有金钱之欲火。甚至爱情和性行为也被反自然的火光照耀,成为更深意义上的相互毁灭。从人之欲望的崇高立场,古希腊哲人论证了普罗米修斯盗火的英雄性。但是在多少年后的一个秋天,在两重大海以外的大陆上,有一个诗人却想以一种懊悔的节奏,重写这关于火的反自然故事。
水
水是这个世界的感性,其形态正如人们所见,是云雾、雨雪、湖海江河以及坚冰。水之感性甚至以无形态的形态充沛,在这个世界,在人们体内。作为原初之物,水有如诞生,生命起源于这个世界的感性之中;作为浇淋之物,水有如洗礼,万有人性和神性显露于感性洁净的表面;而作为湮没之物,水有如毁灭和再造,用感性抹煞现实并让新的感性理想般现身。水作为女人体,则几乎是火焰,是感性中完美的直觉和过敏。太阳理性调节水元素,也调节身体对水的渴意和对水的排斥。但太阳光谱却正因为水而被人们发现。在霓虹和冰棱里,理性之光由于感性而分解成七色,并且不再冷静、公平和均等。在被水过滤的阳光底下,明黄如此盛大,如女性中永恒的男性因素。
树
树跟书的谐音,向我提供了树作为文明进程航船之桅杆的又一个证据。如果没有树,风帆之页将怎么打开,去兜满神的吹息和推动力?在来源于树的众多书籍里,在从桦皮到木简到雕版到纸张的众多言说里,我读到进化论,它告诉我人如何从树上下来,站直了身子;我读到创世纪,它告诉我人如何摘取树的苦涩果实,睁开了双眼;我读到经济史,它告诉我人如何自树取火,养育了光明;我读到圣人传,它告诉我人如何独坐于树下,彻悟了大道;我读到植物学,它告诉我树如何释放出珍贵的氧气,保证人的呼吸和生命……而在一本促使我写下这节文字的美好的书中,我读到对树这样的赞誉:“我们人生的树,我们知识的树,是一棵神异的树,这样地迷人,竟使人不知道怎样来描写它。它是木材所造,它从石上生长;它是那给我们以笔的禽鸟的巢;它荫蔽那给我们以柔皮的动物。而且在它下面,一切生物的伴侣,即人类,读着书,想着思想。”(《世界文学故事》)——从树上下来,人走向书;从书中返回,人走向树。
风
风是空气的语言,风要说出的,是人们无视的空气之存在,正如人们运用语言,说出大地之上人们的存在。风不可索解,空气的语言灵动、变幻、轻易转向、无从捕捉、柔韧、弯曲、飘逸、迅疾而猛烈,其象征性有时并不像诗人们以为的那样。风作为语言令诗人向往,但又有哪个诗人可以拥有一整套完美的风之语言呢?惠特曼有几缕如风的诗行,李白有更多风的品质,其余的诗人只能用诗篇去歌咏清风。风推动世界旋转,给予物质抒情的可能性。风使得仿佛空气般被人们无视者得以吹息。这吹息年轻而俊美,如波斯一本旧经书所言:“最后,创造了外形像十五岁少年的风,它支持水、植物、牲畜、正直的人和万物。”
蓝
蓝近乎精神,天空和大海近乎精神。但就像天空和大海可能是一种虚无一样,蓝也是虚无,有如精神相对于肉身的虚无精神性。涂抹到我诗篇之上的蓝,却常常是从名直到物质的蓝,其精神和虚无的内涵及象征,被括入括弧,或被注入一只朝圣雀鸟用鸣啭缕空的声音花瓶。在我的诗里,蓝总是缩小其范围,使天空成为梦的一角,使大海成为完满的鱼形,使忧郁——这蓝的又一个指代词——成为一滴贵族之血的精液,滴入南方的爱情子宫。我相信,蓝无法把握。当它是名,而又是物质的时候,其物理(光学)的魔性,会令它在诗行里改变诗的音乐和物质性。一首诗因它变得更蓝,变得玄奥、纯粹、精确和无穷。那括弧里的象征,那从声音花瓶里长出的精神,总是在蓝以虚无笼罩诗篇时完成了诗篇。
光
作力主题,光贯穿人类生活及其历史,它更为明确地(仿佛大海体内循环的洋流)贯穿诗歌及其历史。这个名的魔力几乎就是它提示之物的全部魔力,令眼睛看见,赋予字眼、词语、诗行以轮廓线、清晰度、面积、体量和质感。它甚至使诗篇透澈发亮,成为钻石、星辰和灯盏,成为眩晕的根本原因。所以——我想说——诗歌写作近乎一个魔法师企图去展现光之魔力,它也是(越来越是)这光的魔法师对于光芒的猜测、试探、分析、把握和究尽。写作者滑翔在绝对虚无的光之表面,其规定动作和自选花式带来华彩。写作者更深入,他激情和修辞的三棱镜把光芒谱成七彩和更多的颜色。他也许有名之为《光谱》的叙事诗杀青;他还可以再进一步吗?他抵达光的反面,以内视和内敛触及了光的物理极限。在那里,沉默构成黑暗之诗,通常被一位盲诗人说出。
灯
在汉语里,灯的光芒首先来自它的语音。灯——当舌尖触碰上颚,弹出—个清脆之声,语言被突然点亮,词句聚于光晕圈中,阅读之眼几乎盈泪。灯成为汉语里比喻诗歌的天然之名,其寓意也像诗歌一样不言自明。灯——自明,并且把其余的也都照亮;正如诗歌自在,并且证明人的存在。在一盏灯的古典形式里,有石头体液,有植物精华,有一枚火焰,有摇曳更助长其光芒的风,有一只维护的手,有自由殉身的飞蛾和因为被吸引而改变了黑暗性质的黑暗。有时候,我们说,这就是灯盏。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如同灯盏的语言、诗,或一个通体光明的诗人。
尺
它很少以一个具体之名出现于诗行,但它却肯定出现在每一诗行,每一诗篇和所有的诗里。尺是一种灵魂规则,写作的白金法律。尺的不可磨损,正是诗歌理想的不可磨损。尺量出诗艺的程度,跟秤一起,赋予诗篇以“重量、形状和大小”。我把抄录在一本笔记簿里的一段话抄录于此,代替尺说出尺对于每一位诗人的意义——那其实是对人类的意义——“尺象征完善。假如没有尺,技艺便成了瞎碰的玩意儿,艺术便有缺陷,科学便不能自圆其说,逻辑将变得任意和盲目,法律将变得武断专横,音乐将不协调,哲学将成为晦涩难懂的玄学,所有的科学将变得无法明白。”
箭
箭总被用作时间的比喻,然而,箭表现为对由生到死的生命时刻的一次性度量。箭既是命运之弓射出的生命,又是立即射穿这生命的死亡,箭也是,以一声压低的呼啸为全部内容的生命速度。箭也是死亡的速度。箭的这种三位一体,被诗人在前述的比喻中以时间二字顺带着总结了。这一总结是回避性的,故意偏差,企图躲过过于逼人的箭之锋芒——把箭用作时间的比喻,固然也有生命短暂的感伤意味,但却掩盖了命运以箭直取生命,直抵死亡的直截、急疾、严酷和准确。命运之箭百发百中,不可能射失。这箭即是发箭之弓,这箭也是那箭靶本身,这箭还同时是弓与靶子之间的距离。
鱼
鱼是广泛的鲜血,它近于溢出的无限繁殖。它同样众多的纲科种属,足够证明浩淼丰富的创造激情和想象能力。当海被认作涌现诗歌的蓝色心脏,鱼类也同时被注入了作为诗篇的生命。阳光照耀的明净的水下,更多的,在阳光之鞭抽打不及的永恒黑暗的深水之中,鱼类低翔、翻飞,疾掠中划出完美的弧线,或于凝止间突然浮出,就像它同样会突然潜入另一鱼类的幽渺城堡。那靠着虹色细胞组成的异彩,令身体如一盏盏寒冷的灯,闪烁它诗篇的丰华和收敛之美。在有关鱼类的各种传闻里,我感兴趣的,是能够清晰地读出语言、文章、音乐、理想和命运字眼的这样的传闻:一条被放生入海的鱼如何开口说话许下诺言;一条被置于刀下的鱼如何吐出帛书引发革命;一条被星空梦见的鱼如何曼声歌唱点缀爱情;或,鱼如何抱定化龙的志向翻越巨澜;鱼如何变成遮天的大鸟飞进天池……这样的传闻令我欲删去反复写下的同一些词语。因为,我不知道,像“鱼的鳞片上显现出诗行”这样的句子,是否真出自我的构想。
鸟
人的愿望是一次回溯——人向往飞翔的伟大理想,体现在更早诞生的鸟类英姿里。甚至借助机械,靠着对风力的把握而使飞翔成为了现实,鸟类也仍然是人的理想。鸟的可能性,代表一个人心灵的可能。鸟的光洁羽翼、清澈鸣啭、轻盈体态和俯冲的激情,则成为一个人语言的猎物——他一生的努力,其实就是要把一闪即逝的鸟之身形,固定在诗歌深潭的水镜之中。于是,鹰指涉王者和广大的权力,凤鸟显现圣心和仁慈,夜莺造就浪漫的歌喉,鹧鸪是失落是愁绪是怀乡病。鸟类更成为选定的使者,传递人人之间的两地消息,也传递神对于人的残暴爱欲,令历史以蛋卵的方式现世,被孵化。人对于神的意识也总是借助于鸟类的形象——天使,带鸟翅的人形——超凡也就是人性被提升到飞鸟的高度。
蛇
在纸页间,蛇无法有效地展开身体。在我的诗里,蛇无法成为一个比喻、一个象征,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形象。蛇带给我恐惧、惊异、颤栗、过电,真正的被吸引以及迷失。它从性感灿烂的符号皮肤里一次次褪身,令我想到聚光灯下的脱衣舞女,最终不仅要返回蓝色乳房和过敏阴蒂的蜿蜒裸体,而且要呈现为一眼洞穴,洞穴深处的黑暗和黑暗尽头突然透出的乐园之光。正是在乐园,蛇的诱惑之美得以展示,代表物质智慧、肉身抽象和违背神意的语言的胜利。而在诗艺的范围里,蛇总是可以用来说明与精神无关的有毒一面,同时也是美丽的一面。繁复、交错、缠绕、环抱、诡谲、眩移和幻化,这些与蛇有关的词,也有关因为蛇而日臻华美的沉溺的文体。现在,当我毫无把握谈论起蛇(这个名),我想到的是一位以它为属性的写作中的女性。她的脸在化妆术精致的书写背后完全隐去了,她写下的每一行霓虹之诗,是刺在她背上的漂亮纹章和闪闪的鳞甲。她迷恋经籍里蛇用嘴关闭阴茎的说法。因而,很可能,她写下了与蛇有关的这则文字。
猫
此名常常从猫之躯壳里抽身离去……猫,它是一个两面象征,一个庸懒或矫健的身形,一个理想的色情主义者或禁欲与惩戒之兽。它可能是传统的九命妖物,也可能是直觉的死亡大使,它既神圣又难免邪恶,既与月经相关联又常常在叫春中化身为豹子。猫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容,就像它在真实世界里,并不以其名安身立命。猫之名可能只属于主人,就像其媚态、取悦性表演和恶作剧仅属于主人。在诗人那里,猫只是状语,一则逸闻,不堪时却变成腥酸的骚味儿。
马
马在众多的诗篇里丧失实体。马以身影的方式闪现,留传下来的却只有节奏。不是马的节奏,而是不羁的节奏、高蹈的节奏、冲刺的节奏、收拢心力的节奏、在速度中展现广板和柔板的节奏……那个以马为名的节奏。马已经被句子的黑夜没顶,被诗人的想象力催毁,被刺穿万物的阅读之眼忽视或删除。只有它千变万化的节奏,贯穿在诗歌史的血之航线。我严守与马有关的每一种写作规程。我谈论或歌唱马匹,只是想尽可能干净彻底把它镂空。而充沛其间的将会是不断来临的幻象,一个骑手的失败和失眠中灵魂的剧烈运动。“必须把运动和运动的结果这两者截然分开,”奥·勃里克说,“节奏是以特殊形式表现的运动。”
鹰
十字猛禽雄鹰,诗人在两方面展开歌咏,对应它高寒中一动不动的强劲翼翅。鹰是王者,因为能直视太阳感知智慧而又是大祭司,它的权力倾向于远离月轮的一重天,它的宗教则占有略微高一点的位置。它的形象总是强悍,伴随着威武、勇毅、严厉、敏锐、迅捷、神力和洞见。它的对手是两种女性,两种想象的羽翼神灵,是权力凤凰和宗教天使——“彼可取而代之”,这鸟中重瞳的项羽如是说——“张开翅膀的圣训”,那凝望着它的信徒领悟了。而诗人要继续展开诗篇,要让鹰的身形更加孤高、寂然、幽独和凝重。诗人用写下的《时光经》咏叹:“因为鹰,地上的石头开裂,划过宇宙意志的闪电。”
豹
豹是这样的生命:它的出世仅仅为了对应于夜色。这种对应,不仅表现在它那不可思议的闪耀的皮毛,还表现在它的各种现身方式:隐伏的、突然跃起的、激烈的奔走或深邃的静卧。透视之下,它星宿般繁多的美妙花斑向内深陷,被系于一颗蓝色的心——孤寂、忧郁、凶险、冷酷,就像当我们有能力掀开天空的皮肤,我们会见到的夜的神灵。有多少夜,就会有多少豹。有多少种夜,就会有多少种豹。我见过的最为典型的豹,一头在都市神话的火炬之下展开形体的雌金钱豹。它对应奢豪的金钱之夜,它高踞于宽大的幻影台阶,变化成一躯嗜血的尤物。它一定告诉了我,什么是最为恐怖的美。
虎
动物志以外,虎是西方和秋天,以白金为最高形态的纯粹的金属,虎也是夜空中稀疏的星。动物志以外,虎的每一线条纹,都经历了带给它精神之美的卓越的大手笔。动物志以外,虎更为稀有、名贵、凶猛和孤傲。当它活生生伫足于月下的地平线,以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兽性摆脱了繁复的比附、象征、拟喻和美之光环,成为一头真正的“白”虎时,我愿意它能够再迈前一步,进入我的诗篇。
苍 蝇
苍蝇为什么从来也不是马戏团角色?它如此充分地摹仿人事,参与一切日常生活。苍蝇,它跟我们有相似的习性,爱好亮光,在其中盘桓。当我们用餐,它先于我们品评饭菜;当我们如厕,它先于我们发出了哼吟;当我们照镜子,它甚至攀上光洁的玻璃,更欣赏我们被视觉想象力修饰的形象;而当我们打开那歌集,我们发现,又是苍蝇,夹杂在字词之间,添加诗行的音节,补救了天才的欠缺;……是否因为苍蝇的摹仿儿乎是侵略,即使它有着远比猴子更高的天赋,我们也不给它在孩子们面前施展的机会?并且,苍蝇,我们厌恶它,追杀它,要它死。它跟我们过分一致——聚众、嗜腥、喋喋不休,令我们怀疑——是不是我们摹仿了它!
燕 子
燕子是陈旧的。它有如不断返回的光明,但也许是不断到来的对逝去时日的回忆性再现。它在它自身的命运旅程里永远是燕子,而在一个改变了境遇的墨客眼前,则是早年写下的文字,是由这黯淡的字迹连缀而成的怅然的诗。燕子也可能是另一种文字,当它被书写进以无限为背景的真理之中,它也可能是被放送和播撒的确切的箴言。但作为一种智慧,燕子依然陈旧。圣经说:“太阳底下无新事”,晏殊说:“似曾相识燕归来”。
鹦 鹉
英武的鹦鹉并没有羽色,一如它其实不解人语。当我在正午的强光下书写了十分钟,我的眼前就会有镂空黑暗的亮鹦鹉蹁跹,它梦幻的色彩常令我想到闪耀的事物。鹦鹉,一个比喻。它离开全体,丰腴的身形出现在一片虚构的海域,它也曾出现在纤细秋雨中愁煞人的街角。有人给予它奇异的象征,另有一些人分享它那可怕的热病。它被海轮装运过来,它栖止于某个老人没落的窗前。它简单的喉舌学会发出它不可能弄懂的复杂语音,它把一位亡父的复仇指令传达给一个刚刚成人的遗腹子——这些无关紧要的鹦鹉知识使得鹦鹉更只是比喻,一个近于驳斥的比喻。没有人能说出这是为什么——鹦鹉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出它那摹仿人语的啼鸣。
蝴 蝶
没有止境的族类,不时有新品种入谱。它作为生命的必要性,不如它作为奇迹的持久。它被钉在墙上,或被夹入簿册,更为错杂繁复地,它被编排进记忆和语言不可能获得的袖珍迷宫。它的精妙、细微,如同沙子般不断缩小和衍生的存在,令一个人丧失对它的占有。它跟每一首出自幽闭者之手的赞美诗一样对称,一样缜密,一样会投下网结心灵的剔透阴影,它玻璃翅膀上巴罗克风格的眩目图形令它在死后有真正的永生。蝴蝶之名恰切于梦境,说出内视之眼所见幻象的艺术本质,灵魂呈现的灿烂纹饰。所以,对蝴蝶的痴迷是无限的爱;对蝴蝶的想象是一生的信仰;对蝴蝶的搜寻、追捕、认识、鉴别、收藏、欣赏、研究、比较和命名,是无以穷尽的隐秘的宗教。
蝙 蝠
蝙蝠是真正的黄昏派诗篇,飞进了鼠类安排下日常生活之盛大庆典的广袤夜色——
摇摇摆摆地飞行,像没经验窃贼的良心,
里面的天性,在善恶之间徘徊。
它跟随黑暗,亦跟随光明的脚印。
它不是单纯的老鼠,也不是鸟儿,
是所谓鼠鸟……
(布伦坦诺《布拉格的建立》)
但蝙蝠难免是天使,因持久的想象力进入了真实世界。蝙蝠不来自人的想象力——蝙蝠未必人的天使——蝙蝠是真正的黄昏派诗篇,抒情的老鼠塑造其名。人赋予天使以人的形象和多毛的翅膀,老鼠的想象力则给了蝙蝠一脸鼠相和一副光翅膀。正是从它那自多毛的躯体上展开的光翅膀,和它的那张脸(尽管是鼠相,却带着多么纯洁无邪的婴儿表情),它作为鼠类天使的神圣身份被认出;它的超现实性、它的宗教感、它摆脱时间顺序循环的逆向式显现;在诗篇里,它有了非人的象征意义。
——运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