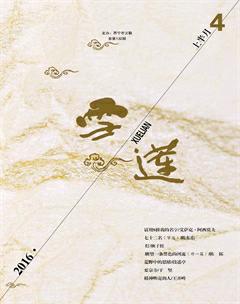一个人的时候
蒋子丹
在你初生的那一刻,你被判处为独立。你沐浴着母亲的喊叫与血,慒慒懂懂接受了判决。那时候你浑然不知,这意味着你将一个人穿越漫长的时光与生命之旅,直至墓碑标记的终程。一位先哲这样描述人的初生:没有人请我们来,也没有人准我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四十年前的那个早晨或者黑夜,你带着独立的胎记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从此有了一个你。
要是你有超人的记忆,或许你还会记得,你离开母体后的第一声啼哭,携带了多少本能的悲愤与无奈。本来你已习惯了在母亲身体里生活的岁月,柔韧的子宫湿润温暖富庶,黑暗里永远有母亲的心跳和呼吸环绕。你以为母亲是你永久的联体伴侣,你是持有子宫绿卡的永久居民。当你终于让无情而有力的宫缩排挤出来,被抛弃在这个空旷干燥光亮刺眼并且完全陌生的世界上,孤独无助的恐惧也随之降临。你的眷恋与哀怨化作啼血的嚎啕,换来的只是母亲幸福疲惫的微笑。母亲在那一刻疏远了你,你从此不再是她血脉相通的一部分。
襁褓里的日子悠长而无聊。自从前来祝贺你初生的人群散去之后,你就不能将大众吸引在你身边了。你常常是一个人躺着,看太阳的光影每天从摇篮上方的天空里静静地走过。你听见沓杂的脚步声在你周围近近远远响,焦躁而忙碌。你想让脚步在身边停留,你想表示我不愿一个人呆着,但你不会说话。你只好哭。这样你发现了哭是一种武器,你一哭,准有某个大人来抱你,看你到底是饿了渴了发烧了还是弄了一身的屎尿。于是只要你身边没有人,你就要发出哭的声响,并且日以继夜地把哭声的锋芒磨得越来越锐利。那些人们开始是莫名其妙接着便是有些厌烦,他们拍着你小小的屁股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哭的孩子。你的老保姆拿你无可奈何,动用了一种古老的办法,她用黄裱纸写了许多相同的招贴贴到每一根电线杆上,让夏夜的路灯下聚起一小群一小群好奇的黑脑袋,他们念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望一望,一觉睡到大天光……你一点没被这些古怪的纸符管住,你逃避孤独的招数就是哭,只有哭,大哭,你不能放弃。渐渐地谁也不太在乎你的哭声,你哭得声嘶力竭撕心裂肺才能得到一小会儿抚慰。你黔驴技穷心烦气躁,踏开被子把肚脐眼暴露在秋天的冷风里,为此你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感冒转成肺炎,差点要了你的小命。等你从高烧的昏迷中苏醒,睁开眼睛一看立刻洋洋得意,你周围坐着站着一大堆人,全都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你。你简直情愿自己从此把肺炎永远得下去,用高烧把他们全栓在病床旁边。你的阴谋当然不会得逞,医生很快治好了你的病,你愁眉苦脸的被欢天喜地的大人抱回家中。就这样你在哭声中慢慢长大了一些,长大一些之后你便不太满足于用哭声与别人交流,有一天你决心开始学人们说话,憋足了劲大着嗓门叫了一声:妈妈!
这一声喊的效果让你始料不及,那个被你称作妈妈的女人应声扑到你眼前手忙脚乱抱住你说,乖孩子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你被她夺眶而出的眼泪鼓励得心花怒放,既然叫了第一声再叫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你叫了第二声又叫第三声,声声都获得亲吻的奖励。这件事真的叫你欣喜若狂,从这天起你全部的精力都转向学习说话。你发现说话的声音比哭声更能调动那些人,为此你叫了妈妈又叫了爸爸,叫了姐姐又叫哥哥忙得不亦乐乎,就这样你一句一句学会了说话,你以为学会了说话就等于逃离了孤独。
设想这些往事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后的一个中秋之夜。你站在南国异乡的海滩上,潮汐正在皎洁的月光下悄悄地上涨。远处有同行者醉心于美味烧烤的喧哗,还有一群少男少女用烛火在沙滩上划出的阵营。你看见你自己的影子,在月下的波浪里轻轻游动,忽然你就有些惊诧它跟随了你三十多年,怎么一直不言不语,而且在不言不语之中一直忠实地陪伴你,让你倍感亲近。它是你的附属物,可是一点不像你。
这三十多年你基本上是一个健谈的人,你岂止是学会了说话,而且被造就成伶牙俐齿,每当你热情或激愤之际,语言的瀑布就从你嘴唇的闸门里喷涌而出,毫不怯场地飞流直下。你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最终选择了文学,也许是并不满足于仅仅用语言沟通。然而过于看重沟通恰恰成了你的弱点,人家不理解你的时候你总是借助于语言和文字强求理解,在你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的时候总是企图寻求多数人的声援。可是在一次足以使你改变人生态度的重大分歧中,你真正体会了语言的无力与苍白。你说很多话,换取一些模棱两可不关痛痒的表态,真好比在用一只纸糊的道具镐头,刨一座封冻成坚冰的山,并企图把掩盖在是非垃圾下边的一小颗真理寻找出来。你终于知道言语在这种场合的功效只能用负数来表示,倾诉者在倾诉之后只能是更加孤独。不光如此你还得知,深埋的真理已经镀上了铜臭,寻它何用?无可奈何之中,愚者选择的可能是再接再厉的游说,而智者一定会选择沉默。你想当一个智者。你决定沉默。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中秋之夜,你在月色茫茫的海边,面对自己沉默的影子,把为真理辩白与表明心迹的功能从语言的说明书上一笔勾销。你感到一阵轻松。从你喊出了第一声“妈妈”,到你彻底怀疑语言的万用灵通,这三十多年你对语言的理解其实是从原地开始又回到了原地。建议你还是从刚刚结识语言的三十年前说起,那样可以让貌似复杂的问题变简单一些。
学会了说话你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太久,你发现人们对你说话的兴趣仅限于茶余饭后,只要他们需要去做那些所谓重要的正经事,就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呼唤留下陪伴你哪怕一小会儿。抱住爸爸的腿拽着妈妈的衣襟或姐姐哥哥的书包带,你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你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跟屁虫”,被他们哄完了骂完了,许以棒棒糖和冰棍之后仍然困守在令你憋闷的家中,跟不会说话不会动的玩偶相伴。这样的时日多了,你就真的成为玩偶的一分子,你在玩偶中间跟这个说话又跟那个谈心。你的千言万语都跟公主狗熊小红帽和狼外婆说了,它们只是默默地瞧着你听你倾诉一声不吭。
到这儿为止你其实已经用幼稚的游戏完成了对语言的全部试验。你完全不知道。
于是某个静悄悄的下午,在一间只有你的自言自语和马蹄表的哒哒响声回荡的屋子里,你萌生了你对群体皈依的向往,你以为缓释孤独的仙丹可以靠群体的八卦炉炼制出来。
浅尝过孤单的滋味以后,你去小学里做了一个依恋群体的孩子。你每天上学很早放学很迟热衷于每一项集体事务小心翼翼地对待班里的孩子王。你说的孩子王,指的是那种天生具有蛊惑人心的理论能够在同龄人中间运筹帷幄的男孩和女孩,他或她身材不一定特殊高大成绩一般都不太好,但他们在班上一呼百应,任谁都要让他们三分。因为要是有一天他或她指着某个孩子说:别理他(她),谁也不准理他(她),这个孩子就成了异己分子被排斥在所有的课余活动之外,连课堂上答错一句话也会引起哄堂大笑。从一开始你满心羡慕的就是这些孩子王,羡慕他们支配他人控制他人的能力,你并不知道比起他们来你的基因里正缺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尽管你成绩优异。你只是凭本能向往着群体,凭本能知道对于缺乏霸气的你来说进入群体的方法是投靠孩子王,你天生是个怕孤单的孩子,你非得成为群体里的紧密的一分子才活得踏实。于是还在小学三年级你就有了软弱与妥协的经历,这种人之初的奴性显现让你在成年以后仍要汗颜。为了讨好王孩你在考试的时候给他们递过纸条,你把一根几丈长的彩色橡皮筋贡献出去强忍着眼泪说,没关系跳断了也不用你赔。既然不用赔它当然就断了断成了好多截,你因此得以参加经他们指定才能参加的活动——旷课,到野外去捞蝌蚪。你又紧张又兴奋地走在曾经把你摒弃在外的队伍中间,迎着旷野里和煦的风,穿过桃花梨花绽开的云霞,那时候你觉得成群结队真好,它叫你享受了强大与荣耀并且不再孤单。正是在一片强大的叫嚣中,你看到黑玻璃珠一般无辜的小蝌蚪,被你们这个团伙穷凶极恶地打捞,装进大瓶子小碗或者遗漏在干涸的泥地上,成为死刑或死缓囚犯。你的心情忽然坏下来,悄悄地退出了那个行列,你不是王孩,无力阻止任何人。你一个人在仲春的田野上独行,想起美丽的橡皮筋,想起劫难中的小蝌蚪,失望和暮色一道笼罩了你。你像丢失了心脏似的感受了空洞,其实你丢失的是你尚说不出名儿的个性与尊严。天黑下来你迷了路,像在婴孩时期摇篮里一样你发出了悲凉的号啕,惊飞了枝头的宿鸟也黯淡了远处的灯。
那个暑假你几乎形只影单,你常常把一条满是接头的旧皮筋拴在小树上,跳一会升高一点,或者跟邻居家刚会走路的小女孩一起过家家。有一天一个班上最不显眼的女孩来找你借书看,你竟然感动得不知所云,你已经让王孩指着鼻子号召过:不准跟她玩,你对女孩说你来找我他们就会不理你。你没想到那个小小的女孩一点都不畏惧,她说那怕什么不理就不理。你一下子就对这个女孩肃然起敬,觉得她比王孩还要强大,不过那时候你怎么也说不出她究竟强在哪里。
其实跟你最初的语言试验一样,你用一些小蝌蚪就探查到了群体的秘密。可是你不是先知,甚至没有任何夸耀的天赋,这些具有暗示性的经验几乎没给你留下印象。不光你,所有不在先知行列的人都如此,你们永远把强大的感觉建筑在别人的沙滩上。你们开始寄希望于父母,父母不能陪伴你人生全程;下一个轮到友谊,友谊不是旱涝保收的高产田,随时可能长出野草;你们又相信了爱情,海誓山盟不一定能让爱人心心相印;然后你们动用了婚姻,一纸契约未必把家庭包裹得坚不可摧;你们最后说,还是靠孩子,孩子是自己的骨血,他(她)可以搀扶你走过容颜衰老的岁月,用亲情驱散你弥留时的阴影,结果孩子长硬了翅膀飞去外面的世界,留给你们一个空空的鸟巢。你不是先知,你一次再次面对独立,感受到的却是孤独或者孤立,你是一个凡夫俗子,在你眼中独立与孤独有同样含义。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中秋之夜,你一个人站在异乡的海滩上,看见自己忠实而沉默的影子在水中游弋,听到从海的深处不断涌来的涛声里,一个混浑不清的声音正在重复宣读你初刻为人的判决辞:判处你独立。然后那个你淡忘了姓名的女孩,从海的中央,被皓月照亮的大海与天空的衔接处,走进你的视野,甩着两条黄黄的小辫子说,不理就不理。
你终于在南国的月光下与强大会晤,它是浩瀚的海和小小的女孩。
几近四十年之后,你才被它们鼓励带着沉默的影子去服从人初的判决,结束你历尽艰辛而且毫无意义的逃亡。你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独立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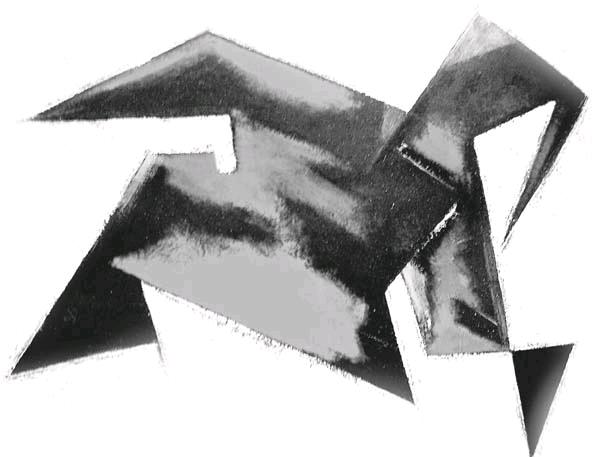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时间是早上八点。你家向东的窗户里,正有一束束并不耀眼的太阳光在百叶窗的缝隙里探头探脑,当一阵小风掀动那些白色的叶片时,阳光就挤进来,点点滴滴掉在桌面上,那上边有你翻开一本书。你应该读过这本书,书页上蓝墨水留下的标记向你证实你的确读过它。你选择了一处被你用笔划过的段落重新读起来:查拉斯图拉又继续奔跑,但他没有找到任何人,永远只找到了自己,享受并留住了自己的孤寂,世界不恰在现在成为美满的了么?一个古怪的德国老头在上世纪写下的书,此刻给你的感觉完全像报馆今天早晨刚刚印出的报纸那么新鲜,白纸上的黑色铅字晃动着,犹如春季绿草地上闪亮的露珠,映照你惊喜的双眸。你看见在你的内心深处,有另一双眼睛轻轻地睁开了,一眨一眨正欢快地舔吮露珠。它们一点点浸润进去,你的视神经受到了滋润,发育得活泼而敏感了,在书页蹦蹦跳跳,好比一个农家女孩在林子里采集蘑菇俯仰皆是。其实你应该明白,这些不朽的蘑菇已经在思想的森林里生长得有几分苍老了,等你来采,你却一次次随着热闹的人流从它们旁边走过去,一无所获徒手而归,直到今天你一个人溜达路过,才发现了它们原来这么多长得这么肥硕。
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忽发奇想,你能用采来的菌种培育起自己哪怕是一朵小小的鲜菇吗?你前所未有地自信起来,以至你用一把梳子梳理蓬乱的头发时,止不住要嘲弄镜子中那个熟悉的面影说,你的妄想多可笑呀!梳好了头发之后,你又改变了想法,有什么可笑呢?后来你坐下来,面对着一堵白墙,墙上有建筑工人在匆忙之中留下的凸凹不平的印记,你想到了一篇著名的小说《墙上的斑点》,你知道有的事情不过从墙上的一个斑点开始的。于是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白墙,钢笔和纸。果然没有什么好笑。
你的感觉和思想坦然地出发了,开向另一个时空里的另一些存在。有时候,你会面对密密麻麻挤到你跟前的往事与幻影大喜过望;有时候,脑子里又成了散场后的戏院空无一人一物。可是你很幸运,时至今日无论熙熙攘攘还是空空荡荡,你都不会焦躁。
你经历过文学大跃进的岁月,你被功名和虚荣的锣鼓催促着,投身了揭杆闹文学的行列。你激动而紧张,注视着视线所及每一位同行者的步伐,强迫自己跟上。你迷信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俗套,把文学沙龙看得至高无上,你们每天煞有介事地互相传阅新作品,或者将尚在构想的小说讨论来讨论去。你们一见面就相互通报又写了多少字,又发表文章在哪一家刊物的第几条。你们发誓要好好写,然后与先出名的那些人一决高低。如此你们也就很重视评论了,评论家成了你们的衣食父母,好像你们写作完全是为了写给他们看。只要说几句你们的好话,哪怕是胡说乱侃你们也兴高采烈,有一篇总比没有强。你们像一批刚入伍的新兵,每打出一发子弹就眼睁睁盼着报靶,一心等待有人喝彩。为了不让前来组稿的编辑空着手回去,你们玩命赶稿,有时候难免强打精神凑凑合合。你们互相撰写印象记,把通信和对话录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你们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唯恐读者忘记了自己。于是你们戴上了作家的帽子,其实很像一群竞技的狗熊。那些日子是多么热闹,你的家常常门庭若市,坐着各地来的编辑与本地的文学朋友。你久久地醉心这种繁忙的生活,又一遍温习着成群结伙的好心情,同时形成了对文学的错觉。
直到你一个人面壁而坐,你才隐约看到了文学的真容。它对你来说它从来不靠运动来制造,它从来只跟一个真诚的作者本人相关。你对它说你懂,但懂得并不彻底。它问你是否一心想栽一棵大树荫盖后人,你说不,我只不过想种一棵我独有的小树甚至一朵属于我的蘑菇点缀我自己苍白的生命。它说那你就去你的园地里耕耘吧,废话打住。你更加坦然了,你觉得文学这个职业跟你天然的生存形式简直一脉相通。所以你不再焦躁,功利不再能蛊惑你,你只写你自己想写的字,谁能够真心喜爱它们你就为谁而写。当往事和幻想纷至沓来之际,你像一条吐丝的茧赶紧把它们吐出来。你很可能做一些无用功,吐出一团乱丝织不成锦缎,但假如吐丝的过程使你快乐,这就够了。
你不可以说所有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你的节日,正相反这样的时候忘我笼罩着忧虑的薄雾,死亡的身影时隐时现漂浮在雾里,给你一种人生苦短的警告。可幸的是你已经直面过自己的出生了,这样你就有正视死亡的可能。跟你独立的出生一样,你的死也需要你独立完成,你的生命是“被给予”的,也会随时地“被剥夺”,属于你自己的,只有在“被给予”和“被剥夺”之间短短的空隙。沉思过死亡以后,会怎么样呢?所有的人都会为之忧虑,但忧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认为它的最高形式应该是创造,你应该选择创造。
要是你从此你只为创造自己活着,那你就错了,作为自然人社会人你永远割不断与世界千丝万缕的瓜葛。不同的是,当你终于清楚你原本是注定是独立的,你会活得更加自信同时获得一种对他人的宽容。你不再对你的同类与同行者包括父母手足朋友爱人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苛求。你明白了他们是你独立生命之外的另一些独立的生命,因而他们为你所作的一切,都被你视为额外的馈赠让你感动。你会少一些时间计算你的善行收到多少善报,多一些时间来考虑如何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因此你不可能对他们漠不关心,你会喜他们之喜忧他们之忧为他们受到的侵害表示你应有的义愤。你再也不会抱怨他们的来信少并且字迹潦草,不会指责他们打电话匆匆忙忙两语三言,在他们偶尔违约的时候,你会设想他们可能遇到了麻烦情非得已,就算他们无意间伤害了你,你也会在他们道歉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你和他们本来互为独立,无论是谁他们并不天生对你承担义务。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再认为有谁欠了你什么,你肯定更加看重默契而不指望把任何想法强加于任何人,也肯定较少失望与失意更容易顺其自然。你追求的是独立,不是卓尔不群,因此你应该还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亲切的妻子真挚的友人已是大庭广众之中行为规范言语正常不疯疯癫癫也不故作深沉的寻常女人。当你如何体会着与其他生命更广义的关联,也就懂得了独立与孤独不是同义词,也不是全等三角形。
此刻是春夏之交的某个晚上,你一个人。你这样写道。尽管在你居住的这个热带岛屿四季一点不分明,你还是固执地用季节的更替来标记时间,你认为这样写更有诗意。下雨了,这是一个例外,岛上夜雨甚少,短暂的阵雨通常下在午后。你不觉有几分欣喜,你一直认为雨和夜合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出神入化的活力,在这样的夜晚,你常常觉得自己思维敏捷嗅觉发达联想丰富,你现实的感官视听可以穿越时空把某种遥远的声音、气息、色彩、画面调动到你跟前。在这个雨夜,你正准备重新感受一下自己的时候,远处的建筑工地上,传来一阵轰响,你判断那是一车圆木被卸下了卡车。声响之间,湘西猛峒河道就在你眼前展开了,河两边郁郁葱葱的峭壁之上,一根根新伐的大树枝不知什么人推下来,笔直地插进河水里,仿佛从天而降,落后又像一支从海底基地发射的火箭被水的力量反弹到半空,沉重的树身溅起巨大的波浪,终于停留不住顺水漂流而去。你在游船上目睹了这种壮观,为之倾倒并且经年不忘。
在这个微风湿润的雨夜,由一声卸木头的轰响引来的故乡河水,冲刷着你安适的心境,又一次唤起了你对大自然由来已久的向往。你是一个在城市里长熟的生命,高楼大厦的夹缝与烟囱汽车的废气构成了你的生存空间,你的生命从一降生,就在等待与野生的自然物嫁接的机会,可是你一次次错过了它。你意识了这一点,你知道自己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先天月份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尽管你殷勤地访问过三峡,奋勇攀上天都峰又在大风中越过鲫鱼背,你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骑马,也在洞庭湖里划船。你与你的同行者在这些地方指点江山,然后回到各自的书桌前激扬文字。可是走过的地方越多,越被大自然的博大精深震撼,你越觉得自己的这支笔绵软无力,有一天,你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独立地完成与自然界的亲和过程,这是一个你无法否认的缺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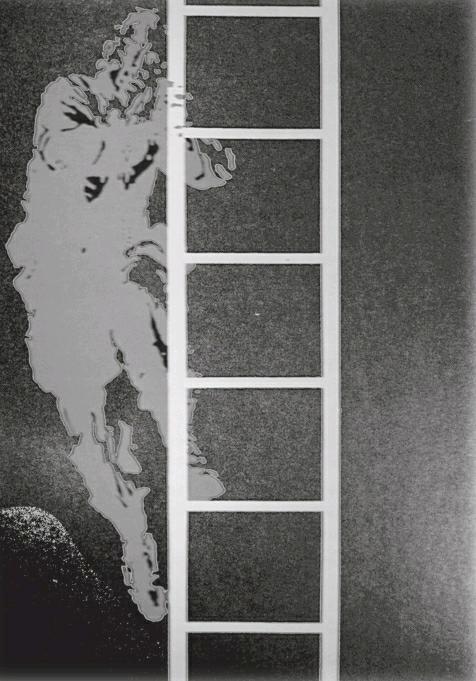
你又苦心积虑设计你只身徒步的孤旅了,这对你来说是一直最高的奢望。旅程也开始在某个平常的下午,你刚睡完了午觉,脸上海挂着枕席的印记。你喝了一杯白开水,穿上最家常的衣裳和一双凉鞋,拿上一些零钱就上路了。出门的时候,你了看看窗外的太阳,反身取了一顶草帽。完全不似以往出发那般计划周密兴师动众,甚至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目的地是戈壁是沙漠是草原是山颠还是大海,你心中只有一个充满诱惑的设想,就是寻找大自然绿荫如盖的拥抱。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只是走,走出城市的茫茫人海灯红酒绿,走出高楼的阴影走到阳光照耀的山间小路上,你预感到有一天你正行走在旅途中,脚下会突然裂开一个豁口,你掉了下去,溶入大自然的诗眼里,由此体验到物我一体天人感应的境界。那时候的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仍然只有自己沉默而忠实的影子跟随,但你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地知道,你终于不但独立了而且完整了。
你变成了那个从大海中央被皓月照亮的波浪里走出来的黄发辫小女孩,你已经淡忘了她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