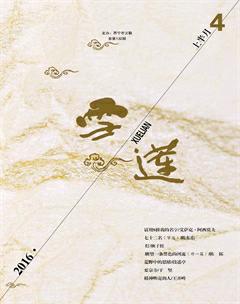珍珠泡的故事
刘国林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放暑假了,我和二哥去牡丹江边的舅舅家玩耍。
一天傍晚,我和二哥在舅舅家吃完晚饭,舅舅点了一袋烟,到院子里的老松树下纳凉。舅妈收拾完碗筷,拿起装针线的圆萝,也到老榆树下纳鞋底去了。二哥捅了一下我说:“敢不敢去珍珠泡游泳?”
珍珠泡是牡丹江边的一个大水泡子,方圆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可能是牡丹江改道形成的。舅舅说,珍珠泡的水通牡丹江,不管天多旱,珍珠泡里的水不见少;不管涨多大的水,珍珠泡里的水也不会往外溢。每到夏天,这里便是孩子们的乐园,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泡子里玩耍。直到去年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来这里看孩子们戏水时,一时高兴,也脱光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却再也没上来,当孩子们把他从水里捞出来时,见他满头满脸全是淤泥,肚子里却没灌进去一点儿水。舅舅说,他是扎进淤泥里憋死的,不是淹死的。再到泡子里洗澡,千万别扎猛子了,慢慢下水,活动着往前游,是不会出事的。尽管舅舅这样说,村里的孩子晚上再也不敢来珍珠泡洗澡了。从那以后,在孩子们的心里就留下一个阴影,再加上大人们绘声绘色的编造:珍珠泡子里有一个水鬼,晚上打着水电筒寻找洗澡的人,发现目标后,它会从水下拽着你的腿,连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变成水鬼了,而成了他的替死鬼,他就能再托生了。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得神乎其神,其目的只有一个:吓唬孩子们别到珍珠泡来洗澡,免得出意外。所以,今天晚上二哥说去珍珠泡游泳,我感觉后背有股冰凉的风往出冒,从心里往外害怕,便说:“我不敢去,听说有打手电筒的水鬼!”“鬼打手电筒?你这个笨蛋!鬼怎么不用探照灯?那东西多亮?”他挖苦道。
想想也是,鬼怎么会用这么现代化的东西呢?于是我心里也镇定下来,二哥是我的主心骨,他既然敢去,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小声问:“舅舅能让去吗?”“笨蛋,你不问不就去成了?”“那咱怎么走?”二哥努了努嘴,指了指后窗。我当即心领神会,二哥想从后窗跳出去,顺着后园子就能溜走。可当我俩跳下后窗时,还是弄出了声响,舅舅在院子里发话了:“淘气包子,什么事能瞒过我?是不是想洗澡去?去就去吧,早去早回!”“哈哈,舅舅同意啦!”二哥边说边朝我挤眉弄眼,我便跟着他像猫似地钻出后园子,朝珍珠泡奔去。
珍珠泡离舅舅家不远,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夜幕下水面像一大块黑色的绸缎,静静地铺在眼前,泡子边的玉米地也黑森森的只能看清个轮廓。几只萤火虫在水面上飞舞,一亮一亮地闪着米粒大的荧光。不知名的虫儿远远近近地鸣叫着,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更给这寂静的夜添几分神秘的色彩。我和二哥都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下水畅游起来。我很佩服二哥的泳技,他一会蛙泳,一会侧泳,一会儿仰泳。尤其是仰泳的水平更高,四肢不动,竟能静静地漂在水面上,呈一个大字形,那个舒坦劲儿让我羡慕死了。我想学二哥的样子也躺在水面上,可是不行,胳膊腿稍一停身子就往下沉。我问二哥这是咋回事,他却说艺高人胆大,你越怕沉越不敢躺在水面上,身子越往下沉。你把身体放平了,稍动一下胳膊腿就行,保准能挺几分钟。我照二哥说的法子做了,果真身子漂起来了,不过姿势没有二哥的优美。
我和二哥心情地在水中玩耍着,不知不觉游到了泡子中间。突然,我发现前边不远处的水面上泛起一片白光。我一下子愣住了。在这空阔的水面上只有我们俩,哪里来的光亮?想起村子里的大人讲起的水鬼故事,我顿时毛骨悚然,声音有些颤抖地问二哥:“快看,那是什么?”二哥似乎正仰在水面上闭目养神,被我的问话吓了一跳。忙翻过身来游到我身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见到一片白光。他一时也怔住了,停了一会儿,便若有所思地朝那片白光游去。
“你不要命了?”我在他身后大声喊着。他没有理我,继续往前游。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过去。奇怪的是我俩快到近前时,白光渐渐消逝,水面又变得一片漆黑。难道水鬼知道二哥是个不要命的主?应了“鬼怕恶人”那够俗话,见他来了故意躲开了?二哥愣愣地看着平静的水面,叹了口气,返回游上岸来。我也上了岸,见他穿好衣服走到玉米地边,折断一根玉米杆儿,插在岸边的泥土里。我大惑不解,问他这是做什么,他又眨了眨眼悄声说:“回到舅舅家再告诉你。”我俩一路无语,见他心思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名堂。
回到舅舅家,二哥在他的小木箱里找出一本书,翻了好一会儿,才把书的一页叠起来,递到我手上说:“看看吧,就知道水鬼是咋回事啦!”我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原来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二哥虽然是个愣头青,却十分喜欢读书,今天他给我这本书一定是有原因的。翻开叠起的这一页,标题是《甓射珠光》,内容大致如下:说嘉佑年中,扬州有一蚌,其壳大如半席,珠大如拳。看完此文,我才悄然大悟地问二哥:“你的意思是咱看见的不是什么打手电筒的水鬼,而是个体内含有明珠的河蚌?”“是的,只不过珍珠泡子里的河蚌要比书上说的小得多,所以它发的光和手电筒差不多,被村里人误传为会打手电筒的水鬼!”“明珠?太好了!”“咱得想办法逮住河蚌,看看明珠究竟是啥样儿?”我一下子高兴得蹦起来。“我早想过了,这只河蚌太精,必须划船用鱼网逮。”二哥顿了顿又说:“今晚我听天气预报了,明天肯定会下雨,隔壁的张大爷肯定不会下江捕鱼,咱可以在天黑前到他那里去借船,早早地到泡子里等候。”
张大爷是生产队的打鱼专业户,五十多岁,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儿。我和二哥经常到他的鱼窝棚里吃鲜鱼解馋,和他混得倍熟儿,找他借船估计没问题。
第二天,果然下起了雨。我和二哥睡了一上午觉。下午雨停了,我躺在炕上捧着那本《梦溪笔谈》看得津津有味儿,二哥一轱辘爬起来说:“别看了,赶紧走吧!”我问:“哪里去呀?”“瞧你那臭脑子,昨晚不是说好了吗?找张大爷借船呀!”
我这才想起昨晚上的事,忙不迭地穿鞋跟他出去。二哥干啥事都是神神秘秘的,经过厨房的时候,二哥跑到菜墩前拿了把菜刀,用报纸包上挟在腋下,我提醒他:“用不用告诉舅妈一声?晚上她做菜找不到菜刀,她会急的。”“不行,舅妈知道了肯定会不让拿,她会以为咱俩拿菜刀会不干什么好事的。咱只能‘先斩后奏啦!”我一想也对,二哥究竟还是有些怕鬼的,拿刀好防身,便问:“要不要把舅舅的枪也带上?”二哥朝我瞪起了眼珠子:“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走就快走!”
二哥就是鬼道,他没直接去张大爷的鱼窝棚,而是去供销社买了瓶“北大荒”白酒揣在怀里,才去张大爷那里。我知道,张大爷爱喝两口,一见到酒就眉开眼笑。再者,我和二哥总吃他的鱼,有来无往非礼也,就算是对以往的补偿吧。这一招儿真灵,张大爷见到酒瓶子顿时眼睛一亮,以为俺哥俩又来混吃鱼来了,一个劲儿地往窝棚里让。二哥骗他说是晚上去珍珠泡子里赏月,老师布置个作文题叫《家乡的月亮》,不亲身体验一下,瞎编不出来。张大爷信以为真,叮嘱说:“用完了别忘了把船拴好,到你张大爷这儿,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其实,他也不想想,又不是十五满月,有什么好赏的?
告别张大爷,我和二哥驾着小船必须找到昨天晚上碰见河蚌的水面。但是,这么大的水面要找到它谈何容易?二哥却胸有成竹,沿着泡子的岸边遛,终于把船停下来。我定睛一看,噢,岸边插着一根玉米秆儿,这才明白他插这根玉米秆的用意,不得不佩服他的心计。
我俩以玉米秆为目标,悄悄地往泡子里划去。二哥是划船的老手,桨划在水面上,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我想起了作家孙犁笔下《荷花淀》中描写雁翎队偷袭日本鬼子的场面,觉得我俩有些相似。不过不是偷袭日本鬼子,而是偷袭大河蚌!估计到了昨晚奇遇白光的位置,二哥将船停住了,把晒在船尾的渔网拿过来,仔细检查有无破损。我无事可做,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如钩的弯月在水面的映衬下是那样的美;小船似水中静卧着的天鹅,沉沉的睡意是一种朦胧的美;我和二哥的倒影映在水面上,既真切又模糊,就像剪影似的,多么好的一幅剪纸画呀!我正看得出神、想入非非的当儿,二哥用胳膊肘碰碰我,又往前方指了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清楚地看见不远处的水面正往外冒出一大片白光。老天,它果真出来啦!
白光朝着小船这边来了,二哥拿起渔网准备往出撒。随着白光越来越近,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地跳,都快到嗓子眼儿了,很快就要跳出来的当儿,二哥果断地撒网了,白光也迅速消失了。它逃走了吗?我在心里嘀咕道,二哥又瞪起眼珠子冲我大喝:“笨蛋,快拉呀!”我如梦初醒,笨手笨脚地上前帮着拉网。怎么这么沉?我俩用尽全力,终于把它拉了上来,“咚”地一声砸在船舱里,小船忽地倾斜起来。借着月光,我清楚地看见网里的不速之客,是个脸盆大小的河蚌!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河蚌,此时它紧闭蚌壳,一动不动地装死。
该它倒霉,如果碰到别人也许还有活路,碰见二哥它只有死路一条!二哥早就拿出准备好的菜刀,“喀嚓”“喀嚓”地撬蚌壳,费了好大的力,无奈蚌壳太光滑,二哥使不上力,怎么也撬不开。“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住它!”二哥又对我下了命令。我挪身的当儿,不小心踩得小船摇晃起来。还没等我把稳河蚌,只见它一哧溜,翻了个跟头,扑通一声顺着船帮掉进泡子里!当时把我吓傻了,蹲在船舱里大气不敢出。此时的二哥气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煮熟的鸭子让你给放飞了!蠢货!笨猪!”说着,扬起手中的菜刀,我以为气疯了的二哥要砍我,吓得赶忙缩回头。就在这当儿,二哥手起刀落,只听啪地一声,水面溅起水花,菜刀不见了。说时迟,那时快,二哥以迅雷不掩耳之势,嗖地一声把网撒下去了。
他慢慢地抖着网纲,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偷偷地观察着二哥脸上的表情。只见他阴沉的脸渐渐地多云转晴,随着手中的网慢慢提起,二哥又有了笑模样儿。网终于提上来了,我看见了被提上来的河蚌少了半边壳,河蚌的半边肉不见了,菜刀插在另一半的蚌壳上。二哥拔下蚌壳上的菜刀,仔细地拨着蚌肉,却怎么也没找到蚌里的珍珠。二哥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船舱里,自言自语道:“完了,养个孩子却让猫叼走了,白欢喜一场!”
我不知道怎么跟二哥回到舅舅家的。舅舅翻看着脸盆大的河蚌说:“这么大的河蚌,连牡丹江里也不多见。”又转身安慰二哥说:“行了,也用不着难过。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怪: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不知舅舅是劝二哥才说出这番话的,还是给我俩听的。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我一直为没得到那河蚌里的珍珠而后悔,常常想起舅舅说的那句话,越想越觉得舅舅说的有道理。或许是安慰吧,就像人们常说的“吃不到葡萄的人总会说葡萄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