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演剧与乡土
岳永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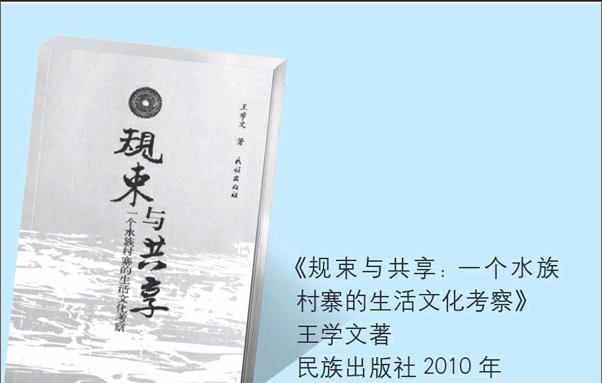

一
无论是对于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主角还是配角、主家还是邻里,作为群体性参与的地方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仪式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类学中的象征人类学派的研究对象就主要是仪式。在象征人类学之前,作为行为的仪式—实践和作为表述的仪式—神话/传说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也是研究者试图澄清的焦点。犹如鸡与蛋孰先孰后的千年谜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地对仪式实践与神话/传说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即后人所谓的神话仪式学派(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与人类学相似,仪式同样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在国内框架基本雷同的民俗学教科书中,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等章节聚焦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仪式。这些仪式是在特定地域享有相同文化习惯的人群,基于既定的时空观、生命观而阶段性、周期性举行的一种表演性、神圣性/宗教性、娱乐性/世俗性兼具的群体活动。当然,这些仪式的主旨究竟主要是针对个体、群体、自然还是社会,则不一而足。
因应社会的变迁演进,技术的创新与普及,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尤其是人们观念世界的变化,旧的仪式会消亡,新的仪式会产生。或者,旧仪式的外形面目全非,新仪式的内核依旧延续过往。近些年被学界津津乐道的“传统的发明”同样多指的是仪式或仪式化的行为。在今天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先声夺人的民族/国族主义大行其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交错并存,都市生活方式蔚为大观。这些都使得当今社会的仪式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此起彼伏。仪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就人的社会化生成而言,相对传统的仪礼和现代民族国家对公民的一系列铸造仪礼犬牙交错,前者如满月、抓周、开锁、拜师,后者如入队、入团、入党、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升迁庆贺,等等。
然而,无论哪种仪式,既因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也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推波助澜,仪式的表演性、娱乐性被大力彰显,及至名正言顺、有板有眼地成为文化景观、景观文化。反之,仪式的神圣性/宗教性,至少说仪式的庄严性则大为衰减。这不仅是远离乡土的公众的常识,也大体是知识界研究的既有前提和必然结论。当然,这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将基督世界神圣性的衰减普世化。可是,就是对于基督世界,当一部分学者在说神圣性衰减—去圣化时,另一些学者则毫不怀疑人的宗教性和神圣性可能有的韧性(吕克·费里、马塞尔·戈谢《宗教后的教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其实,关于当今世界宗教的这两种论调,多少都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在相当意义对作为行动主体的信众的漠视有关。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将今天的中国称之为都市中国还是乡土中国,蜕变中的中国的复杂性、参差性有目共睹。政治、金钱、市场、旅游、电子技术、文化遗产、功夫片,甚至二奶、李一、王林等等光怪陆离的玩意儿都铺天盖地地砸向乡野。此时,河北武安康宿村民是怎样在迎送他们的城隍?赵县豆腐庄的村民如何搭建他们的醮棚,迎送其佛鬼神仙?贵州安顺大山村那些长期被贴上“屯堡”标签的妇女又是怎样在“修佛”行好?这些宗教味厚重的仪式对于当地的操演者、旁观者的生活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表演”,及至成为一种严谨的“演剧”?
二
梅兰芳的精湛艺术曾影响到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理念。不仅如此,翁托南·阿铎(Antonin Artaud)、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都曾贪婪地在诸如巴厘岛戏剧、伊朗塔其赫等类似中国的傩、赛社、社火这些东方的乡土演剧、艺术中获取养分,产生灵感。
对于阿铎而言,这些没有布景、赤裸裸的剧场是“没有间隔、没有任何障碍的完整场地”(翁托南·阿铎《剧场及其复象:阿铎戏剧文集》,台湾联经2003)。对于布鲁克而言,这些剧场是没有门或者说永远敞开着门的“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从第一声鼓响开始,乐师、演员和观众就开始分享同一世界”。对于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而言,这些剧场是祛除了所有伪装的“质朴剧场”(Poor Theatre),演、观双方是“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总之,在这些当下中国戏剧界公认的西方大师看来,诸如傩这样依旧在东方乡野传衍的艺术因应自然、个体和小社会的变化,娱天、娱地、娱神、娱人并自娱。它关注灵魂,拷问命运,驰骋想象,激活生命,赋予意义,天然有着阿铎强调的剧场的“复象”和本雅明所言的“光晕”(Aura),并从哲学意味上表现人所处的演化状态,神圣而残酷,质朴而粗野。
遗憾的是,极力引进这些西方先进戏剧理论的不少学界精英却在相当意义中忽视了这些先进理论的东方源头。这一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谦虚(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卑或者自我否定)心态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二十世纪后期,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的“被压迫者剧场”(Theater of the Oppressed)理念席卷了菲律宾、印度、孟加拉、韩国、日本、港台等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台湾,钟乔等人基于此明确地提出了“民众剧场”,即为民众而存在,属于民众并由民众创作的剧场(钟乔《亚洲的呐喊:民众剧场》,台湾书林1994)。二○○五年前后,还是在外力的帮助下,民众剧场才在大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羞涩登场。
当然,戏剧界主流对本土乡野艺术的漠视(或者说唾弃)与清末以来长期以西方为标杆的发展理念有关。不仅仅是急迫地打倒“孔家店”,傩这样的乡野艺术也大体被贴上了迷信、愚昧、落后以及浪费、劳民伤财等负面的标签。这一主流认知差不多持续到改革开放。二十世纪末,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自上而下轰轰烈烈掀起、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后,傩等乡野艺术才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有了些脸面与意义。与此官方潮流相应,搜集、整理、研究傩的著述日渐增多。然而,民众自有民众的逻辑,民间自有民间的风土人情,乡野自有乡野的桀骜不驯与吞吐能力。
无论大环境是风是雨还是晴,无论是江西南丰泥土味、家族性都很重的石邮傩,还是豫西东常村与西场村粗鄙不堪的骂社火,这些乡野演剧如变形虫般因时应景的传衍又具体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戏剧?在多大程度上是仪式?这些乡民主动投入和参与的演剧难道仅仅是地方风“俗”?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娱神、娱人、娱己的“表演”?仅仅是不同名目、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今天都市并不是太叫座且基本以西方戏剧为准绳的霓虹灯闪烁、卡拉OK式大、小剧场,这些土里吧唧的乡野演剧有着怎样的警示?对于政府尽力送下乡却同样观者寥寥的“文化”“戏剧”,这些不绝如缕的乡野演剧又有着怎样的启迪?
三
作为学文近些年来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魔方》一书并非仅单单回答上述仪式和演剧两方面的问题。在坚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学文尝试说明在当代中国的乡土社会,仪式与演剧的模糊性甚或一体性,试图说明二者之于乡民生活世界的意义、二者之于“乡愁”的不可分离性。可以说,仪式、演剧与乡土正是学文在本书中尝试要破解的三个关键词。本书的第一章就是以北京远郊区房山的石窝村为个案,专章从生活方式与地方感来历时性地考察乡土与乡村的生成。
对于乡土,学文有着他独到的理解。八九年前,为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曾长期在贵州荔波蹲点调查。在其基于博士学位论文完成的专著《规束与共享:一个水族村寨的生活文化考察》(民族出版社2010)中,他不仅描述出水族社会人、神、鬼同在的复杂的生活制度,还清楚地描绘了在此安家落户、心安理得的电视媒介的生存实态,即他所言的“变迁中的村寨”。换言之,对于学文而言,乡土并非是油盐不进的愚顽不化,并非是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但也非文人士大夫想象中的不知魏晋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在学文眼里,乡土既是一位步履蹒跚的龙钟老者,也是一位活力四射的调皮顽童。所以,今天的石窝人还会用口头叙事来强化他们生活的那个山窝窝里的小村与帝都北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有了“先有石窝,后有北京”这样让他者震惊的俗语。用学文自己的话来说,百余年来,主流精英眼里需要改造、提升的乡土实则是一块千变万化的“魔方”。
对于在城镇化、都市化旅程中快马加鞭的当代中国而言,学文长期凝视这些与大城市多少有些距离的乡野的仪式、演剧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显然别有深意。至少,他长期观察、叙写的这些同样有着时代色彩的传统仪式、演剧与日常生活说明:这两年被主流媒体以及学界大肆炒作、品读的“乡愁”绝非仅仅是在高楼大厦之间看得见的静态的山与水。
四
学文是我的同门师弟,更是挚友。二○○三年三月,他曾随同我前往河北赵县调查过龙牌会。当年七月,他协助我前往梨区进行我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后期调查,长达半月。在那半个月中,饿着肚子在烈日下光膀子行走是我们调查的常态。本书中关于豆腐庄皇醮会的文章就是此次调查的成果之一。当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黄昏,在豆腐庄学校空旷的操场边,我们与唱庙戏的艺人们一同席地吃晚餐时,学文吃到了苍蝇。当天晚上,我们也是在这所村小学一间简陋的教师办公室歇息的。办公室里没有床,只有学生上课用的一桌一凳。桌子长一米多些,宽也就六十公分。条凳与桌子同长,宽则不足三十公分。初进民俗学大门不久的学文没有怨言,就着桌子睡下了。次日,除中午吃了一块西瓜,胃多少有些弱的他基本没有再进食。然而,他却依然一丝不苟地和我调查了整整一天。或者正是这吃苦的精神,成就了学文田野调查的能力,成就了他这本处处闪烁着辛勤汗水和真知灼见的专著。
与常见学术著作的理论堆砌甚或言必称西方不同,学文的这本书近乎白描。他仅仅是将他观察到、体验到的乡土中国通过仪式、演剧等乡民的言与行,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但是,本书的质朴、平实也迥然有别于这几年文学界及其评论界建构的有些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虽指向纪实、客观,但纪实、客观本身不是目的,它更在意的是煽情,是能否动情,以情感人,主色还是文学的。哪怕明显有着伤感和隐忧,学文却不想煽情,更不愿一味地替人诉苦。他有自己的思考,却不愿意自己的思考代替乡民的思考,更不愿自己的思考影响读者的思考。他直面的是都市化中国的乡土性本身。在大踏步都市化的中国,这种乡土性有可能是都市化中国的动力,也有可能是都市化中国的阻力,但却没有对错。被都市生活方式快速围攻和清剿的乡土有着无奈与纠结,有长吁短叹也有欢笑,但一切都自然而然,相生相克,荣辱与共。
从字里行间,我分明能感受到,学文不但不越俎代庖式地为乡野、为乡民、为乡村叫苦叫屈,而且也没有虚妄地将乡野视为都市文明的对立面和美好传统的自留地、保留地。他化作了乡民中的一员,将变迁中的乡土中国的阵痛、不适和同时也有的轻快等复杂性、多样性不声不响、不卑不亢地呈现出来。
作为老友,在祝贺本书出版的同时,也祝愿他在繁忙的工作与不断的行走中,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记录,写出更多更好的佳作来。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山西长治
王学文《魔方:当代中国的仪式、演剧与乡土》,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