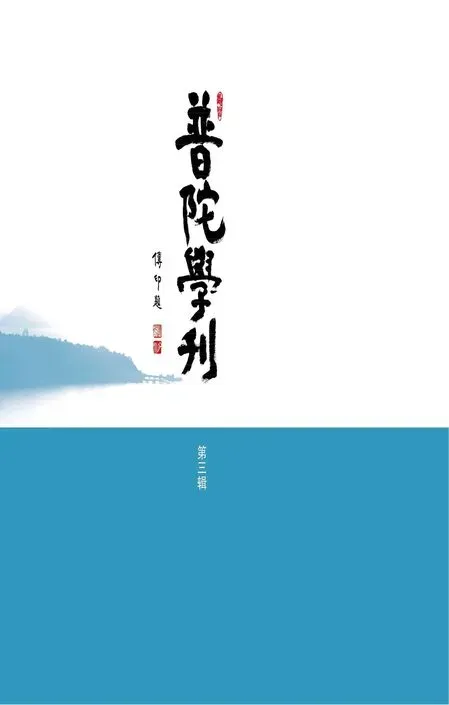论鸠摩罗什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因素
张培锋
(南开大学)
论鸠摩罗什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因素
张培锋
(南开大学)
一

对于法身是否有真实性问题,只能当作一种语言假设,不能作任何确定的回答。“因为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原则,在‘三界’认识中的佛,不可能超出虚妄的程度。因此,人们所谓的佛也好,法身也好,都不是实在的。”*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6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慧远的学生宗炳却沿着他老师“神本”式的诠释方向,越滑越远了。“无生则无身,无身而有神,法身之谓也。”“夫以法身之极灵,感妙众而化见,照神功以朗物。”*《弘明集》卷二,《明佛论》,《大正藏》第52册,第10页。“精神极,则超形独存。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也。”*《弘明集》卷三,《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大正藏》第52册,第2l页。显然持“神”即法身的论调。“在宗教观念上承认‘神’的永存,在现实世界肯定有作为事物本质的‘物种’实有,以及作为现象变化的因素‘生’的真实,是慧远佛教哲学的三大支点,也是有别于鸠摩罗什的最基本的方面。”*任继愈主编《中围佛教史》第二卷,第700页。“法身”理论、范畴之所以能够被道教哲学照搬、借鉴,至少说明中国佛教思想界秉持的“法身”观念与道体论思想之间有玄通之处。*参见黄崑威《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第126—131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
在鸠摩罗什所传中观般若学“扫一切相”的思潮下,慧远坚持从修行觉悟的主体方面去论证“法性实在”的本体论,并令“法性”本体与主体的本质建立内在的必然联系,表达出把世界的普遍本质与主体的真实本质等同起来的理论精神,从而为《大般涅槃经》传入后中国佛教涅槃学的转向做好了理论准备。其后,道生的佛性之说正是慧远理论精神的承续;而被方立天先生阐述为“将法性本体归为真心本体”、“将法性主体化”的《大乘起信论》亦展现了这一思维理路。*谢兴华《法性、法身与神》,《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
不管学术界存在着怎样的争议,这种道家化的、以道体论为宗旨,“将法性主体化”的思路确实是其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这一点不容否认。那么鸠摩罗什“扫一切相”的思想是否一定与“将法性主体化”相互矛盾呢?其实鸠摩罗什与慧远观念并无实质差异,若说有所区别的话,一就“真谛”而言,一就“俗谛”而言,观察和阐述角度不同而已。而大乘空宗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真俗二谛并不对立,真俗不二、空有不二,不可偏废,因此罗什与慧远两人的观点是相辅相成而非矛盾的关系。将他们对立起来非古人之过,而是当代一些学者受主客二元对立观念影响甚深的表现。
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一文*孙昌武《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将鸠摩罗什放到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观点。孙先生认为鸠摩罗什的贡献不仅仅限于佛教领域,实际上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相当巨大的影响,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比如罗什翻译过程中往往有意变易原意,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如日本学者中村元所指出:“鸠摩罗什在汉译佛教经典时,并未忠实地翻译了原文;或是大篇幅地改变了原文的内容,或是在译文中糅进了自己的思想。”他举出《维摩经》为例,将藏文译本(这是更忠实于梵本的译本)和其他汉文译本对照,发现“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部分”什译有若干迥异之处。例如“在肯定人们被烦恼所苦而迷妄生存的本身即为菩提这一点上,罗什的译本是最彻底的”,又“原文并未出现,而由译者插入的诸如‘孝’、‘忠孝’等词语比较多”,等等。意译的翻译法其实体现着一种文化本位观念,这说明,鸠摩罗什本身即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因素不容忽视。此外,在后世对世俗社会影响巨大的佛教净土宗,显然建立于“法性主体化”这一理论根基之上,否则净土宗便难以成立,慧远被尊为“净宗初祖”是有其原因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一点,至今佛教寺院晚课必诵的净土宗根本经典之一的《佛说阿弥陀经》所使用的译本即为鸠摩罗什所译,如果鸠摩罗什真的“扫一切相”,那么他会选择并翻译这部净土宗的经典吗?*很多人认为《佛说阿弥陀经》执于事相而少有哲理,其实不然。对此作出充分揭示的是明代高僧袾宏的《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其注解《阿弥陀经》文句,皆分事、理。如经中“池中莲花,大如车轮”一句,既从事相上指出西方极乐世界确有莲花,又谓:“称理,则自性清静光明,是莲花义”等等。盖理事本来圆融无碍,一体同观,不可分割,说莲花只是一种自性的显现与说确有莲花毫不矛盾,只是不同的经典所言有所侧重而已。在中国大乘佛教看来,这正是法界所蕴含的极大秘密。研治中国佛教思想,不可不重视中国佛教这一根本要旨。

又,佛教徒演唱经文所用的“辞赋”之“辞”正是中国传统“清商”、“相和”之乐。《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所谓“改梵为秦”,正是梵音在中国向“秦”地保存之楚汉旧乐转化的历史记录。任二北先生说:“(敦煌曲)《悉昙颂》……此调用秦音。和声既多,又叶仄韵。”这正是“改梵为秦”之“秦音”,是汉世一人唱,众人和之《相和歌》的旁证。*参看牛龙菲《古乐发隐》第420—42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情况,须通盘考察,方能明鸠摩罗什思想中中国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
二
鸠摩罗什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我以为最重要的正是实相本体观念,也就是中国传统“道”的观念。这种观念经过其弟子僧肇等人及其后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禅宗惠能等人发挥,成为中国大乘佛教最核心的观念之一。
鸠摩罗什曾为《维摩经》译文作注,出言成章,不待删改,其文保存与僧肇的《注维摩诘经》中。他存世的一些偈文,皆辞理婉约,韵味深长,可见其汉语修养之高。兹从《注维摩诘经》中选取若干注文片段,并略作案语以阐发其意:
《注维摩诘经》卷二:
【经文】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
【注文】什曰:此章大明至定,以诲未能,非独明空也。菩萨安心真境,识不外驰,是心不现也;法化之身,超于三界,是身心俱隐,禅定之极也。声闻虽能藏心实法,未能不见其身,身见三界则受累于物,故隐而犹现,未为善摄也。亦云:身子于时入灭尽定,能令心隐,其身犹现,故讥之也。肇曰:夫法身之宴坐,形神俱灭,道绝常境,视听所不及,岂复现身于三界?修意而为定哉,舍利弗犹有世报生身及世报意根,故以人间为烦扰,而宴坐林下,未能形神无迹,故致斯呵。凡呵之兴,意在多益,岂存彼我以是非为心乎?*《大正藏》第38册,第344页中。
按,法化之身——法身,是超于三界的,故其身不现,身心俱隐。法身的这种性质即是《老子》第十四章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体。
卷三:
【经文】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
【注文】什曰:法要谓一切法,略说有二种,有为无为也。迦旃延于后演有为则四非常,无为则寂灭义也。肇曰:如来常略说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无为法,寂灭不动。*同上,第353页中。
【经文】所以者何?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
【注文】肇曰:夫出家之意,妙存无为,无为之道岂容有功德利乎?生曰。正以无利无功德,为出家理也。
【经文】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
【注文】什曰:无漏道品,一切法及律仪,皆名出家法,出家法皆名无利也。若世俗法,则受生死不绝,报利愈积。若出家法于今虽有,终期则无。何以言之?本欲假事以息事,因有以之无,将出于功德之域,入于无利之境,无利之境即涅槃也。今就有利而言无利,是因中说果也。肇曰:夫有无为之果,必有无为之因,因果同相,自然之道也。出家者为无为,即无为之因也。无为无利无功德,当知出家亦然矣。生曰:无为是表理之法,故无实功德利也。*《大正藏》第38册,第357页下。
按,这两节经文与注文直接用道家的“有为”与“无为”概念来解释佛法,大致来说 ,有为法属世间法,为权法,为俗谛;无为法为出世间法,为实法,为真谛。
【经文】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
【注文】肇曰:犹诲以平等也,夫若能齐是非、一好丑者,虽复上同如来,不以为尊,下等六师,不以为卑。何则?天地一指,万物一观,邪正虽殊,其性不二,岂有如来独尊,而六师独卑乎?*同上,第350页下。
【经文】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
【注文】什曰:若去我而有无我,犹未免于我也。何以知之?凡言我,即主也。经云有二十二根,二十二根亦即二十二主也。虽云无真宰,而有事用之主,是犹废主而立主也,故于我、无我而不二,乃无我耳。肇曰:小乘以封我为累,故尊于无我,无我既尊,则于我为二。大乘是非齐旨,二者不殊,为无我义也。生曰: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同上,第354页中。
按,僧肇这两段注文,尤其明显用老庄思想阐解佛法,亦是自骨髓深处悟入,绝非表面词语的格义。它所包含的最重要内涵即是平等思想,一切众生皆平等,其文化根基是华夏文化“百虑一致”、“心同理同”等重要思想观念,即不同的文化、学说在本质上皆一致。*参看钱锺书《管锥编》第49—50页对《易经》;第389—391页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阐发,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国大乘佛教完全吸纳了这种思想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种包容性、平等性背后所体现的和平、和谐精神正是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思想形态的大乘佛教最宝贵的思想价值所在。
这里还需要辨析一个问题,我们在此强调鸠摩罗什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是否是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立场,有意排斥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呢?不是。因为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因素恰恰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界限,寓含着整个人类乃至法界众生一切平等的观念。小乘佛教不承认这种观念,因此为大乘佛教空宗所呵责,但大乘佛教却从来没有说小乘佛教不是佛教,在权乘、俗谛意义上,小乘佛教当然属于佛教的一部分,儒、道等皆可作如是观。另外,很多人对于南北朝以来的佛道汇通问题多持某种观点,或以为道教抄袭佛教,或认为佛教剽窃道家,还有说得好听一些叫做“借鉴”。实际上,若真正以“众生皆如”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事,则根本不可以用“抄袭”、“剽窃”这类此句作出解释,甚至也不是所谓“借鉴”。世间所有典籍著述不过都是对同一大道的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阐发而已。我以为,作为一位来自西域、被当时很多中原人士视为“夷狄”的僧人,鸠摩罗什所传扬和代表的这样一种佛教思想尤其显得非常宝贵。
卷四:
【经文】教化众生而起于空。
【注文】什曰:是弃众生法也,当为化众生而起空也。肇曰:存众生则乖空义,存空义则舍众生。善通法相,虚空其怀,终日化众生,终日不乖空也。
【经文】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
【注文】什曰:无相则绝为,故诲令不舍也。肇曰:即有而无,故能起无相;即无而有,故能不舍。不舍故万法兼备,起无故美恶齐旨也。*《大正藏》第38册,第369页上。
按,这一节注文是对道家有无相生之理的阐述,无相与有相、无为与有为等皆作如是观,所以真谛与俗谛不二,不可对立起来。
【经文】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
【注文】肇曰:万品虽殊,未有不如。如者,将齐是非、一愚智,以成无记无得义也。*同上,第362页上。
【经文】谛是道场,不诳世间故。
【注文】什曰:小乘中说四谛,大乘中说一谛。今言谛是则一谛,一谛,实相也。俗数法虚妄,谓言有而更无,谓言无而更有,是诳人也。见余谛谓言,必除我惑,而不免妄想,亦是诳也。今一谛无此众过,故不诳人也。从一谛乃至诸法无我,是诸法实相,即一谛中异句异味也。由此一谛故佛道得成,一谛即是佛因,故名道场也。*同上,第364页下。
按,这一节阐述也极为重要,实开启天台等宗派“会三归一”的先河。所谓一谛,即是实相,即是道体,是成佛之因,其思想来源应是《老子》第二十二章所谓“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参看《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载道士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赡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见《南齐书》第934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和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谓:
诸所说法,随其义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众生,心之所行,心所动作,心所戏论,皆悉知之。虽未得无漏智慧,而其意根清净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筹量言说,皆是佛法,无不真实,亦是先佛经中所说。*《大正藏》第9册,第50页上。
这里“亦是先佛经中所说”一句极耐寻味,其意应为:在有此佛经之前,此理已先天存在、本然存在,佛经也只是将其表述出来而已。这种先天、本然的存在即是先天地而生、化生万物的“道”。
卷八:
【经文】现见菩萨曰:尽不尽为二法,若究竟尽。
【注文】什曰:无常是空之初门,破法不尽,名为不尽。若乃至一念不住,则无有生,无有生则生尽,生尽则毕竟空,是名为尽也。
【经文】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不尽相,如是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注文】肇曰:有为虚伪法,无常故名尽。实相无为法,常住故不尽。若以尽为尽,以不尽为不尽者,皆二法也。若能悟尽不尽,俱无尽相者,则入一空不二法门也。*《大正藏》第38册,第397页下。
卷九:
【经文】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无阂法门。
【注文】什曰:尽有二种,一无为尽,二有为尽。有为尽,无常迁灭尽也;无为尽,智慧断令灭尽也。今言尽门,是有为无常尽也。言无阂,于二事不阂也。不尽功德有为,无凡夫阂也;不住无为,无二乘阂也。
【经文】不住无为。
【注文】肇曰:有为虽伪,舍之则大业不成;无为虽实,住之则慧心不明。是以菩萨不尽有为,故德无不就;不住无为,故道无不覆。至能出生入死,遇物斯乘,在净而净不以为欣,处秽而秽不以为戚,应彼而动于我无为,此诸佛平等不思议之道也。夫不思议道,必出乎尽不尽门,彼菩萨闻佛事平等不可思议,所以请法,故佛开此二门,示其不思议无阂之道也。
【经文】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
【注文】什曰:慈悲,佛道根本也,声闻无此故,尽有住无也。欲不尽有为,成就佛道,要由慈悲,故先说也。肇曰:慈悲乃入有之基,树德之本,故发言有之。生曰:菩萨之行,凡有二业,功德也,智慧也。功德在始,智慧居终。不尽有为,义在前,故功德不尽之也。住无为,义在后,故智慧不住之也。不尽有为,是求理,不舍生死之怀,以慈悲为本,故始明之焉。*《大正藏》第38册,第406页中。
按,以上进一步通过对“有为法”、“无为法”的辨析,阐明真俗二谛必须融通的道理,揭示大乘佛教净秽平等的要旨、慈悲智慧双运的内涵,尤其深刻。慈悲之道即佛法在入世应用的体现,有无慈悲是小乘与大乘相区别的重要标志,而这一切都通过“有为”与“无为”这一组概念来展开,可见道家思想与大乘佛教空宗绝非字面的“格义”而是深入至骨髓的。
史载鸠摩罗什曾将《老子》一书译为梵语,但这个译本已佚,无从考察。又记载罗什与僧肇等人亦曾对《老子》一书做过注解,翻译与注解似乎应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诔》亦谓:“(罗什)融冶常道,尽重玄之妙;闲邪悟俗,穷名教之美。言既适时,理有圆会。”*《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大正藏》第52册,第264页。但这个注解也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尽管如此,罗什翻译并注解《老子》这一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或许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远的传承。
好在蒙文通先生《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一书中辑录了罗什和僧肇的零星注文,*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巴蜀书社,成都,2001年版。参见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道藏》第13册。黄崑威《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据此作出整理,第310—315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黄崑威《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据此作出整理。(第126—131页,巴蜀书社,2011年版,转录于下。)我以为尽管仅存片言只语,但很多论述仍可与前举罗什等人对《维摩诘经》所作阐发相互对照,可以推想:当初鸠摩罗什注《维摩诘经》和其注《老子》堪称双璧,共同阐发着那个佛道一体的“大道”:
《第二章》:“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句“罗曰:人之受形,皆智爱形而贪名。其所贪惜,无非名善,此善无善,不免诸苦。名虽称遂,无益于己。”“故有无相生”句“肇曰:有无相生,其犹有高必有下。然则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无之表者以祛之。”
《第十二章》:“五音令人耳聋”句“罗曰:不知即色之空与声相空,与聋盲何异?”
《第十三章》:“贵大患若身”句“肇云:大患莫若于有身,故灭身以归无。”
《第二十章》:“绝学无忧”句“肇曰: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
《第二十三章》:“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句“肇曰:真者同真,伪者同伪,灵照冥谐,一彼实相,无得无失,无净无秽,明与无明等也。”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句“罗曰:妙理常存,名为有物,万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第二十八章》:“复归于无极”句“罗曰:忒谓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动与机合,德行相应,为物楷式,显行成行,隐复归道,道本不穷,故成无极。一是智慧无极,二是慧命无极。”
《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寿”句“罗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寿。”
《第三十七章》:“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句“罗曰:心得一空,资用不失,万物从化,伏邪归正。”
《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句“罗曰:智无不积为满,空而能正曰冲。言大满之人能忘其满,虽满若虚,虚则不竭,用能如此,则无穷极。”
“大直若曲”句“罗曰:理正无邪曰直,随物曲成为屈。”
“大辩若讷”句“罗曰:智无不周为大辩,非法不说故称讷。”
《第四十八章》:“为学曰益,为道曰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句“罗曰:损之者,无尘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恶;然后无细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恶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损其非,又损其是,故曰损之又损。是非俱忘,情欲既断,德与道合,至于无为。己虽无为,任万物之自为,故无不为也。”
《第五十章》:“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投其爪,兵无所投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也”句“罗曰:地犹生也,以其摄生无生,故三毒不能伤害。”
《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句“王及罗什二家云:介,小也。我小有所知,则使行于大道也。”“肇曰:有所知,则有所不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贼也。”
“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句“罗曰:取其非有曰盗,贵己之能曰夸。”
《第六十二章》:“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句“罗曰:回向善道,以免诸恶。”
《第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难”句“罗曰:轻而不修,报之必重也。”
《第六十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句“罗曰:心形既空,孰能与无物者争。”
《第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句“罗曰:心定所行,果而忘得,真去邪来,遂获其罪,故言杀。”
“勇于不敢则活”句“罗曰:行柔弱,惟善是与,则获其利。言活活,长生也。若进心虚淡,不敢贪染,则长生。”
《第七十七章》:“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人不欲见贤”句“罗曰:得此虚通而无思无虑,岂有心智而欲贵已之贤,能不恃其为,无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无自满之志,恃为处功则见贤,见贤则是以有余自奉,招损之道也。”
三
作为一位从龟兹来到中原地区的佛教僧人,鸠摩罗什有很好的汉语基础并深受华夏文化影响,这一点似乎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是不难得到解释的。这个问题较复杂,笔者将有专著作出阐述,这里只提出一些结论性的观点:我认为这与自古传说的“老子化胡”有着密切关系,“老子化胡”的实际情形是早期一批道家学派人物——老子应该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从西周末期即开始长达数百年的大规模西移,将道家学说及华夏礼乐文化传播到西域地区,其后又与传播于此地的小乘佛教思想融合,最终形成大乘佛教空宗。因此大乘佛教空宗在最根本的思想层面上与道家思想相通而不是传播到汉地之后才开始中国化的。鸠摩罗什所在的龟兹地区正是西域大乘佛教空宗发展的重要地区。
有关西域存留华夏文化这一点,由于史料的极度缺乏,确实很难作出切实的证明。但是近年来一些考古学者特别是音乐考古学者对于西域的华夏文化遗迹作出过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其观点值得借鉴。牛龙菲先生《古乐发隐》一书主要以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上的乐器为考证对象,对于西域地区古乐文明作出很多富有新意的阐发,具有真知灼见。这里引述他的若干观点:
佛教早在汉代,龟兹音乐已经受到了楚汉乐文化的影响。正是在汉族高度音乐文化的影响之下,龟兹音乐渐渐发达起来,以至于后来去西土求经的唐玄奘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但究其原始,仍是楚汉音乐文化的遗风。正因为如此,在“礼崩乐坏”的魏晋之际,龟兹与凉州一样,都是楚汉音乐文化的保留之地。“土龟兹”,“齐朝龟兹”可以并入西凉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吕光从龟兹得来的“土龟兹”,与凉州所传汉魏旧乐互相融合,便成为“齐朝龟兹”。这种龟兹乐,实际上是楚汉音乐的遗声,因之号为“秦汉伎”。*牛龙菲《古乐发隐》第1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牛龙菲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说:
过去许多学者,都把它当成了西域音乐东渐的记录,从不曾有人指出,这不过是早先西渐之中原华夏音乐的回授。*同上,第172页。
凡此种种,都是先秦古律的遗风流韵。过去一些中外学者,把光辉灿烂之大唐盛世,称作“伊朗式的繁荣”,把叹为观止的隋唐乐舞,完全视为“胡乐”。郭沫若先生就曾说过:“与西乐为对的所谓国乐,其乐理,乐调、乐器,强半都是外来的,而且自南北朝以来,这些外来成份在国乐中实占领导地位。”这些话,现在看来确是说过了头。在远至夏商时代文化之超出今人原先想象的发达程度渐被世人认识的今天,对一些在秦汉以至隋唐之后西域文明的东渐,当先检验其是否系夏商先秦以及秦汉时远播于世界各地之中国固有文化的回授。*同上,第186页。
为何远在西域的龟兹能够“固存华夏礼乐文化”呢?这种中华礼乐文化又是何时传入龟兹这些地区的呢?牛龙菲等先生将其上限定为汉末礼乐崩坏时期,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西域地区在汉末中原丧乱之至,之所以能够发挥传承华夏礼乐文化的作用,是因为在此之前,其地域早已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化,并实际上成为这种文化的中心地区。吴涛所著《龟兹佛教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一书指出:从汉代起,龟兹地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应该是汉文和龟兹文两种文字并行。关于古代龟兹人民习用汉语,史书和考古材料都有记载和发现。他以一个具体例证为据,作出汉代龟兹地区流行汉语的推测。据《汉书·西域传》载:
(龟兹王绛宾)元康元年(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奇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人。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徹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从这段记载看,龟兹与汉朝来往如此密切,习染汉文化如此之深,在西域诸国是十分突出的。绛宾的儿子名丞德,丞与承通,“丞德”义为承继其父之德业,此名为汉名无疑。另外,前述在拜城境内发现的“刘平国治关亭颂”刻石上,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文,据《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条载,谓其王诸属官有左右将。《后汉书·班超传》又记:“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遗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可知刘平国为龟兹的左将军无疑。刘平国是龟兹国人,但采用汉文名字。*吴涛《龟兹佛教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第59—6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都表明汉文在汉代已成为龟兹国官府和民间较常使用的语言文字之一,这是西域地区自古受汉文化影响的记录。总之,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应该即有大量汉人居住,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地区“崩坏”了的华夏礼乐文化在此继续延续和传播着。
古龟兹地区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转变为信仰大乘佛教的过程,其中关系确实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这很可能证明:西域之大乘佛教并非由外部传入,而是印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与华夏文化结合后的产物,大乘佛教正是在西域地区由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与华夏文化融合后形成的。说一切有部的基本信仰是“唯礼释伽”,基本主张是“三世恒有,法体恒有”,同时持律严格,师承有序,教阶森严,僧团组织严密,重苦修,主张渐进成佛。而鸠摩罗什所传播的大乘佛教与此有着明显的不同,也有史料表明,他当时在西域是受到来自小乘佛教学者的诋毁甚至迫害的。佛教史家一般认为,大乘佛教在龟兹传播大约在公元2—3世纪前后。据《开元释教录》卷二记载,曹魏时期,有龟兹沙门白延游化洛阳,于甘露三年(258年)在白马寺译出大乘经典《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及小乘经典《除灾患经》1卷等。白延之后,在西晋慧帝时(290—306年)又有龟兹沙门帛法巨与汉僧法立共译佛典4部12卷,其中《大方等如来藏经》即属大乘经典,而这些经典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某种道家思想因素。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大力弘扬及其声望的日益提高,大乘佛教在龟兹的影响逐渐扩大。罗什到中原后,广译各种大乘经典,对后来中国佛教之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究其根本,是因为鸠摩罗什所传播的佛教思想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因素,而这种因素又是促成佛教能够超越其民族性而真正成为一种全人类的、世界性的宗教的重要根源。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