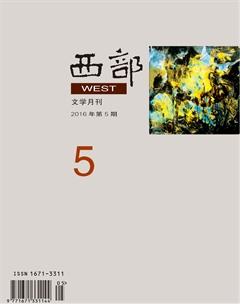学术与思想的双重反思(访谈)
夏中义 张蕴艳
张蕴艳:您好,这是我自1998年跟随您研习文艺学与百年中国文论史案以来与您的第三次公开访谈了。上一次访谈距今也有四五年之久了,不少问题也需要再作斟酌。上几次我们谈话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史、精神史与现时代学人角色价值与活法等话题上,今天我想在此基础上再作一些拓展,谈谈当代文艺学研究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史、精神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兼及您个人的精神小史与微观学术思想史。 先是反映论问题。反映论问题无疑是二十世纪文艺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您近年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反映论与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源流考辨》《反映论与〈文心雕龙创作论〉——对王元化的照着说与接着说》《反映论与王元化——论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等,涉及中苏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与事件,您是希望从诸多个案出发对反映论作一个系统梳理吗?1980年代您致力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时,就可看到隐含的对反映论的批判,您现在对反映论的清理是否可看作一次直接、正面的批评?
夏中义:先说我和反映论建立的关系。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母校执教,有幸参与的第一个正规的学术年会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言选了三个代表,一个是老年代表,一个是中青年代表,一个是青年教师代表。老年代表是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中青年代表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徐文玉;青年教师代表就是我。大会发言文章是我在做徐中玉先生带的硕士时旁听时所写。他当时的硕士生有两个,一个是南帆,南帆当时刚刚从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考过来,那时是1982年春天。还有一个是后来成了王元化的博士生,现在是母校王元化研究中心主任的陆晓光,陆晓光是我的本科同窗。徐中玉给我们第一节课出的题目就是怎么看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让我先讲。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学四年我都在做美学研究,研究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的本科论文也是做西方美学史的,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一下子要我对以群的权威的教科书发表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个好不是说对以群说好,而是说我对发言质量必须有准备。于是我就拟了一个稿子,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以群的教材为何不尽如人意。这个方法论就是反映论。我的基本观点是,以群的教材把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思维准则或哲学指导,整个就错了。因为反映论是一个科学认知层面的哲学方法论,它只关注对象的特征,关心对象的存在样式,科学认知将这么一种反映论的特质演绎到了极致,假如你要写下对象认识的考察报告,他们从来要自觉屏蔽主体对对象存在的任何情态,更谈不上对对象的想象也可写入对对象的考察报告,反映论只讲在对象面前人要激发出一个世界是什么的回答。当你用纯知性的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时,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的情感想象就被这个方法屏蔽了,这有点儿像用高射炮打蚊子,打不着的。错在哪里?第一,我用原始艺术的发生去讲。原始人类创造原始艺术的原动力是什么?假如用反映论去讲,就是摹仿。摹仿说就是解释原始艺术发生的反映论。但是我们深入到欧洲的话,洞穴壁上栩栩如生的刻画勾勒,也可用摹仿说解释,但这是很肤浅的一种解释。为何原始部落要把自己捕猎的动物刻在如此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中?用巫术心理、原始心理就很好解释。原始心理认为宇宙万物都存在着神秘的关联,意味着假如你在原始人背后走,你的脚踩着他地上的身影,他会咒你的。原始人认为他生命的安危与你踩在他投在地上的阴影有关。为了能表达对遥远的未来捕获猎物的憧憬,他就把猎物的形象刻在猎物眼睛根本看不到的洞穴深处,这寄托了一种祈祷。巫术心理这个内核就叫神秘的互渗规律。列维·布留尔对此有很多研究。第二,为什么以群用反映论阐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二环论,一个圈是社会,一个圈是文学,作家是镜子。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再现,这不就是以群的文学原理么?为什么形象再现就是镜像?作家的全部创造作用,就被简化为一面镜子。作家的心理、情感、想象要么不被研究,要么挤在很小的角落。反映论要求作家要有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作指导,也就是要求作家的眼睛一定要看到权力意志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而不让他们看到权力意志不情愿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这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可以这样和反映论很生硬地挂起钩。还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形式永远是跟着内容走的,内容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每一个真正研究文学艺术的人都知道形式是有独立意义的。所以好就好在我当时不但读了列维·布留尔,还读了李泽厚《美的历程》。美的积淀说就是说形式不仅仅是形式,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形式有独立于内容表达的一种生命,这就是审美情趣和生命意绪。形式也是有内涵的,这些内涵和社会生活没有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定义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和李泽厚所说的“艺术形式的意义在于审美情趣和生命意绪”没有关系。所以以群的文学原理对形式没有研究,他一讲形式就是体裁、语言、结构。其实你这个体裁哪里来的呢,叙事模式哪里就是结构,他讲不清楚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像王元化在1975年至1976年读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读到里面大量的微妙的审美创作心理,王元化在这样的丰富的文艺学遗产面前,他的态度是躲闪的,他只是说,啊,黑格尔真伟大。那些微妙的创作心理,他没有去深究。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张蕴艳:还是反映论的问题,我看到王元骧和朱立元有一个争论,朱立元似乎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与主体论作一切割?王元骧则致力于将主体论纳入到反映论中,强调反映论也是注重人的实践能动作用的,认为反映论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致力于挖掘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价值。
夏中义:首先得明确他们争论的时间。我说的是1982年的事,离今天已经三十四年了。时间要搞清楚,不然没有意义了,有个学术史的脉络问题。我1982年大会发言第二天,香港报纸《大碗报》头版就登了我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很大的标题,就像摩天轮上的大幅标语垂下来。我想我怎么那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中山大学会务组的一位青年教师对我说,夏中义你闯祸了,昨天晚上你的发言导致五分之三的老教授一夜没睡着,他们盘坐在蚊帐里骂你。有一个说夏中义你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有本事你自己写一本书。这就是我后来写的《艺术链》。当时那个小青年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后来才明白你骂以群就是骂他们那个群体,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内存中自认为很有分量的东西被我一下子否定掉了。所以你说的朱立元和王元骧的争议,我认为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王元骧就是以群的学生,他现在都九十岁了,他可以说是那代人里至今还在坚持的人。待会儿再说,反映论不是马克思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朱立元的声音很可能是在1985年后发出的。我去年发表的《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这篇文章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1985年大家其实都在用不同方式与反映论告别。主体论、科学主义、信息论、结构论、系统论,都是一种告别。当时把主体论做得最张扬的是刘再复。刘再复之所以高扬主体论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是他要推动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用对个体人格尊严的强调去抵抗“文革”时弥漫的不把人当人的思潮。“文革”要么把人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要么把人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为了告别这种思潮,提出主体论。当然始作俑者是李泽厚。文艺学上,引入主体论是为了突出艺术创作生产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的主导地位。接着就来讲讲反映论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想原型与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从来没有同意要把自己的思想变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至少说过,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面前,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原型思想,至少分三个阶段:一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以1844年《手稿》为代表;二是所谓成熟的马克思,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为代表,提倡阶级斗争,提倡以暴力打碎国家机器,提倡无产者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列宁就是根据这个理论领导了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说法,它是在资本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革命的成功必定会遭受各种各样力量的围剿,要用各种手段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但是他的理论到斯大林这里就演变为社会主义越接近成功,就越遭到更多的敌人的垂死挣扎。斯大林就计划阶级斗争,导致残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就在其麾下蓬蓬勃勃地展开,其实是血泪澎湃地展开。这些东西都不是马克思的。而且马克思晚年,尤其《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恢复了很多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人道情怀,你们去读1844年《巴黎手稿》,我就看到一个要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学者,他的原动力是对处在非人条件下、资本原始积累条件下艰难生存的无产阶级怀有的一种仁慈的爱。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其实是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的思想是第二国际的思路,放弃武装阶级斗争,和平掌握社会主义。现在欧洲是全世界享受国家福利最好的地区。严格讲英国的工党就是当年的第二国际政党。事实证明第二国际的路线没有错误。但是第二国际当年被列宁、斯大林、第三国际宣布为修正主义。而这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在晚年修正了自己中期暴力夺取政权的思路。所以把马克思原型思想压抑住,把他中期激进的思想放大、激进化,这是斯大林的想法。那么反映论是什么?马克思从来没说过反映论,反映论是列宁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提出的关键词说反映论有四个特点,一是人必须承认反映论之前提是物质存在先于人的存在;二是人对对象的认知不应以人的主体意志为转移;三是它是什么你就把它说成什么;四是书写科学考察报告时你不能赞叹,不能带入你对对象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评判。列宁讲得很清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仅仅是在回答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一非常有限定性的问题时才是有意义的。反映论也是这样,其实反映论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一种表达。假如放到二十世纪初,列宁这么讲反映论,把反映论作为科学认知的出发点和基础,列宁的水平是不高的,尤其要去抗衡量子物理学、高等物理学所面对的物质的深层结构复杂景观时,反映论根本是无效的。反映论是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有形的触摸基础上的,而深层结构肉眼根本看不见,只能大概描述。但因为列宁要和波格丹诺夫争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哲学话语权,所以他一定要用反映论去打倒对方。斯大林也把列宁的反映论接了过来。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也把列宁的反映论注入到文艺理论。最早是拉普派。说来话长,我在去年写的反映论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很细致了,也许以后会作更系统的梳理。从列宁到拉普,到日丹诺夫,到季莫非耶夫,到季莫非耶夫的学生毕达可夫,这个脉络非常清晰。
张蕴艳:是否可将您对反映论的反思理解为对百年来“历史决定论”思潮在中国文学学术领域的清理与反思?
夏中义: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这几年工作的一个选项。反映论反思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当代文艺学通过1985年的方法论后产生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当代文艺学研究从反映论框架里走出来,导致当代文艺学研究有了新的前景和出路。但这个反思的背景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不能回答为什么1949年至1979年整整三十年文艺学研究都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至少有三十年是受到了苏联理论模式的殖民,只有从这种殖民的角度才能够解释三十年文艺学研究把方法论全交给苏联理论模式的根源。那么什么是苏联理论模式?现在所说的苏联理论模式是王元化在1986年4月一次很重要的理论会议上作的讲话里出来的,是在安徽屯溪召开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年会。这个讲话很重要,他说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研究都没有逃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个深刻影响包括以下方面:一、研究一个学人是否合格,首先要检查他的政治出身与立场,哪怕研究古代文学也是这样。你去读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一篇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刘勰是出身豪族还是寒门?研究下来是寒门,是中小地主,是革命团结的对象,是可以研究的。所以他们研究一个人,就像组织部考察一个人可否入党一样的,查三代。这就是日丹诺夫模式,日丹诺夫模式我讲得太多了,就是两个正负三角形嘛。政治上的革命、进步或落后决定了哲学上唯物还是唯心,决定了艺术上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革命加上唯物加上现实主义就是红色的正确的三角形,反之就是反动的、黑色的、错误的负三角形。日丹诺夫大约于1947年左右形成他的理论。他1932年加入苏共,后被斯大林内定为接班人,他又是苏共中央政治文化纲领的设计者,这个政治文化纲领主要浓缩在这两个三角形里。王元化之所以说《文心雕龙》研究都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其实就是受到这两个三角形的影响。当然这个话是我说的。所以你们去读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会感到很奇怪的,它分上下编。上编第一篇研究出身。第二篇研究《灭祸论》,因为灭祸论与佛教有关,是唯心的。他一定要证明这个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写的,刘勰在写《文心雕龙》时还不是唯心的,所以《文心雕龙》还是可以研究的,划清界限。第三篇研究《文心雕龙》有没有唯物主义,有没有客观唯心论?他说有的,在讲到文学的宇宙发生的时候,那当然是客观唯心论的,但讲到创作论的时候,他认为是唯物论的。他称之为“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这就是合法性。第一,刘勰不太坏;第二,刘勰是唯物的;第三,刘勰的唯物主义在创作论中保持得很好。所以他有一本书叫《文心雕龙创作论》,明白吗?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实哪里是马克思主义,是日丹诺夫主义!所以王元骧也是,把苏联理论模式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三十年中国文艺理论,全交给反映论去主宰,是因为三十年尤其是前十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地盘全是被苏联理论模式所垄断的。假如不这么做,你要么受批判,要么被剥夺学术研究写作的权利。王元化之所以用苏联模式阐释《文心雕龙》,是因为1961年时他已经正式被打成了“反革命”,行政降六级,在上海作协图书馆当资料管理员,无事可干,要给自己和老婆孩子打个强心针,政治上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学术上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1962、1963年第一篇写《文心雕龙》的文章发表了,庄老玄言诗告退,谢灵运山水诗始承,他把这个状况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告退,唯物主义的兴起,这不是胡扯淡么?但是就是这样的胡扯,周扬如获至宝,马上让当时最权威的《文艺报》登出来了。王元化很高兴,给他老婆看,你看我说的有用吧?这话谁告诉我的?蓝云告诉我的。他把这种兴奋也传递给他当时的秘书蓝云。所以反映论一是方法论的问题,二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三分之一的时间被苏联理论所笼罩,在我看来这是民族国家的一种羞辱,中国学术的国耻。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全面在国内文史哲学界展开,假如是这样的话,三十年的文史哲史全部得重新审视。我还可以说,这三十年获得学界地位的那些人,几乎都是带着病菌的那些人,包括李泽厚、王元化、朱光潜,几乎没有例外。只有两个人没有牵进去,一个是陈寅恪,他用反映论的话根本无法做陈端生的《再生缘》,也无法做《柳如是别传》;还有一个,我现在还在研究钱锺书。钱锺书很有意思,1957年写《宋诗选注》,一方面讲反映论,另一方面又在洗刷反映论。他在跟反映论开玩笑,但没人知道他在跟反映论开玩笑。这大概是我今年要写的一篇文章。
张蕴艳:《宋诗选注》我以前看过,是很有意思的。
夏中义:太有意思了。今天就不讲了。
张蕴艳:回过头来,怎么看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您早在《新潮学案》一书中就已论及,还有早些年的论文如《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一文中,评判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为“犹带梦痕的复苏主题”,即在肯定他对文艺心理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的同时,批评他将认知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作了机械的嫁接,对文艺的独立的审美特性挖掘不到位。但是站在今天的语境下来回顾,文艺心理学从边缘学科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度繁盛几近达到文艺学的中心位置,再到后来的衰退与再度边缘化,与它过多地运用心理学眼光去看待艺术经验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内涵,是否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过于强调审美的独立性是否会因此封闭了艺术经验的丰富性?这样本来是本着关注文艺家的主体地位的目的而切入研究的文艺心理学,会不会反过来因为忽略了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内容而取消了主体性?它是否应该重建与认知心理学的新关系,即避免在庸俗反映论对艺术与社会的机械嫁接基础上的一种新的艺术社会学?我知道,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您在二十世纪百年学案研究中将之作了改造并再创为文献—发生学方法,且运用得得心应手,这里似乎就可看到对文艺心理学方法的内涵向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敞开的倾向,但未作清晰的表述。事实上,审美论也一直是您坚持并自信的方向,它难道没有限度吗?
夏中义:好,我讲两点。第一点是1985年前后文艺心理学逐渐成为新时期文论新潮主要的角色,那么一个理论史的脉络非常清晰的。1949年到1979年的文艺学为什么没有一点文学的味道、美的味道,不能回答文学的美丽是什么?因为反映论只关注对象的认知。后来的政治就将这种认知说成是由一个革命的意志所掌控的历史的规律和社会生活的真实。这就将作家的个人经验和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屏蔽掉了,用洪子诚的话就是“一体化”了。把这个东西打掉了就意味着恢复了作家艺术家作为一个创作主体,恢复了一个读者作为一个审美主体在艺术经验的创造以及艺术经验的传播王国里的一个公民角色、主人公角色。所以文艺心理学从反映论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中释放出来,它马上就绽放了。后来在1980年代几乎成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中心地位。第二,文艺心理学在1985年前后成为中国文论新潮的主角地位,恰恰说明它回应了学术史的需求,也没有辜负学术史对它的一种寄托。假如承认这一点,我很欣慰的。我就有资格这么说,《艺术链》在1988年的诞生也许可以为学术史家提供一块化石。从它可以提供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走了多远。那当然要比以前远得多,我想也要比鲁枢元远得多,但再远也有它的边界和局限性。第三,有边界,有局限性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是没有边界的呢。真理、美都在边界里面。你可以说我现在的知识,我对某个对象的把握,我都把它放在边界里面。我并不是说边界外面就没有真理没有美,但边界外面的真理和美是我的文艺心理学还不能去阐释的。文艺心理学怎么能够包纳天下?!内科医生把心脏病、肺病看好就很好了,骨折这样的毛病不要让内科医生看。一个人骨折了就要到骨科。明白吗?任何学科和学术都有边界,问题在于它在所设定的语境里面能不能把应该面对的对象说清楚。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小张你在方法论里面是有一个乌托邦的。你最好有这么一个方法,什么都能应对,既能应对文学艺术的每个意象,像情感、灵感是什么,又能回答社会政治历史。哪有这样的方法论可以涵盖一切呢。涵盖一切的东西是有的,肯定是粗放的,细腻的东西它是表达不了的。我觉得有三种乌托邦,一种是个人的人格乌托邦。你现在信教,对每一个信徒而言,你可以按照《圣经》对完美人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是可以的,这就是人格乌托邦。人格乌托邦是不影响他人的,我觉得人格乌托邦是非常美丽的,但你不能说你相信这个美丽,你要将它作为一个民族的人类的普遍性。比如你要将你的东西加在我的身上,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觉得你们很多东西都是幼稚的,但我尊重你们的信仰,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因为这就是我的一种尊重。每一种信仰,当一个人去信它的时候,总有他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你有选择信仰的自由,我必须尊重你的自由,只要你不把你的信仰强加在我身上,我也不能去玷污、轻佻地言说你的信仰。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张你身上发现的,思维方式的乌托邦。你总希望有这么一个包罗宇宙万象的回答人世间全部精神现象,终极的,完美的,就像百科全书那样的,对所有问题都能回答完美的方法论,我认为是没有的,就像没有这样的医学一样。假如这个问题回答了,我就要说你为什么要让文艺心理学去回答社会政治历史,要让它承担那么多功能呢。它承担不起的。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呢?为什么不重新打造一个篮子?所以我在学术史案和思潮史案的时候,我注重个案,我就提出了“文献发生学”,这是什么你已经很清楚了。文献发生学并不是简单对文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延伸,它们本来就在承担不同的功能。文艺心理学要承担的是文学艺术的本性是审美的,这是与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富有天才质感的心灵独特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东西以前是被体系所磨灭掉的。我要把这些压抑的磨灭掉的东西释放出来,文艺心理学是一个最好的品牌。后来我要做百年中国文艺史,我要一块一块石头摸过来。于是文艺家在百年学史的过程中作用就特别明显。这是我的抓手。为什么这个理论家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个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会赢得某种程度的认同?为什么这种理论一提出来明明有正当性会造成这样压抑等,都可以从文献发生学里找到根。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理论,这就是文献的问题,那个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就是发生学的问题。而这个发生学又把他所经历的历史和事件浓缩在个体身上了,所以可以从发生学上看到很多历史、社会、心理的有趣事件。因为他承受不了历史的高压而产生了精神的变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塞到文艺心理学里面呢?这完全是两个东西。所以有骨科,有眼科,有皮肤科,精神病还有各种类型的呢。不要把所有的都塞到一个东西里面去,就是文艺心理学它也回答不了微妙的艺术的创造。你这些年接触了太多号称要做社会文艺学、文艺社会学等,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和选项。我有我的选项。我们可以并存比赛,看谁在各自的领域做得更好,但我做得再好也不能做你的东西,你做得再好也不能做我的东西。这是我今天很愿意说的话。不要在思维方法层面上建立一个终极的乌托邦,没有这么一个乌托邦的,你就是有也是混沌的。而科学与学术是要讲究精细。不怕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把问题讲得很透实,而不要好像什么都承包,没有这样的事。
张蕴艳:下面这个问题,跟上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您刚刚也回答了一些,但是我感觉还有一些空白和疑点可以再讨论一下。就是审美论的批判性和局限性。我看到一篇早年您与孙绍振先生的访谈,谈到文学的工具论和目的论。他谈到早在1942年文学工具论达到高潮,到“文革”时,“写中心”“演中心”“三突出”、样板戏更是演化成文化专制,而一步步收紧的表征之一,就是五十年代胡风的“五把刀子”到“文革”时期变成“一把刀子”。这个您在朱光潜研究中也有深入的分析。那么针对文学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变成文化的传声筒而言,就是审美论的提出对工具论批判是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但从文学启蒙的未完成性来说(这一点李慎之先生八十年代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一文我们都是认同的),审美论有时是不够用的,它没有办法全面回答文学在“文革”之后,人民在普遍告别和厌弃革命的情绪之后,文学怎么重建和政治的关系,审美也会因粉饰现实的问题而掩盖了真。看过您评论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的大作,也是基于对文学的审美维度被遮蔽、文学臣服于政治的历史的回答。因为近些年也有很多学者讨论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审美论有自己的合理限度,现在先生是不是可以回答再政治化的问题。
夏中义:再政治化提的比较早的是蔡翔。王晓明、钱理群都有这样一种意念,但是把它说出来的是蔡翔。我先说有好几层意思。最不好的就是认为自己把握了宇宙的真理,就垄断了社会的全部政治文化经济思想。这是最不好的。当一种公权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凌驾于所有人的头上,这就是垄断。文艺理论1985年方法论热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论讨论的背景里把文学的本性应该是什么,非功利地从工具论里解放出来。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学科的重建,其实是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性被确认、非功利性存在的被确认为前提的,它们是伴生关系。当文学的审美的本色非功利性地存在的正当性被学界以这样的态势和力度所认定,这是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很可珍惜的场景,因为很不容易。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政治不仅仅是专制。在汉语语境里面,往往把政治等同于专制,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因为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就等于专制。但是假如我们不是把政治看成共和国当代史上的某一段事件中的重大现象,而是将政治还原到人类活动的广阔背景,政治的特点不是集权,政治的本义是对社会公众的重大裨益的制度性分配,这才叫政治。政治永远是和利益在一起的。问题是私利,是一个人的私利,一个特权阶层的私利,一个政党的私利,还是把政治还原为它的本色,是对社会的合法公民的权利的制度性分配的活动和场域。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个他尽了义务承担了责任的社会里,是否能够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这才是政治的本义。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我可以说,给文学以自由以个性的解放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把文学绑在特权的战车上,只能让它发出权力的声音的政治肯定是不好的政治。所以我其实很了解“再度政治化”,这就是蔡翔同志希望当代文学能够发出像左联时期的文学的声音,就像要写出当年夏衍的《包身工》这样的作品就叫“再政治化”。这样的“再政治化”是有意义的,就是让作家用审美的眼光在对待自己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同时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但这个问题严格地讲,不是文艺心理学的。这个问题是和艺术家的人文修养,和一个要代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在个人的道路与勇气上能提升到什么程度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完全是两个问题,这和文学是不是政治化完全是两回事情。如果单纯提文学的政治化,文学又将变成口号和标语。一个再关心历史人类民族命运的艺术家,他不会通过把艺术廉价地卖给政治来完成自己的公共化。假如我们考虑到列夫·托尔斯泰,列宁都说他是表达俄罗斯农民阶级情绪和愤怒的一面镜子,但是谁能够从他的作品中读出农民的情绪呢?只有极其专业的、敏锐的、天才的读者才能读出来。假如把他的作品给蔡翔看,他能有列宁的眼光,看出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个伯爵贵族的文学创作中也有农民的情绪吗?我不清楚。什么叫再政治化?假如把文学还是作为政治意志的表达,不管这个政治意志是特权阶级的政治意志,还是草民的弱者的政治意志,那么把文学作为政治意志的喉舌的话,文学又消失了。我觉得应该提一个有志于在文学上同时又是在知识分子责任上尽力的作家应该怎么写作。你再关心弱势群体,你也要把弱势群体的声音转化为充分艺术化的画面、故事表达出来。明白吗?不要政治化了又把艺术化没了,于是很愚蠢的,中国文学思潮又回到了一个不珍惜文学的本真存在的一个老套子。所以“再政治化”一说在我看来是似是而非的。似乎,是看到了弱势群体,看到了拆迁户、上访户的声音没人表达,所以要让作家去表达,这就是左联曾经表达过的,这就是文学的战斗精神,诸如此类。再政治化的提出,其实表面上讲是表达了一种道德感,但戳穿了讲,这种道德感是无法落实的。你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自己去写小说,何必号召大家呢。艺术创作的前提就是在自由里写作,是自由创造的。用自由的创造来消解专制意志的所谓号召性。所以它能不能为弱势群体发出一点声音,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时非承担不可的东西。
张蕴艳:我看到您和朱兴和的访谈,对王元化学案的十年回眸(夏中义:这不是最新的。)确实是一个全面深入的回顾。那么我想再多问一步,讲到王元化的三次反思,您认为没有第三次反思就没有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我也赞同。对于第三次反思,您认为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反思,一个是对“五四”的反思。这两者构成百年中国激进主义的来龙去脉。您基本上是在肯定的意义上来看这个反思的,但是我看到对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有很多的争论。比如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也有人认为他对“五四”的反思体现了他1990年代思想的某种倒退。这个您怎么看,比如与胡风相比,您认为王元化的反思是已经溢出了左翼思潮的框架。但如果换一个参照框架呢?
夏中义:怎么换?
张蕴艳:比如从自由主义这个角度。
夏中义:我可以告诉你,你所说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至少有两大内容。一个是所谓消极自由主义,一个是所谓积极自由主义。但是对西方学界研究自由主义的人而言,自由主义首先是政治觉醒,首先是为社会制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的自由主义。假如这是真正的完整的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是半截子自由主义,才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那么消极自由主义是什么?消极自由主义关注每个个体存在的尊严,他的身心活动,行为不受到外力的无端的压抑,这就称为是消极自由主义。这样的自由主义只顾及自身的尊严如何被维系,而不回答如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为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制度保障。伯林是把维系个体身心尊严的存在称为消极自由主义。是的,这是决定民主宪政国家建构的合法性的第一基础。民主宪政国家建构的合法性是在于它的目的是要为每个合法公民的权益提供保障。假如没有这一点,你的正当性就不存在。因为不能为合法公民的权益提供制度保障的制度肯定是专制的。把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抹掉的制度,不把人当人的制度肯定是不好的制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尊严的维系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前提,这是对的。但假如你不向前走,你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制度性保障呢?这就是积极自由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在社会里边,在制度框架里边回答问题。这个回答就不是为某一个而是为每一个。假如从为某一个的角度来讲,我可以这么说,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就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由意识的脉络,至少从我现在自己的揣摩角度来讲,第一个人格的楷模就是陶渊明。陶渊明为了个体的尊严,情愿不当官,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也很有自由的意识。个体身心存在的尊严,为了这种尊严我可以不当官,我可以贫穷。为了尊严我可以忍受匮乏,忍受耻辱、屈辱,忍受难为情。因为他在妻子面前,在儿子面前有时候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他当官的时候家里好过,不当官的时候家里就难过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尊严的重要,虽然他觉得自己愧对妻子,愧对儿子。但是陶渊明的这么一种精神、意志是历代的多数人。我有这样的人去仰慕,包括钱锺书。钱锺书身上也有很多陶渊明的、也有很多《世说新语》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如果你把钱锺书看得很透,你就会觉得钱锺书就是活在当下中国语境的,《世说新语》里面的,其实这个人物都有陶渊明的元素。陶渊明是谁,陶渊明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的、自由意识的第一个经典性的人格符号。但是走向真正自由主义的路还很远,因为从陶渊明到钱锺书,这么一个《世说新语》的谱系,他们不会提出怎么为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你说的那个自由主义是半政治的。假如这样的自由主义同林毓生讲,林毓生会讲:这才不是自由主义呢,不回答社会政治制度建构的理论都不是自由主义理论。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自由意识的中国面孔》。从陶渊明到吴昌硕,从吴昌硕到陈寅恪。我和他讨论陈寅恪,他就说陈寅恪他能不能回答当代中国的,民族宪政的建构。他说不能回答怎么叫自由主义啦。我说是,不是自由主义,但是是自由意识。它和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主义还有可以交接的地方。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讲,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说王元化那个什么九十年代的反思,首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光讲个性解放,独立自由。只是讲了自由主义的一半,甚至可以说讲了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半,但不是最正统的一半。因为他只能面对某一个人的生存尊严,给他们提供证词,提供正当性。他不能为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提供证词,提供想象,提供正当性。而且王元化反思“五四”,反思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主义的政治伦理人格问题,并不排斥自由主义,自由的,解放的,个性解放的,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兴起的“五四”的遗产。并不否定这些东西的。要读懂王元化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对王元化说三道四,不管说好话还是坏话的人,我看了,根本没有好好读过王元化。所以你也不要把他们说过的话太当一回事,因为你也没有好好读过王元化。好好读过王元化,下功夫去研究王元化第三次反思到底为何物的人,全世界很少。我跟你讲,不会超过十个人。包括王元化的一些得意的门生在内,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读过王元化,不管他们现在在哪个大学当教授。
张蕴艳:还是和王元化有关的几个问题,就是高华在评价王元化再反思时他是肯定了对激进主义思潮反思的意义。因为他认为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非激进的革命是有限革命的模式。就是政治革命的目标完成之后,它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所以如果人类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精神领域的革命,那么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所以我想问王元化对“五四”激进思潮的反思,他是侧重于思潮的政治的面向还是侧重于思潮的文化的向度?另外您将王元化对“五四”激进思潮中启蒙心态和意图伦理的反思归纳为“激进政伦人格”,这个应该是出自于您的这个归纳。那么这样的归纳是不是有将一个宏大的、复杂的包涵社会政治制度在内的思想文化命题狭窄化的嫌疑?
夏中义:没有。你在看我的东西时候你带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头,你是听到很多声音以后再来读我的东西,但问题是你自己没有读过王元化反思的来龙去脉。所以你总是觉得这么讲好不好呢?但是这么讲好不好最重要的是请你去读王元化。你才能够面对这些东西。你说高华这个东西说得对,到底对在哪里。你在内心是没有尺度的,因为你没有读过王元化的整个精神发展历程。所以我对你是有一种犹豫的,因为你听到了很多,但是你对你听到的那么多声音是没有过滤机制的。你无法判断这种声音是正当的,哪里正当,不正当的,哪里不正当。你身体里面听到了太多东西,它在里面发酵,但是你没有直接地面对他们去处理。因为去处理这些东西一是凭经验,二就是凭非常刻苦地细读、研读。你这些东西就像你在思维方法上在期待一个终极性的、末日审判那样的方法论,乌托邦的模式。其实是没有末日审判的,任何科学都有它的语境。我们只能追求在有限的语境里能够把话说得透,就像是跳高。谁也不能说我的高论是终极的,你跳了二米四十五高了吧。但你也不过是二米四十五,你为什么不跳到二米四十六呢?要求高了。因为他跳过二米四十五已经够好了,已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个高度上超越他。你就应该仰慕他,你不应该去质疑你为什么只跳二米四十五,你为什么不跳二米四十六呢?这就说明你是有边界的。谁没有边界呢?跳过二米四十七依然是边界。当他比一般的人跳得很高的时候,你就应该仰慕,应该赞赏,应该研究,他为什么比常人跳得高。你不能说你为什么只跳二米四十六啊,还有二米四十七呢。这没有意义,有本事你来跳。你只能跳一米五十,你去质疑,你怎么只有二米三十几呢。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对一个科学家能够治心脏病,我们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能治肺结核?我们看一个医生,那个癌症开刀开得很利索。本来这个人只可以活三年,一开他可以活十三年,已经很聪明了。你不能要求他,你能不能不让人生癌呢?这不是那个开刀医生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永远记住我一句话:学术是什么?学术是富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是什么?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永远知道自己在有限语境里面说话。我说话就在这个圈子里说,圈外我们再讨论。圈外的问题不要放到圈内来。我们讲文艺心理学就讲文艺心理学圈内的事情。社会、政治、历史,那是文艺心理学担当不了的,我们需要建立另外一个学科,建立另外一个方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你一定要有发言权,那么你就必须下功夫。对每一个你认为重要的信息,他的来龙去脉他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你要有一个过滤,有一个判断。没有过滤没有判断你就不能作为一个依据来谈。你不能说某某人说过这个东西不好。你首先要说这个人是谁,他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你看这个话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为什么没道理。你都先弄清楚以后,再进入真正的对话。首先要和自己对话,其次再和人家对话。我这个要求非常高,因为你的信息特别多。在我看来你的那么多信息其实都没有删减,或者说你已经删减了,但是在我看来那个删减力度是不够的,你这个状态要写文章就很难很难。你写一个东西心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牵制你,在否定你。其实每一个理论、每一种说法的正当性都是非常有限的,你只要在有限的意义上把话说清楚,你的论文就可以成立了。人家批评有他的道理,你要把自己的道理讲透。我可以说这大概是学术研究的诀窍,也是最基本的立足点,甚至是生命线,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学术。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建构起来的学科,即使经典的一些典籍,你可以看到他几乎都有一些不证自有的前提。我甚至认为1+1=2都是一种假设。问题是你愿意用这种假设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来组织自己的思维。1+1=2仅仅在十进制里面才是有效的,一定要记住我的话,这是最朴素的常识。假如你连这一点都否定的话,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知识的。任何知识的原点都是假设,问题是你认同这种假设,才把它作为自己思维的尺度、思维的准则。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张蕴艳:我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对于这个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怎么看?因为讲到激进主义,就会涉及到保守主义的话题,我想您认同王元化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不意味着你对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态度的认同,特别针对新儒家而言,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和刘军宁这个政治保守主义又不一样。从对激进主义反思的合理性的层面上,你怎么看待刘军宁所说的保守主义?
夏中义:其实我说过,我谈王元化的三次反思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五四”。他的“五四”反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其实要收缩到以陈独秀为符号的激进政治文明觉悟的反思,我甚至对陈独秀一定程度称为激进主义这一点也是有保留的,我更愿意称陈独秀是激进型。因为你仔细地读我对林毓生与王元化反思“五四”的这几篇文章,我更愿意把陈独秀说成是激进型,而不轻易把陈独秀等同于人格化的激进主义。我为什么这么讲?我首先要说,我是把所有问题的回应与基础都放在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里边。就是放在王元化1993年的激进主义反思的语境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文化保守主义先不要进来,刘军宁的政治保守主义先也不要进来,我们先把王元化弄清楚,再来谈刘军宁的问题,再来谈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早饭还没吃的时候就不要吃晚饭和中饭。于是我就要说,王元化的“五四”反思他的发生源头在哪里?源头就在紧系陈独秀和杜亚泉在东西文化论争时的那么一个态度。那么东西方文化论争,陈独秀和杜亚泉之间发生了什么?很简单。杜亚泉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或者说清末民初,传统的纲纪文化衰弱了,导致社会上的民众在家里边不知道怎么面对上下左右,当官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上下级关系,是不是还要混同于君臣大序的时代,所以他说忧心中国的这个民众做人已经没有尺度了。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么一个现象加重了。陈独秀就批判他,认为他是要颠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要回到满洲晚清的那么一个状态去,就给他带来一点颠覆共和国的意思,而且他的那种推理都是不讲道理的,是生硬的。王元化就在这里面得到启示。什么启示呢?一个在新文化运动里边高高举起民主的科学的旗帜的旗手,在面对自己的思想界的对手的时候,既不科学也不民主。既不科学就是说他不是讲道理的,而是野蛮的推理。也是不民主的,只允许自己讲不允许别人讲。最后弄得杜亚泉通过这场辩论以后被商务印书馆解聘,后来老死家中,郁郁不得志。王元化就从这里边看到一种激进型的政治伦理都有四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首先讲立场,而不讲对象的真目的是什么。讲立场,讲态度。第二,他为什么讲立场,讲态度?因为支撑他的是一种庸俗进化论,年轻的总是比年老的、现代的总是比古代的要优秀,要好。陈独秀认为自己是代表先进的代表未来的,所以他对那种所谓的保守的、过于文雅的、谦让的就瞧不起。就认为历史是在我身上,真理是在我身上。所以就导致第三——言行无忌。言就是说话,行就是行为。甚至杀人放火也可以,只要我的立场是革命的、进步的,我杀人放火不过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要让这个社会遭殃,也是要让这个社会去承担牺牲。不论这个牺牲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最后一个就是启蒙心态。启蒙心态的意思就是说我既然是优秀的,处于历史的进步的一面,你是腐败的,处于历史的淘汰的一面,所以我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我就可以让你到东你就到东,让你到西就到西,如果你不服气我就让你灭亡。所以他是高人一等的,其实是一种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如果转换为政治操作的话,把一个他认为是没有价值存在的人灭掉,他认为也是正当的。王元化分析激进型的政治伦理人格的四个要素,就是这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王元化认为,它不仅在陈独秀的身上存在,也在1938年参加地下党的王元化身上存在,更在造反派的身上存在,也在红卫兵的身上存在。我为什么感应这么强烈,我告诉你我曾经在红卫兵一月革命夺权以后对校园里面的同学看不起,我认为我是老造反,我认为我掌权了。我认为像你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革命的,所以你革命我还写一张大字报,我根本瞧不起你。这就是我和我的红卫兵体验到的,一旦认为自己是革命的,道德上是优越的以后,对应该享有平等尊严的人你是不给他平等和尊严的。所以王元化批评陈独秀就是批评自己。我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篇文章。1948年的时候他才二十八岁,他把钱锺书的《围城》说得一塌糊涂。说到什么程度啊,说钱锺书的《围城》是一个在充满着苍蝇和蚊子的厕所里边炮制出来的一份菜肴,说钱锺书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人,是风月场上的老手,把钱锺书说成这样,真是的。后来我再把钱锺书写的《围城》好好读了一遍。他说的这些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他就这么厉害。他之所以要反思陈独秀,就是在反思自己。他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把批评的文章写得这样苛刻,不是好事情。他就在反思,他的这个反思就是在1993年、1994年,在“五四”反思以后才反思的。在1992年二三月份,还没有反思“五四”的时候,他还说他对钱锺书的批评是对的。所以你假如不了解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的心理道路,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揪住反思陈独秀和杜亚泉的那么一种失态,你根本不理解。那种正当性你根本不知道。我因为知道了王元化一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知道他在批评反思“五四”的时候在反思什么,是反思激进主义,那种左翼的教义,残存在他心里面引起的一种效应。他突然发现自己错了,但是他又不愿意简单地说自己错了,他从自己的内心积累里面看到,激进主义对中华民族百年历史所造成的那么一种效应,狂躁的。他当然看成是豪迈的,现在看成是狂躁的、非人道的。这种东西“五四”里面也有的,所以“五四”在他看来是一种什么都有的大思潮,在这个思潮里面最好的东西是个性解放。假如“五四”的个性解放不能从那种混杂的思潮背景里面提炼出来的话,一个个性解放者很可能会去压抑一个也想让自己的个性得到尊严的人的合法权益,被那个更激进的人所吞没。你去看看伯林写的《俄国思想者》那本书。他说当年追求十月革命的那些人,在他们参加革命的早年初期,都带着个性解放的理想。当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就开始这样。陈独秀就是这样,至少1949年以前。王元化也是这样,没有夺取政权就这样,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根本不负责。人家写《围城》写了九章,王元化只读了第一章就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我们谈王元化,一定要了解他的精神历程,再去读他的文献,这就是文献发生学。你不读他的生命历程,不读他对生命历程的反思,你根本就读不懂他的两个反思。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高华不管怎么讲,他也是从他的历史学的角度去呼应王元化。高华生前是不是好好地读过王元化的精神历程,读过王元化的人格这一本大书,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读,我是怀疑的。至少从他的点评里边我看不到这一点,尽管他的呼应大体上我也很认同。
张蕴艳:好,很多问题可能还需要回去之后再消化再讨论。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2005年您在《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里面谈到,百年学案可以写本纪、世家、列传。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您又写了很多,现在有什么新的构想?
夏中义:其实我还是非常想做那个史案的,我希望我能够在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再完成两部史案。一部是钱锺书,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钱锺书,我很想做。第二个是李泽厚。我希望在七十岁之前完成这两个东西,七十岁以后再说。我会不会写通史,再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