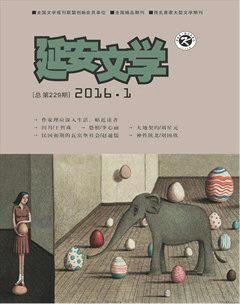众神栖居的岛
林文钦,福建霞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等。曾获孙犁文学奖。著有文集《一个人的星空》《时间旅程》。
一座岛和一个人一样,时常被人们挂念着,并会得到更多的祝福。
走进闽东西洋岛,在29平方公里之内周旋,与渔民、渔船、渔网及鱼虾不期而遇,还与神庙不期而遇。最多的时候。岛上曾有20多座庙庵,计算下来的平均密度是每0.7平方公里就有一位神祗守护。
多神多福吧。当人们的祝福并不能表达心意的万分之一,只有托付给万物之灵。因此,西洋岛就成了个诸神保佑的岛,得到最多祝福的岛。
各路神仙,屈指数来有通行的观音、土地、城隍、关帝、山神、妈祖,还有沿海特有的海神庙甚至是为乡土先贤而立的庙宇。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洋岛上的诸神各有来历,不仅始于继承、借鉴,还源于自发的造神运动。
地方小,人多船多东西多,互相就凑得很拢,整个岛很饱满充实。
岛中心密度特别高的区域是宫东老街,原居民聚居地。小小的三合、四合院贴身挨着,日间门长开,走进去有旧的石板地,旧的板壁,洗得很干净。房子不大,却有点曲径通幽的味道,不宽的门洞,窄的通道,两侧堆了劈柴之类的物什,因为堆得整齐,反显出拾掇者很勤快。再进一点,老的井,尺来高的四方口,旁边搁球状的青色塑胶吊桶,水淋淋的,眼尖的人还能看出其实是被剖开的大浮子。小的方方前院,还有更小的不规则后院,用石块砌出些高低台子。台子上搁满了草花,它们随便种在泡沫盒子里、粗陶小缸里以及其他随手用上的容器里。再大些的直接砌出花坛,四周别出心裁地饰以白色泡沫塑料小浮子,种上并不高大的白栀子、海棠花。人家之间留出的老街主道不足两米,支巷就只有一米。白天青壮年都作业去了,老人留守。时近清明,遇见的老婆婆人手一卷经文或黄媒纸折元宝牒,口中不忘念念有词。
由于正房都隐在着意营造的深处,很多人家厨房尤其餐厅都设在明处。中午时分,家家门口或窗户透出氤氲香气,令你想到在城里人家,为何闻到的就只有油烟味。在这样的路上,紧挨众人活色生香的日子行走,不孤单,温暖。同时只有生活的纯粹动静,也安宁得很。
跟三沙镇的中心街一样,宫东老街也这样将生活区经营得明显区别于作业区,空荡、飘零、粗糙、嘈杂,浓烈的海腥味与狂暴的风浪,所有与渔业相关的元素都尽力摒弃隔绝,然后得到了与此相反的缜密整饬、精致优雅乃至宁静温馨。但还不够,在西洋岛,高密度的神庙以及分布上与民居相依的特质,让人体会到岛上人对于平安幸福的极致追求,那么直接、勇敢。与此同时,这种景象让人隐约触及海上生活的内里,一定有无数次的击打、摧毁让他们备受惊吓与绝望,形成岛上带有明显痛觉的历史与记忆。出海,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他们曾经的委曲、不堪重负和茫然恐惧,都在向神前的深深一拜里。
每年的开渔节都有这样庄重的祭海场景。
公祭的场面浩大,一向放在宽广的大澳沙滩,这几年改为原生态的民祭,就落脚在西洋岛。这一日,沿港马路上绵延人潮,一直通向岛的制高点。岛小,祭台更小,观礼者都靠边站,围着主祭群体——当地渔夫与渔嫂,看他们服饰明丽,神情肃穆,祭拜如仪。
红毡、彩旗、大鼓、海碗,米酒与五谷……虽然是民祭,但组织有方,还是面向大众供人观瞻的。
真正有私密性的是私祭。主妇家赶个早,穿过小巷来到妈祖或海神庙,献上用心筹备的供品,将自己的心思向诸神低低托付。这是岸上。在水上,船老大亦有体己的仪式,是为祭拜船龙爷。地点是神圣而高昂的船首。香烛供品一概齐备,外人多不得见。猜想祝词总不外乎一愿大海丰饶如初鱼虾满舱,二愿船家顺风顺水出入平安。
身处弹丸之大的小岛,固然有地域上的限制,但未始不是本能的指引。屋与屋,心与心,民居与神殿相依偎的西洋岛,一直抱成一团,棒打不散,水泼不进。与大陆连接的铜瓦门大桥开通了多年,担心这个岛会走样、会被同化至今显得多余。
跟三沙街道不一样的是,宫东老街更紧凑更家常。不是专门的旅游区,行在其中的外人很容易被本地人区别开来,加以关注。他们不受打扰的目光里没有淡定与漠视,依然保留了源自纯朴热情的重视、鼓励,似在诱惑人开口,并准备随时回应。
初上岛,明显感觉到因为人神毗邻而居,两者不自觉地相望相守着。岛首钧鸿门门头立着的是平水庙,任谁一进岛就能看见。供奉的居然是大禹,他善始善终,治水一路从河流治到海里。
岛尾立着西洋庙,神号为天门都督,来历缥缈,责任却也明确,护佑从大澳门头经过的讨海人。大澳水道有暗礁群,水流激荡,漩涡密布,非当地人不能过。更近海处还有鱼师庙,里面的海神实为听鱼声找鱼群指挥下网的鱼师,被渔民想当然地列为海神,建庙祀之。经常用大鱼骨作栋梁。
直接处在岛上人家中间的有东津庙,主奉海神菩萨。属于泛称。岛上最大的海神庙是天后宫(妈祖庙)。到达天后宫要穿过西洋老街,深入渔村的内部。天后宫祭祀妈祖。西洋人称妈祖为天后(妈祖),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县人。随父兄来海岛打鱼为生,但她能预言人祸福,乐于助人,每于狂风暴雨之夜,站上高峰高举火把为船只指引航向。
苍茫大海,狂风恶浪里的一只船,船上的一群强壮男子,企求和感激妈祖娘娘的挽救——这个曾经的人间女子。总觉得,这是一种对家和家人的渴望。
妈祖的来历清楚,但祖籍毕竟不在本地。西洋岛最知根知底的神庙是戚将军庙(戚公庙),在宫东村。戚将军本是明代平倭名将,山东微山人。他为官刚正,有勇有谋,多有义举,深受百姓拥戴,这都是肯定的。当地人怀念他,也曾作歌慕之,歌咏不足就为他建庙塑像,一致敬称他为戚将军,尊称戚公。
在此,将一个人神化,敬为神,没有遇见多大障碍。
记得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母亲特地向三沙留云洞里的七老爷许愿,希望他保佑我考中。当时想,这位老爷是何方神圣,兄弟倒挺多,排行到了老七。后来忽然记起要我跟着去还愿,这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亲眼所见的时候方知七老爷原是戚老爷,抗倭名将戚继光。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生前担当国事的英雄,身后就这样被民众继续寄于重望,甚至涉及到我的学习问题。
民间记录历史的方式,一向有虚有实。口口相传,那是虚;传之不足,干脆建碑立庙,那是实打实。文化的积累偏偏没有在纸面上。因此,传说是一种浪漫和理想,以自由飞翔的方式。建筑却是以沉甸甸的存在方式,一砖一瓦,都是记忆,也是愿望。
按纸面上的记载来看,人和神之间必然有很高的门坎,显出严苛的等级制。很多修炼者往往费时久长却容易功亏一篑。这里的人却随时搬掉门坎,将现实中的好人顺利送入神殿。
岛民生存之道,以海为生。船充当了移动的陆地,与海隔着几分薄的船板。这个厚度就是陆世界与水世界的距离,也是生与死的距离。所以,凡界与神界的距离大致如此,有自身开辟的秘密通道作为捷径,有民心的抬举作为台阶,随时完成穿越与上升。人、物莫不如是。至今,渔夫们的网无意中从海底拉上大鱼的头骨或肋骨,还会收在船上,上岸时送到鱼师庙里受香火之供。一根躺在海底的鱼骨就这样成了神物。小小的土地庙里,有时不凑手,香被插在切开的萝卜或大头菜上,萝卜们上升为香座,同样不成问题。
神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慈悲长者,因为出身人间,所以最知疾苦;因为最终拔离尘世,所以显得大智慧,大手段,允许众生凡有休咎随时求教。也许,所有神的前身都是人,只是他们的高度普通人难以企及,只是海边人难以完全抗拒命运中的灾难,所以,这座岛被神庙覆盖,被无数的神联手护佑,被接下来无数自觉的禁忌所禁锢。就像长命锁似的,一重重锁住海上人的身家性命。
频繁的祭祀活动会一直延续,直到休渔。因为出海过程中,有收获颇丰的人,记得大张旗鼓地来谢神;也有不顺利的,再来暗暗讨神的示下。以此推断,岛上神庙密布的另一原因:地方小,成功者、行善者修桥铺路的作为有限,造神庙就成为一个重要出口。
客观地说,平常日脚——这里的人将太阳称做日头,将自身的生活叫日脚——庙里并非香火鼎盛,也非寥落不堪。它处在一个常态里,就像庙宇处在人居中间,与左邻右居只隔着一堵墙,与前后人家也只隔着一条小路,正处在日常生活之中。
一座岛,就这么被众神呵护着,以吉祥的气场预示着一年好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