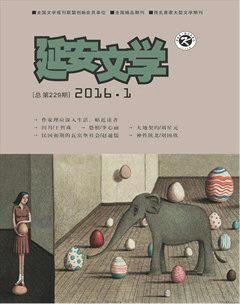租爸
支海民
一
夜的幕布掩盖了都市白天所有的瑕疵和失意,随着那一排排街灯的亮起,那些在白天看来毫无生气的、积木般的高层建筑也闪烁着粼粼灯光,显得温情脉脉充满诗意。
街心公园的一隅,一大块空地上,一台老式录音机反复地播放着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几十个男女踩着音乐点子翩翩起舞。
启江离休后,也随着儿子和老婆一起来到这座城市居住,老婆带孙子做饭收拾家务,启江每天早晨把孙子送到学校以后,便坐在沙发上手拿遥控板反复地更换着电视频道,看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打发着无聊的时光。只有在晚上,儿子和媳妇下班回家,一家人坐在桌子边吃了晚饭,启江和老婆互相搀扶着来到街心公园,享受休闲时光。
老婆当年曾经是村里的秧歌头儿,一听见音乐响起便浑身发痒。老婆子撇下老头子不管,独自一人融入街舞队伍,跳得非常投入。启江一生活得拘谨,从不善于在人前抛头露面,看那些舞蹈动作也不太难,就是舍不下这张老脸,于是便坐在木椅上,看人影摇晃,思绪便长了翅膀,随风飘荡。
启江在木椅上久坐,想了些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抬眼望,铅灰色的天幕上挂着一弯浅月,那月儿好似受了谁的欺负,摇摇欲坠悲痛欲绝;几颗星星暗淡无光地围在月儿周边,好似在祭祀逝去的岁月;公路上的车辆渐渐少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进入思考;些许凉风扑面,便涌出岁月如梭的感叹。目光漫无边际地在周边寻找,看那灯的暗影里,影影绰绰,一个女人在独舞。
好多日子以来,那独舞女人候鸟一般,准时而来,独自一人占据一方天地,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己的舞姿,显得不那么合群。一开始大家也不在意,都市表面的繁华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大家都把自己包裹得很严,谁也不愿意窥探别人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窥探,即使经常在一起共事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家长里短。那独舞女人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只是有人在不经意间,朝那边瞥上一眼。
一开始启江也不那么介意,他已经逐渐适应了都市的冷漠和荒凉,只是在百无聊赖间免不了朝那独舞女人多看几眼。夜的背景给女人罩上些许虚光,看那女人双手交叉着举过头顶,身材悠长,水波纹那般舞动,长发飘逸,千媚百态,好似形象设计师的佳构,给夜的都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眼珠便不听大脑的支配,直勾勾地盯着那舞女看,直到耳朵被老婆揪住,才回过头。原来,街头舞会已经散场,那独舞的女人也已离去,启江看到的,只是那女人留在大脑里的幻影。
幸亏是在夜间,看不清老婆脸上的表情,可从声音也能判断出来,老婆已经震怒:人老了心还嫩着呢,有本事跟那女人过到一起!
启江有些悻然,站起来,下意识地拍拍屁股,跟着老婆向家里走。看老婆颤颤巍巍的样子,心便温暖起来,向前走近一步,伸出手,想把老婆的胳膊挽住。谁知老婆胳膊猛一甩,紧走两步,把老头子撂在后头。
启江宽容地笑笑,猛然间记起了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爱吃醋的女人证明她非常在乎你……想到耄耋之年老婆仍然像一个少妇那样维护着自己的巢穴不被同类侵犯,感觉有趣而幸福,自我解嘲道:都快见马克思的人咧,你还不放心?
老婆不再说啥。老俩口乘电梯来到自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屋门,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已经入睡。老俩口悄悄进入自己屋子,铺开被子睡在床上,一宿无话。
二
儿子媳妇和孙子都不在家吃午饭。老婆子正做午饭时没有食盐了,于是对老头子说:你给楼下买包食盐去。启江来到电梯口,摁下开关,电梯自上而下,自动打开,里边站着一个妙龄女郎。
素不相识,也就无话。只是启江觉得那女郎跟夜间独舞的那个女人有点像,忍不住多看一眼。现今都市里漂亮女人多了,启江也说不上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有点那个——用现今流行的话说,叫做“养眼”。电梯下到一楼,自动打开,启江抬脚迈出电梯的瞬间,那女郎突然说:叔吔,我住三十三层,有空上来坐坐。
启江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一个妙龄女郎主动邀请一个素未生平的老头子到她家“坐坐”,当然应该摒弃男女之间有关其他方面的嫌疑,可是这里边也不能没有蹊跷,究竟为什么?费尽思索。启江下意识地“唔”了一声,说不上是答应还是拒绝。看那女人径直走到停车场,打开一辆红色轿车门子,坐了进去,汽车无声地滑出了小区,融入街心的车流。
买好食盐上得楼来,启江便被一种情绪捕获。说不上什么原因,感觉下午的日子特长。老婆坐在沙发的一头,织一件好像永远也无法完工的毛衣,启江手里的遥控板不停地换着频道。老婆终于忍不住了,吼道:看你那失神落魄的样儿,该不是门外有相好的等你!启江脸上微露尴尬之色。启江绝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年轻时也曾风流,甚至还有一些把柄攥在老婆手里。老婆一辈子活得颤颤兢兢,总算守住了启江这棵歪脖子树。现今风水轮流转,也到了老婆子伸腰展腿的时候,有时故意拿一些噎嗓子话猛砸启江,好在启江并不在乎,反而感到那是一种享受。
启江有些不耐烦,把遥控板放在茶几上,站起身,伸伸懒腰,说:闷死人了,出去转转。一边说一边换上皮鞋,开了门,走出屋子,关门时老婆叮咛道:早点回来吃饭。
下了楼来到小区花园的凉亭,看一年轻的妈妈正教自己的儿子蹒跚学步,那男孩一见启江便伸出双手,口里叫着:爷爷——。启江觉得有趣,便不由得伸手把孩子接住,孩子的妈妈灿烂地笑着,眼角溢出幸福。启江逗孩子玩了一会儿,那孩子便被妈妈抱走。难得一见的晴天,看那太阳落在楼顶上摔得粉碎,火花四溅;花园内几株樱花怒放,杨柳吐翠;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生命伸伸懒腰,开始了新的周期。一小贩推着板车叫卖草莓,那红得透心的果子叫人眼馋,想买两斤尝尝鲜,一摸身上没带钱。正遗憾间只见那辆熟悉的红色小车无声地滑进了小区,启江想吃饭的时间快到了,打算上楼。那女郎出了汽车便一眼瞥见了启江,叫声:叔,您先等等。启江只得在凉亭的木凳上坐下来,心里忐忑着,不知这女郎要对他说什么。
那女郎径直走到凉亭,挨着启江坐下,话也说得直接:叔,我认识您,您跟姨常在街心公园跳舞。启江略感震惊,看来自己这个目标人家已经偷窥了许久。女郎接着说:我住三十三层东单元,您有空上来坐坐,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一次启江不可能含糊其词,许多问题来不及思考,他必须表态。启江回答:好的。双方互换了电话号码,那女郎也不多坐,说了声谢谢,起身离去。正在这时,启江的电话响了,是老婆叫他吃饭。
三
可是启江还是犹豫了许久,打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去会那女郎。听说城市里有些专做人肉生意的女子常常瞅准老男人的钱袋,因为老男人的钱好哄。加之自己老婆儿子媳妇孙子全在一起住着,万一弄出个啥动静这张老脸往哪儿搁?继而又一想,看那女郎不像是那种坏女人。据启江所知,一般能住在楼房顶层的业主基本上都很富有。很难想象一个开着名车住在顶层的女人会做那种交易。也许这个女郎真的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难题……
正打不定主意时启江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是那个女郎发过来的:叔,我这阵子没事,您上来坐坐。
启江编了个理由出了屋子,为了保险起见,他乘电梯先下到一楼,然后从一楼乘电梯上到三十三搂,摁响门铃,女郎开门,把启江让进屋子。启江坐进沙发,感觉屋内的奢华压迫得他透不过气。那女郎给启江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在沙发对面的圆凳上坐下,双腿并在一起,面对一个长辈,谈了她的遭遇。
三年前,女郎在都市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在大学念书时结识的男友去了国外。男友临走时撂下话,除非她也能够出国深造,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中断。女郎感觉受了羞辱,下决心不出国誓不罢休,可是四年学业最少也得二十万美金,女郎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还有一个弟弟在北京念书,从那里筹集这笔资金?无奈中以身相许,做了煤老板的情妇。煤老板答应三年后给她一笔钱,送她去国外深造……现今三年时间已过,煤老板却一拖再拖。
启江嘴张着,胸闷气短,脸紫胀,说不上的震撼。一个念头一闪,马上把他牢牢攫住:假如对面这个姑娘是我的亲生女儿,我该咋办?他不知道该问姑娘些什么,有点茫然。一口气喝完一杯咖啡,对姑娘说:再来一杯。
姑娘款款站起身,又为启江冲了一杯咖啡。启江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才问:这件事你爸爸妈妈知道不?
我没有告诉他们。姑娘的目光有些黯淡,她说她不想让爸爸妈妈为她操心,同时也是为了自己不被家人误会,所以一直瞒着家人,爸爸妈妈和弟弟只知道她在一家外企上班,收入不菲。
启江还想问姑娘怎样跟那个煤老板认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可能牵扯到人家的隐私,既然姑娘不愿意告诉你,你就不必再问。双方稍许沉默,启江突然问道: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跟煤老板摊牌,想让您做一回我的“爸爸”,增加跟煤老板谈判时的筹码。当然,我也不会白让您帮忙,我将会给您一笔报酬……看来姑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说这些话时神态平稳,一点也没有激战前夜的那种紧张情绪。
伤害的不全是自尊,有一种被人误解的伤悲。启江耳朵后边的青筋直冒,如果在其他场合,他直想摔门而去。可是此时此刻他却不能,姑娘的命运太令他揪心!启江有点悲哀地说:姑娘,你以为金钱能买来一切?我可以帮你,但绝不会要你的报酬!
姑娘可能也感觉到她的失言,有点着急地解释到:我不是那个意思,从您的外貌我猜想您一定直爽,我看准的人一定不会出错,您一定会帮我逃出苦海。叔吔,您就帮侄女这一次吧,我会一辈子记住您的……
姑娘还说,她当年跟煤老板做情妇时有约在先,煤老板亲口答应每年给她五十万元人民币,现今已经将近四年,她应当得到二百万,不过再少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她能顺利脱身。
谈话结束时启江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对姑娘说:我已经答应过我要帮你的忙,决不反悔。但是这件事必须告诉我的家人,避免引起他们的误会。
姑娘流泪道:叔吔,今天的事您知我知,我再也不想让任何第三者知道。我连我的父母都不想告诉,您一定知道我的苦衷。
启江有点为难:容我再想想。我担心万一瞒不过我的家人,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你对我都不好。况且,我做为你的“爸爸”,在煤老板面前必须装得很像,不能让他有任何怀疑,所以煤老板回来时,我还必须在你家住下来,等煤老板走了以后我才能走。这件事不对我的家人说清楚恐怕不行。
姑娘擦干眼泪,有点悲戚地说:我的确还没有想过那么多,我只想这件事必须做得密不透风……
启江的电话响了起来,老婆子在电话那头对他吼道:这么长时间还不见回来,死到那里去了?!
启江一打开自家屋门就看见老婆的脸胀成猪肝,对他吼道:你上楼顶作甚?
看来自己的行动已经被老婆发现,再隐瞒下去已经没有必要。启江坐下来,对老婆说,你先不用发火,容我慢慢对你讲……随着误会的解开,老婆脸上的容颜慢慢恢复正常。老婆也是热心肠,在老家时跟左邻右舍相处融洽。听完那个女子的遭遇后,老婆子义愤填膺,竟然诅咒那个煤老板不得好死!并且漫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有俩脏钱就烧得不知道自己算个老几!等着看吧,恶人有恶报,那个煤老板迟早得躺到汽车轮子底下变成个死鬼!
启江等老婆诅咒完以后,问老婆:你说,咱们应不应当帮帮那个姑娘?老婆子反问启江:我说过不该帮了吗?启江心里暗喜:这么说来你同意了?老婆子说:我担心你做事莽撞,把人家女子的事情搞砸。启江装着洗耳恭听的样子回答:愿听老婆教诲。老婆吭一声笑了:别跟我卖关子了,你这号人咱又不是不知道,一辈子最爱帮助女同胞。如果一个男的遇到困难找你帮忙,你帮不帮?启江说:那要看是谁,遇到啥事。这件事的确有点特殊,我的确想帮那个姑娘逃出火坑。老婆说:咱们同住一幢楼上,这件事不可能不让儿子和媳妇知道。启江为难起来:人家姑娘连她的爸爸妈妈都不想让知道,咱何必要扩大影响。老婆说,她担心儿子万一撞见后产生误会就麻缠咧。启江想了半天,觉得老婆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况且自己年纪大了,行为做事必须谨慎,绝不能让儿子产生误会。于是有点无可奈何地对老婆说:要说还是你来说吧,我在儿子面前没法开口。
四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了晚饭,老婆洗锅刷碗,启江便一个人下了楼,在店铺门前探头,看那各色广告琳琅满目,瞪着色迷迷的眼睛招徕顾客。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迎面扑来的微风带着温热的气息;靓丽的女郎穿起了夏装,裸露着青春的健美;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悠闲地漫步;冷不防一个小伙子往你面前一站,向你手里塞上一张有关性药的广告。
启江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小伙子的纠缠,正想回家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叔,怎么就您一个人出来?启江抬头一看,正是三十三层楼那个姑娘。启江没有回答姑娘的提问,而是反问姑娘:你怎么今天晚上没有去跳舞?姑娘也没有回答启江的提问,而是说:叔您要是方便的话我想邀您到附近的酒店坐坐。启江不可能拒绝姑娘的邀请,但是也不想让姑娘破费,于是说:刚吃过晚饭,酒店咱就不去了,要去咱到公园坐坐。姑娘说她的车就在附近停车场停着,她让启江稍等。
启江坐进了姑娘的汽车,融入满街的车流,一排排街灯在汽车的碾压下纷纷倒下,夜的都市溢满温馨。姑娘没有把车开到公园,而是来到一家名吃店的门口,看来姑娘也是这里的常客,门口的小姐向姑娘绽开笑脸。
进入两个人的房间,姑娘点了几样小菜,问启江:叔,您喝点什么?启江答:来一杯咖啡。看来启江叫姑娘的咖啡喝上了瘾。不知为什么,启江突然脸颊发烧,浑身不自在起来: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竟然雇佣一个老男人做她的“爸爸”,这算什么交易?继而又一想,既然有人把你推上了前台,你就是再不情愿也得把这出戏演到底,心态便有些平稳。看姑娘低头用吸管向嘴里嘬吸冷饮,启江从内心替姑娘惋惜。假如姑娘出身名门,这阵子可能在地球那边的某所名校里攻读,用不着为了上学而卖身……这个世界真他妈的势利,有钱人就可以随心所欲。
相互间都不说话,气氛有点沉闷。启江突然想到,他至今还不知道姑娘叫什么名字,以后遇到煤老板,他对姑娘该怎么称呼?于是问道:姑娘,你能不能把你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更详细地告诉我,以免咱俩跟煤老板摊牌时出现纰漏。
姑娘低头想半天,像在自言自语:我……有点害怕。
启江暗自思付:看来这个姑娘还没有想好,那她为什么要把她目前的处境告诉我?继而又一想,这也难免,人人处于这种境况都会出现反复。便有些释然,他对姑娘说:现在打退堂鼓也不迟。
姑娘咬牙切齿:我早受够了,必须离开!
启江不再说话,两人傻坐着,看那姑娘的瞳仁里有泪珠在转,启江便开始进入姑娘的“爸爸”的角色。他安慰姑娘:孩子,噩梦即将过去,你还年轻,要打起精神重新活人。
姑娘吃惊地抬起头,不自觉地叫了一声:爸爸。启江下意识地答了一声:哎。气氛便融洽了许多。姑娘介绍道:她叫康芳荣,在家时爸爸妈妈叫她“荣儿”,二十七岁,将近四年来她从来没有让爸爸妈妈到过她跟煤老板住的地方,有一次爸爸来都市看她,她让爸爸住酒店,爸爸要到她的“单位”看看,她撒谎说单位谢绝参观。
姑娘还说,这一次跟煤老板谈判仍然安排叔叔住酒店,然后跟煤老板一同来看望“爸爸”,“爸爸”可以装着不知道内情的样子严厉“训斥”女儿,女儿装着委屈的样子向“爸爸”倾诉她的苦衷,这出戏就这样开头。
启江在想:看来这姑娘已经经过周密部署,但是他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便问:荣儿,假如那个煤老板不肯跟你一起来见我呢?
姑娘说:不怕,煤老板四年来一直对我表白,他要跟家里的那个“黄脸婆”离婚。他一直想见我的家人,表明他的态度。可是我却受够了,不想跟他在一起纠缠,因为那样一来,我将会悔恨终生。
启江还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电话响了起来,是儿子打来的。儿子在电话那头问他:爸,你在那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启江隐约意识到儿子打电话的内涵,有点抱歉地对康芳荣说:对不起,儿子打电话找我。康芳荣凄楚地笑笑,买了单,车载启江来到小区花园。启江下了车,看凉亭那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肯定是儿子!启江心想糟了,儿子要阻止父亲的行为。
还好,儿子给他留足了面子,站在原地没动。眼看着父亲跟康芳荣一起开了电梯,上了楼。
启江刚在沙发上坐下,儿子便跟着进来。儿子没有谈启江跟康芳荣相约的事。只是说,过几天就是五一节了,儿子打算给启江的信用卡上打两万块钱,让爸爸带着妈妈去旅游。儿子已经电话订好了机票,明天就走。儿子说完就去睡了,丝毫没有给爸爸留下申辩的空间。
启江睡在床上,听老婆拉起了鼾声。心想一家人已经商量好了,共谋对付启江的行为。启江不胜惋惜,却也无可奈何。他总不可能为了一个陌生女子而跟儿子闹僵。况且在这件事上,儿子已经给老爸留足了面子,启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沉着和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