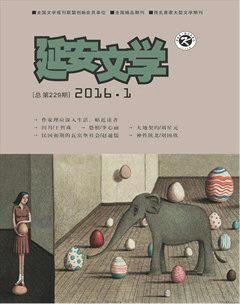知青
陈延民
知青,这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彻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字,如前尘往事,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是街头巷尾谈论的主要话题。如果不是偶尔翻看《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名录》,我想,我也快忘却了这个名字。人就是这样,当你不经意间捡起记忆里曾经丢失的东西,比如一个故事、一件物品、一个名字……都会生出些许感慨来,甚至会觉得弥足珍贵。
记忆里,在我懵懂的孩提时代,村子里那几位说着好听的普通话,穿着塑料底鞋,戴着“火车头”帽子,背着黄挎包的大哥哥和梳着剪发头,围着红围巾,爱说爱笑,给我糖吃的大姐姐,让我新奇了好长一段日子。我很想知道哥哥姐姐从哪里来?他们是谁家的孩子?……可眨眼功夫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听得大人们说:“他们都回北京啦。”哦,原来他们是北京的孩子!那时,北京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的,只是觉得等我长大一些,就可以在邻村找到哥哥姐姐们。
日子在时间的指缝里一天天流过,我也在哥哥姐姐的故事里慢慢长大。把麦苗当韭菜吃,将庄稼秧当杂草锄,分不清马儿、驴儿和骡子,饿急了、馋急了把老农的狗儿、鸡儿偷了来吃,为得到姐姐们的好感,本地小伙与哥哥们相互打架,晚上想爸妈偷偷地流泪,白天面对着大山无端地吼叫……哥哥姐姐们的这些故事,大人们如讲述自己孩子的劣迹,在眉飞色舞间好像还多了一份炫耀。末了又一句:“唉,北京娃受苦啦!遭罪啦!”这让我含着糖的那份甜甜的记忆似乎也变得苦苦的,又似乎有一种亏欠的滋味从喉咙瞬间滑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县知青办公室,当我再次见到几位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时,哥哥姐姐们已变成叔叔婶婶了。除了依然说着好听的普通话,叔叔婶婶们已和当地人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只是多了几份沧桑,几份感叹。在与他们经历过生活磨砺的眼神的对视里,我渐渐读懂了他们背后深藏的许多故事。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隆冬时节,作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中的其中一支,哥哥姐姐们如羽翼未丰的小燕子在兴奋与忐忑之中被有计划地装入“北京知青专列”,用三天时间从北京飞抵革命圣地延安。这是一支近三万人的队伍,他们驻足的地方不是虫草丰美的暖春,而是食物匮乏的寒冬。一边是啁啁啾啾的他们,一边是望眼欲穿的父母;一边是贫瘠的陕北高原,一边是温馨的家园;一边是丢掉课本、学业荒废,一边是落户农村、汗洒粮田……如做梦一样,他们由北京城里的读书郎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
即便如此,十五六岁的心志坚强地经受住了岁月的历练。宝塔山下,延河畔上,哥哥姐姐们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风雨同舟。延安的山山洼洼到处都洒下他们辛勤的汗水,留下他们年轻的身影。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乡亲们共同创造了丰收的果实,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延安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他们在抛洒着思亲泪水的同时也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农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农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苦难。随着岁月的流逝、身心的融入,延安成为了知青们的第二故乡。
心儿依恋着第二故乡,丰满的翅膀却要去山外飞翔。在辛勤劳作的日子里,三万多名远离家人的孩子,夜夜都做着回家与飞天的梦。招工、参军、上大学……哥哥姐姐们努力地跨越着“农门”,改变着原本不该改变命运。如筛子过滤一样,在精神煎熬、身心疲惫、跌跌撞撞中,他们大部分人终于挤出了筛网,陆陆续续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飞向了更能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回家与起飞的路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漫长,如今仍有300多名知青因种种原因还继续工作生活在延安,有140多名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与延安的山水草木融为一体。
今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用三天时间由北京来到延安,又用三十多年时间回到北京,以及至今还未回到北京的知青们,从十五六岁哥哥姐姐般的花季,变成五六十岁叔叔婶婶样的年纪,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为延安老区奉献着自己的那份光和热。他们所带来的都市文化和始终坚守的甘于吃苦、乐于奉献、顽强拼搏、胸怀远大的优良品质,依然冲击着延安这块神圣的土地,启迪着一代代青年人不断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安排着自己的生活。
这些,也许正是延安人民无法忘记知青、感念知青的理由。
责任编辑:王雷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