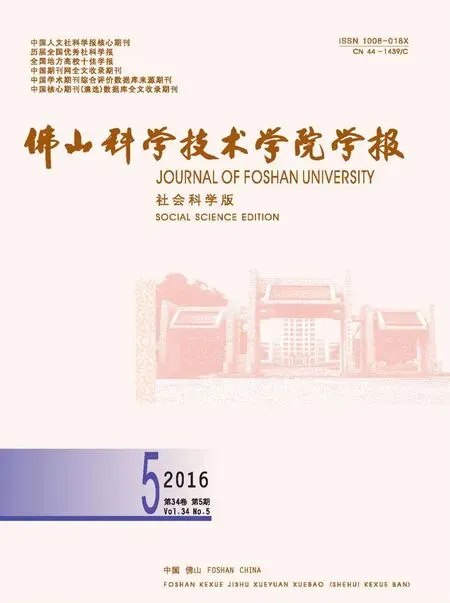观人学视阈下的“贫富”诗学范畴研究
万伟成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佛山528000)
观人学视阈下的“贫富”诗学范畴研究
万伟成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佛山528000)
贫穷、富贵,从观人学运用到诗学,充分体现出儒家为主的价值观念与诗教的影响,因而成为传统诗学术语,并衍生出贫寒气与富贵气、山林气与台阁气、诗穷愁而词富贵、“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等一系列相关又相近的诗学概念或命题,影响到诗学中的品第分类学与选诗学,大大丰富了观人学与诗学,构成中国传统诗学最奇葩的一支——命相诗学,对诗学产生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观人诗学;贫寒气;富贵气;诗谶
自从20世纪90年代文论界“失语症”说之后,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诗学范畴越来越受重视,并取得了相关成果。然而其中与观人学相关的贫穷、富贵概念,在宋代曾经引起热议,在当代除了“穷而后工”命题外,其他基本上被忽视。贫穷、富贵似无关诗学宏旨,却体现了传统道德观念与诗教精神,对于进一步探讨观人学对诗学建构的影响,促进民族特色的古代诗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诗学中的贫富术语来自观人学。战国时代就盛行以贫富观人,如《文王官人》:“富贵者,观其礼施也;贫穷者,观其有德守也。”并说:“贵富虽尊,恭俭而能施,众强严威,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1]李克曰:“夫观士也,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观矣。”[2]反映了儒家倡导的守德行礼等价值准则。第一部观人学专著《人物志》继承了“五视”富贵观人法,并于《七缪》中将人划分为上材之人、中材之人:“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达有劳谦之称,穷有著明之节。中材之人,则随世损益。”[3]将贫富观人进一步系统化了。虽然以达、穷对文,穷兼有贫穷与不得志之义,但实际上仍是贫富的观念。那么,观人学中的贫富范畴,是如何延伸到古代诗学的呢?对古代诗学范畴体系来说具有哪些价值与影响呢?如何评估这些价值与影响?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向方家请教。
一
贫富观人属于观人学范畴,先秦有之;而以贫富观诗与诗人则属诗学范畴,盛于唐后。以贫富观诗,并进一步观察诗人,其实也是观诚、考志、观色、揆德的观人过程。
先看“观诚”。欧阳修说:“诗源乎心,贫富愁乐,皆系其情”[4],无论贫诗富诗,皆以情为主,而情以真诚为本。李衡也认为:做诗“若未老说老,不贫说贫,便不是诚意”[5],所以古代诗论反对缺乏真情、纯粹摹拟的形式主义诗风。明雪畴子说:“未老言老,不贫而贫,此是杜子美家窃盗也;不饮一盏而言一日三百杯,不舍一文而言一挥数万钱,此是李太白家掏摸也”[6],虽是有感七子的形式主义诗风而发,但也体现了《易·乾》“修辞立其诚”与观人学“观诚”的影响。反面的例子,如寇准“富贵之时,所作诗词皆凄楚怨感”,没有真情实感,纯系无病呻吟,所以成为后来“憔悴走窜”、富贵难久的先兆[7]。剥去其先兆的神秘外衣,不难发现其中强调诗歌真情的合理内核。
“考志”就是考察诗人的志识与器量。同是穷愁,杜甫“穷年忧黎元”、“一饭不忘君”,《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想到“失业徒”与“远戍卒”,《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想到“天下寒士”,兼济思想使得杜甫优入“圣域”;而孟郊自韩愈《送孟东野序》之后,自鸣不幸之说为诗界接受,刘永之“譬之寒蝉、秋螾,哀吟悲唱于灌莽之中”[8]214,“吴处厚以渠器量褊窄”[9],杜、孟志趣、器量不同,品亦以分。这说明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说,对贫富诗的取舍除了要求胸襟阔大外,还强调“风化”标准与诗歌的社会功用。
“观色”,据《文王官人》,指的是人的五性(喜、怒、欲、惧、忧)“诚于中,必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贫富诗中的感情外发,也为诗论关注。如宋人评柳宗元“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10],所以“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11]83;又评孟郊贫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曰:“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而死”[12],就连他的平生快诗《登第》也备遭非议,如“议者以此诗验郊非远器”[11]150,“宜其虽得之而不能享也”[13],明瞿佑亦谓“谶其不至远大之兆”[14],孙能传谓“非延福凝禧之道”[8]6000,把它说成是终生贫穷的诗谶。之所以出现千口一评的情况,是因为柳、孟贫穷之诗,在感情的抒发上都不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标准。
儒家圣人处贫,要求“贫而无怨”(《论语·宪问》),“死守善道”(《泰伯》),“贫而无谄”不如“贫而乐道”(《学而篇》);道家站在“尊生”立场上,主张“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第二十八》),“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则阳第二十五》),发挥“忘”的作用,才能达道。陶渊明备受称赞,正在于此,方东树就认为“渊明之学自经术来。……《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如颜回)。……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饥寒,而后存节义也”[15]101,符合儒道要求。另外,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关睢》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16],阐述了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对贫富诗的感情抒发上“不伤不淫”的要求。所以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推崇“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17],要求贫穷诗做到婉而缓。显然孟郊、柳宗元都不符合这个要求,其源头可上溯到屈原。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为“不合经义”,所以,“庄以放旷,屈以穷愁,古今诗人,不出此二大派,进之则为经矣”[15]5,反映了怨怼派并不为儒经所许。
揆德,也是贫富观诗之法。孔子主张富贵必须在仁义道德的前提下获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富而不骄”未若“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孟子也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滕文公上》)。一个人没有“德”,即使“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而道家也主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九章),“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三十四章),实是儒家之补充。后人否定李白诗歌者,也往往体现出这种道德评判。如苏辙《诗病五事》一评“李白诗不知义理”,王安石说他诗歌近俗,“十句有九句言妇人酒耳”[18],胡震亨说得更加直白:“宋人以荆公四家诗不选太白(引者注:王安石将李白排列四家诗之末),嫌其羡说富贵,多俗情”[19],陆游更把李白蔑视权贵比附“富贵而骄”,斥之为“浅陋”,“宜其终身坎壈也”[20],都反映了儒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观人观念。儒家的贫富观念,塑造了许多君子、圣人、大丈夫的典型,而《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数语可谓尽之,所以明人赞赏程颢《秋日偶成》“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21],也正基于“不伤不淫”的儒家观点。
贫富观人学还影响到诗学中的品第分类学与选诗学。前者如吴乔品第诗人的优劣云:“读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遗弃世事,放旷物表者,契于庄列,为次之。怡情景物,优闲自适者又次之。叹老嗟卑者又次之”[22],这正反映了《人物志》将贫富划分成“上材之人”、“中材之人”的影响以及先儒后道的价值观念。后者如方回《宦情类》“所选诗不于其达与不达之异。其位高,取其忧畏明哲而知义焉;其位卑,取其情之不得已而知分焉。骄富贵、叹贫贱者,咸黜之”[23]233,选诗标准,也反映了贫富观人学与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
二
贫富进入诗论,不仅深化了诗学对诗人、诗作的认识,而且还派生出一系列诗学范畴。
最早诗论专著《诗品》与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中,提到贫富穷达者,多半是“辞富”、“辞穷”、“富言”、“穷文”、“穷力”、“穷变”、“赅富”、“穷究”、“宏富”、“意穷”,即使贫富对文,如“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神思》)、“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事类》),多偏于才学与辞藻之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如欧阳修《读蟠桃诗寄子美》比较韩孟之诗:“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揫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既保留了“才学”之义,又衍生出声情之义,有所发展。南北朝对后世影响的贫富诗论概念,当是颜之推:“扬都论者,恨其(何逊)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24]23后人概括为“贫寒气”与“富贵气”。
“贫寒气”,又称“寒乞气”,指诗作反映的诉穷乞怜、叹老嗟卑、慕膻附腥等衰意思的内容、褊窄器量及其外呈的憔悴枯槁、局促不伸的琐屑寒气。“贫寒气”最早得名于建业人对何逊的评价。后人推孟郊为“贫寒气”的代表诗人,沿用了齐梁原义,如说孟郊“思苦奇涩”(《新唐书》卷一七六),“尤喜自为穷苦之句”(《六一诗话》),特别自苏轼《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读孟郊诗》“听此寒虫号”后,“寒”字遂成孟诗定论。此外宋人更注意到他的胸襟狭小,“器宇不宏”,“赋性褊狭”[25]75,气象“憔悴枯槁”[26]195,感受到孟诗情志之凄清、境界之幽冷、语言之苦涩、色调之阴冷,甚至读者的感受,如严羽以为“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26]181。这些无疑都丰富了“贫寒气”的概念内涵。苏辙《诗病五事》斥孟郊为“陋于闻道”,纪昀《俭重堂诗序》批评说:“以龌龊之胸,贮穷愁之气,上者不过寒瘦之词,下而至于琐屑寒气,……甚至激忿牢骚,怼及父母,裂名教之防者有矣。兴观群怨之旨,彼且乌识哉?”更从儒家诗教、道德上予以批评,反映了“贫寒气”在诗论上的概念提升。
“富贵气”指诗歌反映的富贵闲适的内容及外呈的富丽华贵、雍容闲和的天然气象。本出于扬都人对刘孝绰的评价,刘出身将门新贵与士族联姻之家,与萧纲、萧绎兄弟关系密切,故诗多侍宴应制、赠妓咏美人内容,且多金玉字面,体现了宫体靡丽之风与雍容之态,反映了齐梁诗坛主流风气,故为时赏。后人因有以雍容论富贵气者,如《批点唐诗正声》评韩翃《寒食》:“禁体不事雕琢语,富贵闲雅自见。”正是齐梁人的审美观念。不过齐梁是在雕琢之中达到雍容境界的,而唐人是在“不事雕琢”中实现的。此外,富贵气还在诗歌的色泽上派生出绮丽、富丽、富艳等概念。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的“绮丽”说:“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明显是对六朝以绮靡华丽为宝贵的有力反拨(李白《古风》所谓“绮丽不足珍”),对后世影响深远。北宋诗坛更着重从气象层面上认识“富贵气”,这又比色泽、态度的层次要深刻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晏殊。
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见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25]46-47
晏殊认定“腰金”与“金书”数句是乞儿相,是因为它有金玉字面;而“笙歌”、“楼台”等“善言富贵”,是因为它尽弃金玉锦绣的庸俗字句面,在华丽中糅合了清淡自然,而以极其疏淡的笔墨绘出了身居高位时的赏心乐事和富贵气象。此后“善言富贵者不说锦绣金玉,惟说气象”几成诗学公言。然《后山诗话》批评“笙歌”二句:“非富贵主,看人富贵者也”,与晏殊又有不同。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两人的观点,不妨将白居易《宴散》抄录如下:
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归。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将何迎睡兴,临卧举残杯。
从整首诗看,小宴、残暑,以及末句“残杯”,未免儒酸衰意。正如《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主人去而客独醒,无限凄凉,非富贵语也。”唯一与富贵气沾边的是三、四句,所以沈德潜谓“三、四传出富贵气象”[27],正来自晏说。陈师道否定此说,但没有说出理由,如果按查慎行说:“三、四即俗所云无不散之筵席也,虚谷引此谓是富贵语,失其旨矣”[23]298,也未搔到痒处,因为晏殊诗词后面也往往带有淡淡的哀愁,未害其为富贵气。陈师道否定二句,我认为涉及到“富贵气象”概念的修正问题,洪亮吉说得明白:“作富贵语,不必金、玉、珠、宝也,如‘夜深斜塔秋千索,楼阁冥蒙细雨中’及‘夜深台殿月高低’,仅写雨及月,而富贵气象宛然。然尚有楼、台、殿、阁字也。温八叉诗云:‘隔竹见笼疑有鹤,卷帘看画静无人’,韦端己诗‘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第二等人家即无此气象。”[28]而白居易二句,虽无金玉字面,却有楼台字面,所以不是彻底的“富贵气”。宋以后论家常用“天然”诠释“富贵气象”,如《皋兰课业本原解》:“富贵华美出于天然,不是以堆金积玉为工”,如王士禛所谓“外间摹写,自多泛设”自然不如“内家本色,天然流丽”[29]。明陈衎推崇孟浩然《春晓》,也有内在本色与胸襟方面的考虑:“第思‘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此真富贵人自道也。功成名遂,无一欠缺,世上纤尘,不入胸中,方能有此一佳眠”,代表着“富贵气象”的无上境界。所以,从后山开始的一系列观点,实际是在崇尚“富贵”的旗帜下借“平淡”、“自然”为由,消解了“富贵”学说。
三
围绕着“贫寒气”与“富贵气”,古代诗论又进一步深化到对题材之气与体裁之气的认识,以及诗学史上的重大命题。
先看题材之分,衍生出与台阁题材相关的台阁体、台阁气、廓庙气、衙门气、仕宦气、官场气、馆阁气、应酬气、庙堂气等,与山林题材相关的山林体、山林气、烟霞气、石气等概念。宋初晚唐偏重山林,西昆、白体偏重台阁,俨然有山林、台阁之分的态势,而西昆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影响了一代诗作,而且影响到一代诗论特重尊富贵之体,好以廓庙、台阁论诗,如王钦若题诗:“龙带晚烟离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宋真宗以为“落落有贵气”,后擢致上相[30];盛文肃评夏竦“文章有馆阁气”,杨徽之评夏竦诗歌“真将相器”。吴处厚总结说:“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25]46枯槁憔悴与温润丰缛,将山林气、台阁气概括入微,然已有轩轾之意。晏殊论诗特重“富贵气”,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评“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廓庙富贵之气”,张戒评韩愈“诗文有廓庙气”[31],都是一代风气反映。相反,若清吴雷发所言:“诗以山林气为上。若台阁气者,务使清新跋俗,不然则格便低”[32],则扬山林而轻台阁。明李东阳《麓堂诗话》:“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作山林气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气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33]此实调和二派,貌似公允,然以“诗言情”较之,台阁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即使有真情也缺乏深情,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有工丽而已。
再看体裁之别。词产生于花间樽前,用于佑酒佐欢,且为艳科,故论者多谓词宜富贵;而自“诗穷而后工”说盛行后,穷愁、富贵成了诗词区分的依据。如秦少游词比贫家美女,终乏富贵之态,故为易安《词论》恨之;杜甫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与晏几道词“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以为“诗词分疆”[34];朱彝尊谓“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升平”[35],如果站在早期词或者固守“词别是一家”的立场看,词多写富贵,有一定的依据;但若从词的长远发展来看,未免引入偏途。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以论为词”、“以赋为词”,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早已从题材、艺术上打破诗词界限,大大开拓了词境。所以清代陈廷焯谓“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36],应该说比上一种观点有重大进步,然而这与“诗穷而工”论一样,陷入了另一种偏颇。即以诗而言,也有主张“五言长篇宜富而赡”者,或“七言长篇宜富丽”者[37],其实都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涉及贫富观人观诗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
尽管“穷而后工”命题的来源广泛,但真正成为诗论重要命题、并反复为人引用,甚至引起诗学上的贫富之争,还是韩欧以后的事,甚至发展到“以辞之工拙,验夫人之穷达”[38]的地步。后世有三种意见:一是否定欧说,如质疑“穷”与“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纪昀《俭重堂诗序》指出穷愁诗未必皆好,袁枚举出富贵诗之好者[39]491。有的引反面事实为证,如清陈澧说:“古今诗人致位卿相者往往而有,岂必穷哉!”[40]陈无巳序《王平甫集》,葛胜仲叙陈简斋诗,更有“诗能达人”之说,可谓矫枉过正。第二种意见是赞成欧说,苏轼《答陈师仲书》则推论出“诗能穷人”结论,已有偏离;刘克庄《跋章仲仙诗》:“诗非达官贵人所能为……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隐士,然后有标致”,王世贞说:“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便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然而入诗便俗”[41],都支持了诗穷愁而词富贵的观点。第三种意见超越“贫穷、富达”论诗,主张以“道”论诗,如明方孝孺在《夷山稿序后》重新界定“穷”的含义:“人之穷达,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贵贱贫富”,刘永之《刘子高诗集序》说:“昔之论诗者曰:诗人少达而多穷。或为说以解之曰: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耳。是二者皆非也。唯不以穷达累其心,而后辞有大过人者。”相较之下,第三种意见流露出儒家“兴观群怨”之旨与道家超越贫富的精神,又体现出对前几种意见的修正与超越,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与价值标准都迥异世俗的人格精神,境界更高。
四
儒道都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穷达贫富“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命是一种不受人的意志、与人的生命有关的规定,一种对人的自然生命予以制约的、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外在力量。这种观念促进了相术的发展。相术是一种通过观察人物的外在形貌、言语动作以推断其内心世界及其前途命运的方术,属于广义的观人学范畴。秦以后以贫富相命逐渐多起来,与之相应,王充主张:“凡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42]20,“寿命修短,皆禀于天”,“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42]46-52,明确地肯定贫富贵贱由先天命定,并提出贫富是可知的:“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按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42]116奠定了相学贫富观的理论。当以诗相人与两汉谶学、韩欧诗论结合,产生了特殊的诗论形式:诗谶,一种中国式的命相诗学。
大量事实证明,以相术相诗,从贫富观诗到以诗相人贫富,已成为古代诗论的特殊部分。谢肇淛肯定了诗中“富贵相”、“寒素相”[43]的存在,沈德潜进而提出读诗“而性情之厚薄,品诣之邪正,遭遇之荣枯,年寿之修短,皆可豫决”[44],阐述了观人学、相学与诗学的内在关系,明确了诗歌可以预言贫富穷达。这里的“诗”实际上成为一种隐秘的语言,通过诗评家来预决吉凶,用谶纬学来解释,就是“诗谶”了。诗谶是命相学与谶纬之学运用到诗论中的产物,它主要是鉴诗者通过观诗来预决作者及相关人物的前途吉凶,其中就有贫富、穷达的内容。由于它大量被诗论著作采用,成为诗学的一个范畴。如袁枚推断“东坡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39]243,结论是“诗谶从古有之”[39]250。
必须承认的是,诗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建立在传统诗论因内符外、言志言情的理论上,邵雍《伊川击壤集序》就在传统诗学肯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基础上,将诗歌的“情”概括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与一个时代的“兴废治乱”,并且说批评家“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肯定了诗人“志情”的可知性、可预测性。其二,建立在传统诗论的“气象”说上。如北宋论诗、作诗风气,“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人谓之‘诗谶’,谓之‘无气’”[45]贫富气象观诗说已经为许多人接受,如纪昀批苏子美《春睡》诗云:“人之穷通,亦往往见于气象之间,福泽之人作苦语亦沉郁,潦倒之人作欢语亦寒俭,不必定在字句之吉祥否也”[46]。气象观诗之贫富,在晚唐北宋已蔚为大观,这显然是韩欧理论的影响以及西昆(特别是晏殊)推崇富贵的产物。如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诗之作也,穷通之分可观: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李洞诗穷悴,故竟不第;韦庄诗壮,故至台辅;何瓒诗愁,未几而卒。”[47]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对孟郊、李贺诗歌的认识,如陆龟蒙视李贺诗为“暴天物”、“抉擿刻削,露其情状”,以致天罚,“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藉而死,正坐是哉!”[48]这一论点常常为论家所引,如清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李长吉诗奇险,孟东野诗劖刻,皆凿丧元气之人,故郊贫而贺夭”[49]919,实申陆论。而北宋以富贵观诗词,甚至“官人”,也往往巧合应验,这在前文已经分析过了。
不容否认,诗谶论扩大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理论上非常致命的局限。一、二首诗的气象与人物的贫富命运并没有必然关联,象《江南野录》记李璟见江为诗“吟经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说:“吟此诗者,大是贵族”,而江为坎坷终生。倒是晏殊以为“乞儿相”(《漫叟诗话》),乃为得之。可见有富贵气象之诗,未必就能达人。所以,正统而严肃的诗论家斥之为“富贵人相诗法,风骚家恐不烦尔尔”[49]408。
综上所论,以贫富论诗是古代诗论中常见现象,它是以贫富观人、以诗观人的产物。从观人学到观人诗学,体现了深厚的儒道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观人学中的贫富观念,对于古代诗学以贫富观人、基本范畴以及选诗学、品第学等方面的影响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而命相诗学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而负面的。古代诗论包容了观人文化的正负面养料,故成其“大”,这对今天诗学建设来说,不无启益。
[1]无名氏.大戴礼记解诂[M].王聘珍,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87-194.
[2]韩婴.韩诗外传集释[M].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86.
[3]刘劭.《人物志》评注[M].王玫,注.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156.
[4]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347.
[5]金沛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641.
[6]江盈科.江盈科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705.
[7]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8.
[8]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9]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212.
[10]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52.
[11]葛立方.韵语阳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554.
[13]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351.
[14]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10.
[15]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6]无名氏.会评会校金瓶梅[M].刘辉,吴敢,辑校.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2093.
[17]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18]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43.
[19]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65.
[20]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79.
[21]叶廷秀.诗谭[M]//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9257.
[22]吴乔.围炉诗话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4.
[23]方回.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评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4]颜之推.颜氏家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5]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7]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91.
[28]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54.
[29]王士祯.五代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303.
[30]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95.
[31]张戒.岁寒堂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459.
[32]王夫之,等.清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3:902.
[33]李东阳.麓堂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1387.
[34]刘体仁.七颂堂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8:217.
[35]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国学整理社,1937:487-491.
[3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99.
[37]王士禛,等.诗问四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5:55, 58.
[38]黄溍.黄溍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56.
[39]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0]辛朝毅.番禺县续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548.
[4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0.
[42]王充.论衡校释[M].黄晖,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43]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66.
[44]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M].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45]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
[46]顾实.诗法捷要[M].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26:175.
[47]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53.
[48]陆龟蒙.笠泽丛书[M].《四库全书》本.
[49]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Category Study on the“Poor and Rich”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Divination
WANG Wei-cheng
(Editorial Department,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Poor and rich,which is applied from people divination to poetics,fully represents the value concept centered on Confucianism and the effect of poetry.Traditional academic term of poetics consequently develops the concept and theme of poetics associated with poor and rich,sadness and happiness as well as“joy of speech difficult and poor words easy good”,influencing taxonomy and anthology of poems.That also greatly enriches divination and poetics and constitutes part of fortune-telling poetics which generat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poetics.
poetics of people divination;poor atmosphere;rich atmosphere;poetry prophecy
J207.2
A
1008-018X(2016)05-0030-07
2016-07-2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15)
万伟成(1964-),男,江西南昌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