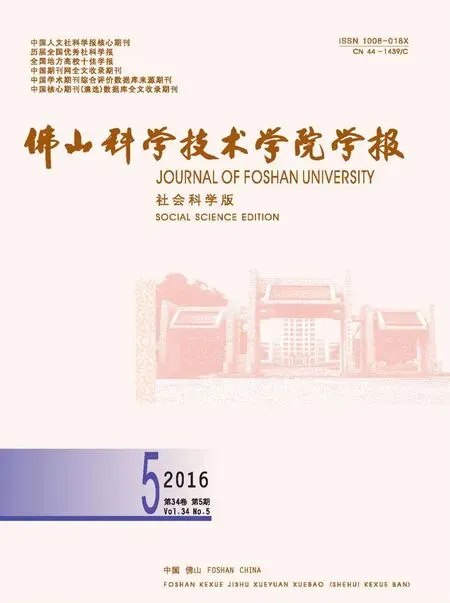试析符号消费视野下的时尚及时尚经济
陈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CHEN 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试析符号消费视野下的时尚及时尚经济
陈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从社会名流到市井平民,时尚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词汇。它或许是具体的餐饮服饰等生活潮流,或许是众人追捧的价值观念。但在符号消费的架构下,它更应该是直接践行的、贯穿着“生产——流通——消费”的行为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被它以简化为“符号”的形式来进行操作的,始终强调着“示差性”的视觉符号特质,造成奇异的社会景观。处于市场化的浪潮下,符号化的时尚也走上了时尚经济的道路,并以“谋定而后动”的实体型时尚经济和在网络狂欢中“自寻出路”的虚拟化时尚经济两种模式存在着。需要注意的是,二者不是对峙关系,当后者在自谋的出路上进入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就必然会转向前者,成为前者的后备力量。
符号消费;时尚;时尚经济
处于消费时代的人们,对于“时尚”二字绝不陌生。无论是高端如世界四大时装周的展演,还是亲民似微博热门#冬至吃什么#的话题讨论,生活中的一茶一饮、一蔬一菜都可演化成“时尚”的代名词而跨越千山万水、连接亿万人群。作为一个可效仿的对象,“时尚”可以是具体可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可以是直接践行的贯穿着“生产——流通——消费”的行为过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致力于让人们围困其中的“时尚”,一定是可视且可操作的。换言之,时尚一定是作为一个高度凝练的符号象征存在于大众眼前,其自身必须具备魅惑的形象或是特定的内涵来诱人入瓮,时尚的产业化后续才会成为可能。所以齐美尔才会说:时尚就是要“引人注目”,这也是为时尚的消费性埋下伏笔。
一、时尚的界定
我们今天从消费社会的角度,可以直观简明地将“时尚”定性为视觉消费,或是符号消费语境中的名词,但事实上这一概念在时代潮流中总是表现为众说纷纭的态势,存在着界定的困难。时尚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简而言之就是“时代之风尚”。在中文语境中,譬如宋代俞文豹的《吹剑四录》中载有“夫道学者,学时大夫所当讲明,岂以时尚为兴废”[1]观点,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艺能·成衣》里也有“今之成衣者,辄以旧衣定尺寸,以新样为时尚,不知短长之理”[2]一说,这些与时尚的浅层含义都是契合的。但是从西文的角度考量,它的含义就显得更为宽泛。“从英文词典对fashion的解释来看,至少包含如下意思:style,mode,vogue(时髦),look,new look,craze(狂热或疯狂),trend,set(趋势),rage(热衷或狂热),等等”[3]203,表层含义的泛化直接催生了对它的理性分析呈现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以下就是几种经典性的对于时尚的理论性解析。
(一)时尚的概念沿革
首先是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他被认为可能是西方最早对时尚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学者。他于1899年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观点,认为人的消费欲望除了物质需要外,很大一部分是心理满足感的推动。尤其是处于社会高端的中上层阶级,他们知道“如何以得体的方式进行消费,他必须按照恰当的方式度过他的休闲生活”[4]。这些“恰当的方式”显然专属于特定的阶层,以便直接显现出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其他阶层的民众也通过模仿这些“恰当的方式”实现了时尚的传播。之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指出了时尚是一种价值观念,说明其具有诸多二元对立特性的复杂性。并且提出了“时尚消费”的概念,附和凡勃伦的观点,觉得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超然于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必然会积极投身于时尚消费之中,也就是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谈到的“地位消费”问题。以上三种都是从时尚的功能性角度出发,认为它会强化社会圈层的分化,使得各阶层一直处于“紧密——疏离”的拉锯状态,时尚在此成了人们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
到了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领域,“时尚”一词就有了新的面貌:“它从不固定意义但却保持意义的某种机制,它永远是落空了的意义,但它也是意义:它没有内容,于是便成为一种景象,即人类赋予自己以权力,用没有意义来意指;时尚于是便呈现为一般表意行为的范例形式,因此便与文学的存在本身重新结合起来……所以它变为‘真正人类’的符号。”[3]204-205符号化的“时尚”,总是以无意义的形式来表情达意,却又以“范例”的标准化模式统摄着不断变化的现状。及至法国社会学家鲍徳里亚在1977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一书,符号化的时尚又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鲍徳里亚认为消费时代准确而言是符号消费时代,人们在消费产品的物质性以外,还消费着附着其上的格调、档次、意义以及价值。但是这种高于物质性的“价值”又不是处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精神意义,它仅仅是物质由“实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一种转变:“美丽的逻辑,同样也是时尚的逻辑,可以被界定为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能量的、动作的、性的)‘实用价值’向唯一一种功用性‘交换价值’的蜕变,它通过抽象化将光荣的、完善的身体的观念、欲望和享乐的观念进行概括——且由此而当然地否定并忘却它们的现实直到在符号交换中耗竭。因为美丽仅仅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5]125可见,时尚符号连接的是人的本真欲望,也正是在这种物性欲望的驱使下,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才得以“消费”,符号的交换价值才能够顺利实现。
(二)时尚是“解码”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还认为,“一旦人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这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6]“消费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7]如果说产品的生产是在持续不断地“发送”编码,那么消费者的消费就是有选择地“接收并重新创造”编码,也就是对符号编码进行“解码”的过程。恰如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谈及的那样,文化的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语形式流通的。”[8]而对于“解码”的形式,斯图亚特·霍尔也给出了三种假想地位。陆扬在《大众文化理论》中对三种地位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一种与权力密切相连,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生发下来的“主导—霸权的立场”,意味着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第二种是“协商的代码或立场”,观众在认可霸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二者处于不断商议的状态;第三种是“对抗代码”,观众利用“对抗代码”为信息解码[9]。斯图亚特·霍尔的立场是鉴于电视消费在符号化层面上的考量,那么同属于视觉化的符号消费,“时尚”同样适用于以上论述。无怪乎约翰·霍尔发出这样的慨叹:“在社会学家中,用特定意义和‘符号表达’的属于来定义文化的趋势正在不断增长。”[10]时尚产品的存在及运作,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迁转、相互作用的过程,更是人与外部世界进行符号互动的过程。“解码”的多重地位解读,其实就是时尚受众对于“时尚”的不同态度,代表着他们各自的解读能力和潜在的解读倾向。而能力和倾向的展示主要是依赖于主体的能动性,所以布尔迪厄才会说:“看的能力就是一种知识的功能……也可以说是感知的范式。一部艺术品只是对那些拥有文化能力(亦即可以译解符码能力)的人来说才会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3]223时尚的生机在于静待能够“解码”的观众,成功解码的观众是时尚的知音,也是时尚的伯乐。他们通过“解码”获得的心理满足和情感体验,就是时尚符号在产生伊始具备的“能指”的娱乐性以及“所指”的意义性,这与当今社会流行的符号经济架构下的“体验消费”倾向的宗旨是不谋而合的。
二、时尚的差异化追求
鲍徳里亚曾经说过:“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它便进行‘个性化’,或是进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性……”[11]布尔迪厄在《语言与符号权力》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将符号消费的领域由物质消费扩展至精神层面的文化消费的同时,肯定了文化产品的独立价值,也就是文化产品间迥异个性化的体现。但是也坚持“只有把文化产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化生产场中,其独特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12]“独特性”就是鲍徳里亚在消费领域所说的“差异性”,而差异性的逻辑就是符号消费的基本逻辑之一,是体现符号价值的关节点。我们既然从符号消费的层面来探讨“时尚”,就不能忽视时尚的差异性追求。
(一)阶层、个体间的奋战
从前文对于时尚概念的界定来看,理论家们就时尚在强化阶级分层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基本认可的。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理论》中这样描述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忆和符号产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出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景的范围。”[13]“自恋式的满足”是每个文化消费者获得的心理体验:引领时尚的中上层阶级在时尚的陪衬下实现了引人注目的表现欲和自我扩张的占有欲,跟从时尚的平民大众则在时尚的笼罩中获取了愿望的实现以及自卑的补偿。前者依赖时尚去强化自身与其他圈层的范围距离,所以一旦后者妄想通过倚仗时尚去缩短圈层距离的目的被实现,前者就会爽快地抛弃现存的时尚,转而寻觅另外的风向标。也就是有人戏称的“时尚的任务是保持一个延续不断的平庸化过程”[3]201。如果从福柯的权力观念来看,“在权力/话语的运作过程中,一个被权力/话语所控制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传播或再生产出这一权力/话语的主体”[3]332,时尚追逐者和时尚就应该是两相操纵的对峙关系。时尚的获得便是某种权力特别是虚幻优越感的享受,其落脚点还在时代话语权的谋求上。当然,现代社会固有圈层的距离维持还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平民阶层在反向上的远离——自立时尚。牛仔装的流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工人之后,是艺术家开始穿牛仔裤,接着是左翼政治活动者和摩托党,这赋予了牛仔裤一种表达反对现状的特质。”[14]不过,这种反叛性只有在现代消费社会才算获得适宜的生长土壤。因为只有在这样不囿于既定传统的场域下,它的反叛才足够在视觉上引起震撼,也足够在符号象征上产生标新立异的效果。而当它的反叛一旦成为时尚,成为另一项“平庸”,“反叛性”就得到了削弱。换言之,任何自下而上的反叛式时尚都会被消费社会利用、改造、重构,演化为另一种符号形式,以便服务于现有价值体系下的普罗大众。
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缺乏权威评判标准的个体在认知自我时,通常按照“与下行社会比较”和“与上行社会比较”两条线路来进行[15],这正是促成平民阶层“自立时尚”和中上阶层“另寻时尚”的两种心理机制。这样的路径从侧面反映出现代的社会流动性:时尚在社会不同阶层肆意流窜,时尚的代言人也在时尚的转向中几度更迭。这种社会各层次间的交流甚至是互通、交换也促使了时尚的繁荣,同时再一次印证了齐美尔对于“时尚”二元对立特性的分析:“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16],时尚在对外区分不同阶层的同时也对内统合了同一群体,它用两者的互动来构成了自己的边界。
(二)民族、国家间的对阵
时尚依存于每个社会人、每个社会阶层的复杂欲望,牵涉多元化的日常需求和个性化的价值取向,看似思绪繁多难以把握,其实可以从民族、国家等相对固定化的社会集体找寻根源。时代的发展影响着不同审美趣味的诞生,也见证着民族国家的盛衰进程。实际上,时尚虽然会在“新”的层面上不断演进有所要求,但仍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以民族特质为底蕴的日常生活或是艺术表现形式。作为流行性的文化现象,它必须寻求并力图得到民族的、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理解和认同,寻觅到适宜发展的语境,才能获取更长久的生命力。如果从“新旧”的时间角度理解时尚,满足这一要求并且能和“新”时尚遥相呼应的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代先民创造出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充当着体现民族个性、情感、凝聚力的载体而被称为“活的记忆”。荣格在谈到这种“种族记忆”时曾这样描述:“在每一个这些意象之中有着人类心理和命运的一些东西,一些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余”[17],集体性的认知揭示人们共同普遍的深层意识心理结构,是会从一个人出生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心理活动的。所以当落实到时尚——这一由各种社会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符号聚合物,它就同样摆脱不了特定族群的集体无意识以及文化的前理解。也就是说,时尚即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通达的理解,也仅是局限于某一范畴中,各层次团体的对抗依然存在,时尚的交锋仅是多样化的文化根基换了一个比武场后的较量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时尚在集体层面强调的差异性,在时代的纵向上还蕴含着循环性的表征。鲍徳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过一个关于职业经验、社会资格以及个体发展的“再循环”概念,“事实上,‘再循环’一词便能发人思索:它不禁令人想到了时尚的‘循环’: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同样都应该做到‘跟上潮流’,并且每年、每月、每个季度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等进行再循环。”[5]86这种“循环”是就其使用的频次而言,和“文化再循环”勾连,强调的是“永远动荡着的简单摆动”[5]88,我们希望突出的“循环”,则是就一种方式的唤醒或是意识形态的复辟来说,是对将循环文化视作过时的文化符号和成分的否定。恰如后来鲍徳里亚在面对“流行”这一关键词时直指它是一个人工操作的符号场所,具有两重性:“首先它是一种社会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当今社会=自然=理想社会——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链式结构是其逻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复辟了整个艺术圣化的过程,这便取消了它的基础性目标。”[5]108
(三)奇异的时尚:陌生与熟悉的结合
谈到“复辟”,譬如中国民众对于“旗袍”这种改良型服装的心理认同,章子怡、范冰冰之流曾在国外红毯穿过的“肚兜”、“龙袍”和“瓷器”,都是将传统文化中的认同物再度提炼,发扬光大。特别是今年亮相戛纳红毯的张馨予,一袭“红绿大花棉袄”式的印花拖长裙摆震惊全场。其实早在三月份的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冬发布会上,造型哑剧表演家王德顺为设计师胡杜光“东北大棉袄”开启序幕的走秀已经引起不少关注。设计师认为相比起“龙袍”、“瓷器”,东北大棉袄更接地气。平日里一件礼服要耗多少人力、镶多少钻、花多少时间裁剪,这件大花袄不过两天的工期几百块的原料费,“造价不高,工期不长,一件礼服最终能达到轰动世界的效果,这是时尚吗?我觉得这就是时尚。”胡杜光在微信朋友圈中如是说。不论国内舆论如何揶揄和嘲讽,不可否认的是,张馨予的这身“花袄”因被搬上国际舞台而赢得了足够高的关注度,并且从侧面展示了时尚作为符号而言既陌生又熟悉的奇异景象。这种“熟悉”,不仅指文化上的传统认知,还可以指向功用上的习以为常。可以作为例证的是“维密”(美国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简称)的“Fantasy Bra”,从1999年诞生开始就几乎是每一个女性无法拒绝的诱惑。2015年的梦幻文胸出现在大秀的Fireworks板块,总重量375克拉,含18K金、126颗钻石、400余颗其他珍贵宝石,价值200万美金却只是正常水平。因为早在2000年的大秀上,吉赛尔·邦辰身穿的那件缀有1300多颗宝石的红色宝石内衣,就因其1500万美金的天价而载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原本简单舒适的私密性内衣摇身一变,成了舞台上众人歆羡的宝石制品,性感奢华的“Fantasy Bra”便成了亿万女性梦寐以求却难以触及的时尚。
我们知道,审美经验的差异是潜存着“社会共通性”的,公共领域下这种共通性既不是独立纯粹的,又不是以某种狭隘范畴中的经验认同为根基的[18]。所以,时尚产品的符号生产和意义指涉在多元化文化背景就必须具备可通约性。于是就出现了以陌生符号(展示功能)横空出世的熟悉形式(布质外衣)——东北大花袄,或是以熟悉符号(内衣形态)熠熠生辉的陌生形式(展示功能)——“Fantasy Bra”。菲斯克曾经这样解读大众追求新事物的景象:“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新事物的欲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进步的意识形态……将时间看成是直线的,向前运动并不可避免地生出大量的变化。时间的向前运动及其带来的变化就通过进步、提高和发展而被作出了社会性的理解”[19]。换言之,“与时俱进”是时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时尚需要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间的认同,它要异于常态又不能完全剥离于传统,它还要另辟蹊径却不可完全割舍实用价值。如果说共时性领域中的特立独行是它称之为“时尚”的原则,那么历时性空间里的不忘传统以及追本溯源的实用功效亦是其立足的根基。在这样的多重要求下,时尚呈现出奇异的景象,成为陌生符号与熟悉符号的结合体,反映出在不同需求下时尚得以显露的差异性形态。
三、复合型的时尚经济
由上文可以发现,时尚作为一种符号是异于一般意义符号的:它既没有局限在基本的物质性的意义呈涉方式,也没有高悬在超物质的精神领域的价值探讨。它重视的仍是人和物之间的欲望关系,并由此衍生出划定社会圈层、实现符号意义上的交换价值等复合功能。基于此,时尚符号的生产——时尚经济也应该是一种复合型的模式,而且这种复合性质最起码会体现在审美追求和市场驱动两个层面的抵牾与结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从审美的角度还是出于利益的考量,都是基于时尚经济的发生机制。时尚产业以“时尚”为基础,且这里的“时尚”一定需要物质性为载体、为依托。物质结构本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围绕物质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活动。
在审美追求的维度上,主要凸显的是时尚经济对人心理需求的满足。我们说时尚是“引人注目”的视觉文化,是“示差性”的消费符号,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新奇却又不断地将这种新奇消化成平庸的行为过程。人们追逐时尚的最本源动机,依然是潜存着的蠢蠢欲动的炫耀欲望和个性要求。为了永葆这一心理上的新奇满足,创意要求就成了关键。那么,创意的“度”该如何把握?压箱底的传统当真一无是处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陈旧保守的主张需要保留,但是只能在民族性的范畴里得到维护。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早在鲁迅谈到“文学”时就有过类似的表述:有地方色彩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梅特·希约特也说过:“只有当我们以自己的特色展现自己时,我们才可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企图径直接近符合国际口味的现存标准,至少在三个方面来看是失策的。”[20]民族性不等同于一元的“族性”现象,它是围绕血统而生的个体认同与公共认同的结晶。所以说若是命令时尚符号必须体现差异性特质,就一定要依赖于意义与形式的创新,但这种创意又绝非信马由缰,必须由大众行为保驾护航。时尚创设者不能过分强调它的意义指涉、形式猎奇,而忽略其文化根基以及欲望需求。换言之,时尚是人类基于现实的对于浪漫主义的不懈追求,肆意的浪漫仅可远观,只有带着镣铐跳舞的浪漫才是大家乐见其成的把玩对象。这一审美追求是时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遗忘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对于发展伊始的时尚经济而言,其审美追求蕴含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维度;另一方面,时尚经济一旦以高歌猛进的姿态进入利益的争斗场——市场,其本身也会衍生出实体型和虚拟化两种经济模式。
(一)实体型的时尚经济
将时尚发展成实体经济,或是将实体经济范畴中的某一产品时尚化,都不是新闻。因为时尚既然可置于符号消费的视阈下,就必然会走上实体经济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使用过“精神生产”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精神生产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分工开始之际,是与人类的物质生产相对应的活动,“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1]时尚作为以文化创造或文化再创造形式存在的“精神生产”,所投入的时间、所能创造的产值都绝不亚于物质生产。
作为中国市场上最具活力的咖啡公司,星巴克(Starbucks)的成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当承载着美国精神的星巴克在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时,“咖啡文化VS茶文化”的对阵并不为人看好。而事实上,星巴克不仅做到了与中国传统茶文化共存,而且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品消费习惯,甚至促使了“不在社交媒体秀图就相当于白喝了星巴克”的理念为每一位年轻消费者所接受。为了将自身品牌打造成消费时尚,星巴克做出了许多努力。为了减轻消费者的抵触情绪,在进驻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初期,星巴克各分店都会定期为顾客开设一次咖啡讲座。上海的星巴克在一定时期还推出了“咖啡教室”的服务项目,为结伴而行的顾客配备专门服务的咖啡师。产品类型上,也开发了中国传统的绿茶文化。星巴克在创业初始坚守的宗旨就是“体验文化”,移民至中国市场就致力于渲染一种崇尚知识、尊重人本位,且带有“小资”情调的文化氛围。所以在产品定位上,星巴克的价格定位为“多数人能承担得起的奢侈品”,而消费者定位则是看中了具有追求稳定、享受时尚气氛与优质服务的心理倾向的白领阶层。为了使较高消费层的顾客产生产品依赖,在咖啡原料上也是精益求精,力求带给人们最纯正的咖啡。宣传策略上注重的是品牌形象推广,不屑于在广告、促销上投入高额成本,只赞助文化活动,比如上海当年的达利画展和APEC会议等。咖啡店的内部装潢也以“消费者的第二客厅,特别是白领的第二客厅”的标准设置,现场钢琴演奏、欧美经典音乐背景、当季的时尚报纸杂志极力赋予消费者“时尚”的观感享受。为了尽量实现消费者的“再次光顾”,星巴克的会员制度也与众不同。例如今年刚推出的施华洛世奇卡价值168元,含一张升杯券、一张早餐券以及三张“买一赠一”,除此之外没有优惠。平常每消费满50元获得一颗星星,满5颗星星就是玉星级,此时你会有一张生日邀请券和买三赠一(单次消费买三杯送一杯),25颗星会有专属金卡邮寄给会员,以及每消费十次就送一张中杯券。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名目就越多。但作为一种饮品消费,高级别的会员如果要充分利用这些优惠项目就势必携朋带友,这就又扩大了时尚消费的群体范围。此外,星巴克还会在每年圣诞节和其他节假日推出当年专属咖啡杯,样式年年翻新但上面都印有显著的星巴克LOGO,种类含随行杯、玻璃杯、保温杯,价格由几十到几百不等。携带这样的杯子去星巴克消费,不仅能在原价上享受优惠,更能享受周围人对你是“星巴克人”的羡慕目光。星巴克就是以这些方式奠定了自己“时尚消费”的地位,并在中国市场站稳了脚跟。
如果说“星巴克”是在中国市场为自身树立了“时尚消费”的形象,那么“维密”则是成功地化身为世界标杆型的时尚经济案例。“穿出你的线条,穿出你的魅力,带着轻松舒适的享受,穿出属于你的那一道秘密风景。”[22]打开“维密”的官网,会发现维密丰富的产品种类,包括内衣、居家服、泳装、护肤品、化妆品、香水、女鞋等你可以想到的一个女孩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美体装扮。但是“维密的产品类型将优先聚焦于文胸和底裤。财务数据也能说明这一点,文胸和底裤占据着一大半的销售份额。”除去文胸和底裤的奢华性感,其他的产品都以平民式的价格和设计进入市场。”[23]从1995年维密公司首次举办了内衣时装秀,到2005年开创性地与电视网络媒体合作直播,维密秀今年已经实现了在全球192个国家及地区的转播宣传。维密公司通过一年一度的“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使得维密品牌名声大噪。“魅力”、“美丽”、“时尚”、“一点儿浪漫”在每一个走秀版块得以呈现。“斑斓波西米亚(Boho Psychedelic)”、“异域彩蝶(Exotic Butterflies)”、“天使绘卷(Portraitof an Angel)”、“冰雪天使(Ice Angels)”、“粉红美利坚(PINK USA)”、“璀璨烟花(Fireworks)”等各具特色的主题似乎超越了内衣本身存在的意义,成为构筑一场宏大而瑰丽的童话意境的元素。而维密秀也不局限于一场秀的理解,更像是一出常演常新的百老汇舞台剧。作为舞台剧的主演,维密天使们也借此发挥了品牌价值。秀场上性感自信而又俏皮可爱的她们,生活中和其他年轻女性一样酷爱自拍、热爱健身,投身于公益环保事业,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2009年的维密秀中就不断插播新维密天使的选拔过程。从几千人的海选到最后两人在后台候场,整个过程的直播就像是一次“造梦”工程。维密天使由此展示出的,不仅仅是亿万男性眼中身着梦幻内衣的性感尤物,更是为了梦想不懈奋斗的新时代女性代表。维密天使的代表——超模吉赛尔·邦辰,就曾以一个巴西乡村小姑娘的起点,一跃成为《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被英国《独立报》称为时装历史上的标志。“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以维密超模吉赛尔·邦臣为灵感,发明了‘吉赛尔·邦臣股票指数’,以她为风向标,监测雇佣她的企业的盈亏状况,结果发现,邦臣股票指数远比道琼斯指数坚挺,领跑了时尚GDP。”[24]无论是在台上的魅力展示,还是在台下的个性活跃,维密天使们都在延伸着维密传播的时尚价值和品牌精神。
可见作为实体型的时尚经济,从市场定位到营销策略,它自己已经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运营模式。这意味着处于资本操控背景下的时尚文化符号,“不仅不是想象中的诗意符号自由,而且更是管制中的异化符号压迫。”[25]53在这个“管制中的符号压迫”的情势中,无论是消费者自己的消费选项、时尚偶像们的角色定位,还是时尚产品的消费走向,都已被制度牢牢地管制住。一项产业既然是可控的,就说明它在发展路途中对于条件配置的诉求是明晰的,包括“风险资本配置、资源聚集配置和市场激活配置等”[25]56。时尚虽然不是民生意义的刚性需求,但难得的是当它作为实体型经济出现的时候就涌现了极为规范化的发展要求和步骤。这也是我们不断呼吁企业甚至是政府的权力意志干涉时尚运行、不使其成为浮现云端的“空中楼阁”的原因所在。不过,我们在实体型时尚经济中期冀决定性意见的加入,却不能将其移植到虚拟化的时尚经济中。因为在后者的领域,时尚的兴起与走向不是“谋定而后动”,而是“出其不意、善谋者胜。”
(二)虚拟化的时尚经济
这里定义的“虚拟化时尚经济”,并不是指摆脱物质、在意识领域的空谈,而是指它最开始是以一种超越产品而存在、难以指涉具体含义的全民关注,然后才下降为对于产品本身的青睐以及拓展。譬如今年五月一下炒热的“头上长草”事件。一个价值低廉、小草形状的塑料发卡,其形态从“豌豆苗”扩展到“小蘑菇”、“小草莓”等各类植物,其范围由成都景区的大街小巷蔓延到北方“帝都”的国际马拉松赛场,忽然间在中国大地上成为时尚,一时间风头无二。究其根源,中国文化确有“头上长草”的传统,诸如“插草卖身”、“衔草报恩”,但是似乎都与当下年轻人的“长草”时尚无关。为此,境外媒体倒是表达了各自的解读。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直言:中国的本土时尚常常令人无法理解,无镜片眼睛和自拍杆都是这样,“头上长草”也是如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在做了一番街头调查后认为:这种在中国人脑袋上发芽的时尚,只是想展示一种嬉皮士精神(hipness),是彰显个性的嬉皮士精神的中国式表达。英国《卫报》深觉既然我们越来越束缚于工业品的包围,那么“长草”潮流就是一种亲近自然的环保主义运动。英国网站Business of Fashion则脑洞大开,将其看作是屡被关心情感归属的80后、90后,通过“装嫩”来应对社会的“逼婚”而发出的“宣言”,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抵抗。外媒不约而同将这一潮流卖力引入“主义”、“运动”的范畴,中国民众却未必买账。其实早于现实,“长草”的风尚在网络语境中就已有萌芽。博主“@伟大的安妮”在青春漫画《安妮与王小明》中,就为主人公王小明的头上安了两片叶子,符合“小明头上长草,是为萌”的段子。“暴走漫画”里的王尼玛拥有的经典头像,就是夸张的面部表情外加头顶的两片草。而因其口头禅而生的网红博主“@两条毛腿肩上扛”,更是直接将“头上长草”融入日本“颜文字”,绘制了一系列表情包,受到网民的热捧。这和当年微博上红极一时的“歪脖子头像”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反映的还是一种“萌”系时尚,是将对某一特定行为、形象的执着肯定,发酵为群体性的互动交流活动,从而演变为现实中的时尚认同。暑期大热的《捉妖记》中那个极肖“短腿萝卜”的小胡巴,以头顶一坨绿草的姿态荣登华语电影票房榜榜首。即便没有借鉴“头上长草”的萌系传统,在吸引观众上也多少有借它的东风。头顶的一棵小草,就在这样的舆论助推和商业运作下,由幕后走向台前,将虚拟性的关注转变为触手可及并且存在延展性的现实时尚。
此外更具代表性的还有“反手摸肚脐”事件。2015年6月10日,网上出现了热帖“有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女孩子能反手摸到肚脐眼就是身材好”。一时间,杨幂、蓝盈莹、张嘉倪、许飞等明星迅速跟上、“以身试法”,纷纷在社交网络晒照秀身材。霍思燕虽挑战失败,但也大方晒出照片,网友们随即跟帖予以效仿,在微博、微信掀起了刷屏的浪潮。对于摸不到的原因网友也以“手短”、“两手长度不一”、“柔韧性差”等理由予以自嘲,并逐步发起“锁骨放硬币”、“酒窝夹笔管”、“睫毛放牙签”等五花八门的检验好体貌的方式,实在是“城会玩”。对于这一时尚现象的评判众说纷纭,各领域都有着多种声音。英国一家名为“Curvy Kate”的内衣品牌就斥责这样的行为几近荒谬,还说这种“炫腹”行为根本就是对身体的伤害,他们反而鼓励女性要将时间花在爱护自己的身体上。因此,他们和乳癌慈善团体“CoppaFeel!”合作,共同推出“正面捧胸摸乳”(BoobsOverBellyButtons)挑战。他们希望以此敦促女性重视自我乳房的检查,确定乳房是否健康,能提早发现不适来降低乳癌发生的几率。“Curvy Kate”此举发挥了这一时尚在社会意义上的功效。与此同时,有一家公司则巧妙地将其热度转移到了公司的理念宣传和产品营销上,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式时尚在伦理范畴的价值评估予以了延展性的升华。2015年8月下旬,法国糖果SUGAR时尚手机在微博微信上发起了名为“反手夹手机”的游戏,众多媒体、时尚人士、段子手疯狂传播,甚至连国民媳妇海清、台球女神潘晓婷都摆出反手夹手机的姿势在微博分享。从8月24日登上新浪排行榜,一日之间阅读量就飙升到2.6亿,讨论量有14.4万之多,有媒体将它的火爆形容为“一场半失控的社交狂欢”。对于这一脱胎于瑜伽动作“反手在背部合十”的游戏,SUGAR大中华区高级品牌总监Queenie指出他们只是将它视为跟年轻人沟通的方式,在本质层面,他们是想向中国的年轻人传递一种平衡之美,这是在SUGAR所坚持的科技与时尚的平衡的价值观中得到的灵感。如果说第一层次“反手夹手机女神/男神鉴定图”无需露脸的颜值测试是寻求与消费者的沟通,第二层次手机侧面122颗施华洛世奇人工宝石的折射光泽则是SUGAR品牌烙印的加入,而第三层次就是意识形态的导入,即Queenie所说的健康生活与时尚工作的平衡哲学。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下虚拟型的时尚经济的根基,就是借助网络热度而运行的社交狂欢。“头上长草”这一狂欢是将网络漫画嫁接到了现实生活,注重的是形式上的跟风,至于心理动机实难揣测,深层意蕴也是暧昧不清、隐而不宣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一场直接停留在舶来的“萌”系时尚的、浅层次上的无厘头式的狂欢。它在经济效益上探求的深度还不够,远不如“天线宝宝”头上的“天线”值钱。“反手摸肚脐”比之则有了进步:一方面,大众在接受这一狂欢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思考,舆论导向偏重于正能量的宣传;另一方面,组织、团体对它进行了合理的再利用,譬如SUGAR公司就敏锐地抓住并升华了它的符号含义,通过三个层面的引导将产品信息和理念灌输到消费者的脑中,为自己的产品营销带来了极大的关注度。
在竞争渐趋激烈的时尚市场,硬资源的换代升级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研发,软资源的情怀内涵又易步入空洞抒情的困局。更重要的是,如果希望借此来达到对于受众群体范围的维护、培养乃至扩大的目的,操作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若能以多层面引导、渗入的方式将产品信息和理念灌输到消费者的脑中,或许就是今后创建有态度、有温度的时尚品牌的关键所在。作为实体型时尚经济的补充和延展,这也是它可以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时尚作为以“符号”为媒介和标准的视觉性的感官追逐,显然有审美追求的存在;但作为消费目标,它又是消费欲望驱动下的产物,离不开市场的运作和利益的考量。甚至在发生机制和展示形态上,也会有实体型和虚拟化之分。不过这二者不是对立关系,因为发展良好的虚拟化经济一定会转向实体型经济,成为实体型时尚经济的后备力量,是第二条道路。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时尚经济的“复合型”定位就是顺理成章的。
四、结语
虽然作为代表一个时代前沿性文化的社会产物,“时尚”理应从人类拥有自知意识阶段就开始萌发,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论探讨在19世纪才步入正轨。社会化大生产脚步的加快,使得时尚的范围由少数人的福利逐渐变成大众的需求;在消费时代演进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它视作典型的视觉符号进行“解码”。那些通过“解码”获得的心理满足和情感体验,都是在时尚“示差性”特质的基础运作而生。个体与集体多维度展现了时尚的差异性追求,并且强化了“熟悉”与“陌生”共存于时尚符号的奇特景观。我们将这种景观看成是一种浪漫与现实交融的“奇异的美”并孜孜以求,却不得不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形的手”看似“无形”,也有“实体型”和“虚拟化”之分。实体型的时尚经济需要倚靠成熟规范的运营模式,虚拟化的时尚经济则只在网络构筑的狂欢中自谋出路。而发展态势良好的虚拟化时尚必将转向实体型时尚的怀抱,在“审美amp;逐利”的的子维度——“逐利”上继续丰富着时尚经济的复合型形象。Coco Chanel曾言:“Fashion changes,but style endures.(时尚会变迁,不过风格会永恒。)”当五光十色陈列着的“时尚”被精简为排序着的“符号”时,或许我们更有可能透过物欲的迷雾,去触碰到这位时尚先锋所说的永恒的style。
[1]俞文豹.吹剑录全编[M].张宗祥,校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5.
[2]钱泳.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履园丛话[M].张伟,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罗钢.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
[5]让·鲍徳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让·鲍徳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0.
[7]让·鲍徳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
[8]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5.
[9]陆扬.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1-92.
[10]江凌.产品、符号、精神生产与品牌价值的传播——以“维多利亚的秘密”为例[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4(1):32.
[11]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2-223.
[12]李昕.符号消费——文化资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33.
[13]单世联.文化产业研究读本(西方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78.
[14]拉斯·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1.
[15]江凌.时尚文化符号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运行机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3.
[16]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2.
[17]赵宪章.20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71.
[18]李春媚.审美经验与公共领域的审美建构[J].北方论丛,2012(6):140.
[19]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4.
[20]大卫·鲍徳韦尔.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M].麦永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10.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0.
[22]沈玺.更好的品牌,更高的品牌资产——“维多利亚的秘密”品牌资产的建立与提升[J].中国制衣,2010(11):69.
[23]杨攀.维多利亚的秘密[J].销售与市场(评论版),2012(4):67.
[24]衣露申.吉赛尔·邦臣——领跑时尚GDP的超级女王[J].西部广播电视,2010(8):169.
[25]王列生.时尚产业:符号生产与市场操控[J].艺术百家,2014(1):53.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Fashion and Fashion Economy under the Horizon of Symbol Consumption
From celebrities to ordinary civilians,the fashion is the familiar word for every social member in daily life.It may be a specific food or clothing trend,or values popular with all people.But under the architecture of symbol consumption,it should be a more direct-practice behavior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To simplify this process should be in the form of“symbol”.This always stresses the“differential”trait of visual symbols and peculiar social landscape.Under the wave of market,symbolic fashion is also taken to the road of fashion economy,and exists in two modes of entity type and virtualization.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two are not confrontation relationship.When the latter is on the way out into the mature and stable stage of development,it will inevitably turn to the former,as the former reserve forces.
symbol consumption;fashion;fashion economy
CHEN 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F713.8
A
1008-018X(2016)05-0020-10
2016-07-01
陈玉(1992-),女,江苏泰兴人,扬州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