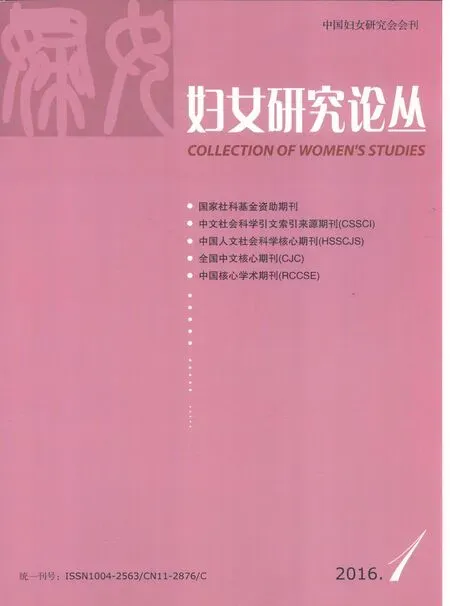社会变迁及文化视野下的女性犯罪研究述评
杨庆武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社会变迁及文化视野下的女性犯罪研究述评
杨庆武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妇女史;女性犯罪;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犯罪问题亦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章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就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新史学的兴起,研究方法以及视角的更新,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诸如妇女运动、妇女解放、婚姻家庭、文化教育、职业、思想观念、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研究,一些原先少有关注的议题,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犯罪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涌现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女性犯罪,在概念上,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如国内代表性的定义为“犯罪主体为女性,而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国外的代表性阐释则为“因为犯罪的是女性,所以才说成女性犯罪”[1](P1)。尽管在阐述方式上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内涵都强调女性犯罪即以女性为犯罪主体而实施的一种犯罪行为。目前,对女性犯罪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稀少,仅有王金玲[2]、陈劲松[3]的两篇,其着眼点是在于从社会学、法学的角度对当代女性犯罪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从史学的角度对女性犯罪研究进行专题性回顾的综述性文章尚付之阙如。因此,本文对现有的史学类女性犯罪研究成果,按照其研究界限大致划分为秦汉至元代、明清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三个历史时段,择其要者进行回顾和简评,以利于女性犯罪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对秦汉至元代女性犯罪的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日渐成熟的典章制度,而且在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领域,逐步确立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以及相应的父权家长制的社会性别体系,并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女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儒家伦常秩序的规范与约束之下,女性的生活和行为模式既有与之相融合的一面,亦有与之相背离的一面,因而形成了诸多与礼教伦常不符的犯罪行为。
林红在《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一文中认为汉代的女性由于礼教的束缚,因而其犯罪行为具有家庭性、从属性的特征,汉代对于女性的刑罚亦具有较为明显的性别区分,而且“男尊女卑”色彩鲜明,主要表现为维护丈夫的特权、夫妻同罪不同罚[4]。李彤认为,对于违反礼教的女性犯罪,汉代政府虽然在法律层面予以严惩,维护夫权和家庭内部的上下尊卑秩序,但是此种犯罪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仍广泛存在[5]。贾丽英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及《奏谳书》对汉代女性的犯罪形式如不孝罪、悍罪、奸罪等进行了考证[6]。对于秦汉时期的悍罪,贾丽英认为此种类型的犯罪虽然并不局限于女性,但是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却主要是女性,其判断标准是以丈夫的价值取向为依据,体现了秦汉法律对于父权制以及阶级特权的重点维护[7]。王金丰的《秦汉女性犯罪研究》[8]除了考证秦汉时期女性犯罪的各项罪名以及刑罚的类型和流变之外,还就女性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除了女性自身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受当时医疗条件、生存现实、社会观念及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的女性犯罪还具有类型多样、犯罪空间广阔以及作案独立性强等三大特征,从而体现了秦汉女性参与社会、超脱家庭限制的倾向以及鲜明独特的个性。与林红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秦汉时期对于女性犯罪的刑罚并无明显的性别特征。
自秦汉以降,及至唐宋时期,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社会性别规范和伦理秩序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而且,随着社会局势的变迁以及国家法令的调整,女性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行为模式也在演变。与之相应,在司法领域,女性犯罪的种类以及刑罚亦出现明显的变化。岳纯之认为,唐代的女性犯罪主要集中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破坏家庭伦理的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前两种犯罪尤为多见[9];而且在时空分布上相对广泛和集中、性犯罪比例较高,杀人意图较强;对于女性犯罪的原因,他认为除了女性自身的性格等内在因素外,其他诸如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政治地位、经济生活状态以及婚姻家庭状况等外在因素亦影响较大[10]。对于唐代女性犯罪的诱因问题,王文渊亦认为,自唐至宋,由于儒家礼教规范的约束、男女地位的差距致使女性心理失衡,进而容易导致各类犯罪[11]。该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唐宋时期法制的儒家化进程以及与女性犯罪之间互动关系的论述较为薄弱。
在宋代女性犯罪研究方面,曾京贤认为,在宋代由于父权制规范对于妇女的约束,致使妇女的法律社会地位相对于唐代日渐下降,在伦理规范中有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挣扎,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涉及犯罪活动,而且,由于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空间局限,宋代女性犯罪以家庭内亲属为对象的杀伤类犯罪居多。作者认为父权制、儒家伦理规范是导致女性犯罪的动因,但在司法领域中,女犯又可以据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特权和保障。因此,宋代女性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父权制的受益者[12]。此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宋代女性犯罪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少。此外,吴羽的论文还以宋代的瑶华宫、洞真宫为中心,研究了宋代皇室贵族女性因涉嫌犯罪而入道的问题,进而探讨了道教对宋代司法的影响[13]。
奸非罪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女性犯罪类型。黄伟廷对唐宋时期女性性犯罪的流变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他指出,唐宋时期对于性犯罪的法律规范既有延续性,又有明显的革新,总体上呈现出愈加细密严苛、刑罚加重的趋势;在性犯罪的立法意旨上,唐代以夫家为中心,保障家族利益,维持家族的完整性;而宋代则转变为以保障具体的小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为主,避免家庭的权益受到损害[14]。此外,美国学者伊沛霞在其著作中也对宋代妇女诸如通奸和乱伦等性犯罪有所涉及,她认为夫妻之间不和睦和年龄差距等因素都是性犯罪产生的重要诱因,妾和媳妇是经常涉及乱伦案的两类犯罪主体,宋代官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性犯罪一般采取规避和轻判的态度[15]。
相较于以往的中原王朝,元代在司法领域具有其特殊性,但目前学界对元代女性犯罪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蔡新中以元代公案杂剧为中心分析了元代妇女的家庭生活以及犯罪问题,指出,元代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前朝延续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受到冲击而逐渐崩坏,因此,元代女性较少受到礼教的束缚,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维护自己的家庭利益,甚至不惜为此犯罪[16]。但作者对于这些杂剧的写作者的身份及其书写女性犯罪问题意图、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分析有所忽略。
二、对明清时期女性犯罪的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有着明显的转变,各类妇女犯罪活动也随之而起,因此,明清时期的妇女犯罪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台湾学者林丽月利用明万历末年的公案体小说《杜骗新书》为基本史料,并结合晚明其他笔记、小说对晚明妇女犯罪尤其是诈骗犯罪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妇女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很多妇女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犯罪活动中,充分显示了晚明妇女形象的多样化[17]。杨瑶和陈超则重点对明代的妻妾群体和品官命妇群体的犯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杨瑶指出,明代的妻妾犯罪有多种形式,但主要集中于杀伤及奸非罪两种类型,并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以家庭成员为作案对象,手段残忍,以性犯罪为主。明代妻妾犯罪问题的凸显,表明了明代传统礼教的衰落以及女性意识的崛起[18]。陈超认为,明代的品官命妇,她们依靠其夫或子而得朝廷荣宠,在法律上亦享有特权和优待,级别越高,其特权亦越大,一般性犯罪,可以用钱钞收赎,但若犯十恶重罪,亦同样受到惩处,也因其具有依附性,故若品官犯罪,命妇亦受牵连,反之,命妇犯罪,品官有时亦受惩罚[19]。
在清代女性犯罪的研究方面,米雪对清入关之前的满族女性犯罪问题进行了考察。她认为,满族入关之前的汉化进程以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致使满族妇女犯罪问题日渐显现,主要以通奸犯罪居多,多以家庭领域为中心,以已婚女性为主,对于女犯的司法审判受习惯法的影响较大,与男犯并无明显的区别[20]。作者对于满族入关前的汉化状况、儒家文化以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满族女性、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满族妇女传统的生活制度和习惯论述较为薄弱。王强认为,清前期女性犯罪既有法律、婚姻制度的因素,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女性所受的束缚压迫日重,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从而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产生分歧,由此诱发各种犯罪行为[21]。
《刑案汇览》《刑科题本》是满清时期记载各类案例的司法档案汇编,是研究清代司法、社会问题的重要史料,不少学者依据这两部司法汇编中记载的有关女性犯罪的案例,对清代女性犯罪进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杨晓辉的专著《清朝中期妇女犯罪问题研究》是目前清代女性犯罪研究领域中颇有分量的一部著作。她指出,清中期的妇女犯罪主要有略人略卖人罪、杀伤罪、奸情罪以及干名犯义等家庭伦理犯罪,其中奸情犯罪数量尤多,这些犯罪多与家庭范围密切相关,已婚妇女是主要犯罪主体,同时还具有残暴性以及被动性的特征,具有恶逆变的倾向。不良的家庭环境、贫困、婚姻与等级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要教育的缺乏等因素是为清朝中期妇女犯罪的主要原因[22],不过,该书对于边疆及其他民族女性以及贵族妇女的犯罪情况涉及较少。
总体上看,奸非罪以及杀伤类犯罪仍然是清代女性犯罪的重要种类,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性考察。如台湾学者赖惠敏、徐思冷利用清代刑部档案讨论了女性的犯奸案件。作者认为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发生,与当时人口的普遍流动以及男女性别比差距较大有关,而且还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在大量外来人口移入的新开发的地区,奸情案件发案率较高,因奸情而引发杀人是女性杀伤类犯罪的重要诱因,而且,男女情奸并不只求情欲的舒解,还可能代表了下层社会人士的生活模式,士大夫所提倡的妇女贞节观念未必成为民众普遍信奉的行为准则[23]。郭松义亦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出于感情、迫于家庭生计或缺乏劳力、遭遇挟制等原因,易发生和奸、通奸等不法行为,继而诱发犯罪,这种行为的发生与清代的婚姻制度有密切关系。妇女缺乏婚姻自主权,而社会对于男女私情的过于苛严,导致奸情演变成恶性案件,这也是清代私通行为所表现出的时代特点[24]。
除了性犯罪之外,杀伤类犯罪亦是清代女性犯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犯罪类型。朱阁雯指出,清代女性的杀伤类犯罪一般发生在家庭领域,受害者一般也为家庭成员,犯罪手段较为残忍。故意杀人、过失杀人、预谋杀人和伤害等是杀伤类犯罪的主要类型,性犯罪、诬告罪、拐逃罪等其他犯罪类型都有可能诱发杀伤性犯罪的产生,此类犯罪的产生既有女性自身的因素、社会经济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的因素、恶逆变因素等[25]。
三、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犯罪的研究
清末至民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向近现代急剧转型的时代,这种社会转型是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以及思想意识导向,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延续已久的传统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日渐由乡土社会向商业化、工业化的近代城市模式转变,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流动性的发展趋势。这一剧变的时代,对广大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女性不仅成为公众论述的主题,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化程度亦有着明显的转变和提高,而伴随着女性走向社会的进程,各种问题亦随之层出不穷,特别是女性犯罪问题,更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由于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女性犯罪虽与传统时代存在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更多的却是呈现出新的演变态势和特征,尤其是民国时期都市女性犯罪现象的凸显,从而赋予了这一时期女性犯罪以新的时代色彩。因此,以下就从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民国时期都市女性犯罪研究两个方面,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应的概述和评析,以厘清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犯罪问题的变迁脉络及其凸显的特色。
(一)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
对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犯罪问题,艾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博士论文《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1901-1919)》[26]从社会性别的视角,不仅论述了自清末至民初女性犯罪的种类以及流变,同时还系统论述了女性犯罪与婚姻家庭、职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自清末至民初,女性犯罪不论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犯罪类型由性犯罪、杀伤性犯罪向经济型犯罪转变,并出现大龄化的趋势;女性犯罪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末以来女性主动或被动的走向社会,自我意识增强有关,是女性自我觉醒和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此外,对于民国初年女性犯罪的原因,艾晶认为,经济和职业压力是民初女性犯罪的根基,年龄、婚姻和家庭是其犯罪的动因,教育的缺失和不良是其犯罪的诱因,面对生活的压力,犯罪也就成为女性进行抗争的方式和手段[27]。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其经济化的趋势日渐增强,大多数犯罪主体的资产、生计和职业状况都较差,犯罪实为女性解决经济困境的无奈之举[28]。
相较而言,艾晶对于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合理性,但是在某些方面亦有所不足,如她认为清末民初女性犯罪是女性群体自我觉醒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同时,自清末以来,政府修律对于女性犯罪的宽宥程度有所提高,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女性借机行不法之事,使之成为其进行犯罪并逃脱法律惩治的手段和策略,作者对此在文中没有深入论述。此外,艾晶对于民初女性犯罪原因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偏向于总体宏观性的阐述,而且作者大体上是将女性犯罪行为视为一种被动、受压迫的产物,将女犯视为一种受害者的形象,忽视了女性犯罪之中所含有的主动性、自主性的因素,此外,作者将犯罪主因归咎于经济困难,颇有大而化之的经济决定论倾向。
王奇生也从宏观角度对民初以来的女性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元以降,广大的女性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大多缺乏应对的能力,尤其是下层女性,其智识和谋生能力缺乏,境遇更为艰难,经济压迫导致的贫穷是她们犯罪的主因,对女性犯罪者来说,有时犯罪只是她们为谋生或逃避不幸生活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29]。王奇生所提出的观点与另一位著名学者严景耀有相似之处。严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关系》一文中亦提出,中国近代以来急剧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危机,使乡村女性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变动,从而产生严重的个人危机,进而走向犯罪之途。作者还指出女性的犯罪率要低于男性,具有地域性的差异,多以拐骗、绑架等经济性犯罪为主,男女犯罪的差异不在于犯罪性质而在于犯罪手段[30]。
赵凤喈亦对女性犯罪问题有所涉及,通过钩稽史料,概略地梳理了自传统时代以来女性犯罪及相应刑罚的流变。作者将女性犯罪分为普通类犯罪与特别类犯罪两种,而特别犯罪即是指基于女性生理特征所犯之罪,如奸非罪、和诱与略诱罪、堕胎罪、重婚罪等[31]。此外,Paul Bailey主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20世纪初期的女性犯罪问题进行了审视。作者指出,晚清以来女性犯罪问题的显现,逾越了官方、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女性所期待的规范,令其感到恐惧和焦虑,事实上这是近代以来整体社会文化变动的体现[32]。
(二)民国时期都市女性犯罪研究
正如严景耀所言,近代以来的女性犯罪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不仅城乡之间,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间,亦有所不同,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表现更为明显。具体而言,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都市如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由于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和冲击较早且更为广泛,相较内陆或者农村地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和行为模式改变亦更为显著,在这种近代化的都市环境中,城市的聚集效应引起的人口的大量集中和快速的流动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疏离和陌生,商业化导致的对消费主义的崇尚,使得一些人为名利、为生存而苦心钻营、不择手段,都市也就成为一处“风俗浇薄”之地。而对于众多或主动或被动进入都市的女性来说,近代化的都市氛围固然使其有机会摆脱传统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获得更为宽阔的社会化的空间和余地,但同时也使得女性自身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从而诱发各种犯罪行为,也就致使民国时期的城市女性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比乡村更为凸显,而且不论在犯罪率、犯罪类型以及犯罪手段与方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民国时期都市女性犯罪现象的凸显,引起不少研究者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北平、上海等城市,较早关注这一议题的主要是民国时期的部分社会学家,主要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对都市女性犯罪现象进行考察和研究,如严景耀的《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33],张镜予的《北京司法部犯罪统计分析》[34],周叔昭的《北平一百名女犯的研究》[35],何贞懿、田镐与钟文惠合著的《北平男女犯性欲罪及女犯杀人罪、经济罪之社会调查》[36],徐蕙芳、刘清於的《上海女性犯的社会分析》[37]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周叔昭通过对北平100名女犯的调查研究指出,1920-1930年,北平地区的女性犯罪以略诱、和诱、奸非、窃盗、诈欺、伤害、吸食鸦片和吗啡等为多,略诱罪居高不下是北平女性犯罪与国内一般女子犯罪不同的一点。作者认为,北平女子之所以犯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压迫、女子的无知以及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何贞懿等人的调查结果亦表明,20年代北平女性的犯罪类型仍然是以略诱、窃盗、诈欺等经济性罪为主,由性欲问题引发的奸杀类案件在女性杀人犯罪中较为普遍,女性之所以犯罪,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健全、法律的失衡所致。在周叔昭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马静对1927-1937年北平地区的女性犯罪问题进行了考察。她认为,这一时期的北平下层妇女被迫从家庭走向社会,但其参与社会的程度有限,仍遭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迫,贫困和婚姻问题仍然是女性犯罪的主要诱因,而且几乎扩展至所有的罪名,但在某些犯罪领域,仍保有传统女性犯罪的特点[38]。
在上海女性犯罪研究方面,徐蕙芳、刘清於通过对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3个女监300余名女犯的调查和统计分析指出,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女性犯罪以鸦片犯居多,其次是拐骗、绑票、强盗等,多属于经济性的犯罪,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上海地区女性犯罪的最大动机。曹关群采用《申报》等资料指出,1927-1937年,上海地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日益增多,空间日益扩展,女性的职业日趋多元化,由此导致女性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日益严重化、多样化。作者认为,上海城市社会的过分都市化、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以及普遍的贫困化,加剧了女性犯罪的产生[39]。但是,该文对于整个上海地区的中上层女性、知识女性以及外籍女性的犯罪问题没有涉及,亦欠缺对于女性犯罪问题的管控和司法处置等方面的论述。此外,在史料利用上,该文以报刊资料为主,没有采用丰富的司法档案,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民国时期上海部分特殊女性群体的犯罪行为以及单类型案件进行了研究,如王书吟考察了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奶妈群体的犯罪问题,作者通过对《申报》相关案例的梳理指出,奶妈群体的犯罪行为主要以绑架、诱拐、窃盗为主,多是与同乡或者姘夫合伙进行的有预谋的犯罪。这一时期随着上海迅猛的城市化转型,乡下贫穷的奶妈面对各种刺激和诱惑,从而易诱发诸多犯罪事件[40]。堕胎入刑是近代法律改革的产物,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城市中,各种女性堕胎事件频发,并引发诸多刑事案件。对此,龙伟通过《申报》所载发生在上海的堕胎案例的分析,进而指出虽然在国家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堕胎非法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女性堕胎犯罪,一般有着明显的轻判倾向[41]。
民国时期,上海的娼妓业一度繁盛,贺萧则对娼妓业所附带引发的女性犯罪问题有所论述。作者指出,由于娼妓业的存在而附生的诸如对于女性人口的买卖和绑架,老鸨对于妓女的虐待、逼良为娼等行为则很明显是一种犯罪,实施或参与犯罪者中,女性为数不少[42]。倪万英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的婚姻刑事案件所涉及的诸如重婚、通奸及和诱等女性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后指出,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予以从轻处理[43]。
除了北平、上海之外,孙巧云、梁津晃还分别考察了天津、广东新会地区的女性犯罪问题。孙巧云指出,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的女性犯罪相较传统社会而言,犯罪数量及犯罪类型都大为增多,这一时期的女性犯罪以虐待罪为主,其次为拐卖与赌博,盗窃、诈骗最少,这与女性自身的特点以及女性的社会化、生计贫困等原因有关[44]。梁津晃指出,民国后期新会地区的社会转型,海外丰富侨资的物质刺激,传统社会控制力的削弱、社会的不稳定、贫富差距等因素促发了女性犯罪的产生,而且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伤害、窃盗、侵占、烟毒案件为主要类型,主动型犯罪和“双向告诉”刑案较多[45],但相对缺乏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而且对政府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对控制女性犯罪的举措论述不足,同时亦缺乏对女犯自身的关注。
四、研究评价及展望
综上所述,就现有的女性犯罪的研究成果而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妇女史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还是相当的薄弱,其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亦不容忽视。
首先,既有的女性犯罪研究成果,大多是以各种论文的形式发表,有分量的专著较少,而且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具有学术水准的、有创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研究时段上分布不均,大多集中于唐宋、明清及民国时期,而对其他时代女性犯罪情况关注有所欠缺;在对史料的运用和解读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倾向于化约性的综合性论述,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女性以及外籍女性犯罪问题进行具体的、微观的实证研究则少有人关注。
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研究的主题虽然是关于女性犯罪的问题,但现有的研究能以社会性别理论和视角进行研究的反而不多,大多还是侧重于国家政府的视角来看待女性犯罪,更多仍是偏重于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分析,侧重于相关法律条文的梳理。现有的这些研究中,各类女犯的身影和声音反而被各种律令、法规所屏蔽,各类女性刑案中所蕴含的社会本身的鲜活性、多样性亦无法得以显现。
第三,在研究的结论方面,不少研究者认为经济贫乏是导致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女性犯罪是被迫而为之,是她们对于生活困境和社会进行抗争的手段和策略,亦有研究者提出女性犯罪是受压迫女性反抗父权制的伦理秩序,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这一结论将犯罪之女性形塑为一个受迫害的反抗者形象,然而是否全然如此,有待商榷。一般而言,犯罪行为的发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所致,也有可能是某种“情景力量”所驱使和左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若将其视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似乎更为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若过于强调经济困乏的驱动性,反而有化约性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此外,女性犯罪能否被视为对父权制的反抗,是否意味着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人认为应当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具体案情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某些犯罪如单纯的诈骗、诱拐等经济犯罪、虐待以及涉毒类犯罪,很难说与对父权制伦理规范的反抗有多大关系。
为了促进女性犯罪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必须正视现有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不足,尽可能找出更好的出路和解决办法。个人认为,未来女性犯罪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首先,要将女性犯罪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中,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去进行审视和考察。女性犯罪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是社会演变进程中的产物,同时亦是社会生态的体现。按照美国犯罪学家路易斯·谢莉(Louis Sheley)的说法,女性犯罪可以说是广大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范围和卷入社会活动的程度的晴雨表”,其“犯罪行为的多样化以及参与犯罪活动的增多与她们的社会作用扩大直接相关”,而且女性犯罪也是“犯罪行为的最好的衡量尺度之一,……因而有可能一清二楚地研究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犯罪率和犯罪形式的影响”[46](P103)。因此,结合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女性犯罪的时代背景、流变、共性和差异性,而且可以更为明确地剖析女性犯罪的特性,了解女性犯罪多面相的复杂性。
其次,更新研究视角和理念,除了社会性别视角之外,更主要的是新文化史研究理论及方法的运用。新文化史的基本特征,按照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论述主要表现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47](P32),而这些特征对女性犯罪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如上所述,新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的一点在于其中心议题关注的是文化,“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47](P65),因此,可以利用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去充分发掘女性犯罪内涵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此外,女性犯罪研究与新文化史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以及微观历史的取向也极为相符,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新文化史对历史叙事的倡导,对叙述史学写作的强调,对于女性犯罪研究而言,“一百个女性会产生一百部《女人的一生》式的小说,当然,在痛苦的人生之路上,人们的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女人靠卖淫勉强糊口,有些女人则靠偷盗行窃来维持生计”[48](序言P1),也可以说“每一个女性犯罪的案件,都诉说着一个悲惨的故事”[48](前言P1),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去关注这些案件,方能真正实现对女犯自身的关注,实现对其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感知,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犯们的行为,理解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
最后,要充分发掘和利用新的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史料以及民间文献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传统的官方性质的档案、报刊、方志、官箴书之外,还要充分利用笔记、文集、诗歌、弹词、契约等各类民间史料,在近现代女性犯罪的研究中,还要注意口述史料搜集和运用的可能性,同时借鉴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史料进行分析和解读,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女性犯罪问题的研究。
[1]赖修桂,赵学军.女性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王金玲.妇女与本土: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犯罪研究[J].浙江学刊,2002,(6).
[3]陈劲松.近20年中国女性犯罪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2,(6).
[4]林红.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1).
[5]李彤.礼教形成中的汉代妇女生活[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6]贾丽英.汉代有关女性犯罪问题论考——读张家山汉简札记[J].河北法学,2005,(11).
[7]贾丽英.秦汉时期“悍罪“论说[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1).
[8]王金丰.秦汉女性犯罪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9]岳纯之.唐代的女性犯罪与女犯监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3).
[10]岳纯之.论唐代的女性犯罪及其法律惩治[J].比较法研究,2009,(6).
[11]王文渊.唐宋女性犯罪问题探研[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12]曾京贤.宋代妇女犯罪问题[D].嘉义: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07.
[13]吴羽.道教与宋代皇室女性犯罪——以瑶华宫和洞真宫为例[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5,(3).
[14]黄伟廷.唐宋奸罪研究[D].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2010.
[15]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6]蔡新中.元杂剧中的家庭戏与女性犯罪[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6).
[17]林丽月.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3).
[18]杨瑶.明代妻妾犯罪及其司法实践——以法律文书为考察中心[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
[19]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20]米雪.清入关前八旗女性犯罪问题[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
[21]王强.清前期女性犯罪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22]杨晓辉.清朝中期妇女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3]赖惠敏,徐思冷.情欲与刑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历史解读(1644-1795)[J].(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6).
[24]郭松义.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J].历史研究,2000,(3).
[25]朱阁雯.清代女性杀伤类犯罪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9.
[26]艾晶.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研究(1901-1919)[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
[27]艾晶.民国初年女性犯罪的原因解析[J].求索,2010,(11).
[28]艾晶.民初女性犯罪的经济化趋势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29]王奇生.民国初年的女性犯罪(1914-1936)[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1).
[30]严景耀著,吴桢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1]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修正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2]Paul Bailey著,古伟瀛,蔡岚婷译.女子行为不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犯罪、逾矩与性别[J].(台湾)女学杂志,2008,(25).
[33]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J].社会学界(第二卷),1928,(6).
[34]张镜予.北京司法部犯罪统计分析[J].社会学界(第二卷),1928,(6).
[35]周叔昭.北平一百名女犯的研究[J].社会学界(第六卷),1932,(6).
[36]何贞懿,田镐,钟文惠.北平男女犯性欲罪及女犯杀人罪、经济罪之社会调查[J].监狱杂志,1930,(2).
[37]徐蕙芳,刘清於.上海女性犯的社会分析[J].大陆杂志,第一卷二期,1932,(10).
[38]马静.1927-1937年北平女性犯罪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3,(8).
[39]曹关群.民国时期上海女性犯罪问题(1927-1937)[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40]王书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奶妈群体的历史考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41]龙伟.堕胎非法:民国时期的堕胎罪及其司法实践[J].近代史研究,2012,(1).
[42]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3]倪万英.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婚姻刑案研究:以1945-1947年上海部分婚姻刑案为例[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44]孙巧云.清末民初天津下层市民犯罪问题研究——以《大公报》为中心[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45]梁津晃.民国后期新会女性犯罪的法律控制(1945-1949)[D].广州: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9.
[46][美]路易斯·谢利著,何秉松译,罗典荣校.犯罪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犯罪的影响[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47]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48][日]广濑胜世著,姜伟,姜波译.女性与犯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责任编辑:绘山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emale Cr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e
YANG Qing-wu
(Department of Histor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women's history;female crime;social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history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scholars have produced a large amount of papers and monographs examining female crime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This paper intends to assess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research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propose alternatives based on the identified shortcoming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D669.8文献标识:A
1004-2563(2016)01-0121-08
杨庆武(1980-),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