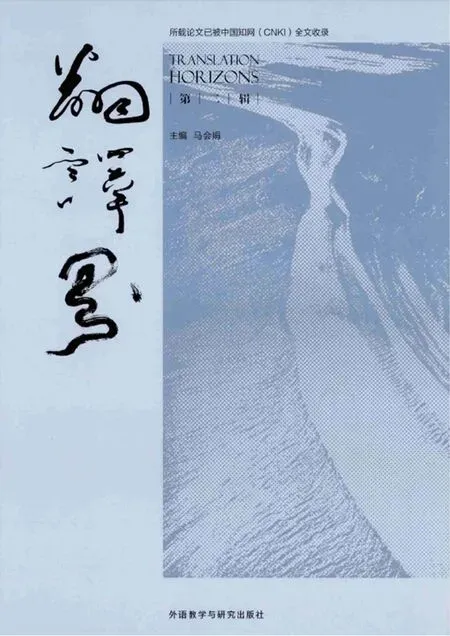圣经汉译与“信达雅”
——吕振中圣经翻译思想探究①
任东升 井琼洁
中国海洋大学
圣经汉译与“信达雅”
——吕振中圣经翻译思想探究①
任东升 井琼洁
中国海洋大学
哲罗姆提出的“圣经翻译用直译、文学翻译用意译”主张,划分了神圣文本翻译和世俗文本翻译的严格界限。直至坎贝尔和马礼逊分别提出圣经翻译在三个层面的追求,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才有所改变。提出“信达雅”翻译原则的严复曾翻译过《圣经》片段;《圣经》译者吕振中则明确提出圣经翻译应均衡运用“信达雅”并努力实践这一标准。本文结合吕振中的翻译思想考察其圣经翻译实践,探讨“信达雅”之于圣经翻译的内涵及其翻译实践价值。
圣经汉译;吕振中;信达雅;翻译原则
1.引言
“神—人”之间的不可约性奠定了“神圣文本”与“世俗文本”的划分依据,以至于“神圣文本”最初被视为不可译。因此,神圣文本的翻译,只能是单向性翻译,即由神圣“降为”世俗,世俗文本则不可能经由翻译“升为”神圣文本。在基督宗教圈内,圣经历来被认为是“神的话语(God’s word)”,基督教的传播和壮大过程几乎与圣经翻译的历程同步展开。原初意义上的“圣经”与以“译本”出现的各民族语言圣经的关系,用Nida所谓的“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s”(Nida, 1952: 1)定位,还是贴切的。然而,回顾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历史,把圣经翻译与文学翻译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思维,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直至George Campbell和RobertMorrison分别提出圣经翻译在三个层面的追求才被打破,甚至严复基于中国传统文论而提出的“信达雅”原则也被接纳为圣经汉译的指导原则。第一个以一人之力把整部圣经翻译为中文的华人学者吕振中(1946)明确提出圣经翻译应均衡运用“信达雅”,并努力实践这一标准。本文拟结合吕振中的圣经翻译考察其圣经汉译思想,探究“信达雅”之于圣经翻译的内涵和实践指导价值。
2.圣经翻译思想流变
圣经翻译始于公元前306—公元前246年间,从希伯来文翻译而成的“七十子希腊文本”(The Septuagint),传说译者不在一处翻译,但翻译出来的译文却一模一样,犹如“听写”出来一般,这就是圣经翻译史上著名的“听写式翻译”。这种翻译思想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只有经过神的感召,译者才能够从事圣经翻译。“听写式”直译,无疑是机械、刻板、僵死的翻译。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哲罗姆参考希伯来语《圣经》和“七十子希腊文本”翻译了拉丁文版《圣经》,他认为“圣经中连词义都是一种玄义”(St.Jerome, 2006: 25),提出圣经翻译用直译,文学翻译用意译的主张,划分了神圣文本翻译和世俗文本翻译的严格界限。这种圣经翻译和世俗文学翻译二元对立的局面直到18世纪英国圣经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坎贝尔(George Campbell)提出圣经翻译三原则,才有所改变。坎贝尔认为《圣经》的翻译应为文学和宗教两种目的服务,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应努力做到三个原则:
(1)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
(2)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移植原作的精神与风格,
(3)使译作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转自Nida, 2004: 18-19)。
坎贝尔的圣经翻译观意义重大。比坎贝尔晚一年的Tytler在其翻译论著《翻译原理简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1790)中,提出了与坎贝尔圣经翻译三原则极其相似的论点,来自圣经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如此相似,可见圣经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的距离正在缩小,圣经翻译开始逐步摆脱二元对立的局面。20世纪著名的圣经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Nida)基于圣经翻译实践提出了“动态对等”,这对圣经翻译,以及文学翻译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圣经翻译和文学翻译的距离进一步缩小。进入21世纪,就连参与过圣经翻译的学者也认为圣经翻译应该摈弃“逐字译(word-for-word)”和“功能对等(dynamic/functional equivalence)”这两种对立的“圣经翻译哲学(Bible translation philosophy)”,认为圣经翻译除了追求准确(accuracy)和清晰(clarity)之外,还要追求美(beauty)和雅(dignity)(Scorgie, 2003;Barker, 2003)。beauty和dignity就是“雅”。实际上,圣经翻译追求“美”和“雅”,既是圣经文本自身的经典性所决定的,也是圣经翻译出于普及圣经并尽力保持圣经译本生命力的外在需求所决定的。
不仅西方圣经翻译家,来华传教士译者以及中国本土圣经译者也在积极探索更有效的圣经翻译方法。1807年马礼逊到达中国,开启了圣经汉译的新局面。马礼逊提出圣经汉译要表达原作的意义和精神,文笔要“忠实、明达、地道,能做到典雅更好”(Morrison, 2013: 15)。马礼逊的主张,与之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极为相似。马礼逊的圣经翻译思想也得到了中国本土圣经译者吕振中的响应,吕振中认为圣经翻译要将“信达雅兼筹并顾”,并在圣经翻译实践中努力践行这一翻译标准。无独有偶,1999年出版的圣经“新译本”在其简介中声称翻译团体“共同朝向信、达、雅兼备的目标努力”(中文圣经新译会, 1999: 1)。独立完成全部《新约》和大部分《旧约》汉译的冯象(2012)认为“译事须‘信达雅’兼顾”。另一位华人圣经译者王汉川(2010: 260)则提出“准、达、通”的三字原则,更多地强调忠实、明白、易懂。査常平(2014: 207)认为圣经汉译应该遵从“信中雅”的原则,并据此将圣经翻译分为三类:(1)以道成肉身的“道”为中心的翻译,侧重于以原初语言的意义表达为目的,遵循以传递上帝之道为中心的直译原则;(2)以道成肉身的“肉身”为中心的翻译,侧重于以译入语言的意义理解为目的,遵循以强调接受者的肉身处境为中心的意译原则;(3)以道成肉身的“成”为中心的翻译,介于直译与意译之间。圣经翻译需要“忠信于原文、雅致于汉语”(査常平, 2014: 209)。
吕振中提出的圣经汉译要“信达雅兼筹并顾”,得到了后世圣经译者和学者的回应。将“信达雅”原则作为圣经汉译实践的指导原则,是圣经翻译思想的一大进步。从西方早期的“圣经翻译—文学翻译”之“直译—意译”的二元对立思维转变为信、达、雅兼筹并顾,使得圣经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之间的距离得以缩小,甚至有望沟通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
3.吕振中的圣经翻译思想
《圣经》的翻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镶嵌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受着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制约。从唐朝景教徒阿罗本(Rabban Alopen)翻译部分圣经《旧约》和《新约》算起,圣经汉译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景教士以“儒释道释耶、全盘汉化”(颜方明, 2014: 259),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则试图“依儒避佛”(傅敬民,2008: 127),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从瞄准知识分子精英转向普通大众,经历了“文理-浅文理-官话”的语体转变。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译者对圣经汉译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任东升, 2007)然而,在严复根据中国传统文论提出翻译的“信达雅”原则之前,圣经汉译与“信达雅”从未发生联结。中国学者摆脱来华传教士的主导或牵制而翻译《圣经》是近一百年的事情。中国学者王宣忱(1933)、吕振中(1946)、吴经熊(1949)翻译出版了圣经《新约》。吕振中的圣经翻译思想最为丰富。
3.1 吕振中及其圣经译本
吕振中出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省南安县,毕业于香港大学,后又在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神学。1946年,他前往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并于1948年到英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一步进修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等译经学问。吕振中的圣经翻译历时三十多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翻译成果分别为:《吕译新约初稿》、《新约新译修稿》以及《旧新约圣经》。为了表彰吕振中在圣经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香港大学于1973年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莱纳德·肯尼思·扬(杨国伦)(Leonard Kenneth Young)在学位授予仪式上称赞吕振中“单枪匹马,顽强战斗于翻译之战场,游历于语言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纷繁错乱之竞技场……”作为启示荣光的硕果,他以同时代的人们所能听懂和理解的语言,把所罗门之歌那摄人心魄的美和登山宝训的感人纯朴倾注到他们所熟悉的思想与词汇中去(吕冲, 刘燕, 2013: 78)。
1997年,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出版了《新约圣经并排版》(The Parallel New Testament),由香港圣经公会代理,包含按章节并列印刷的共六种版本的新约圣经,其中就包括吕振中译本。英文《圣经》“钦定本”有87万单词,汉语“和合本”有110万汉字,在众多的《圣经》“全译本”中,由一人独立翻译完成出版的只有吕振中译本。吕振中翻译的《旧新约圣经》是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里程碑。
3.2 吕振中的圣经翻译实践与信达雅
翻译活动是异常复杂的,普通文本的翻译会受到各种因素,如文本内部语言的差异、文本外部权利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用途等的影响和制约。作为基督教的典籍,圣经翻译更是比其他文本的翻译要复杂得多。译者的翻译思想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直接影响译作的生成。吕振中在1946年由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的《吕译新约初稿》序言中明确指出,《圣经》的汉译“须将信达雅兼筹并顾”。他把翻译比作一面镜子,认为“信达雅之均衡运用,即为最平译镜,即可反应原文之真意义”(吕振中, 1946: 3)。吕振中在圣经翻译实践中努力践行“信达雅”的原则,给信、达、雅分别注入了新的内涵。
3.2.1 “信”的内涵
所有的圣经翻译者,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华人译者,基本都宣称以忠于原文为翻译的宗旨,如“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委员会制定的四项翻译原则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译文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以忠于原文为翻译《圣经》最重要的原则,与《圣经》作为宗教文本的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享有绝对的权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16-17),也就是Nida所说的《圣经》是“神语人言”(Nida, 1952: 1),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祂的话是绝对无误的,这就要求翻译《圣经》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若有译本被认为是不忠实的,该译本很可能受到教会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受到信仰较为保守的教会的批判。那些被视为不忠实的译本,最终会被否定和淘汰以致不能流传。(林草原, 2003)因此,翻译《圣经》,首要要求就是在解经与释经过程中对圣经字面意思和属灵含义层面的忠实,尽最大努力使圣经译本具有原本意义。
既然圣经译者都宣称自己的译本是忠实的,为何圣经译本又如此繁多且各个译本都有一定差异呢?首先,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一方面《圣经》的原本已经遗失,现有的都是“抄本”,现有的圣经文本,都是“原本意义”上的圣经译本。其次,正如司徒雷登(1946)在《吕译新约初稿》弁言中所言,“圣经所涵真理,原无尽藏……圣经每一新译,均可视为一种注释”,马丁·路德也认为每段圣经经文都有无穷的理解,在了解《圣经》的事上,始终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每一读者对《圣经》的理解,每一译者的翻译,都是对圣经“原本意义”的探索和丰富。(转引自李广生, 2015: 94)然而对《圣经》的理解和诠释不是任意的,它与圣经文本是分不开的,无论释经学如何发展,“对经文的历史背景和字面意思只会更加重视”(李广生,2015: 112)。美国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赫施(Eric Donald Hirsch, 1991:214)认为某一文本的“本文含义(signif i cance)始终未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含义的意义(meaning)”,本文的含义具有确定性和可复制性,变化的只是意义,也就是译者与本文的一种关系。因此,译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追求最能确切传达原文全部信息的译文。(谢天振,2000: 59)绝对的忠实是不可企及的,译者只能力求尽善尽美。(万兆元,2013: 202)这也是圣经翻译历经两千多年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原因。
吕振中在为1946年出版的《吕译新约初稿》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圣经翻译需“用字之划一与精辨,行文合于原语法及变化,一词一句,一字一点,皆须注意周到,不可轻率放过”。吕振中提倡的直译,不是死译、硬译,而是反映原文的真实精神、准确转达原文语意、“不失原文语气与文情”的直译(周建人, 2009: 729),“不能以词害意,须将信达雅兼筹并顾”(吕振中, 1946: 3)。
例1:《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2节:
官话和合译本: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下划线为作者所加,下同)
吕振中译本: 当那些日子、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野地宣传,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
钦定本之修订本: And in those days cometh John the Baptist, preaching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ea, saying, Repent ye;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官话和合译本”虽以钦定本之修订本为翻译蓝本,但该句话的翻译却改变了钦定本之修订本的语序,翻译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该句的希腊语原文为(是 repent,悔改之意,悔改是第一位的。“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更像一句平铺直叙的叙述,原文所包含的强烈劝导、督促的韵味并没有译出,吕振中译为祈使句“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种劝导、说服信徒的含义就很明显了。吕译本把for译为“因为”,比省略不译的“和合本”也更加忠实于原文。
纵观吕振中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译文的语序上更加贴近原文,尽最大努力保持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和句子结构,包括许多“美丽独特之观念”(吕振中,1946: 3),力求准确忠实地再现原文的精神和含义。
3.2.2 “达”的内涵
官话和合本圣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美国和苏格兰圣经公会以及多个差会与华人信徒集体合作的成果,自1919年出版以来,俨然成为了中文圣经译本的“钦定本”,对广大华人基督徒及中国教会影响深远,可以说是“一本‘标准译本’”(刘美纯, 2013: 80)。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与“和合本”翻译时的汉语已经有很大不同,现代汉语日臻成熟,修订“和合本”或者重译圣经的呼声越来越高。吕振中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坚信重译圣经非常必要。圣经是“神语人言”,经文本身所包含的真理要义“必须假以‘人言’传达,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读懂,就需要使用简朴、平直的语言”(郑海娟, 2012: 33)。为使译文晓畅流利,在公众场合诵读时,能令普通人易于聆听,他选择使用平实质朴的白话语言,用“较长之白话”取代“优雅恰当之文言”(吕振中, 1946: 3)。对于近代文人学子喜欢用半文半白的方式写作,吕振中不敢苟同,白话文并不低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语言一等,“表达方式的卑降无害于主题的神圣”(郑海娟, 2012: 34),《圣经》经文中隐藏的奥义也可以用朴素平实的句子来表达。上帝的启示不应仅为读书人显现(尽管这是其目的之一,或许还是最重要的),还应撒播其恩泽至孩童与百姓。人们不仅能在阅读中得到启示,也能借助于口耳相承,而简明的口语化圣经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吕冲,刘燕, 2013)
对于圣经翻译的文体问题,吕振中亦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洋化文体,此为任何译作之永久问题。或曰,圣经既为中国人而译者,则须译成纯粹之汉文。试问,此可能乎?欲强行之,势非漏失许多美丽独特之观念不可。旧文理译本正蹈此弊!查历代各国各宗教之译经(我国佛典亦在其内),未有能全免于洋化者。即七十子之希腊文旧约译本,其希伯来之词句,亦所在多有;而希腊文新约且有不少之希伯来气味在焉!拉丁本与英重订本,更无论矣。准是以观,译经之文体问题,不必完全避免非中国式之语法,实可尽量应用中国之语法,或中国人所说得通而听得懂之新语法,将新约时代原文之真意义与思想,予以他译介绍,使今日读者宛然置身于二千年前之犹太社会中。(吕振中, 1946: 3-4)
在这里,吕振中结合传教士翻译的文理《圣经》、希腊文译本、拉丁译本和英文译本论述文体问题,过于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和句子结构,会形成读不通的译本,导致死译、硬译。相应的,过于与目的语保持一致,又会丧失许多原文的特色,比如传教士翻译的文理《圣经》,这也不值得提倡。因此,他提倡使用中国式的语法,并且要尽量应用中国式语法,如果实在行不通,也可用中国人说得通、听得懂、看得懂的语法,实际上就是要达到功能上的对等,即:“接受者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Nida, 2004: 159)。
圣经翻译的宗教目的是传播福音,吸纳更多信徒。在不曲解圣经原文本基础上的译语通达是译者不懈的追求。圣经翻译者永远处于两难之间,不是过于拘束地求准确,便是太随意地意译。他只能在他的文字的可能范围之内求准确,不过分亦不足。(贾保罗, 1965)这也正是吕振中所努力追求的:一方面要尽量保持原文字句译法的准确划一,做到“信”,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在公共场合诵读时易于普通读者聆听,保证译本的可读性,做到“达”。通过对比官话和合本与吕振中译本会发现,吕译本避免使用“和合本”中一些拗口、生僻罕见、有歧义甚至是误译的字词句法,语言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为方便读者理解,减少阅读困难,译者用现代通用的时刻表达法代替昔日的时辰表达法,同时减少不知所云的音译词。例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2节,官话和合本将希腊词语”和“分别译为“拉加”、“魔利”,读者并不知道其具体含义,吕振中则将其表达的真实含义翻译出来,译为“饭桶”、“傻瓜”,并注明希腊文为“拉加”、“魔利”。译者有义务了解词语“所负载的源语言文化,从而明确源语言作者意欲传达的真正含义”(杨清波, 杨银铃, 2012: 66),而不是将不知所云的译文呈现给读者,从而保证译文的可读性。
3.2.3 “雅”的内涵
严复所提“信达雅”中的“雅”是指汉以前的字法、句法,遭到很多指责和争议,后世也曾重新审视“雅”的含义,认为“雅”既可以指“文字优美,富有文采”,又可以指“风格的再现”(金文俊, 1991: 30)。圣经翻译与文学翻译一样,同样追求一定的文学性和原文风格的再现。汉语追求均衡美,常通过对仗、排比、四字格来实现铿锵有力的节奏,吕振中在翻译中尽可能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0节,吕振中翻译为“似乎忧愁,却永远喜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拥有万物”,对仗、排比的运用使得译文更有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圣经翻译中的“雅”不仅仅指文学性和原文风格的再现,那圣经翻译所追求的“雅”还有什么更丰富的内涵呢?词源当中对“雅”的解释是“正确、规范”。古人对《史记》和《汉书》中“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一句中“尔雅”的解释为“近正也”,也就是文章要正确、规范的意思。“雅”的本义就是“正”,对语言文字来说,就是必须正确、规范,“合于正道和正统”(沈苏儒, 1998: 49)。其实这也是严复所追求的雅,他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翻译,也是因为当时的桐城派古文符合当时的文章正规。而吕振中所追求的“正确、规范”更多的是使圣经译本具备反映圣经之“经典”地位的经学特征。单从《圣经》中文译名就可以看出译者对其经学特征的不懈追求,儒家经典称为“四书五经”,道家经典“道德经”,释家经典“佛经”,可见“经”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译者没有音译而选择译为“圣经”,实在是有助于这个外来经典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接受程度和传播速度。(钟志邦, 2012: 24)吕振中在对圣经书名的处理上,并非遵循马礼逊的“圣书”(1823)书名传统(1919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做“圣书与文学”的演讲时还在沿用“圣书”一词),而是沿用传教士汉学家贺清泰的“古新圣经”(1803)书名模式,遵循了圣经书卷之“旧约”在前“新约”在后的“旧新约”的文本顺序,这样就区别于有凸显基督教新约文本重要性之嫌的“新旧约圣经”书名传统(如“和合本”)。时代在变,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规范”的语言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圣经的翻译也要与时俱进,使其具有符合某一特定时代的经学特征,才能保证其经典地位不衰。真正的正典不是圣经,而是“圣经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游斌, 2003)。吕振中翻译圣经的时代与“和合本”圣经所处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译者结合时代需求,赋予圣经更加丰富的含义。
例2:《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7节:
官话和合本: 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阿。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都也听从了他。
吕振中译本: 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讨论说:这是什么?新教训阿!带着权柄阿!他吩咐污灵,污灵竟听从他!
钦定本之修订本: And they were all amazed, in so much that they questioned among themselves, saying, what is this?A new teaching! With authority he commandeth even the unclean spirits, and they obey him.
“灵”属于基督教的语域,而“鬼”则属于佛教的语域。吕振中将unclean spirit翻译为“污灵”,正如holy spirit被译为“圣灵”一样,spirit的翻译是一脉相承的。“污灵”要比“污鬼”更加正确、规范,也符合基督教受众的心理预期。按照对现代汉语之“雅”的理解,“雅”就是“译文需用规范化的语言,并达到尽可能完善的文字(语言)水平,还有符合译入语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以使译作为其受众所便于理解、乐于接受或欣赏”(沈苏儒, 2005: 8)。显而易见,吕振中采用“污灵”的做法更符合这一理解。
没有一个译者可以穷尽对《圣经》的理解,吕振中的翻译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圣经》在这个时代作为经典所需的经学特征,是译者在圣经翻译过程中追求“雅”的表现。圣经翻译追求“雅”,吕振中并不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早在19世纪担任委办译本助手的王韬曾应用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来表达这种思想,他认为传教的每一本著作,都应该“文质皆备,真理与文采皆显”。而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圣经翻译上开始转向文风的雅致”(游斌, 2007: 353)。基督教在中国得以长足发展后,其宗教文本的翻译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忠实、通顺的问题,而是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雅”,圣经汉译与信达雅是密切相关的。
4.结论
“信达雅”曾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郁达夫, 185: 837),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精华,“其影响深度之深和覆盖面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刘云虹, 许钧, 2010: 17-18)。严复基于中国文论提出“信达雅”针对的是其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实际上严复翻译圣经片段《马可福音》前四章时,也贯彻了“信达雅”原则。(任东升, 2011)沈苏儒(2009:1048)早就指出“应该赋予这三字以新的含义,继承和沿用之”。具体到圣经汉译,从最初只重视忠实甚至机械的忠实,如1803年的贺清泰译本“不图悦人,唯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转自徐宗泽, 1949: 20),后来“和合本”注重中文的地道和文采,从传教士译者宾为霖1867年采用“四音步”翻译旧约《诗篇》、湛约翰1890年采用“九歌体”翻译《诗篇》,到中国译者李荣芳1932年采用“骚体”翻译《旧约·耶利米哀歌》、吴经熊1946年采用“五言”、“七言”、“骚体”翻译《诗篇》(取名《圣咏译义初稿》)(任东升, 2007: 313-327)、张久宣翻译《圣经后典》诗歌(张久宣, 1996: 238-240),这些都是朝向圣经汉译“雅化”的尝试。作为中国本土圣经学者和圣经翻译家的吕振中,首次明确圣经翻译应均衡运用“信达雅”,“信达雅”运用于指导圣经汉译,不仅考虑到圣经文本自身的宗教经典地位和文学经典身份,丰富了“信达雅”翻译思想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神圣—世俗”文本翻译的单向性和“宗教—文学”翻译的二元对立思维,有望在实践层面弥合“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之间的沟鸿。
Barker, K.(2003).Bible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In G.Scorgie, M.Strauss & S.Voth (Eds.), The challenge of Bible translation (pp.51-64).Michigan: Zondervan.
Morrison, E.(2013).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2).London: Forgotten Books.
Nida, E.(1952).God’s word in man’s language.New York: Haper & Row.
Nida, E.(2004).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corgie, G.(2003).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In G.Scorgie, M.Strauss & S.Voth(Eds.), The challenge of Bible translation (pp.19-34).Michigan: Zondervan.
St.Jerome.(Trans.).(2006).The best kind of translator (letter to Parmmachius).In D.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冯象.(2012).美极了, 珍珠——译经散记.书城, (8), 28-32.
傅敬民.(2008).《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124-130.
赫施.(译).(1991).解释的有效性.北京: 三联书店.
贾保罗.(1965).评吕振中牧师新约新译修稿.载于贾保罗(编), 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
金文俊.(1991).“信达雅”的模糊性.山东外语教学, (3), 29-32, 37.
李广生.(2015).马丁·路德的圣经观及其圣经诠释.圣经文学研究, (11), 64-113.
林草原.(2003).忠信与操纵——当代基督教《圣经》中文译本研究(硕士论文).
刘美纯.(2013).经典的延续——《和合本修订版圣经》介绍.宗教经典汉译研究,79-95.
刘云虹, 许钧.(2010).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中国翻译, (5): 13-18, 94.
吕冲, 刘燕.(2013).吕振中: 一位中文圣经翻译家.圣经汉译文学研究, (7),72-94.
吕振中.(1946).序.载于吕振中(译), 吕译新约初稿(3-5).北平: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任东升.(2007).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任东升.(2007).西方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索.外语教学, (1), 87-91.
任东升.(2011).论严复的圣经片段翻译.东方翻译, (24), 15-26.
沈苏儒.(1998).论信达雅: 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沈苏儒.(2005).翻译的最高境界: 信达雅漫谈.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沈苏儒.(2009).论“信达雅”.载于罗新璋, 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修订本)(1041-1048).北京: 商务印书馆.
司徒雷登.(1946).弁言.载于吕振中(译),吕译新约初稿(1).北平: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万兆元.(2013).巴哈伊经典翻译: 历史、标准与程序.宗教经典汉译研究,193-210.
王汉川.(2010).心灵牧歌.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谢天振.(2002).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外国语, (3),53-60.
徐宗泽.(1949).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
颜方明.(2014).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中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 259-263.
杨清波, 杨银玲.(2012).专有名词的汉译与译者的素养.上海翻译, (4): 65-68.
游斌.(2003).谁的圣经?何种神学——评James Barr《圣经神学的概念: 从旧约观之》.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 (19), 281-286.
游斌.(2007).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圣经文学研究, (1), 348-368.
郁达夫.(1985).郁达夫文论集.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査常平.(2014).主祷文的翻译与神学.基督教研究, (4), 207-212.
张久宣.(1996).圣经后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郑海娟.(2012).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中文圣经新译会.(1999).圣经新译本.香港: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钟志邦.(2012).中国学术界的“圣经学”:回顾与展望.载于梁工(编),圣经文学研究(1-33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建人.(2009).关于“直译”.载于罗新璋, 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修订本)(728-730).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蒋剑峰)
① 本文为2015年度中国海洋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建设资助项目“圣经与西方文学艺术鉴赏”阶段性成果;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圣经》汉译话语动态诠释的文化研究”(16BYY027)阶段性成果。
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翻译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宗教翻译思想。井琼洁,硕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主要研究方向:典籍翻译研究。
作者电子邮箱:任东升dongsheng_ren@ouc.edu.cn井琼洁1115404682@qq.com
——以翻译《沉默的大多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