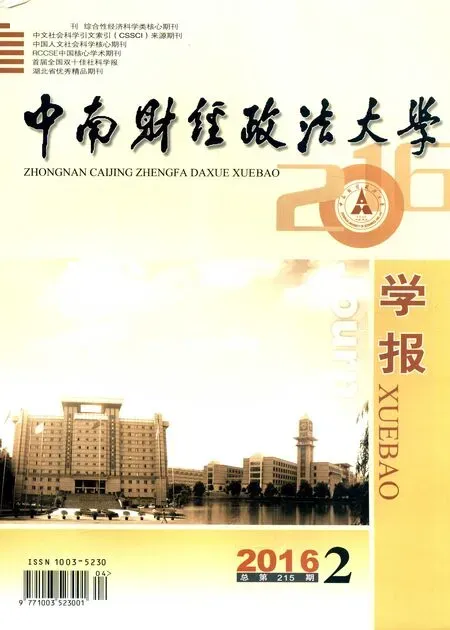经济解释范式:经济思想史中的又一次综合
高少慧 罗必良 何一鸣
(1.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2.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2)
经济解释范式:经济思想史中的又一次综合
高少慧1罗必良2何一鸣1
(1.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2.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张五常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争取利益最大化为内核,加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等约束条件作为保护带,推导出一系列可验证的理论假说,从而得到一般化的经济解释范式。它继承了穆勒范式和马歇尔范式的“稳定性偏好与理性选择”前提假设,又增加了“科斯革命”中的交易费用约束,因此,其解释能力远远超过了萨缪尔森范式和新凯恩斯范式。经济解释范式与穆勒范式、马歇尔范式、萨缪尔森范式和新凯恩斯范式一样,都应该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次重要综合。
关键词:经济学综合;经济解释;研究范式;穆勒综合;马歇尔综合;萨缪尔森综合;新凯恩斯综合;张五常综合
一、引言
经济学从1776年创立以来,经过不断的变革与修正,逐渐演进为今天的主流范式。然而,在这段人类知识扩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思想史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观点各异的学派与不同思潮的相互碰撞。其中,“经济学革命”与“经济学综合”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中可谓交互辉映。诚然,关于“经济学革命”的研究已经出现[1],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影响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经济学综合。事实上,经济思想史上已经出现了“四次综合”:穆勒的古典综合、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萨缪尔森的宏微观综合和斯蒂格利茨的新凯恩斯综合[2]。那么,这四次综合是以什么标准加以划分的?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或将会出现第五次综合?
本文根据上述四次综合的演进历史发现,除第一次综合之外,每一次经济学的综合都是在最近一次经济学革命的基础上加上前一次综合的内容而形成的一种新范式。之所以第一次综合没有这样的规律,是因为它没有上一次综合的新范式存在,不过,它仍然是在最近一次革命的基础上加上其他理论而构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用集合的数学公式表示的话,前四次综合都具有以下的一般性:{第t次综合}={第t次革命}∩{(t-1)次综合}。

图1 经济思想史“四次综合”与“张五常综合”
除本节外,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主要回顾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开创的四次经济学综合;在此基础上,第三节重点讨论张五常开创的经济解释范式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价格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关键概念等方面所完成的综合性工作,寻求经济解释在经济思想史上所处的坐标位置;最后一节是对全文进行总结性述评,对“张五常综合”与经济思想史上其他四次综合进行比较与评价。
二、经济思想史上的四次综合
(一)穆勒的古典综合:斯密革命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历史主义
穆勒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确立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3]。穆勒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于他对前人和同时代的经济学的综合。可以说,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穆勒是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改良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穆勒利用功利主义的“快乐与幸福”主题去掉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悲观主义色彩,并认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观点,因此,他的综合更是一种改良主义。它不但包括了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理论学说,而且调和了古典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等相互冲突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对于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带来很大便利的情况下,政府管制才是可行的,而自由市场则是主要的“自然秩序”。可见,在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上,穆勒也表现出一种改良主义的综合思想。
总之,穆勒的古典综合是在斯密革命的基础上融入了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历史主义等学派的学说。若从集合论的角度看,则可以得到一个推论:
推论1 :{穆勒综合}={斯密革命}∩{{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历史主义}}
通过外圆面积-内圆面积=横截面(圆环)面积计算一卷厕纸平均长度,以普通厕纸R=60 mm,r=20 mm,基于上面的推理,设厕纸的长度是y m: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边际革命与穆勒综合
在《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马歇尔把杰文斯的局部均衡边际分析方法与穆勒的古典综合范式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静态局部均衡边际分析方法,从而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4]。诚然,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被称为传统价格理论,而现代微观经济学就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价格理论最重要的地方是构建了一个决定市场价格的供求均衡分析框架。需求和供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均被统一在供求理论框架下,从而形成一个均衡价格,即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因此,一旦需求或者供给发生改变,均衡价格也随之调整。不过,马歇尔的供求变化理论仍然属于比较静态分析范畴,没有考虑价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除了讨论资源配置之外,还进一步把分析一般商品价格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分析当中,形成新古典的收入分配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相比,马歇尔在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动与资本)上增加了第四个要素——企业家才能,利润则是企业家才能的要素报酬。换言之,马歇尔把企业家才能视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认为它有自己独立的报酬和供给价格。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是第一个在经济思想史上给予企业家以一定位置的经济学家,他把企业家定义为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寻求价值的代理人,认为企业家能够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和产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大的领域。可见,马歇尔是把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与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并从斯密的利息理论中把利润分离出来,定义它为与工资、地租和利息并列的第四种要素报酬,从而最终形成新古典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新”主要体现在从“边际革命”中引入“边际分析”这种与过去的“平均分析”不同的分析方法上,但它仍然包含穆勒的古典综合的基本元素。换言之,经济思想史上的新古典综合是在古典综合的基础上,加上边际革命而形成的。如果从集合论的角度看,那么,本文可以得到第二个推论:
推论2 :{马歇尔综合}={穆勒综合}∩{边际革命}
(三)萨缪尔森的宏微观综合:凯恩斯革命与马歇尔综合
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宏微观综合是继马歇尔综合之后占据欧美经济学界主流的理论范式。萨缪尔森在名为《经济学》(1948)的经典教科书中,把凯恩斯的宏观总收入决定论与马歇尔的微观价格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把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综合起来,把单纯的总需求分析与生产要素供给分析结合起来,试图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框架应用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中[5]。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建立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来自新古典价格理论中的供求模型,与之不一样的是,横坐标变成了总量概念,纵坐标从原来的商品价格变成一般物价水平。因此,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变动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不过,萨缪尔森已经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即把马歇尔的比较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分析。
总之,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综合其实是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均衡理论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加以综合;二是把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与新古典支持的货币政策综合在一起。可见,萨缪尔森主导的第三次综合其实是把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和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从集合论的角度看,本文得到第三个推论:
推论3: {萨缪尔森的新古典宏微观综合}={马歇尔综合}∩{凯恩斯革命}
(四)斯蒂格利茨的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理性预期革命与新古典宏微观综合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既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微观选择基础,又继承了新古典宏微观综合关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观点,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
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在其撰写的教材《经济学》(1993)中,构建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6]。事实上,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在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假设上加上了信息约束条件,造成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关于商品质量的信息量上的差异。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往往比生产者要少很多,那么,理性的消费者在面对质量不确定的商品的时候,会预期生产者将以高质量商品的价格来提供低质量的商品给他,所以,消费者只愿意支付低价格来购买该商品。另一方面,理性的生产者也预期到消费者将出低价的行为,因此,他也只愿意提供低质量商品给消费者。这样,低质量的商品就充斥着这个市场,而高质量商品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同时。商品价格也一直“粘”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府干预。不过,在长期,理性公众也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因此,新凯恩斯主义只坚持短期的政府干预,而在长期,它就引入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认为应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由此可见,斯蒂格利茨为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理性选择的微观理论依据,实现了理性预期与新古典宏微观综合的有机结合。综上所述,新凯恩斯主义其实是将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微观综合结合在一起。如果从集合论的角度看,可得到第四个推论:
推论4 :{新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古典宏微观综合}
三、经济解释范式创造的新综合——科斯革命与马歇尔综合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全力专注于应用传统价格理论和创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只有3个人,即科斯、阿尔钦和张五常。1959年张五常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得到导师阿尔钦的言传身教,于1968年完成了作为今天契约经济学开山之作的《佃农理论》。他也因此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奖学金,并在法学院跟随科斯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证研究。1969年博士后出站后,张五常加盟华盛顿大学,从而有机会与另外两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巴泽尔和诺思共事多年。1982年张五常回到香港大学从事中国经济制度研究,并在2014年用中文写下了把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与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融为一体的集大成之作《经济解释》,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继新凯恩斯主义综合后的又一次重大的理论综合。《经济解释》自成体系,首先从经济学中最基础的分析工具需求曲线入手,梳理出一套关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论述需求的镜像——供给行为,将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与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结合起来;最后,沿着科斯范式,成功地把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三者组织起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具体地,《经济解释》相应地分为《科学说需求》《收入与成本》《受价与觅价》与《制度的选择》四卷,分别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基本概念与新制度经济学内各派观点进行综合,最终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7]。可见,《科学说需求》《收入与成本》《受价与觅价》仍然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供求框架,只有《制度的选择》是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换言之,如果从集合论的角度看,本文可以得到第五个推论:
推论5: {张五常综合}={马歇尔综合}∩{科斯革命}
事实上,“张五常综合”也应是对“马歇尔综合”的一次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任何理论的突破都是顺应客观现实变化和理论逻辑变化的结果,那么“张五常综合”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但是,纵观经济思想史上前四次理论综合,它们均不像理论革命那样,并不是在某些重大历史现实变革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理论困境下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张五常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成为终身教授之后访问香港,并到香港的街头巷尾观察当地的市场现象。结果他发现,自己虽然曾经在被誉为经济学“少林寺”的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讲授过高级价格理论,对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了如指掌,但发现自己无法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香港小贩的讨价还价行为。一个当时被国际同行称为价格理论第一把手的职业经济学家竟然遇到这样的“理论尴尬”,促使他反思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并下定决心重新修正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走经济解释的实证主义之路。
十几年之后,张五常受科斯之托,加盟香港大学,把新制度经济学传进中国内地并观察和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回香港大学之后,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企业的契约性质》[8]。该文把其博士后合作导师科斯教授的“企业的性质”和博士生导师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以及自己的“佃农契约”综合起来,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要素市场理论与产品市场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划分,并形成“张五常综合”的雏形,这也是张五常第一次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思想史上,《企业的性质》乃交易费用学说的开山之作[9],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是迄今为止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剩余索取权的定义也是原创于此)[10]。同时,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又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对契约选择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学术创作,该文的“综合性”思想最终在《经济解释》中体现出来[11]。
在《经济解释》之前,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并没有把产品与要素严格区别开来,即使在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中,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内容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认为产品或要素的价格都是由边际价值与边际报酬来决定。而“张五常综合”只是简单地以“间接定价”或“直接定价”就把产品与要素清楚地区分开来。在微观经济学说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之所以张五常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贡献,是因为他通过实地调查香港建筑工业的契约案例,并综合了科斯、阿尔钦和自己的产权与契约理论,成功地把交易费用引入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当中,从而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产品—要素市场决定论。这也是张五常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范式修正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保护带的具体表现,即把新古典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保护带改造成为正交易费用的保护带,因而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解释》除了通过引入交易费用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之外,还以“供求原理”为主线,同时对科斯、阿尔钦和弗里德曼三位经济学家的相互冲突的理性人假设进行梳理和重新整合,并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修正。首先,张五常的博士后合作导师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开篇第一段就开始讨论经济学中基本假设的真实性与可操作性问题。科斯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必须是现实且容易处理的。接着,张五常的博士生导师阿尔钦在195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文章,触发了长达近二十年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大辩论[12]。在《经济解释》中,张五常引用阿尔钦在这篇鸿文中的“无知者与汽油站”的例子说明经济学总是假设每个行为主体都是理性人,假设他们能够明智地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换言之,阿尔钦认为,行为主体的本质是否理性并不重要,只要经济学家假设人是理性的就可以,因为竞争约束会使人们的实际行为最终与理性假设推导出来的行为相一致。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在作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前言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弗里德曼以台球游戏为比喻,他认为,经典物理学中关于速度、动量和角度的定理是台球游戏适当的理论模型。台球高手在打球时,似乎都遵循着那些定律,但若问他们是否懂得这些物理原理,大多数会承认不懂。既然这些物理定律对台球的操作做出了十分正确的描绘和预测,那就不能因为球手不懂这些定律而将它们排斥为不合理的理论模型[13]。按此逻辑,不管台球手懂不懂物理定律,只要假设他们懂而最终得到的行为结果又与观察到的行为相符,那就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模型。同理,在经济学中,不管行为主体是否理性,只要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行为没有被事实所推翻,则可以暂时接受这个理论模型。
在《经济解释》中,张五常在理性人假设的问题上,综合了阿尔钦和弗里德曼的观点,强调人的本质是否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可能被事实所推翻、但最终又没有被推翻。换言之,张五常沿袭了马歇尔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关于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进一步,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主体为了获得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人们为了减少竞争过程中的资源耗费而设计的游戏规则,即经济学中的产权制度。在《经济解释》中所有的成本概念都是被理解为被放弃的最高代价,它们都是理性人对稀缺性资源的用途进行最优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张五常综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选择、成本、竞争与产权等基本概念。
另一方面,张五常综合了弗里德曼和科斯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理念,坚持经济学的价值不是经世济国而是解释与预测现实,且用于解释现象的假说必须是可验证、可操作的。换言之,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家的根本任务在于运用需求定律去解释复杂的经济行为。他明确强调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解释真实世界,所以,经济学是一门解释人类行为的实证科学。进一步,他认为要想检验用于解释经济现象的假说是否正确,就要找到可测量的证据。比方说,现在需要验证的假说:有X和Y 两个事件,且若X发生,则Y发生;反之,若Y没有发生则X肯定没发生。在实际测定中:若Y没发生而X发生了,则原假说就被推翻了。因此,在检验假说时,就需要看当Y没发生时,X发生与否。若X也没有发生,则只能暂时接受该假说,但当约束条件改变后,就需要修正假说。世界上没有永远成立的理论,也没有唯一科学的理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是否被事实所推翻。真正科学的理论只能拿来考虑而不能视为圣旨。当然,X与Y 的可观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们是不可以观察到的,那么,就不可能对其进行验证,因此,张五常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哪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
张五常相信,人的行为不是布朗运动而是可以由选择理论来解释的。而影响选择的变量包括不可观测的和可观测的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那么,对于不可观测的变量,张五常把它们作为“假设”来处理,而可观测的约束条件就变成解释行为的关键变量。这样,理性行为主体在约束条件下将目标函数最大化,因此,处理选择决策的条件是在“均衡” (边际上)时给出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的“均衡”是源于物理学的均衡概念,但后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前者是经济学家自己臆造出来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因此,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均衡条件应该理解为能否被事实推翻。若能被事实推翻而又没被推翻,则是均衡;反之,则是非均衡。所以,要解释行为,还需要从均衡出发来发展可反驳的命题。最后,张五常指出,在整个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问题上,我们始终要懂得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通过经济解释推导出来的理论假说是否有可能被事实所推翻。所以,经济解释在方法论上可定义为“寻求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辩驳的解释”。
显然,《经济解释》确立的体系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张五常强调通过观察约束条件的转变从而解释了各种人类行为的变化,所以,解释世界、解释现象、解释行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贯穿于整部《经济解释》。可见,张五常一直坚持经济解释的信念。他认为经济学的最终使命是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过程做出解释并从中把握其一般性规律。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告诉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微观战略管理者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将会有怎样的经济后果。换言之,若要“经世济国”,就必须先改变约束条件从而影响经济行为,但这是决策者的事情,即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解释世界,后者才是经济学家应该做的,这也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功能所赋予的责任。更为关键的是,任何经济政策均建立在“准确”的理论基础之上。这里的“准确”是指能够通过观察约束条件的转变来推测(非预测)出人类经济行为从而解释绩效的变化。这种经济推测的前提是经济解释,而经济解释又以基本概念、约束条件与价格理论为依据。如果我们对最基本的经济概念一知半解,对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的观察漠不关心,对传统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置若罔闻,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从而经济政策建议都是缺乏经济学依据的。例如,华盛顿共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建议东欧转轨国家实施价格自由化、宏观调控稳定化与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经验结果表明这种转轨对策的失败。就最后一项政策来说,私有化导致企业内部人故意低价收购甚至掠夺国有资产。这种转轨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轨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解释》将交易费用引入到传统价格理论当中,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强了经济学的整体解释能力。
总之,《经济解释》其实是把马歇尔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综合在一起。例如,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就分别是马歇尔经济学与科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张五常在讨论完价格理论中的生产费用后,就紧接着引入交易费用。由此可见,《经济解释》不是把新古典价格理论与交易费用简单地加总起来,而是用交易费用的新理念改良传统价格理论,从而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范围。《经济解释》就是将新古典价格理论和交易费用论合二为一,正是基于此,张五常并没有创立什么新的理论,他的《经济解释》只是把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引进马歇尔的传统价格理论中。如果根据库恩的“范式”定义[14],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组成经济学的内核,其保护带则分为三个部分:(1)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2)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3)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按此逻辑,张五常的经济解释范式其实是以马歇尔新古典综合的个人争取利益最大化为内核,再加上科斯革命的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等约束条件作为保护带,从而推导出一系列可验证的理论假说,得到一般化的经济学意蕴,最终实现经济思想史的又一次综合(具体见图2)。

图2 张五常综合、马歇尔综合与科斯革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图
四、总结性述评:张五常综合与其他四次综合的联系与比较
首先,从“张五常范式”之前的四次经济学综合来看:第一次综合的“穆勒范式”不但包括了“斯密革命”的古典经济学思想,而且调和了古典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等相互冲突的经济思想,属于改良主义的经济学体系;第二次综合的“马歇尔范式”主要从方法上把“边际革命”与“穆勒范式”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三次综合的“萨缪尔森范式” 结合了“凯恩斯革命”与“马歇尔范式”,把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综合起来,把单纯的总需求分析与生产要素供给分析结合起来,力图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框架应用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中;第四次综合的“新凯恩斯范式”吸收了“理性预期革命”的理性选择思想,又继承了“萨缪尔森范式”关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观点,为宏观经济学找到了微观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综合,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由《科学说需求》《收入与成本》《受价与觅价》与《制度的选择》四卷构成,分别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基本概念与新制度经济学内各派观点进行综合:第一,《科学说需求》主要以“需求定律”为例,他综合了“科斯革命”与“货币主义革命”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理念,坚持经济学的价值不是经世济国而是解释与预测现实,且用于解释现象的假说必须是可验证、可操作的。第二,《收入与成本》和《受价与觅价》是将新古典价格理论(“马歇尔范式”)和交易费用理论(“科斯革命”)合二为一。张五常认为新古典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统一的基础,他把所有约束条件都转换为价格。正是基于此,张五常的《收入与成本》和《受价与觅价》只是把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引进马歇尔的传统价格理论中。但是,《收入与成本》和《受价与觅价》不是把新古典价格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简单地加总起来,而是用交易费用的新理念改良传统价格理论,从而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范围。第三,《制度的选择》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把交易费用、产权制度与契约选择这三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首次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
相比之下,“张五常综合”与其他四次综合一样,都拥有“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的内核,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各自的保护带上:“穆勒综合”和“马歇尔综合”均综合了“斯密革命”与“边际革命”的“竞争环境约束”保护带,而“张五常综合”则以“产权约束”替代“竞争约束”。此外,“萨缪尔森综合”和“新凯恩斯综合”保护带中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可以理解为“张五常综合”保护带中的“政府与公众之间达成的管制契约”。不过,“张五常综合”中关于信息(交易)费用的保护带则是其他四次综合所不具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张五常综合”继承了“穆勒综合”和“马歇尔综合”的内核,但其保护带的厚度和弹性又远远超过了“萨缪尔森综合”和“新凯恩斯综合”(见表1)。

表1 考虑经济解释范式后的五次经济学综合及其比较
诚然,从“张五常综合”的内容上看,它是在“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加入了“科斯革命”的元素;而“萨缪尔森综合”也是建立在“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不一样的是,它吸收的是“凯恩斯革命”的元素。从历史演进的时间轨迹看,尽管“科斯革命”和“凯恩斯革命”都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萨缪尔森综合”却比“张五常综合”早四十多年。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解释的乏力,加上凯恩斯本人身兼英国财政部官员和英国的“一战”和约谈判代表,并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所以,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政界和新闻舆论。就是在那个时期,凯恩斯的学说以宏观经济学的名义进入到欧美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当中,成为了当今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萨缪尔森因而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综合起来。相反,“科斯革命”以《企业的性质》为标志,但当时科斯只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讲师,直至他在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后[15],主流经济学界才开始关注他的学说,等到他81岁高龄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再加上,科斯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一直反对主流“黑板经济学”的模型化倾向,所以,无论在政策和学术影响上都比不上“凯恩斯革命”。此外,尽管身为学生的张五常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高举“科斯革命”的旗帜,但是,张五常在1982年回到香港大学任经济学院院长之后就很少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规范的学术论著,反而把大量时间与精力放在“街头巷尾”的实证调查之中,只是在2000年退休之后才开始集中精力撰写这部《经济解释》,导致“张五常综合”到了21世纪初才开始形成。
最后,既然“张五常综合”是在“马歇尔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萨缪尔森综合”也是从“马歇尔综合”分离出来的,它们的本质区别表现为:前者是在马歇尔的价格理论框架上加上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后者是把微观供求模型拓展成为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换言之,前者是沿着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而展开分析“超微观”的缔约行为,并完善与深化传统微观经济学,后者则沿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并寻求其微观基础,力图实现宏微观经济学的统一。换言之,从时间上看,“张五常综合”出现在“新凯恩斯综合”之后,而前者也并不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就不能按照本文引言部分提出的经济思想综合公式把“张五常综合”定义为继“新凯恩斯综合”之后的第五次综合。不过它的确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综合,这是因为,如果不考虑时间出现的先后,根据“张五常综合”的实际内容来看,它应该是与“萨缪尔森综合”一起,成为继“马歇尔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综合。
参考文献:
[1] 何一鸣,罗必良,高少慧. 科斯范式与经济思想史革命[J].理论学刊,2014,(8):42—49.
[2] 柳永明. 略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四次综合[J].经济学动态,1997,(4):63—65.
[3] Mill, J.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M].London: John W. Parker,1848.
[4]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Macmillan and Co, 1920.
[5] Samuelson, P.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McGraw-Hill,1948.
[6] Stiglitz,J. Economics[M].New York: W.W. Norton, 1993.
[7] 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Cheung,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1):1—21.
[9] Coase, R.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4(1):386—405.
[10] Alchian, A., Demsetz, H.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5):777—795.
[11] Cheung,S.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M]. Chie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12] Alchian, A.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1): 211—221.
[13] Friedman,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4] Kuhn,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5]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1):1—44.
(责任编辑:胡浩志)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16)02-0003-08
作者简介:高少慧(1985— ),女,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农经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项目“农业制度经济学”(NJX1520);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特色创新类项目“农业管制经济学的学科型构、课程创新与实验方法” (20150212);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质量工程项目“《制度经济学》双语课程”(2015jgzlgc202)
收稿日期:2015-10-25
罗必良(1962— ),男,湖北监利人,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何一鸣(1981— ),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