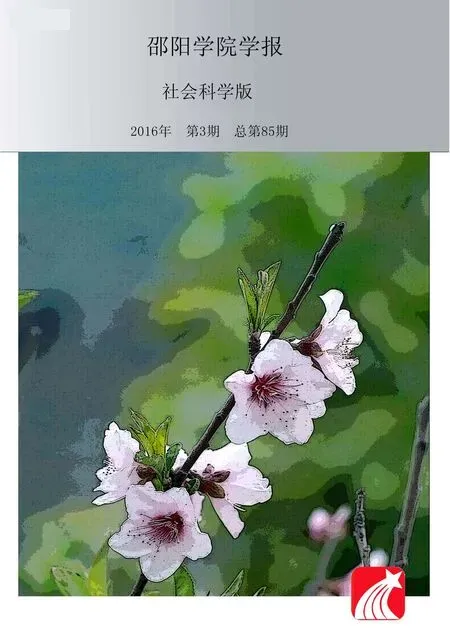独特的“长诗”
——也谈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384)
独特的“长诗”
——也谈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
曾思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300384)
摘要:《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晚年诗歌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首独特的长诗:篇幅与体裁独特,写作与发表独特,思想与内容独特,结构与手法独特。
关键词:《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 长诗; 独特
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则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为纪念这位成就突出的20世纪俄罗斯诗坛最杰出的女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她的百年华诞1989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
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歌大多是爱情诗,她以本人的切身经历为题材,咏叹身边发生的一切情况,展示女性心灵的隐秘,生动真挚,细腻感人,因而被称为“室内抒情诗”,她本人也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或“20世纪的萨福”。[1](P312-341)20世纪20年代以后,诗人经历了苏联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解冻”等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过程,亲历了人民的苦难和时代的悲剧,因此,诗歌内容从早期的吟唱爱情更多地转向反映社会问题、人间苦难,而最能反映人间苦难的诗歌,则是其著名的《安魂曲》。这是一首独特的“长诗”,其独特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篇幅与体裁独特
《安魂曲》虽然被称为长诗,但篇幅并不长:它由4行题诗、代序、献辞、序曲和12首短诗——写于不同年代的10首短诗(第10首又包括两首4行短诗)以及两首短诗组成的尾声——构成。全诗的诗行全部加起来,还不到 200 诗行,代序则是只有不足100字的散文,因此,历来被称为“小长诗”,堪称独特。更为独特的是,学界对其体裁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抒情长诗,有人则称之为叙事长诗,另有人把它当成组诗。
如上所述,《安魂曲》诗歌部分主要由题诗、献辞、序曲和12(或13)首短诗构成,逐一考察,这些诗每首都可以说是抒情诗,此处略举一例便可见一斑,如长诗之五:
整整十七个月,我都在高喊,
千呼万唤喊你回家。
我曾跪倒在刽子手脚前,
你是我的儿子,我的惧怕。
一切都已永远颠倒混乱,
究竟谁是野兽,谁是人,
而今,我已无法分辨,
判处死刑还要等待多少时辰。
只留下落满尘土的鲜花,
香炉叮当的声响,还有那
不知去向的足迹。
一颗巨大的星星
直逼逼地瞪着我的眼睛,
用压顶的毁灭把我威逼。*本文所引《安魂曲》中的诗句,均由曾思艺译自(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纽约,1969年版,并参考了莫斯科,2002年版。
这首诗就是面对唯一而又心爱的独子在人妖颠倒的时代无辜被捕,而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几乎是直抒胸臆般地表达了自己的恐惧之情。再加上长诗所运用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耐曼指出的,“另外一个人”代替“我”或者和“我”一起的人称转换手法,在诗人早期诗歌中已经出现过,《安魂曲》诞生前诗人就掌握了在抒情诗绝对完整和统一框架内创造这种对话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只是《安魂曲》中这种艺术手法不仅以诗人先前所掌握的炉火纯青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而且又以另一种完全崭新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而且诗人为长诗取名《安魂曲》,也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首先是大众文化的意义,其次才是宗教的意义,按作者的意图,读者在接受它时大概会联想到音乐会演出中的安魂乐曲(莫扎特、威尔第),而不是联想到教堂中的安魂弥撒。[2](P294,297)此外,后文所说的大量的宗教用典、象征手法,则使长诗更富抒情色彩。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叙事长诗,如辛守魁称之为“叙事长诗《安魂曲》”[3](P416),阿曼达·海特虽没有直接称之为叙事长诗,但显然认为它是这类诗:“《安魂曲》不单单是串在一根轴上的一系列诗歌,而且是某种有机的整体,它以纪实般的准确性刻画出苦难历程中的所有阶段,诗人用这些阶段标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况。”[4](P134)
另有学者干脆认为它就是“组诗”:“这种精神的压抑与痛苦,糅合成俄语最伟大的组诗《安魂曲》。”[5](P207)汪剑钊也认为《安魂曲》是“组诗”[6](P139)。
其实,《安魂曲》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既可看作抒情长诗,也可称为叙事长诗,更可视为组诗——它本身确实是由一首首短诗构成。正因为如此,俄国一些学者在论述中有比较模糊的表达,如帕甫洛夫斯基,一方面声称:“三十年代的阿赫玛托娃不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公民,她的主要成就就是她的叙事长诗《安魂曲》的创作,它直接地反映了‘大清洗’的年代——描写了深受迫害的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抒情长诗:“她写出了类似于赞美诗般的《安魂曲》。”[7](P161-162,158)
二、写作与发表独特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为了清除政敌、巩固个人的独裁统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大范围的大清洗——恐怖的“肃反运动”。他擅自破坏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量红军军官、政治委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处决、流放或者驱逐出境,在叶若夫任内务部委员时,肃反尤为凶残。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恐慌中,正常的社会生活几乎崩溃,逮捕、流放、处死的人数极其惊人。一种说法是,从 1930年至 1950 年的 20 年间,据统计共有 78 万人被处以死刑,377 万人遭到政治迫害。另一种说法是,光是30年代的大清洗,被逮捕、流放、处决的人数高达50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都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仅1937—1938年间被处死的,据赫鲁晓夫承认,就有681692人,对这次大清洗死亡人数的最保守估计也有140万之多,而这几年被捕的作家有6000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以上材料综合参考了以下著作的数据材料:陈启能:《苏联肃反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辛守魁:《阿赫玛托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俄)帕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守魁、辛冰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935年,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仅因在大学就读时私下里读过讽刺斯大林的诗,就被逮捕,关进监牢。虽经多方努力,最后被释放,但这种逮捕先后持续了三次:1935年、1938年、1949年,被流放共计14年。1938年,她的第三任丈夫普宁又无端地被认为是“反苏分子”而被捕。因此,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指出:“当时,她丈夫和儿子都被逮捕并被送往劳改营流放……棺材高悬在苏联各城市上空,这里几百万无辜的人遭到严刑拷打和枪杀。”[8](P3)
就是在这么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反运动背景下,阿赫玛托娃面对自己和人民的苦难,不吐不快,写诗悼念无辜的受害者。但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下,这样的诗歌不仅无法出版,即使传抄手稿也会惹来杀身之祸。特定时代于是产生了独特的写作方式:阿赫玛托娃构思成熟,就把诗写在小纸片上,然后把其中的单独几行诗给信得过的朋友看,让他们帮助记忆,当她确定读诗的人记住了这些诗句时,就把纸片烧掉。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对此有颇为具体生动的记载:“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话,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她还具体谈到:“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抄写了《疯狂已如翅膀一般》(即《安魂曲》第九首《疯狂早已振翅猛抖……》——引者),待我读完,即就着烟灰缸烧掉了。”[9](P90)就这样,全部诗作仅仅保存在诗人和七个密友(一说十个)的记忆中,绝不留一点儿文字记录。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安魂曲》的发表也比较独特。全诗主体部分于1935—1940年完成,诗人在“解冻”后相对不那么严酷的年代里,于1962年把几位密友先后约来,让他们共同回忆《安魂曲》的诗句,把密友们和自己记忆中的诗歌加以核对、认定,亲自把它们写到了纸上,形成一部长诗《安魂曲》。但代序却写于1957年,而第一首短诗则写于1961年。据诗人好友列沃尔德·班丘科夫说,序曲是在1962年列入《安魂曲》的;据另一女友柳鲍夫·达维多芙娜·波尔申卓娃说,尾声是阿赫玛托娃在1964年刚刚写出并给她吟诵过的。也就是说,《安魂曲》在1962年已基本定型:“基洛夫被杀后,在斯大林策划的政治暗杀最激烈的时候,阿赫玛托娃创作了30首诗歌来悼念无辜的受害者,同时揭露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一些没有政治倾向性的诗歌(如《一句话像石头落了地》《疯狂张开了翅膀》)甚至发表在刊物上。从这30首诗歌中,她挑选出创作于1935—1940年间的14首诗歌*此处作者计数有误,并非14首短诗,而是12(或13)首短诗。,1957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散文体的《代序》,1961年增加了《我们没有白在一起过穷日子》一诗中的一节做为题词。……《安魂曲》的打印稿在1962年被介绍给了更多的朋友和熟人,其中包括新朋友和一些年青的朋友,同时被推荐给《新世界》杂志。*之所以投给《新世界》杂志社,是因为该杂志主编是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思想比较开放,且是阿赫玛托娃诗才的崇拜者。然而,1962年12月16日,书刊检查官戈洛万诺夫看过《安魂曲》的校样后在自己的日记里指出:“它不适合出版。”因而未能面世。在那儿由于多种原因它没有出版,但是1963年在‘预先没有通知作者也没有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它却被慕尼黑的‘外国作家协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2](P292-293)而它在俄国与广大读者见面,则“直到诗人死后二十二年,它才首次问世,——这已是1988年了,而且一下子出版了两次:在《十月》杂志(1988年第三期)和《涅瓦》杂志(1988年第六期),1989年它才收入在列宁格勒出版的一卷本的阿赫玛托娃集中”[7](P161-162,163)。
三、思想与内容独特
如前所述,《安魂曲》包括题诗、代序、献辞、序曲和12(或13)首短诗,它们反映了与当时歌功颂德的作品截然不同的独特内容——表现大清洗时代人们的苦难。
《安魂曲》的题记是4行短诗:“不,既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曾受他人的翅膀遮庇,/在人民遭受不幸的国家,/我曾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表明了自己在极其艰难的年代,没有背弃自己的祖国,更没有到异国他乡寻求庇护,她选择了留下,与不幸的人民站在一起,共同经受和承担苦难。
《代序》则用散文交代了创作这首诗的原因。1938年3月10日,诗人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无辜被捕,被关押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诗人极力营救未果,只能一次次地排队探监送东西,就这样在监狱外等候探望儿子,排过17 个月的队,站立了整整300 个小时。有一天排在她身后的一个嘴唇发青的妇女认出了她,便在她耳边悄声问道:“这情景您能描写吗?”“能。”诗人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诗人的天职,肯定、有力地答道。这简单的承诺,给了黑暗中探索正义、追求真理的人民最后的希望,她看到这位妇女的脸上掠过了曾经有过的一丝笑意。
《献辞》描写了探监的母亲们沉痛的心情,并以其作为《安魂曲》的抒情主人公,从而以所有妇女巨大的悲剧命运为全诗开头并且定下全诗的基调。尽管群山为此低下头颅,大河为此停止流动,但监狱的大门紧关,只听到钥匙可恶的哗哗响声和士兵重压压的脚步声。“我们”像奔赴晨祷一样赶早去监狱门口守候,希望之歌在远方吟唱。回忆当时听到判决,“我”泪飞如雨,心似刀绞,步履踉跄。由此联想到两年来结识的、失去自由的姐妹们,不知她们如今在哪里?“我”想给她们送上临别时的致意。诗人对她们的致意,源于她们共同承受的这份苦难。
《序曲》描写了被判罪者的悲惨情形。在鲜血淋淋的皮靴践踏下和囚车黑污污的车轮的压碾下“无辜的俄罗斯在抽搐挣扎”的大背景中,那些被判罪的人们走在一起,痛苦把他们折磨得痴呆笨拙,火车还要把他们带到远方。
正文的前几首写道,就在拂晓的时候,“我”的儿子也被抓走。“我要以射击兵的妻子们为楷模,到克里姆林宫塔楼下长号悲啼。”这哭声,曾经响彻1695年彼得一世处决射击兵的红场;这哭声,也暗含着诗人在1935年奔赴克里姆林宫找斯大林请求赦免儿子。“我”身患疾病,孤苦伶仃,丈夫已死,儿子在坐牢,不再是富有个性的女人,也不再是朋友们的宠儿,更不是皇村学校那个快乐的叛逆者,而是第300号前来给犯人送点衣物的探监者。“我”知道,大墙背后有多少无辜生灵涂炭。“我”呼唤着儿子,盼望他回家,甚至不惜给刽子手下跪。但是黑白已经颠倒,人兽难以分清,“我”只有忐忑不安地等待判处死刑的消息。死亡之星似乎时时都在发出威吓,“我”不能不日日夜夜牵挂儿子的生死安危。
1939年8月17日是母子俩离别的日子,列夫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诺尔斯克劳改营,阿赫玛托娃心如刀割,写下了《判决》。判决终于来临,如一块巨石落在“我苟延残喘的胸口”。但“我”早已准备就绪,不论怎样“我”都能承受。从今以后,“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连根拔除记忆,要把心儿变成石头,要学会独自一人重新生活。
《致死神》表明:“我”在等待死亡,无论是毒气弹、惯偷、伤寒病菌还是瞎编的故事,不管死神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不能吓倒“我”。“我”心中只留下儿子那双蓝光闪闪的眼睛,它们遮住了种种恐怖的场面。“我”向死神乞求,哪怕让我仅仅带走儿子那恐惧而沉默的眼神,或是那来自远方的温馨慰语,但它什么也不允许我随身带走。这一部分中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充满疯狂、苦难和焦虑不安;而另一种声音却神秘、静默而又安详,那是让母亲“大彻大悟”的神启。两种不同的声音、力量,相互对抗、冲撞,形成一股强劲的张力,一起将诗歌推向高潮——《钉上十字架》。
《钉上十字架》附有《题辞》:“别为我哭泣,母亲,在我入殓的时分。”它摘引自教堂圣歌,奠定了诗节庄严肃穆的基调。这是用儿子的口吻写成的两个篇章。“我”,作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听天使在颂扬伟大的时刻,并看见烈火熔化了天穹,“我”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我抛舍!”“我”劝慰母亲:不要为我泪下如雨。然而,“母亲默默站立之处,没有谁敢投去自己的目光”。
《尾声》的第一部分用音乐的旋律再现了“我”观察到的监狱高墙下排队等候的人们形象:憔悴的面容、惊恐的神色、骤然从浅灰和乌黑变成银白的鬈发和凋萎的微笑。“我”并非为自己一个人祈祷,“而是为和我一起站立的所有人”。第二部分则进一步升华。“我”多么希望一一报上她们每个人的姓名,“但名单已被夺去,早已无从查清”。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她们,我的嘴巴“曾为亿万人民的苦难而大声疾呼”,即便有一天被封堵,她们也会怀念“我”,倘若有那么一天有人想为“我”建立纪念碑,请不要把它建在“我”出生的海滨,也不要建在皇村,而是建在“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
《安魂曲》在思想上的独特之处主要有二。
一是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年代,诗人竟然大胆地把斯大林暗喻为专制独裁、残酷镇压的彼得大帝和尼古拉一世。长诗在《序曲》中写道:“我要以射击兵的妻子们为楷模,到克里姆林宫塔楼下长号悲啼。”这里,借用历史——1695年彼得大帝镇压发动政变的射击军,四千人中被绞死于莫斯科红场和流放的近一半,他们的妻子、父母在等待判决时,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痛哭,用专制残酷的彼得大帝暗喻斯大林。随后,诗人在《献辞》中借用普希金《致西伯利亚囚徒》一诗的语典:“我自由的歌声,会传进你们苦役犯的洞窟。”并在《致死神》中用“北极星”象征十二月党人,进而影射斯大林是专制暴君尼古拉一世。
二是独特地用个人的苦难来代表人民乃至人类的苦难。如上所述,在《安魂曲》中,诗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她作为社会一分子所经历的社会事件,思考由这一事件的悲剧性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现整个环境内的人们对公正和正义的祈求。诗人将这一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事件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并积极关注遭遇不幸的人们和同他们相关的一切,思考在这样残酷的现实社会中生命的卑微和脆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而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包含丰厚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诗歌中反映的事实和表达的情感不仅属于阿赫玛托娃一人,而且属于遭遇不幸的所有受难者和整个俄罗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此,汪剑钊指出,《安魂曲》的主题是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在谴责刽子手的卑鄙和残暴的同时,歌颂了受难者的崇高与尊严。[6](P145-146)林咏进而指出,诗人超越了自我的局限,将自传性的诗章赋予了千千万万的母亲们,赋予了整个受难中的人民大众,使得诗歌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心声,具有了普遍性。《安魂曲》的《献辞》,以所有妇女心头巨大的痛苦起笔,记述了她们探监的沉痛,并将她们定格为《安魂曲》礼赞的直接对象,诗人“要把临别的那一份敬意给她们捎去”。诗人对她们的敬意,源于她们对这分苦难的担当,和不假辞色的承受。诗人与她们也因这共同遭遇的命运而融为了一体。《尾声》中诗人更是站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高度,代表亿万人民,为大清洗中的被迫害者,为人类劫难中所有无辜者、牺牲者建造纪念碑,以宗教奠祭的仪式悼念和追忆亡魂。[10](P93)
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当诗人把《安魂曲》读给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听时,后者叹息道:“遗憾的是,您的诗中只写了一个人的命运。”女诗人立即反驳道:“难道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就不能表现出千百万人的命运吗?”[11](P67)也正因为如此,在逝世不久前写的小传《我的简历》中,阿赫玛托娃自豪地宣称:“诗歌连结着时代,连结着我的人民的新生活。我写诗的时候,我生命的节奏与我国英勇的历史的节奏是一致的。我很幸福,因为曾经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亲眼目睹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12](P292-293)
四、结构与手法独特
如前所述,《安魂曲》主要是在1935—1940年间创作的,它的献辞、序诗、代序等等,更是创作于不同的时期,这就决定了其结构的独特性:第一,这是一首由不同时间创作的诗歌构成的组诗;第二,这是由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乃至散文构成的独特长诗(其代序是散文体的)。可以说,这首独特的长诗具有异常明显的片断性。不过,《安魂曲》虽然各首诗分别写于不同的时间年代,由不同的片段组成,具有明显的片断性,但整组诗是围绕大清洗下人们的苦难这同一事件展开的,在时间上有内在的先后顺序,同时全诗的整个感情基调是统一的,此外,开头的献辞部分和结尾部分在内容上的一致,使得整首诗首尾呼应,结构严密。
长诗的手法也颇为独特。
首先,它借用宗教内容作为象征,使诗歌内涵更深广,含义更丰富。安魂曲是一种特殊的基督教弥撒曲,是其在悼念死者、超度亡灵的祭奠仪式中,演唱的圣乐套曲。安魂作品以抚慰和祈祷为主。诗人选用安魂曲作为诗歌的标题,使得这首组诗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更重要的是,诗人在长诗中运用宗教形象、借用宗教的普世观反衬极权专制的残酷,以受难者与耶稣对照,暗示这不是一个人的苦难,而是全民族的苦难乃至整个人类的苦难,从而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不幸,把母亲的形象从个体的母亲升华到全俄罗斯、全人类的母亲,颂扬了母性的伟大与崇高,同时反衬整个民族的不幸是人类无可估量的悲剧,从而使这首安魂曲不仅是倾诉诗人个人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是对所有在大清洗中无辜牺牲者们的悼念,深刻地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人道主义情怀。尤其是长诗的第十首《钉上十字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宗教意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天使、天穹、耶稣、耶和华、玛利亚、玛格达琳娜和门徒等等,用《圣经》中耶稣、圣母玛丽亚来隐喻灾难中的儿子与母亲,充满了神圣悲壮的气氛。诗歌以耶稣隐喻“儿子”,以圣母玛丽亚献出耶稣,隐喻母亲为时代的罪孽献出儿子的壮举。抒情主人公形象由一个母亲上升到了成千上万的母亲们,诗歌代表了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具有了普遍性和人类性。因此,帕甫洛夫斯基指出:“在阿赫玛托娃笔下,扩大所描写事件意义的艺术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圣经》的情节、类比和联想。”“《圣经》中的形象和基调使诗人有可能极大地拓宽作品的时间和空间,以便表现在国内占上风的恶的力量,它同全人类的最大悲剧完全相关。”[7](P157,144)
对此,金洁有颇为具体而又全面的论述。金洁指出,诗人选择了“安魂曲”来命名,使得这首组诗包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东正教中的安魂曲是救赎的歌谣,给死去的人唱安魂曲,使他们能够在地下安息长眠。诗人在诗中直接面对死亡,用声音抚慰尘世中的受难者。面对国内大清洗中很多的受害者,诗人选择了“安魂曲”为他们安魂祈祷。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虔诚的正教徒,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妇女,但她代表的则是俄罗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她像耶稣一样肩负着救赎的沉重使命。背负十字架的路途是何等的艰辛,耶稣每走一步都是为了救赎人类、洗去人类犯下的沉重的罪孽。在第十章节《钉在十字架上》中,诗歌中的女主人公肩负着救赎的使命,她忍受着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她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所有妇女:“玛格达琳娜颤栗着悲恸不已,仁爱的信徒如同一具化石,母亲默默地站立的地方,谁也不敢向那里看上一眼。”她的坚守表达了坚定的信念:女主人公依旧每天站在监狱门前,她虔诚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甚至把仁慈的圣母玛利亚也感动得悲痛万分。而每天都有很多妇女默默地在监狱门前排队,这分明就是一个无声的控诉,以至于谁也不忍心去看如此悲壮的场景。
金洁进而指出,《安魂曲》的抒情女主人公是一个失去亲人的母亲,她很痛苦,就像玛利亚因耶稣,俄罗斯因她成千上万个牺牲了的孩子。在这部巨作中,阿赫玛托娃的笔下所有人物,已不再是具体的人物,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所有的母亲,俄罗斯的全体人民。阿赫玛托娃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已经由一个心怀祖国的爱国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胸怀祖国胸怀天下的神圣的母亲,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是心怀俄罗斯未来的母亲,是心怀俄罗斯全体人民命运的伟大母亲。因此,《安魂曲》“是俄罗斯的,是时代的,是所有人的安魂曲”,这首长诗的主题则是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在谴责刽子手的卑鄙和残暴的同时,歌颂了受难者的崇高和尊严。诗人以《圣经》的内容为写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让虔诚的女信徒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从而使整个诗歌像一部控诉没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的历史小说。有的批评家指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是具有最崇高的痛苦力量的诗篇,同时也是人类的文献”。阿赫玛托娃从母性心理角度出发,把东正教中的“圣母”形象与蕴含着母性因素的祖国大地联系在一起,使民族命运的悲剧意义更加浓厚,其悲壮色彩显得更加庄严,突出地表达了一个虔诚信仰东正教的女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尤其是人道主义情怀。[13](P260)
其次,《安魂曲》借用了俄罗斯民间文学的一些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民间古代哀悼题材文学形式的运用、口语体的运用,大量拟人、比喻、对比、设问等民间常用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一些富含一定象征意义的颜色、数字的运用等。对此,帕甫洛夫斯基有颇为精到的论述。他指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是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这不仅是指这一意义的:它反映和表达了伟大的人民悲剧。而且也在于其诗的形式:接近于民间的送别曲。由平平常常的,如阿赫玛托娃写到的、“听到的”话语所“编织起来的”叙事长诗以极大的诗的和公民的力量表现出了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苦难心灵。[7](P158)
再次,人称不断转换。俄国学者耐曼指出,长诗中抒情主人公的人称时常转换,阿赫玛托娃时常变换观察女主人公的立场,在一首诗那浓缩的空间里时而称女主人公为“我”,时而称之为“她”(Ⅱ),在接下来的三首中(Ⅲ、Ⅳ、Ⅴ)从“我”转为“你”,再重新转为“我”。准确地说——跟在诗人后面的——既是“我”又是“另外一个人”(Ⅲ)。“另外一个人”也是站到探监队伍中成为队伍一分子,与“我”站在同等地位上的一个人。[2](P294)在一首不到200行的小小长诗中,人称有如此多次的转换,这种艺术手法不仅新颖而独特,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而且相当出色地借此使抒情主人公成为普通人和大多数备受灾难的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表达了受苦受难民众的普遍心声。
综上所述,《安魂曲》的确是一部相当独特的长诗。
参考文献:
[1]曾思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2](俄)阿纳托利·耐曼.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M].夏忠宪,唐逸红,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3]辛守魁.阿赫玛托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英)阿曼达·海特.阿赫玛托娃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5](英)伊莱因·范斯坦.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M].马海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汪剑钊.阿赫玛托娃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7](俄)帕甫洛夫斯基.安·阿赫玛托娃传[M].守魁,辛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辛守魁,阮可之.伟大诗人的惊人勇气——初读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6.
[9](俄)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诗的隐居·阿赫玛托娃札记[M].张冰,吴晓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0]林咏.俄罗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幸福的阿赫玛托娃[J].宜宾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91-93.
[11](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诗的蒙难·阿赫玛托娃札记(1952—1962)[M].林晓梅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俄)阿赫玛托娃.我的简历[C]//阿赫玛托娃诗文集.马海甸,徐振亚,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金洁.阿赫玛托娃组诗《安魂曲》中的东正教思想[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259-260.
Unique Long Poem——on Anna Akhmatova’s Requiem
ZENG Si-y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Requiem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 in her later years. The uniqueness of this long poem lies in: length and genre;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thought and content; structure and technique.
Key words:Requiem; Anna Akhmatova; long poem; unique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曾思艺(1962—),男,湖南邵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3—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