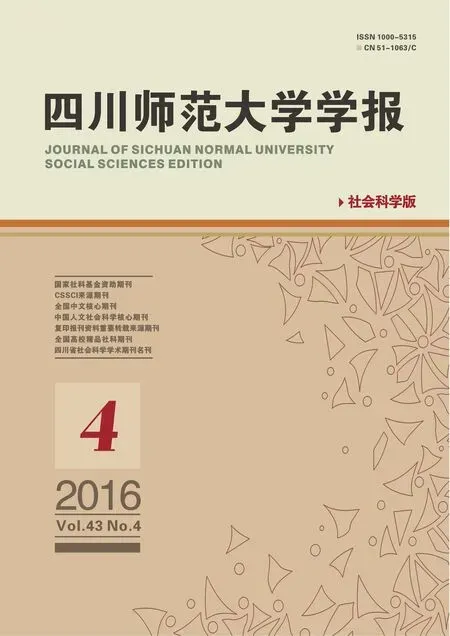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王红雨,闫广芬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4)
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王红雨,闫广芬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4)
摘要: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塑造了学校时间的初设轮廓,星期与钟点的出现完成了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请假制度的日益严密造就了学校时间的边界控制,严密的新型学校时间体系就此确立,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发挥规训作用。与此同时,乡村中的私塾学校依旧滞留于旧式时间轨道之中,其对新型学校时间的公然反对与消极抵制表征了“传统”与“现代”间的有力博弈,并折射出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无奈与艰辛。
关键词:学校;时间管理;早期教育现代化
学校时间是学校内一切教育实践展开和延续的条件与背景,教育实践本身也在学校时间的顺延与叠加中存在与发展。作为“背景”存在的学校时间虽因其隐而不彰的特性而被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但也客观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校时间不但持续地否定、发展、重塑着自己,更制约、规训着各种教育实践活动的落实与走向,由此成为我们考察近代学生生活节奏与教育环境的有效手段。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当我们开始研究一所学校时,先勾划这所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所遵循的时间模式,无疑会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局部解剖工具。”[1]225
一学校时间的轮廓初设: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
教会学校一直是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急先锋。作为早期基督教学校的代表,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在山东开办的登州文会馆,从设学之初就开始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施行以“年”为单位的阶段性学习制度,以此将学年制度带入近代中国。该馆规定:从第一学年的“天道溯原”到第二学年的“天路历程”,再到第三学年的“救世之妙与省身指掌”与第四年的“心灵学与是非学”[2]23,学生在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课程安排中获得宗教知识,并于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常规测验,年末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
山东登州文会馆只是一所具备初级办学水平的民间教会学校,尽管其创办初衷乃是“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3]32,但它的确在客观上将一种新型的时间规划引入到中国的教育场域中。新旧时间的比较之中,晚清教育改革者开始注意到传统学校时间安排的不足:过长的学习时间不但降低了学习效率,更间接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洋务学堂的建立过程中,学校设计者们纷纷自觉引入学年与学期制度,希望以此保证学校时间的稳固化、规程化与秩序化。1902年,《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次以官方文本的形式公布了学期设置的相关要求:“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节散学,为第一学期;立秋后六日开学,至十二月十五日散学,为第二学期。”[4]408-409一年后,《奏定进士馆章程》中关于学年与学期的规定与之相差无几:“每年分为两学期,自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自暑假期满后至年终为第二学期。”[5]628在这里,中国学校教育首次获得了由官方赋予的“学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学年”的划分。此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将学期制度落实下来。直隶省师范第一小学,“每年于正月开印,即日入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入学,封印日放学,给年假”[6]83。山东大学堂,“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放学,给年假”[7]50。当然,随机应变的灵活应对也是存在的。如(上海)民国法律学校预科便将一学年划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自正月至三月,第二学期自四月至七月,第三学期自八月至十二月。”[8]这种选择也使得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在第二和第三学期中进行课程的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学习效率。
二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星期与钟点的出现
精细的时间分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以“星期”与“钟点”为代表的时间安排,开始了学校时间第二次分割的历程。
(一)“礼拜”与“星期”
“礼拜”源于西方宗教仪式,新式学堂对于“礼拜”的引入源于洋教习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需求。《同文馆章程》称:“每年夏月洋教习息伏期内,及每月外国礼拜洋教习不到馆之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在馆内学习汉文。”[9]34这意味着以七天为一轮回的休息制度开始在中国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学校中正式出现。
虽然“礼拜”开始在校园内出现,但此时诸多学校对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依然抵制,它们纷纷选择传统的时间表达方式来表征与“礼拜”相一致的概念。浏阳算学馆使用“休沐日”来代替“礼拜”一词,称:“除厨役、杂役外,通馆均前后七日中,隔六日一休沐。遇房、虚、昴、星四苏值日,即为休沐之期,此固文武张弛之道。”[10]368到戊戌维新运动高涨之时,一些学堂内仍使用二十八星宿值日法来抵制“礼拜”一词,以房、虚、昴、星四字代替每月中的四个周末。如江宁江南储才学堂便规定:“每逢房虚昴星日,照西例休息。”[11]“新”“旧”称谓的共同出现,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新”“旧”势力博弈的胶着状态;而站在这种状态背后的,正是近代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始终相伴而生的“旧”的艰难转型与“新”的深刻变迁。
随着西风的猛力劲吹,“新”的势力不断强大,以七天为一个休息单位的时间观念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开始在学校中落地生根,“星期”开始代替“礼拜”出现。至20世纪初,《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学时的安排成为政府承认星期制度的代表。在此章程的文字表达中,学生的课程安排均是以每星期所占钟点为单位来进行划分的,其表述中已经含有“初等小学堂科目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刻表”的字样[12]417;《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同样规定:“学生休业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四点钟。”[13]797-800
当“星期”概念在中国本土新式学堂中脱离宗教性质而走向学校科目编排工具时,教会学校依然秉持着“礼拜”的最初特色。苏雪林回忆其在基督教所创办的安庆培媛女学的求学经历时说:“学生入校后,连星期日都不许回家,只许家属来校探视。入学者以一学期为限。半年后,继续来校听便,但学生可以回家了。我初亦不知其故,原来一到星期日——男女两校的学生都要到那个教堂行礼,仪式繁重,费时半天,下午又要读经做祈祷,不管学生信教与否都非参加不可。以后便是休息,不准做任何工作,说这天是上帝定下的安息日,学生只有拥被睡大头觉。”[14]23同样,曾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后任学校校长的吴贻芳,虽然平时功课繁忙,但每周在金陵女大参与礼拜、学习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最后甚至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15]27。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中式学堂采用的“星期”概念仅仅是一种作息的规划方式,而西式学堂所采用的“礼拜”概念则更偏重宗教礼仪的色彩,这是中西学校遵从中西文化而自主选择的结果。
(二)“钟点”的出现
与“星期”在教育领域的出现相似,最初的“钟点”同样延续了带有传统色彩的称谓方式。1864年,即洋务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的第二年,《广州同文馆章程》中将学馆课程规定为:“每日巳、午、未三时,由西教习训课。早晚各时由汉文教习训课。”[16]10735年后,传统表达方式依然存在。1899年,《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仍以天干地支的计时方式表征着时间的分割,称:“学堂大门启闭,夏季卯初开锁,戌正落锁;冬季日出开锁,戌初落锁。”[17]450
相比于本土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的时间表达更为细密、精致。1879年,在由美国天主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书院中,几乎所有的学生生活都没有逃离被时间切割的命运。徐善祥回忆称:“全校学生清晨6点半闻钟即起,至楼下盥洗后,7时入操场,做半小时集体哑铃体操,8时至聚集所点名早祷,8时半早餐,9时上课,午12时午餐,下午1时又上课,4时下课。凡遇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半至5时半,群至操场参加军式操演。下午6时晚餐,7时至9时温习自修,9时半均须熄灯就寝。”[18]11
很快,本土新式学校的时间规划也赶上了教会学校的脚步,开始严格规定学生作息。1901年,袁世凯便在《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展示了其务实派注重效率的个性,规定:“学生在学堂,每日寝与食息,均有一定时刻,届时各鸣钟为号。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学生晨兴,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半钟、午后十二点半钟及六点半钟,各鸣钟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钟又鸣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冬季早六点钟鸣钟一次,学生晨兴,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钟、正午十二点钟、午后六点钟各鸣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半钟又鸣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晚十点钟一律止灯就寝。”[7]50不仅如此,精细化的时间分割也开始入侵到学校的休闲场所中。梁实秋在回忆清华生活时曾说道:“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1点或5点或9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差而且风雨无阻。”[19]30
在“钟点”中,学生的一切行为都被钟点所囊括,被填充到不同时间段内的活动在“开始”和“结束”间被赋予明显的时间意义,并在时间的调配中完成集体的组织与协调。当学生的日常生活被无所不在的学校时间切分得日益细密时,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与控制也就变得更为精准与细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20]174
三边界控制:请假制度的不断完善
“惜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主题,而“勤学”则是实现“惜时”的主要途径。近代以来,“惜时”的精神内涵更开始由个人的意愿走向集体的追求,提高生产效率与增加社会责任成为“惜时”观念的应有之意。“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过程太过漫长,高速度、高强度的效率追求则更为实际。“惜时”不再是长久的坚持,而是尽快的占有。“国难当中各校学生务宜努力读书,以造成国家有用之人才,而靳达教育救国之目的”[21],当这种急切的社会心态映射到教育领域中时,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减少学生请假次数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一)请假理由的控制
在急需新式人才的社会语境中,教育内容获得了革命式的翻新。为快速吸收这些大量涌进新式学堂中的西方新学,学生请假外出、荒废学业的情形遭到严厉的批判与完全的杜绝。新式学堂首先对学生的请假理由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非有重大事故不得请假。
和所谓重大事故,即与侍祖有关的服丧与健康有关的重病两项。“亲丧与疾病二者而已,我国旧俗,亲丧有守七之说,然学业所繁,中辍可虞,即稍变通,于事无妨,正不必拘虚文而蒙实害也;至于疾病之来,恒由于起居饮食之不慎,如平时忽于卫生,致不免为疾病所困,则其暂时修养自不容已”[22]。因此,此两项请假理由在晚清学校章程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几乎成为所有学校的定式。同文馆章程中,学生“丁艰”可请假百天,回乡路费也由学校支付;重病者同样给予照顾,“各学生如有患病者,应以假期两个月为限,但不得藉词就医,托故外出”[9]33-34。与此同时,一些请假理由虽不在“重大事故”的范畴之内,但仍获得准许。“应试”便是“服丧、重病”之外极为正当的请假理由。如同文馆规定:“遇乡、会试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均不扣除膏火。”[9]34
(二)请假流程的控制
与请假理由的限制一致,请假流程同样处在严密的制约之下,“书面申请——获得准许——领取假票——回校销假”这四个环节中的每一环节都会以各种方式得到完整的记录,从而实现严格的请假流程管理。
签到与点名是监督考勤最常见的方法。在京师同文馆,住宿学生必须每天辰时三刻聚集签到,迟到者会被老师记录在考勤簿上并扣罚学金;不在馆内住宿的学生每日也要在学务提调的监督下当面画到,迟到者亦扣学金;随后补签或请他人代签者,与迟到者同,须同样扣除学金[9]33。点名也在各学堂中广泛地存在着,甚至延伸到学生休息的时空之中,即便是周六日的寝室与餐厅也成为学生接受点名的场所。据报道:“师范男生指导部自校务联席会议议决限制学生请假离校办法后,即首先遵照施行,每星期六晚及星期日中午,均由该部主任躬在寝室及膳厅点名,多数学生均能遵循约束,不敢擅离。”[23]
各类专门记录师生考勤情况的工具也开始逐渐出现,并得到充分的运用。直隶法政学堂设“旷课簿”,点名未应者以迟到论,于开课前15分钟未到课堂者以旷课论,迟到与旷课者之姓名会被记录到旷课簿内,满三次旷课者,便又会被记录到学监手中的“记过表”中,至学年终了时,“旷课簿”与“记过表”均会送交学务监督与教务提调手中,成为评价学生品行的重要参考依据[24]。标明学生身份的“名牌”,也同样被广泛地应用到学堂请假制度中。湖南明德学堂规定:“堂中生徒如需外出,必须去管理处说明缘由,领取名牌,于号房内挂号,将牌悬置外出挂牌处。归时自取此牌,交呈管理。”[25]388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名牌被请假券取代,“告假者必须持有请假券方可离校,回校时,须持原请假券到办公处进行销假”[26]前言25-26。
除学生与学校外,第三方担保也是请假制度中较为常见的管理方法,担保人包括学生父母、法定监护人、宿舍成员、斋务长与学监等。其中,与学生关系最为紧密的父母或其他亲属、监护人充当担保人的情况最多。山东大学堂规定:“业精于勤,学生无事不准请假。如实有紧要大故,应由其父兄家属具函陈明,经总教习核准,交由监督发给假单,单内注明期限,届期即须销假回堂。”[7]51清华学校规定:“请假时必须由父兄或保证人先行直接致书本校斋务处,确实紧要之事由,方可照准。”[27]564宿舍成员充当担保人的情况虽不多见,却更具代表意义。复旦大学仿照明清人口管理的方式,在学生生活中施行保甲制度,每间宿舍推选一名代表,由其向学校负责并保证宿舍的基本秩序,再由这些舍长中推选出一名宿舍楼长,由宿舍楼长代表住宿学生与校方进行交涉;如遇学生请假外出,则需要舍长与楼长向学校进行共同担保后,方可离校[28]211。
其他的时间管理方法也被应用到请假制度中。北京高等师范施行“稽查法”,规定:“每晚学生自习下课,学生就该管域,偕本区事务员稽查火烛,督促夫役洒扫,将门窗关闭,由事务员取钥执掌,并将现状填写查视报告簿,每日送校长及主任核阅。又学生下自习归寝室后,约三十分钟即须熄灯。唯私自燃烛,及炉火未净亦事之所或有。故学监于学生就寝后,须再次稽查一次或二次。”[29]57浦东中学利用“座位检阅法”进行学生缺勤情况检查:“教师检查学生缺席不用旧式点名表点名报到,仅凭各学堂教室座位表检阅,如发现有人缺席即将缺席者学号填入教务处所发之缺席报告单,退课后将该单撕下投诸教务处,按日统计并每星期将缺席生姓名及所缺课程名分别公布,借以示警;教师于检查缺席必须将缺席学生学号朗诵一遍,若有错误,学生当场声明,事后不得向教务处请求更正。”[30]在各式各样的请假管理方法中,学生的在校时间得到有效的保障,学习时间也相对获得了延长,这是时代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亟需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应然表现。
四模糊时间的存续:乡村学校对于学校时间的抵制
尽管新式学堂似在一夜之间纷纷建立,但传统教育载体的影响仍不容小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曾经这样估算近代中国旧式书院的数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尚有旧式书院2000余所,在院人数15万人;而到1909年,新式书院只有700余所,学生人数是7万左右[31]372。且不论此处的数字统计是否精确,但考虑到中国土地上广袤存在的农村地区,旧式书院的势力始终不可轻视。除数量上的优势外,民众的认可与思维惯性也为旧式书院的存续提供了土壤。容中逵在对颐村学校进行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后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尽管道县于光绪二十八年将玉城书院改为新式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下令将各学堂改为学校,但颐村并未设立新式意义上的学堂或学校,读私塾之风仍然很盛。举凡入新式学堂读书者,无不先是读了私塾再上学校的,有的甚至在新式学堂毕业后仍返读私塾的。”[32]这种优势是新式学校无法比拟的,正所谓“洋学是在政府的政令下挣扎维持着,私塾则在百姓们的烘托里枝叶繁生”[33]3。
(一)乡村学校对新式学校时间的抵制
当新式学堂中的学期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之时,乡村学校始终行走在旧有的时间轨道上,乡学中的塾师依然“自清晨而日暮,时与小儿画虎涂鸦,时与高材生讲经论史,丹黄影本,辨别之无,心目交瘁,刻糜暇咎”[34]316,时间的流动依然缓慢、连绵,甚至停止不前。在此背景下,在乡村私塾中推行新式时间倡导下的学年与学期制度遭遇极大阻力。而新式时间与旧式私塾间的互不适应是造成推行困难的主要原因,“村中上学的学生大多是12岁的孩子,他们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实践教育的年龄。在农事活动的日历中有两段空闲时间,即从1月至4月和7月至9月。但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却停学放假。到了人们忙于蚕丝业或从事农作的时候,学校却开学上课了”[35]51。出于农业劳动的需要,大部分的乡间学校依然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为界点将全年的授课时间分为三个学期,平时初一、十五放假。按照李景汉等人的调查,在河北定县62所小学均有“春假”和“麦假”,学生们在这两个假期中承担播种与收获的农活,这是城市小学没有的;而在城市小学中普遍存在时间较长的暑假,在这些乡村学校中却没有那么重要[36]207。在学校与农忙的矛盾中,学期制度在乡村教育的推行中遇到抵制。如张宗麟所言:“学校放寒暑假、星期假等,在乡人以为是无需要的;但是在农忙时,乡人实在需要儿女在家帮助工作,学校反而天天去催着来校。这样,学校与乡村便发生龃龉,乡人对学校就讨厌。”[37]192
同样,尽管政府与教会在新式学校中以“星期”为手段而建立起了一种统一性的教化时间,但这种结果并未在农村地区收获功效,“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38]39。即便是在位于晚清教育改革中枢地区的北京宛平,也依然行走在旧有的农时轨道上,其辖区内的黄土店村小学校,全体师生一年的休息时间约百天,其中秋假由农历七月十五到八月十五,农假由农历四月二十至五月初九,年假由腊月二十至正月二十,余下的16天假期也多与村内的公共活动相联系,如庙会、祭祀等[39]87。除此之外,一些开明教师虽了解“星期”为何,但也公开反对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授课进程中。陶钝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王师傅时曾如是说:“他不是顽固保守的人……但也认为学校里不读圣贤书、只习西洋文字不是正道……而六天学习,一天休息(的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忘掉先前所学内容,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办法。”[40]11
在更为细化的时间单位中,“时”、“分”、“秒”的概念似乎更与乡村教育无缘。“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38]50。同样,学校对于时间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38]37。梁实秋说:“老师渐渐觉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朱笔划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日久季节变幻阴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动,朱笔线也就一条条的加多。”[41]16如果这些私人的回忆尚存缺少权威的代表性,那么官方的学校访查似乎更能有效地说明这个问题。1908年,李搢荣奉学部令在天津武清历时三月进行学堂访查,他所看到的学校时间也是模糊的:“查小营村初等小学堂情形:该学堂……学生二十人,尚皆安静,诚朴木讷,终日读书而未察休息。”“查杨村两等小学堂情形:该学堂……学生每早六点即来,晚七点始散,仅午饭间休息。”[42]136-141可见,此时的乡间学堂大都“规模简略,讲堂北向。……(学堂内)并无计时钟表,未能遵照定章教授,半沿从前训蒙性质”[43]。这是新式时间遭遇到旧式学堂的无奈境遇。
(二)抵制背后的逻辑:农业时间与世界时间的距离
是什么造成了旧式学堂对新式时间的公然反对与消极抵抗?要回答此问题又需要我们重新返回到早期教育现代化中“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经典问题的追问之中。费孝通先生曾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中这样写道:“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私塾因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早已和其他社会制度搭配得很凑合,只有在这凑合里我们才了解一个私塾真正的功能。若是不从这方面去了解私塾,而想在其他社会组织中去抄袭一个教育制度来,强制配入中国传统组织尚强的农村社会中去,自然会发生格格不入的情形。”[44]
新式时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遭遇了无奈,以农业、农耕为生存根本的中国乡村已经深嵌于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文化土壤之中,在这些土壤并未完成真正的新陈代谢之前,它怎能接受符合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时间表达方式呢?以世界时间为代表的新式学校时间是西方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而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依然处在一种农耕阶段,时空之不同步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鸿沟,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生硬移植势必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舒新城所言:“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扞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45]446因此,尽管国家以强大的权力意志自上而下地将工业化新型时间照搬到乡村学校的教学活动中,但这种忽略现实情况的改革很难获得人心与成效,再加上在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官方始终缺少切实的执行能力来保证政策的推行,这使得整个近代时期的新式教育在与乡村私塾的博弈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在整体上造成乡村教育“新旧并存,矛盾兼与,刚毁刚成,方生方死”[46]55的无奈状态。
以新式学校时间在乡村地区的推行为契机,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转型的迟滞与困难。毫无疑问,以农为生、以农为本的现实状况是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但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近代中国农村而言,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并迅速走向富强独立是一个更为急迫的历史任务。“以农立国”的观点虽可解决温饱,却未可强国,若持续下去,乡村或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沉重负担,或最终被现代化转型所抛弃。在西方自发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教育转型是在整个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经济转型完成之后才铺展开来的。而在近代中国,处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教育改革始终缺少强大的经济支撑,教育改革不是追随整体现代化进程亦步亦趋的结果,而是引领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力量。所以,近代乡村的教育改革不仅不能落后,反而要担当农村改革的推力,这样的教育改革才符合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语境。由此,在近代乡村学校中,新式时间的引进与推行,既可成为“传统”与“现代”间的冲突表征,又可视为“传统”接受“现代”的先行准备。在近代新式教育与旧式学校的摩擦与纠葛中,尽管乡村的反应缓慢、消极,但它最终也走上了朦胧初醒的萌发状态。以接纳新式学校时间为代表,这是乡村教育迈向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M].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
[3]Records of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10-24)[R].Shanghai:1877.
[4]钦定小学堂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5]奏定进士馆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6]直隶总督袁世凯.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附章程)[G]//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7]山东巡抚袁世凯.办山东大学堂折[G]//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8]民国法律学校招考预科广告[N].申报,1912-12-21(01).
[9]光绪二十四年以前的同文馆章程[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0]经常章程五条[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1]江南储才学堂章程[J].时务报,1897,(41):15-22.
[12]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3]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G]//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4]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5]钱焕琦,孙国锋.厚生育英才:吴贻芳[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6]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毛鸿宾奏[G]//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7]京师大学堂规条[G]//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8]徐善祥.“约大”的回忆[G]//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科教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9]梁实秋在清华学校[G]//朔之北,许毕基.名家上学记:那时大师如何上大学.济南:济南出版社,2010.
[2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第4版.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1]限制各校放假[J].福建教育厅周刊,1932,(109).
[22]约龛.学生告假问题[J].教育杂志,1910,(12):28-29.
[23]师范限制男生请假及扩充娱乐部设备[J].集美周刊,1935,(5):21.
[24]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法政学堂章程规则折[J].教育世界,1906,(139):1-4.
[25]湖南明德学堂规则[G]//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6]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7]清华学校章程[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8]〔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9]陈明远.那时的大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30]学生缺席请假办法[J].浦东中学校刊,1926,(6).
[3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第4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2]容中逵.百年中国乡村学校教学变迁的历史轨迹——基于颐村学校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3):70-78.
[33]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M].[出版者不详],1936.
[34]稼畦.改良私塾之意见[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6]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7]张沪.张宗麟乡村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8]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39]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社会调查[G]//李文海,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0]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41]梁实秋.梁实秋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42]李搢荣调查武清县东北两路各学堂报告[G]//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43]金华府浦江县各学堂调查表[J].浙江教育官报,1909,(12).
[44]费孝通.写在《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的前面.益世报,1936-08-12.
[45]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J].中华教育界,1924,(4):1-14.
[46]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罗银科]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in Early Education Modernization:with School Time Manag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Case
WANG Hong-yu, YAN Guang-fen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China)
Abstract: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rocess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emester and school year system shaped the preliminary outline of school time, whil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eek and class hour completed the secondary division of school time. A more and more strict system of ask for leave formed border control of school time. In this way, a strict new school tim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began to play an imperceptibly disciplinary role in educating human behavior and thoughts. Meanwhile, the private schools in rural areas kept their outdated stereotype. The open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demonstr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reflect the frustration and hardships in early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education.
Key words:school; time management; early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目标体系研究”(12BKS073)。
作者简介:王红雨(1987—),女,河北东光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史; 闫广芬(1964—),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0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