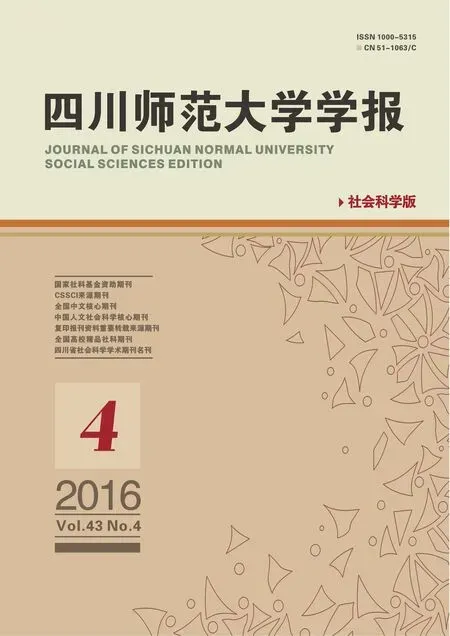救国与娱乐:抗战时期成都戏曲行业面临的舆论压力及其应对
车 人 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救国与娱乐:抗战时期成都戏曲行业面临的舆论压力及其应对
车人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抗战爆发后,戏曲作为成都大众主要娱乐方式,面临着地方报纸以“救国”为名义的强烈批评,戏院被建构成一种与“救国”话语相对立的形象。在“救国”话语的压力下,成都的戏曲行业一方面以演出“抗敌”戏曲来遮蔽其“娱乐”性质,另一方面则以参与募捐来化解“救国”与“娱乐”的对立。然而,戏曲行业的相关努力,无法扭转大众娱乐在社会舆论中的不利处境。以“救国”的名义,大众娱乐被改变了,但这种改变终究有一定限度。因为传统戏曲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的基本作用一旦消失,传统戏曲的生存必将面临危机。
关键词:抗战时期;戏曲行业;成都;戏院;娱乐;救国;舆论压力
近年来,在“新文化史”、“微观史”等研究取向的影响下,史学界对中国传统戏曲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①,其中政治在戏曲演出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颇受学者关注。既有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是政治介入戏曲演出活动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戏曲的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1]105;国家“利用民族危机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最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2]145-146。相关研究无疑为理解戏曲与近代政治、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实践。不过,抗日战争时期何以成为政治介入戏曲演出活动的“黄金时期”,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当我们分析政治对戏曲的介入时,除了关注介入的主体(如政府、政党等)、介入的具体行动(如具体措施、规章条文等)外,政治权威(authority)的树立也不应忽视,具体表现为知识界与舆论界对政府干预戏曲演出的“鼓噪”与支持以及戏曲行业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与“配合”。相较而言,既有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加强控制戏曲演出论之甚详,而对政治权威在大众娱乐中的树立及其影响关注相对有限。本文试图从抗战时期成都地方报纸对本地戏曲娱乐的批评入手,探讨“救国”作为政治权威如何在大众娱乐中得以确立。我们可以看到,戏曲演出并非天然就是“抗日宣传”的有效工具,而一定程度上是在外部压力下戏曲演出者趋利避害的自主选择。然而,观众看戏的首要目的仍在于娱乐,以戏曲作为“教化”和“宣传”的工具,尽管有其时代的特殊性,然其完全忽视戏曲的娱乐功能,终将影响到戏曲本身的生存空间。
一战时社会舆论对戏曲行业的批评
20世纪的前30年是成都传统戏曲演出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06年,第一家近代戏院“可园”在成都创办,标志着成都的戏曲行业开始走向市场化;1912年,近代川剧界最有影响力的戏班“三庆会”在成都建立,则是近代川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3]132[4]143。此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成都市内已形成了一个较为繁荣稳定的戏曲演出市场,“听戏”更是当时成都市民重要的娱乐休闲方式。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根本改变了成都戏曲所处的外部环境。随着抗日救亡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共识,“救国”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戏曲演出的娱乐属性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都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由于戏曲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于战时戏曲业而言,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可能并不亚于来自政府方面的高压与管控。
战时成都戏曲业所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主要来自新闻媒体。作为当时四川省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一方面,《新新新闻》强烈的地方化、平民化和商业化特征,使得其十分关注成都的戏院与戏曲演出;另一方面,从报社人员的教育背景看,《新新新闻》的主笔皆川籍人士,全部具有专门学校以上的文凭,有的人还具有留学经历,这又为该报有关戏曲娱乐的评述染上了明显的精英色彩②。在整个抗战期间,《新新新闻》针对成都戏曲娱乐的批评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但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其批评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由此,《新新新闻》对成都戏曲娱乐的评论,可以作为观察知识分子对于大众娱乐态度的一个窗口。
1937年7月25日,即“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18天,《新新新闻》首次出现批评本地戏曲娱乐的声音。其刊载的漫画《马路上的看客》为:马路边贴着“本园重金礼聘京沪超等驰名文武花旦今夜登台玉堂春”的广告下“人头攒动”,而“抗敌宣言”前却只有“看客”一人[5]。漫画无疑是想用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告诉人们,“玉堂春”之类的戏曲演出对成都人的吸引力超过了“抗敌宣言”这种“现象”是不对的,其潜台词则是“救国”与“娱乐”不能兼容。
“救国”与“娱乐”为什么不能兼容呢?批评者们的解释是,“娱乐”意味着轻松,与“救国”的氛围不符。《新新新闻》“七嘴八舌”栏目的一位评论者声称:“靡靡之音”本身不会亡国,而它却是亡国的“征象”,“我们却不该有这种征象,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要来的悲壮,激昂,亢奋一点,与普遍的抗战情绪取得联系”[6]。因此,随着淞沪会战爆发,全面对日抗战的形势逐渐明晰,戏院等体现出的“娱乐”景象和氛围,与“悲壮”、“激昂”、“亢奋”的“抗战情绪”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起来。1937年8月29日,《新新新闻》再度刊载漫画:“某某大戏院”门口车水马龙,顾客如织。漫画作者还特意给漫画取了一个讽刺的标题“共赴国难”,实则批评戏院生意的繁盛与抗战主题不相容。
一开始,批评者们的“矛头”指向了去戏院看戏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抗战时期还看戏的人们“神经”显然不够“锐敏”。1937年9月,抗日话剧《保卫芦沟桥》在成都上演,一时反响巨大,然而《新新新闻》的一位评论家却借题发挥,批评平日喜爱看戏的民众道:那些看了《保卫芦沟桥》后哭的人是“神经衰弱”,因为他们观看《苏三起解》也“一样会哭”,可“长城,吴淞正演看一齣真刀真枪的戏,场面比这更伟大,情节更逼真,然而却没有人哭过”;这些人“哭过之后”,“出了戏场又哭(笑)嘻嘻,而且仍然□看公子多情,小姐赠巾的戏,去看穷汉淘金,骑士救美的戏”[7]。地方文人王怡庵则于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九一八”到来之际,撰文批判成都人已经快要淡忘“九一八”是什么日子了,因为“娱乐场不是依然有人满之患,包车汽车停满了各娱乐场门外么”;王怡庵认为,此类现象表明,作为“重要后方的都市”的成都,“寻不出全面抗战的精神来,找不到前方已经血战很久的后防应该如何紧张的态度来”[8]。
尽管遭到批评的是看戏的人,但戏曲行业难免“池鱼之殃”。一封“读者来信”呼吁:“奢华”的“太太小姐们”把她们“穿华服,吃美食,搓牌雀,看戏剧的钱,拿来出点到前方去,慰劳勇猛的将士,救济不幸的同胞”[9]。另一位“读者”则干脆呼吁:对娱乐场加“国难捐”,理由是“十二个娱乐场,日夜装满”,“娱乐场这么多人,何不抽点娱乐捐”,“他们及时行乐的,如九牛拔一毛,少吸一根纸烟就得啦”,而且“想来他们也乐为,并且也成全了他们娱乐不忘救国的志愿”[10]。“看戏”作为一种娱乐消费,在抗战时期不仅不正当,甚至还“奢侈”,戏院则是“不爱国”的“有钱人”们爱去的“奢侈”场所;既然劝说“奢侈”的人们不去看戏效果不大,那么社会舆论的压力转向制造“奢侈”的戏曲行业似乎“顺理成章”。
于是,进入1938年后,批评者的矛头由看戏的人转向了戏曲行业,报纸上针对戏曲行业的批评与“建议”可谓“五花八门”。有人主张将“剧团”赶到农村去,因为它们打着“爱国宣传”的招牌,实际上却“祸国害民”,为“都市所有的大人先生,豪商富贾,挥霍浪费”,“纯系为了交际娱乐混目,终日到戏院去爱国”[11]。有人主张对戏曲行业抽收捐税:“一切荒淫的事,均征收特别捐”[12]。有人对戏曲行业的“繁荣”耿耿于怀,因为成都戏院数量之多,只会证明本地“笙歌管弦,朝秦暮楚,不似战时状态,直如升平气象”[13]。“国耻日”的到来也会勾起对戏院的不满,因为戏院在“国耻日”不仅不停演,还减价招徕观众,以至于把参加“火炬游行”的人都“勾引”过去了[14]。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战局的紧张使人们更加“痛心疾首”:“战争愈进步,奢侈娱乐也随之而进步,不管大武汉怎样的危急,它们困在戏院的,仍然困在戏院”[15];“昨天广州失陷的消息传来,但我看几个娱乐场所完了的时候,人像蛆一样拥出……啊,你看,将来纵然武汉放弃,娱乐场一定还是满座……一切亡国的现象一定还是照常”[16]。面对“木包一样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们,“依然天天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依然天天看戏看电影”[17],批评者们似乎已“无计可施”,干脆直接向政府呼吁:“我真不明白,我们的成都当局,怎么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还不取缔这些消灭抗敌情绪的事业一样?”他们甚至要求“一律禁止”无关抗战的旧剧和影片,将戏院等“一律收归公有”[18]。
对于戏曲行业而言,如果之前的批评只是无关紧要的“七嘴八舌”,到1939年,随着成都面临日本战机轰炸的威胁,防空疏散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后,这些“七嘴八舌”突然变得“有力”起来。1939年2月12日,《新新新闻》刊载漫画《疏散人口》,在漫画中,四位“衣着时尚”的男女(从右到左)分别说:“我要去看悦来!”“我喜欢听京戏!”“我去听扬琴!”“听说智育今晚换片。”③[19]以“疏散人口”为题,显然有影射戏院阻碍防空疏散的意思。
随后而来的疏散使得“戏园、影院生意一落千丈”[20]21,但这并未使其逃脱被批评。因为戏院是“吸收都市有闲阶级人们的有效场所”,只要把它停业,“享乐的红男绿女自然会无聊而离开城市生活”[21]。1939年5月26日,《新新新闻》的“小铁椎”直接建议当局“停止娱乐场所营业”,因为“许久不闻空袭警报,人心似乎又有些痺麻了,警备疏散,趦趄不前”,已经疏散的人又回到了城里面,“而娱乐场所的客座,又密不通风了”,许多人“眷恋城市,不肯疏散”,“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以政府应立即责令娱乐场所停业,“使那些醉生梦死者无所留恋亦无可留恋”[22]。省主席王缵绪最终“顺应”舆论的呼吁,将戏院一律停业,“以杜荒嬉而策安全”④。为此,成都戏院停业近两个月。同样的情形又出现在1940年的夏天,在成都又面临防空疏散问题时,有人再次指责戏院,称:“迄今为什么尚有一部分人不去疏散,我觉得仍然是娱乐场所的吸引力太大了”,因此,“应当照过去的办法,从取缔娱乐场所实行起来”[23]。戏院于是再度“自动疏散”[24]。
1942年以后,日机停止了对成都的大规模空袭,防空疏散问题得以缓解。抗日战争长期处于相持状态,战争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已属常态。与此相应的是,抗战前期针对戏曲行业的许多批评逐渐沦为“老生常谈”,最终在报纸上“销声匿迹”。戏院的门票价格成为了抗战中后期备受批评者们关注的问题。早在1939—1940年戏院在防空疏散后恢复营业时,报纸便希望戏院减少票价[25][26]。然而,抗战中后期,随着成都物价的不断上涨⑤,戏院不断提升票价,于是报纸便代平民“发言”,批评戏院涨价是发“国难财”。
1942年9月,影剧业⑥大幅提高票价,“市民望政府取缔”[27]。10月,署名“尖兵”的作者评论娱乐场的票价说:成都是“后方的重镇”,“然而许多人只是昏昏梦梦□□,每一娱乐场所,场场满座,有些未开场就‘免战高悬’,人满为患”,因此,“娱乐场的老板,却呵呵大笑,随时提高票价,叫戏迷影迷挨大竹杠。戏院座票更是因为戏迷拥挤,不仅发生黑市,而且黑市之价极为惊人。一张数元的座票,暗盘要卖到四五十元,否则戏迷便哭天无路,戏瘾难熬”,人们甚至为求得进入娱乐场而常常大打出手,于是尖兵提醒当局:“为了疏散,为了使人们不要荒淫,本市是否需要这样多的娱乐场?是否该请他们疏散下乡?”[28]戏票不仅与当局较为忌讳的“黑市”发生了联系,还能酿成“治安问题”,实在是戏院的一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又批评说:“一般物价都在下跌当中,而有些东西却偏要涨价,事情之怪,无以复加。”“戏园电影院更因为冬天雾季,影迷戏迷痰迷增太多,尤其无声无臭一再涨价——但这与穷人无关。”[29]
1943年11月中旬,影剧业联合在成都各报发出启事,说明其票价高涨的原因⑦。有人作文反驳称:“电影戏剧之能协助抗建,乃在普通观众,深入民间,以期文字宣传之不逮,若以纯粹商品化,图谋厚利,则全失其功用与价值”,现在“一票辄以数十元,即中产阶级亦不胜其苦,至于公教人员,文化人士,则望洋兴叹欤”,至于影戏院方面所“辩解”的“生意不好”,这位批评者却认为那是其自身的问题所致;他指出,全国的影戏院都面临相同境遇,但成都三十八到四十元的票价已达全国最高,因此影戏院方面应该“好好反省”自己,而政府则应出手限价[30]。是文发表后,有人在报纸上刊文“响应”,要求限制票价“不能超过十八元”,否则“未免有失政府威信”,定价之后,“应强迫实行,敢有违者,照章处罚,或令其停业”[31]。影剧业的涨价与限价问题,可供我们从侧面观察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经济与社会生活,观察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批评者们反对票价上涨,固然有为民生考虑的成分,但他们不愿意戏曲行业“赢利”的心态,亦有以致之。实际上,这仍然属于其自抗战以来一贯的对于“娱乐”的批评态度。
二戏曲业的应对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随着“救国”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报刊舆论建构出的“娱乐”与“救国”相悖的话语,导致“娱乐”本身的正当性丧失。“看戏”既与“救国”冲突,则戏院的生意自然会受到严重影响;诸如“奢靡”、“妨碍疏散”乃至“发国难财”之类的“罪名”接踵而至,甚而可能招致政府的打压。对此,戏曲行业当然不会“等闲视之”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在战时社会舆论中的处境不利,但这一时期的戏曲未必没有机遇。抗日救亡运动既然是“全民参与”的事业,则“救国”的话语必然进入普通大众的娱乐口味中。换言之,带有“救国”色彩的戏曲,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因此,采取适当的行动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既可抒发爱国热忱,也能用来改善在舆论中的不利处境,还能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戏曲行业来说,应当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对于戏曲业来说,参与抗日救亡,最为切合自身实际的方式仍然是演戏。戏曲演出的重要功能是娱乐,然而自清末起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戏曲演出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教育”,因为“下等社会不能读书识字者,全藉观剧以印证历史教育于脑筋”,故“欲知下等社会为何等样人,试先问演者为何等样戏”[32]。即使到了抗战时期,戏曲依然“负有导扬国家文化和启迪民族意识的伟大使命”[33]1,3。演戏是“社会教育”的观念,无疑是当时官方、知识界及戏曲界的共识。教育部转发各地的一份文件指出:“查戏剧一道,可以褒贬善恶,移风易俗,不独为娱乐之一,在社教工作中,实居重要地位。”⑨“川剧大王”张德成也说:“戏剧对于国家民族政治风化社会人心至为重大。”[34]11
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时期应演出什么样的戏曲?其实,抗战前后在成都戏院里表演的许多“传统”戏目,本身已是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中重新编写或改写的“改良”戏。这些剧本虽然以古代历史故事为主题,但戏中多灌输了“正义”、“爱国”、“忠诚”的观念[35]367[36]251。但是,这些“改良戏”的题材和教育功能,在戏曲行业的批评者看来,显然已无法应付抗战的需要了,因为这些戏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表现封建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贯穿了大部分旧型戏剧的宿命论的观念、奴隶思想、男尊女卑,旧型戏剧所表现的民众是与国家与民族不发生任何关系的”[37]10,30-32。鉴此,他们提出“现在别来什么风花雪月,神仙鬼怪的戏文,多演一点民族抗战的戏”的主张[6]。
原有的戏目既然难以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时装戏”的出现似乎顺理成章。所谓“时装戏”,即在清末出现的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新编戏曲,因其穿戴“时装”而得名。“时装戏”的编剧方法,“大致和传统戏差不多,上场引子下场诗,唱作念舞都有,一般不用布景,演员表演也多用传统手法”[38]130。川剧的“时装戏”出现于辛亥革命时期,30年代又涌现了以写“时装戏”剧本见长的刘怀绪,其创作之“时装戏”剧本中,与抗日话题相关的剧本即有《枪毙田玉成》、《芦沟桥姐妹花》、《枪毙殷汝耕》、《汉奸之妹》和《抗日英雄王铭章》等,此外尚有《南口之战》、《王上将殉职》等剧本[35]529-532。



有时,戏曲艺人们在一些“新编小戏”、“连台本戏”与“传统折戏”中加唱“新段子”,反而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抗敌效果”。如由古代故事改编的《新打神》一戏,故事情节正当高潮时,演员突然加唱一句“猛想起前方正吃紧,要打就该去打日本兵”[40]13。1939—1942年,在“三庆会”会长肖楷成领衔下,连台戏《济公活佛》在悦来戏院演出,“场场满座,久演不衰”;某次戏院突然停电,肖楷成“灵机一动”,突然加了段“抗日”台词,引起喝彩,于是此后都在《济公活佛》的“适当地方”加上一段这样的台词,“收到抗日救亡、宣传和艺术鉴赏完美的融合效果”[44]191。其实,这种演出方式仍属于传统戏曲演出中“抓哏”的范畴,其之所以成功,在于契合了戏台表演与观众互动的游戏与娱乐性质[45]5。不过,刘成基将《济公活佛》的这种做法视为川剧发展中的怪现象[38]132。我们不知道他批评的出发点是什么,或许是批评其仍然是旧的题材,“固步自封”,或许是这种加唱“新”段子的做法“不伦不类”。
应该说,通过演出“民族抗战”戏曲,戏曲行业在“抗日宣传”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也在为自己营造“抗日”、“社会教育”的社会形象,但显然收效不佳。一方面,舆论的反映表明,戏曲的批评者们似乎并未领情;而另一方面,“抗战戏曲”看来也无法在戏曲舞台上站稳脚跟。到1941年初,成都的戏曲舞台已退回了原样,戏院“排演的戏目,也不过是些古代的忠孝节义故事而已”[46]。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戏曲的“社会教育”功能已无法满足趋新知识分子们的要求,相对于“社会教育”的场所,戏院在大多数时间里被视为“娱乐场所”,批评者们难以容忍“娱乐场所”在抗战时期的繁荣,因此不断批评。
相较于上演“民族抗战”的戏剧,参与抗战相对容易的方式是参与各式各样的募捐。募捐当然可能是出于爱国热忱,但也可藉此树立其参与抗战的形象,规避诸如“奢侈”、“不爱国”等负面评价。成都募捐支援前线的活动始于芦沟桥事变后不久,随着战事日益激烈,抗敌氛围开始浓重,戏院也参与到捐款的行列中。
举行公演是戏曲行业募捐的重要方式。由于戏剧表演对人们的吸引力,往往能得大量门票收入,而戏院则将所得门票收入拿出捐献。1937年10月4日,新闻报道春熙大舞台“募捐救难民”,称其“鉴于沪战爆发,受灾同胞急待救济,本娱乐不忘救国之旨,遵影剧业公会之发起各院园募捐救济灾区同胞”,“以一日所得全数捐助灾区同胞”[47]。10月6日,成都各戏院遂举行“演剧捐”,“贡献一日所得,以尽国民一份子之职责”,戏院一日的收入,包括“月饼费”被一并捐给前线[48]。
“游艺大会”也是一种重要的募捐形式。所谓“游艺”,即不局限于一种艺术形式,往往传统戏曲、话剧乃至音乐多种形式同台演出。如1938年11月13日,新又新大戏院举行的游艺大会,成都京、川、话剧的名角王泊生、贾培之和白杨等“义务助演”,还邀请“外籍音乐名家演奏”[49]。戏院往往充当“游艺大会”的演出场所,戏院里的戏班则参与其中[50]。由于汇聚诸多艺术形式,而且名家荟萃,因此,“游艺大会”对于不同艺术口味的观众颇具有吸引力。大会的举办者和戏院为吸引观众,在广告上也颇费心思。如新又新大舞台举行游艺大会的广告声称:“内容精彩,意义深厚,爱国兼可看戏,买票等于捐衣,机会难得,爱国同胞幸勿交臂失之。”[49]这里将“爱国”与娱乐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以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而“热血剧团”募捐寒衣的游艺大会广告则称:“多买一张票,多制一件寒衣,多增一份抗战力量。”[50]


尽管如此,参与募捐并未根本改变批评者们对戏曲行业的不满情绪。尽管没有否定戏曲行业的募捐,但这并未消减对娱乐的批评。1937年10月以后,尽管新闻相继报道成都的各戏院演戏募捐,但同时期报纸上仍充斥着要求征收“娱乐捐”、“奢侈捐”的呼声。人们并不认同“爱国兼可看戏”,戏院的募捐活动不足以遮蔽其在批评者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娱乐”标签。正因为戏院是娱乐场所,又吸引那么多的观众看戏,其募捐被视为理所应当,甚至应该成为正式的税收。
由此不难理解,一旦戏院参与捐款不“积极”,将会陷入怎样的舆论“风暴”中。1939年度的“寒衣”捐款,戏院最初表现得不太“积极”,为此招来诸多批评。人们原本认为,戏院积极捐款“理所应当”,因为“名伶主角”能亲自征寒衣,不仅“定能收到很大成绩”,而且“还能表示他们并不是在‘隔江犹唱后庭花’”[53];退一步讲,戏院“既无其他负担,对此项协助加捐之事,想不致多所拒绝”[54]。然而,“有一二影戏院坚不接受”,舆论对此大为不满,于是痛斥这些戏院的“老板”们“究竟是何居心”:“寒衣捐之附加在入场捐上,出钱者仍为观众,与剧院并不相干。”如果是怕影响营业,那么这些老板们应该对前线将士心怀感恩之心才对,因此,“若要以停业相要挟,要停便停,何必惺惺作态”,停业“不会少了一只耳朵和眼睛”,如此“做作”,只能证明其“愚昧与鄙陋”,“希望大多数剧院,股东们切莫跟着他们采取一致行动”[55]。随后舆论对戏院施加强大压力,11月5日的新闻报道要求:“正当商人,勿予附和,否则政府尽可实施强迫予以制裁。”[56]有人则声称:自影戏院复业之后,演映的都是“明目张胆的妨碍抗战,消磨抗战意识”的作品,现在居然拒绝加收寒衣捐,还“以停业相威胁”,因此“要停就停”,只有“行尸走肉的凉血动物”才希望他们复业[57]。影剧业反对增加寒衣捐,也可能是因为会亏本,但显然批评者们没有或者不愿考虑这点。最后在舆论压力下,各戏院只得“深悟大义”,“自愿接受寒衣会所定捐款征收方法,于昨(十)日起复业也”[58]。在此类“捐款”造成的“风波”中,戏院不仅没有改善其在舆论中的“不良形象”,而且还可能形塑一种类似于“发国难财”这种在大后方舆论中颇为负面的形象。
三“救国”与“娱乐”的平衡
临近战争结束的1944年,成都的各戏院依然“常告客满”[59]93。同一时期游历成都的黄裳,也提到成都的戏院,“每天总是客满,里边全是茶余酒后来欣赏这乡土艺术的人,裙屐连翩,情况是相当热烈的”;不过,黄裳本人对“乡土艺术”的那份“欣赏”,在他定居重庆后却消失了,“时时经过剧院门口,听见金鼓的声音,心情激动,殊不愿再听这离乱之音”,他甚至哀叹:“沧海波澜,战乱未已,这种蜀音,简直发展成为全国的声音了。”[60]303
黄裳的“失望”以及《新新新闻》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不断的批评声音,似乎表明,战时针对戏曲娱乐的批评并未达到批评者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这些批评既没有影响一般民众看戏的“热情”,也没有撼动戏院的“繁荣”,甚至没能让“救国”的戏曲占据戏院的舞台。只有在与“防空疏散”相结合时,对戏曲行业的批评才一度“抑制”了娱乐。更多的情形下,报纸对戏曲行业连篇累牍的“批判”可谓“孤掌难鸣”,得不到观众、戏曲业及政府的“响应”,这无疑给原本充满热情的批评者浇上了失望的“冷水”。
对于戏曲行业的批评者而言,批评戏曲行业的目的是为了动员民众“救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娱乐活动天然带有的“放松”性质,既不符合知识分子们为抗日救亡所营造的“悲壮”氛围,更不符合知识分子们心目中抗日救亡所应具有的“紧迫感”,这无疑是其受到这些知识分子排斥的主要原因。对于身处成都的地方知识分子而言,成都地方的“特殊性”无疑使得其更加排斥“娱乐”。战争爆发后,原本僻处西南内地的成都成为了“重要后方的都市”,因此,成都在“战争进行当中负着如何重大的责任”,本来“不待国家要求,是应该自己明白的”[61]。然而,成都地理上远离战争前线,救亡危机本不易为本地民众所感知。戏曲行业的“繁荣”,意味着“在这重要后方的都市中,寻不出全面抗战的精神来,找不到前方已经血战很久的后防应该如何紧张的态度来”[8]。所以,批评“沉迷”看戏的民众,批评戏曲行业的“繁荣”,是地方知识分子希图扭转地方社会风气,从而动员民众抗日的一种方式。
无可否认的是,戏曲行业的批评者颇有爱国热情,而报章中联翩累牍的“呼吁”与“规劝”,更是把新闻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与引导责任发挥到极致。然而,过于强烈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最终使得批评者们事与愿违。这些人大多视抗战时期还要去看戏的民众为“木包一样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17],他们“不可救药的神经衰弱”[7],而自己显然“神经锐敏”。他们以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要求一般民众,呼唤“悲壮”、“激昂”、“亢奋”的氛围,期待民众也“将神经练锐敏一点”,不要“天天去看戏”。至于戏院和戏班,即使出于生存需要演戏,也只能演出“民族抗战”的戏。概言之,这些批评者不仅要求所有民众一起“爱国”,同时还要按照被他们限定的方式“爱国”。
然而,知识分子们引领“救国”话语,规训民众生活的“雄心”终究无法实现,针对戏曲行业和看戏观众的批评更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将“救国”与“娱乐”建构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注定了这些批评无法为观众、戏曲行业真正接受。归根结底,娱乐作为大众的一大精神需求,并不能因为“救国”而被根本取消。对于戏院和戏班来说,戏曲演出的首要目标是得到观众的认可,投其所好。这种关系受外界社会变化和政治发展的影响较小,也不因为战争的发生、发展而发生根本的不同。尽管随着抗战话语的深入,戏曲演出中的“抗敌”因素本身也会富于吸引力。如时人的回忆中,“最受欢迎的戏”全部是与抗战相关的戏,也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62]45。然而,大众的娱乐“口味”中不可能只有“抗日”因素。对于观众来说,戏剧演出的意义不仅仅是被教化,更重要的还是休闲与放松。戏剧理论家刘念渠认为:“万万千千的观众不尽是有正确判断力的,他们不能因为在抗战期间没有抗战宣传戏剧就不去看戏;也有人不愿意花五角钱看一次话剧,情愿在三天之前就定了座位去听名伶的拿手好戏。”[37]33刘的本意是“告诫”话剧界人士要加紧编写“抗战宣传戏”,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休闲娱乐之于一般观众看戏的意义。其实,戏曲所提供的休闲,不仅未必分散人们对抗战主题的关注,反而能放松人们因战争而紧张的神经。针对成都戏曲娱乐的大多数批评都流于情绪化,缺乏可操作的具体建议。批评者们动辄呼吁“停止娱乐”,既忽略成都戏曲行业的现实处境,又无视战时娱乐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更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实际上沦为了尴尬的道德说教,只能反映出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大众娱乐的偏狭态度。
不过,抗战时期针对戏曲娱乐的批评,虽然未达到批评者们希望达到的效果,但并非全无作用。“川剧大王”张德成表示,川剧能吸引众多观众“并非偶然”,因其曲牌众多,能将“喜怒哀乐”“传神入化”,同时因其“辞藻佳丽”而“雅俗共赏”;不过,“值此发动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的今日,各种地方剧曲,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伟大的责任,完成伟大的使命,川剧当然不能例外”[34]11。张氏的言论像是为戏曲行业“辩解”,也可作为戏曲界人士的一种“表态”。尽管无法完全迎合批评者们的种种“要求”,但戏曲行业采取了诸如演出抗战戏曲和参与募捐等实际行动加以应对。作为抗战社会动员的组成部分,针对戏曲行业的批评,推动了“救国”作为最高政治权威在大众娱乐中的形象树立。
对于戏曲行业而言,这些批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戏曲从业者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处理艺术与现实、演出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传统艺术形式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得以延续。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式,戏曲演出与现实结合是戏曲艺术应有的“题中之义”。对于战时戏曲行业而言,“救国”无疑是必须予以回应的时代命题。然而,如果单纯将戏曲作为“救国”工具,忽视戏曲艺术应为观众带来的艺术享受,或者单纯以“娱乐”为出发点,无视戏曲艺术应与时俱进、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都会造成戏曲艺术的严重异变。概言之,对于传统戏曲而言,“救国”与“娱乐”,应实现某种形式的“平衡”。
对于抗战时期的一些戏剧界人士而言,选择戏曲作为抗日宣传的“武器”,主要是因为“旧剧”的观众与演员众多;至于演出的戏目,则必须重新“注入新内容”,“新内容必须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吻合抗战情势的发展”,他们“希望做到每一地方每一剧场的每一场演出都是抗战宣传的新剧本”[37]28,29,37。然而,过于强烈的工具理性,使得这些“改造旧剧”的努力陷入了困境。事实证明,传统戏曲中灌输过多的“抗战内容”与“现代思想”,往往造成戏曲形式与内容严重失调,严重影响戏曲本身对观众的吸引力。1939年,成都春熙舞台上演改编后的《血染黄州》,一向主张改造“旧剧”的刘念渠观看后却认为其“主题不明确”,布景海派戏和话剧的杂糅风格颇“不着调”,声响效果采取话剧的形式则显得“不伦不类”[37]52。1945年,剧作家郑沙梅将川剧经典曲目《红梅》改编为话剧形式上演,结果却引得观众一片“倒彩”,为此剧作家洪深撰《哀红梅》一文反思: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应兼顾其创作“企图”和演出“效果”[63]285。战后的1946年,田禽反思抗战时期的“戏剧运动”时指出:“抗战初期的创作,大多单纯的重视了宣传作用,而忽略了宣传必须与艺术统一的真理。”[64]9一些川剧界人士则认为,抗战结束后,川剧已经陷入了“危机”中,除却动荡的时局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在电影等新艺术形式的冲击下,传统戏曲形式本身严重“异化”,从而导致其观众基础的丧失。刘成基在评论抗战后成都戏院里的“时装戏”时更严厉地指出:“它(时装戏)既不同于早年间的时装戏,也没有半点川剧艺术在其中。它在文艺舞台上预告人们:川剧要垮台了!”[35]547
对于传统戏曲而言,政治宣传与教化的系统介入始于清末戏曲改良,兴盛于抗日战争时期,并最终在共和国时期达到极致,其中得失利弊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如何在教化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对于整个戏剧界而言,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而对于像川剧这样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戏曲形式而言,如何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保留自身的艺术特色,维持并扩大观众基础,则更是事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
注释:
①近十年来史学界关于戏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魏兵兵《“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的公共娱乐》,《史林》2010年第5期;姜进《越剧的故事:从革命史到民族志》,《史林》2012年第1期。近年来,关于近代四川戏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蒋维明《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马睿《晚清到民国年间(1902—1949)政府对四川地区戏曲表演活动的介入与控制》,四川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周鼎《“世界亦舞台”:民初成都的戏剧与文人——以《娱闲录》(1914—1915)剧评为中心》、李贤文《川剧界对抗战的反映(1937年7-12月)》,两文均收入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又收入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8-119页。
②有关《新新新闻》的相关情况,详见:王伊洛《〈新新新闻〉报史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悦来”即“悦来戏院”,“智育”指“智育电影院”。
④参见:《成都市政府转四川省主席令》,成都市档案馆:民国成都市政府档案,全宗38/4/5459。
⑤据研究,成都的物价自1940年始呈几何增长态势,零售物价指数在1937年为103,到1940年为615,而到1945年竟达214343。参见:谯珊《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⑥时人所提到的“影剧业”指的是“影剧业同业公会”,是成都的电影行业与戏曲行业联合成立的同业组织。参见:《影剧商团结 组织同业公会》,《新新新闻》1933年4月15日第9版。
⑦据说该启事是针对“卯金刀”《请评一下》而发出的“郑重声明”。见:万承松《读回答影剧业联合启事有感》,《新新新闻》1943年11月24日第8版。由于报纸散佚的原因,笔者未曾找到《请评一下》一文以及影剧业所发出的“联合启事”。
⑧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一些艺术界人士极力撇清艺术与娱乐的关系。参见:史东山《对于艺术的认识:艺术的真正目的所在决不是供人娱乐》,《国讯》1942年总第297期,第9-10页。
⑨参见:《民国成都市政府档案》,成都市档案馆:全宗38/4/5766。
⑩战时《新新新闻》尚有数则新闻涉及“时装戏”,大多“语焉不详”。如1938年10月2日有报道称:“影剧同业公会昨会商,双十节各院演映抗战戏”,此“抗战戏”或可算“时装戏”,但未知具体演出戏目,也无后续报道(见:《东鳞西爪》,《新新新闻》1938年10月2日第7版)。1938年11月,华瀛舞台开业,所演戏曲中有号称“第一部抗敌新戏”的《民族英雄抗敌史》(见:《新新新闻》1938年11月16日第6版)。1939年10月,由“川、平、话、评”各剧联合的“成都市戏剧界协会”成立,并举行公演,内有《日本的间谍》、《民族光荣》两戏,根据剧名判断应属“时装戏”(见:《成都市戏剧界协会定期成立》,《新新新闻》1939年10月5日第7版)。





参考文献:
[1]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J].近代史研究,2006,(6):90-105.
[2]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成都之戏园[M]//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4]蒋维明.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5]佚名.马路上的两种看客[N].新新新闻,1937-07-25(14).
[6]圣·彼得.消夏琐记[N].新新新闻,1937-08-04(10).
[7]圣·彼得.戏剧还是戏剧[N].新新新闻,1937-09-07(10).
[8]王怡庵.从九一八说到全面抗战[N].新新新闻,1937-09-18(11).
[9]周茂.希望太太小姐捐奢侈费救国!以盛妆美食打牌看戏的钱 慰劳战士救济灾民[N].新新新闻,1937-10-05(11).
[10]慧.请娱乐场实行加国难捐[N].新新新闻,1937-11-11(8).
[11]凑热闹.成都市的怪现象[N].新新新闻,1938-02-18(8).
[12]打更匠.抽取摩登捐[N].新新新闻,1938-02-20(8).
[13]快快觉醒[N].新新新闻,1938-08-15(8).
[14]名学士.纪念国耻 鼓励娱乐[N].新新新闻,1938-09-20(8).
[15]后防的一角[N].新新新闻,1938-10-21(8).
[16]名学士.节约运动到现在[N].新新新闻,1938-10-25(8).
[17]名学士.怎样惊醒木包的迷梦[N].新新新闻,1938-10-27(8).
[18]申小卒.醉梦的人们醒来吧![N].新新新闻,1938-11-11(8).
[19]佚名.疏散人口[N].新新新闻,1939-02-12(□).
[20]成都市文史委.抗战八年成都纪事[G]//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1985.
[21]沈冰斋.疏散办法的我见[N].新新新闻,1939-05-11(8).
[22]停止娱乐场所营业[N].新新新闻,1939-05-26(5).
[23]秤主.几个防空问题[N].新新新闻,1940-06-12(8).
[24]娱乐场所自动疏散[N].新新新闻,1940-07-07(5).
[25]尖兵.娱乐场所复业问题[N].新新新闻,1939-08-16(8).
[26]秤主.娱乐场所恢复营业[N].新新新闻,1940-04-21(8).
[27]影剧业提高票价 市民望政府取缔[N].新新新闻,1942-09-03(7).
[28]尖兵.娱乐场的票价[N].新新新闻,1942-10-16(8).
[29]尖兵.畸形[N].新新新闻,1942-11-23(8).
[30]章华祺.回答影剧业联合启事的一封信[N].新新新闻,1943-11-21(2).
[31]万承松.读回答影剧业联合启事有感[N].新新新闻,1943-11-25(8).
[32]光绪三十一年研究所第一次开议[N].四川学报,1906,(1).
[33]赵容予.改良地方剧与充实军中文[J].政工周报,1944,14(10).
[34]张德成.漫话蜀剧[J].戏剧新闻,1939,(8-9).
[35]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36]谭清泉.黄吉安[G]//任一民.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37]刘念渠.战时旧型戏剧论[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0.
[38]胡度.川剧艺闻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39]春熙舞台表演胡阿毛 日内公演[N].新新新闻,1937-10-01(10).
[40]成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川剧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41]刘念渠.战时中国的演剧[J].戏剧时代,1944,1(3).
[42]电影戏剧业 捐一日所得 制寒衣送前线[N].新新新闻,1938-10-18(10).
[43]李一非.旧剧的整理与运用[J].戏剧新闻,1939,(8-9).
[44]廖友陶.肖楷成与“三庆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制作会议.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45]陈建森.戏曲与娱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6]唐泽稜.一年来的成都市(续完)[N].新新新闻,1941-01-06(7).
[47]春熙舞台募捐救难民[N].新新新闻,1937-10-04(10).
[48]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各界爱国情绪高扬[N].新新新闻,1937-10-07(10).
[49]新又新大舞台“游艺大会”广告[N].新新新闻,1938-11-13(6).
[50]九十五军热血剧团公演广告[N].新新新闻,1938-10-30(7).
[51]名学士.妇女寒衣募捐游艺会以后[N].新新新闻,1938-11-23(8).
[52]名学士.开支愈少愈好[N].新新新闻,1938-11-24(8).
[53]周正之.征募寒衣一点意见[N].新新新闻,1939-10-04(8).
[54]东鳞西爪[N].新新新闻,1939-10-04(7).
[55]剧院拒绝加收寒衣捐[N].新新新闻,1939-11-02(10).
[56]娱乐寒衣捐问题未解决[N].新新新闻,1939-11-05(10).
[57]电影应该停业[N].新新新闻,1939-11-07(8).
[58]东鳞西爪[N].新新新闻,1939-11-11(8).
[59]成都社会概况调查[J].社会调查与统计,1944,(4).
[60]黄裳.关于川剧[G]//曾智中,尤德彦.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
[61]诵数.在后方的人应该怎么干[N].新新新闻,1937-09-01(14).
[62]李笑非.忆抗战时期成都三益公艺员军训连[J].四川戏剧,1990,(3).
[63]洪深.哀红梅[M]//洪深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64]田禽.中国戏剧运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责任编辑:凌兴珍]
Save the Nation or Entertainment: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Chengdu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E Ren-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As the major public entertainment in Chengdu, the traditional opera was facing a strong criticism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from the local newspapers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theater was constructed as an opposite side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national salvation discourse,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dustry in Chengdu tried hard to perform the anti-Japanese opera on one hand, in order to mask its entertainment proper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devote to the raise fund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tertainment. However, all the exertion couldn’t revers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alvation, public entertainment was changed, but this change was limited. The entertainment, 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 was onc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opera may face a crisis of survival.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dustry; Chengdu; theater; entertainment; national salvation;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收稿日期:2015-12-04
作者简介:车人杰(1990—),男,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J8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6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