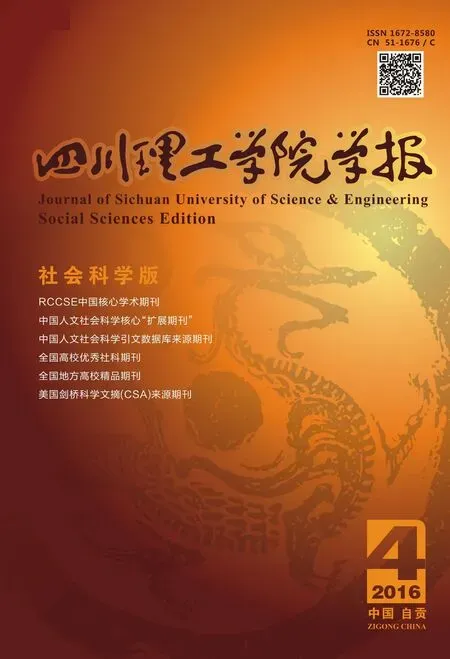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本土化特色
刘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成都 610000)
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本土化特色
刘星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成都 610000)
在中国电影产业格局日渐优化的当下,悬疑惊悚片以低投入、高回报、产量大而备受关注,遗憾的是悬疑惊悚片的质量却一直发展保守、缓慢。受中国内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观众心理诉求的影响,中国的悬疑惊悚片自出现就具有强烈的本土特色,网络的无国界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观众的审美体验,这无意中提高了观众对内地悬疑惊悚片的要求,增加了内地悬疑惊悚片的发展难度。内忧外患下,更好的“本土化”成为悬疑惊悚片作为舶来品扎根中国市场的最佳手段。在中国悬疑惊悚片中,鬼怪文化、儒家、道教、佛教文化是独有的文化特色,东方美学原则不自觉渗透在视听语言中,传统戏剧思维影响着剧作结构,但当下中国的悬疑惊悚片总体依旧呈现出“本土化”不高级的现象——文化特色不突出、视听语言风格混乱、剧作缺乏新意,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焦虑没有通过视听手段和剧作很好地在悬疑惊悚片中得到表达。本文通过对当下中国悬疑惊悚片中文化特色、视听语言特色、剧作特色的“本土化”程度的分析以及悬疑惊悚片在中国发展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的解读,为中国悬疑惊悚片深化“本土化”提供参考。
悬疑惊悚片;本土化;文化特色;视听语言;剧作
DOl:10.11965/xbew20160409
纵观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悬疑惊悚片因低投入、高回报、产量大风头强劲,遗憾的是悬疑惊悚片质量却一直发展保守、缓慢,这也让悬疑惊悚片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几乎和西方的悬疑惊悚片同时起步,但受中国内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观众心理诉求的影响,中国的悬疑惊悚片一直是“戴着镣铐”的舞者,这也让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呈现出独有的本土化特色。
一、悬疑惊悚片的定义
恐怖片几乎是电影诞生便随即产生的,在哥特小说、狂飙美术运动以及现代派意识流文学的文化土壤下,欧美各国的恐怖片(Horror)迅速兴起,魔鬼、异形、杀人狂、僵尸、狼人、吸血鬼等虚拟恐怖形态也随之产生。随着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出现,恐怖片势头更为强劲,而惊悚片(Thriller)就是“由电影史上最早形成风格的类型片之一的恐怖片发展、派生而来,是恐怖片的一个重要的亚类型”[1]。1960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Powell)在《偷窥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精神病患者》中都引入了精神分析学说,意味着现代学说引入悬疑惊悚片。惊悚片通过声光布景制造非理性刺激,通过使观众在无法预测的深度刺激中精神退化,从而达到忘却现实烦恼的精神疗效。从词义上分析单词“horror”和“thriller”,两者都有“恐怖”的含义,但“horror”偏重“惨状”“嫌恶”的意思,“thriller”偏重“毛骨悚然”的心理体验,由此可见,相对于注重血腥暴力效果的恐怖片(Horror),悬疑惊悚片(Thriller)更注重悬疑情节带来的智力挑战、惊悚气氛中情感的宣泄以及极端境况中人物内心的扭曲异化,他给观众的快感就是那份想看的欲望大于不敢看的胆怯的刺激。
二、悬疑惊悚片的历史与现状
“人类本能的欲望和压抑的变态成为了恐怖片最重要的内在心理基础,使电影制作者和观众都能通过恐怖、惊悚和宣泄,在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展开交流与对话。”[2]西方的悬疑惊悚片深受基督教和吸血鬼小说的影响,有很重的屠龙和古堡情结,随着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取代道德,导演们开始借助悬疑惊悚片思考社会问题;日本的悬疑惊悚片以民间的鬼怪文化为土壤,擅长通过各种灵异现象来制造惊悚效果,缓慢的故事节奏、平淡的对白、狭小封闭的空间、日常的物件……都是日本悬疑惊悚电影制造惊悚效果的常用手法;泰国悬疑惊悚片的思想和气质则受到佛教教义的深刻影响,“色不异空”使鬼魂在泰国电影中日常化,“因果相续”使泰国悬疑惊悚片的结局往往带有宗教归化的意义。寻根溯源,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文化根基则来自于中国的玄秘文化。中国自古对恐怖的标准与西方就有差异,从《聊斋志异》等古代鬼怪小说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妖魔形象多来自民间文化中的奇闻轶事,少有类似西方僵尸、异形、吸血鬼等血腥暴力丑怪形象出现。
19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兴盛之际,中国电影人费穆、马徐维邦等也开始了对惊悚片的探索,先后产出了《情场怪人》《夜半歌声》《狼山喋血记》《春闺断梦》等大量佳作。这些影片风格上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创造性的运用歌剧咏叹调、雷电声、呐喊声、乐队演奏声等声音元素以及倾斜、变形的镜头。同时民众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现状的惊悸、躁动与不安都在这类影片中得到抒发,从一开始,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就与社会心理紧紧相扣。在中国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中,悬疑惊悚片注定只是先锋尝试,难以进入主流,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秉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变成了“人民电影”,以发挥教化功能为主,悬疑惊悚片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神出鬼没》《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等谍战片、反特片中,融入了许多富有惊悚效果的视听手段,算是悬疑惊悚片在夹缝中的挣扎,也为现在悬疑惊悚片与谍战片结合发展成有本土特色的谍战悬疑惊悚片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悬疑惊悚片才逐渐重回中国电影市场。1980年的《神秘大佛》揭开了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的封印,随即的《恐怖夜》《鬼妹》《危情少女》《雾宅》都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潮中导演们表达个性的欲望。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大发展以及观众释放焦虑的诉求,中国市场对悬疑惊悚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悬疑惊悚片虽整体票房不高,但从票房和投入比来看属于高回报的电影类型,这也激发了更多的资本进入悬疑惊悚片制作。由于中国内地审查制度对电影中血腥暴力镜头的限制,中国内地没有真正的恐怖片,只有悬疑惊悚片,虽然审查制度依然是内地悬疑惊悚电影发展的首要限制,但商业价值加上新媒体的迅猛势头,使得近年内地的悬疑惊悚电影在形式、内容上都有很好的突破和前景。
三、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文化特色
在欧美恐怖片中常见撒旦、恶魔作为恐怖之源,但在中国悬疑惊悚片中,鬼魅魍魉才是东方人的恐惧对象,不同的文化语境会削弱文化理解力和审美诠释力,这也是《女巫布莱尔》横扫北美却在亚洲地区反响平平的原因,所以要让悬疑惊悚片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开枝散叶”,必须要以中国文化作为沃土扎根,中国独有的鬼怪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都是中国悬疑惊悚片很好的“肥料”。
与日本来自怪谈文化的鬼文化不同,中国的鬼文化来自祭祀、占卜,从上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祖先就信奉肉身死亡但灵魂不灭,信仰、祭祀灵魂。进入奴隶社会后,鬼神文化更成为统治阶级压迫民众的工具。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鬼怪的篇章大多是当时人们对一些现象的好奇,这种“好奇”也成为恐怖文化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依托形态。“当人们在自己力所不能及,而又不愿意轻信某种理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理解或想想的权利。”[3]东汉《风俗演义》中就设有《怪神篇》,明代又有了《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多次被日本小说家改编,对日本恐怖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聊斋志异》算是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的鬼神小说,《画皮》《聂小倩》等诸多篇章都被改编成经典的影视作品。鬼神主角多为女性,衣着也多为象征死亡的白色或鲜血的红色,少有西方血腥狰狞的形象。广电总局明确要求中国内地的电影不能出现“怪力乱神”,但又允许《西游记》《聊斋志异》《搜神记》等经典文学著作翻拍成影视作品,所以古典文学著作可以作为中国内地悬疑惊悚古装片的重要题材来源。
在儒家思想中,对祭祀活动重视度极高,侧面可见儒家对鬼神也是承认的,但在“不语怪、力、乱、神”“达则兼齐天下”的指导下,所有文本都必须要有“惩恶扬善”的教化意义。在“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庸思想引导下,即便是《画皮》中的妖,只要她所表现的是真爱之情便可以让人抹杀妖与人的界限,成为符合人们接受的美的化身。“重务实,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则让中国人对“鬼神”保持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实用功力态度,这也让中国的鬼魂少了些恐怖色彩。综上可见,中国的鬼文化深受统治阶层思想的控制,如同今天中国的悬疑惊悚电影一样,都是戴着镣铐跳舞。
中国的道教、佛教对中国悬疑惊悚片也有深远影响。《京城81号》一开头就引出了佛教中“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八苦,还引入了冥婚、还魂、轮回、蜕尸等中国传统鬼文化中的概念来制造惊悚氛围。《绣花鞋》中也出现了“头七还魂”的说法,也有作为冥界符号的彼岸花出现。借鬼魂之说营造惊悚氛围的悬疑惊悚片更是数不胜数了。在香港,盛行着七八种宗教,众多的宗教信奉者为香港悬疑惊悚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观众基础。香港盛行一时的“僵尸片”中“僵尸”的形象就是恐怖形象本土化的一个成功典范。“僵尸”这一恐怖形象借鉴了西方的吸血鬼脸色惨白、夜间出没、吸血为生等特点,但他又受制于黄符、桃木剑、阳光等中国化的宗教信物。
四、中国悬疑惊悚片的视听语言特色
英国的悬疑惊悚片追求严密的逻辑推理,韩国则擅长用唯美的声画给观众精致的视听体验,日本常利用日常物件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冲击,泰国喜结合本国独有的风情,让惊悚也变得有地域特色。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在视听语言上对以上各国优秀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但融合、移植或本土化很好的例子似乎还没有。视听语言缺乏新意也成为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质量一直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悬疑惊悚片产生至今,仍然延续着用快速反应、特写、主观及跟拍的镜头来烘托气氛、推动叙事的特点,灵活的镜头剪切,可以极大增强惊悚氛围。《笔仙》中就大量的运用了全景加大特写的经典镜头手法制造惊悚效果,全景给人荒芜寂静的氛围铺垫,紧接一个大特写,快节奏转换的强烈对比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使观众在落差中获得类似死亡的极端体验,产生观影愉悦。小艾的慌乱中,紧接小孩儿的眼睛的特写,特写镜头吸引观众注意,预告被摄物体的与众不同,暗示危险的降临,眼神里的仇恨和诡异让人预感到不详的威胁,紧接着一个摇晃的全景,让人有在偌大空间被窥探无处躲藏的虚无感。中国悬疑惊悚片的配乐发展尤其滞后,大多采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留白。在没有更好的配乐选择下,这种“静音模式”可以让观众更好的集中精力,细节被放大,“这种高度注意力的审美期待下,观影者与画中人物宛若置于同一空间,从而达到身心认同”[4]。比较遗憾的是中国的悬疑惊悚片至今基本没有采用原创音乐或配乐比较出彩的代表作品。
在内地悬疑惊悚电影里老旧的环境、封闭的空间、昏暗的灯光组合已成固定套路,对观众而言没有悬念的固定声画组合很容易堕落成故弄玄虚。《床下有人》中,一开场就是大雨的夜晚、闪电下的旧楼、滴水的龙头、篮球落地的声音等一连串充满惊悚元素的试听冲击,但看到最后观众发现这些元素既不是为后文做铺垫的“悬念”,也不是什么令人背后一凉的有新意的“惊悚”,难免让观众大失所望。“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已在内地悬疑惊悚片中泛滥,《枕边有张脸》《孤岛惊魂》《绣花鞋》等电影的惊悚都显得缺乏诚意。
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在人物造型上从单一丑陋到趋于日常化。早期电影里的恐怖形象很固定——飘逸的长发、煞白的脸、耷拉的舌头、流血的眼睛、扭曲的身体等等,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以及对恐怖的深层认识,恐怖不再是传统魔、鬼、丑、怪的形象。以《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为例,原著中女鬼剥腹取心的厉鬼形象深入人心,87版就曾因为形象太过恐怖被禁播,后来2005版中的女鬼就只是半边脸被毁容的形象,但仍缺乏些许美感。韩国2003年上映的《蔷花红莲》,叙事节奏按照好莱坞模式推进,但同时延续了韩国电影一贯画面唯美、服装精致的风格,这种结合对东方观众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和视觉体验,对欧美观众来说贯穿始终的东方视觉美学风格也充满了吸引力。在2008版《画皮》中,也做这样的本土化设计。小唯的服化摒弃了一贯扭曲、幽暗的风格,造型冷艳精致、服饰华美,场景上也选择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江南水乡和苍凉大漠,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壮美共同勾勒出古朴清冷的画面质感,大色块的运用制造出风月无边的梦幻效果。由此可见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如何以中国的美学风格来讲东方的神秘故事,还有很大的可发挥空间。
五、中国悬疑惊悚片的剧作特色
与恐怖片主要靠血腥暴力的画面吸引观众不同,“故事”是悬疑惊悚片的灵魂。如何设置悬念、如何解开秘密,是悬疑惊悚片能否精彩的决定因素,主题上除了对传统“复仇”母题的开发,中国的悬疑惊悚片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的流变,并开始杂糅进其他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悬念的设置
1.叙事性悬念
“根据现代动力心理学的研究,常人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一件事,专心致志地介入其中的最长单位是十一秒,超过这个时间就需要主体采取强制措施。这种强制对篇幅较短的作品自然不成问题,但在阅读篇幅较长的作品时则是个障碍,因为过多的强制会使心理产生疲劳。”[5]所以大电影必须不断设置悬念,对观众而言,悬念是吸引他继续观影的冲动和欲望;而对创作者来说,悬念是推动故事展开的动能。《黑楼孤魂》中,接二连三的出现的悬念不断的推动着叙事,谁害死的小菊?导演和此案件有何关系?女演员为什么能感觉到小菊的悲伤?一个个的谜团中,观众随主人公一起变得敏感而小心,随着真相的逼近,我们不知道真相带来的是祸是福,紧张气氛也达到最高值。在中国内地的悬疑惊悚片里不能出现妖魔鬼怪、孤魂野鬼,所以创作者只有通过这些扣人心弦的悬念营造惊悚。
根据“悬疑大师”希区柯克的“麦格芬(MacGuffin)”手法,悬念和情节应该来自于一个虚无的东西,如果过分写实就会导致麦格芬失效,观众就会对角色动机、故事由来以及行为逻辑的真实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相反在麦格芬有效的故事背景下,观众根本不会关注角色的行为逻辑,为了使观众“移情入梦”,悬疑惊悚片的“疑”和“惊”则该集中在主人公在面对危险源时是如何完成冒险和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午夜火车》中,从来历不明的信开始,随着列车前进,哭泣的女孩儿、怪异的乘务员、神出鬼没的红毛、奇怪的中年妇女……一个个诡异的人物陆续登场,观众的关注点不再是主人公杨洁为何就登上了这列车,而是已在车上的杨洁将如何与这些诡异外力抗衡。
中国内地电影中不能出现怪力乱神的规定让“鬼”退出了电影荧幕,但如果把悬疑惊悚片中的种种异像统统归结到“装神弄鬼”,难免有敷衍了事之嫌,于是“精神创伤”成了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电影的一个新出口。主人公们敏感多疑,遇到刺激便启动心理防御机制,在最后揭秘时,发现前文中的惊悚元素“常常源自某种痛苦的童年记忆或心理创伤”[6],影片中的“灵异现象”是主人公遗忘、投射、否认的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外化,这类影片“随之发展成了一种新的类型电影——具有中国特色的恐怖片亚类型——笔者将其称为‘心理创伤惊险片’”[7]。《笔仙3》中媛媛就是因为在经历一系列悲剧后选择遗忘来逃避伤害。媛媛敏感而神经质,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总是在她脑海里不断闪回。影片通过对媛媛潜意识、意识的交错表现制造悬念、营造紧张氛围,最后一个个片段拼凑出完整的往事,影片结尾主人公和观众都从紧张步入松弛,主人公心结解除,观众得到合理的解释。《地下室惊魂》《救我》中也把精神病患作为电影题材,人气较高的《咒·丝》《怖偶》也对受到“精神创伤”而人格分裂的群体进行了关注,但是“精神创伤”并不是解救内地悬疑惊悚片的万能药。《床下有人2》中,故事设定为医科学生唐玉松因为被好友骗了钱便决定对他施联体手术来抒发自己“好朋友间不该有背叛”的呐喊,先不说一部大电影单靠联体手术来撑起“朋友间不该有背叛”这一主题有多单薄,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把“被好朋友骗了钱”作为主人的“精神创伤”设定,是不是也略显牵强。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催眠大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将电影中每一处细节都变成一种等待受众解码的文本,既让观众觉得科学合理,又使当下人们更加关注心理问题,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促进身心健康”[8],这才是“精神创伤”的正确打开方式。
2.符号性悬念
对中国观众来讲,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奇特的怪兽生物都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你去看,而是引导你去想象”[9],通过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里发生的不可知变化才最让人慌乱。老旧的医院、雨夜的学校、郊外的屋子……这些先天具有惊悚因子的荒凉幽闭空间似乎成了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的标配场景。意象在国内的悬疑惊悚片中似乎也被固化,红色的高跟鞋、沉默不语的小孩、深夜的野猫……这些意象符号的确能引发观众丰富的恐怖想象,但国内悬疑惊悚片长期、反复的使用这些符号,过度消费和同质化严重使得这些符号也就失去了原本“惊悚”的含金量。也有影片试图模仿欧美国家悬疑惊悚电影,这样的设置一方面很容易勾起看国外悬疑惊悚片习惯了的观众的共鸣,但一方面反映了国内悬疑惊悚片原创力的缺乏,把场景全盘移植到国内悬疑惊悚片身上,没有进行本土化加工,缺乏空间文化隐喻。在《催眠大师》中,创作者也加入了很多西方心理学中的符号——旋转的楼梯、黑白格子图案、螺旋式的挂画等。创作者在治疗室内符号化的摆设、徐瑞宁反常的举动、任小妍被催眠的场景中连环设置悬念把故事推向高潮,最后剧情大反转,原来是任小妍拨动了时针催眠了徐瑞宁。创作者基于对心理学的尊重以及了解从心理创伤的角度“设秘”成立、“解密”环环紧扣,影片中的心理学符号把电影中每一个细节都变成一个可以解码的文本,全剧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可谓本土悬疑惊悚电影悬念设置的惊喜之作。
(二)主题的设置
欧美日韩的系列惊悚片,长久以来有稳定的票房表现,其根源在于其除了对惊悚形式的不断创新,同时没有放弃对影片思想性的挖掘。韩国导演金成浩就曾表示韩国近年来惊悚片产量高的根源是社会压力大,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录》中,导演就对军政府时期进行了反思,彰显着人文情怀。在美国电影《源代码》中表彰了远在中东地区军人为国家做的贡献。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也出现过一次惊悚片热潮,把战后的民族虚无感和挫败感在其中抒发。导演把社会及民众心理的变迁融入电影,观众在导演引导下对影片进行细致的逻辑推导,进而对社会、人性产生反思是悬疑惊悚片不可放弃的阵地。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也乐于展示他对人心理世界的解读,他设置的悬念更像是主人公内心焦虑的具象化表现,让我们由主人公关照自己,与潜意识、意识、无意识对话。而部分导演为了通过审查的功利心,强行把结局最后走向了科学释疑、传播“正能量”的道路,影片中便常出现结局与前篇衔接不自然、不贴合的毛病。不过可喜的是,这两年国内悬疑惊悚片也开始关注人性、社会。《京城81号》透过民国那段被伦理秩序破坏的爱情反思当代这个自由开放的年代,我们的爱情又被哪些因素阻隔,影片还对“求而不得”进行反思——莫宣求而不得的婚姻、根叔求而不得的家园、霍连修求而不得的陈蝶玉……观看悬疑惊悚电影时,主人公在极端环境、境遇下的行动以及心理状态,很好的呼应着荧幕外观众面临社会压力下无从选择的境遇时的状态。《楼》中,原本要去探寻鬼楼真相的人最终发现,一切都是房地产公司为了独占楼盘设下的阴谋。《笔仙惊魂》中一连串因为请笔仙而发生的诡异事件,不过是凌菲儿为了争取女二号陷害好友的精心设计。人心,此时原比面貌丑陋、无所不能的鬼怪恐怖。这些对人性的质问与思考,都是来自于人们对快节奏生活的焦虑与不安,更多的悬疑惊悚电影开始聚焦社会热点,但这种尝试还停留在关注,哪怕是《催眠大师》也止步于呈现心理问题,而对于影片中涉及的幼童领养问题、心理咨询市场规范化等问题依然显得力道不足。
“复仇”是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的一个重要母题。与欧美国家惊悚恐怖片中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主人公不同,亚洲地区惊悚恐怖片中的复仇多是个人的。日本电影《午夜凶铃》中怨念不灭、循环往复复仇的贞子,折射出亚洲金融危机下日本人对前途的绝望。从泰国的《鬼影》到《恶魔的艺术》可见,泰国从母系氏族向男尊女卑社会转变过程中女性的焦虑也在寻找出口。在中国,为姐姐复仇的小涵(《夜半梳头》)、为爱人复仇的张宇(《笔仙惊魂3》)、为自己报仇的白雪(《诡替身》)等一系列复仇角色,在深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的中国观众中极易对因亲情、友情、爱情被破坏而进行的复仇产生心理认同。虽然容易认同,但不代表中国观众会因此盲从,有的悬疑惊悚片设置的人物自带复仇属性,人物本身并没有鲜明个性作为行动的驱动力,观众很难对人物行动信服,这里就不得不再次列举《床下有人2》的唐玉松,可谓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人物设置失败的典范。关于复仇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81号》中,影片展现了冤魂复仇的情节,并且最后导演也未对此进行强行合理化,这部片子的成功过审给出了审查制度有所宽容的信号,终于悬疑惊悚片看到最后不再只是因为做梦或发疯了。
(三)杂糅的类型
因为中国电影类型发展的不完全,也给了中国悬疑惊悚片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叙事方法上除了遵循传统叙事原则,创作者还尝试模仿国外悬疑惊悚电影的叙事手法。《咒怨》中毫无关系的人因为都来过同一个房子而受到诅咒被联系在了起来,中国导演也在尝试类似《咒怨》的段落式叙事,如李碧华导演的《迷离夜》《奇幻夜》就是采用了类似的段落式结构。《致命请柬》则采用多线叙事,电影中的七个人都因为一封请柬来到郊外的别墅,这七个人都曾与前阵子跳楼的一个女孩有过交集,自杀女孩儿的姐姐把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观察,七个人多线叙事把关于女孩死前后的事组成一场罗生门。《夜惊魂》还较成功的尝试了套层结构,影片中不能出现的鬼魂在影片中的戏里出现,影片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在拍戏过程中展现,戏中戏的结构给观众带来了更多层次的审美体验。《黑楼孤魂》里也是导演所拍的故事、文革时被残害的小女孩的故事、金佛的故事戏里戏外相互交融、影射,套层结构极大的增强了作品的丰富性。
对翻墙看国外悬疑惊悚片培养起试听素养的中国观众来说,如今再进影院看本土悬疑惊悚片,必然不会对电影中生硬的情节、唐突的悬念、敷衍的结尾买账。类型杂糅已经成为电影保持活力的一个大趋势,和其他类型杂糅是悬疑惊悚电影一个不错的选择,《暮光之城》系列就是将爱情和惊悚融合的成功之作。这两年国产小成本喜剧走俏,“一些青年导演随意地在小成本惊悚片中加入喜剧、动作等类型的桥段,使国产小成本惊悚片更多呈现出山寨闹剧的特征。以至于当很多观众在看完这些影片时,不是恐惧不安,而是愤怒或哂笑。”[10]2016年愚人节上映的惊悚喜剧《撸鬼屋》中,人物按照角色定位根据谐音取名字:伊叶晴(一夜情)、鲁亚路(撸呀撸)、贾作乐(假作乐)、甄寻欢(真寻欢),这种取名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一再出戏,电影基本依靠一个个段子拼贴出一部电影时长,影片最后的效果就是该惊悚的地方惊悚得很搞笑,该搞笑的地方搞笑得很惊悚。反倒是2008年上映的《画皮》把魔幻、惊悚、爱情多个类型糅合,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有不错收获。影片将小唯原著中“狞鬼”的形象改编得娇媚妖娆,王生由原著中的胆小羸弱的书生改编为骁勇善战的将军,故事矛盾也从原著的道士与妖怪转为佩蓉、王生、小唯三人的爱情纠葛,这些改编无疑更符合现代审美和观众观影诉求,增加了电影的可看性,也增大了受众群体。
六、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新火花
(一)针对受众群体的变化所做的改变
根据《2015中国电影产业观众观影行为分析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观众中“85后人群总占比达到70.46%……专、本学历占比接近七成”[11],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主流受众集中在都市青年群体,都市青年释放社会、生活压力的需求也成为带动悬疑惊悚电影市场的直接原因。商品属性日益显著的电影也在根据受众群体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近年来的本土悬疑惊悚片中,主人公职业多设置为白领、大学生、作家等都市角色,在获得观众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为了保持观影的陌生感,环境通常设置在荒野、古宅、孤岛等有别于都市的环境,在两个维度上满足观众的诉求。80后一代是游戏的一代,为了适应受众群体思维方式的变化,悬疑惊悚电影中也融入了很多游戏元素——《床下有人》中出现了大量的类似“自从我得了精神病,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的网络语言;《绝命岛》采用了网络游戏闯关的形式叙事,让人物通过闯关决定生死和最后的命运;《笔仙惊魂》则以在年轻人中盛行的招灵游戏“笔仙”为背景展开故事的。
中国悬疑惊悚片观众是被国外悬疑惊悚片“养大”的,所以这两年本土悬疑惊悚片中不自觉也表现出了国外R级影片的因子。悬疑惊悚片中常出现女主角洗澡、湿身、穿着单薄的镜头,甚至《模特魅影》直接把主人公职业设定为模特,堂而皇之的出现大量内衣模特尽情展现的女性身体曲线的镜头,这些镜头的喧宾夺主以及悬疑惊悚元素的缺失常常让人忘了看的是一部悬疑惊悚片。情色作为卖点的确会增加影片的话题性,但这不能成为本土悬疑惊悚片导演们为求票房自暴自弃的手段,否则会把中国的悬疑惊悚片以及悬疑惊悚片观众都引入歧途。
(二)警匪片与谍战惊悚片的复兴
受中国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复合类型成为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电影要发展的捷径,谍战片、警匪片、黑帮片、侦探片与悬疑惊悚片都有较高融合度,但在内地的政治环境下,黑帮片和侦探片是没有生存土壤的,所以谍战片和警匪片与悬疑惊悚片融合是最符合中国市场的。
从鸳鸯蝴蝶派创作“国难小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谍战故事,再到文革后谍战片的第三次高潮以及新世纪后富有娱乐性的新谍战片,间谍身份的复杂性、伪装性、神秘性天生注定谍战片与悬疑惊悚片的“门当户对”。2009年上映的《风声》可谓给谍战与悬疑惊悚融合做了一个完美示范。1942年,在汪伪政府举办庆祝国民政府成立30周年的仪式中,一名汪伪政府的要员被杀,这次事故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伪军与日军为了找出“老鬼”,把嫌疑最大的顾晓梦、吴志国、李宁玉、白小年、金生火五人关在裘庄进行心理和肉体的严刑拷打。谁是“老鬼”成为牵动整部影片最大的悬念,过程中中共抗日分子与敌人斗智斗勇,既要防范被陷害、保全自己,又要找出队友、辩出敌人,整个过程悬念四起险象环生。除了将悬疑惊悚与谍战元素有机结合,还在内倒叙、全知视角叙事、二元矛盾设置方面下足功夫,锦上添花。之后的《听风者》《触不可及》等一系列电影都对谍战和悬疑的融合做出了好的尝试。
峨影厂1988年拍摄的《恐怖夜》是悬疑惊悚片与警匪片早期结合比较成功的案例,内地与港台合拍风兴起之后,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无间道》系列和《窃听风云》系列更是借助香港高品质警匪片制作水准开启了内地悬疑惊悚片新的票房点。《无间道》系列中在对两个卧底做梦都怕别人拆穿身份的局促的刻画中、对他们挣扎着离开所处的不辨是非的境地的描写中、对当下社会中人们身份定位茫然的探讨中,给观众带来了警匪、悬疑、惊悚几大元素碰撞出新的审美体验。
(三)内地与港澳台的合拍片
内地与香港虽分离发展多年,但内地文化和香港文化都是源于中原文化,“21世纪,内地与香港的合作进入了后合拍时代,未来华语地区电影工业的地理分割即将越来越模糊,合拍的物理结合将越来越变成后合拍的化学反应。国产片、港产片的称呼已经很难表明影片的真正身份,华语片将成为未来合作的共同基础。”[12]尤其在CEPA签署后,合拍片从原本香港的单项文化输出发展到现在更注重内地的主流情感,两地形成交流互动的关系。
香港产出过僵尸系列、《开心鬼》系列、《异度空间》等大数量高质量的恐怖片、惊悚片,悬疑惊悚片发展比内地早,但香港电影人来内地合拍还是需要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首当其中的就是两地尺度的不同,其次是文化差异。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找题材是不错的出路,以古装作为大标签,对两地观众都没有障碍,王祖贤版《倩女幽魂》是众多影迷心中的经典,2011版中香港演员及导演的加入与内地资本的注入也成就了刘亦菲版的《倩女幽魂》。最近大获好评的《催眠大师》又是合拍片的另一种尝试,故事设置在一个架空的城市,创作者有意将这个现代的、都市化的故事的地域性模糊掉,以适应各区域观众。把任小妍设置为一个被香港夫妻领养的女孩,也让莫文蔚的香港口音得到解释,解决了合拍片中演员口音使观众跳戏的尴尬。
(四)微电影惊悚片的兴盛
“新媒体的流行,打破了传统媒体‘中心’—‘个人’的辐射式传播格局”[13],个人作为传播者辐射影响,这极大地降低了电影的门槛,促成了微电影的流行。微电影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格局,微电影也从最初的微时、微制作、微投资发展到如今可以大投资大制作,仅保留了“微时”这一便于在新媒体传播的特性。
网络相对宽松的播出环境,以及悬疑惊悚片与微电影受众群的高度重合,使得悬疑惊悚片类型的微电影在网络上蓬勃发展。如果说中国悬疑惊悚片在大荧幕是被绑着镣铐跳舞,那网络平台似乎给了中国的悬疑惊悚片一片更自由的舞台。《亲切的贞子》对日本恐怖片中经典恐怖形象“贞子”进行解构,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男主角在与其抗争中笑料百出,最后竟然两人产生感情,生儿育女。这部影片既有悬疑惊悚成分,又巧妙的融入了喜剧元素,在短短十几分钟内牢牢控制着观众的情绪。原创悬疑惊悚片《死亡烙印》、校园悬疑惊悚片《我在你身边》的超高点击量,也意味着网络平台让更多的草根创作者加入到推进中国悬疑惊悚片发展的大潮中。
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审查制度的影响,中国悬疑惊悚片的发展一直比较艰难,一直到今天似乎也是因为他的高回报比让电影人和观众才对他重唤激情。悬疑惊悚片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越是想在全球化的包裹下有竞争力,中国悬疑惊悚片越是要挖掘本土特色、凸显本土魅力,既满足中国观众的审美,又能勾起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但当下中国的悬疑惊悚片无论是剧作还是试听方面,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焦虑的表现都还显得力不从心。如何更好的借鉴好莱坞一些通用的创作模式、日韩泰的本土化经验,并在其中渗透入中国元素,“找到中国人的真实恐惧和深层忧虑,然后把他化为个体的忧虑和恐惧,并用形象化的方式具体的表现出来”[14],是中国悬疑惊悚片未来要走的路。
[1]卢燕,等.聚焦好莱坞文化与市场的对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5.
[2]蔡卫,游飞.美国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269.
[3]陈梦然.论惊悚片的特质及美学价值[J].理论与创作,2007(4):108.
[4]丁文文.恐怖镜像的诗意表达——安兵基惊悚电影叙事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23.
[5]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39.
[6]刘起.恐惧炼金术——浅谈欧洲惊悚片[J].当代电影,2011:2.
[7]向乃禾.幻由“心”起·乘“险”抵巇——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华语电影中的心理创伤惊险片[D].广州:暨南大学,2013:1.
[8]何晓诗,游溪.惊悚片:2014之后当如何?[N].中国电影报,2014-08-15.
[9]朱桓墨.浅谈东西方惊悚片的对比与发展——以欧美和日本的惊悚片为例[J].大众文艺,2016(4):180.
[10]杨柳.并非类型的类型——国产小成本惊悚片的问题及出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3):144.
[11]2015中国电影产业观众观影行为分析报告[R].(2015-06-01)[2016-07-07].http://www.docin.com/ p-1276166698.html.
[12]尹红,何美.共造后合拍时代的华语电影——中国内地与香港电影的三十年合作[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3):30.
[13]缪子梅.“碎片化”视角下运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思想引领策略研究[J].2014(11):121.
[14]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J].电影艺术,2003(4):8.
责任编校:梁雁
The Localization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Suspense Thrillers
LIU Xi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00,China)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ation of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pattern,the suspense thriller has got great attention due to its low input,high return,and high yield.Unfortunately,its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ervative and slow.Impacted by the Chinese mainland cultural background,ideology and audience psychological demands,the Chinese suspense thriller has had strong localization feature since its appearance. Internet without the concept of borders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Chinese audience's aesthetic experience, which inadvertently increases the audience demand for suspense thriller and the difficulty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mainland.Under this situation,better"localization"is an optimal approach for the film to take the root foot in the Chinese market.In the Chinese suspense thriller,the ghost culture,Confucianism,Taoism,and Buddhism cultures ar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Oriental aesthetic principles unconsciously appear in the audio-visual language and the traditional drama thinking affects the drama structure.However,the present Chinese suspense thriller overall has the phenomenon of low"localization"-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outstanding,audio-visual language style is in chaos,and the screenwriting is lack of new ideas.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anxiety are not reflected and expressed via the audio-visual meas in suspense thriller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dio-visual language,and "localization"level of the present Chinese suspense thrill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localization of suspense thrillers in China.
suspense thriller;localization;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udio-visual language;screenwriting
J901
A
1672-8580(2016)04-0088-12
刘星(E-mail7457552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