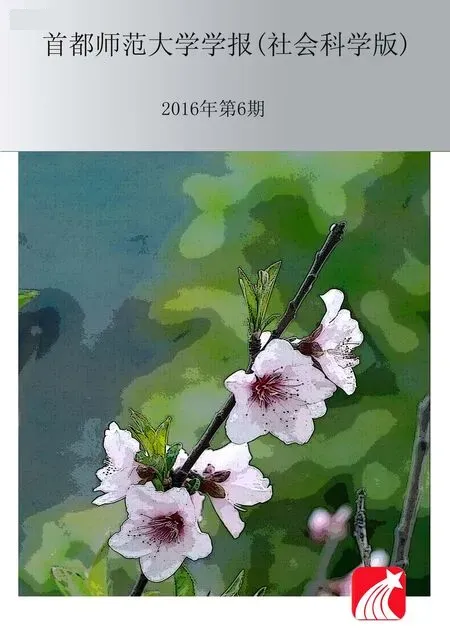怀念恩师齐世荣先生
赵军秀
庆贺齐先生70岁、80岁生日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原本大家说好今年10月给齐先生做寿,庆贺先生90 华诞。2015年12月3日先生离世,晚辈学生共同的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了,悲痛万分,永远怀念。
指点迷津
齐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但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却远远早于我跟随他读博。记得1981年初大学3年级寒假,打算毕业后考研,得知齐先生在世界史领域的学术造诣,利用回京探亲期间拜访了齐先生,以求得先生的指教。当时作为在读学生的我十分怯懦,近乎战战兢兢,但先生与我交谈后我逐渐放松。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大师气度和长者风范,领略先生对后辈求学者的诲人不倦。他问我读过哪些世界史特别是国别史的书,因当时中国学者的国别史著作凤毛麟角,中译本也很有限,我将看过的几本书一一作答后,先生还较为满意。他特别提到学习历史要心静,甘于坐冷板凳,勤奋读书。当先生得知我竟然没有读过一本英文历史著作时,指出这是很大的缺憾,并告诫我若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读英文原著。这次拜访使我大开眼界,深感先生的博学多才,并有追随先生学习的志向。回到陕西师大以后,给先生写致谢信,先生回信再次鼓励令我感动。
大学毕业因条件限制未能报考读研,但幸运的是回京工作并能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最初被分配在中国现代史专业,离开比较感兴趣的世界史,我有些失落。一次在教学2 楼走廊遇到齐先生,他询问我近况后提醒我,即便担任中国史教学也千万不要放弃外语,特别举例说如研究北洋军阀史,直系军阀吴佩孚就是被英国支持,英国为什么支持直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需要研读英文专著,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寥寥几句话的点拨,使我茅塞大开,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学习心境,探讨学习与思考问题的视角。
当时作为青年教师,我积极旁听历史系名师的课程,先后听过齐先生、宁可先生、谢承仁先生和黄一欧先生的课程,他们的课程都对我启发很大。齐先生的讲授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曾说,对历史的研究,任何人都可能有局限性,且不说阶级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肯定有。他还用苏轼诗句加以论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结论是:对历史的研究一定要保持一段距离,什么距离,即时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冷静研究,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我觉得这些话很经典,使我受益匪浅,也指导我日后的教学与学术研究。
收我为徒
1986年底,因工作需要我转到世界近代史专业,此后直接间接得到齐先生许多指导。先生给予的鼓励、批评与帮助,促进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成长。记得先生在授课时和许多场合多次强调要多读书,不倦地读书,勤奋、持之以恒地读书。他谈到因为多读书才能有联想,而灵感恰恰产生于联想之中。先生的这番话语千真万确,掷地有声。后来我的一些论文乃至科研项目的选题都来源于读书中的联想。如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帝国防御研究问题就是在看书过程中有感英帝国防御与其战前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而选择的题目。我带研究生之后也将先生这番话传授给我的学生,使他们领悟读书的要领以及与联想、灵感和思考之间的关系。我的一个硕士就是在阅读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一书的注释中突发灵感,进一步拓宽思路并查找资料确定她的论文选题“从格雷-豪斯备忘录看一战期间的英美关系”。先生这番话对我的教学也大有裨益,讲课中的即兴发挥以及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多读书的积淀,才能使课堂教学的质量更上一个台阶,给学生更多的教益。
记得我写第一篇论文“试论七年战争中英普同盟的建立与破裂”,当时认为国内对近代早期国际关系的研究涉猎不多,选题学术性很强。自己阅读查找了诸多英文资料,包括七年战争时期老皮特的演讲和书信集等。初稿完成后有些许沾沾自喜,请齐先生提修改意见。后来先生一句话惊醒我:“你以为你把资料都堆放在那里就是一篇好文章呀?”这是先生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批评,对我而言,可以说刻骨铭心,但从内心感激涕零。因为有了先生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指正,才让我逐渐学会怎样梳理与运用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论证自己的见解与观点。这不仅是日后写论文的首要思考,也成为我指导学生写作的重要告诫。另外,一般认为写论文收集资料要多多益善,乃至收集资料的脚步停不下来。针对这种弊病,先生也曾指出:“雪球不能总在滚动中,资料是无尽的。”他告诉大家恰如其分地运用资料最为可贵,深刻阐释收集资料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更为难忘的是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学院访学时,曾考虑延期读个学位回来,并将此想法告知时任系领导的陈曦文、于祥莲两位老师。她们回信告知,与齐先生商量后建议我准备回国后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喜出望外,因从不敢想象,主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的先生能收我这个近代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学生。我被先生对中青年教师的学术关怀和具体帮助深深感动。同时我也知道,这是先生对我担任3年历史系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工作的肯定与爱护。我只有以勤奋学习报答先生的培育之恩。
我曾经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中期两次聆听齐先生给研究生讲授“史学方法”课程。先生对史料的分类及各种史料的价值分析有其独到见解,这已经在他近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精辟阐述,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些论文汇集出版《史料五讲》一书,我这里就不赘言。但我想说两点:一是先生注重史料的“旁征博引”,先生既给予日记、私人信函和回忆录等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以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不能听一面之词,要讲究互证或者多方引证。先生以身示教:他讲课和作报告非常注意举例,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有时会用3个事例反复说明。不仅使听者印象深刻,而且从中领悟到深入浅出、以事喻理的重要。先生强调的多方引证对我后来探讨战前英国外交战略颇有启发。我注意将兰斯多恩、贝尔福、格雷、阿斯奎斯、丘吉尔、劳合乔治等英国决策人物回忆录、书信集及传记进行比较鉴别,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取舍。二是先生论证“小说的史料价值”,阐释小说如何能作为史料和怎样作为史料。先生特别看重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史料价值,他引用经典作家恩格斯谈及《人间喜剧》的名言:《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写出来,围绕着这些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因此从中所学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此外,先生也十分关注与肯定《水浒》《儒林外史》和明清野史的史料价值。正是先生的分析与论述,使我在教学与研究中也注意到近代史一些名著的史料价值,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拿破仑战争时期法俄关键性战争“博罗迪诺”战役的史料价值,等等。
在我写博士论文与修改论文成书的过程中,先生悉心指导并提出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与建议。不仅如此,先生百忙之中为书稿作序,序中特别提出学者的成就基本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勤奋;第二,天资;第三,机遇。先生强调勤奋是最主要的,并援引黄侃的话进一步论证:“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先生称赞黄侃是大学者,自幼聪慧过人,且都不认为天才是学者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因素,而把“辛苦”做第一位因素。他称赞黄侃一生勤奋治学,临终前一天还圈点《唐文粹补编》两卷。我从中体会先生阐述的“勤能补拙”的道理,也是对我这个“不是很聪明”学生的鼓励。当然我必须说,机遇也十分重要。学术成长道路上遇到先生的指教与提携,是我最大的幸事。
先生不仅称赞黄侃,对一代学者大师都十分尊重与敬佩。在授课与聊天中多次介绍与宣传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陈垣等诸位先生的学术成就,赞颂他们的学术精神。先生认为:学者的价值在于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科学,尽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社会。先生自己就是勤奋、严谨治学的表率与典范。他学贯中西,博闻强记,聪明睿智,依然不倦地学习与研究。即便年近90岁,仍笔耕不缀,每天伏案工作研究。他《史料五讲》中的几篇论文就是在近几年陆续发表的。他曾说,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先生正是这样做的,直至最后在病榻上,还敦促女儿为其有关纪念二战稿件的校对联系学报编辑杜平。
共同怀念
先生不仅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的两个妹妹也都得到过先生的指导与帮助。
妹妹军华是我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师,1992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她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感兴趣,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的齐先生恰巧赴港访问,积极支持她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军华回校后在全校两课开设“中华伦理课程”,受到学生的好评。军华后来主编、撰写《中华伦理》一书,得到齐先生肯定。该书申报并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军华对齐先生非常敬佩,她回忆中说到:齐先生作为长者,大师级人物,可对当代青年提出的问题,热议话题甚至是爱开的玩笑都饶有兴趣,每次交谈中都会询问这方面情况。这说明先生始终俯身向学,精神永远年轻。
妹妹军利1980年代末曾在北外纳忠先生门下攻读阿拉伯语言文学博士,纳先生指定她来首都师大聆听齐先生的史学方法课程。在听课过程中,军利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与鼓励,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有关中世纪阿拉伯史学理论。1993年军利在科威特不幸遇难。后来先生几次对我提到他在国图与纳忠先生相遇,他们都非常惋惜学习阿拉伯语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军利妹妹英年早逝。
我们姐妹都十分敬重并由衷感谢齐先生。如今,先生离我们而去。在此我代表我们姐妹共同缅怀先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先生的学术风范,令人敬仰,道德文章,永存人心。永远怀念恩师齐世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