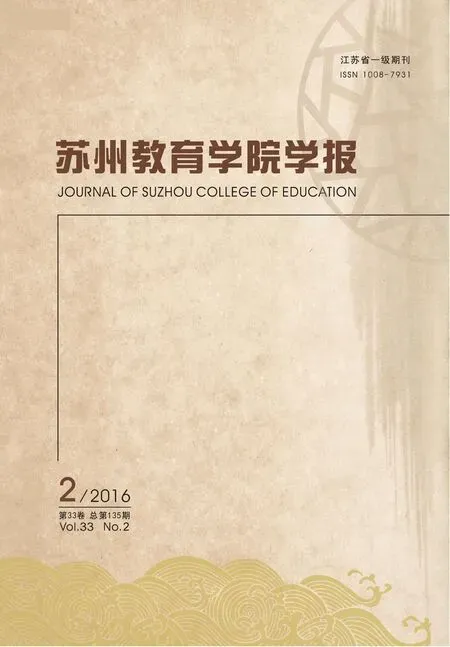蓝色乌托邦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水孩子》
张 杨(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蓝色乌托邦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水孩子》
张 杨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儿童成长的童话故事,更是一个充满了生态智慧的文本,其中所描绘的海洋世界象征着作者理想中的生态和谐之境。金斯利将对工业革命的反思落脚于对人性的反思之上,重点批判了扭曲的欲望及“人类中心主义”,并借汤姆“死亡—重生”的历程,揭示出人性完善对于生态和谐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水孩子》;生态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乌托邦;精神生态
引文格式:张杨.蓝色乌托邦—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水孩子》[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2):60-63,77.
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Joseph W.Meeker)首次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在其所著《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四年后,另一位美籍学者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生态批评”的出现意味着批评家们越来越关注文学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正如美国高校首个获得文学与环境研究教授席位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导言中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1]62-63。对生态批评对象的界定而言,有两种观点较具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批评的产生是以生态危机的出现为前提的,因此它所要分析研究的文本对象仅限于那些产生于生态危机的时代并有着明确生态观点的作品;另一种观点以美国学者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为代表,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应过分狭窄,应“包括研究所有类型的任何作品—努力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1]69。后一种观点虽然有模糊生态批评界限的倾向,但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却能从多方面汲取生态智慧,丰富生态理念,不失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一种策略。
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写成于1863年的《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被誉为世界十大哲理童话佳作之一,通过一个扫烟囱的孩子的蜕变过程,表达了作者对儿童精神成长的关注。尽管金斯利所生活的年代并未出现真正的生态危机,他也无从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2],但他已关注到工业革命对坏境的破坏及对人性的损害。汤姆的成长历程,即从“黑色的”人类世界,经过漫长的中间过渡地带,最终到达蓝色乌托邦—自由天国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如何摆脱欲望及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人性的完善的过程。其中海洋作为精神净化之场域,涤荡了汤姆身上所残留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使他到达乌托邦之地。这恰恰给处于生态危机中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从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人性入手解决问题。
一、黑色此岸:对欲望的批判
《水孩子》虽然是一部童话,但前两章为写实,作者通过汤姆的眼睛,展示了工业革命下英国的社会现状。由于煤矿的大量开采,一批批工人纷纷到来,在煤矿周围逐渐形成居住区。汤姆和格林姆思先生在凌晨三点前往哈特霍维尔府上,“他们缓慢而吃力地走在布满灰尘的黑色道路上,道路两旁是堆成小山似的矿渣,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采矿机不时发出巨大的呻吟似的响声”[3]6。(原文为英文,译文为笔者所译,下同。)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黑色矿渣侵入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致使其失去了应有的缤纷色彩,甚至代表光明与希望的晨曦都变成了灰黑色。同时,由于煤的大量供应,出现了众多如汤姆般的扫烟囱的童工,他们不仅要从自己的应得报酬中抽取绝大部分交给雇主,而且经常受到雇主的打骂与虐待。更加糟糕的是,这些未受教育的孩子耳濡目染的是成人对儿童的倾轧与对自然的征服,于是,汤姆长大后的理想便是成为像格林先生那样的雇主,拥有几个能经常使唤、欺负的童工。而受格林先生偷猎山鸡的影响,汤姆看见山鸡的第一反应便成了盘算它们的味道。在生态批评家看来,自然关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社会关系中的“强者中心主义”有着相同的本质。当人类运用科技的力量拥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之后,自然的神性与魅力便被剥落殆尽,这种从征服中获得利益的欲望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便形成了强者(富者)对弱者(贫者)的剥削与压榨。于是,不仅人类与自然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之中,而且,人类自身也存在着鲜明的对立关系。
这个黑色的、冰冷的、没有温暖的社会最终导致汤姆走向了“死亡”。当这个因扫烟囱而浑身黑乎乎的孩子误闯进艾莉的房间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来抢劫与破坏的,这种误解的本质显然是强弱对立的二元主义。那些霍尔庄园的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开始了对汤姆的“围剿”,其场面之混乱堪比追捕一只狐狸,“所有的人都跑进花园里,大喊‘抓贼’,他们相信在汤姆空空的口袋里装着至少价值一千英镑的珠宝;那些喜鹊和松鸦也一路追着汤姆,尖叫着,似乎汤姆就是一只被捕猎的狐狸,正在夹着尾巴逃跑”[3]15。在这样激烈的状况下,惊恐的汤姆躲进了树林,但“立刻陷入了茂密的杜鹃花丛中,粗大的枝条困住了他的双腿和胳膊,并不时戳中他的脸和肚子”[3]16。这些“充满恶意的”植物对待汤姆的方式正象征着自然界对人类无休止的欲望的报复。
此外,作者还通过汤姆的视角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从高高的山顶看去,一边是哈特霍维尔府所在的乡下,有着大片的树林与金色的河流;一边是烟囱林立的、始终被灰黑色笼罩的城镇。这种对比的背后是金斯利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而松鸡所唱的“世界末日就要到了”[3]18,正是他对欲望笼罩下的世界走向的担忧。于是,在金斯利笔下,人类是贪婪而永不满足的,贪婪导致暴富,暴富又激起贪婪,这种罪恶与阴暗对自然、对社会来说都不啻为一种灾难。金斯利看到了科技发展对人性的侵蚀,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即诉诸宗教。正如教堂的钟声给予汤姆以生的希望那样,宗教能够净化人类心灵,使其产生洗去一切罪孽的欲望,从而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虽然诉诸宗教的观点值得商榷,但通过人性的完善以拯救人类的观点却与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深层生态学”以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为代表,强调“总体观念”,即人属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应当“通过‘自我实现’,即发掘人内心的善,来实现人与自然的认同”[4]。汤姆的重生之路即是一种“自我实现”,他对大海中其他生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愚弄到尊重的过程,在完善人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的认同。
二、天路历程:“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
在金斯利的笔下,大自然成为汤姆获得重生的重要场域,比如小河所给予他的水孩子的生命,以及大海所洗涤后的灵魂等。其实,在前往哈特霍维尔府的路途上,自然已经多次对汤姆发出了灵魂的召唤,云雀的歌声、芦莺的啭鸣、蓝色的天竺葵、金黄色的金莲花、野生的木莓、清澈的泉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神秘的爱尔兰女人对大海的描述更是激起他无限的向往。“水孩子”这种生命形式的存在,一方面显示了金斯利丰富的想象力,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对自然的敬畏。正如书中所言:“当你谈到自己所身处的这个伟大而丰富多彩的世界时,永远不要用‘不是’或‘不可能’等字眼,因为即使最聪明的人也仅仅了解它的一小部分而已。”[3]34仅凭想象,金斯利为人们呈现出一幅绝佳的水中世界的图景,这里蕴含着他对生态多样性的肯定。此外,这种肯定还表现在对狭隘、可悲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上,如艾莉的家庭教师明明看见水孩子,还坚持否定水孩子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理论受到质疑。这种自卑而又自大的心理正是造成生态失衡的原因之一,而生态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人类对自身处境的不觉悟。小说中汤姆为寻找格林麦思先生,首先必须经过废纸岛、污水海、废物山等才能到达格林麦思所在之地,在那里,仙女们为了让孩子们不食用垃圾食物,不得不想方设法处理它们,但“她们刚把旧的垃圾食物隐藏起来,愚蠢而又道德恶劣的人们又制造出新的、绿黄色的、充满毒素的垃圾食物,他们甚至偷了科学小姐的大书以配制这些‘毒品’”[3]123。这里作者所流露出的情绪可以说是对生态启蒙缺失的焦虑。
虽然金斯利在小说中对人类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揭露,但他也十分清楚,只有人类才能拯救人类(尽管需要上帝的引导)。当汤姆真正成为了水孩子,变成水陆两栖的生物之后,他已部分忘记了之前作为人时的生活状态,但他的思想观念中仍然保留有浓厚的二元对立意识。“如果说汤姆在与他人交往时体现出‘自我中心主义’思想,那么他对海底生物的所作所为则突显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残余。”[5]比如仅仅为了嬉戏玩闹,不断追逐与折磨水中的那些生物,打破石蚕的门,寻小鳟鱼的开心等等。直到亲眼目睹了蜻蜓的蜕变过程,汤姆才开始变得懂事了。但汤姆的自我完善却远未完成,在圣白兰登岛因为偷吃糖果而浑身长满尖刺和老茧,正是欲望驱使下的人类的模样。人类为了利益而相互斗争,从掠夺大自然的经验出发,去剥削弱者,以自我为中心,以满足私欲为目的,自然的生态失衡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生态失衡,而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失衡。因此,汤姆的自我修炼过程,也是逐渐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真善美的过程,更是平衡自己精神生态的过程。特别是最后,他历尽艰险解救格林先生,学会了去讨厌的地方,帮助讨厌的人,也恰恰预示着他的道德的完善。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博物学家的金斯利在描述水中世界时又偶尔会流露出人类的优越感,这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定语词的运用上,比如刚变成水孩子的汤姆“全身有3.87902英寸长”[3]34,这种量化的描述显然是机械时代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生命本身的神圣性。金斯利的这种矛盾思想在当代生态批评家那里发展成为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肯定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地位的同时,也认为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去协调好自身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保证人类整体与长远利益的同时实现生态系统的平衡。[6]“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不仅是对“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矫正,更是对“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三、蓝色彼岸:理想的生态和谐之境
海洋自古以来就不断地被歌咏,那个浩瀚的、无垠的蓝色世界始终是那么神秘而迷人。在金斯利的笔下,大海更是成为了一种生态的乌托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汤姆的重生之旅开始于那个神秘的爱尔兰女人对于大海的描述:冬天翻腾怒吼的力量、仲夏温柔呢喃的静谧,都吸引着小汤姆。当汤姆变成水孩子之后,在水中各样生物的影响下,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到那浩瀚广阔的大海中去。最后,汤姆所到达的自由天国—圣白兰登岛,象征着金斯利理想中的人类的最终归宿,这里的生态和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一是浓郁的人文关怀。
首先,生态整体主义主张“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7]在圣白兰登岛上,每种生物都把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这恰恰与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相近。圣白兰登岛作为水孩子的家园,其自然生态当然不必说,到处都是香柏与美丽的鸟儿,而且所有的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是圣白兰登岛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海葵、珊瑚、石珊瑚维护着海水的纯净,螃蟹负责捡起地板上的碎片,水蛇则像警察一样维持治安,水孩子也一样工作,修补水草,整理水潭、海贝等,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当完成自我救赎返回圣白兰登岛后,“汤姆首先看到雪松在玫瑰色的曙光中高耸着,平静的海面上是圣白兰登岛的倒影。风儿在雪松间温柔地呢喃,海水在礁石间浅声低唱,海鸟欢叫着在海面上飞翔,岛上的鸟儿则啭鸣着在树枝间做窝”[3]134。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亲近大自然,在他们看来,自然界里的种种生物都是富有灵性的存在,“人与自然会以一种深切的生命感知的方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和谐与共鸣”[8],如云彩也会感到疲惫而酣睡,它们也会成群结队地游荡等,这样的描述将人类与大自然的其他物种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可亲可近,营造出一个美好的、童话般的生态世界。
其次,汤姆在圣白兰登岛所受教育的过程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关心劳工以及儿童教育问题的牧师,金斯利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丰富的人文性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态的关注。汤姆刚到圣白兰登岛时,思想观念中仍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残余,但惩恶仙女与福善仙女对他的教育方式与格林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她们从来不会“训斥、催促、吓唬、威胁、迫使”。汤姆承认做错了事,仙女们试图让他明白是“灵魂造就了躯体”,并且通过艾莉对汤姆产生影响,让他明白必须学会去讨厌的地方,帮助讨厌的人,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灵魂变得美丽。此外,格林先生之所以迈出自我忏悔的第一步,也正是因为母爱感动了他。
事实上,金斯利笔下的圣白兰登岛不仅是汤姆等水孩子的天堂,更是我们当下所寻求的生态乌托邦的一种范本。汤姆寻找乌托邦的经历,启发着人类应该像水孩子一样,关注自己的精神危机。对汤姆而言,大海中的圣白兰登岛成为他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残余、荡涤灵魂的重要场所。在仙女的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教育下,汤姆认识到,为了去到心中的“美丽的地方”,必须经历磨难,去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帮助自己不喜欢的人,于是他踏上了解救曾经虐待过自己的格林先生的征程,最终在一切都结束之后,真正融入了蓝色乌托邦。同样,人类若要实现自我救赎,首先要实现对自然的认同,并通过人性的完善,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从而构建起各方面都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
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家,查尔斯•金斯利已关注到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种种困境,渴望寻求一种解决之路径,并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人性”上。《水孩子》中汤姆从一个沾染了种种“恶习”的孩子,变成了乐于助人的善良的水孩子,这种“死亡—重生”历程中所蕴含的是对人类欲望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等思想。尽管金斯利所描绘的这种精神蜕变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从人性入手拯救自身的观点在后来的生态批评家那里得到了应和。正如鲁枢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有效地解决地球上的生态问题,还必须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尤其是从人类内在的精神深处找原因。”[9]在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水孩子》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不仅为我们构建出一种蓝色乌托邦式的生态和谐之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研究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
[3] 金斯利 查尔斯.水孩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 雷毅.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J].世界哲学,2010(4):20-29.
[5] 肖明义,崔丹.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解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28(9):135-136.
[6] NORTON B G.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J].Environmental Ethics,1984(6):131-148.
[7] 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J].文学评论,2009(1):63-68.
[8] 李会君.迟子建文学语言的生态美学价值[J].小说评论,2011(2):32-35.
[9]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视阈[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20.
(责任编辑:刘中文)
The Blue Utopi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ter Bab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ZHANG Yang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Charles Kingsley’s The Water Babies is not only a fairy tale about Tom’s adventures, but also a text containing ecological wisdom.The author depicted a harmonious scene in the sea world, which symbolizes the utopia in his mind.In addition, Kingsley criticized the distorted desi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anthropocentrism”.The introspection of human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ithin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f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rough the death-rebirth of Tom, Kingsley emphasizes that, only by keeping the spiritual balance can human beings arrive in the blue utopia.
Key words:The Water Babies;ecological criticism;anthropocentrism;utopia;spiritual ecology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2-0060-04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2.012
收稿日期:2015-12-07
作者简介:张 杨(1991—),女,河南叶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