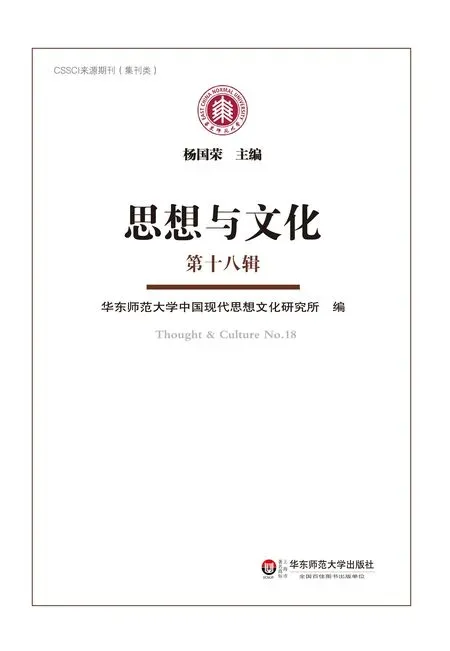以道观之与物我齐一
——《庄子·齐物论》平释*
陈志伟
《庄子·齐物论》是一篇非常难以理解的奇文。要想真正地理解《齐物论》,我们要将整个《庄子》的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注意将某一句话与其前后语境、文本脉络相联系,把这句话放在整个《庄子》的宗旨下解读,特别是此一句话中所出现的术语、词汇、概念,是否在《庄子》其他文脉中也出现过,如果出现过,就需要比较两处语境下这些术语、词汇、概念的含义之异同。如此,对这些语句的理解则庶几可近之。经典之解读,都应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正如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个有机体,各部分都相互联系而成为一个整体,每一部分言辞都反映所要论述之灵魂的天性,以使各种天性和谐共处(264b7-c5,275d4-276a7以及277b5-c7)。*参见刘小枫编译: 《柏拉图四书》之《斐德若》,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65页,第393—394页,第398页。《庄子》必定是一部好作品,而且《庄子》中任何单独的一篇,都是非凡之作,《齐物论》更是出类拔萃,所以我们更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的词句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齐物论》不仅在《庄子》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是《庄子》内外杂篇相关义理得以发挥的总枢纽和总根据,而且还是其后魏晋玄学、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关哲学问题的总根源,如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辩以及总体而言的名教与自然之辩等,佛学的空无、动静、物我等概念,宋明理学的体用、理气、心物关系等问题无不与《齐物论》有着极为密切的思想史关联。*陈少明: 《〈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因此虽然历史上和现当代不少人都对《齐物论》有过诸多阐释,但作为一篇处于中国思想史源头的经典哲学文本,我们有必要一再回望,从中寻找哲学智慧的新的可能道路。
一、 《齐物论》题解及“彼我”之对待
古典历史上对《齐物论》主旨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齐“物论”,即主张庄子在此篇中要齐的是纷纷纭纭的是非之观点,持此旨者以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 《庄子解》,《船山全书》,长沙: 岳麓书社2011年,第93页。近人钟泰唱和之;*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页。其二是“齐物”论,即认为庄子要齐的是世间复杂多样的万物,持此旨者人数众多,以宋人为主。今人陈少明在这两种主旨之外,又提出新的理解,即齐“物我”,他在认同如上两种主旨均为《齐物论》文本内含之意而不应两相对立或排斥之外,还主张庄子所齐的还有“物我”二者,即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出发得出的一种必然结论。*陈少明: 《〈齐物论〉及其影响》,前揭,第13—28页。在陈少明看来,《齐物论》的这三种主旨呈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从齐“物论”(齐是非)进而至于齐“万物”,因为“物”是“论”之所以兴起的客观依据,物之不齐则是非难一,万物齐一则是非之论不起;再从齐“万物”进至于齐“物我”,一方面我原为万物之一物,万物之齐,自然包含其他物与我的齐一,这样齐“万物”就成了齐“物我”的一个前提条件或本体论根据*陈少明: 《〈齐物论〉及其影响》,前揭,第71页。。另一方面,物为客观之存在者,我则为生存着的主体,而无论是齐“物论”,还是齐“万物”,或者齐“物我”,动词“齐”的施动者都是“我”,这使得“我”在诸“齐”中居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我”是一个“此在”,而这个“此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提问者,同时又是对所提问题的应答者,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之中,存在之意义得以显现。因此,齐“物我”中的“我”其特殊性就在于: 这个“我”在施以“齐”的过程之中被“齐”,即施动的主体在施动的过程之中得以消解,从而融入于另一个更高的存在——道——之中,庄子用“吾丧我”以及“心斋”“坐忘”“化”这样的观念来表达这一主旨。由此可见,齐“物我”又成为达到齐“物论”和齐“万物”之目的的唯一方式。
庄子之所以要齐“物我”,根本原因在于他明确意识到物我对待的关系是产生各种“物论”或“是非”的根源。这充分表现在《齐物论》的如下一句话之中,即“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这是《齐物论》在论述了天籁、地籁、人籁以及人的各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之后,突然插入或转入的一句话,很突兀。那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它与前文在逻辑上是接续在一起的吗?如果是,其中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寥寥九个字,其中包含这么几个关键术语: “彼”、“我”、“取”。而我们还记得就在《齐物论》上文中南郭子綦刚刚向我们展示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之超越境界,并在解释“天籁”时明确提出“咸其自取怒者其谁”的观点。如果再往下追溯,在《齐物论》的下文里,庄子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 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以及“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所以这九个字所构成的简短语句,其中的关键词汇,在《庄子·齐物论》中都不止一次出现,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个突兀的句子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人对这句话及其中术语词汇的疏解。郭象将“彼”字训为“自然”,并把“彼”“我”关系看作是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说: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3版,第62页。这种解释将“彼”“我”之间的相互对待关系完全遮蔽,从《齐物论》上下文脉来看,明显与庄子原意不符。成玄英接受了郭象的这种疏解,并进一步将“彼”“我”两者等而同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完全取消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对待关系。*成疏: “彼,自然也。取,禀受也。若非自然,谁能生我?若无有我,谁禀自然乎?然我则自然,自然则我,其理非远,故曰是亦近矣。”同上。我们注意到,无论是郭象还是成玄英,他们二人都没有将这里的“我”字与《齐物论》前文的“吾丧我”联系起来解读,也没有将此处的“彼”字与《齐物论》后文中的“彼是方生”观念联系起来诠释,笔者认为,这是郭、成二人对此句疏解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林希夷的解释表面上看与郭注成疏不同,但细绎之实则相通。他把“彼”字解释为紧接上文的“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的“此”,同时又将这个“此”字解释为“造物”,即下文的“真宰”,因此也就是郭象所说之“自然”。*林希夷: 《庄子卢斋口义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7年,第18页。在这一点上,钟泰吸取了林希夷的观点,也将“彼”字释为上文的“此”字,但却并没有把“此”字解释为“造物”“真宰”或“自然”,而是认为它指代的是前文所说的“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这十二种心理状态,并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心理状态,与我相待而生,故称“彼”。钟泰认为,“离彼心,即不复有我”,这即是将“彼”“我”看作是对待而存在的两物。*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方以智在《药地炮庄》中将“彼”字释为“物”,而这个物是与“我”相对待之“物”,故他说: “此正明我见本空,以对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无有。”*方以智: 《药地炮庄》,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虽然方氏以“空”来释庄子的“我”或“我见”,显然是受佛教思想影响,从而得出大大偏离庄子宗旨的“物亦无有”的结论,但其将“我”与“物”相对,则是基本符合庄子原意的。
王夫之在《庄子解》中将此句中的“彼”字释为“外物”,并明指“彼我相待而成,如磁芥之吸于铁珀,此盖无所萌者,而抑不然: 我不取则物固莫能动也。”*王夫之: 《庄子解》,载氏著《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88—89页。磁石与铁块的关系就是相互吸引的关系,两者不即不离,而“彼”与“我”的关系亦是如此,相待而生,相对而成。
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明确将此处的“彼”“我”作为相互对待之二物来看待,他疏解此句说: “绝待无对,则不得自知有我,故曰非彼无我。若本无我,虽有彼相,谁为能取,既无能取,即无所取,故曰非我无所取。由其以谈,彼我二觉,互为因果,曾无先后,足知彼我皆空……”*章太炎: 《齐物论释》,载《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页。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其《齐物论释定本》中又补充了如下一段文字: “此因丧我之说,而论真我幻我也。庄生子綦之道,以无我为户牖,此说丧我,《消摇游》云: ‘至人无己。’《在宥》云: ‘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天地》云: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皆说无我也。我苟素有,虽欲无之,固不可得。我若定无,证无我己,将如乔木枯腊邪?为是征求我相名色,六处我不可得,无我所显,真如可指,言我乃与人我法我异矣。”*章太炎: 《齐物论释定本》,同上,第83—84页。这是将此处的“我”与《庄子》前文的“至人无己”“吾丧我”以及《庄子》后文的“无己”“忘己”这种“无我”的状态关联起来,从而将“彼”“我”作为一副对子,正确地指出,庄子持一种“彼”“我”双谴的态度,从而希望达到“无己”“丧我”或“忘己”的“心斋”“坐忘”之超越境界。
另外,钱穆在疏解《齐物论》中这句话时引严复: “‘彼’、‘我’,对待之名,‘真宰’,则绝对者也。”*钱穆: 《庄子纂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页。这是直接将“彼”“我”看作是相互对待的双方。
纵观上述所引历代注庄解庄者对“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解释来看,凡是将“彼”“我”和“取”这三个关键词汇与《庄子》中其他地方出现的相同词汇对应起来理解者,几乎都能一致性地得出,这里的“彼”“我”是一种对待关系,而“我”则是“吾”之所要消除之“我”,是观念和形体之“我”,观念“我”的消除,其效果即是“心如死灰”,形体“我”的消除,其效果即是“形如槁木”。尤其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郭象、成玄英的解释没有看到庄子此处真正想要说什么。庄子用“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这句话所强调的是,“彼”“我”这种对待双方表明了,有彼,才会有我;有我,才会进一步有所择取;有所择取则必定有是非观念的产生,自己所择取的,就判其为“是”,而被自己所抛弃的观念,则判其为“非”。而如果将“彼”“我”这种对待的关系取消掉,则无彼无我,无我就无所择取,那么,庄子在《齐物论》后文所批判的是非观念也就不会出现了。这只能通过对观念之我和形体之我的消除来实现。观念“我”与形体“我”的共同消除,其效果则为“吾丧我”,也就是《庄子》前文所说之“至人无己”和后文所说之“心斋”“坐忘”。在这里,“我”是带有“成心”的,这种“成心”使“我”有所“取”,所取者即“非彼无我”之“彼”,因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况且“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而结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知,根本而言,拥有“成心”的“我”真正所“取”的恰恰是“是非”: 定己为是,断他为非,并且在“是非”相争的过程中,“与接为构,日与心斗”,“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终陷于“其形化,其心与之然”这种为形躯所驱使、被外物所诱导而不能自我定位、自己做主的人生大悲哀之中。
二、 “吾丧我”
庄子从彼我对待中看到只有取消此对待方可摆脱如上境地。在庄子看来,取消对待的方法不是取消外物,而是要消除“我”,这即是《齐物论》开篇所提出的“吾丧我”。
关于“吾丧我”这三个字的意义,罗安宪在《庄子“吾丧我”义解》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和解释。*罗安宪: 《庄子“吾丧我”义解》,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其观点之要者有如下两点: 第一,“吾”与“我”在先秦文献中有明显区别,“吾”仅指对我这一客观存在之对象的描述,着眼的是我的外在性因素,没有突出强调主体性含义,而“我”则是带有突出强调自我之主体的含义,往往与他者或彼者相对立而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情意性的表达;第二,“丧”字不是庄子后文所说的“坐忘”之“忘”,而是特指原来有而后丢弃掉的意思,而“忘”仅只是认识或观念中的遗忘,却不是真正的丢弃。对于罗安宪的如上看法,虽然我们接受他将“吾”与“我”明显区别的这个立场,但我们最多只能有保留地承认其对“我”的部分解释,却很难认同其对“吾”和“丧”这两个字所持的观点。仅就《庄子·大宗师》颜回向孔子陈述“坐忘”之后孔子回复“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这两句来看,当与道为一(同)并且与物同化时,就是“坐忘”。应该说这里的“忘”与“丧”没有本质区别,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荅焉若丧其耦”,形如槁木而心若死灰,这即是将形体和心智与万物(茶几、桌子等)相同一且与之俱化的一种形态。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庄子明确意识到彼我对待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取消这种对待。庄子取消此对待之势的方式是取消“我”而不是取消物,因为按照道家自然之观点,“物”是不可能取消的,取消了物也即是取消了自然之载体,因此只能走取消“我”的途径。如何取消“我”呢?庄子认为,只有化解“我”的主体性,使“我”与万物齐一,也即是说,将情意之我和观念之我完全去除,令“我”与万物没有差别,让“我”变成万物之一物,如此以来,就能达到取消彼我对待的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取消”“我”的这种行动本身也必须要有一个施动者才是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区分了“我”与“吾”,认为“吾”是不同于“我”的,且能够施加“取消”“我”之行动的这样一个施动者。由此可见,庄子的“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然客观的只有外在性因素的存在对象,而应该是一种自我之个体的本真性存在,是体悟了道且达至道通为一之境界的庄子意义上的圣人、神人或至人的存在形态。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将“物”“我”齐一之后,如果不能留下任何与“物”不同的自我,这显然不符合庄子本意。《庄子·缮性》篇认为: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也就是说,庄子反对将自我完全等同于物或消解于物,相对于物而言,自我(人)拥有绝对的优先性。*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所以庄子说“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不以物易己”(《庄子·徐无鬼》),并提出“物物者”这样的存在者: “物物者非物”(《庄子·知北游》,另见《庄子·在宥》),“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首先,这是强调“道”在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其次,这也突出了人这种存在者对于其他存在者(物)的绝对优先性地位。
如果按照罗安宪对“吾”与“我”的解释来看,“吾丧我”的意义将难以显明,因为他的解释并没有突出这两个意义相近的自我指称之间的根本差异。而关于“吾”与“我”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这个问题,时人亦有分歧。有趣的是,我们在汤用彤先生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发现汤先生引用《四十二章经》的第二十章的文字如下: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疑是各字)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并明确强调: “‘无我’此译‘无吾’,汉魏经典又称‘非身’。盖无我仅认为精灵起灭,寄生不久,形尽神传,其事如幻。释迦教义,自始即不为华人所了解。”从而将佛教的三世因果思想“误认为鬼道之一,内教外道遂并行不悖矣”。*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1页。按照汤先生的考证,《四十二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部汉译抄佛经,且其翻译甚早,认为“东汉时本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而汉晋间已有多人引用此经。*同上,第24页。不过,吕瀓先生的考证却得出了与汤用彤先生不同的结论,即认为《四十二章经》并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译抄经,而是要晚于《法句经》,因为前者是从后者的汉译本中抄录出来的。详情参见吕瀓: 《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载氏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276—279页。但即使吕先生的考证更可靠,却不影响本文的论证。汤用彤先生之所以认为“释迦教义自始即不为华人所了解”,端在于《四十二章经》将“无我”译为“无吾”,而这种译法本身无疑是受到先秦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深刻影响。汉末及魏晋间,为从黑暗的政治现实中解脱出来,给心灵寻找到寄托之所,士人喜谈玄论道,尤好老庄。而东汉明帝前以及之后的魏晋时期恰恰是佛教初入中国时,佛典就在此时开始翻译成汉语。由于佛道之间理念上似是而非的相似性,为方便计,同时亦为使佛教适应中国思想之土壤,译者在翻译佛典过程中,往往参考老庄之言,用道家概念来译佛学术语,此谓之“格义”*所谓格义,即是指为了将佛典中的佛学术语尽量准确地翻译成汉语并使读者充分理解,最初的汉译者往往取中国典籍中的概念与佛学术语进行比较,把其中相类同的固定下来,从而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即“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参见吕瀓: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45页。,这样,就出现了上引《四十二章经》中的有趣译法。而在“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这种译法中,“吾”与“我”正是沿用了《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的区分,只不过《四十二章经》的译法与庄子“吾丧我”在区分的意义上恰恰是相反的。在《齐物论》中,“吾丧我”之“吾”是个体之本真存在,而“我”则属肉身存在和作为偏见和执见的观念存在,因此需要靠本真存在之“吾”通过心斋坐忘的工夫去除(“丧”)掉作为肉身存在和观念存在的“我”,从而达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的精神境界。而《四十二章经》中“无吾”,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观点,即“非身”,所以这里的“吾”即是个体之肉身存在,“我者寄生亦不久”说的是作为本真存在的“我”寄生于这个肉身存在之中,因此,这里的区分与《庄子·齐物论》的区分在意义上是相反的。而且,《四十二章经》的译者之所以如此来译这两句话,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佛教观念,因为此经中的“无我”是指前面所说“身中四大”虽各有名称,假名而立,但却俱无自性,这里的“我”是独立自存的根据之义。故后来随着对佛教观念理解上的逐渐深入,在《四十二章经》后世流传过程中,上引经文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当今流行的经文是: “佛言: ‘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赖永海主编《佛教十三经》之《四十二章经》,尚荣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第46页。这就与佛教观念相吻合了: 各自有名,即假名而立,但都无我者,是确定它们都没有自性,即我身是空,也就是“四大皆空”。而庄子哲学中却绝没有“空”的概念。
但是,无论如何,《四十二章经》作为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佛教经典,译者最初的译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一般人对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理解,即在他(们)看来,《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表明了庄子对“吾”与“我”二者作了严格的区分,唯其如此,译者才能对佛教经文做如上译法,并产生这样的误解,即认为佛教也有本真之我和肉身与观念之我的区别。
在《庄子·应帝王》中,蒲衣子向齧缺描述了泰氏“未始入于非人”的境界: “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所谓“未始入于非人”,即是强调得道之人在取消了“我”的同时,并没有使自己完全变成物(非人),而是在道的支撑之下,保存了本真之我(其知情信,其德甚真)。所以,庄子认为“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庄子指出“物物者非物”(《庄子·在宥》),“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庄子·知北游》),“物物者”即是“道”或得道之人,后者“以道观之”“道通为一”,也可以“与物无际”,也就是泰氏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这就是在“丧我”之后作为个体存在所呈现的与物齐一的状态。“物”是有分际的,因为每一物之所以成为这个物,原因就是与其他物有所区别,这个区别就是“际”,而当齐“物我”之时,“我”与“物”没有分际,但是这个没有分际,又不是完全的混同为一,因为那个“我”还有其存在的“情信”“德真”这种本真性在那里,这是保证“未始入于非人”的前提,如果连这个前提都没有了,那么这种个体的存在就变得不可能了。因此,“吾丧我”中的“吾”就是得道之人的本真性存在。而其中的“丧”字最堪玩味,既包含原来有而后恍然若失之义,还有虽然遗失但却又保有所遗失之“我”中的“情信”“德真”的存在,而并非是完全地丢弃掉。那么,这种“丧”不恰恰是“坐忘”中的“忘”吗?忘掉的是情意我、肉体我和观念我,但同时“吾”又是实施“忘”的那个主体,即一种本真性的存在又在这种“忘”之中得以保存。这即是庄子意义上的语言深层的“吊诡”(《齐物论》)。这种以“情信”和“德真”为特征的本真之人,其所遵循的不是世俗之是非、善恶和礼义观念,而是“天”也即自然,因此,“在庄子那里,‘天’相当程度地构成了本真之‘人’的实质规定”*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所以庄子也称这种本真之人为“天人”: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庄子·天下》)“忘人,因以为天人矣。”(《庄子·庚桑楚》)“不离于宗”即是本于天性或自然,而“忘人”即忘掉世俗之人所遵循的诸多规范与原则,包括是非、对错、善恶以及儒家的仁义,还有肉体的各种欲望和情感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世俗的存在方式,而成为“天人”或本真之人。这就与“坐忘”相关,而“坐忘”是庄子通过颜回的修道进阶过程来展现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转向如何“离形去知”而“同于大通”这个问题。
三、 坐忘: 离形去知
《齐物论》开篇给我们展示的南郭子綦的“吾丧我”,是其得道之后的精神状态的呈现。但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精神状态呢?庄子认为必须打破我们的观念之限阈以及情感和欲望对心灵的宰制与约束。
庄子在《齐物论》中亦以人体感官之间的关系以及感官之上是否仍有一个真宰这样一种问题意识,表达了“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的心为形役的悲惨状态,最终必将陷入“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下场。心灵为物欲所驱使,则欲望指向哪里,心灵就随之跟到哪里,庄子用这种方式说明肉体之我对心灵自我的影响,即“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而他将这种心为形役的状态判断为人生之“芒”,即人生的迷惘。无独有偶,先秦时期对这种人生状态的关注并不止庄子,儒家人物也同样对此有所醒察,例如孟子曾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从而提出心官和耳目口鼻之官的大体小体之辨。由此可见,心物之间的关系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当然,孟、庄虽然在某些具体表述上有重合之处,但根本旨趣和最终目标却完全不同,孟子强调大体贵于小体,这或许也是某种小大之辨,但庄子却要超越小大之辨、贵贱之分,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对立的两者,从而达到“两行”,即小大、贵贱、对错等价值均停留于“天钧”*韩林合先生在其所著《虚己以游世: 〈庄子〉哲学研究》一书中对此处的“钧”字作过考证,认为这个“钧”字应指制造陶器的机器中间的那个转轮,而不是成玄英所说“自然均平之理”。参见韩林合: 《虚己以游世: 〈庄子〉哲学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7页脚注(成玄英参见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79页)。不过,韩先生以研究维特根斯坦著名,他也强调此书是以维特根斯坦思想为参照重新解释庄子,而其竟未察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晚年留下的最后笔记式文本《论确实性》中有几段话,恰可看作是庄子“天钧”之后世共识:“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像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hinges)。”(第341条)“某些经验命题的真实性属于我们的参照系。”(第83条)“具有经验命题形式的命题,而不仅仅是逻辑命题,属于一切思想(语言)运作的基础。”(第401条)“我不能怀疑这个命题而不放弃一切判断。”(第494条)以上引文参见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张金言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页,第14页,第62页,第80页。维氏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一再强调他的“命题”是“经验命题”,在这一点上,庄子可能与维氏有着根本差异。但承认逻辑上存在确定性(明)所必然依赖的某种基础性和本体性前提,在这一点上,庄子与维特根斯坦应该是一致的: 前者用“天钧”作比喻,而后者则用“赖以转动的枢轴(hinges on which those turn)”来表达,更多的时候用“规则”来表示。参考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Edited by G.E.M. Anscombe and G.H. von Wright, Translated by Denis Paul and G.E.M. Anscomb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9.之上而随造化自然交替流转,使“是”与“非”共在却和而不同(《庄子·齐物论》: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这与孟子“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的价值选择、明辨是非的智识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齐物论》还以另外两个人物形象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观念限阈的解除方式。齧缺与王倪之间关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的对话,以王倪的三问三不知这种方式揭示了对“物”的知识进路的把握的深刻反思。齧缺问他的老师王倪*《庄子·天地》: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庄子·应帝王》开篇记叙齧缺问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大喜雀跃,“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对齧缺教诲以“非人”之意,崔撰曰: “蒲衣,即被衣,王倪之师。”其实《齐物论》中王倪对于齧缺之四问,只有前三问以“吾恶乎知之?”来答,当齧缺又以“利害”相问时,王倪不再以“不知”对之,而是向齧缺描述了“至人”的生存状态,以表明“利害”这种功利性目标并不是得道之人所关注的问题。详见下文。“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王倪答“吾恶乎知之!”齧缺又问: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王倪又答: “吾恶乎知之!”齧缺不依不饶接着问: “然则物无知邪?”王倪仍然答: “吾恶乎知之!”表面上看,“物之所同是”恰恰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要确定的一个观点,即齐“万物”、齐“物论”以及齐“物我”,也就是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但王倪对“物之所同是”的这样一种坚持到底的“无知”态度却又表明,庄子又不以“齐”为是。从自然角度来看,物之不齐,乃物之本然,世界本来就是纷繁复杂变化多样的,强为之齐,必然是对自然状态的公然否定甚至破坏,这样就违背了道家的基本立场。正是基于此,庄子笔下的王倪面对“物之所同是”这样的论断绝对不可能给出一个断然肯定的回答。而巧妙之处在于,庄子并没有让王倪直接面对“物”是否“同是”,即“物”是否“齐”这样的问题,而是问他知不知道“物之所同是”?齧缺这个问题已经表明,“物之所同是”是不言自明的,他想问王倪的只是,后者知道不知道这个不言自明的论断以及物之“同是”之点何在?显然,齧缺陷入了庄子所提出的“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执念之中,并且更为严重的是,从后面紧接着的两个问题来看,齧缺还坚执于知与不知的区别之中。由此可见,王倪三问三不知的态度首先是对齧缺提问本身的一种否定,即在王倪看来,齧缺之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康德说: “知道应该以合理的方式提出什么问题,这已经是明智与洞见的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证明。因为如果问题本身是荒谬的,并且所要求的回答又是不必要的,那么这问题除了使提问者感到羞耻之外,有时还会有这种害处,即诱使不小心的听众做出荒谬的回答,并呈现出这种可笑的景象,即一个人(如古人所说过的)在挤公山羊的奶,另一个人拿筛子去接。”*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在《庄子》文本里,提出“知不知”的问题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被提问者往往答非所问或竟至以沉默对待。但是面对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王倪并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给出三个连续的反问式否定回答,作为老师的王倪,这样一种态度即是在强调,对于他而言,知与不知的区别并不重要。
王倪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有时候,我们所谓的“知”往往是一种“不知”,而我们所谓的“不知”,却很可能是一种“知”。这是因为,当我们确切地对某物做出判断之后,这个判断的确然性就将此物的其他判断加以排斥。我们说这个物“是”,那它就不是“非”,反之亦然。但任何判断都是在一定的立场和前见之下做出的,立场和前见的改变往往会使得本来是合理正确的同样判断变得不合理而成谬误,但坚执于一种立场,被自己的前见所拘囿,往往很难洞察与这种立场和前见相对立的其他识见的合理性。相对于自己的立场和前见来说,自我之知是某种真知,但若从其他立场和前见来看,自我之知却转而成为不知。王倪的两个反问,目的就是要消弭判断者所持有的立场和前见,从而给自我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从上篇《逍遥游》的立意来看,这正是庄子由“小知”走向“大知”的必要方法。
正是基于此,《齐物论》中庄子继而借王倪之言向我们描述了处于不同情境和立场从而以不同视角看相同事物而得出的不同结论,同是湿地,人与鰌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从而对湿地的评价也不同: 人非之而鰌是之;同是树梢,猿猴悠然荡乎其间,如履平地,而人则“惴慄恂懼”,胆战心惊: 猿猴是之而人非之;其他如各种动物的饮食习惯,每一物种所欣赏的交配对象,以及进一步深入到仁义和是非,谁能定出唯一的能统一各家的标准呢?所谓“正处”“正味”“正色”,都是事物所处情境与我们的视角所决定的“是”之标准,脱离开具体的情境与视角,则此标准立即失效,从而就变成了“非”。在这一点上,庄子似乎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位哲学家是一致的,其一是尼采,他在真理观上坚持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的立场: “世界是可以有不同的解说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透视主义’。”“世界是由这些生命体组成的,而且对每个生命体来说都有一个细小的视角,生命体正是由此来衡量、觉察、观看或者不观看的。”*尼采: 《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4页,第122页。另一是海德格尔,他提出情境解释学,*海德格尔: 《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赵卫国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2年。为后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基本原则奠定了前提性基础,并在其后期思想中坚持澄明、显现、揭蔽的真理观,而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真理观提出批判。将“是非”的标准看作是情境或视角的产物,即是抽离了所是所非的基础和前提,这样以来,我们才能跳出“是非”之淆乱,从而走向消弭观念之限阈的路途。因此,王倪说: “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这是打破自我之观念限阈的方式。
齧缺并未就王倪的话表示满意,而以“利害”再问王倪: “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这是直接以世俗功利的态度来理解“至人”,对此,王倪不再回避,以“至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回答之。至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在《逍遥游》中已经有所呈显,此处重提是为了进一步揭示与“自我观之”所不同的另一重境界。“自我观之”是以“我”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样一种视角必然携带着非常严重的自我偏向,在庄子看来,这既是“是非”观念产生的前提,也是“利害”考虑生发的根源,正如老子所说: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是非”是自我的观念之限阈,而“利害”则又回到了自我的情感与欲望层面。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与欲望的层面才是更为切己的自我,所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因此齧缺才有此问。王倪所答,“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这是强调至人“神”的一面,而至人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神奇绝妙,端在于至人已经脱离了肉体情感和欲望的限制与约束,而达至化境,所谓化境,即火来则为火,水来则成水,雷来则化为闪电,风来则变成空气,热则同热,寒则共寒,如此水火雷风又如何能伤害他呢?这是对“荅焉似丧其偶”的一种形象描述,成玄英释“偶”为“匹”,认为“身与神为匹,物与我为偶也”,这是继承了郭象注的解释*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48页。;俞樾认为“偶”释为“匹”不妥,因为不合后文“吾丧我”之意,而主张应遵循司马彪的解释,即“耦身也”,同时又认为“然云身与神为耦则非也。耦当读为寓。寓,寄也,神寄于身,故谓身为寓。”*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49页。其实这两种解释只有微弱的差异,抛开此微弱差异不论,“耦”首先为肉身则当无疑,而“荅焉”是“解体貌”*郭庆藩: 《庄子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2012年,第49页。,这样就与上引老子之言相一致了。至人“丧其耦”即舍弃或忘掉了肉身之欲,才能做到无“利害”而逍遥乎四海之外: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所谓“死生无变于己”仍然是强调“化”,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庄子·至乐》)即是依据这一“化”境对惠施作了解释。正因为至人消弭了肉身,所以“无己”,既然“无己”,何来死生之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倪认为至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利害”的担忧。
紧接着瞿鹊子向长梧子转述孔子的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义: “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对“利害”皆淡然处之(“利害齐矣”*钟泰: 《庄子发微》,第56页。),无世俗之欲求,尤其是不去刻意地遵循道,而是达乎自然中道*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第48页。钟泰将“不喜求,不缘道”解释为“道欲齐矣”,与上文的“利害齐矣”相一致,同上。,当此之时,言辞(谓)已失去了其特定功能,或者说,圣人之行为方式已达至超名言之域,言说与沉默皆无可无不可,则“语默齐矣”*钟泰: 《庄子发微》,第56页。。因此《庄子·寓言》中有“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之说,《列御寇》且将“不言”置于“言”之上: “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而不言”是默而识之,如此必无是非之辨而纯任自然(之天),反之,“知而言之”则在观念表达中必有是非之产生(之人),是非一起,何谈自然?又将陷入观念之争而樊然淆乱矣!齐“利害”、齐“道欲”、齐“语默”,这些都是“齐物论”中所内含之意,其指向则在“物论”“万物”和“物我”之中。
王倪“吾恶乎知之”的不知态度以及摆脱“利害”的至人境界,包括上文所分析的瞿鹊子引述孔子之言,被庄子借颜回的话总结为“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也即“坐忘”(《庄子·大宗师》)。因此,无论是王倪的自认不知,圣人的“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还是狂屈的欲答而忘答,或者无为谓的“不知答”(《知北游》),抑或泰氏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应帝王》),都可归于颜回的“坐忘”。*“坐忘”又以“心斋”(《庄子·人间世》)为前提,此处不赘述。
小结: “以道观之”作为对待世界之本真方式
以上是从观念之限阈和情感与欲望的肉身宰制与约束这两个方面说明如何达到“吾丧我”。庄子最终将此归结为“以道观之”和齐“物我”,后者我们在上文中已有所论述。“以道观之”是《庄子·秋水》篇中所表达的一种观念,河伯问: “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小大?”北海若答以“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庄子·秋水》: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舜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河伯之问着眼于如何分辨贵贱和小大,恰与《齐物论》的主旨相关联,北海若的回答对不同的观念标准加以区分,从而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贵贱小大之别。“物”“俗”“差”“功”“趣”均属世俗标准,而“道”则是本体标准,或曰天地标准、自然标准、终极标准。以世俗标准来看这个世界,自然会有世俗的贵贱、小大之别,而以终极标准来看这个世界,则世俗之区分自然泯灭,从而“物无贵贱”,庄子之“齐物论”根本目的其实就是要实现这样的视域转化。*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第62页。“以道观之”要以“道通为一”(《齐物论》)为前提,也即是说,将“道”作为沟通万物为一体的统一性之本体,是我们“以道观之”的基本前提。在这里,“道通为一”之“道”是作为本体的“道”,是“无所不在”的“道”(《庄子·知北游》),是《老子》中“道之为物”(《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的那个“道”;而“以道观之”中的“道”则是作为一种观念标准的“道”。*陈少明认为“以道观之”的“道”主要是“‘观’的方式,一种视角或一种看法”,参见陈少明: 《〈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但在庄子那里,“道”不是一般的视角或看法,而是看待所有视角与看法、评价一切观点和主张的终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与上文提到的尼采的视角主义或许更为类似,因为尼采也有其终极标准,即“永恒轮回”和“超人”的标准,而“永恒轮回”恰恰类同于庄子的“天钧”。正是从后一种意义而言,庄子才说: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但对于前一种意义上的“道”,即作为本体的“道”来说,却无所谓增减亏损。*成玄英持此观点,参见郭庆藩: 《庄子集释》,第81页。当然,对庄子而言,作为世界中的存在者,我们人的观念亦是其中之一物,所以作为观念标准的“道”并不与本体之“道”相违背。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破除观念之限阈和情感与欲望的肉体宰制与约束,最终需要以道作为终极标准来看待世界。庄子在《齐物论》中已经预示了“以道观之”的可能性: “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所以要“和之以天倪”,郭象认为“天倪者,自然之分也”,而班固释“倪”为“研”,“天倪”即是“天研”*郭庆藩: 《庄子集释》,第114—115页。,钱穆引马叙伦: “当从班固作‘天研’。《说文》: ‘研,礳也。’‘天研’,犹言自然礳之。礳道回旋,终而复始,以喻是非之初无是非也。”*钱穆: 《庄子纂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2页。如果班固之解合于庄子,那么,这里的“研”字还有“研判”之意,而结合“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以及“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这样的表述来看,庄子并非要将是非完全和而同之,而是任是者为是,非者为非,自然如此则循自然之道不刻意去改变,不因他人之“声”(言辞)的变化而自己也随之变化(化声),也即是说,在庄子看来,争辩只不过是相待于他人之言辞而改变自己的言辞罢了,如其这样,还不如“若其不相待”,也即“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庄子·达生》)。所以“和之以天倪”即是以自然之分判而不以自我或他人的世俗之标准来看待世间万物,由此而使自我之内心与万物自然相适而不违,所以遵循“天倪”即是“以道观之”。庄子也用人的认识层次来显示这一点: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也,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也,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人的认识层次与世界的存在形态有密切的相关性,世界的存在形态因在逻辑上不断追溯,可被区分为“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和“有无”“未始有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以及我们日常所经验的已然分化了的物的世界,针对不同的存在形态,人的认识也就有了如上分别。与道相一致的世界存在形态无疑就是“未始有物”的形态,所谓“以道观之”即是要求人能透悟世界之未分化状态,以此来达到“齐”万物、遣是非,从而使自我的存在形态与道相蕴合。
庄子通过《齐物论》消弭物我之对待,先遣是非之知,再遣明此是非之知者,又同生死*成玄英语,参见郭庆藩: 《庄子集释》,第116页。,一万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通过这种方式而做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且“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将世俗的声誉、功利、权谋、操劳乃至以知识为目的的主体性统统消解*“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这是消解肉体欲望的宰制,即“离形”,而“无为知主”则是消弭观念之限阈,即“去知”。,从而达到“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庄子·齐物论》)的游于至极无穷之域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齐物论》最终是为获得《逍遥游》中所提出的“逍遥”、游于“无何有之乡”或者“以游无穷”境界的一种手段。
FromthePerspectiveofDaoandBeyondtheDeferenceofThingand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