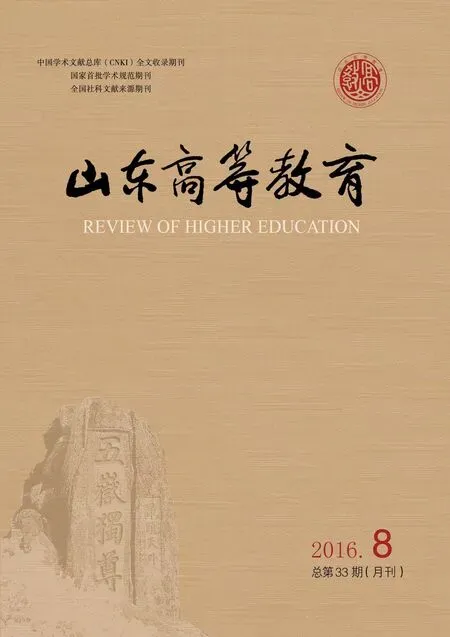国际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模式和趋势
李 虔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进修部,北京 102617)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公立高等教育在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垄断性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私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已占据全球高等教育约30%的份额。*数据来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PROPHE)全球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数据。同时,营利性高等教育以更迅猛的速度扩张,逐渐成为传统高等教育以外的新增长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分类对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演进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考察全球范围内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因素、基本模式和共性趋势,对于促进完善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规范发展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的主要背景
(一)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多元化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和人才竞争,带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大众化进程的加速,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使各国政府不得不放开教育市场,加速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
目前,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的多元格局初步显现。从教育需求角度看,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因有二:一是“过度需求”,即现有高等教育系统无法在数量上满足社会公众的过剩需求;二是“差异需求”,即公立高等教育无法在类型上满足社会公众的多样化需求。[1]579-585基于过度需求的私立高等教育扩张多见于发展中国家,使一大批“需求满足型”私立高校迅速崛起;而基于差异需求的私立高等教育增长多见于欧美国家,使一大批“精英型”和“半精英型”私立高校崛起。[2]
(二)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异军突起与差异化发展
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了传统私立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也为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公私立高校的传统教育项目很难满足成人和在职学生的教育和培训需求;另一方面,现代技术手段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为新型教学模式提供了可能。[3]营利性高等教育敏捷地回应了市场需求,凭借着在线教育和开放教育技术手段,提供低成本、高回报、授课方式灵活的高等教育项目,迅速占据了全球学生市场的较大份额。
但是,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与传统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有较大的不同。原因在于,传统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属于“维持性创新”,即在已有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以追求更高的教学绩效、更合理的资金使用和更有效的筹资方式为主,其目标群体仍然是传统学生和家长。而营利性高等教育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破坏性创新”,即以不同于传统方式的特色教育服务,针对非传统的市场群体,带来了较大的高等教育消费改变。营利性高等教育的“破坏性”为私立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竞争力,也对传统私立高校形成了较大的冲击。[4]
(三)私立高校的政府管制与有序发展
私立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私立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私立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强大引擎,在许多国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文化渊源;而在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学费的非营利性私立高校近年来发展迅速,为增加更大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5]38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益性的私立高校在使命、结构等方面越来越趋同于公立高校,逐渐模糊了其在公众印象中的私立性质。
在公私立界限逐渐模糊的同时,私立高校内部出现明显分化:除了纯公益性或慈善办学的私立高校以外,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以及选择非营利性类别但实则营利性作为的私立高校。在此情形下,对营利性、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区分比传统意义上对公、私立高校的划分更有现实意义。而政府对私立高校进行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分类干预是完善制度环境、规范发展秩序的大势所趋,也是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重要举措。
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强化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拓展。通过海外进出口市场的开拓,加大加快对外人员、物资、文化的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城镇”建设文化,生活文化,提高自己的城镇生活的品质,建设好属于自己的“新城镇”。
二、当前世界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的基本模式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清晰分类模式
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成熟,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分类管理体系。国家层面严格按照社会组织性质的类属,依据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分类体系对两类私立高校进行管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国家法律体系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的划分,早于教育系统中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高校的区分;而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小学,都从属于社会组织的基本法律框架,即先将高校按照“是否营利”进行基本分类,其次才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类别下进行“公立或私立”的划分。第二,受到基督教利他主义价值观和慈善捐赠之社会风尚的影响,美国绝大多数私立高校在其创始人在世时期就实现了管理权从个人向董事会的转移,并将大学的使命置于慈善和社会服务的层面。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公益性的私立高校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其办学使命和运行结构越来越趋同于公立高校。因此,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公私立分野并不明显,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区分反而更为重要。
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虽然私立高等教育系统并不发达,但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较为清晰,如加拿大基本复制和学习美国经验,通过立法保障各类私立高校的地位和作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2002-2004年相继推行地区改革试点,从地方政府层面完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分类配套措施。具体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清晰分类模式主要通过稳定性的政府奖助政策、普惠性的税收政策和灵活性的监管政策,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实行差别化管理。
第一,政府奖助是最直接的分类政策工具,其内容主要包括直接拨款、赠款、补贴、学生奖助学金、服务购买,形式可分为现金奖助和非现金奖助(如土地),方式包括有条件的政府奖助和无条件的政府奖助。例如,美国《高等教育法案》规定,符合相关条款要求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高校及其学生,均可以申请斯坦福贷款、联邦家庭教育贷款等合法资助项目。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支持法案2003》以及与之配套实施的“高等教育贷款计划2005”(HELP)规定,经过核准的私立高校和营利性或非营利性非自治高等教育机构,其学生可一视同仁地申请高等教育奖学金计划包括“联邦学习奖学金”(CLS)、“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金”(APA)、高等教育分担贷款(HECS-HELP)、全额付费贷款(FEE-HELP)和海外学习贷款(OS-HELP)。总体而言,清晰分类模式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适用不同的奖助体系,营利性高校只能通过以学生补助/援助的方式获得政府补助,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既能获得学生补助/援助,还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建设费和科研费支持。
第二,税收是最有效的分类管理政策,政府多以财政预算形式对分类管理中的税收支出进行规范化管理,使之具有长期性。根据课税对象不同,现实操作中有三种情况。一是对私立高等教育供给主体的税收区别待遇,主要通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的系统差异实现。无论是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明确营利性高校合法地位的美国和加拿大,还是在地方层面进行营利性高校试点的澳大利亚和日本,非营利性私立高校都是免税组织,而营利性私立高校都是纳税组织。国别政策的差异,不在于免税资格的基本设定,而仅在于特定国情下营利性高校纳税优惠幅度的设计。2002年,日本启动特区改革,鼓励地方发挥各自优势,最大限度地激活各领域的经济活力。教育行业也可以不拘泥于原有法律法规关于“教育不得营利”的限定,私营团体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在特区创建营利性高校的方案。目前,日本营利性高校的提案资料尚未公开,但基本明确的是,营利性高校均需纳税,但最多可申请12%的税率减免和50%的所得税补偿。二是对私立高等教育需求主体的税收统一待遇,主要体现在学生及其家庭可享受教育抵税和减税等税收优惠,而这种税收优惠与学生所就读高校的(非)营利性性质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税收优惠与高校教育质量是否达标有关。美国、澳大利亚政府都拒绝向不具有高等教育学位证书资格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私立高校提供学生教育费用的税收优惠。三是对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民间资本和捐赠方的税收区别待遇,主要体现在向非营利性高校捐赠的个人或机构可获得税收抵免,而出于对部分出资方“将资金从左口袋挪向右口袋即换取便利政策”的担忧,向营利性高校捐赠一般不享有此类税收优惠。
第三,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监管主要包括机构设置或登记管理,以及办学行为和办学质量监督。机构设置或登记政策取决于地方政府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大学的身份定位。若将营利性私立高校视为商业组织,则采用许可模式,予以营业执照或办学许可证,并根据消费者保护法进行办学行为监管;若将营利性私立高校视为教育组织,则采用认证模式,与非营利性私立高校适用同样的审查程序。以美国为例。各州对私立高校的分类和管理有所不同。一种以印第安纳州为代表,侧重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属性,州政府首先依据“是否营利”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区分,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由单独的部门进行管理;再根据是否具有学位授予权对营利性高等私立教育机构进行分类,并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另一种以纽约州为代表,侧重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属性,州评议委员会和教育厅首先依据“是否为学历授予机构”进行划分,非学历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由单独的机构进行管理,然后将学历授予的私立高校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再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20世纪后半期,由于政府的学生经济援助向营利性高校放开,但前提条件是高校需获得非政府评估机构的认证,越来越多的营利性高校像非营利性高校一样,自愿参与办学质量评估和认证,使得政府部门和非政府认证机构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和合作逐渐深化。
(二)以巴西为代表的模糊分类模式
模糊分类模式多见于巴西、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转型国家。社会发展带来旺盛的高等教育需求,政治经济发展又激活和释放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为拓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完善高等教育供给结构,转型国家政府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开放营利性高等教育市场,使需求满足型私立高等教育迅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营利性高校已经占据私立高校总数的70%~90%。①由于传统的公立高校系统具有典型的精英教育特征,且“学位”明显不足,普通家庭出生、学业表现不够突出的学生只能转向营利性私立高校。与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同,巴西、南非、马拉西亚等国的营利性私立高校扩张并未遭遇太多质疑和批评。由于这些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对政策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分类管理多采用模糊处理的方式,以配合仍处于结构性探索和调整期的高等教育改革。
模糊分类模式有以下两大特征。第一,私立高校分类管理体系属于后期追加,即私立高等教育先发展,后规范;营利性高等教育先存在,后立法。例如,1999年之前,营利性高等教育在巴西的法律框架中未取得合法身份,但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导致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出现内部分化,大量的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在政策夹缝中开展经营性办学行为。为避免大量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性高校一面享受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一面营利性作为,巴西政府不得不进行分类管理。[6]与巴西类似,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实行营利性高等教育合法化和私立高校分类管理,也基本出于此番考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国家纷纷在法律框架中明确营利性私立高校的合法地位,但具体分类政策“模棱两可”,实际操作性和约束力不强,仍然不能杜绝相当数量的非营利性私立高校进行变相的营利作为。
第二,分类管理配套政策具有较强的激励性、临时性和不稳定性。转型国家对私立高等教育的依赖较大,但社会慈善资本先天不足,且无法在短期内大量催生,政府往往通过阶段性低息贷款、奖励基金、一次性拨款等政策激励私立高校坚持非营利性办学。例如,在税收工具方面,大多数模糊分类国家并未将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税收优惠纳入政府收支管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对不同性质的私立高校予以税收奖励,多基于《所得税法》和投资、销售类法律法规,而非教育类法律法规。在这些国家,私立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社会组织存在,既是利用非公资金消化本国过剩教育需求的工具,又是吸引国外生源教育投资和消费、抢占全球教育市场份额的载体。由于政府对民间资本的逐利性质心存戒备,导致分类管理政策存在波动和反复。例如,菲律宾政府在60和70年代对营利性高等教育持认可和鼓励态度,但80年代以后,禁止成立新的营利性高校,并对已存在的营利性高校施以重税和各种条款限制。[7]177-196
(三)以乌克兰为代表的假分类模式
假分类模式的国家案例较少,以下以乌克兰为例。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才有了第一所私立高校,并于一年后获得政府批准。分类管理主要存在两大特征。第一,分类管理只是一种提法,不具有可操作性。非宗教类的私立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营利性质,并归于商业法和股份公司法管理;但2002年议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其产权归属如何,均为非营利性组织。由于这一重大政策转向与《预算法》、《国家税收内部法案》等相互抵触,一时难以付诸实施。[8]
第二,分类管理同时存在过度管制和监管不足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对私立高校的审批和认证异常严格,其设置标准过高,除非通过贿赂等不正常渠道,否则很难获得政府批准。[9]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模糊不清,政府部门甚至无法鉴别私立高校的非营利身份,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往往通过各种方法,向政府证明其非营利性质。[10]与之类似,越南的私立高校在法律框架中均为营利性,而在实践中,各私立高校努力向政府证明其非营利性,以获得相关政策优惠。直到2012年,越南《高等教育法》认可了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法律身份,分类管理才逐步实质化。*数据来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PROPHE)全球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数据。
三、世界私立高校分类管理的发展趋势
从未来世界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看,“多元化”从最初的政治口号变为切实的社会目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分类管理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选择,营利性高等教育崛起趋势仍将继续,进一步完善私立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将继续成为政策重点。
(一)改革模糊分类,力求清晰分类
分类管理被普遍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欧美国家通过分类管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私立高校营造公平、良好的制度环境;转型国家通过分类管理,更好地落实了政府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鼓励和扶持;而前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分类管理,限制了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维持了本国非营利性高等教育的传统性。而模糊分类作为一种阶段性选择,促进了私立教育在一定时期内的蓬勃发展,也不断暴露出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足。近年来,多数国家的私立教育管理呈现由模糊分类向清晰分类过渡的改革方向,而各国模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其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界定。为与国际接轨,大多数国家正尝试参照美国经验,以“再分配约束”为统一和唯一标准,将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私立学校的区分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配以不同的行为规则。
(二)坚持有分有统,做到统分结合
实行私立学校分类管理的国家,首先都在不同程度上根据“是(否)营利性”实现配套政策上的“分”,即对非营利性与营利性私立高校实行税收、政府拨款、慈善捐赠、教育活动和设施融资、土地使用差别化政策。其次,分类体系发达的国家根据“教育公益性”程度实现相关政策的“合”,即对非营利性与营利性私立高校实行教师和师生权益公平化政策。这主要出于对“营利性教育也具有公益性”的肯定,以及在教育多元化背景下,对受教育者受教育需求差异的尊重。而在大多数分类体系不成熟的国家,营利性私立高校被排除在政策支持对象之外。由于对“高等教育能否营利”问题的迟疑,营利性私立高校的师生被视为公司雇员和一般消费者,无法享受保险金、教育贷款、教育奖助等方面的基本国家保障。为解决由此产生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空间不足问题,完善涵盖各类私立高校的教育资助政策,打造统分结合的分类体系将持续成为政策重点。
(三)建立普惠机制,过渡刺激措施
分类系统尚不成熟的国家,对政府主导型刺激政策较为依赖,普惠性政策的设计与实施较为弱势。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刺激性政策,如奖励性基金,特殊优惠,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容易造成分类复杂化,政策利好不能均衡地传递到不同类型、层次的私立学校,难以维持办学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反,分类系统成熟的国家,对短期性激励政策较为克制,以便捷性的普惠政策为主,尤其是主要依靠拨款、税收和土地三种政策工具引导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经实践检验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因此,大多数国家在积极探索低门槛的政策普惠机制,在寻求普惠政策与刺激政策有效组合的同时,也不断将效果良好的阶段性激励政策过渡为长期性普惠政策,并上升为法律法规固定下来。
(四)淡化行政干预,实现合作治理
“政府-社会-市场”的教育治理模式由欧美国家实践并发展,进入国际视野,成为全球共识。对私立高校进行分类管理的教育系统,都在转变政府职能,在学费标准、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校长任命等学术相关问题逐步放权,避免直接干预学校发展;增加扶持力度,以购买私立高等教育服务为据,为私立学校提供包括经常性补助、特别补助、学生奖助、贷款利息补贴等公共政策支持;注重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确保学校发展需求为政府所获悉、政府政策为学校所接纳;强化以第三方为主的监管机制,聚焦办学质量保障和办学行为规范方面的监管。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教育责任在公私之间的划分[A].教育经济学百科全书[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Levy Daniel. C.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Private Challenges to Public Dominance[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3]Morey An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For-profit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2004, 48(1).
[4]Christensen Clayton & Henry Eyring. The Innovative University: Changing the DNA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Inside Out[M].John Wiley & Sons, 2011.
[5]World Bank.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il and Promise[M].Published for the 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2000.
[6]Salto D. J.A For-profit Giant: Brazilia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C].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Toronto, Ontario, Canada,2014-12-10.
[7]Tyler C. & Sam Papenfuss.The Economics of For-profit Higher Education[A]. In Hall J. C. Doing More with Less: Making Colleges Work Better[C].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10.
[8]Stetar J., Panych O. & Berezkina E. Evolution of Ukrainia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1991-2003[R]. Ukra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USSR), 2003.
[9][10]Osipian A. L. Corruption and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in Ukraine[J].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9, 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