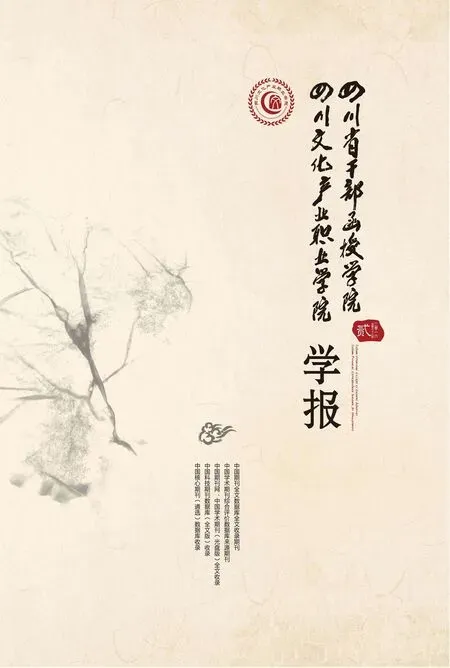人类学口述史研究的技艺
——以平武县民主改革口述史为例
曾穷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四川 成都 610000)
★社会·经济·法律★
人类学口述史研究的技艺
——以平武县民主改革口述史为例
曾穷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本文从人类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口述史研究的差异出发,以平武县民主改革为例,讨论了人类学口述史研究的技艺。本文认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对口述史有重大影响,口述史的成果,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取决于调查者和受访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查者对谈话过程的操纵能力。
【关键词】人类学口述史民主改革历史记忆
一、口述史:历史学与人类学
对于生活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的普通个人来说,那些导致社会性质转变的政治事件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高层的政权更迭、国家机器的转换,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更是这些“事件”对表现于日常生活的观念、心态、个人的生命历程所造成的影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积后,听事件的经历者讲述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和认识,唤起他们的历史记忆,听他们组织语言,看他们在事件之后生命历程的变化,研究他们的心态,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事件”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反映,比较真实地认识不同于“大历史”书写的历史的另一个面相。
历史学和人类学对于口述史,有着各自不同的取向。历史学认为,口述史形成的文本是一种历史记载,将其与有记录的文献进行比较,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从而丰富对事件的认识,更接近真实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因而历史学对口述史的运用,多是从被访谈者那里获取一些被正史遗忘的“真相”,一般而言,历史学选择的口述对象,往往是有较高文化的事件亲历者,或者重要的政策制订者,从他们的谈话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以复原他们所认为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补充历史大事件的一些细节。这样的口述史对访谈对象的选择有着较大的局限性,需要口述者本身有讲话的技巧,知道取舍讲话的内容,比如胡适对唐德刚的讲述;如果被访谈对象的言说天马行空、漫无边际,采访者会按照自己需要的时间顺序和逻辑过程来对讲话者进行诱导,甚至重新编排口述的内容,比如唐德刚对李宗仁口述的加工与制作。
而人类学对待口述史则有不一样的态度。这门学科的看家本领和基本技艺就是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跟他们聊天,从他们的话语和观察到的行为得出访谈对象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进而理解他所生活的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关乎社会整体的基本认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述史天生就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从研究“不会写字的人”中提炼出来的,因而那些没有文化的“村里人”的缺乏逻辑和时间顺序的言说,正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即使“村里人”所说完全颠覆常识,在历史学家看来荒诞不经、没有价值的口述,在人类学家眼里则如获至宝,因其背后隐含着言说者的世界图式和宇宙观模式,他们用与研究者所生存的“文明世界”不同的话语体系来表述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在口述过程中,口述者如何选择叙述的要点,虚构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学来说,比从口述中获得历史信息更有价值和意义。吊诡的是,在实际操作中,人类学又具有更宏大的目标和野心,从与个人访谈着手的人类学,本质上是对集体的、共同体的或者社会的整体研究,追求科学地认知世界,寻求一种科学的文化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个体性叙述为主的口述史又是与“科学”相背离的,认为专注于个体的叙述并不能认识整体社会形态,而认识整体社会形态又恰恰是人类学的目的和任务所在。因此人类学家在访谈中,往往过于专注分析报导人言说背后的“结构”与“意义”,而对于言说者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丰富多彩的个人经历,却往往视而不见,随手丢弃在历史的垃圾箱中。
本文并非探讨历史学和人类学对口述史不同取向的争辩,仅仅是与作者研究中的遭遇有关:在笔者的研究中,遭遇到的困惑正与这两门学科对待口述史的方法和态度有关:笔者在聆听口述者的叙述之前,对所研究的课题“民主改革”已经有了基本的文献基础,听民改亲历者述说,往往会用自己从文献中习得的知识来判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因此口述史变成了由自己的主观目的来取舍,根据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来取舍材料,这样得出来的口述史,能否超越既有的材料,究竟有没有意义?在具备了文献基础之后,听取口述者言说,其本意并不在于从他们那里获取“历史信息”,而是听他们对事件的表述,以分析其时间和空间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说者在言说中表达出来的世界观。此外作为提问的访谈者,自己的学术知识对于访谈对象的言说又起什么样的引导作用?研究者和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于访谈有什么作用?笔者遭遇到的这些困惑,或许能够从经验的层面反映口述史目前在不同学科中的发展状况。
二、平武县民主改革背景
2007年6月底至7月初,笔者作为“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课题组”的成员到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做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
上个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我国走向发展与现代化,改变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举措,它反映了由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的转变。开始于1955 年11月的民主改革,是新中国建国后基层建设、改变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的一件大事,四川民族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民主改革工作的重心。
选择去平武县,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平武县并非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由于县里有藏族(白马、黄羊、虎牙、泗尔、木座五个大部落)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进行了民主改革。而政府在对藏区进行民主改革之前,已经在汉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从档案记载来看,平武藏区的民主改革相当和缓,没有出现叛乱与反复,顺利地从原来的土司、番官、头人制度过渡到了乡、村行政建置,与同一时期发生在三州的叛乱形成鲜明的对比,同为毗邻的藏族地区,为何平武的民改能够按照国家希望的步骤进行?当时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民改后的土司、番官、头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经历了改革以后,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自己如何看待这个变革?参与民改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是选择以平武县民主改革做为口述史研究对象的原因。
选择平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笔者的家乡。在笔者看来,平武县的少数民族异文化色彩并不强烈,只是街上不时出现的插着白鸡毛的白马藏族,戴着狐皮帽的虎牙藏族,以及泗尔藏族……这些历史上称为“番人”的少数民族由土司老爷管辖,直到民主改革,土司才退出他们的生活世界。在民主改革之前,土司老爷在他们生活中的权威远远大过皇帝——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中,权力的象征,都是与“土司老爷”息息相关。作为“过去式”的土司老爷和家乡今天的面貌之间有什么关联?生活在三条沟里的白马藏族、虎牙藏族、泗尔藏族和县城的汉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来找寻这些问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年代毕竟太过久远,然而,从这个稳定的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刻入手找寻变化,或许是一个有利的观察视角。民主改革正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时刻。
为了对这些问题有整体性的把握,在进行口述史之前,笔者查阅了平武县关于民主改革的相关档案记载,发现探讨民主改革这一事件在平武的影响,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感,因此对平武历史的关注推前到了50年代以前。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对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所做的最大的“动作”,那么从一个更长程的历史来看,平武这个小小的边地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两次不亚于民主改革的变动:
平武这个仅有2万余人口的小县城,有着很长的建置历史,汉代即开始设“道”,当时生活在这个“道”的人群是被称作“氐”的人群,后来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边鄙之地,和帝国时代所有的基层行政机构一样,如果没有大的事件发生,“大历史”的书写很难将其记录在案。然而,这个地方在南宋末年的时候,开始进入大历史的书写,帝国的动荡映射在边地,“番人”与汉人之间出现了战争。景定三年,朝廷派出进士薛严前往镇压“叛乱”,留在平武,由金榜题名的进士而为一地之土官,当时被称为龙州的平武从此划归土司管辖。薛严之后又来了王行俭,朝廷封其为龙州三寨长官司,专管龙州三番。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隐藏了多少历史?在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的帝国体系之下,反而作出这分疆裂土的举措,引起了平武多少变动?帝国的直接控制减弱,转而由土司作为代理,来负责这一地方的番汉人民。这是平武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
第二次是明代中后期,嘉靖四十五年,龙州土司薛兆乾叛乱,帝国于是分土设流,降低薛氏土司官衔,缩减统治范围,退避到虎牙番地;分王氏土司为前王、后王两支,分别到黄羊关、阳地隘两番地。除了土司直接管辖的三大番地、五大部落之外的平武的大部分地区从此归龙安府管辖,变为编户齐民,开始承担起一个“有户口”的帝国子民的义务:给帝国交纳赋税,服兵役,等等。汉区重新进入帝国体系。番区的番人仍然为化外之民,只认土司,不认皇帝。
分土设流使得平武内部的番、汉之间有了更结构性的区分:原本长期住在龙州城里的土司住到了番地,和番官、头人开始了密切互动,土司署所在的三个部落(虎牙、黄羊、木皮)直接受土司文明教化,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活方式和观念上渐渐模仿汉人。直至近代,这三个地方的番人在客观特征上已经与汉人无异了,从而与白马路的番人由同族变为异族,不得不在“藏族”的通称前加上地名作为区分。这次变动,对平武的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变革,使得这一个地方出现了7个衙门并立的奇观:土知事薛土司衙门,世分府前王土司衙门、长官司后王土司衙门、龙安府衙门,武库衙门、都捆府衙门总爷衙门。①
把平武藏区的民主改革放到与历史上两次大的变动一起进行比较,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待平武的民主改革,可以知道,与历史上这个地方的多次遭遇相比,民主改革对于平武社会性质的改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一区域的人已经具有了应对变革的心态,这个心态是历史造就的。这一心态在我的访谈对象的言说中,有直接的体现。
我选择了4个访谈对象:土通判前王衙门的最后一任代理土司王生沛,76岁;土长官司的族亲,王生桐,72岁;曾经任黄羊部落民主改革工作组长的藏族,瑟哥,78岁;民主改革积极分子、民改期间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白马藏族,曹茂生,72岁。
这4个年过70的老人,都是当时民改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按照民主改革时候划分的阶级成分来看,王生沛、王生桐和瑟哥是地主,曹茂生是贫农。他们4人在民改中的经历各不相同。
王生沛,解放后曾经短暂担任过土通判、俗称前王衙门一支的最后一任代理土司。他原本不是土司直系,解放后参加征粮工作队。1950年6月,平武县成立藏族自治委员会(后改为自治区),任命土长官司(黄羊)、俗称后王衙门的王蜀屏为主任(区长),作为王家族人,王蜀屏吸纳他加入新的自治区政府工作,7月,他跟土通判王金桂到火溪沟搞宣传,1951年,王金桂作为统战对象到南充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学习,后留在行署工作,王生沛就成为“天然的土司”。1952 年2月,他和代理土长官司王信夫一起,带领40名少数民族青年到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并任少数民族队的队长。就在这一年,平武汉区进行土改,他的父母自杀。1953年他回来后到木座,参加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但没有在工作组任职,而是在木座小学当老师,并和从南充来平武指导民主改革的川北行署“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服务队”的女干部结婚。同年又到广元接受教师队伍思想改造,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直到退休。
王生桐,土长官司(俗称后王衙门)一支的族人,1951年作为平武县派出的第一批川北行署少数民族访问团(9人)到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学习,后又到西南民族学院(原西南民族大学)学习。回县后在虎牙小学任教。57年,反右时划为右派坐牢,出狱后离开教师队伍,到县公交局养路段劳动工作。1995年退休在家。
瑟哥,土长官司辖区黄羊部落的藏族。是1951年县上派出前往南充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学习的9个少数民族青年之一。后到西南民院学习法律,学成后在黄羊从事民主改革工作,1956年任黄羊民主改革工作组组长,是民主改革的骨干力量。民改尾期到雅安四川省委第三党校学习,学成回来后在虎牙藏族乡工作,后在水晶等地的司法系统工作,至平武县法院退休。
曹茂生,土长官司辖区白马部落的藏族,1952年在王生沛的带领下,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前往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学习。1956年3月,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身份,在白马开展民主改革工作,4~7月作为四川省各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全国各地参观,7月20日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任白马藏族乡的乡长和书记。
这4位访谈对象,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民主改革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也不相同,因而对于民主改革的记忆也各有侧重。王家的两个老人,建国后作为统战对象,接受了新中国的教育,但都没有任过“有实权”的职务,也没有具体参加民主改革,但由于土司的身份,多多少少被卷入到了这一事件中。两个民族干部,则是民改的骨干力量,也是获益者。他们学了专业知识,成为了国家干部,居处从山沟迁到了县城,成为“吃国家口粮”的人,同一事件带来的不同的命运,使他们对民主改革各有看法。然而调查中,他们谈得更多的却不是民主改革,而是刚刚解放的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他们进入川北行署革命大学学习的那些事,这比民主改革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更重要。
三、民主改革中四个人的生命史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开始收缴各个部落的枪支。土长官司王蜀屏有200多支枪没有上交,人民政府把他抓到平武县城的监狱,白马路的番人连夜赶到县政府,要求把“客巴”②放出来。
关于这一“缴枪”事件,4个人在谈话中都提到,王生沛如此说:
王蜀屏喊收缴枪支,王蜀屏没缴完,没缴完把王蜀屏,那时候还没成立自治区啊,没成立自治区晓得啵。就把王蜀屏关起,押起。活哟,白马路晓得了。“客巴,我们要见客巴,我们要找客巴。”客巴就是老爷,客巴就是番人喊的老爷,见了来了一群,跑去县政府去坐起,请愿嘞,晓得啵。后来才放了,把王蜀屏放了。过来才明白这个事,必须采取少数民族政策,晓得啵。这个成立自治区,就喊王蜀屏来承头。后来,民主改革就把王蜀屏抽下来了的嘛,抽下来了喃,斗争嘛。抽下来了嘛,还是给安了个文教科长,后来交通局长,这么安了唛,后来是病死了的,就这么来的,晓得了啵。
……
7月,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区,平武,没得个“县”,平武藏族自治区,即将成立,就是我昨天跟你摆的,就是喊王蜀屏缴枪喃。把王蜀屏押起,押起过后,少数民族跑来闹事唛,就把王蜀屏放了。(曾:少数民族特别喜欢王蜀屏?)也不是特别喜欢。(曾:那他们咋个要来闹事喃?)客巴的嘛,就是老爷嘞,把老爷关起了,那个时候老爷嘞,王蜀屏在里头种鸦片的嘛。你要说剥削,那个里头有啥子剥削头喃?上了税了,就几斤麻,粮食也没得。(曾:那些藏胞些还是很拥护王蜀屏?)当时是拥护,当时是拥护王蜀屏。王老爷嘞,客巴嘞,晓得啵,客巴。闹事过后,反映到胡耀邦那里去,这个就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成立一个藏族自治区,搞筹备工作,就喊王蜀屏来承头。王蜀屏他有钱,有枪唛,有烟唛,有枪唛。
王生桐说:
1949年,才解放,解放过后,那阵喊缴枪,喊手枪。王蜀屏嘛,他的枪比较多,晓得啵?都少数民族手里。(曾:枪在少数民族手里?)他发的嘛,保卫嘛,过去土匪又多,没得那个东西咋行嘛?过去白马路里头老林边上经常发生抢案。那没得保卫,咋行嘛?他就发动各个寨子嘛,各个头人嘛,晓得啵,就把枪就分下去了嘛,有啥事就召集拢来了。所以说王蜀屏就叫古英杰给关起来了嘞。平武解放后的第一届县长。这哈子王蜀屏就关起,关到监牢里头。这哈子哦,白马路的人,来了一批人哦,坐到大堂里不走嘞。要把我们客巴放出来嘞,老爷嘞,喊的,要把我们客巴放出来,不放出来不行。
瑟哥:
(曾:你父母被王家人杀了,你恨不恨王蜀屏?)王蜀屏那个我们晓得嘛,那是时候是红军长征那一个历史段,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杀了嘛,那是他的哥,又不是他。王蜀屏,因为他长期住在平武,不在黄羊,对他没得好多反感。他还是有能力的,也护番人,白马那边杨汝跟他们好,二番官嘞。每次过白马路都住二番官屋头。他不缴枪遭抓了,二番官还弄起人去闹,才放出来。
曹茂生:
(曾:说是那一年王蜀屏就是因为有枪,被抓起来关起了,白马路高头就来了几十个人喃,去请愿,要喊把客巴放出来,有没得这回事?)这个事情,是51年的事情了,那个时候藏区民改都还没得搞。(曾:照理来说,王蜀屏压迫、剥削他们,关起来不是大家更高兴啊,那咋个还要喊放出来喃?)那个是这个没批斗,那个时候都才解放,他没得那个政治觉悟,没得那个思想觉悟。二一个是当地的番官头人那些,利用那些老百姓,不懂那个机会,支使出来闹。不是出于当地老百姓的内心。不是。(曾:你跟到去没有?)我没有。(曾:有哪些去了的喃?)那些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曾:从白马路走路去的?)嗯,我听到说过。(曾:哪个寨子去的人多些喃?)这个我就不晓得了。不过王蜀屏点鸦片,有些实力。
从这4个人的叙述中,对于“缴枪”事件,总体来说比较一致。这个故事也由末代长官司王信夫写在《王氏宗亲录》中。③
从这个事件以后,人民政府意识到土司在民族地区的重要性,不能一下子打死,还要利用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感召力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因此在此事件后,王蜀屏被少数民族访问团选中,随少数民族访问团到了南充,见到了当时的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把王蜀屏作为藏族对待的,到了南充,胡耀邦才知道,平武这个地方是有藏族的,并且土司还不是藏族,是汉人,因而指示平武县成立了藏族自治委员会,让王蜀屏任主任,二番官杨汝任副主任。并让两人写信给松、理、茂等藏区各部落。④在县档案管藏的《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政府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草案》的第二点,第六条为“宣传人民政府队藏胞的重视与川北行署胡主任此次在人代会对本县藏族代表的提高地位馈赠物品及借包谷三万斤筹建牧场发还藏区枪枝(支)等种种的实惠与对各藏胞之优待。”⑤可以知道,缴枪事件发生之后,人民政府对平武的少数民族政策作出了调整。平武遂成为建国初民族工作的样本,1951 年9月,自治委员会改成自治区政府,从而成为“西南最早的区域自治政府”。⑥
缴枪事件从两个层面上对平武的地方行政造成了影响:一是直接导致了对平武土司政策的转变,在各个分散的部落之上建立了自治区政府,任命王蜀屏当主任,与此同时,5个部落保留土司制度,1950年10月到1951年9月,白马、木座、黄羊、虎牙、泗尔5个部落,再次任命了土司。这其中,白马、泗尔原来并不由土司直接管辖,而是由头人管理,人民政府则把任命的管理人员都称为“土司”,使得平武5个藏族部落成为建国后政府任命的土司地区。第二个影响是土司老爷的威信空前高涨,番人和土司之间原本具有的阶级矛盾消融了,番人站在保护他们的土司老爷的一边,这个关系在文革中体现得最明显:文革时期王蜀屏被弄到白马路批斗,王生桐说:
王蜀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给我摆过,把他弄到去斗,就是所谓造反派,把王蜀屏弄到去,喊牛瓦来的嘛,就是藏区区长,把他弄到区政府,就说,这哈哪个寨子上,要开批斗会了,要斗老爷,把他弄到去。王蜀屏说,那个有点笑人,啥叫批斗嘛?年轻娃娃站到那里干吼些,坐到这儿批斗啊,那些老头儿家啊,半老十岁的,就是我们两个椅子搭起,摆条(四川土话,指聊天——整理者注。)样的。哦,你哪年子那个事情没有作对,你哪年子的事情作的好,就是说这些,拉家常样的。(曾:牛瓦那时候当的是区长?牛瓦也会斗他?)牛瓦斗他啥子喃?牛瓦在保护他。牛瓦把他弄到区政府,一天茶水、饭都送到去,关系好。(曾:也就说是为了给县上完成任务?)造反派嘛,那阵啥子县上,你晓得文革那乱得。那个想啥子就是啥子。我给他说你遭批斗不是把你整惨了?他说那个整啥子嘛,一天火烤起,一天木炭火烤起,火多大……
这两次事件分别发生于民主改革之前和民主改革之后,平武的土司老爷和番人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关系”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改革而中断。在土司老爷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番人却用他们的智慧保护土司老爷,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或许是平武这个地方在经历了多次的变动之后,形成了一套应对变动的方法,长程的时间中,固化为一种心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当四川其他地方,藏区、彝区因而民主改革而发生大规模叛乱的时候,平武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对于生活于此的人民来说,这无非是再一次的“改土归流”。
这是在调查中得出的认识。由于熟悉平武的历史,因而在访谈中,笔者以自己的历史感引导报导人的言说,造成了调查结果与进入的初衷——集中对民主改革进行调查——有了距离,尽管也对这个地方的民主改革有了认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发现对于这个地方来说,民改前和民改后发生的变化,人们的心态,远比民主改革造成的社会形态变化,更值得关注。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口述史的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果换做别的调查者,不考虑历史的因素,带着民主改革的问题意识直接进入访谈,或许会得出另外的认识。正是由于调查者和受访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调查者本人对谈话过程的操纵能力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差异。
【责任编辑:桂静】
注释
①平武地区土司政治的具体研究,见曾穷石:《汉藏边缘的土司政治:13~16世纪龙州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四川大学2005届硕士毕业论文。
②客巴,是白马话,指老爷。
③《王氏宗亲录》写于1998年,由时年83岁的王信夫手写。王信夫,名生杰,1916年9月出生,2000年2月12日故。
④1950年1月19日《给松潘各部落的信》,1950年8月29日《致藏族兄弟姐妹的信》。见平武县档案局县
⑤平武县人民政府1950年文书档案10-1-8案卷号永久卷(3张)
⑥王维舟:《西南区民族工作的报告》,载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印的《法令汇编》,1951年。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784(2016)02-101-6
收稿日期:2015-09-08
作者简介:曾穷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