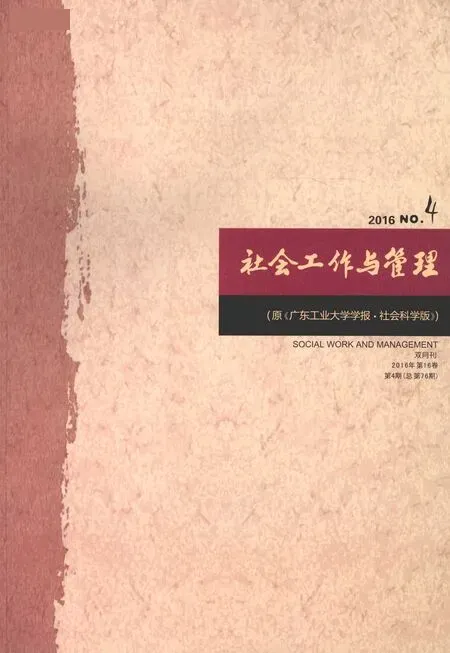去人情化: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倾向和社区“脱域”策略
孙旭友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去人情化: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倾向和社区“脱域”策略
孙旭友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基于T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风格与治理倾向的研究发现,与老一辈社区工作者不同,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倾向于采纳“去人情化”方式处理社区关系和治理社区事务。这种社区“脱域”的工作风格,是社区工作职业化、科学化和行政化的自我认同、现代工作的自我定位和自主意识、对社区工作的短工化期待和女性化片面认知等因素多重效应的结果。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去人情化”实践,既可能在短期内阻隔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导致居委会组织的“悬浮”和失去扎根地方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也可能会对基层社区的民主化建设和事务的合作治理起到倒逼作用,进而推动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去人情化”治理倾向的效用还有待观察和验证,而社区善治的达成仍需继续加强社区参与、社区信任关系和社区民主化等基础建设。
社区工作者;去人情化;脱域;社区民主化;社区治理
一、去人情化: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社区治理倾向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以及资源分配向获得方式多元化等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居委会的占有资源和组织权威进一步弱化。因此,利用感情、面子、互惠等人情机制来动员居民、培育积极分子和治理社区事务,成为社区工作者①必然延续的工作传统和强化的治理策略。社区工作者利用邻里人情机制开展社区工作,既被看作“在缺乏相应资源条件下,国家为低成本维持国家控制动员体系的传统延续”[1],也被认为是“实现社区治理、落实国家社区政策和完成社区工作的有效方式”[2]。社区工作者利用人情化策略力图建构一种嵌入社区(空间/关系)的“社区群体关联”,更被社会工作相关学者看作是建构社会工作求助关系本土化的重要表征②。如黄耀明提出,社会工作者应“使自己与服务对象更进一步地血缘化或拟亲属化,成为服务对象的‘自己人’或‘内人’”。[3]社区居委会非制度化的人情治理方式,虽然只能在某一群体或有限程度上实现动员居民、运转社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目的,但是依然获得了包括街道、居委会、驻区单位、居民等社区相关行动者的关注和重点培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区工作者的人情化策略作为一种微观动员机制和关系建构手段,已成为社区邻里权力运作和社区运转的重要因素。
与社区行政化相伴而来的社区工作专业化与科学化的职业转型,导致“整个社会都对居委会干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是社区专职工作者、是要逐步成为职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的社会工作者。”[4]居委会工作逐渐被社区事务所容纳、居委会干部称谓逐渐被社区工作者话语所替代,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通过招聘、竞选、招考等方式,走上了社区工作的岗位,成为专职的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与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利用和沿袭人情化策略完成上级任务、“嵌入”社区和建构人际关系网不同,新一代的社区工作者采用去人情化的“脱域”策略来处理社区关系和治理社区事务。“脱域”(Disembedding)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与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略有不同,本文的“脱域”是指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进程中,不但不注重社区人情关系的建构和人情化策略的运用,而且有意识地与社区的空间、关系等保持距离,刻意保持一种彼此可以感知的距离感和疏离感。就是说,当老一辈社区工作者把“人情化操作”内化为一种工作理念和实践方法的时候,相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却主动放弃了人情关系建构和实践运作。他们大多不住在本社区,大部分时间呆在居委会办公室完成任务,并有意与社区保持距离。他们既不注重运作社区人情关系,也不会刻意与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甚至是居民积极分子建构亲密的地方化人情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问题是:在同样的国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区微观结构下,为什么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倾向于弱化人情机制的社区运作,并采取与老一代社区工作者相反的“去人情化”的社区治理倾向和工作风格?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社区“脱域”的策略和“去人情化”工作风格,仅仅是标志着社会工作正在“从熟人关系到专业关系的现代转向”[6]吗?其对社区治理、社区民主化甚至国家政权建设带有何种潜在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南京市T社区③工作人员的分析,回答上面的问题。
T社区共有工作人员9人,其中8名为女性;年龄在50岁以上的1位,40—49岁的2位,30—39岁的2位,剩下的4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在20—29岁之间;学历水平大专学历的2位,大学本科毕业的有7位,其中几位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员,都是利用工作之余获得同等学历。其中两位年轻工作者拥有社会工作师证书。T社区显示出老中少搭配的人员组织结构,退休返聘或下岗招聘的老一代社区工作者比例占40%,平均工作时间10年以上;而通过招聘招考来社区工作的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占到60%的比例,工作时间都在5年以内。社区工作者年轻化、学历化、职业化和科学化趋势明显。
本文资料来源于对南京市T社区工作人员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T社区是南京市G区R街道的行政规划社区,2007年经由原来J社区与Z社区等合并而成,各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合并在现在的居委会驻地办公。笔者从2013年10月至12月,对T居委会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查,既对包括居委会主任书记、普通社工、积极分子等在内的20人次进行了深度访谈;也参与到了社区工作者的办公场景、事务处理现场和日常生活过程。
二、脱离社区空间和社区社会关系
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去人情化”治理倾向的自主抉择把人情关系从“社区”抽离的治理倾向与工作风格,是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个体独立自主做出的选择。这是他们面对社区行政化和社区工作职业化、科学化等结构性事实,基于社区工作短工化与女性化的片面认知、现代工作与生活方式的自我定位等因素,主动从社区“脱域”的自主决策。
(一)社区工作行政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自我认同
居委会对政府的社区职能延伸和任务转嫁的承载即社区行政化,是与社区工作职业化、科学化趋势纠缠在一起的。社区工作的三种趋势和结构性事实(行政化、职业化与科学化)在城市基层社区的结合,对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讲求社区工作的科学知识运用和人力资本拥有、按照科层制的规则工作和内化政府“老板”角色等因素,深刻影响着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方法和事务处理方式的选择空间。
一方面,社区工作被当作一份“谋生”的职业。在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看来,他们是经由政府招聘或招考来工作并赚取工资的准政府人员,社区工作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全职工作而非老一辈居委会干部讲奉献、搞兼职的“兼职工作”。在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概念里,签订正式工作合同,要求政府缴纳“三险一金”、嵌入科层制管理体系和对给发工资的上级政府负责,是社区工作职业化的内在要素。一位年轻女性社工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也换过好几个工作,最后觉得给政府做事好些,比较稳定、有保障。我们都是经过考试招聘来的,政府给发工资、交养老保险啥的。当然要替“老板”工作啊,谁给钱给谁工作,天经地义的,我们又不是搞奉献的,是领工资的好吧了!再说了,现在上面的事情那么多,成天开会,填表格都没时间,哪有空走访啊!上面的(人和部门)都不能得罪,先干好这个最重要。
另一方面,社区工作是一种需要“科学知识”的现代职业。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相对于老一代居委会干部,更看重工作职业道德、职业资格证书、科学技术等人力资本的拥有。在他们眼里,社区工作是一种需要方法、理论、知识的现代工作,而不是“社区老大妈”家长里短的邻里活动。因而,他们不但把缺少学历和科学知识的老居委会干部看作为不专业的业余“货色”,而且也认为搞人情关系是去技术化的工作方法。社区主任的观点如下:
现在整个居委会就我一个人拥有中级职称的社会工作师证,没有这个证书显得不专业。所以除了书记几个人年龄大点的,其他年轻的都想考。现在社区工作不是以前的聊聊天、谈谈心、搞搞人情关系就行的,那样就显得太没有技术了。现在社区工作还需要各种技能,例如电脑、打字、制图等等;还需要各种社区工作方法和知识,像女性增能、社区照顾,社区政策、法律法规等。上了年纪的都不懂这个,她们比较擅长串门聊天,拉关系。
(二)社区工作短工化和女性化的片面认知
社区工作行政化、职业化和科学化趋势以及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使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事务管理中会与上级结成“政绩共同体”[7],干好工作似乎是社区工作者的必然选择。但是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的认知,却同样受到来自社区工作职业等级和社会评价的影响,导致他们对社区工作隐含主观性排斥,以及社区工作“短工化”和“女性化”等片面认知。
现代化社会中一个人的工作状况,对一个人的经济收益、社会地位、权力来源和生活期望等越发重要。新一代有知识、学历和文化的社区工作者,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提高技能以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在“理想照不进现实”的中国劳动市场,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具有高学历的大学生被迫把社区工作作为职业次选择。“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8]社区工作带来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低等社会职业评价现实,导致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选择的非自愿性和职业非认同。他们对社区工作的无奈和坚持,受到当前中国学术资本贬值、国家政策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对大学生就业“围追堵截”等结构性力量的影响。这也导致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存有“先干着、有机会就跳槽和随时准备换工作”的观望态度。社区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和“短工化”倾向,已成为困扰社区工作的一大困境和社区人所共知的“秘密”。T社区老书记对此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年轻人待不住的。要不是没办法,他们也不会到社区这种地方来工作,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我经常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个月收入2 500元左右,很满足。但是他们这些年轻人不知足,总是赚的钱不够花,觉得在社区工作钱太少。以前社区很多大学生干不了多久就辞职或者考公务员走了,他们才不安心干这个呢!(低声)她们这些也是“骑驴找马”的,他们有机会也是随时准备换工作,家里有门路的也在操作。他们很多人就把这里当个临时的工作,或者是考公务员的跳板。
另外,社区居委会工作适合老大妈的传统职业形象,与新时期社区工作收入低、工作不重要而且相对繁琐等特征结合,导致了社区工作更适合女性的工作刻板印象和职业性别偏差。社区女性社工就此颇有发言权:
按照现在社工的工资,只有女孩子才会干,男的要是干这个,一家人非饿死不可。居委会都是娘子军,男的很奇缺,男生即使来了很快就走了,自己都养活不了。 女生不用找太好的工作,只要是个工作就行,以后生活还是要靠男人。只要别丢了饭碗就行,干好干坏的有什么区别,养家指望不上,也不会多发几个工资。没意思!能糊弄着有个工作做就行啊。
社区工作适合女性的职业女性化刻板印象,不仅深深刻印在社区工作者的思维中,也反映了社区人员结构中性别构成的现实状况。女性对社区工作的“偏爱”或者职业认同,既是女性对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等现代女性标准追求的结果,也渗透出男权逻辑依然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社会地位等主要衡量标准。
(三)现代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的自我定位
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作为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有着与老一辈居委会干部不一样的自我人生定位、生命历程和生活方式。他们既注重个体隐私和休息、自由、安全等公民权利的行使,而且对“八小时工作时间、周末双休”等国家法定工作制度和自我生活方式等有着严格的个体要求。因此,建构社区人情关系不符合现代工作的职业定位,而用休息时间去拉关系、谈感情更有悖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既不太喜欢这种强调人情纽带关系的工作风格,也“缺乏、忽视对隐私性的地方知识、人际交往技巧及日益复杂化的都市环境中采取有效策略的能力的拥有”[9]。
当笔者陪着年轻社工D周末值班的时候,她几乎从不出居委会大门,除了外出吃饭,就呆在居委会办公室上网。即使有居民电话打来或者邻里有矛盾需要调节,她也会以“周末不上班、不方便下去、等周一再说吧”等合理的理由推脱。这些被政府招聘而来的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大多都非本社区居民。他们通常都在早晨八点五十分踩着时间来居委会上班,而且除非上级安排的任务非常紧急需要大家合作或者社区领导把任务分给个人,他们只会安静的做自己分内工作或者坐在办公椅上发呆。社区党员积极分子ZH阿姨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孩子跟以前的居委会干部不一样,他们是社工,但是其实就是个名分上不一样,没啥区别。我看啊,除了Q书记经常到社区转转,走访居民,就连S主任也很少深入居民,更别说这些社工了。他们都是替政府工作的,按时上班,准时下班。时间固定,需要自己的时间,要不然居委会工作这么多,连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们都懂得为自己争取;再就是他们不善于这些东西(人情世事)。都是大学生,在家都是被宠着的,让他们低三下四地跟老头老太太拉关系,有时候还被居民骂来骂去的,他们才不干呢!
三、居委会组织“悬浮”抑或“倒逼”社区治理民主化
“去人情化”治理倾向将潜在地影响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对去人情化策略的选择和运作,必然会逐渐弱化“参与式动员”等工作传统和人情逻辑在社区参与中的运用。另外,社区干部双重代理人身份、居委会组织的地方扎根优势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社区民主化建设等方面,也必将受到潜在影响。
(一)阻隔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居委会双重代理人的组织属性,决定了社区工作者的政府与社区的双重代理人身份。社区工作者既要承载基层政府转嫁而来的任务,还要通过组织活动、发动居民等展示居委会的自治性。在居委会权威弱化和资源不足的状态下,人情化操作成为社区工作者治理社区事务和达成政府意图的必然选择。而“去人情化”的工作实践,把人情逻辑从“地方性权威”中抽离,只剩下政府赋予居委会组织的代理人身份。社区工作者成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甚至得过且过的社区事务“撞钟者”[10]。这势必影响政府社区职能的完成、社区事务的治理效果,甚至会造成社区工作者自身利益受损。Read对居委会的系统研究表明,居委会及其与居民之间的联系是国家赖以进行城市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11]也就是说,人情机制是国家维持低成本国家动员社会体系及意图贯彻的依赖路径。然而,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去人情化社区治理风格,无疑会给当下有限的居委会与居民社区关系网带来摧毁性损害,进而增加国家治理城市的资本和弱化治理成效。刚被街道调任T社区不到3个月的Q书记深有体会:
也可能是我刚到社区的原因,基础还没打牢。很多居民都不认识我,积极分子也不是太熟悉,除了几个党支部书记。这样工作就不大好做了。要是放到以前的那个居委会,那都是顺手拈来,熟得很。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支持,很多活动开展不起来,指望我们几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就像这次“文明城市测评”的检查,跟居民、积极分子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不行,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为什么?就是感情没到,不给你帮忙。还需要做工作,把基础打牢,建立关系。没有居民骨干和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靠我们几个根本玩不转。
社区书记Q与S主任都是刚刚从别的社区调来的,不仅不甚熟悉T社区情况,而且与居委会一贯响应力量—积极分子的私人关系也在深化之中。她们的工作经历与自身体会,从侧面证明了“在本土化资源缺失的条件下,一般化的基层社会权力运作与事情操作模式难以通行”[12]。缺少深度的人情关系约束和背景,不但居委会与居民互动显得晦涩和牵强,而且社区事务的治理也步履艰难。
(二)导致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悬浮”
社区工作者双重代理人身份是基层政权有效实施国家政策的基础,也是国家渗透社会的通道,而这都需要历来就有效的支持策略——借助人情、面子等本土化文化资源。原本越发行政化的居委会和远离居民的国家形象,通过社区工作者私人关系的运作强化了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居委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表面印象。但是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去人情化社区实践和工作方式,在强化社区居委会对上级政府的依附和行政化关联的同时,也会导致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进一步脱离社区居民生活和社区关系网络,使得居委会“悬浮”[13]特征更加明显。
一方面是社区工作者动员能力的弱化和社区社会关系脱离。利用扎根社区地方优势和社区干部私人关系的建构,都能为居委会治理社区事务动员各种资源,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这无意之中为原本依靠上级政府财政支持而开展公共服务的居委会组织找到了扎根社区基层的路径。居委会在“服务型组织”建设背后还隐含着一个“动员型组织”的自治性组织样态。然而“去人情化”治理方式和居委会干部主动脱身于社区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弱化了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动员能力和居委会扎根社区地方的优势。
另一方面深化了居委会机构的政府象征。居委会与居民的地域比邻和社区空间上的同处,在社区工作行政化和职业化趋势下,原本就类似于政府“植入”社区的代理人和外部力量。随着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去人情化”工作风格和治理方式的社区实践,可能会增强社区工作者“在办公室办公、发发通知、搞搞活动”等服务居民的政府代理人角色。这既会加重原来社区居民“闻其声不见人”和“不关心、不在意”等冷漠心理态势,也会更加凸显居委会组织的政府代理人形象。新一代社区工作者脱离社区群体关系和远离居民,更加固化了居委会组织只是一个传达和完成政府任务的机构和矗立在社区标示的已有印象。
(三)“倒逼”社区治理民主化
借助人情、面子等本土文化资源来实现社区治理的制度惯性和工作传统,不会被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去人情化”工作方式立马斩断。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在除了借助原有的人情关系网络,更多的是利用公民权利话语、利益刺激和更具功利性的交换关系以及居民自身参与需求等非人情化的方法,来发动居民和治理社区事务。如同社工W所言:
该来的来,不来的也不强求。那些党员都有党性和党组织的要求,一般都会来。那些从单位退休的,在家待着也没事,也想参加点活动,锻炼身体。再说了,不论是参加活动的居民还是跟社区共建的单位,都是有目的的,没有利益和目的,他们也不会来。到时候有事情了,我们就贴通知,打电话,都告诉他们了,来不来无所谓。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要搞关系,我也不想去,没必要。要去也是书记、主任他们去啊!
笔者参与的几次社区居委会选举和社区党委会选举,虽然不乏给面子、求帮助、借助关系等人情机制的运作,但是那些年轻的社区工作者更倾向于“告知事件”而非“帮助做事”的沟通。他们更关注“参与选择是你们的权利”“上级通知了要XXX”“单位共建是驻区单位的义务”等权力话语带来的动员效用。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对人情逻辑的弱化与正式权力和制度规则的强调,既可能把居民带入正式权力关系和正式的政治“场域”之中,也能把政府的正式意图、规章制度和公民自身权利进行原本的阐释。社区工作者对去人情化与去地方化的运作,既可能给居民灌输权利话语和利益相关性刺激,也可能“倒逼”政府去除对人情机制在基层社区运作中的默认和鼓励,而采取更加民主化的治理机制。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作为年轻、有知识、有学历的被政府招聘招考而来的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行政化、科学化和职业化趋势下,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非人情化的工作风格来处理社区事务和居民关系。他们关注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尽量与工作的社区保持应有的空间距离,而把工作地点集中于居委会办公室而非社区空间。在国家政策、社会职业评价体系、压力型体制以及就业市场压力等外部力量挤压下,作为受到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浸染的一代,社区工作被他们当作不得已的次要选择和临时跳板,也形成了社区工作女性化和短工化的片面认知。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在与社区居民或驻区单位等行动主体交往中,倾向于发展基于规则、权利、利益等为基础的正式交往。他们尽量弱化基于私人交往的群体性关系即由群体交往而形成的支配关系和社会网络,进而与社区居民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而从社区中“脱域”。
新一代社区工作者这种切断人情纽带关联和不刻意建构私人关系的行动风格,力求把社区“动员—参与”和资源获得过程中的人情因素降至最低。这既是当前就业市场、市场逻辑、国家制度和现代思想等结构性力量与80后、90后的一代对社区工作认知相结合的结果,也必然会阻隔当前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导致居委会动员能力的下降和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悬浮”。然而,这种“去人情化”治理倾向和工作风格的持续运作,也可能会给社区治理的正规化运作和正式权力关系带来可能;同时也将“倒逼”政府弱化人情关系在履行政府职能和治理社区事务中的作用,为加速社区治理民主化进程带来可能。因为利用社区非正式权力而形成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的现代传承[14],既可以推动基层治理的有效进行,也可能造成诸多治理困境。而剔除基层治理中的非正式权力关系和非正式治理机制,正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实现社区善治的必然要求。
(二)讨论
加强社区民主化建设进而推动社区参与和基层治理,既符合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是社区治理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如同张静所指出,“当代国家政权建设不但包含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同时也伴随着国家对民众的增权。”[15]因而实现私人关系向公共关系转向、构建公共责任和制度化权力关系以及人情逻辑向法理逻辑的转型,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的必然走向。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去人情化”工作风格和治理倾向,似乎契合了社区民主化建设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品格。随着社区工作职业化与科学化的深化、老一辈社区工作者的退去以及现代社会法治化、公民权利的深入,去人情化的脱身策略和治理方式,或许正是社区治理正规化和正式权力关系建构的另类表述。然而,目前这种去人情化的治理倾向和工作风格还远未结构化,因而其对居委会组织的行政属性与自治属性之间矛盾调和、社区民主化建设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验证。但是如同某西方学者总结“信任网络”对政治的重要性时所言:“在民众信任政府的时候,国家往往会变的很强;而在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地方,国家则渐渐变得很弱。”[16]只有更加积极地加强社区参与制度、法制化和社区民主化等基础建设,进而推动居委会自治、居民参与热情和社区信任关系的建立,才是最终实现社区善治和强化国家政权建设的解决之道。
注释
①理论上,居委会干部与专职社工在法律定位、职能分工、产生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详见:李少虹发表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的文章《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居委会干部之专业比较》。但是在社区实践和制度文本中,他们既可以转换角色,互相合作也可以交叉兼职,故统称为社区工作者。详见《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年)中“逐步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论述。为了区分需要,笔者把退休返聘和下岗再就业招聘而来的年长者称为老一代社区工作者,而把专门通过招考招聘而来的年轻大中专毕业生称作新一代社区工作者。
②相关研究还可以参见:王思斌2001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第4期上的《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一文,以及田毅鹏和刘杰2008年发表在《社会科学》第5期上的《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本土化》,杨生勇和王才章2011年发表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上的《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社会工作建构——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探析》,潘绥铭等2012年发表在《中州学刊》上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的本土化探析》等文章。
③按照学术惯例,对文中地名、人名等做了技术处理。
[1]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和社区参与[J].社会,2005(5):78-95.
[2]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9-98.
[3]黄耀明.试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家文化”情结[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9-72.
[4]寿静心.时代呼唤“小巷经理”——城市社区与女性工作者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28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
[6]马志强.从熟人关系到专业关系:社会工作救助模式的转向[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0-144.
[7]于建嵘.破解“政绩共同体”的行为逻辑[N].南方周末,2011-02-10
[8]张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J].社会学研究,2010(6):41-57.
[9]PAN TIAN SHU.Neighbou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D].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Ph D dissertation,2002:169-179.
[10]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撞钟者”和“守夜人”[J].开放时代,2001(12):114-117.
[11]READ, BENJIAM L.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J].The China Quarterly, 2000.
[12]桂勇.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231
[13]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1-38.
[14]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2):10-29.
[15]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J].开放时代,2001(9):5-13.
[16]CHARLES TILLY.Trust and Rule[M].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徐朝科)
Removing Humanized Factors: New Generation Community Workers’Community Governance Tendency and “Disembedment” Strategy
SUN Xuyou
(School of Society and Law,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00, China)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 community worker’s work style and governance tendency. Unlik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ommunity workers, the new generation tends to adopt the “removing humanized factors” approach to deal with community relation and govern community affairs. The disembeding work style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a self identity featuring professionalization, scientific and administrative tendency of community work, self-positioning and sense of selfhood of modern work, temporary employment expectation and female-oriented percep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work. The new generation community worker’s practice, may not only obstruct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in the short term, which will lead to dissociation of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organization and loss of its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and mobilization ability; but also bring the reversed effect to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 communities, thereby promoting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autonomy. The utility of the “removing humanized factors” governance tendency is to be observed and verified, but to reach good community governance still needs us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trust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y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community worker; removing humanized factors; disembeding; community democracy; community governance
2015- 12- 04
孙旭友(1981—)男,汉族,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
孙旭友.去人情化: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倾向和社区“脱域”策略[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16(4):49—55.
C916
A
1671- 623X(2016)04- 0049- 07
——致敬殡葬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