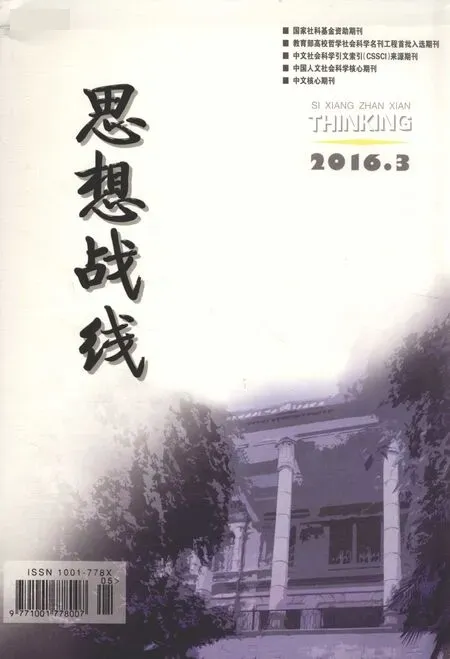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
——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郭中丽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
——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郭中丽①
摘要: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以及其与孩童之间,实现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在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方面,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同域共居,在沐村这个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傣族孩童教养方式启示我们,在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中,应增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
关键词: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构建
云南红河流域居住着近15万傣族,其中新平县境内就有大约5万人。沐村即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漠沙镇大沐浴村,是当地一个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104户,430人(2009年统计),妇女以彩带缠腰的筒裙着装,被称为“花腰傣”,与彝族、汉族、哈尼族等民族毗邻而居。地处哀牢山中下段东麓,红河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属“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典型立体气候,具有“天然温室”之称,动植物种类繁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旅游业发展迅速,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较多,经济文化上互市往来,相互渗透,形成了傣族与当地区域内其他民族的联系比区域外同源民族联系频繁得多的格局,受区域内的其他民族的影响非常大,各支系的文化同源异流,各具特点。*参见陶贵学《新平花腰傣文化大观》,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3页。当地傣族孩童教养文化与周边民族明显不同,特色独具。
一、沐村傣族孩童的多元化教养主体
在孩童成长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根据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等学者的观点,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和大教育观念的不断深入,由此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冲击着沐村孩童教养的方式和内涵,并促动其关涉着更多元化的教养主体,如家庭、村寨、学校及其他诸如旅游参与者、大众媒介等。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教养方式是沐村孩童接受社会影响、教育和训练的基本路径。
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并使孩童养成“初级惯习”。也就是说,在孩童养成“初级惯习”的过程中,家庭的重要性比其他教养群体要大得多。在沐村家庭教养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父母和祖父母。孕育喂养,生产生活技能养成,伦理道德教育,性别意识与婚恋观念的导向等,都是家庭教养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观察模仿中,傣族孩童逐渐体验和经历着初期的成长。沐村自给自足、轻松愉悦的生活状态,让傣族在对孩童的教养上显得悠然自得,漫不经心,极少激烈的呵斥和打骂,也很少表现出高期待、高控制的教养特点。在宽松平和的随境式温和型教养中,沐村孩童的成长也往往轻松自由,率性纯真,性格温和,独立性较差,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Baumrind)“宽容型家庭中的儿童缺乏独立性”*俞国良,辛自强:《社会性发展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的研究结论。但温馨的家庭气氛,平和的生活方式,随意的沟通交流,让沐村孩童从小在家庭中就维持了良好的亲子互动,使他们逐渐发展成认知自我、信守承诺、懂得感恩的健康人格,为日后的学校教育做好了铺垫,而各种学校教育的成绩“从根本上依赖于在他们之前进行的初始教育”。*[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的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页。
沐村作为传统的民族村寨,其文化整合性较高,村民们共同享有整个村寨文化空间,延续着他们自己的地方性文化生活。于花腰傣孩童教养而言,家庭与村寨是叠合的,教养时空是重叠的,村寨生活与教养空间的重叠恍惚间让人觉得家庭教养就是村寨教养,村寨教养就是家庭教养,两者合而为一。在家庭和村寨之间,教养边界是模糊不清的,走出家门就进入了村寨视野中,回到家里仅仅是缩小了生活空间而已;在教养观念认知与实践中,家庭内的教育即为村寨的教育取向,家中这样教,村寨内也这样看待,少见相互背离现象,孩童的“角色表演”反差不明显。傣族不散居的族群集体聚居特点决定了孩童教养的独特性,家庭与村寨在时空上的叠合,孩童教养与村寨生活的相互嵌接,使得村寨是以叠合性濡化的方式对孩童施以影响和教化的,村寨认同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言行参考依据。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
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便已是他的戒律。*[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页。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结合,家庭与家族的结合,尤其是村内“拟亲属关系”的联结,都对族群产生强大的整合功能,形成村民之间平和稳定的内聚关系,成为凝结村落和族群内部关系的重要力量,使孩童从儿时起便享受着互帮互助、温情和融的村寨生活氛围;民族语言、集体观念、花腰傣服饰和赶花街,都是孩童眼中最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互动符号,时空上的交叠让家庭和村寨长期浸润濡化着孩童,共同的教养取向代代相传,教养孩童成为自己社会中所希望的成员。另外,除了民族文化模式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外,村民也在熟悉的村寨文化生活中作出孩童教养的趋同性接受和能动性选择,而且“个体越熟悉对象,也就愈感觉到对象与自身达成统一的愉悦,也就愈亲近这些对象”。*唐震:《接受与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孩童在村寨内受到傣族文化熏陶濡染的同时,也在构建着个体自身的“弟兄”关系、游戏同伴关系以及亲属网络等初步社会关系,在对语言文字、表情手势等符号的学习中理解他人扮演的角色,同时获得社会反馈,从而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产生自我意识,不断强化着民族情感的认同;孩童对鬼魂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的相信或恐惧,使得沐村宗教生活世界对孩童是框束性的,心头隐隐约约的恐惧或是成了遵从某种约束或规范的源头,并用其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处世言行,对孩童有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教育意义。但孩童将信将疑的摇摆不定同时又让孩童游离于宗教生活世界,而往往是仪式中的在场让他们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深信不疑,一旦退场其宗教信仰便又可能土崩瓦解,在框束与游离之间的切换中反复感知体验着花腰傣的宗教生活。
和其他孩童一样,沐村孩童接受着以汉文化为主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家庭教养的补充和延伸,老师是父母教育的延伸,对孩子影响巨大。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学校可以完成孩童社会化,整合庞杂的人口,筛选出不同工作的优秀个体并且发展新的知识体系,将社会中占领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传输给下一代并形成共同的国家观念。因此,作为教育主体角色之一的学校,多采用统一的学制,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选拔制度,的确对沐村孩童施与了个体社会化成长以及社会流动的诸多教育,并力求反复通过各种课程与教学改革,实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和教育互动。但往往是在看似极为公平的教育实施框架内,却难以真正将沐村傣族孩童置于一个教育平台上同等待之。单以学业成就状况来说,地方学校教育往往缺失地方性知识,忽略了本民族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实际需求,更少将其作为地方课程的主要内容列入学校知识体系中,造成学校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区隔;父母、家庭的收入和财产,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家长的教育义务与期望,家庭学习资源,社会交往中的邻里、工作、亲属等关系网络以及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等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形式的不同程度的弱势占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傣族孩童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态度,销蚀着学校教育对当地傣族及孩童的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家庭和村寨内初级生活圈中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和观念的影响,以及语言类型的差异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孩童的学业成就,进而导致沐村村民对学校教育的认知和抉择是有所保留的,对孩童的学校教育持“读得好就读,读不好就退学”的态度,在不强求的期冀中多了一份淡定。
对沐村孩童而言,作为“文化他者”的电视媒介大大拓展了孩童的视野和认知。在萨拉·迪基(Sara Dickey)看来,媒体有助于主体性的构建,传媒信息、文本、生产者、受众主体或消费者都参与了一个竞争互动的整体,消费者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麦克尔·休斯(Michael Hughes),卡罗林·克雷勒(Carolyn J.Kroehler):《社会学和我们》,周杨,邱文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77页。符号互动论也强调,电视以及其他媒体的意象必须首先被观看者界定并解释,然后才能影响观看者的行为。“如果家庭、同辈媒体、学校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媒体意象的意义,那么他们则是社会化的关键主体。”*[美]麦克尔·休斯(Michael Hughes),卡罗林·克雷勒(Carolyn J.Kroehler):《社会学和我们》,周杨,邱文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73页。沐村傣族孩童可以在电视媒介中不断获取社会知识,定位性别角色,在“虚拟现实”中不断模仿或养成个体的社会行为和消费行为等等。但学界研究也表明,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儿童,儿童并不是完全被动地使用媒介,不同的儿童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不同的媒介及其内容,最终的结果也会各不相同。旅游业的发展又给沐村孩童注入了激情与活力,在旅游者的消费过程中,村民与孩童在与外界“他者”的互动中使得自己的生计和娱乐方式更加多样化,商品意识逐渐被强化,也增强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不断牵引着沐村孩童对外流动的向往和决心。
总的说来,这些多元化教养主体因子之间是互动的也是互补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以各自的教养角色影响着孩童的成长。源自各教养主体的技能和学识一起构建出了孩童个体自己。这些孩童把这些文化“并列起来使用”,且“学到的内容是互补的”,只是学习的方式有差异。*参见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3~614页。
二、沐村孩童教养互动机制构建
“机制”是指“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97页。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在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机制往往体现为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制度化了的方法”。*陈丽秀:《构建城区小学家校教育互动有效机制的探讨》,《新课程研究》2010年第12期。据此,孩童教养互动机制是指在教养孩童的过程中,教育主体与孩童之间以及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和互动关系,以及通过这种互动而形成的教育各因子之间的运行方式和运动过程。而“教育因子互动是以人为中心的多边互动。因子只有与人互动,才能产生教育的作用”。*刘廷杉:《教育因子论》,《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域共居与教养主体(如父母、村寨、学校及其他教育者)的教养期待是各因子之间互动的前提。通过以下重要途径,沐村孩童教养互动机制得以形成。
(一)代际间的濡化相承
赫斯科维茨提出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一般是指代际间文化传承的过程,国内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人接受某种文化拟子从而型塑他的文化‘品格’并使其‘文化’‘化’的社会机制过程。”*韦森:《文化与机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页。书中提到的“文化拟子(meme)”是指文化濡化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或人类行为“模仿”的“基本单位”。濡化最初开始于家庭,父母、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等,将本民族的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给子女或晚辈,濡化就开始了。沐村孩童父母及其他长者对孩童的影响是随境式的、宽松平和的、非强制性的,甚至连话语说教都很少,孩童也在“重要他人”的观照视域中安静、内敛地顺应着濡染,实现文化的代际传递,“在家庭濡化教育时期,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代际间的传承使民族文化能够保持连贯性”。*孟志梅:《SOS儿童村维吾尔“家庭”的濡化教育——乌鲁木齐SOS儿童村维吾尔“家庭”濡化教育与和田地区皮山县藏桂乡维吾尔族家庭濡化教育的比较》,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7页。当孩子能自如穿梭于村寨、家庭间隙时,家庭以外的亲属、同辈群体、村民等也被带进了濡化过程之中。在基于共同的教养取向的叠合性濡化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文化熏陶和传递外,孩童在他人的参照中看到自己并按村内他人的期望接受濡化,在建立起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认知村内的规范戒律,感受宗教生活,强化着本民族认同感。不同于家庭、村寨或“他者”教育的潜移默化的濡化,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明确教育目的意识的濡化过程,对孩童接受主流文化内容、形成不同类型文化的学习能力是强制性的参与和介入,孩童对学校规定的学习内容以及各种制度规范,按照各自的意义阐释表现出抗拒、“拟剧”表演或主动融入和适应。文中述及的电视媒体和旅游因子是以“文化他者”的角色深入孩童生活的,电视的高普及率让孩童更加频繁地接触到电视,甚至有“看电视就会说汉话”的鲜明效果,濡化更深。旅游者则是以其参与中的自身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通过动态的或静态的方式向当地沐村孩童予以示范,由个体及群体,再由群体和社会赋予其意义,最终形成示范效应。正如杜威说的“无意识中开始”,“不知不觉”的“继承”,这已是濡化教育中的适应与传承,但孩童及其父母、村民的接受和内化还取决于他们对教养内容、方式的意义赋予。
(二)多元文化互动
多元文化的互动是指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一般有文化的冲突、文化的融合两种基本方式。文化的冲突强调异质文化在相互接触中的敌对与对抗的状态,融合则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调和的过程。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冲突中了解彼此的差异,从而促进相互之间文化的融合。当地傣族与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创造了文化互动的前提条件,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又提供了互动的场域,语言(傣语)、服饰(花腰傣传统民族服装)、节庆(花街节)、宗教信仰(“鬼”世界)以及各种生活习俗等文化符号,既维持着、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族群文化边界。由此,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或者说多元文化“导致教育体系、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个性化变革”。*滕星:《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多元文化也可能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冲突。在文化冲突最为集中的学校教育场域内,对学生不同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并给予公平对待是难以真正实现的,这也让教育者经常在考试升学和傣族学生学力不尽如人意(当地人自说成“读书笨”)的两难中艰难前行。实际上,所谓“带着镣铐跳舞”的教育者,还是得以汉文化作为引导民族文化互动的核心力量。在沐村傣族与其他族群互动的过程中,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都会与“他者”保持一种持续的互动关系,虽然最终各民族的认同及其民族内聚力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族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是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得以形成的文化土壤。
(三)开放式教养系统
自从“大教育观”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被提出后,相信就不会有人把教育还仅仅局限于传统上那种狭隘的学校课堂教育了。有人认为,教育应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综合的大系统,其特点是空间广(各类教育)、时间长(终身教育)、效率高(智能教育)、质量好(未来教育)、内容多(博才教育)。从空间上来说,沐村内外的家庭、村寨、学校及周边生活环境都可能是教育活动的发生地;从教学内容来看,教学目标、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皆可开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叶澜教授认为,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两大类教育活动构成了“教育系统”,而“非学校教育”是指学校之外的其他一切形式的教育,“教育系统”包含着全部的教育现象。而“人类学者正是将世界视为一个相互关联、正在进行的动态系统,方能提供给人们以不断更新中的设计方案”。*冯跃:《教育的期待与实践——一个中国北方县城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5页。这样的“大教育”观念,不仅从理论上为傣族开放式教养系统的构建提供了理解视域,而且也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强化着对教育/教养系统的关注和构型,力求搭建起立体的教养框架体系。
项贤明的解读更为宏大,“对整个人类来说,整个世界就是学校,从宇宙的开始到终结都是学校;同样,对每个人来说,他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学校”。*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理解和构建层次结构庞杂,构成要素、结构关系、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等不尽相同的“完整意义上的教育系统”,其实就是从人的全面生成的角度把握系统的有机整合性这一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也使沐村孩童教养得以在更宏大的框架内多维整合、多向互动,构建起以家庭为中心,依托村寨(社区)、学校以及“文化他者”等教养因子,有序地、连续不断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进而发挥其整体功能,真正构建优势互补的教养互动模式,让其在社会场域中进行“交响乐式表演”,*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124页。每个教养因子既被牵涉进去,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各自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表现出主动和被动的双重态度。通过长期的和日常的生活实践,那些“前理解”慢慢地呈现为“应该那样地表现”的形象和“应该那样做”的模式,以便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网中,逐步确立既有特征的那种关系样态。
三、傣族教养互动中的平衡与守望
傣族具备善于平衡的机制和精神。“平衡”的内涵很丰富,在这里除了包括中国人自创的心理学术语“心理平衡”的理解——人们用升华、幽默、外化、合理化等手段来调节对某一事物得失的认识外,*百度百科:“心理平衡”词条,http://wapbaike.baidu.com/subview/641656/641656.htm?更多的是从动词形态“自我调节使其平衡”角度使用的,也即面对各种情况或荣辱得失时进行的自我调节,让内心世界处于和谐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童的自主性、能动性也在增强。但有能动性并不等于可以自我独立,孩童期的不成熟状态依然决定了个体必须在“群体依赖”的关系状态下才能走向个体独立,从刚出生时的母婴依恋到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同伴关系再到学校里的师生关系、与他族群的各种关系等等;孩童的关系网络以自身为圆心不断进行辐射互动,活动能力在增强,交往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从家庭开始,到村寨内,到学校,由不成熟到成熟,直至最后生命的终结。互动持续不断,当教养各因子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时,花腰傣人的平衡机制开始启动。
平衡涉及整个矛盾系统中的多对对立面。花腰傣人有着平和随意又执著坚韧的刚柔相济的“平衡和谐”。*魏美仙:《生活与舞台的互文——云南沐村旅游展演艺术的个案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花腰傣女人操持家务,主持日常祭祀,参与旅游艺术展演,无疑是家庭和村寨生活的“好手”,但花腰傣男人又在女人难以能及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犁田耙田强劳力、家庭对外关系的建立和协调者、解决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者等等;婚姻关系中,未婚先孕和婚后通奸都会遭人耻笑且被处以“撵寨鬼”或“洗寨子”的重罚(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一旦有孕在身就立即操办婚事,“认得认不得也不管了”)。婚前可以男女同浴,可以在各种节庆节日中约会择偶,男女之间也可以在公开场合打情骂俏,拉拉扯扯有身体接触,也有婚前同居的,但婚后却有着较为严格的夫妻关系,偶有女方外出打工和别人有染的,经常会成为村民们的谈资笑料和鄙夷不齿之事。村民们玩笑中谈及谁谁有“老姘”,其实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性开放。一位大爷说自己真有“老姘”,但只是偶尔路过那村子时进去看看她好不好,双方配偶也都知道,双方都能够平和坦然相待,并不会越矩。外出打工大多为了挣钱回家补给家用,但出去看看,挣不挣钱回家也无所谓。在对待孩子的学习问题上,读书好,考高分是父母和村民们的共同愿望,但面对学业成绩不尽如人意的孩子时,又往往以“考得上就读,考不上就不读,回来还可以帮大人的忙”的心态对待之,孩子承受的学习压力负担不大。
实际上,这种多重矛盾关系的协调维持是通过平衡机制的运作才成为可能的。教养主体在孩童教养比较的过程中获得了“我族群”孩童教养的某种相对优势理解,如从不打骂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自由,“不像彝族汉族那样打骂,心疼,舍不得打”。而这种相对优势恰恰被沐村傣族用来平衡其各种矛盾性关系的内在张力的影响。同时,尽力寻求不同的流动渠道而进行量力而行的教养,通过自我劝说的方式说服自己接受当前现状,“读不进去也没有办法”。最终,当自身难以顺利实现社会流动时开始静观其变,自我守望。家与村寨,成了沐村傣族最后退守安顿的生存之境,避让着与多元文化渗透、植入的冲突和锋芒,在自我平衡中,就此安放了沐村孩童教养的困顿与期冀,守望着一代又一代花腰傣孩童的幸福。
四、启示: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
(一)增强文化自觉
“场域”和“惯习”可以更好地解释教养行为实践。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个“网络”(network)或是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沐村场域中,其传统孩童教养实践就在场域空间运行,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场域的逻辑规则和符号,并通过惯习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形成“持续的”、稳定的“性情倾向系统”,*[法]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故要影响或改变其内化了的、固有的教养惯习是不易的。但这种惯习又是“可以转换的”,*[法]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文化自觉为少数民族教养文化取向转变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边缘”的不同民族参与当代主流社会和经济社会是必要的,不同民族共同体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自我保护与生存的基本条件,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之上的文化或制度需要融合与创新。*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杨红新认为,在快速多变的时代面前,傣民族应该对自己的性格缺陷进行“剖析与自省”。*云南省民族学会傣学研究委员会:《云南元江傣族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而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理解中的“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载潘乃谷,王铭铭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年,第53页。更是民族孩童教养的起点,也是更加合理化教养的良好开端。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要想在社会场域中得以生存、发展,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和自由度,就该尝试着以主体的意识和心态去调整自己的原有惯习,以适应自身在新场域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而且,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多种文化的基础上,经过自主适应,才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多元文化社会,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提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增强文化自觉,对于少数民族孩童教养实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二)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
调查中不难发现,傣族孩童教养文化认同构建过程中,教养主体发挥的效用有所不同,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主要侧重于孩童的主流文化认同,家庭和社区(包括旅游场域)教育则更突出地作用于孩童教养的本民族文化认同。而对于周边其他互动较为频繁的如彝族、哈尼族的教养取向,当地傣族常言“老山头人(指彝族、哈尼族)娃娃读书厉害,老实苦得呢”,有认同有羡慕,却对其教养方式不以为然,“太苦了,又不是吃不饱(意即生活丰衣足食)”,抑或是不忍心严加管教等等,村民在教育子女上很难真正接受他民族的教养行为文化并由衷地理解知识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在人的教养上往往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但他民族的教育文化同样对民族社会成员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需要构建“共生共谐”的“互补机制”,*田夏彪:《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5页。把“老山头人”以及汉人在孩童教养中的坚定、执著、吃苦的传统与本民族文化互补,实现家庭、社区、学校、电视媒介等教养因子的教养实践互补,取长补短,量力而为,顺应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在多元文化理论的期待中,往往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或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导致的学生学习不良的问题,尤其强调教育者应对学校文化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正确对待文化间的冲突,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在国外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启发下,国内滕星等一批教育人类学者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Education)理论,反复强调学生进入多元文化世界的适应力与发展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环境中能够有文化选择的权利,学会尊重和欣赏文化差异等观点,其对“关注弱势群体”“去中心化”“一体化”等关键概念的强调,也让教育者开始以承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整体的观念从多渠道教养孩童。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只有经历一个“自觉的批判、深刻的反思、认真而审慎地选择和接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才能变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前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构建本民族与汉族、与他民族的多元教养文化的互补机制,积极发挥其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教育意义,将会使少数民族教育运行更有效,当然,有效发展需要进行接纳和选择、反思与变革。
(三)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
教养是“活”的,在这种交往式的教育中,沐村傣族孩童教养中特有的平等尊重、轻松随意以及平衡守望的文化取向,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实践提供参考,只是我们需要更恰适地找到教养的平衡支点。
的确如此,过度的教育期待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很难激活个体潜在的创造能力。而当部分父母无力承担子女的教养任务,“对成长中的个体在尚未具备部分生存能力的前提下进行放逐”时,“无期待”(虽然花腰傣人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无期待”)显然也构成个体成长的“潜在约束性要素”。*冯跃:《教育的期待与实践——一个中国北方县城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页、第56页。并且,在学校教育的“效率(学业分数)优先”的框束下,孩童会内化其内含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从而使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认同不同程度地受到消融,在追逐主流文化的过程中消解自我的民族个性,却在面对社区外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时,时常又会感到隔膜和无力。因此,寻找平衡支点,让只追求效率逐渐转向以“人”为本,既不放弃本民族传统的教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也不故步自封排斥他民族的教养行为方式,而是主动适应,扬长避短,在多元化教育理念下进行孩童教养实践,“合目的、合规律地帮助儿童进入文化,实现文化与儿童的双向创生”*苗雪红:《人类学对儿童教育研究的意义》,《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7、8期。,从而丰富和深化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廖国强)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傣族孩童教养研究”阶段性成果(15FJK003);全国教育科学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项目“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与学校教育的冲突与调适——云南沐村傣族个案研究”阶段性成果(FFB108120)
作者简介:郭中丽,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国际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