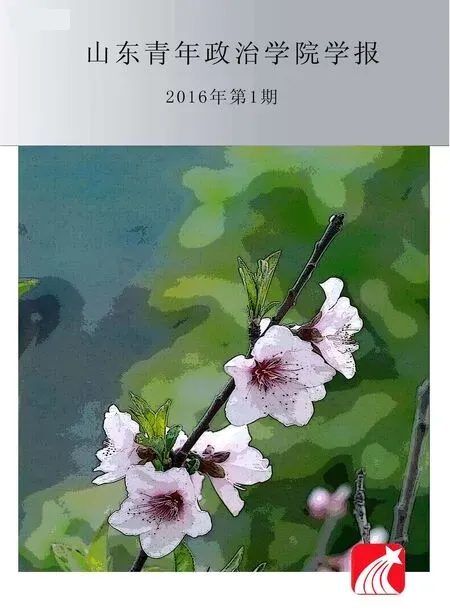中国德育的辩证发展:从传统儒家德育到中国现代德育
孙飞争,刘晓雷
(中山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中国德育的辩证发展:从传统儒家德育到中国现代德育
孙飞争a,刘晓雷b
(中山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摘要:中国德育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德育的正题乃是传统儒家德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德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现代西方德育在中国取得“独尊”的地位,传统儒家德育则与整个传统儒家思想一起,处于一种被解构之境地。这一阶段乃是中国德育的反题。现代性自身问题的不断凸显,招致了广泛的批判;与之相反,传统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则日益重新彰显。因此,中国现代德育的合题应该是二者的优势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我们应该向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中去进行“文化寻根”。
关键词:传统儒家德育;现代西方德育;当代中国德育
纵观中国德育史,可以看出,大致经历了一个三段式的辩证发展过程。在中国传统德育中,儒家德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先秦孔孟创始,至清末西学兴起之前,儒家德育一直居于中国传统德育的核心地位。在这一漫长时期中儒家德育乃是中国德育的正题。清末民族危亡,西学由东渐至大兴,再至中国“全盘西化”,中国德育也突然革命式地由以传统儒家德育为核心一变而成为以现代西方德育为惟一准绳。迨至改革开放之前,传统儒家德育相比于现代西方德育,都始终处于一蹶难振的局面。这一时期,儒家德育可以看作是中国德育的反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巨潮,中国教育改革也在逐步前进。在当代中国德育中,已经有必要重新看待中国的传统儒家德育,正视其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同时,也需要看到中国现代德育全盘西化确实存有弊端。由此,当代中国德育应当整合中国传统儒家德育和现代西方德育,互择其善,优势互补,是为中国德育之合题。
一、正题:传统儒家德育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春秋之前,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时期,文化脉络尚未分明。文化鼎盛的春秋时期,则是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正是在春秋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格局,才肇始了日后中国文化的流派纷呈。尽管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说还只是众说之一。但是,在经历了“焚书坑儒”短暂低潮之后,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家学说历来是中国的正统官方哲学。在此后的中国文化长河中,儒家学说堪称中国三大文化主流之主流,而漫长的文化融合过程,也正是以儒学为主导的。
儒家学说,本身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文化。因此,以其为主流,“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德性文化。”[1]若就中国传统德育而言,则传统儒家德育,更是无可争议地居于核心地位。传统儒家德育几乎可以与中国传统德育相划等。道德,从而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任意一家里,都未曾像在儒家之中那样,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正是以崇尚道德、注重德育的儒家学说“文化天下”,传统中国社会才得以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作为中国德育正题的传统儒家德育,笔者将就其先秦源头略作三方面展开:
(一)德育地位:先导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德育是处于先导地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以“仁”为核心,“仁”乃是居于统帅地位的道德范畴。在《论语》中,孔子对“仁”有过不同的解释,但其最核心的内涵则是“爱人”,孔子对其学生的要求就是“弟子出则孝,入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学说,首先看重的是对受教者伦理道德的培养——先重品德,后辅知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知识需要道德的统御。
尽管孔子觉得“圣人”的标准过于崇高,难于实现,但还是极为注重将其学生培养成“仁人”、“君子”。而在孔子看来,“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就在于道德情操高尚与否。在《论语》中,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照比比皆是,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在教育中对德育的优先强调,为后世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涌现提供了精神动力。
(二)德育目的:德政
作为入世之代表,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与其政治理想紧密结合的。孔子希望以德治国,他对比道德教化和刑罚治国两种模式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刑罚可以惩戒百姓的过失,却不能使百姓产生道德自觉,治标不治本。
从其吁求来看,孔子主张德育的目的,是希望以统治者的德政为标榜,使百姓养成一种道德自觉。孔子强调社会的群体和谐,而只有个人身具道德自觉,其所希望建立的和谐社会方有可能成为现实。正是由于现实使孔子有“礼坏乐崩”之叹,而孔子所追求的又是每个人都具有良好道德的社会,因此孔子才向往尧舜周公之治。当然,这在今天也多少还为其招致了批判,被认为是“社会上的保守主义”[2]。
(三)德育根源:人性
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育思想,都将德育的可能性归结为人性问题。其区别则在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之善源于人天生的“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四心”乃是“仁、义、礼、智”四德之端。因此德育乃是一种“反省内求”或者“求其放心”,是对人性本善之复归。
荀子的德育论则以“性恶论”为基础。荀子认为“人性”乃是天生的,而后天培养的则应该被称为“伪”。人的天生之“性”为恶,而德育的目的正是要对人性之恶加以约束,从而达到“化性起伪”(《荀子·性恶篇》)的目的。
先秦儒家的德育学说,除此之外,还已经开始强调“孝”,这一点,《论语》中多有体现,并且在孔子之后有专门的《孝经》一书。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忠孝社会”。从成效上来看,自儒学独尊之后,“举孝廉”在东西近400年间始终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制度;在此后更加漫长的时期里,“忠孝”伦理也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儒家的德育学说,由于对个人的道德情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从孔子开始,中经孟子,再至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皆对个人提出了修持己心的要求。
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传统儒家德育作为思想正统,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严密而稳定的道德体系,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两千余年发展。然而,近代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了革命者眼中禁锢思想自由的樊笼,必欲除之而后快。“全盘西化”之后,中国教育制度一应仿效西方,传统儒家德育不仅失去了正统地位,而且成为了批判对象。中国德育由正题步入反题。
二、反题:传统儒家德育解构与现代西方德育兴起
(一)儒家德育的解构
传统儒家德育能够长期保持其主流地位,与其政治化的特征有着深刻的关系;儒家德育学说的解构,也就与其所服务的政治集团之衰败同样有着深刻的关系。儒家德育的政治化,使得儒学长期以来处于稳定的状态之中,不仅东汉的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学术和政治地位,甚至在经历过唐朝三教鼎立的局面后,最终在宋明时期所实现的三教思想融合,也还是以儒家为主导。
就民族而论,尊奉儒学的汉民族,尽管在历史上屡遭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举凡能够长治久安者,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学的教化。儒家的德育学说,可以概言为“文化天下”——“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中华民族的融合,也是以尊奉儒学的汉民族为主体的融合,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过程,间断地为汉民族和儒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汉民族和儒学也反向影响了少数民族。
从三教合流和民族融合的漫长历史来看,儒家学说并非是自足完满的封闭系统,而是在以其为主体的融合过程中始终保持了稳定。然而,随着儒家德育学说所依附的封建生产关系的不断衰落,到了明清之际,即使是在儒学德育学说的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批判性的反思。明末清初的儒学大家,纷纷批判“宋明理学”,创立了一种“儒理学”[3]。这种“儒学内部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建构的结果,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思潮”[4]。
西学尽管也是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在晚清之前,还始终无法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学学说,也未对中国传统儒家德育学说构成致命威胁。然而到了清末,随着中国主权的不断沦丧,儒家德育学说不仅倍受内部声音的质疑,而且在西学面前,更加显得不堪一击。“过去,异族的军事侵略从未动摇过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信念,儒学的信条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5]但到了近代,信念终于被打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可以被看作是保留儒学德育思想的最后一次尝试,但终究以失败告终。自此之后,康、梁之派的政治改革虽然托名孔子,实质却已经是“去儒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兴办,使得儒家典籍不再是教育的核心文献,中国的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开始西化。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意味着儒家教育失去了其评价体系。
儒家的德育学说,在由孔子创立时的本意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最终却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作为儒家德育核心的仁道精神,本意是强调德育相对于智育的优先性。但是这种对人格培养的强调,毕竟还需要政治强力的支撑。在与封建政治捆绑到一起之后,儒家德育学说就必然需要面对与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列文森在评论中国近代时期儒家德育学说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时,毫不客气地说:“当儒家传统失去了它的体制依附时,它的理论体系也难以为继。伟大的儒家传统正在衰落,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6]
列文森的论断是有史实作支撑的。不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接踵而来,传统儒家德育学说在中国终于遭受到了彻底的批判,现代西方德育学说则以革命式的狂飙猛进,快速地取代了儒学德育思想曾经的地位。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现代西方德育学说的基本内涵,也像曾经的儒家学说一样,在一段时期里将会被人们当做万古不易的绝对真理来奉行。
(二)现代西方德育兴起
关于“现代德育”,其核心在于“现代”一词。尽管从时间上说,如今每一个国家都正在经历着“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这一提法,从出生到成熟,都完完全全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现代化”也正是以西方为主导而展开的。
“现代”一词,与工业发展有着深刻的渊源,在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化”就意味着“工业化”。而在“现代”背后,作为支撑的思想则是自文艺复兴开始、经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性”。就其内涵来讲,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科技理性、工业理性都可以被涵盖在“现代性”一词当中,而其内涵的核心,则是“理性”。
现代德育思想最初无疑是从西方兴起的,而其传入中国的过程,则恰恰是中国传统儒家德育观念解构的过程。“西学东渐”自明朝开始,持续了很久的时间,但是只有到了清末,工业水平的差距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从最初的器物学习到紧随其后的制度学习,中国的求变努力始终以失败收场,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开始积极向西方进行思想学习,“科学”和“民主”被标榜为两面旗帜。
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功不可没,现代工业社会则对社会成员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相比于更加注重集体价值的儒家德育思想,现代西方德育思想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传统儒家德育与政治相结合,希望建立一种德政,现代西方德育对政治和道德的划分则像产业分工一样精确。具体到中国,“五四”时期的教育家也不再像孔子一样注重培养一种“君子”品性,而是要培养平民人格。此外,现代西方德育的功能由于有学校作为固定的实施场所,并且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在评价体系上也有着科学的量化标准。
作为一个变动的概念,中国德育在此前百余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是一个可以和“现代西方德育”相等同的概念。面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德育事业依旧是方兴未艾,路漫漫兮。问题在于,当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实现,从而中国德育也正在建设之中时。作为现代德育源头的西方,已经开始反思其理论内核的绝对合理性。
毛泽东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当下所进行的,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嫁接自西方的“现代性”,却长期以来始终忽视其如今生长的土壤。事实上,即使不是出于对“现代性”绝对合理性的反思,在文化多元的今天,中国现代德育也必然要重新思考传统儒家德育和现代西方德育之间的关系。
三、合题:当代中国德育的重新建构
(一)传统儒家德育与现代西方德育结合的必要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的这句话,为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从源头上注入了一种开放的精神。因此,“传统儒家有强烈的一元化倾向,但排他性不强,有包容的倾向。[7]”正是这种蕴含开放精神的一元化倾向,使得儒家思想历经冲击而不倒,反而在与其它各派思想相融合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现代西方德育却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中国降生的,从其日后的发展轨迹来看,更多的时候也的确是与传统儒家德育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决裂。
但是,今天重新审视现代西方德育的内核——现代性,科技理性与工业理性使人们处于被异化的境地当中,而对个人的过分强调则导致了唯利是图现象的泛滥成灾。“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带给当代人的病痛就是在精神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8]如果说现代教育在智育上具有传统儒家德育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德育上现代德育对儒家德育的“仁道”精神的解构,则“使现代人从道德信仰中抽离,道德教育仅仅停留在规范的层面上,而难以进入信仰的层面”[9]。这种道德信仰的抽离不仅造成德育的实效性降低,而且“瓦解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愈加明显,而精神上的孤独感与空虚感也愈加强烈”[10]。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区别,具有稳定性,因此很难被釜底抽薪式地加以改变。即使不考虑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缺陷,以其为基础,华夏文化受众如何接受,就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人们的生活需要道德基础来加以指引,但是单纯移植自西方的“现代性”显然很难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始基。
反过来,传统儒家德育,同样难以再次单独担任道德始基。现代西方德育自传入中国之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德育思想被割裂了近百年。如果从按照刘述先的精神儒家、政治儒家和民间儒家的划分,这种割裂最严重的体系则是政治儒家。精神儒家尽管得以传续,但相比之前也已经影响泛泛。唯有在民间儒家之中,儒家的道德思想才得以较好地留存。而在现代性高涨的今日,完全忽视现代西方德育而过分依赖传统儒家德育,也并没有实现之可能。
此外,儒家德育本身需要指摘之处也很多。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审视传统儒家德育,其资源和限制是同时并存的。儒家的思想“附带着盲从权威、愚忠愚孝、讲究关系、做作虚伪一类的陋习”[11],这些因素必然需要弃如敝屐。
从现代西方德育和中国传统儒家德育两方面所各自具有的缺点来看,二者皆不适合单独地作为当代中国德育。因此,在构建当代中国德育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将现代西方德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结合。惟其如此,方能使当代中国德育以最完备稳健的姿态向前发展。
(二)传统儒家德育与现代西方德育结合的可能性
如果说现代西方德育和中国传统儒家德育各自的固有缺陷决定了二者互相整合的必要性,其各自的优点,则是二者互相整合的可能性之一。包括现代西方德育思想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传播,最初更像是以文化入侵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但是在现代西方德育的核心——工业理性——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系统内部和外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之后,现代西方德育的优秀品质最终还是可以得以彰显。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不以民族、国别和意识形态为评判真理之标准的;对自由的强调也意味着西方文化具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西方文化过去和现在所表现出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姿态,与其说是本性如此,不如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政治、经济、军事之优势推行的结果。
儒家德育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需要发现的只是儒家德育学说自身的合理性,而这种发现事实上并非难事。撇开其从前与封建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落后的阶级性,撇开“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对个人的强烈束缚。儒家德育思想的“仁道”精神体现出的乃是一种博爱的价值观;对于德育优先性的强调也同样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功利社会中加以反思自身;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和个人自由与个体价值备受强调的今天,儒家德育思想中的“慎独”自律要求同样不失为一种救济心灵的良方。
此外,作为中国德育发展的正题和反题,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史实。而中国传统儒家德育与现代西方德育是否能够结合成当代中国德育的合题,则尚属未知。然而,对于此一点,东亚各国的崛起同样为当代中国德育的这种构建方式之可能提供了旁证——尽管近代中国在经过初步尝试之后,选择了放下儒学包袱来建设中国。当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日本时,儒家文化却并未妨碍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适应现代化的挑战。“相反,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中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都是由日本的儒家学说和理论提供的。”[12]在韩国,儒学同样是“民众政治思想和精英政治方向的唯一基准”[13]。
新加坡在上世纪迅速崛起之后,也看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过于注重物质享受和崇拜金钱和地位的弊病。“过去一直为人所称道的优良素质即传统价值观念如勤劳朴素,刻苦耐劳,敬老尊贤的精神都被冲淡。”[14]青年人则染上了吸毒、好逸恶劳和生活颓废等恶习。在此情况下,新加坡开始考虑实行传统儒家德育,并成为将儒家道德伦理编成教材在中学讲授的第一个国家。今天看来,儒家德育在新加坡的推行同样未曾妨害其现代化,反而使其国民素质备受国际称道。
现代西方德育和传统儒家德育都具有包容的性格,而东亚其他国家将二者融合的成功经验也印证了将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作为“东亚文化圈”国家,其融合经验直接为中国提供了实践借鉴。
(三)德育的“还乡”:中国德育向传统儒家德育的辩证复归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文化根源,西方文化的根源与中国文化的根源并不相同,传统文化乃是中华文化的根源,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近代以来的长期割裂而改变。叶飞将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的传入和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过程称为“文化拔根”[15],而这一文化拔根的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我们在许多时候缺少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当代中国德育需要进行寻根,而其文化根源就只能是传统儒家德育。因此在整合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和现代西方德育思想时,就应该以前者作为整合过程的基底。“个一个民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家’可归”[16],而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则无疑是传统儒家文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描写了“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这实际上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寻根。人的理性冲破了神话束缚却最终蜕变成了新的神话,这正是西方现代性文化寻根的原因。因此当现代性在今天面临了诸多问题,传统儒家思想开始引起世界性的关注,西方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借鉴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以其自身的文化根源作为基底。
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也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开放融合,这种融合过去无论是以儒家为主体,兼容诸家,还是汉民族为主体,兼容诸民族,都只是同一个文化系统内部的整合。而今天,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和现代西方德育思想的融合则是中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整合。但是,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依然需要有一种主次之分。因此当代中国德育对传统儒家德育思想和现代西方德育思想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当是向传统儒家德育的一种辩证复归。因为,诉诸于“人心秩序与道德建构”[17]的传统儒家德育思想才更加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当代中国德育思想的这种文化寻根,也正是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德育还是现代西方德育都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只有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前提之下,向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寻根,并将中国传统儒家德育与现代西方德育作一有机的整合,当代中国德育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陈守聪,王珍喜.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德育构建[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9.
[2]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5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213.
[3][4][9][10][15]叶飞.现代性视域下的儒家德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集团,2011:34,34,120,120,77.
[5]唐文明.与命与仁[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
[6]列文森著.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73.
[7]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85.
[8][16]郭齐勇.论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G]//儒学与道德建设.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52,77.
[11]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89.
[12][13]黄炳泰,著.儒学与现代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M].刘李胜,李民,孙尚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473,476.
[14]王永炳.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A].儒学与道德建设[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95.
[17]戚万学.京师道德教育论丛总序[A].现代性视域下的儒家德育[C].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集团,2011.
(责任编辑:孙书平)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to the Chinese Modern Moral Education
SUN Fei-zheng1, LIU Xiao-Lei2
( 1.College of Marxism; 2.Rsearch Center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Abstract:Since ancient times,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dialectic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The thesis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is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Since modern times, modern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has obtained the overlord position in China, whereas,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has been deconstructed.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ing of the problems from modernity itself, modernity drew widespread 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the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was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Thus, the synthesis of Chinese modern moral education should integrat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and modern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we should find our cultural roots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Key words: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Modern Western Moral Educ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1-0091-06
作者简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中国个人品德建设的文化生态研究”(12YJA710041) 孙飞争(1989-),女,河南许昌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刘晓雷(1988-),男,河北邯郸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