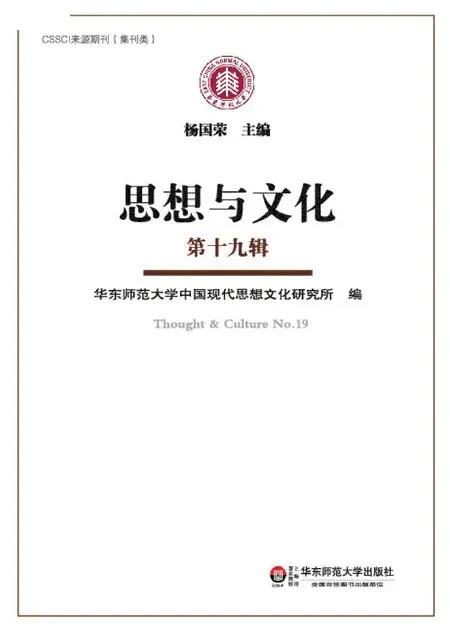〗从人文教化到知识研究
——儒家教育在清末新学制中的转型*
●袁晓晶
前言
儒学发展至清末,遭遇到了千百年未有之变局。儒学内部的争论与西学的冲击纠缠难分,导致了儒家原有的教育方式从传统教化而逐渐变为新式教育。儒家教育的转型,发生于清末的学制改革之中,这一转型,不仅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社会传播的新形态,同时也影响了儒学发展的新趋势。
清末开始的学制改革,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它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教育观念的转化,同时更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在教育史的研究中,清末的学制改革研究一向居于重位①教育史中关于学制改革的文献有1989年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大型丛书《民国丛书》中收录了周予同先生编著的《中国学校制度》,此外还收录了《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著)、《中国书院制度》(盛朗西编)和《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姜书阁编著)。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搜集编著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4册。196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舒新城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册。近年来,有璩鑫圭、唐良炎编的《学制演变》(收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丛书),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酝酿、颁布及执行之全貌。,这是由于清末的学制改革从三大方面,促成了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首先,在学校体系上,表现出对传统“双轨制”学校体系的突破。由太学、庠、序,一变为新式学校。并且,在此基础上,设立大、中、小学堂并推行以“实用”为主的各类实业学校。②清末学制改革对近代学校建设的影响,一直是学制改革研究的重点内容。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新教育》杂志1922年,学制研究专号)、蒋维乔:《清末明初教育史料》(参见《学制改革》一书附录)、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桑兵:《晚晴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等都是对此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最新的研究有:陈睿腾《从学校教育制度看〈钦定学堂章程〉的废除》(《教育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27页),刘辉、王小丁《论壬寅-癸卯学制与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58页),杜永清的《近代学制研究综述》(《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2期》,大致廓清了对近代学制研究的现状,从教育史研究的角度,梳理了近代学制研究的现状等。其次,在行政体系上,开始对传统的“吏师制”有所分化。“学部”的成立,本着以独立于皇权的身份来行使全国的教育管理工作,分化了原有的皇权对于教育行政的控制力。师长的身份也由官员一变为教员,进一步分化了权利的拥有者与教育的传播者之间的关联。最后,在实践体系上,改革了传统教育中所强调针对士子的经学教育。一方面,推行各类学科的综合发展,引进西学、物质教育,加强军事、体育的教育,不再独尊于经学;另一方面,强力推行普及教育,兴办乡镇的蒙学、小学,设立贫民学堂等,甚至延伸至女子教育的开创。虽然其实际的影响并未达成“全面教育”的效果①当时的新学校的普及率,较之1895年,已有了较大的进步,即便是偏远的蒙、藏、新疆地区,也开办了新式学堂。参见桑兵:《晚晴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3页。而实际上到了1908年,全国的学生总数为874 642人,仅占总人口的0.21%。参见杨齐福《清末明初新教育发展缺失略论》,《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20周年论文集》(3),2009年。当时对于新学制的推行状况,清政府还举行了大型的全国教育情况的调查与统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元年(1909)连续三年,公布教育统计图表。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第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但却依然撼动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教育观。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学制改革在针对传统教育体系进行变革的同时,更直接地撼动了作为传统教育体系内核的儒家教育。进一步而言,是对作为传统教育的核心价值及核心内容的儒学传播及其自身形态的重大改变。其一,新学制的变革,意味着西学、新学对中学、旧学的冲击,是现代教育观念对传统教化观念的冲击,儒学必须在面对这一冲击时,努力保证其权威性;其二,儒学也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试图融入到新学制之中,保障其传播的有效性。其三,在内外相合之力下,新学制的变革,亦造成了儒学传播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了儒学自身发展的新形态。儒学由传统的教化之学开始向近代学科体系靠拢,进而形成以德育为主的道德知识形态。
一、中学为体:新学制中儒家教育之地位
学制,即学校制度,指得是由国家所制定的学校系统的制度,它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年限、课程及考核等相关内容。学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传统的学制以双轨制运行。官学与私学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官学主要针对贵胄士子进行教育,为官僚体系选拔人才;私学主要针对中下层的士大夫基层,它虽然也为官学储备人才,但同时也强调私人性学说的传播,与官学既有联系,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成为民间教育传播的重要组织。从隋朝起,科举制逐渐形成,“以文取士”的风气逐渐取代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以德取士”之风。学校与官僚体系的联系,由此加剧,并使得以往学校的相对独立性被取代,成为了为官僚体系输送特定人才的机构,丧失了学校本身的自主性。这是对中国学校制度①周予同将学校制度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上古时期(三代至战国),中古时期(秦至南北朝),近代时期(隋唐至清代中叶),现代时期(清末至民国初年)。参见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民国丛书》第45卷,上海:上海书店,1933年。发展的严重打击。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时,“八股取士”的风气尤重,考试之内容,又以儒学经典为重。乾隆九年谕云:“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可见《四书》之重,是士子们参加考试的首块敲门砖。对于考试文章的评价,也以“理、法、辞、气”为准。“理”,就是儒家之理,具体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义理”,以及宋儒的思想精神。②龚延明:《论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为科举制度废除百年祭而作》,《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30页。这样一来,八股取士为官僚系统所输送的人才,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难以应对时局。清廷囿于取士之路的限制,导致了新式人才的缺乏。同时,也导致了儒学自身发展的枯竭。
虽然,1900年前的清廷,尚不能以彻底取消科举来实现对这一局限的突破。但是同治初年,清廷开始了改革传统学校制度的尝试,意在维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宗下谕建立新式学校:
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於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从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为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力。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22页。
新式学堂的建立,依据的虽还是传统学校制度之根基——“圣贤义理之学”,但在内容上则力求能容纳西学,以求实用。在考试内容上,也与新学校的建制相互配合。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诏谕《策论试士禁用八股文程式》中:
己卯,谕:科举为抡材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戈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自此次降旨之后,皆当争自濯磨,务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究心经济,力戒浮器,明体达用,足备器使,庶副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①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
一方面,在新的考试中将禁用“八股”文体,但是在试题的范围上,还是强调儒家的学说为最基本宗旨。另一方面,以往立于头场试地位的“四书”,被政治、史论所替代。可以看出,清廷力图以“务实”的态度来改革考试方式,与新学校的建制有所对接;但同时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作为其根本的指导原则。
这一改革的思路,在清末的新学制中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七年(1902),张百熙奉旨为官学大臣,拟奏学堂制度,遂有《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又“宥于满汉畛域之见,再加入满人荣庆、及张之洞之参与,方正式议定新制,颁布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②沈云龙:《编辑说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页。,史称“癸卯学制”。张百熙在《进程学堂章程折》中称:
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
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
着笔点皆以西洋之法,佐证中国旧制。可见最初的改制其权威性的来源虽有借鉴西方,但根本还是依据中国传统。古今之别,在于学校与人才的统一与分裂。在“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恢复古制,即是要以传统上学校与人才的统一,来改变当时学校已成为空壳的局面。因此,改制就是要将“复学校之旧”视为“第一要图”③张百熙:《进程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42页。。
这种“求革新,实复古”的改制思路,并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而是儒学在新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为力保其权威性,而采取的策略。在学制改革之初,清廷内部力求以“逐渐变通”为上策,而反对“骤行偏废”。尤其对“尽举‘六经’‘四书’概置不读,即有奇材异能,而于大纲大本之地未加讲求”的做法深为排斥。①王之春:《安徽巡抚王之春:复议新政疏(节录)》,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7页。虽然,此时“独尊儒术”的表达已开始遭到怀疑。但是,一方面,新学校的人才培养与新人才获取权力之间的途径依旧密切;另一方面,新学制又借复古来表达对儒家教育观念的重视,使得儒学依旧处于新学制中的核心地位。
儒学的核心地位,在张之洞等人次年奏请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被明确得表达为“中学为体”的原则。此次新订的学制,“详细推求,倍加审慎”、“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之改之,其有过于涉繁重者减之”。②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97页。可见学制改革已受到了清廷内不少儒臣的支持。这次学制改革比之上一年的改革,不再强调“复古”之道的正当性,而是采取了张之洞等人所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③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98页。
清廷新学制的本意在于为朝廷培养新人,可防流弊。所谓“流弊”在清廷看来,不光是儒生们空谈八股,流于清议。更严重的流弊则在于“图救世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④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页。正因学者无所主,而新旧之辩愈激烈,清廷的权力危机就愈深,社会之动荡也愈加无法控制。面对已经到来的西学狂潮,张之洞认为,必须要折中中西,因而,只能走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
由此观之,清廷的两次学制改革,都坚持了“中学为体”的核心原则。这就使得儒学在新学制中,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权威性。但是,随着新学制的不断推进,儒学的权威性愈发的徒有其表,从而在实质层面,发生了变化。
二、由经世致用到道德教育:新学制中儒家教育之新形态
儒家虽然是新学制的“体”,但在应用之处却颇显乏力。两部学制中的儒家的角色,几乎都只能起到道德教育之用。这与之前所流行的“经世致用”思潮大为不同。
宋明间儒学强调心性之说,其学术末流,更是流于心性空谈,“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黄梨洲语)所以晚明大儒黄梨洲等,才以“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愚儒之学”为宗,追求经史相合,治世之实学。魏源等人在求学之实用的维度上继承了黄宗羲之说。以魏源、龚自珍为代表,建立了顺、康间的“经世致用”之学①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7页。。魏源批评“庸儒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②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页。,是丧失儒学之本意。他认为:“今必本夫古。轩、挠上之甲子,千岁可坐致焉。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③魏源:《皇朝经世文·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1页。故作《春秋公羊论》、《孝经集传序》、《孟子小记》等文,返求诸经,立意为“验于今”之“治”。但这种经世致用思潮,在遭遇到西方的多次冲击之后,开始陷入了困境。儒家虽有“经世致用”之理念,而在实际的“致用”过程中,却远不如西来的物质之学。经世的理想与致用的现实相分离,导致在晚清时期的经世文编中,儒家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④在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中,就曾指出“儒行、文学、师友等子目”“于富强之术,毫无补益”而不予采用。参见章可:《论晚晴经世文编中“学术”的边缘化》,《史林》,2009年第3期,第71页。这一转变,在新学制改革中,更为突出。如果教育的实用之功,无法从儒学中获得,那么就只能外求于西学之中,如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有:“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这里所指的“实际知识”即是“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物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①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168页。夏偕复的学校“当具生活必要之智识技能”,又因“农、工、商各事业学校为富国之本源”,②夏偕复:《学校刍言》,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178页。宜大力兴举。日本人辻武雄所倡言应学习欧美之“日夜孜孜讲求政治、法律、经济、兵法、历史、舆地及农、工、医、商学术,其人材之盛,勃然可观,各出其所学以效用于国家,立功立德,不亦盛乎”③辻武雄:《支那教育改革案》,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192页。诸种论说,皆认为西学有“致用”之功,而儒家的经世理念,则无力对抗西方的物质之学,从而只能于别处寻找“经世致用”之可能。既然儒家不能依靠自身完成“经世致用”的理想,那么,新的学制之中,儒家只能转向其他方向,来体现自身的价值。简而言之,即是由此转向了道德教育之维。
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明确以“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④《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43页。。故而,各省高等学堂课程,无论政科、艺科,皆“伦理第一,经学第二”⑤《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45页。。《钦定中学堂章程》中,中学课程“修身第一,读经第二”⑥《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73页。。《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而道德依旧以“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为基本课程设置。⑦《钦定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79页。至于《奏定学堂章程》中,更是突出了儒学的道德教育之用。“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⑧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97页。,因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强调“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所授课程“修身第一,读经讲经第二”。至于高等小学、中学均以“修身第一,读经讲经第二”,高等学堂则以“人伦道德第一,经学大义第二”。⑨《奏定高等小学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338页。对照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不难看出,修身即是“德行”为主;读经则是“文学”之功。二者列于新学制科目中的一、二条目,恰是以儒家作为新学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不仅在新学制的课程规定中,儒学之于德育教育如此重要,当时的知识界也多对儒家的道德教育之功用抱有信心。如梁启超所谓“新民说”,虽是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但其依据依旧是要使“过往之善良思想复活”,由《孟子》“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而发,要“淬厉其所本而新之”①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梁启超的《新民说》写自1902年到1906年之间,是东居日本后受日本思想界影响而成之书。当时寓于学制改革中的儒学教育之转型,多受到了日本思想界的影响。1902年,杨度与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谈论《支那教育问题》,其中嘉纳氏对儒学之观点,即将儒学视为道德教育之本:“德育仍宜用孔子之道,而必得学人取其精理,以作为教科书,由浅入深,由粗入精,以教幼儿及于成童。惟宜审度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适宜之性质,不可徒为迂远之论,乃为有用。”②杨度:《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页。又如罗振玉所言:“守儒教主义,使学与教合一。(他宗教皆主神道福利之说,故宜教与学分。儒教主伦理致用,故宜学与教合。)”③罗振玉:《学制私议》,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161页。亦强调了儒家在道德教育中的典范作用。
通过新学制的改革,儒家教育在其实行过程之中,逐渐转向了道德教育之用。这对于以往以人文教化为目的的儒家教育而言,是一重大的转型。但是,儒家在新学制的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影响,却因为“体用不一”的弊端,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使得由教化而至道德教育的儒家,进一步滑落到了新式教育的学科体系之中,最终走向了知识化研究的倾向。
三、由道德教育到知识研究:儒家教育新形态之发展
清末学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儒学一方面主动承担了新学制中道德教育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运行,作为德育主体的儒学也被迫发生了新的变化。具体而言,即是在被置之于蒙学、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中的儒家教育,随着学制改革的推进,在新学科观念逐步渗透和与其他学科竞争其功用的过程中,逐渐地被视为了众多普及知识中的一种。
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中指出:“中国办学之初,大家心目中只知有人才教育……光绪二十八年《奏定学堂章程》开始顾及到一般人民之教育。”①陶行知:《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1074页。在《奏定蒙学堂章程》中,就规定:
第三节 城内坊厢、乡镇、村集,均应设立蒙学堂;
第五节 凡家塾招集临近儿童附就课读……
第八节 蒙学堂之设,以多为贵。凡地方官绅,总宜竭力督劝,俾儿童咸有成就之始基,不至荒学失时,终身废弃。②《奏定蒙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290页。
在蒙学堂的具体课程中,修身、字课、习字、读经与史学与舆地交叉上课,虽然儒学之经学、小学、修身等,依旧是课程的重要内容,但不过是诸多“科目”之一,其功用偏重于知识的普及,其目的在于使儿童不至于荒废,而有所成就。较之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教育之道而言,此时的儒家教育已远非“成己成人”之教。进一步而言,随着蒙学的推广,被置于新学制系统下的儒家,也逐步地由原有的人文教化之义,向知识研究的维度转化。
以往对儒生士子的“教化”在于正心诚意、化成天下,偏向于“育人格”;而新学制改革后的“教育”在于普及文字、育人常识,偏向于“懂知识”。儒学在新学制推进的过程中,非自觉地走向了这一趋势。
首先,新学制改革中,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从而打破了儒学原有的“四部之学”的体系,儒学渐落于与其他学科一级的地位。西方学科观念在甲午战争后,迅速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所接受。③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1901年,张之洞等人在新学制改革中,综合英、法、德、日各国大学分科设置,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大学分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七科分学”,这其中,传统经学和文学同属于经科。④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185页。但到了1902年,张百熙重新设计了“七科分学”,取消了经科,而是在新设立的文学科中将经学纳入其中。这样以来,经学的地位便与同样被纳入文学科的史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列为一个等级。在具体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如大学预备科,作为道德教育核心内容的儒家,虽列有《书》、《诗》等经为授课内容,但因授课年限限制,又与诸子、词章等列于同级,而趋于普及知识的传播,大不同于旧时儒林士子的“穷经”之法。虽然至1903年,张之洞又重新提出“八科分立”,加入经科第一,但这时已无法扭转儒家在新学制体系中与其他学科相提并论的局面。
其次,新学制改革中,教师团队发生了变化,海外师资、留学归国者以及新师范教育所培养出的老师,逐步取代了以往的传统儒生。仅以日本学者荫山雅博的统计为例,1903年日本人在中国担任教习及教育顾问者为99名,这一人数至1904年升至163名,到1909年达到顶峰,有424名。①荫山雅博:《清末における教育近代过程と日本人教习》,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日本:第一书房,1983年,第9页。虽然日籍教师并不担任经学的教育,但在“教育、博物、卫生、物理、理财等”②荫山雅博:《清末における教育近代过程と日本人教习》,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第28页。科目均有教授。尤其在师范教育中,无疑对培养新的教师阶层,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在这样一股新势力的冲击之下,往旧之儒生士子,则面临穷困潦倒,不得已在乡间以“行医”糊口。在众多的失业者中,曾排为四民之首的“士”,更是“穷困者,十之七八”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随着曾承担“传道”之责的儒生阶层逐步从新的学制体系中退出的过程,“以身传教”的儒学教化,也逐步地转向了一般普及性的知识教育。
再次,新学制改革后,社会对于人才的评价标准已不同于科举时期的八股取士之风。尤其是在废除科举之后,从学生自身到社会对教育规范的评价,都不再以通经之儒为单一标准。“自国家变法以来……所重者外洋之法……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26页。“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从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以至于“师道之衰于今益甚”(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0页。。儒学更进一步的在社会对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中,而趋于边缘,逐渐成为知识体系中的普通一科。
由此而发展出的儒学知识化的倾向,亦加速了近代以来儒学研究的革新。第一,就方法而言,儒家经典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地位。由新学制而教导出的民国人士,已对儒家经典不再尊崇。第二,就学科而言,儒家开始主动与西方之学说汇通、融合,将自身视为诸种学科体系中的一种,以“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来主动实现中西学说之贯通。另一方面,新的儒学研究动向,反作用于儒家之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知识研究倾向,从而使得儒家进入到了较为封闭的研究体系之中,而非传统的“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的实践体系中。于是,作为众多知识之一支的“儒家知识”,在科举被废除之后,更不能从制度的层面作用于社会。集学统、政统、道统于一体的儒家,在不敌于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新教育观念后,逐渐瓦解,从而愈显腐朽、陈旧。
简而言之,尽管清末的新学制本着“中学为体”之宗旨,然其实行却“种瓜得豆”。最终使得儒家教育的形态由传统的教化,转向了道德教育,并进一步走向了知识研究的趋势,而这一变化,亦预示着儒家在近代的曲折命运。
结语
清末的学制改革,自上而下推行,不仅是清廷力图挽救自身衰败之举,同样也是儒家的既得利益者所发动的一场改革。在这一场学制改革中,儒学逐渐由独尊之位,下落到与其他学科相平等的地位,最终又因丧失了科举制度的保证,而落得比其他学科(西学)更边缘的地位。新学制改革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力图将儒家立为学制改革之正宗,以儒学为体,统摄诸学。然而,体用不一的矛盾,使得这一努力也仅仅存在于颁布的学制文本之中,未得到贯彻。社会所需之人才,由中学转向西学,张之洞等人“慎防流弊”之目的未曾见效。
在此等环境之下,儒学由教育之大本一落为道德教育,再落为普通知识之组成。作为“知识”的儒家,在身份上演变为“价值中立”的客观对象,在内涵上又与西学冲击下的新观念多有矛盾,因此,传统德育之功能不免失效。唯有作为普通知识的儒家,还存在于学校之中。但作为知识形态的儒学,在遭受废除科举、取消读经等一系列打击,几乎覆灭。最终,被作为填充于新式教育体系的素材,而被碎片式的保存了下来。这也是儒家教育在近代以来转型的曲折命运之管窥。当代儒学复兴,方兴未艾,尤其是作为对现代教育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传统学术正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当代教育的学科建设中。
首先,现代学科系统是自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因受到民族危亡的时代危机影响,此借鉴过程可谓逐步“全盘西化”。蔡元培在1912年在民国教育部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时提出: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含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①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第617—623页。以教育当超越政治,全盘否定了晚清的学制改革,进而否定了“经学科”建立的合法性。“经学科”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学术体系的彻底崩溃;另一方面,也奠定了现代学科体系“去传统化”的基本趋向。这一趋势,在当时是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有效地为积弱贫苦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的新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救国”的目标。但是,这样一种趋向,在中国历史的百年嬗变之后,则需要一番全新的审视,才不至于使中国教育,尤其是学科建设,丧失本民族的基本特色。
其次,教育要回应时代问题,但更要有超越的眼光。晚清的学制改革,使传统学术走向了知识研究的维度;民国的学科改革,使教育超越了政治的藩篱。在现代学科建设中,既注重知识性、基础性学科的建设;发展和创立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的功效,积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科技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注重传统优秀文化在学科建设中的重建,对于增强本民族文化自信、文化传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从传统的人文教化到现代的知识研究,儒学学科化的改革在其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古今中西之争”的影响,经历了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怀疑期”,并在怀疑的过程中,逐渐生出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转化的“创新期”。当代学科建设的改革,恰恰证明了在积极拥抱知识研究的同时,学科建设仍应重视传统的人文化成,学科建设应立足本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才可能回答这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具有既有传承,又有革新的学科体系及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