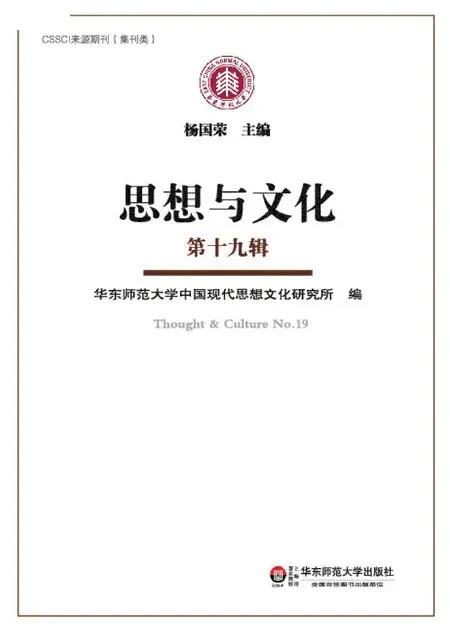〗论格林对康德伦理学的挑战*
●江宇靖 孔文清
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虽然在休谟提出了“是”与“应当”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鸿沟以后,任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与道德哲学的理论联系起来的企图都会马上受到是否忽视了“是”与“应当”之间存在着逻辑鸿沟的质疑。自然主义的谬误是随时都有可能贴在他们观点上的一个标签。但是,这一阴影似乎并没有阻挡住科学家的脚步。在最近的研究中,通过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来讨论伦理学问题的大有人在,以至于出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神经伦理学。这些研究在国内也引起了反响,亓奎言、朱菁、李建会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相较于达马西奥的小心翼翼,格林在其研究中则大胆得多,将其研究直接与伦理学理论联系在一起。本文拟就格林的实验对康德伦理学的挑战作一点分析,试图辨明格林的挑战中是否存在错误,以及格林的研究是否对伦理学有意义。
一、格林的实验
与其他科学家不同,格林的研究一开始就与伦理学紧密相关。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试图找到道德判断与人的神经活动之间的联系。通过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格林的研究团队对被试处理道德难题时的大脑进行扫描,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找出人们在处理不同的道德难题、得出不同的结论时,大脑的哪些部分参与了工作,哪些部分更为活跃,并找出不同的结论与大脑活动的方式间的对应关系。
实际上,格林在实验中对伦理学问题的涉及是逐步深入的。在2001年发表在《科学》的论文中,格林在实验中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人们在电车困境中会选择牺牲一个人去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而在天桥困境中同样是面对牺牲一个人去挽救五个生命的困境,人们却会做出相反的决定。格林通过对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中被试做出不同结论时大脑活跃区域以及反映时间的不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不同的关键在于天桥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反应而在电车困境中则没有。”①Joshua D.Greene,R.Brian Sommerville,Leigh E.Nystrom,John M.Darley,Jonathan D.Cohen,“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Science,Sep.14,2001,293,5337,pp.2105 2108.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在电车困境中要挽救五个人的性命,只需按一个开关,而在天桥困境中则需将一个人推下去。格林将前一种情况称为非切身的(impersonal),后一种情况则是切身的(up and personal)。切身的情形更能激发人们的情绪、情感反应,而非切身的情境则更少会激起这种反应。正是在“涉及情感之间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判断”①Joshua D.Greene,R.Brian Sommerville,Leigh E.Nystrom,John M.Darley,Jonathan D.Cohen,“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Science,Sep.14,2001,293,5337,pp.2105 2108.。这时,格林对自己的实验还是很谨慎的。“我们主张情感反应可能是这两个例子中的关键差别。但这是一个对心理谜题的解答,而不是对哲学谜题的解答。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我们没有主张实验表明哪种行动或判断是对还是错。我们也没有认为情感反应是判断这些道德困境的唯一决定因素。”②同上注。
在2004年的文章中,格林对人们处理困难的道德困境与容易的道德困境进行了实验,认为在处理困难的道德困境(哭泣的婴儿案例)时,人们面临着情感与认知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反应时间较长。而在容易的道德困境(杀婴案例)中则不存在情感与认知之间的冲突,因此反应时间较短。进而,格林将这个实验与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在得出功利主义的结论时,需要认知活动在冲突中战胜情感反应,这反映在实验中就是大脑中与认知相关的部分的活动更为活跃。“我们认为,道德哲学中的功利主义与义务论(deontology)规范之间的紧张反映了人类大脑结构中更为基础的紧张。我们继承自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并被文化经验塑造和修正的社会情感反应,构成了作为义务论核心的绝对禁令的基础。与之相对,定义了功利主义的‘道德计算’则可能是由更为晚近进化而来的、支持抽象思考和高阶认识控制的额叶结构所造成的。”③Joshua D.Greene,Leigh E.Nystrom,Andrew D.Engell,John M.Darley,and Jonathan D.Cohen,“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Neuron,Vol.44,Oct.14,2004,pp.389-400.这一结论由以下论据支撑。“首先,我们在义务论的直觉凸显的例子中发现了社会情感过程增加的证据。其次,我们发现在功利主义的判断占优时与认知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更加活跃。”④同上注。在这些实验结论的基础上,格林进一步认为:“它将带来讽刺性的暗示,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从心理学上说,不是奠基在纯粹的实践理性原则上的,而是奠基在被理性化的情感反应上。”①Joshua D.Greene,Leigh E.Nystrom,Andrew D.Engell,John M.Darley,and Jonathan D.Cohen,“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Neuron,Vol.44,Oct.14,2004,pp.389-400.
在2008年的论文中,格林再次确认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义务论的判断倾向于由情感所驱动,后果论的判断倾向于由认知过程所驱动。”②Joshua D.Greene,“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In Walter Sinnott-Armstrong(Ed.)”,Moral Psychology,Vol.3,pp.35 8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格林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为什么义务论与情感走到了一起?我相信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道德情感为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难题提供了自然的解答。其次,义务论对道德情感进行了自然的‘认知性的’解读。”③同上注。格林的意思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类似,认为义务论将情感的驱动力解释为理性的思考过程,不过是一种理性化,或者说是文饰作用。由此,格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义务论可能是错的。”④同上注。因为那些主张通过思考命题、规则的方式得出义务论结论的理论,明显与实验结果相矛盾。义务论与情感,而非与理性相关。
二、格林的问题
对于格林的结论,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例如,朱菁教授在其论文中就曾指出,在格林的推理和实验设计中,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还有可能在“非切身”的情境中做出符合道义论的道德判断。
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朱菁教授还设计了一个案例,并进行了调查。在此,朱菁教授想要表达的观点是,道义论与切身、情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格林的实验只是表明了道义论与情感反应之间的联系只是偶然的,那么“道义论的判断倾向于由情感所驱动”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这样一来,格林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也随之不成立了。
朱菁教授的这一观点确实是看到了格林的一个问题,但格林结论中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首先,我们需要就格林文章中的 deontology的确切含义进行梳理。Deontology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成道义论,也可以翻译成义务论。国内学者在讨论格林的实验时,大都将它翻译成道义论。按照通常的理解,与后果论相对的道义论,主要是指判断一个行为的对错,主要是依据行为本身而不是后果。杀人是错的,是因为这一行为本身是错的,而不是看它的后果。而同样的行为在后果论看来,在不同的情况下却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杀一人而挽救五个人,功利主义会说这一行为是对的。如果杀人只是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人员死亡,而没有造成幸福的增加,或者增加的幸福的数量没有超过所造成的痛苦,那么这一行为就是错误的。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某一行为本身是对是错与基于何种理由得出这一结论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换言之,是根据理性得出杀人这一行为本身是错的,还是根据情感得出杀人这一行为是错的,都可以是道义论的。道义论可以是理性主义的,也可以不是理性主义的。例如,儒家的德性论就带有强烈的道义论色彩,被很多人认为是道义论的。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又说:“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也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儒家的这些主张毫无疑问是属于道义论的。
但是,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不能简单地被划入理性主义的范围的。因为在儒家那里,理性、情感等西方式的分梳是不存在的。这表现为儒家既讲理性又讲情感,而且认为情感是道德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所谓情理情理,情与理是不能分离的。孔子认为情感是道德的构成要素。“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赡养父母是礼的要求,履行这一道德义务要以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爱为内容,这样才真正符合道德的要求。孔子曾以人的感情来解释三年之丧的礼。“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是天经地义的,为人子女者在父母去世后,自然而然地会食不甘味,居不安寝,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也是一种道德情感,而非单纯的道德理性。
即便是在西方,最近兴起的道德情感主义也能在情感主义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道义论的结论。道德情感主义并非是一种纯粹的道义论,而且有时它还需要道义论的约束以防止我们由于倾向于亲近的人而做出有悖于道义的行为。“如果拒绝了道义论,就很难看出关怀伦理学这样的特殊主义如何能够避免允许甚至主张杀死一个陌生人以挽救自己的配偶。”①Michael Slote,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Routledge,2007,p.43.但是,道德情感主义却能在情感的基础上说明道义论的行为。在道德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斯洛特看来,我们理解杀人、伤害等行为本身是错的这些道义论的观点的一种方式是“有着相同结果的主动行为在道德上要比被动的行为更糟糕,例如,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要比任由一个人死亡更坏。”②同上注。斯洛特是从感同身受(empathy)具有的直接性所带来的结果这一角度来解释这一道义论的观点的。“我们对其他人的悲伤的义务的强度根据我们是否知觉了这一悲伤,或这一悲伤是否是当下的,而有所变化。我们也对不同形式的悲痛或伤害与我们的因果关系有着感同身受的敏感,因此,建立在感同身受基础上的关怀伦理学可以认为杀人比任由死亡在道德上更坏,道义论的一个主要部分可以用情感主义的术语做出解释。”③同上书,p.44.按照斯洛特的观点,由于感同身受具有直接的特点,因此,对于那些由我们直接造成的痛苦、伤害我们更能感同身受,而对于那些不是我们直接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感同身受到的要少得多,因此,主动的杀戮、伤害在道德上要比任由死亡、伤害更坏,是我们更不能去做的。
格林在文章中所使用的deontology更多的是与康德的道德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康德的道德哲学正是以义务论闻名于世的。康德的道德哲学既是一种道义论,也是一种义务论。国内通常将康德的道德哲学称为义务论。本文在论及格林所说的康德或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deontology时,将它翻译为义务论。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格林有时候在deontology前面加上了定语rationalist,但是,格林显然是将义务论仅仅理解为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义务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就不会在其实验的基础上得出义务论,或者是理性主义的义务论可能是错的结论了。因为从逻辑上说,一旦肯定了义务论既有理性主义的,也有非理性主义的,那么,即便格林的实验证明了义务论的结论是由情感所驱动的,他只能从其实验结论中得出其实验支持了非理性主义的义务论观点的结论,而不能得出理性主义的义务论是错的结论。
在厘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后,我们回到关键的问题上,即格林的实验是不是对康德的义务论构成了挑战呢?
格林的实验实际上并不能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构成挑战。正如朱菁教授已经指出的,格林的实验并不能说明情感与义务论、认知、理性与功利主义存在着内在必然的联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格林的结论与他所设计的案例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用其他案例来进行实验,结论可能就正好相反了。
试想以下案例:
一位母亲带着两位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但她却不能为他们提供食物。要让这两个婴儿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是杀死并抢夺一个陌生人所拥有的食物。在这种情境下,这位母亲将怎么办?
如果这位母亲认为杀人是不对的,她选择不杀死陌生人而让自己的孩子死亡。这时,按照格林的理解,她是在认知的、理性的驱动下做出了一个义务论的选择。这位母亲的大脑活动应该是代表了认知、理性的区域活动强烈。格林从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位母亲通过理性认知活动得出了一个义务论的结论。如果这位母亲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孩子的痛苦,出于对自己孩子的爱,她选择杀死陌生人,并抢夺他的食物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活下去。她的这一选择是功利主义的,这时她的大脑中应该是与情感相关的区域活动强烈。格林根据这一结果应该得出一个功利主义的判断是由情感所驱动的结论。
通过这一例子,我们不难得到与格林的实验结论相反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我们只要对道德困境中冲突双方的情况做些不同的设计,结论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格林的结论实际上是他对实验的一种解释。而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却并非是唯一的。这也会对在情感与义务论、认知与功利主义之间所建立的必然联系之间带来了疑问。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行为当事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但旁观者却不能建立起这种联系。以功利主义为例。格林认为功利主义需要计算后果造成的痛苦是多少,幸福又是多少,然后经过累加得出后果是幸福多过痛苦还是痛苦多过幸福,这一过程本身是“系统的、计算的”,因此功利主义的判断必然是由认知的过程得出的。但是,人们在判断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功利主义的善恶标准时,只是,并且只能从其结果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来判断,而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心理过程是不予也不能考虑的。这正是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论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上述案例中母亲杀死陌生人的行为是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其动机如何是旁观者不会也不可能去讨论的。
格林的实验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想要从旁观者的视角去确定当事者才能确认的联系,格林是在做从逻辑上说无法完成的事情。试以康德的义务论为例。众所周知,康德义务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是看这一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的,而并非是符合义务的。而格林的实验从逻辑上只能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义务论的要求,而永远无法判断这一行动是否是出于义务的。格林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实验发现被试做出义务论的选择时大脑中与情感有关的部分更活跃,由此得出作义务论判断时被试更多地是一种情感活动的结论。而在符合功利主义(后果论)的判断中,则是与理性、认知相关的部分更活跃,由此得出此时认知的活动更活跃的结论。这一方法毫无疑问只是在判断一个符合义务论还是功利主义原则的行动与大脑活跃部分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判断一个出于义务论的行动与大脑活跃部分之间的联系。
对实验结果进行推测,而不能确定无疑地在行为的动机与结论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这一问题格林实际上是承认的。对于自己的观点,他在论文中不止一次地说自己的结论是“推测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
其次,格林显然没有考虑到另一种情况,即在道德冲突中,我们并非只能在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间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有时候互竞的驱动力或某一驱动力会产生既符合义务论又符合功利主义的行动。
格林得出其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预设了情感与认知活动是互竞的,竞争的结果是其中一种过程导致了我们的道德判断。格林之所以认为情感过程与认知过程是互竞的,在某一种道德判断中总是某一过程战胜、克服另一过程,这与他的实验所检验的都是大脑处理道德难题时的情况有关。道德难题都是存在着道德冲突的,格林进而猜想道德冲突背后存着大脑功能间的冲突。而且,格林显然认为人们的行动要么是符合义务论的,要么是符合后果论的。但是,是否所有有着道德冲突的案例都会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不妨以一个曾被伦理学界使用的案例为例。一个人生病了,他的朋友并不想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却有着探望他的义务。这时他面临着情与理之间的冲突。我们假设这个人在内心中充满着不愿意的情绪的情况下按照道德义务的要求去医院探望了他的朋友。这时,他的行为是符合义务论的要求的。但是,这一符合义务论的行为有可能也是符合功利主义的。如果他的不情愿所造成的痛苦少于他的朋友因为有人去探望而感到的高兴,并因此而病情好转所造成的快乐,那么这个行为所造成的幸福大于痛苦。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这一行为也是符合功利主义的。
在这种情形中,行动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我们可以说去看望朋友的人行动的原因是出于对义务的遵从,但是,如果我们去扫描此时他的大脑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从仪器上看到他的大脑与情感相关的部分是处于活跃状态的。因为他始终是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下按照义务的要求去做的。那么这时我们如何判断他行为到底是由情感引起的还是由认知引起的呢?即便我们将这种情况排除,设定他大脑扫描的结果显示是在认知活跃的部分去看望朋友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将这一原因导致的结果看作是符合义务论的行为,还是符合功利主义标准的行为呢?对这一问题我们恐怕无法给出答案。
最后,即便我们承认格林的结论是正确的、是无可挑剔的,他的这一结论对康德的义务论也不构成威胁。正如前文已提到的,康德的义务论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即出于义务(责任)的行为和符合义务的行为。在康德看来,“道德的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①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而那些出于偏好的行为也可能是符合义务的,但这些行为却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康德并不是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理性驱动的,也并不否认有很多由情感所驱动的行为是符合义务的。他所说的只是,这些不出于义务的行为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在另一方面,保存生命是自己的责任,每个人对此也有一种直接的爱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人对此所怀抱的焦虑,是没有内在的价值的,他们的准则并没有道德内容。”②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第13页。一个热爱自己生命的人保存自己的生命,虽然符合责任,但是却并没有道德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保存自己生命的行为是有道德价值的呢?“反过来,假若身置逆境和无以排解的忧伤使生命完全失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那身遭此不幸的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去和命运抗争,而不失去信心或屈服。他们想要去死,虽然不爱生命却仍然保持着生命,不是出于爱好和恐惧,而是出于责任,这样,他们的准则就具有道德内容了。”①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第14页。从康德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格林的结论——义务论的判断倾向于由情感所驱动,后果论的判断倾向于由认知过程所驱动——即便是正确的,也不会对康德构成任何的威胁。面对格林的实验,康德主义者可以说:哦,确实有很多行为是出于义务以外的动机却符合义务的,就像你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不愿将人推下天桥的行为确实是由情感驱动的,也确实是符合义务论的。但是,这种情况和我的道德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是不相干的。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都是不具有道德价值的。只有那种在面对这一道德困境时,通过思考不能杀人的禁令,并按照这一禁令做出判断并行动的,才是可以对之作善恶评价的行为。我们的道德哲学是讨论这些问题的。
只要存在着如康德所说的出于义务的行为,那么,康德伦理学在格林的实验面前就是泰然自若的。格林如果想要真的对康德的义务论提出挑战,就必须说明所有的义务论的行为都是由情感驱动的,不存在不由情感驱动而符合义务要求的行为。这肯定是格林无法完成的任务,而格林确实也会让康德泰然自若。“人们可以,从原则上讲,通过思考绝对命令以及行为是否基于可以成为普遍律令的法则,而做出典型的义务论的判断。如果可以这么做,他的心理过程将是认知的。”②Joshua D.Greene,“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In Walter Sinnott-Armstrong(Ed.)”,Moral Psychology,Vol.3,pp.35 80.格林不得不承认存在着康德意义上的经由理性思考而做出的道德判断的情况,他不得不承认的,也正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所确证的事实。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着,那么,康德的义务论又有什么错误呢?格林得出的那个康德的伦理学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又从何谈起呢?
三、格林的实验能够给伦理学提供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得不说,格林在得出他的结论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或者说,格林给自己找了一个不正确的攻击对象。如果我们将格林批判的矛头指向其他方向的话,我们会发现,格林的实验对于伦理学而言还是有意义的。
格林的错误在于他把自己的实验结果用来证明他无法证明的结论,他错误地将康德的义务论作为批评的对象。如果他将批评的某头指向道德理性主义——他在2004年的论文确实这么做了,但并没有将自己批评的矛头聚焦于此——那么,他的一系列实验确实能够为我们反对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提供依据。
道德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一传统自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康德。在理性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中,情感、欲望等与理性无关的东西总是被排斥的。哈奇逊、休谟等人的情感主义在这一潮流中被遮蔽得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尼采、柏格森等人虽然对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这些挑战也产生了影响,但理性主义的地位似乎并没有被撼动。理性主义的代表即是被格林批评的康德。康德的理性主义,确切地说是理智主义,将所有经验性的、具体的东西清扫出了道德的领域。人的理智活动、理论思考活动超然于他的身体,身体的存在与参与只能妨碍理智的活动。在道德领域,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应当、是否合乎规则——根据规则进行推理的过程——是一种纯粹理智的过程,它应该关涉到的是概念的推理等活动,而不应有情感、欲望的参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理智主义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人们可以有与情感、身体完全无关的纯粹的理性、理智活动。正是存在着这种纯粹的理智活动,人们才有可能有所谓的出于义务、责任的行动。换言之,才能有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人们能否可以有与情感无关的纯粹的理智活动?这是一个关乎事实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乎价值的问题。认知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可以对这一关乎事实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观点。
达马西奥曾经在一系列的研究基础上,指出笛卡尔的二元论是错误的。他认为所谓纯粹的理性过程是不存在的。人们的理性活动都离不开身体、情感的作用。“生物内驱力、身体状态和情绪可能都是理性必不可少的基础。推理的低级神经基础与调节情绪和感受的加工过程,以及身体本身的整体功能的低级神经基础相同,只有这样有机体才能生存下来。这些低级神经基础与身体本身保持着直接和相互的关系。于是,身体就成为了整个运转链的一环,使得推理和创造力得到最大水平的发挥。理性可能是由身体信号塑造和调控的,即使是在理性表现出它最极端的特性并做出相应行动的时候也是如此。”①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如果不存在能够完全与身体、情感相剥离的理性活动,那么康德的纯粹理性也就不存在了。
与达马西奥一样,格林在这一问题上实际上可以对康德的理性主义提出挑战。格林在他的研究中一再强调一个观点,即认知活动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不存在与情感无关的认知过程。“像休谟一样,我们猜想所有的行动,不管是否由‘认知’判断所驱动,应该都有情感的基础。”②Joshua D.Greene,Leigh E.Nystrom,Andrew D.Engell,John M.Darley,and Jonathan D.Cohen“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Neuron,Vol.44,Oct.14,2004,pp.389 400.在2008年的论文中,格林在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马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说明。“然而,我马上得补充,我不认为这两种途径是严格的情感的或‘认知’的(或存在着‘认知’和情感间的严格区分)。③Joshua D.Greene,“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In Walter Sinnott-Armstrong(Ed.)”,Moral Psychology,Vol.3,pp.35 80.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格林对认知和情感的区分是相对的。认知过程并非是与情感无关的纯粹理性活动,相反,他更倾向于认为认知过程有着情感基础。格林的实验实际上呼应了达马西奥的观点,并比达马西奥更前进了一步。他似乎倾向于休谟的情感主义。而休谟的情感主义恰是理性主义的反面。在休谟看来,理性不仅不是与情感无关的,甚至理性实质上是平静而持久的情感。而近十多年兴起的道德情感主义也正是继承了休谟的传统,试图在情感的基础上构建道德哲学的体系。在康德的理性主义与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之间,达马西奥、格林等人的科学实验似乎更能支持道德情感主义,而非康德主义。
格林的实验还能为另一个伦理学论争提供依据,即不偏不倚地与特殊主义的论争。这一论争实际上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论争相关。这一论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表现为儒家与墨家的论争,在西方则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间的论争。
理性主义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道德判断中,所有的人与事具有同等的意义,不存在某些人和事比其他人更为重要。在道德判断中,对所有人与事,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墨家的观点与理性主义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墨子主张兼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自己与他人、亲近之人与陌生人是一视同仁的。与理性主义不同,很多道德哲学持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观点,例如儒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爱有差等,我们对他人的爱与关心根据他们与我们关系的亲疏,由近及远,逐渐递减。墨子的观点在儒家看来“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认为“仁”“义”首先是亲亲、敬长。“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在亲亲的基础上,然后才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而道德情感主义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认为直接性与能否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的强度密切相关。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直接性的对象,以及亲近的关系更容易通过我们的感官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对它们更容易感同身受。因此,“它使我们倾向于朋友、家人和能看到的人”①Michael Slote,“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Routledge,2007,p.28.。正是由于这一点,斯洛特在讨论辛格的文章时,提出了与辛格不同的观点。辛格认为救助遥远国度的饥荒中的儿童的义务与救助身边人的义务是一样的。斯洛特则认为,当一个儿童在我们面前即将落水时,我们感到的救助义务感要远远强于救助遥远国度的饥饿儿童。其原因是,具有空间上直接性的对象,更容易通过我们的感官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对它们更容易感同身受。
特殊主义,或者说儒家和道德情感主义所持的观点,是否有依据呢?格林提出的切身与非切身之间的区别,恰好可以为特殊主义的主张提供支持。
实际上,类似于切身的、非切身的概念并非是格林首先提出的。弗洛姆在格林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在讨论到现代社会的定量与抽象化特点时,弗洛姆说:“我们所对付的度和维都是些数字和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具体经验的范围。再也没有适合于人类尺度的可以为我们所掌握、所观察的参照系统存在了。我们的眼和耳只能从人所能把握的程度来获得印象,可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恰恰没有了这种性质,认识已不再能与我们的观察维度相适应。”①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抽象与感官直接性之间的区别对于人们的判断与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毁灭。他只消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办到;他大概不会因所做的事感到心情变化,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杀的人,仿佛他按钮的行为与千万人之死没有真正的联系一样。同样是他,可能不忍心打一个无助的人的耳光,更不用说去杀人了。”②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第94页。
格林实验的意义在于,用实验证明了由于感官所激发的情绪、情感在人们的判断和行动选择中具有的作用。他在2001年的论文中对切身的和非切身的问题的讨论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特殊主义不仅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而且有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基础。
综上所述,格林的实验确实能为伦理学提供一些支持,他的研究也确实能够对康德的伦理学提出挑战,只不过它能挑战的是康德理性主义,而非他所认为的义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