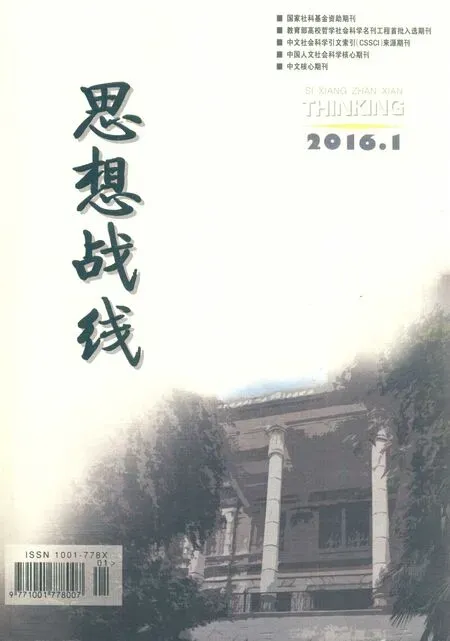中美医学化个案比较研究——以网络成瘾和多动症为例
韩俊红
中美医学化个案比较研究
——以网络成瘾和多动症为例
韩俊红①
摘要:工业化社会一向被认为是医学化的沃土。美国多动症的医学化扩展过程,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越轨行为医学化的典型案例,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医学化,则是发生在中国的典型案例。基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医学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拥有着跨文化的渗透能力。两个典型个案的社会文化背景迥异,并且存在着医学化程度上的显著差别,但二者医学化背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病理学基础,即复杂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归因。医学化的社会后果极其复杂,如何平衡医学化与去医学化之间的张力,是21世纪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艰巨挑战。
关键词:越轨行为;医学化;网络成瘾;多动症;比较研究
回首20世纪越轨行为社会控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一个方兴未艾的社会过程一再重演,这就是所谓的越轨行为医学化进程。所谓越轨行为医学化(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指的是不合乎规范或是道德上评价欠佳的某些表现(肥胖、注意力不集中、侏儒症)、观念(精神障碍、种族主义)以及行为(喝酒、赌博、吸毒),成为医学加以仲裁的对象。*McGann F & Peter Conrad,“medicalization of deviance”,in George Ritzer(eds.),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alden,MA:Blackwell Pub.,2007,pp.1110~1114.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潜在意涵是——有关越轨行为的社会干预由此成为医学界的专属权,医学的社会控制潜能得以激发。通过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社会进程,原本属于宗教系统或司法系统仲裁范围内的越轨行为问题,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逐渐被转换成为临床医学问题,相应的治疗实践蓬勃开展,越轨行为者最终成为医学意义上的患者。医学化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色彩,它指出,现代医学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张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医疗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些新兴的“疾病”范畴,本质上更可以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晶。分析医学与社会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机制,并揭示蕴藏其中的理论意涵,正是医学人类学介入医学化问题的独特贡献所在。
就其具体类别而言,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案例可谓层出不穷。以美国社会为例,诸如多动症、*Peter Conrad,Identifying Hyperactive Children: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Burlington,VT:Ashgate,2006.吸毒、*Peter Conrad & Joseph W. Schneider,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From Badness to Sickness,Expande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0~144.同性恋、*Peter Conrad & Joseph W. Schneider,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From Badness to Sickness,Expande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72~213.虐童、*Pfohl S,“The‘discovery’of child abuse”,Social Problems,vol.24,1977,pp.310~323.精神障碍、*Thomas Szasz,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NY:Harper & Row Pub.,1974.社交恐惧、*Scott, S.,“The Medicalisation of Shyness:From Social Misfits to Social Fitness”,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vol.28,2006,pp.133~153.虐待妇女、*Kurz,D.,“Emergency Department Responses to Battered Women:Resistance to Medicalization”,Social Problems,vol.34,1987,pp.69~81.整容手术、*Kaw,E.,“Medicalization of Racial Features: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Cosmetic Surgery”,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New Series,vol.7,1993,pp.74~89.怀孕、*Barker,K.,“A Ship upon a Stormy Sea: the Medicalization of Pregnancy”,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47,1998,pp.1067~1076.闭经、*Banks,E.,“From Dogs’ Testicles to Mares’ Urine: The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Use of Hormonal Therapy for the Menopause”,Feminist Review,vol.72,2002,pp.2~25.经前综合症、*Zita,J.,“The Premenstrual Syndrome:‘Diseasing’the Female Cycle”,Hypatia,vol.3,1988,pp.77~99.肥胖症、*Hill,J.& Peters,J.,“Enviro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Obesity Epidemic”,Science,vol.280,1998,pp.1371~1374.老龄化与残疾、*Irving K. Zola,“The medicalization of aging and disability”,In 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Greenwich,Conn:JAI,1991,pp.299~315.注射死刑、*Haines,H.,“‘Primum Non Nocere’:Chemical Execution and the Limits of Medical Social Control”,Social Problems,vol.36,1989,pp.442~454.Groner,J.,“Lethal Injection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Health and Human Rights,vol.6,2002,pp.64~79.购物狂、*Lee, S. & Mysyk, A.,“The Medicalization of Compulsive Buying”,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58,2004,pp.1709~1718.色情成瘾,*Voros, F.,“The Invention of Addiction to Pornography”,Sexologies,vol.18,2009,pp.243~246.以及男女两性性高潮障碍*Hartley,H.,& Tiefer,L.,“Taking a Biological Turn:The Push for a‘Female Viagra’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Women’s Sexual Problems”,Women’s Studies Quarterly,vol.31,2003,pp.42~54.Tiefer, L.,“The Medicalization of Impotence: Normalizing Phallocentrism”,Gender and Society,vol.8,1994,pp.363~377.等等诸多原本并非医学问题的生活问题或生理现象,均被建构成为一种医学问题,从而纳入医学化的势力范围。根据国际医学社会学界顶尖学者的研究,美国社会中的某些越轨行为,在特定社会机制的作用下被逐渐转换为临床医学问题,即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社会进程,是一场历时两个世纪有余的渐进式社会转型。*Peter Conrad & Joseph W. Schneider,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From Badness to Sickness,Expande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Preface,p.xi.越轨行为医学化过程作为一种全社会集体性的政治成就,一种显而易见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断扩展精神障碍既有的诊断范畴。因此,越轨行为医学化,实质上已经成为越轨行为精神病学化的代名词。
具备哪些社会条件,特定社会土壤才会变成医学化的温床?美国医学社会学家康拉德(Peter Conrad)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发现儿童多动症:越轨行为的医学化》(Identifying Hyperactive Children: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中率先提出了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条件理论,从而迈出了越轨行为医学化理论系统化发展的第一步。具体而言,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条件理论,适用于具备以下两种一般社会条件的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科学世界观(而非道德世界观或神学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医学职业享有较高声望且成为这种世界观的技术工具。*Peter Conrad,Identifying Hyperactive Children: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Burlington,VT:Ashgate,2006,p.93.康拉德这一理论模型旨在揭示西方发达国家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生成条件,在该模型的演绎下,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条件包括五个前提条件和两个附带条件。五个前提条件是:(1)某种行为必须首先被定义成为越轨行,为并且需要社会中的某些部门/单元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措施。(2)原有的或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失灵,或者遭到弃用。(3)可资运用的医学社会控制手段出现。(4)提出某些模糊的有机体证据作为越轨行为问题的病源学基础。(5)医学界愿意将越轨行为问题纳入自己的业务范围。两个附带条件是:(1)各种现有社会设置(established institutions)的获益程度越高,医学化的可能性越大。(2)有关越轨行为的科学解释社会接受程度越高,医学化的可能性越大。*Peter Conrad,Identifying Hyperactive Children: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Burlington,VT:Ashgate,2006,p.94.
在越轨行为医学化条件理论的基础之上,康拉德和施耐德在二人合作的重量级专著《越轨与医学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越轨行为医学化的顺序模型理论和扎根概化(grounded generalizatons)解释,这是目前为止越轨行为医学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顺序模型理论是用于描述越轨行为医学化实现过程的五阶段分析模型,扎根概化则是对于越轨行为医学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型。所谓顺序模型的五个阶段分别是:行为的越轨定义;越轨行为医学命名的探索性研究;医学界和非医学界利益相关群体对越轨行为医学命名的推广;国家对于新兴越轨行为医学范畴的认可(合法化阶段);越轨行为医学命名的制度化(新兴疾病命名纳入医典以及配套科层化组织的设立)。扎根概化理论由以下五点理论陈述组成:越轨行为的医学化与去医学化是周期性的循环现象;越轨行为的医学化是对越轨行为犯罪化的超越;医学界中只有少部分人介入了越轨行为的医学化;越轨行为的医学命名通常是以“冲动控制障碍”(compulsivity)的名义出现的;医学化和去医学化本质上是政治上的成功而非科学意义上的成就。*Peter Conrad & Joseph W. Schneider,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From Badness to Sickness,Expanded Edi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66~273.
尽管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较好地解释西方社会医学化进程的条件、过程、对象、机制等问题,但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却难以直接用来回答以下问题:以中国为例的非西方社会中,医学化现象是如何发生的?非西方国家医学化的发展程度如何?非西方社会医学化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机制?考虑到越轨行为医学化作为一种跨文化存在这一社会事实,我们有必要开展跨文化比较个案研究。本研究分别选取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个案和美国多动症医学化个案,以此作为中美两国的医学化典型个案,在明确医学化范畴早已渗入非西方工业化社会这一基本事实之余,进而阐明两个典型个案在医学化程度上存在的差别。
一、网络成瘾与多动症:两个典型个案
(一)网络成瘾的前世今生
网络成瘾这一术语滥觞于美国,并且先后在医学界和心理学界粉墨登场。国际上提出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概念的先驱,是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的伊万·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教授。1994年,戈登伯格借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关于药物依赖的判断标准,指出网瘾是一种应对机制的成瘾行为。其症状为:过度使用网络,造成学业、工作、社会、家庭等身心功能的减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初戈登伯格其实是戏谑式地提出网瘾概念的,他本人根本不相信网瘾的存在。*Suler J.,“Internet Addiction Support Group”,1998, http://www.rider.edu/suler/psycyber/supportgp.html.谁曾想,伴随着全社会对于医学需求的成瘾,网瘾概念的建构最终弄假成真。1996年,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杨(Kimberly Young)在第104届美国心理学年会(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上提交了《网络成瘾:一种新型的临床疾病》(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一文。*这篇会议论文的正式发表则是1998年。Kimbley S.,Young,“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vol.1,1998,pp.237~244.文中,她将网瘾定义为一种没有涉及中毒(intoxication)的冲动控制障碍(impulse control disorder),也就是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受到国外学者的启发,中国医学界也开始介入网瘾问题的界定与治疗。国内在推动网络成瘾临床干预和诊断标准研究方面,最为积极的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陶然和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陶然等人最早曾于2005年提出,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是指由于反复使用网络不断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神经系统内分泌紊乱,以精神症状、躯体症状、心理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从而导致社会功能活动受损的一组症候群,并产生耐受性和戒断反应。*陶然等:《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9页。从学术渊源上来看,这一定义借鉴了DSM—Ⅳ关于成瘾性的定义,突出了耐受性(tolerance)和戒断反应(withdrawl)这两个成瘾要素;对于网络成瘾者社会功能受损的强调,则非常接近于精神障碍的诊断模式;所谓的内分泌紊乱假说,似乎并未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支持,否则陶然不会在3年以后推出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时彻底放弃这一假说。2008年9月,陶然等进一步提出,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网络的再度使用产生强烈的欲望,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时出现戒断反应,同时可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陶然等:《网络成瘾的命名、定义及临床诊断标准》,《武警医学》2008年第9期。
2008年11月8日,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订的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北京通过部分军队和地方专家论证并经由媒体向社会颁布。这是我国网络成瘾问题正式迈向医学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从第二天开始,国内舆论界围绕此事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各界对此褒贬不一。笔者对比后发现,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的这份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中的核心内容,正是出自陶然等人2008年于《武警医学》上所刊发的文章。国内精神医学界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网瘾医学化,比如天津市安定医院有医生认为,将网络成瘾归为精神疾病的科学依据不足,容易引起误解和误导。因此“网络成瘾目前不适宜普通精神科医生处理”。*寻知元,杨桂伏:《由网络成瘾列为精神疾病反思医学化倾向》,《医学与哲学》2009年第9期。
时至今日,《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仍未得到国家卫计委的官方认可或驳回;在医学分类典籍中,与网络成瘾障碍相类似的诊断名目,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尽管网络成瘾作为一个医学问题的医学专业合法性远未达成共识,但就社会层面而言,由于《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高调问世,网络成瘾医学化已经成为涂尔干意义上的一种社会事实,它已经成为外在于个体和社会,并反过来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一种社会建构产物。作为全球第一个开展网络成瘾医学化干预的国度,中国在网瘾医学化干预的规模和力度方面,至今仍然雄居“天下第一”的宝座。
(二)多动症在美国的诊断与扩展
我们今日所耳熟能详的多动症,曾经历过一场“命名的革命”。从最早的称谓“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MBD)到“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最终又定名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与之相匹配的是,美国与多动症相关的临床诊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发展历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对所谓的儿童“轻微脑功能失调”进行药物干预,始于1961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微脑功能失调”这一特定儿童临床诊断标签,被儿童“注意力缺陷障碍”所取代;“注意力缺陷障碍”随后又演化成“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1994年,“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这一诊断名目不再仅适用于儿童,存在行为多动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成年人口,也同样可能成为诊断对象。多动症作为一种新兴的诊断类别,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年龄结构边界,实现了对美国人口的“全覆盖”。这无疑是一场医学化节节胜利的宣言。
有医学界人士指出,在现有儿童多动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碍(ADD)方面的文献之中,神经生物学影响因素被过高估计,有关研究却忽视了影响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因此作者认为,ADD及药物治疗的过度普及,是一种“现代性的流行病”。*Ruff,M.,“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nd Stimulant Use:An Epidemic of Modernity”,Clinical Pediatrics,vol.44,2005,pp.557~563.在康拉德看来,多动症的广为流行,恰恰是美国社会全面医学化的典型案例,在综合分析多动症以及其他案例的基础之上,康拉德曾以“医学化”为关键词,来概括当代美国健康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总体性特征,进而提出,从“社会的医学化”视角来理解21世纪美国社会转型。*Peter Conrad,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Treatable Disorder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
还应该强调一点,中国越轨行为医学化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成瘾,不代表美国不存在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正如中国同样存在多动症医学化一样。2013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了基于自愿参与的网瘾临床治疗,疗程为期10天,费用高达1.4万美元。*http://abcnews.go.com/Health/hospital-opens-internet-addiction-treatment-program/story?id=20146923,2014年11月14日检索。中国多动症患者数量也有数百万之多,美国制药巨头强生公司和礼来公司旗下的多动症药物,早已登录中国市场,2005年中国ADHD市场份额就已经达到3亿元的规模。*张旭:《ADHD药物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医药报》2005年4月7日。
二、不同典型案例医学化程度之比较研究
根据不同医学化案例之间医学化程度的深度差别,我们可以将医学化划分为初始医学化、中度医学化、重度医学化三种类型。当代各国社会中重度医学化的典型越轨行为被视为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而医学化的其他越轨行为,在程度上一般都达不到重性精神病的深度;其余所有已经纳入权威医学分类典籍的医学化越轨行为,由于已经获得医学专业领域内的合法性地位,在程度上应属于中度医学化范畴;对于那些医学干预已经初步介入,但未被纳入权威医学分类典籍或有待官方机构最终认定的医学化现象,则属于初始医学化。
衡量不同案例的医学化程度,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即该案例是否收录于权威医学分类典籍(尤其是精神医学界通用的典籍)之中。举例而言,由美国精神病协会修订,且被誉为“精神医学界圣经”(psychiatry’s bible)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th Edition,Arlington: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2013.中国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以及由世界卫生组织颁行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10)等医学分类典籍,在越轨行为医学化过程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在医学典籍的诊断目录之中,能够正式占有一席之地,也就宣告了该医学化个案具有了医学专业意义上的合法性。
就本文选取的典型案例而言,网络成瘾问题和多动症问题,在医学化的程度方面存在着鲜明反差:多动症问题属于中度医学化问题,而网络成瘾问题仍处于初始医学化阶段。初始医学化在外界因素的干预下(如遭到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或大规模抗争性社会运动的抵制),有可能会最终退出医学化的行列,但也同样存在着迈向中度医学化,甚至重度医学化的可能性。
从疾病的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网络成瘾是对一种社会越轨行为的医学界定与命名表达,网络成瘾者首先违反了一种社会公认的行动常模,并因此被一般公众界定为越轨者,随之而来的是,这种越轨行为的医学命名(即网络成瘾障碍)的兴起。网络成瘾初始医学化背后,隐含着施加在网络成瘾者身上的双重社会控制。网络成瘾的非正式医学化标签,最初由青少年网民的家长们加以认定,当家庭层面的种种社会控制努力悉数宣告失败之后,家长们为了遏制孩子的上网行为,开始寻求另一种权威系统,即医学力量的帮助。随着医学力量的正式介入,网络成瘾的社会干预,迈向了初始医学化进程。*韩俊红:《网络成瘾何以医学化——基于家长作用的视角》,《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在网络成瘾医学化干预的实践层面,陶然负责的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科、杨永信负责的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在2006年前后先后开始网络成瘾临床治疗实践。后者所使用的电击疗法,因为该疗法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已于2009年7月初被卫生部叫停,*《卫生部叫停临床电击治疗网瘾技术》,《新京报》2009年7月4日,http://news.sina.com.cn/h/2009-07-14/015018213662.shtml。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杨永信电击治疗事件曾经引起美国《科学》杂志关注,详见该杂志2009年6月26日总第324期,第1631页。此后杨永信改用低频脉冲治疗。根据互联网上可以公开查到的相关资料,上述两家机构对外宣称的治疗人数均超过5 000人。由此不难看出,网络成瘾问题的临床干预,在中国已经得以大规模地开展,网络成瘾医学化在实践层面,已经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事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网络成瘾临床治疗,深谙“先斩后奏”之精髓。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中国网络成瘾医学化方面的实践力度和规模,在当今世界处于“一骑绝尘”的地位。放眼国内外医学界,网络成瘾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科学性问题,在医学界远未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成瘾医学化很难达成医学专业角度的合法性共识。因此,中国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现实图景,是一方面大胆推进临床干预,另一方面却深陷于临床干预专业合法性的危机之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见证这样一个初始医学化典型案例。
与网络成瘾尚未通过医学界合法性认定不同,多动症早已纳入权威医学分类典籍,由于其程度没有重性精神病那么严重,所以处于中度医学化阶段。MBD早在 1968年就已将多动症收入《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二版。1980年,ADD收入《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1987年,ADHD作为ADD的替代诊断名目就已经出现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ⅢR)之中。
康拉德对于美国多动症问题的实地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康拉德仍在追踪美国多动症医学化的进展。21世纪初的情况与30年前相比,虽然有所变化,但是疾病的概念化过程和使用药物进行治疗的社会理念依然如故。有关诊断仍然多见于学龄阶段儿童,中枢神经兴奋剂仍然是现有的主要治疗选择,父母、老师和医生仍然是发现和确认这一疾病的中坚力量。尽管新的医学理论开始探讨多动症的脑科学和基因学基础,但是多动症作为一种医学疾病的生理学基础,仍然没有得到科学证实,该领域的病原学研究目前依旧充满争议。*Peter Conrad,Identifying Hyperactive Children: 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Burlington,VT:Ashgate,2006,p.xi.尽管如此,多动症的中度医学化地位仍然非常稳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医学化的程度与医学化的科学性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医学化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进程,医学化与去医学化(demedicalization)之间存在着可逆性。一个初始医学化终遭弃用的例子是所谓的“漂泊狂”(drapetomania),在19世纪的美洲,该诊断曾流行于从奴隶主家中逃跑的家奴。*Chorover,L.,“Big Brother and Psychotechnology”,Psychology Today,October,1973,pp.43~54.同性恋作为曾经被美国精神病协会确定的一个疾病病种,于1994年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被正式废止,同性恋问题也由此从一个医学问题转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问题。另外一个去医学化的案例是神经衰弱,作为神经症中的典型病种,神经衰弱于1980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Ⅲ)中被删除。后两个去医学化的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发展到中度医学化程度的诊断名目,仍有可能落得被医学典籍“扫地出门”的下场。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医学化的范畴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中度医学化的个案,也不过是医学界和社会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暂时赋予医学界干预越轨行为问题以专业合法性。
三、医学化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后果
客观而言,医学化的社会功能具有两面性特征。医学化的正功能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是针对某些越轨行为提供了基于医学话语的全新社会定义,使得越轨者可以免于社会道义指责。二是为越轨行为当事人开启了“社会免责”机制,患者得益于自己的疾病标签可以暂时/长期免于承担健康状态下所要承担的某些社会功能。三是为越轨行为者提供治疗,即使不能治愈,至少维持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信念,即越轨行为必须得到特定社会机制的控制。医学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维系了越轨行为社会控制链条的可持续性。
与医学化的正功能相比,康拉德认为,医学化的负功能更具有复杂性。首先,当下的医学化发展路径,明显倾向于将任何个体差异都赋予某种病理学解释,这种泛医学化趋势,直接威胁到了对于人类个体生活多样性的接纳与欣赏。其次,社会规范日益受制于医学规范,医学对于“正常”和“不正常”的界定,主导了相关社会规范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三个负功能孕育着更强烈的社会学意涵,即由医学化所导致的复杂社会问题个体化归因的社会倾向。医学化带来的个体化归因,可能会模糊公众的视线,使公众忽视对个体福祉产生影响的复杂而又多元化的社会因素。这种医学化的简化论,掩饰了社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社会革新的必要性,从而将公众连续不断地引入公共问题个体化归因的陷阱。如果说,米尔斯主张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意图将个体困扰转换成为公共议题,那么医学化的实践逻辑,则反其道而行之地将公共问题予以个体化的病理学归因,以便针对个体展开医学干预。第四,医学化对消费者和市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医学化进程与新兴医疗市场不断扩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医学服务与治疗日益商品化,从而出现了医学化与医学服务商业化的融合。*Peter Conrad,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O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Treatable Disorder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8~157.
中国在网络成瘾问题研究的起跑线上,虽然相对滞后于国外同行,但在临床干预的力度、治疗模式探索,以及现有治疗规模方面,则比国外同行走得更远。面对处于失范状态下的网络成瘾干预行业格局,我国卫生部在2009年就曾经着手研究网络成瘾临床应对规范问题。根据媒体报道,卫生部已经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进行网络成瘾试点治疗并总结经验,并将尽快出台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网瘾标准年内出台 一周上网超40小时即认为成瘾》,参见http://www.szhe.com/zonghe/toutiao/200920573.html。然而时至今日,国家卫计委仍未给出有关网络成瘾问题“盖棺定论”式的结论。考虑到网络成瘾医学化既没有得到官方机构的最终确认,也没有在收入医学典籍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网络成瘾问题仍徘徊于初始医学化阶段。
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科和山东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作为业内知名度最高的两家医学机构,其治疗对象均为青少年网瘾患者,背后的医学化运营模式均以“强制治疗”为主要特征,实难逃脱医学伦理层面的质疑。尽管不同成瘾行为(如毒瘾、赌瘾和性瘾)的成瘾机理不尽相同,但国际国内相关经验一致表明,成瘾行为干预的实际效果,普遍维持在低水平。外界对网瘾治疗的疗效和复发率、被动医学化所衍生的社会后果等问题,仍然所知甚少。就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而言,我们面临的仍旧是处于非均衡发展态势下的越轨行为医学化个案,医学话语过于强势,其他社会主体的声音均被边缘化。
药物治疗是多动症临床干预的不二之选,但有关治疗的疗效及其副作用问题,同样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仅就美国而言,服药人群就多达数百万。长期服药的多动症少年儿童,轻者面临睡眠障碍、食欲下降、生长抑制等副作用影响,*钟新:《过半的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患儿使用药物治疗》,《中国医药报》2005年9月15日。甚至有人会遭遇心肌梗死、中风、猝死等严重的健康风险。*佚名:《美国发布通告——利他林可能致人猝死》,《大众卫生报》2007年4月3日。事实上,药物治疗无法根治多动症,只能起到缓解或控制有关症状的作用,这意味着患者需要终身用药。对于国际制药巨头而言,这是一场饕餮盛宴,而药物治疗的社会风险,却悉数转嫁到患者身上。这正是多动症医学化背后隐藏的严峻现实。
美国社会学家阿兰·霍维茨(Allan Horwitz)认为,都市文化的膨胀和扩张、社会分化以及精神病学对于20世纪话语结构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在全社会层面上更多更广范围的精神病标签的出现。*Allan Horwitz,The Social Control of Mental Illnes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2,p.82.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一旦形成医学化的路径依赖,其本质就是,将越轨行为精神病化。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医学化进程,似乎在宣判现代文明背景下,人类境遇日趋精神病学化。尽管每一个医学化个案背后的社会博弈过程不尽相同,但网络成瘾和多动症,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殊途同归地走上医学化道路,这至少表明医学化进程拥有跨文化建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化视角的适用性已经超越工业化国家的边界,同样适用于理解和分析出现在非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事实。无国界医学化是医学意识形态的全面告捷,面对医学化领地的肆意扩张,我们在批判医学化进程之余,更要从理论上强调并重视越轨行为非医学化社会干预的可能性。*韩俊红:《被动医学化及其超越:青少年网瘾医学化问题再研究》,《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我国一位资深医学哲学家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资讯社会,人们生活在疾病恐惧中,疲于求医,一种‘疾病恐惧症’笼罩在人们的心中,生命和生活都被医学化”。*杜治政:《困惑与忧思:医学的边界在何处》,《医学与哲学》2014年第8期。面对医学化的汹涌浪潮,如何抵制医学化对社会领域的侵袭与蚕食,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巨大挑战。
(责任编辑 陈斌)
作者简介:韩俊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北京,100081)。
基金项目:①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海外中国人与中国企业跨文化适应研究”阶段性成果(XTCX150605);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团队项目“海外中国人与中国企业文化适应研究”阶段性成果(2015MDTD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