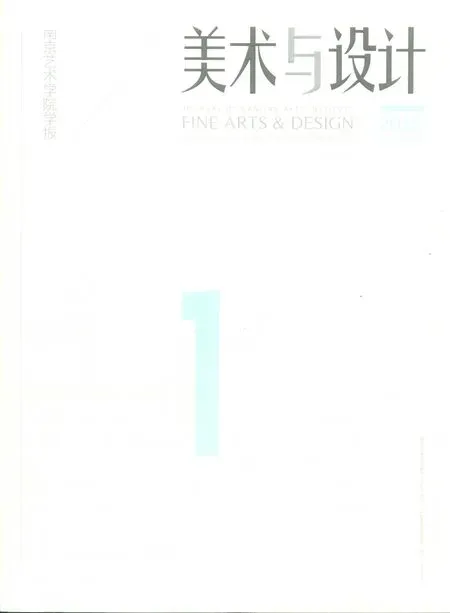篆刻与中国画关系的当代思辨与启示①
邝以明(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广东 广州 510210)
篆刻与中国画关系的当代思辨与启示①
邝以明(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广东 广州 510210)
[ 摘 要 ]在走向纯粹艺术形式的当代篆刻发展格局中,同属于中国民族意识形态的中国画与篆刻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在相互的影响和作用下,产生了内外的发酵。概而论之,一则篆刻与中国画在技法、品评等层面上的融通;二则(金石)篆刻积淀对当代中国画发展传统理念与民族意志的强化与认同。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画品评叙述语系及其发展的框架为参照,对篆刻与中国画表现技法与审美品格等方面的关系进行微观地考察,并进一步探讨篆刻视域对延续至今的中国画改革与发展的传统立场的支持。
[ 关键词 ]篆刻视域;品评参照;中国画改革;民族意志
导 言
无论是中国画一门在清季即已形成画坛只事临摹、陈陈相因而使艺风萎靡不振的本身症结以及“西风东渐”的外来势力冲突,还是书法一门在近代西式书写工具对中国传统书写工具的递更和文字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语系等书写载体、书写内容的动荡,都促使作为中国民族意识形态体现的书画艺术产生深刻地改革,其具体体现为形式语言、技巧乃至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全面调整和转变。出现了诚如“中西之争”、复古与创新等命题的思辨以及延至今日的“现代主义”、“实验水墨”、“书法主义”、“流行书风”、“新书法”、“实验水墨”、“学院派书法”等新理念和实践。然而,中国社会百年来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千百年来书画赖以生存的精神依附:如古典人文哲学等传统根基被近乎彻底地抽离,成为直接导致书画艺术变革最为根本性的原因。艺术家一方面必须主动选择或者被选择的去面对古典话语系统、传统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向现代语境的转型;另一方面又必须在20世纪救国存亡的社会背景和民族意识认同,以及21世纪至今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与地域文化独特性突显之间的矛盾互动中,承续和坚守书画的传统技法、程式和审美规范,从而达到民族艺术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色。因此,民族意识、时代特征被进一步强化,民族性和世界性、传统和现代等成为近百年来书画艺术发展始终绕不开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明清以降,文人参与印章的刻制,篆刻一门逐渐兴盛并趋纯粹化的艺术倾向。然而,其时篆刻的兴盛并不能动摇其作为同是艺术书画的附属地位。从篆刻的钤盖作为元明清以降文人画重要组成部分和完成书画作品的规定动作,到篆刻印色的红与书画的黑白彩的相映成趣,乃至钤盖在书画作品中的篆刻审美性格也为配合书画作品风格的统一而制作。这种作为书画艺术的附属品格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诚如当下大量的中国美术史出版物以艺术种类分而述之,却或将篆刻列于书法艺术之下,或列于雕塑艺术之中,更有甚者——洋洋数十万字的中国美术史竟然没有关于篆刻只字半言的描述;另外,官方的艺术组织中国书法家协会分设篆刻委员会,篆刻同样却也仅仅只是作为书法的附属而并非并列的同等地位,凡此种种莫不如是。基于此,走向现代的篆刻必须为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的、与书画三足鼎立的视觉艺术的确立与认同作出巨大的努力,又必须面对上述书画艺术中西冲突、社会结构变革等种种困境与遭遇,实行技法审美、艺术观念、理论研究、学校教育等方面的调整。篆刻有着“篆”与“刻”的双重属性,与书法的关系自不赘言。而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出“援书入画”的观念以来(尤其是宋元文人画滥觞之后),“以书入画”的研究也代不乏其人。以画家为主体的书法创作的思辨亦随之兴起并在现代的书法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为学界所忽视的是:既然书法、篆刻和中国画同为中国特有的视觉艺术并关系密切,何以篆刻与绘画关系的当代思辨却一直阙如?历来篆刻与绘画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与关联?这些关联在
一、品评参照·技法异通·当代启示
宋米芾《书史》称:“画可摹,书可临,惟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米氏在这里讲的是印章(篆刻)在鉴藏中的作用,并以此叙述书画印在创作表现方面的一些区别。不仅如此,书画印属于不同的艺术种类,自然在工具、载体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立的属性。书法是以抽象的文字为载体表达心象的一种表意艺术形式;中国画是表现外在世界和心灵图像的一种造型艺术形式,篆刻则以文字、图形为内容,兼具书画的一定属性并具有自身的个性品格。所以,篆刻与书画虽然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却也关系密切。
就篆刻与中国画而言:不同于书法书写轨迹的不可逆性,篆刻在用刀刻制作品时的可逆性(如复刀、补刀等)与中国画用笔墨塑造形象时的可逆性(如复笔和层层积染等)存在程式的共通;“计白当黑”审美法则以及印章(篆刻作品)之“小”体现空间之“大”的哲学审美意味又与中国山水画“方寸之间,体百里之迥”存在着两者空间处理的类比。“画有六法,印亦有六法”(近代潘天寿语)。尤须注意的是: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六法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画品评的金科玉律,这种由技(技法)而道(气韵)的艺术阐释,以及大量如“六法”、“三品”、“三病”、“六要”、“六长”、“十二忌”等归纳、提炼出来要诀式的中国画叙述语系亦随之延续,并对篆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正是在借鉴中国画叙述语系的篆刻研究中,展开两者在技法异通方面的讨论。
1.入印内容
相对于明清时期文人才参与篆刻的刻制实践,并逐步形成众多的技法要诀和规范,中国画技法实践和理论的提炼自然要早得多,积累也更为丰富。总体而言,中国画技法无非两个要素:笔墨和程式。笔墨包括笔法、墨法和用色法(另外,还包括当代所强调的、古已有之的、非笔法系统的表现技法,如肌理制作等);程式则包括造型结构、山水皴法、工笔渲染、章法构图和款识等等。皴法、渲染法、用色法等是中国画特有的塑造画面形象的手段。而笔法、墨法、章法、款识,甚至非笔法系统手段、造型结构等方面,却给予篆刻技法叙述语系提供了很大的借鉴空间和支持。基于这种技法分类的参照,明甘旸《印章集说》即较早地提出了篆法、笔法、刀法、章法四个印章(篆刻)技法要素,并成为后学臬范。其“篆法”云:“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正,虽刻龙镌凤,无为贵矣……如各朝之印,当宗各朝之体,不可溷杂其文,以更改其篆……”[1]80作为进入印章的内容,除以篆书为主的书写字体外(还包括楷、行、草、隶),还包括满文等等各种文体,以及图形印、鸟虫篆等特殊形式。图形印、鸟虫篆这种特殊形式与表现事物形象的中国画有着非常相似的外在表现,在篆刻与中国画关系中颇为重要。尤其在篆刻发展到以艺术为最终评价标准的当代更是如此。所以,笔者称之为入印内容,而并非“篆法”。就入印文字而言:既然称之为入印,必定会在进入篆刻印面时,要做适合方寸印面的调整变化,使之在印面中妥帖自然又具有美感。这种被大部分篆刻研究学者称之为“印化”的过程中有时会破坏篆法的纯洁性,甚至有悖于千百年来的篆法“六书”规范。基于文字学的立场,这种破坏篆法纯洁性的举措自然不足取。但是,作为篆刻艺术美的立场,却未必尽失之。当然,这个有悖于——是在掌握了深厚的篆法基础上主动地、以艺术上的新意为依归的有意识行为,而非胡编乱造。以西夏文入印的近人邓尔雅和以甲骨文入印的简经纶则是在这种活用篆法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篆刻作品中对开拓未见于古人的书体入印时,就是以艺术效果为主导有意识地去应用、“印化”入印的文字,从而达到具有现代艺术中几何形式美感的效果和新颖感。
图形印是篆刻的特殊种类,自春秋战国开始出现,到秦汉时已具相当的规模。图形印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人物、车马、山水、花草和动物无所不包,社会生活中的骑射、歌舞、饮宴、杂技、神话等等都可成为其表现的内容。然而,秦汉以降,问津者寡,有则徒求形似,境界不高。晚清到民国期间的黄士陵、齐白石等人偶尔为之,虽皆出手不凡,但因所作甚少而难成体系。直到近人来楚生、丁衍庸出现,才遥接秦汉法乳。来楚生诗书画印四绝,其中国画清新朴茂,格调雅逸;丁衍庸则擅长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和中国画,对造型简练,带有几何图像类作品也尤为关注,有着“东方马蒂斯”的称誉。创作图形印既要懂得文字造型,更需懂得图画造型。这种图画造型既跟中国画造型有许多外在的相似(也与汉画像砖、唐宋元佛像石刻等相似),但却不尽相同:中国画是对事物造型进行提炼和程式化,图形印则是对事物造型抽象、概括与简略化,是接近于文字的图画造型。也正是这种造型手段,使图形与文字结合的篆刻形式中,文字与图形相得益彰,统一自然。虽然如此,具有重大拓展和创新意义的来氏创作的、富有时代感的工农兵形象图形印,无疑是来自中国画特有的造型敏感;而丁氏近西方“野兽派”和中国明代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则直接影响其图形印创作形成浑穆洗练、朦胧稚拙和漫画式诙谐的艺术效果。另外,传世大量的画像砖石、石刻艺术等为中国画与篆刻的图形印搭建了艺术桥梁,并在当代大美术、视觉艺术的两者中切入新的创作空间营造一个极其重要的契机。总而言之,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如何应对层出不穷如英文、印刷字体、交通标志等标识系统的新事物题材,寻找其合适的篆刻表达,通过对中国画造型与篆刻图形印的某种关联的思考,或许就能从中找到合适的参照与借鉴吧!
2.笔法·着墨·刀法·做印法·章法
近人邓尔雅《治印示儿辈》云:“画有笔墨色,印有笔墨刀。”
明甘旸《印章集说》“笔法”云:“篆故有体,而丰神流动、庄重典雅,俱在笔法。然有轻有重,有屈有伸,……此数者各中其宜,始得其法。”[1]80稍晚的徐上达《印法参同》亦再次指出:“笔法者,非落墨之谓也,乃谓一点一画,各有当然。而运动自我,又不可执,或屈而伸……笔法既得,刀法即在其中……(笔法)自然、动静、巧拙、奇正、丰约、肥瘦、顺逆。”[2]可见,甘、徐所述的篆法是基于文字的立场,即入印文字的正误和风格统一等方面的法则。笔法则基于审美的立场,即入印文字美感表现的技法要求,并强调这种要求对刀法的重要性。近人潘天寿《治印谈丛》一书从“篆刻源流、别派、名称、选材、分类、体制、参谱、明篆、布置、着墨、运刀、具款、濡朱、工具”等方面对印学源流及篆刻技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中“篆刻源流”、“别派”等为篆刻史和知识性的介绍,“明篆”、“布置”、“着墨”、“运刀”、“具款”则属于篆刻具体操作的技法阐释。然而,潘氏全书并无上述甘、徐“笔法”之谓,仅在其“运刀”一节说道:“治印执刀如写字之执笔,故只称铁笔,故刀法即笔法也。”[3]131由此引出的思辨是:入印的篆法无疑是篆刻特有的要素,而篆刻的“笔法”与中国画的“笔法”叙述则异中存同。篆刻笔法表现的载体是文字线条(或者图形印接近于文字的抽象图画造型),而中国画笔法表现载体则是画面形象造型,它通过一定的笔法具体表现为或依附于、或结合于画面造型(或者具有独立审美和抽象意义)的点、线、面。这些点、线、面的笔法轨迹又体现了一定的美感、品格,如浑厚、古拙、清刚、秾丽等等——又与篆刻笔法有着一致的审美认同。因此,作为艺术的篆刻,不仅有着如潘氏所列的“明篆”:篆体正误、风格统一等方面要求,还包括对入印内容在美感方面的取向。潘氏由此在《治印谈丛》设“着墨”一节并谓:“作印须有笔有墨,有墨者谓其具有篆笔之致也。”[3]128这里的“篆笔之致”其涵盖的内容既与甘、徐二人所述的“笔法”基本相近,又有许多内涵的延伸。因以中国画叙述语系借鉴而来的“墨”的概念去表达入印内容的美学立场。一方面可看作潘氏诗书画印“四全”的身份认同与他在这些方面共通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画技法启示,赋予入印内容在美学方面更多的韵致与发展。如篆刻线条之间的焊接点、笔画的粘边,与中国画涨墨线条效果的类似;通过篆刻线条的粗细、空间等方面的排叠,与中国画焦、浓、重、淡、清等墨阶层次的某种关联等等。这无疑是通过中国画技法体悟与参照,为开拓篆刻技法提供更丰富的创作形式语言。
在篆刻创作中,作为文字学要求(篆法正误等)和作为美学要求(入印内容的美感)的目标达到后,作品的完成还必须通过刀法来实现,即使入刀前的印稿再美也必须由刀法表现其最终效果,这个效果自然与印稿有或多或少的区别。明秦爨公《印指》:“章法、字法虽具,而丰神流动、庄重古雅俱在刀法。要使肥中有骨而无臃肿之失,瘦中有筋而无枯槁之弊。又如梓匠斫轮莫可端倪,所谓无斧斫痕乃为贵,柔而不柔,劲而不劲,苍然有骨,浑融古朴,圣不可知之谓也。”[4]又有潘氏《谈丛》之“刀法”:“刀之于石犹笔之于纸也,善作画者必讲求运笔,善治印者必讲求运刀。徐孝先云: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神寓于内而溢于外,难以力取。古人论诗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谓此也。”[3]131正如中国画“骨法用笔”是气韵以外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样:将篆刻刀法直接类比为中国画的笔法,可见其重要性。因此,潘天寿先生又说:“画有六法,印亦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刀法古劲,三曰布置停匀,四曰篆法大雅,五曰笔与刀合,六曰不流俗套。此六者气韵生动最难,气韵生动以下五法皆人所能为也。”[3]143刀法是第二位的,“笔与刀合”——虽然“笔”未必作为“刀”依附的结合,但至少“刀”、“笔”是并列甚至是强调“刀”的本位。中国画笔法轨迹(点、线、面)从唐宋时依附于形体而存在,到元代两者的结合,进而到明清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最后进入当代对中国画笔法轨迹的抽象审美品格有着越来越重视的体现,从而产生“抽象水墨”、“现代水墨”等形式。或许受到这种来自中国画的启示,在当代篆刻艺术发展格局中,针对于重篆轻刻、重书轻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强调刀法轨迹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并展开了基于刀法立场的创作探索。诚如1996年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96全国新概念篆刻邀请展”中将篆字解构,以不可辨识的、纯粹的刀法轨迹作为审美落脚点的篆刻创作实验等皆应作如是观。
另外,唐张彦远《论吹云泼墨体》中论及以口吹粉色的形式表现自然之云的“吹云泼墨体”[5]。宋邓椿《画继》卷九《论远》亦有“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问,干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6]的“影壁”山水。这些“不见笔踪”(张彦远语)的表现手法,古已有之,在当代的中国画的技法发展中则更为丰富和多样。诚如喷水、撒盐、揉纸、熨贴、肌理等非笔法去表现物象等等。无独有偶,清汪维堂《摹印秘论》之《雕虫清话》中有:“摹印有八法:制印、画格、落墨、用刀、蘸墨、击边、润石、落款。以为八法,不可不知。”[7]明沈野《印谈》:“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学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8]清张在辛在《篆印心法》中提出,为达到篆刻的最终展现效果,而使用垫印纸的厚薄、印色之浓淡因素来钤印的方法,以及上述“击边润石”、“掷地剥落”等自然并非刀笔之法而属于制作的技法。清吴昌硕和近人邓散木、来楚生等人治印除了运用常见冲、切刀法外,还经常视印章艺术效果使用敲、击、磨、削等制作手段来表现,以求达到补救章法或刀法上的不足。如果运用得当,可将较差的印挽救为好印,也可使好印锦上添花。近年来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篆刻技法百讲丛书,在章法、篆法、刀法以外,又设“做印法”;今人马士达也在《篆刻的制作与效果》中指出:“所谓篆刻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即是一个充分强调艺术表现手法的过程,亦即为造成某种艺术效果而充分调动和运用种种可能的表现手法的过程。”[9]这里强调“种种可能”的表现手法,可谓不择手段,一切以艺术视觉效果为依归。可见,在当代的篆刻创作中越来越强调“做印法”的使用,这又与中国画特殊制作方法相与呼应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有意思的是:清邓石如提出:“密处不使通风,疏处可令走马”本属于来自篆刻章法体悟的疏密观念,却被近现代中国画家借鉴(或曰应用)到中国画章法要领之中。可见,两者在叙述语系中亦有着作用互换和相与影响的一面。当然,仍以中国画叙述语系为再者主要的方式。如篆刻的章法:“书画不能无章法,治印亦然。治印如作画,画之佳者疏密浓淡恰臻其妙,治印至精能处亦当如此。”[3]124篆刻的边款:“印之具款,犹书画之题也。古今名画之题款,每与画相得益彰,印亦何独不然……作画难长题,因长题须文辞书法有深沉之功力者,方能完美,足以相俪成观,否则一露破绽全画减色,印之具款亦然。边款之长短,须视地位与空白之多寡及画材之配合,随便落笔均臻妙境。”[3]134-135在此不一一举例。
3.创作心态·品评标准。
清袁三俊《篆刻十三略》之“写意”称:“写意若画家作画,皴法、烘法、勾染法,体数甚多,要皆随意而施,不以刻划为工。图章亦然,苟作意为之,恐增匠气。”[10]可见,无论是何种技法,应用起来务求灵活多变,正如中国画表现的“随意而施”。也直接道出两者的相通之处并强调以“意”为主导的创作心态。在这种创作心态下,必须心地安闲、成竹于胸,然后挥笔(刀)以“意”为之。而这种“意”出于创作者的天性,清秀或是浑厚,各如其人,若俗而不韵,虽勾金勒银、雕龙镂凤亦不足以观。
“沈启南论画云: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治印亦然。”(潘天寿语)[3]144艺术水平的高低与人品优劣有联系但未必是必然的联系,在此,笔者无意对此论作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但是,“画有品,印亦有品”(明杨士修语)。既然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参与印章的刻制,其中对完成的篆刻作品势必有着一套艺术欣赏评价体系,其定义的品类及其发展与中国画的画格及其发展则如同一辙。
关于中国画的画品,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在张怀瓘《画断》中神、妙、能三品以外拈出逸品,这种“不拘常法”的逸品与其他画格并非如神、妙、能那样有着高低、偏正、优劣之分。但是这种朦胧混沌的状况已显示出有着无穷生命力的新画风——文人画的滥觞已经开始。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阐释了“四品”的含义。即“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逸格”;“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的“神格”;“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自心拊手,曲尽玄微”的“妙格”;以及“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的“能格”。其中,黄氏直接将“逸格”列于各格之首。进而宋苏轼首次提出:“士人画”和宋邓椿《画继》明确地提出:“画止一法,传神而已……画者,文之极也”,并宣布“逸品”为高、特立轩冕、岩穴二门以示气韵之非师等等,可证文人画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的完全奠定。明甘旸在《印章集说》之《印品》:“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然轻重有法中之法,已见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婉转得情趣,稀密无拘束,增减合六文,挪让有依顾,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长短大小,中规矩方圆之制,繁简去存,无懒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有此三者,可追秦汉矣。”[1]84稍晚的程远《印旨》沿用此说,并拈出“气韵高举,如碧虚天仙游下界者”的“逸品”一格。进而到清陈鍊《印说》则直接提出:“笔墨间另有一种别致,是为逸品。此则存乎其人,非功力所能致也。故昔人以逸品置于神品之上。”[11]从唐初至宋的画格微妙变化为日益奠定中国文人画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之于篆刻,类似由明至清的微妙时序流变,却同样可以引起相应的思辨:随着明季文人篆刻的滥觞,对篆刻这种秉乎天授,以气韵高举为特征的个性品格追求奉为最高,而不是“体备诸法,错综变化”的“神品”(明程远语)——技法并非篆刻作为独立的艺术最为重要的因素,艺术个性才是最终的依归。尤其是篆刻在当代高速发展的社会变化以及篆刻日益强调的艺术纯粹化之中更是如此,紧张的生活节奏使人们的审美趣味倾向简洁、明快,倾向于一目了然的对比美,以及单纯的视觉冲击,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篆刻视域对近现代中国画传统理念与民族意志的认同与强化
社会变革、人生轨迹势必影响艺术家对事物的审美视角、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其创作的风格和艺术的理念。
1.金石入画
近人黄宾虹无疑是现当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山水画大师之一,他将金石篆刻宁朴厚雄浑的艺术精神融入到中国画艺术的笔墨当中,又将绘画艺术构图的精神核心反馈到篆刻的章法中去,为世所称著。黄氏晚年曾一而再地提出:“道咸金石学发兴,画学鼎盛”之说,并称:“清二百年中,惟金石家画尚存古意,其余不足论也。”
清季金石学一门经过长久积淀和发展,至道咸时期趋于鼎盛。而与之相关的训诂考证、文字小学、文献学、书画等亦随之发展。道咸以降,基于金石对书画发展的影响,许多书画研究也将古代金石作为重要的资源进行探讨,“金石书画”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而以“金石入画”也成为其时中国画学发展最重要的技法和审美关联,中国画家通过这方面的孜孜以求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黄氏所述以金石入画的“卓卓标著”百余人群体中,其绘画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古意”,这种“古意”既是其时画学鼎盛最为关键之处,也是来自于金石所产生称之为“真内美”的艺术审美选择。黄氏所称的“真内美”的审美精神,事实上就是三代金石文字、秦汉篆隶、北碑等书法篆刻艺术审美意韵。这三者都倾向质朴、粗拙、大方的审美品格,并有着混沌朦胧、回归原始的艺术张力。无论是以金石博物如汉砖、钟鼎之类的金石题材作画或者以金石书法的线条绘画,还是包括如篆刻所悟来的“知白守黑”、空间开合、结构取势等全方位的技艺参考,都使书画同源这一特征被进一步强化。金石学在艺术上的延伸,也使“诗书画印”的全面追求也成为文人画的主要诉求。然而,中国画以“气韵生动”为审美的最高准则,作品的气息、韵味等才是评价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在艺术家篆刻创作、博物考订、文字训诂等常态中,形成比金石书法笔法融入中国画技法更为重要的,是从金石、博物之属浸淫中所带来的古拙、浑朴的“真内美”的精神意识形态。一方面,使诚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傳抱石、黄宾虹、潘天寿等艺术家在“四全”、“三绝”的全局统摄中得到很好的诠释;另一方面,在这种以中国本身内在的精神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艺术审美,阐发了世人对中国画民族特性的新思考:通过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总结和实践,从道咸金石发兴引起书画鼎盛的启示中,探索在强调民族意志和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可持续再发展可能的、适应于新时代的美术理论体系和新的实践基础和样式。在这样的艺术理念下,金石入画所带来的艺术体系的方法论和价值观,都为当代的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2.篆刻视域·传统理念·民族意志
篆刻包含于金石之中,但与金石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
在应对来自中国画本身的萎靡不振、外来势力的冲击踫撞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发展,百年迄今的中国画变革思潮中;在21世纪至今全球一体化大趋势与地域文化独特性突显之间的矛盾互动中,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等成为近百年来书画艺术发展始终绕不开的、最为重要的课题。笔者无意展开过多的讨论与思辨。但是基于篆刻的视域去考察,却引发了有趣的思考:在以全盘西化或结合中西等为阵营的中国画家群体之中,绘画而外,兼善篆刻或者篆刻关注颇多的人并未多见;而以坚守传统、复古维新为立场的中国画家群体绘画而外,兼善篆刻,甚至以篆刻知名,余事才从事绘画的人却为数不少。篆刻虽小道,然其对文字训诂之学等基础的要求却很高,从事篆刻的学习,一方面来自于如家富收藏的长期熏陶或从事文史考订、博物院文物鉴定,考古等常常与古、与传统打交道的事业在篆刻的兴趣培养与篆刻的学养生成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些方面甚至金石博物、鉴藏等下一番工夫。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艺术家形成了一种很深的尚古情怀,既多了一份诗书画印“四全”的全局统摄,又在继承传统的理法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恪守于斯。由此产生在对中国画的风格认知上、在中国画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上,时刻以中国本身的内在精神为坚定的立场。从黄牧甫、邓尔雅、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等莫不如是。
然而,这种对传统理念与民族意志的认同与强化,并不等同于抱残守缺。随着中国画家对传统的长期浸淫,尚古情怀越深,传统积学也越丰厚,艺术创作自然强调规矩古法、渊源有自,也势必力学以光大之。死学者抱残守缺、不思求变,既不愿放弃半点从古人处学来的一笔一画、形壳,又忽略自己对艺术的创作激情,作品自然味同嚼蜡。因此,“复古维新”始终是传统立场的近现代至今中国画家的夙愿——复古是艺术的手段和方法,维新才是艺术最终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研习中国画和篆刻以外,曾致力西洋画法者亦不乏其人。但是无论古今,还是借鉴外来,始终强调“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两端深入”——即从中国画传统本身内在去应对外来势力的踫撞。潘天寿、傅抱石、邓尔雅等人或曾在东京研究西方艺术和日本艺术,或曾对日本艺术有过深入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位非常中国化的艺术家,就连有着“东方马蒂斯”之称的丁衍庸,在其创作中国画时,仍然是一派八大山人传统面目,凡此种种以篆刻家身份介入中国画创作与理念研究者、中国画外兼善篆刻者均本于传统出新的角度,这或许是我们当下篆刻与中国画关系有待更深一步探讨的课题吧!
余 论
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艺术传播无疑是当代艺术研究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三大主题,并且这三者又存在着相互作用与影响。面对社会急剧的发展,除艺术创作本身以外,包括了展览、群体组织、艺术教育、信息媒介等方面的艺术传播与中国画(或者美术)同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联,基于一个视觉艺术形式的立场和为推动篆刻艺术的发展目标,这方面的内容自然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当代的展厅为方寸篆刻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纯粹以印谱为主要的展示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强化了篆刻作品的视觉效果而弱化其可读性,从而影响篆刻创作必须以简明、明快和对比强烈为现代追求;另一方面,篆刻艺术的展示的形式也由单一印谱形式,转变成印谱、印蜕(包括原钤和放大的)、印屏、印章实物、甚至多媒体动态播放等丰富多样的展示。这种从案上到壁上、从单数到复数、从方寸到放大、从单一到多样、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的展现方式转变成为当代篆刻传播一个重要的特征。除展览以外,从传统的印谱到现代的报刊、杂志、电脑、手机等信息媒介又为篆刻艺术在当代的传播提供更多的方式。而借鉴篆刻艺术形式的、具有现代标识意义的北京奥运会标志以及现代建筑仿照篆刻印章形式的装饰等文化景观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然而,篆刻作为独立的视觉艺术,其官方群体组织,却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附属机构;而篆刻教育除面对传统师徒授受式教育向学院教育转变的问题,又遭遇了依附于书法一门的尴尬境地,这其中的完善与发展,正是时代给我们的责任与任务,并寄托的殷切希望!
参考文献:
[1]甘旸.印章集说[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2]徐上达.印法参同[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124—125.
[3]潘天寿.治印谈丛[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4]秦爨公.印指[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100.
[5]刘万鸣.中国画论[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121.
[6]图画见闻志·画继[M]. 米水田,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414.
[7]汪维堂.摹印秘论[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155.
[8]沈野.印谈[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64.
[9]赵明.做印技法百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105.
[10]袁三俊.篆刻十三略[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64-65.
[11]陈炼.印说[G]//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295.
(责任编辑:梁 田)
[ 中图分类号 ]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1-0091-06
收稿日期:2015-12-04
作者简介:邝以明(1980- ),男,广东河源人,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研究部主任,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岭南书画篆刻文化的研究。
基金项目:①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12BF041)以及2014年高校省级(人文社科)重大科研项目、特色创新项目(编号:2014WZDXM031、2014WTSCX132)阶段性成果。同处于应对外来冲击和社会剧变的近现代直至当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互动?如果说当代对篆刻非刀法范畴的“做印法”与中国画非笔法范畴的肌理制作等探讨与实践;以及李可染“屋漏痕”式的中国画线条启发于其师齐白石“单刀法”的篆刻线条是属于篆刻与中国画技艺层面的融通;而潘天寿《治印谈丛》中《布置》、《着墨》、《具款》、《余论》中提出的“六法”、“六要”、“六长”、“三病”等则是篆刻对中国画叙述语系和品评修辞的参照;那么,在近现代以京津、上海、广东为主要阵地,“国画复活运动”等为推动中国画变革、改良中国画等延续至今的艺术思潮中,大量中国画与篆刻兼善的艺术家在其文字小学、金石博物、鉴藏方面长期熏陶的积学,又为上述中国画变革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并发生重要的作用,这无疑为我们扩宽中国画和篆刻的研究视域以及二者关系在当下的意义与启示无疑都是非常重大的。